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与中法文化交流
未知 2009-01-05
[摘要]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物质及精神成果。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或国家,首先必须了解其文化,文化交流也因此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他们拉开了中法交往的序幕,成为了当时两国间交流的主要媒介和桥梁,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果,也使法国成为了欧洲的汉学中心。
[关键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 文化 文化交流
一、文化概述
“文化”一词含义广泛,人们对其下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权威的汉语词典《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故广义上的文化概念,大体可以包括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两方面,它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物质及精神成果。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成果,从而也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我们知道要了解一个民族就必须了解它的文化,否则对这个民族的了解就是肤浅的,这反映了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以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同样地,要了解中国和法国,就要从了解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入手。
二、中法文化概述
中法两国距离遥远,一个地处东亚,一个地处西欧。中国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文化的影响,法国受基督教影响。当我们思考和研究中国和法国的历史和现状时,我们会发现古代和近现代史上的中国和法国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两国有很多共同语言,首先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心,都有着古老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中世纪以来,中国为东方文明之摇篮,法国则为西方文化之中心。两国人民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双方都很注重维护它自己的文化。两国都较早实现了统一,并且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传统,两国都非常注重独立。目前,中法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们都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路线。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其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延伸至广阔的地区。直至17世纪,即在西方干涉和入侵之前,中国在教育、文化、知识和科技方面一直独树一帜,呈上升之势。
法国的人口为6000万,有着2000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上具有罗马文化色彩,从10世纪起,法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法国也是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底蕴深厚,法国人的艺术欣赏能力超过了一般的民族。
中法两国都是世界上重要的文化大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和进步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两国人民早就有交往。而历史也证明了文明的进步存在于东西方不断的交流活动中。“中法关系可上溯至13世纪中叶,但双方完全意义上的接触则始自16世纪以后传教士来华,并由此引发了中国热和汉学的创建。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由法国传教士进行的汉学研究初见端倪。”
三、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活动
13世纪中叶的1248年和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15-1270)两次派多名我会修士到蒙古(当时的中国)。1477年,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后传到了法国。16世纪后期,欧洲传教士来华人数逐渐增多,至17、18世纪,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已达数百人。1610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原名尼古拉•特里戈)来华传教。金尼阁和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欧洲传教士利用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艺博得了中国朝廷的欢心。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 法国传教士首先进行了汉学研究,这也拉开了中西两大文化交流、碰撞以及相互汲取营养的序幕。
17世纪下半叶,中国是康熙(1654—1722,1661-1722在位)皇帝统治时期,而遥远的欧洲大陆西部的法国正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这两位伟大的君主统治时期也正是历史上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时期。路易十四(1638-1715,1643-1715在位)掌权初期,法中两国之间的交流极其有限,互不了解。在其后的数十年内,两国间的交流逐渐加强。当时两国间交流的主要媒介和桥梁是耶稣会传教士。当时的中法文化交流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果!
为了了解遥远的东方帝国,路易十四于1685年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向中国增派耶稣会传教士。这批传教士以洪若翰神甫(Jean de Fontaney,1643-1710)为首于1685年3月3日从法国的布勒斯特港出发,于1687年7月23日抵达浙江宁波,最终五人(洪若翰、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1655—1728)、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张诚(Jean-Fran ois Gerbillon, 1654-1707)、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于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叩拜康熙皇帝。这些耶稣会士均为饱学之士,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他们中的张诚和白晋被留在清朝宫廷之中,担任康熙的科学顾问,其他几位传教士则被允许到其他地方传教。这是第一个到达中国的法国代表团,由此开启了中法两国官方早期交流之先河。他们既传授西方天文历法及医学、化学、药学知识,也潜心研究中国文化。
他们后来又受康熙皇帝的派遣回到法国传播友谊与中国文化。如1697年白晋回欧洲时,带回去很多中文书籍,包括《书经》、《春秋》、《易经》、《本草纲目》等。白晋把这些书连同康熙大帝赠给法国国王的礼品一起进呈给路易十四。1700年,洪若翰回欧洲的时候,曾将康熙大帝赠给法国国王的礼品茶、丝、瓷器和一些书籍呈送路易十四。1715年,传教士马若瑟将十三经等中国典籍带回法国赠皇家图书馆。1722年,通过耶稣会传教士运回法国的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典籍达4000种,这批书籍构成了今天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最早特藏。20世纪30年代,仅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各种刊本、写本汉籍就已达一万册以上。白晋还曾撰写了一部《康熙帝传》在法国出版发行。这些传教士不仅在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之间互送礼品书籍,还通过书信、汇报等方式向法国宫廷和社会介绍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这对“中学西传”起了重大作用,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及道德等逐渐被欧洲人所认识,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引起巨大震动。
四、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的历史功绩及其影响
包括法国传教士在内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在科学文化传播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传教士们远涉重洋来中国的主观愿望是要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时也负担了了解中国的地理、历史、天文、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科研工作,但这些传教士客观上也为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体系的建立贡献很多,这正应了中国的古话“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们不仅在中国积极参与朝廷的天文观测等科学活动,还把相关的科学资料送回法国科学院,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同时,中欧贸易逐渐加强,欧洲各国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将各类中国物品源源不断地输出到欧洲,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便逐渐风靡欧洲。
曾任法国皇家科学院主席的德梅朗于1728年10月14日给在中国宫廷长达四十余年之久的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写了第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对中国的优秀之处作了肯定:
“我对它的崇敬在于它的君主政体的久远;它的政府结构,君主们的睿智和公正;它的人民对于劳作的热爱和温顺服从;总体上对于次序的理念;以及这个民族毫无动摇地坚持对于规则和旧习俗的眷恋。我不知道是否中国人性格中的最后一点,即对于旧习俗的不可侵犯的热爱,加上对于父辈和长者的尊重,以及在生前死后给与他们几乎神话的敬意,正是其他各点的源头。”
法国传教士在华传教事业发展迅速,在华发展的教徒在1918年曾达到190万人。“法国天主教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创办教育事业。尽管从本意说是为了促进传教,但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法文化交流。”和法国相关并影响很大的震旦大学于1903年由中国基督教徒马相伯出资创办。“至1943年,据估计有3800名震旦大学毕业生分布于中国所有的工作领域且大多居于显要的位置,担当重要职务。那些没有得到显赫职位的人,大多数成为律师或教师……天主教教育事业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法国政府发现,要在中国举行文化事业,不得不借助传教士的工作。虽然在理论上,传教士不能成为民族势力的传播媒介,但在中国他们却是法语教学的先驱,而且法国政府官员认为他们同时也是法国势力的代言人。”与之相对的,大量的中国书籍也被翻译成法文,法国汉学也继续蓬勃地向前发展。
正如《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的译者郑德弟教授在该译著的中文版序中所写:“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融入程度以及对我国了解的深度是以往来华的任何外国人无法相比的,他们称得上是当时的‘中国通’。而这些‘中国通’又长于著述,勤于写信,于是,在近两个世纪中,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便通过他们的著述、书信或报道源源不断地传到了西方,西方人由此才开始真切地认识中国,西方的汉学也由此才得以奠基……他们是16至18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主要角色和先驱者。”
由于在华传教士们的介绍以及他们带回法国的大量中国物产,至路易十四统治后期的18世纪初,法国兴起“中国热”,“上至君王重臣,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无人不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兴趣,在华传教士们的出版物成了热门读物,来自中国的商品受到热烈的欢迎,有关中国的消息和知识不胫而走。中国瓷器在法国拥有无数喜爱者,在十七世纪中期,任何一个别墅或宫殿中若无中国瓷器点缀,便不可能被看作完美。”除了中国瓷器,中国风格的建筑、中国的漆器、丝绸、家具等工艺品也逐渐传入欧洲,先是在宫廷和贵族中流行,然后风靡整个欧洲长达数十年。当时法国宫廷中的中国影响几乎到处可见。路易十四本人习惯使用中国或按中国式样制造的家具。凡尔赛宫内,王后有一整套中国家具。王太子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四把中国扶手椅和若干折叠椅。甚至国王的仆人家中,也有中国的漆桌、花瓶与挂毯等物品。17世纪,即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凡尔赛宫中举行的庆祝娱乐活动经常包括中国题材。在王室贵族的引领下,这股“中国热”风靡17、18世纪的法国上流社会,并传布到其他欧洲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了欧洲人的审美情趣。
如前所述,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陆续涌入中国,但到欧洲去的中国人却是寥若晨星。“中国热”虽然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热火朝天,但汉学研究却相对滞后。这里我们想提一个人,即黄嘉略(Arcade Huang,1679-1716)。黄嘉略于1702年随法国传教士梁宏仁(Artus de Lionne,1655-1713)赴法,后定居法国巴黎。在他的启蒙和影响下,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和弗雷莱(Nicolat Freret,1688-1740)从事并开启了法国汉学研究,他们也成为了法国18世纪初汉学的领军人物,对汉学在法国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他们开始,法国人对汉语和对中国的研究不再是传教士的专利了。”这也使法国成为了欧洲的汉学中心。
五、小结
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民族,也影响着世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但同时它也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中法两国历史上最初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研习汉语,考察中国的风土人情,介绍和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籍,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引发了法国甚至欧洲的中国热,促进了法国汉学的兴旺,起了主导性和开创性的作用。无疑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历史性功绩。
[1]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窦坤.中法汉学研究所与中法文化交流述略[J].北京社会科学,2000,(4).
[3]朱仁夫.儒学传播法国——为中法文化年而写[J].云梦学刊,2004,25(3).
[4]韩琦.17、18世纪法国科学家眼中的中国科学——从德梅朗和巴多明的通信谈起[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5.
[5]张雪永.20世纪20年代的中法文化关系[J].中华文化论坛,2003.
[6]杜赫德著,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M].大象出版社,2001.
[7]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M].中华书局,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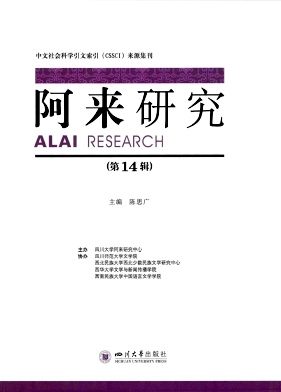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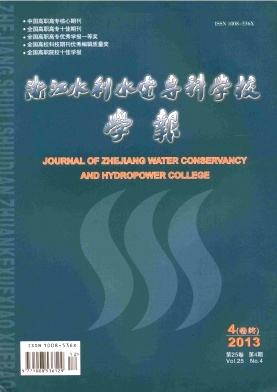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