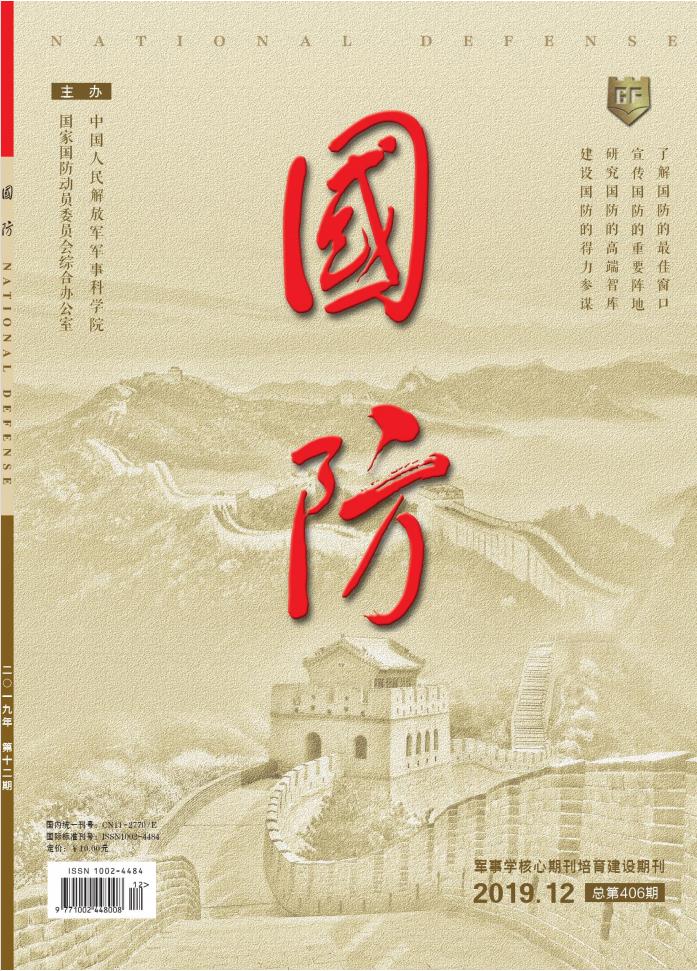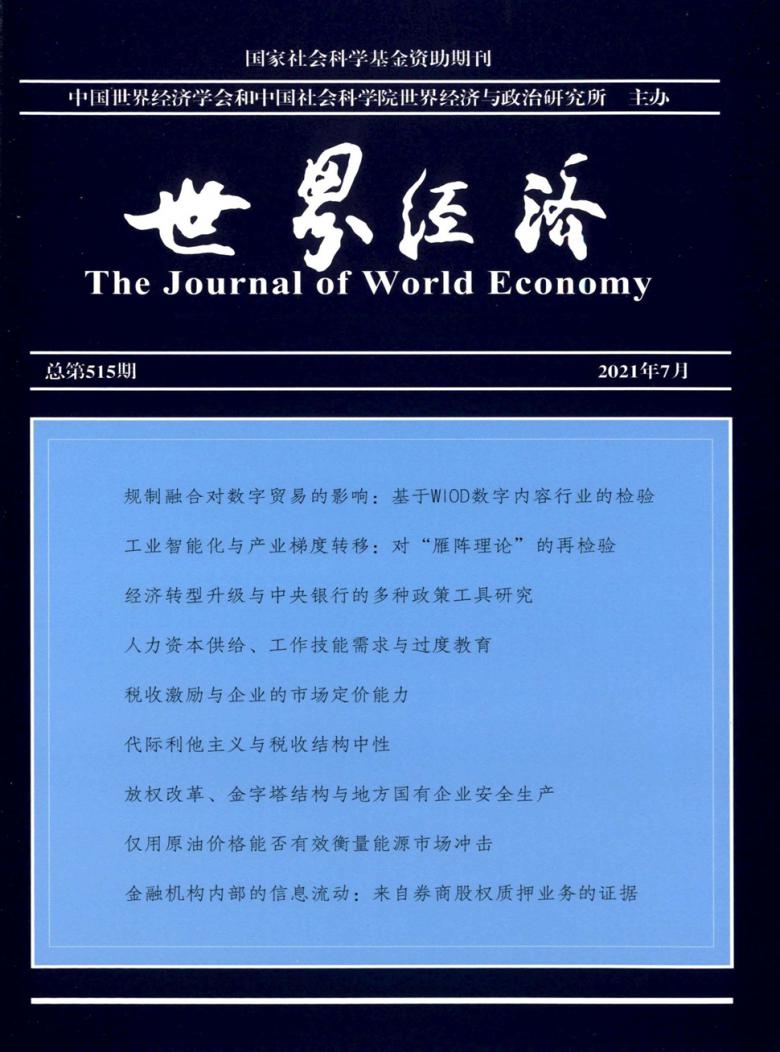“体知”儒学 考量文化——杜维明儒学思想评述
宁新昌 2006-04-10
在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中,杜维明可算是一位领军人物。这不仅因为他对儒学有独到的解读,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学究式的教授,而是一位公众型的知识分子。在解读儒学方面,他不同于大陆的研究范式,也摆脱了港台的思考模式。而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依凭着自己良好的中学功夫和西学素养,以及怀着对现实的问题的关切而走进儒学,“体知”儒学的精神内涵,挖掘其潜在的“普世性”意义。
儒学中的儒者,一般认为是“出于司徒之官”,其职责是辅佐周天子“明天道,正人伦”(《汉书·儒林传·序》)。用今天的话来说,“明天道”属于形而上,“正人伦”属于形而下。而“学”的意义,《说文》释之为“觉也”,即觉悟的意思。因此就字面意思而言,儒学实际上就是要对“明天道,正人伦”有所觉悟。以此去诠释儒学,即可以说它首先不是一门今天意义上的学问体系(logy),而主要是一种实践认知方式。这样一来,杜维明先生在研究儒学过程中所创设的“体知”方式就很有意义,也很有特色。提出这一实践认知方式的意义在于,它突破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上的主客二分的“霸权”思维模式,另外也为人们走进儒学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如其所说:“‘体知’,在这种语境里,可以规定为人心固有的感性觉情。正因为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性觉情不把任何东西‘对象化’,它才能包容天地万物,让一切都在其关注之中而成为人心中无对的内容。”(胡治洪:《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三联书店 2004年版,第98页。下引用该书仅注明页码)儒学的思维模式不同于西方人思考问题的模式,宋代程颢曾讲:“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二)陆九渊也曾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年谱》,《象山全集》卷三十六)程颢的观点是研究儒学需要“体贴”,陆九渊的观点则是,宇宙和心是同一的。宇宙是心的宇宙,心是宇宙的心。宇宙的心不同于一般认知的心,一般认知的心往往与宇宙相限隔,即把宇宙作为心的认知对象,反而二分了心和宇宙。如其所说:“宇宙不曾限隔人,人却自限隔宇宙。”依笔者理解,陆九渊所批评的就是类似于今天人们所说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由此可见,杜维明的“体知”倒是儒家一种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用此人们可以走进儒学。对于这一实践型的认识方式,杜维明作了很好的说明。
与此相契,则是现代新儒家的“内在超越”,牟宗三先生对此多有论述,杜氏在这个问题上乃是接着讲的。他说:“在本体论上,自我,我们原初的本性,为天所赋。因而,就其可涵润万物而言是神圣的。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它为我们所固有,同时它又属于天。”(第84页)在此,他继承了儒家的传统的思想“天命之谓性”,又摆脱西方思考问题的模式,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特征。所以,他不同意郝大维、安乐哲和冯耀明等人对“内在超越”的形式逻辑式的理解。因为那样不能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只能曲解中国文化的价值。为了证明自己的立论,他也阐述了自己的本体论主张,这就是“存有的连续性”。他的这一思想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如李明辉就以此来区别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第81页)。
对于“存有的连续性”之说明,主要立足于“气”的理论,他对“气”是这样理解的:“气”是“构成宇宙的最基本材料”,但它“既不是单一的精神,也不是单一的物质,而是兼有两者。它是一种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应当看成是游离于肉体的精神或是一种纯粹的物质。”(第58页)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学界对“气”的一般理解。即一般多是从物质性方面理解之,而他则赋予了“气”存在的精神性内涵。当然,我们也能理解他的初衷,就是要用此说明世界的连续,说明形上和形下无断裂、主观和客观无分离,说明“天命”和“性”的内在相通。
他承认儒学的宗教性,并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现代诠释去说明这一点。实际上这一问题和上述的“内在超越”、“存有的连续性”紧密相联,即他承认超越者的存在,这个超越者就是 “心”(“真我”)。他认为:“儒家宗教性是经由个人进行自我超越时具有的无限潜在和无穷的力量而展现出来的。”“可以把成为宗教的人的儒家取向界定为一种终极的自我转化,这种转化……是对超越者的一种诚敬的对话性回应。”(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105页)杜氏在超越的意义上理解宗教,并把儒家的宗教取向解释为“终极的自我转化”。他认为,“终极”指的是人性的最大限度的实现,“自我转化”意味着尽管我们现在还不是我们之应是,但是我们经过修身能够达到人性的最高境界。
要达到人性的最高境界,即人性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其切入点是“深层和动态的主体性”,“深层和动态的主体性”的展开分为身、心、灵、神四个层次。身是主体性展开的出发点,杜氏为之赋予了重要意义。“我们的身体并不是单纯地为我们自己所拥有,而是父母赋予我们的神圣礼物,因此,它充满了深刻的伦理宗教意义。”(第68页)但是他也认为“身,在儒家那里,经常是一个带有特定含义的词汇,这一词汇隐含着自我更为内在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圣人之所以能够充分了解他的形体,正是因为他已经修养并超越了形体。”(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101页)这样,自我转换的可能性问题就引向了“心”。“心”的特点是“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孟子·告子上》)这体现了它超越时空的特性。由于“心”兼有认知和良心双重功能,其“体知”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这正是其修养工夫的所在。“灵”是“心”之主体性的进一步展开,“灵”即“灵觉”,它“是一种道德智慧,是对存在情境的一种觉感。”(第74页)也是对超越境界的一种追求。“神”指的乃是超越境界,孟子有“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神”(神明)是“天地鬼神”的超越境界,它也是人们“在实现自身时所应不断身体力行的激励人心的鹄的”。(同上)人生不能没有目标,有了目标,才有追求,有了追求,人生也才有了意义。“神”是杜维明为人生所设立的境界和目标。所以,从“身”到“心”到“灵”到“神”,不仅是主体性的动态展开,而且是主体性的递进深入。这就是他具体化了的“内在超越”之路。
在走向“内在超越”的途中,杜维明并不忘却人性的现实展开,人性的核心是“仁”,“仁”本质上属于关系范畴。所以,对于儒者来说,杜维明认为:“作为关系的中心,我们并不是孤独地走向我们的最终归宿;我们总是生活于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之中”,“我们的自我理想正是通过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兄弟关系以及其他许多社会角色才得以产生存在”;甚至于“天所赋予我的本性只能通过作为种种关系之中心的我的存在去表现”(第106~107页)。这样一来,杜氏就把他的社会政治理论归结在“信赖社群”上,“信赖社群”成了人之情感的现实依托,同时也成了人之精神的最终归宿。这也倒符合于儒家的主张。
所以,在拜读胡治洪先生的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专著《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的过程中,笔者能深切地感受到,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杜维明的确是在“体知”着儒学的精神,秉承着儒家的命脉,承担着儒者的使命,关怀着儒学的复兴。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学者,他没有把自己的研究视域狭限在儒学内,而是延伸到儒学以外,面对文化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做出认真地考量,并积极地予以回应,当然儒学始终是他的出发点。
从后现代的立场看,启蒙理性是需要批判的,因为它有许多限制和弊端。对于这个问题,杜维明的基本态度是需要继承,更需要超越。这显示了他比起第一代、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有更宽阔的胸怀,他积极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揭橥的大目标‘民主’与‘科学’,到现在还是中国十分需要的,而这是儒家传统中最缺乏的。”“继承‘五四运动’时期以开放的心灵向西方学习是有现实意义的: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科学技术、乃至自由、人权、个体人格的解放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信念都是中国文化所缺少的现代价值。”(第145页)但是要知道,五四时代的价值观是欧洲启蒙主义的,这种价值观的局限是它的反宗教、反自然(征服自然)、反传统的倾向(第148页),所以,人们应该对它有所警惕,更需要去反思。
在反思启蒙理念时,首要的是个人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理论诉求和实践表现是自由主义。它们都曾被尊奉为社会的崇高价值,其积极意义已经被历史证明,“从西方中世纪到现代,自由主义的价值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宗教等各个领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及其所标示的价值如自由、独立、多元等,都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尤其应指出的是,自由主义在政治建构、制度设计的作用更不可加以忽视。”(第151页)还有“所有的大传统包括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希腊文化、兴都教、耆那教、锡金教、佛教、儒教、道家,都要面对”自由主义的“挑战做出调节”。因此,自由主义成了所有传统实现现代转化所必须通过的“卡夫丁峡谷”。但是,自由主义理论本身也确实存有悖谬,如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一整套理论而提出,而实际的结果却是“博爱”遭受弃置,“自由”和“平等”成了对立的两极。不仅如此,由于缺少道德的支撑,自由的结果只能是冲突。即“没有修身哲学的自由理念特别突出权利观念,创造了一个冲突矛盾的社会”(第153页)。与自由主义相关的民主政治体制,则被视作现代政治的图腾。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民主乃“是一种抗衡制度,是社会上各种压力集团相互抗衡、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相互冲突的结果”(第156页)。其缺陷是,在这一体制中,道德没有地位,信赖受到排斥,情感也被剔除。所以丘吉尔认为民主是个很坏的制度,但是其他制度比它更糟,所以只能用它。因此为了补救缺憾,就需要道德和宗教,因为这些价值系统能避免人成为普通的庸人,能纠偏制度中的糟糕的东西。
启蒙主义所崇奉的另一重要价值是理性。由于它在这个时代中的权威地位,因而它所在的时代也被叫做“理性的时代”。理性也被冠上了“理性主义”的称谓。客观说来,理性主义的确为科学的发展,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因为其无限制的张扬和膨胀,使之也被赋予了傲慢和僭妄的性格,而这种傲慢和僭妄所导致的是理性自身的工具化,由于工具理性本质上属于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它对社会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即“这类意识形态使很多应该在现代文明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精神资源被边缘化,甚至被消解”。所以它本质上“是一种对人文精神而言杀伤力很大的消解主义”(第159页)。
基于此,他提出要超越启蒙心态,并提出了超越资源的所在。也许是因为所处环境的限制,他对于目前中国大陆思想界的启蒙情节感到费解,并批评说:“启蒙心态在今日中国却很有生气、很活跃,这是令人奇怪的。”(第164页)在这一点上,笔者是不同意杜维明的观点。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中国目前仍处在实现现代化的途中,仍需要科学,也需要民主,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中国的民主更需要健全,自由和人权的理念还需要提倡。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还做得不够,与之相关的理性主义思想还需要借鉴和吸收,这也就是一些学者提出的补课问题。当然,杜维明先生的超越启蒙心态的主张对于人们也很有启发,即他在提醒人们不要再犯西方人已经犯过的错误,不要把科学神话,不要把民主图腾化,也不要把自由绝对化。应该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超越和补救“启蒙心态”的人文精神,而这不仅在我们传统中有,而且内容非常丰富。
杜维明的另一重要论域是文明对话。文明对话问题的提出源于国际生活中的现实矛盾,两大阵营的冷战结束以后,国家与国家间的争执、民族与民族间的冲突并没有减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主义仍在蔓延。据此,美国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亨廷顿认为这些都是由“文明的冲突”造成的,具体表现是过去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地缘政治已经让位于现在的文明支配下的地缘政治,过去的冷战集团的对立代之以现在的价值上的冲突。亨氏承认“多元文明世界”的存在,但由于其学术背景以及对冷战思维的承袭,他在承认文明多元性的前提下,否定了文明间的和谐共处,在追寻冲突的原因时,却把它归咎于文明的多元性。且不说其观点的唯心性,即没有探讨文明冲突(动机)背后的动因(物质原因),单就其 “相信西方所代表的模式是将来唯一的模式”(第254页)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和霸权思维模式。所以,他的观点一经提出,就受到来自多方的诘难,中国学者对此批评尤为激烈。因为它不仅反映了文化上的一种霸道,而且有悖于中国“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杜维明的批判也是儒家式的,他肯定了亨氏对“文明多元的预设”,但批判了他的冷战思维,批判了他承认多元文明的排斥性理论。提出文明积极互动“对话”的主张,这体现了他的儒家包容性人文主义的主张。
与亨廷顿的意见相左,德国神学者孔汉思在坚持文明对话时,提出了自己的“抽象的普世主义”理论。但是他的理论有缺陷:一是这种“抽象的普世主义”“如果再和西方霸权结合在一起,会产生许多不可预期的不良后果”;二是在理论上它的“最基本的还是自由人权等导源于现代西方的‘启蒙’价值。”(第255页)所以,他的理论不切实际,如杜氏所说:“他一生是从事基督教研究,他有一本书讨论如何在现代做个基督徒,有一千多页,其中只有三十多页是讲比较宗教,讲到儒家只有二三段。”因此,“我们如何相信他的普世伦理真能超越特殊和排他性,而他的淡化削弱不只是传递福音的策略。”(第255页)
基于以上因由,杜氏的新轴心时代的平等、多元的文明对话的具体主张是,“从积极方面看,在多元架构中,诸文明均‘采取以仁心说、学心听和公心辩的态度,从容忍、共存、参照、沟通,逐渐提升到尊重、了解和学习的祥和之境,’乃是‘迈向全球伦理共荣的先决条件’;从消极方面看,一味承认多样则‘又怕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因此,我们特别要强调社群伦理,全球的社群伦理’。”(第256页)
在建构全球伦理时,杜氏从文化角度提出全球伦理的建立必须以根源性与普世性的结合为基础,形成“一种能够符合全球任何人都应该遵循的原则”(第257页)。这就是各大文明思想家得出的人类社群可以共同奉行的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可以用孔子的话表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另一个是可以用康德的语言说的“人是目的”。他说:这两个原则不仅与“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是相契的”,而且“和佛教、道家、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伦理也可以合拍”(第258页)。但是,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相比,儒学在建构全球理论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儒学实质上是“一种修身性命之学,一种个人、社群、自然、天道面面具到的包容性人文主义,在当今多元根源性与全球一体化双向深入,人的状况已经面临困境,生态环保、女性主义、宗教多元以及全球伦理等思潮日益成为人类强烈诉求的时代条件下,相对于其他在个人、社群、自然、天道四层面中所偏畸或缺失的文明传统,特别是相对于表现为个人/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作为一种排斥性人文主义的现代启蒙理性,具有很大的说服力”(第261页)。他的这一段话不仅表达了儒学在建构全球伦理中的意义,而且也反映了杜维明对自己新儒学立场的坚守。
除了反思启蒙理念、进行文明对话、构建全球伦理外,他还对文化中国、多元现代化诸多前沿性的问题作了深入探究,提出了许多创发性的观点和论断。读完之后令人颇受启发,也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写的《论学者的使命》一书。书中有这样的话:“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学者的存在不是个人的事,而是社会的事,学者是为社会而存在,社会的使命就是学者的使命。杜维明就是为社会而存在的人,为儒学而存在的人。一次直肠息肉手术之前,他竟然想到如果一命呜呼,墓碑上是写“一个在美国进行儒学思考的从业员”还是写“现代新儒家”?(第26页)这件事情本身反映出在他的潜意识层儒学对他的生命意义。可惜,在目前的学术界像杜维明这样的人太少了。总之,在认真读完胡治洪的《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后,感觉他对杜维明思想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全面性。研究内容涉及杜维明思想的全部,有哲学本体论、宇宙论,认知方式、道德形上、人学思想、政治理论、儒学的宗教性、启蒙理念、工具理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女性主义、生态环保、文化中国、多元现代化、文明对话、全球伦理等各个方面。二是系统性。即研究不仅有杜氏业已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而且有他早年的读书笔记、老师的讲课大纲以及个人的日记等,可谓资料系统详实。三是深刻性。他有幸去杜维明身边工作学习,使之能真切感受杜氏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为学问道,从而为其掘井及泉式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他本人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条件。四是前沿性。由于杜氏思考问题的前沿性,所以也使得他在研究杜氏思想时而走到了新儒学研究的前沿。人们据之可以“了解当今世界学术界儒学讨论的前沿课题,以及国际学术界与儒学研究相关的社会、文化研究的最新发展”(陈来语,见书后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