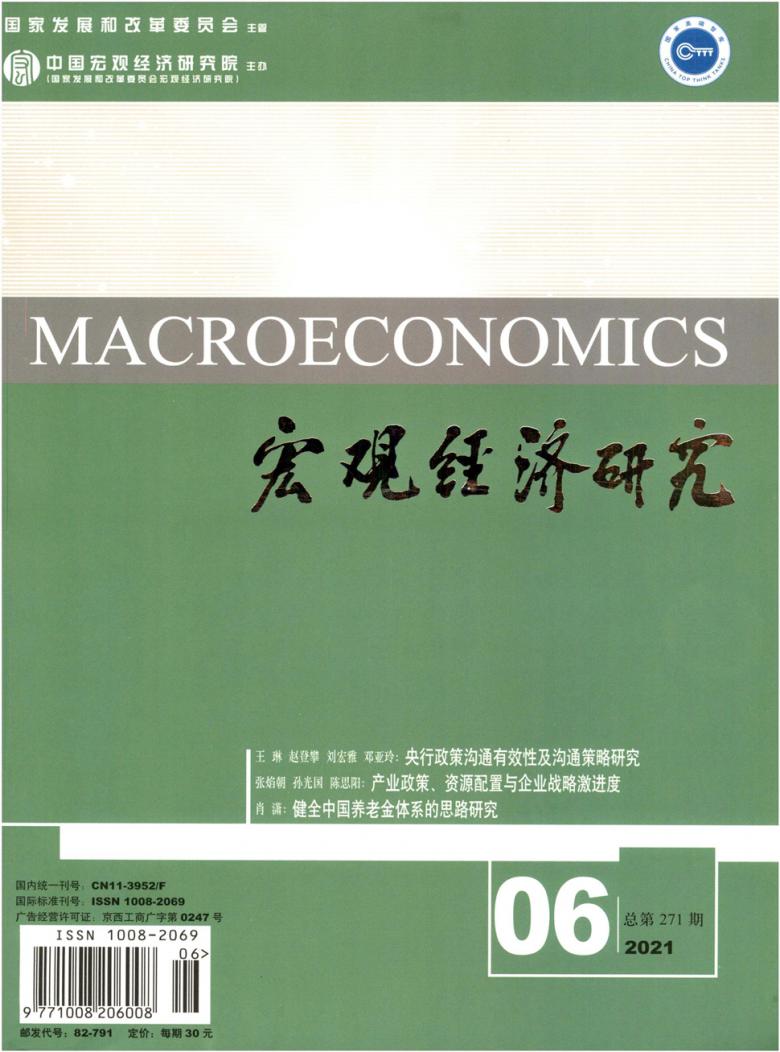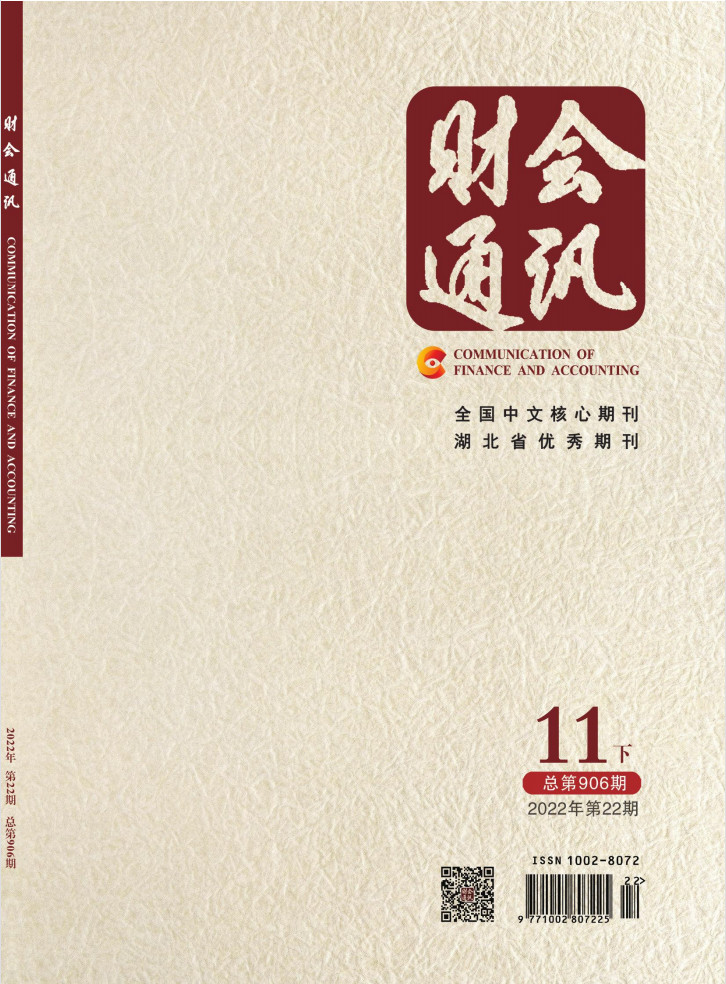性爱分离: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的文化选择
毛正天 2006-01-19
[摘 要] 性愛分離作爲中國現代性愛文學的文化選擇,以宣示人性復蘇和反叛舊禮教的“深刻的片面性”標示著對西方以精神分析爲代表人學思潮的接納,標示著文學性深度探索的勇毅與執著,不僅具有深刻的批判意義,也寓示著重建健全的性愛結構的文化意義。
[關鍵字] 現代文學;性愛;人性;特質
(一)
性愛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也是産生、形成人類全部文明的最原始的動因之一。性愛觀有兩種,一種是理性論,一種是本能論。前者要求運用理性控制性愛,以道德、以美來規約性,讓性與愛達到最佳的和諧狀態。在這種觀念裏,性愛既完善又完美,性與愛和諧統一,充分體現理性。別林斯基說過:“愛情之需要理性內容,猶如燃燒之需要油脂”。黑格爾認爲“愛情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生活旨趣,也要求實現。”言下之意,愛情雖然是熱烈的情感,但卻不能使它成爲至高無上的事。柏拉圖式的愛是這一性愛觀的經典。與之相反,本能論則將性愛定位在人本的、非理性的層面,性愛就變成自然自由、強烈瘋狂和至高無上。盧梭談過這樣的體會:“在我所愛的人身邊,曾不止一次地被喪失理智的性欲所引誘,從而變得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興奮的全身戰慄”。弗洛伊德則從性單向深入角度,反復提出“追求快樂”乃是人類性欲的“第一目的”的“快樂原則”(lust principal) 靄理士認爲性是人的基本衝動,是生命的動力泉源。弗洛伊德的性愛觀也應該是這種性愛觀的極致。
中國現代性愛文學選擇了弗洛伊德性愛觀,即本能論,也就使它有了本能至上的特徵,即性與愛分離的偏至。綜觀現代全程的性愛文學創作,凡是受到精神分析影響者,都程度不同地走向性偏至。這當然與中國現代性愛文學的文化環境有關,也可以說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西方雖然有遠祖柏拉圖創造了無性之愛的愛情模式,但在多元化的西方並不能一統天下,文藝復興的衝擊及20世紀初性觀念的全面更新已將它的影響消解殆盡。20世紀中後期在西方連番掀起“性革命”浪潮,已經在柏拉圖式的愛的相反方向走得很遠了。弗洛伊德的性愛觀充分代表了西方性愛觀的現代性。這於中國“五四”新文學是新鮮的,能刺激“五四”新文學興奮點。另一方面,幾千年文化傳統不變的老大中國,走過了與西方性愛觀相反的性曲折歷程,由開放到禁錮,到宋代已定位在“存天理、滅人欲”的反性文化上。不僅與西方性愛觀相反,而且走上極端。兩者的衝撞,迸爆的不僅僅是火花,而是驚天動地的裂變。借西方之性觀念療治故國之性萎縮,抓的是猛藥,治的是重症,性偏至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也富有前所未有的革命的意義。當然性愛的終極形態應該是二者的和諧與統一。但無庸置疑的是,中國現代乃至整個20世紀的性愛文學都還處在通向終極的遙遠的途程之中,它的存在是合理的。
如果說,性與愛的和諧結合是一種常態的愛的話,那麽與愛分離的性偏至就是一種廣義上的病態的愛。從“五四”時期被時代與社會革命推向前臺的性愛文學到逐漸與社會革命功能分離走入邊緣而自足生存的性愛文學,性愛始終是一條貫串的筋線,是一條保持性愛文學內核、銳氣與體現精神分析魅力的紅線。抽去了這一條貫串線,中國現代性愛文學將會失去特有的神采,變成另一番模樣。
從整個受精神分析影響的現代性愛文學的性愛形態來說,性偏至表現爲性饑餓和性變態或性愛兩極分離兩個方面,構成一道特殊的風景線。
“性饑餓”是現代性愛文學走筆的重要內容之一,作品普遍描述了由本能所發動的性饑餓參與到人的社會生活和事業創造中。他們把性當作生命本能的釋放,也當作愛,借性的形式來對抗孤獨,對抗壓抑,來顯示“我”作爲“人”的“在場”。如果將性饑餓單值的看,似覺意義不大,這也往往是道學家的批評者們的口實。但如果聯繫弗洛伊德對人性的揭示和特定的國情,就不難明白這一特質之深意和重要程度。按弗洛伊德的科學揭示,本能以巨大的能量方式存在著,它的轉移代表著生命的流動,鬱積太多太久,會導致生命的疾患,他所解析的“歇斯底里症”就是內在出了問題。他強調指出:“精神分析的實踐證明,歇斯底里症只不過是一種替代物,它們同一系列動人心弦的精神歷程、期待及願望之間的關係親密,簡直可算得上是這些東西的忠實記錄。這些期待的願望之所以爲患,完全是因爲它們遭受了一種特殊的壓抑作用之後而鬱積下來,不能在意識的精神生活中宣泄。它們被封閉在潛意識中,但由於其感情方面的力量,又不能不力求表達和呈示,最後終於在歇斯底里症中經由轉化的歷程而以肉體的變化表現出來,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歇斯底里症狀。”[1]從弗氏的揭示看,性饑餓的始作俑者在於“特殊的壓抑”,是壓抑導致“鬱積”,最後不得不宣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總可以從現代性愛文學所展示的性饑餓中去追溯原始的壓抑,總可以將主要是人性本能的呈示追尋到人的社會性方面,這應該說是現代性愛文學在精神分析影響下所形成的表達策略。
另一方面,“五四”擔起了解放人性的全面使命,從性愛去打量人性,便深刻體會到性愛的缺失。“滅人欲”既然已進入正統體制,就要從承認“人欲” 的合法存在入手解構這一體制。這是性饑餓普遍進入現代性愛文學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說受弗氏影響還主要耽於感性,後者則表現了不失強烈的社會意識。創造社作家的性愛文學作品可以證實上述觀點,施蟄存、葉靈鳳等的作品以及沈從文、張愛玲的作品又何嘗不能體現這一點。郭沫若掩不住浪漫激情,在他的一些性愛作品中,主人公的強烈欲望無拘地表達出來,那主要是他高歌人性,蔑視禮教的表現。郁達夫作品中所展示的性饑餓則是身負道德重荷的弱國子民在異國他鄉種種壓抑下的綜合反應;施蟄存寫性饑餓如《春陽》等,也暗示了“積欲”的原因和尋求“解欲”的理由;沈從文所思所寫,是在人性視野下對湘西鄉下的美好懷念和對都市社會的認識批判,“對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張愛玲基於自身的體驗認識,對人性作廣義的揭示,這些都表明,雖有程度區別,但一無例外性愛本身含有社會性內容。
就表現性饑餓的意蘊指向來說,主要是放歌人性,表明性愛的合法存在,不可折殺,向封建禮教及其衍化的種種陳規陋習叫板。因此,性也容易偏至,,而且,有意與其情、愛相脫離,將之當作自然本性加以禮贊,可以與愛統一,也可能單向作孤軍深入,比如亂倫等。
性變態或性愛兩極分離則進一步透視人性,揭示人性的個性。
弗洛伊德提出人的幼兒時期即存在性欲,其前提就是將性與生殖功能分離開,指出了性目的多元化,或在正常性目的外的性目的變異,出現性倒錯之種種現象。如受虐傾向、物戀、同性戀、手淫、窺淫癖等。在現代性愛文學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到這種描寫,郁達夫簡直可稱爲這方面的專家。在他的作品中,上述現象應有盡有,《茫茫夜》的主人公于質夫是個性自虐者,他用謊言騙得了女人用舊了的繡花針和手帕,急奔回家,忙著在鏡前用針紮自己的面頰,“對著鏡子裏自己面頰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腥紅的血迹,聞聞那舊手帕和針字的香味,想想那手帕主人公的態度,他覺得一種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透了。”于質夫把女人所用之物視作性愛物件(“物戀”症狀),在這種荒唐之中抗衡由張力導致的緊迫感和黑夜般在他周圍逼攏過來的空虛孤獨感。在變態的自虐中尋求新的痛感,麻醉主體,泯滅自我,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解析的將痛感轉化爲一種不同質的快感,用來提供潛在或現實的滿足,從而獲得暫時的精神超脫。應了美國心理學家卡倫·霍妮“以苦爲樂”是“作爲他保護自己以避免在眼前的危險的惟一方式”[2]的斷言。
在《沈淪》中則既有嫖妓,又有窺淫、手淫等變態行爲,儘管如此,主人公的性張力還是只能艱苦地釋放,因爲每一個性變態暫時疏緩了主人公的焦慮,但同時又不斷在自責中産生了新的焦慮,主人公陷入了性行爲和性心理對逆的惡性循環。
由例舉的郁達夫作品的典範表現來看,無論哪一種性病態,都帶有明顯的性愛分離性,從積欲到解欲並不是建立在性愛統一上的,也不完全需要具體性物件的契合,而往往是借助於性行爲本身暫時減緩焦慮感,因而往往是性愛心理與行爲的兩極悖逆走向——有性則愛,有愛則無性。然而,這種性愛是並不能帶給人真正滿足的,如音樂大師貝多芬所說:“沒有和靈感結合在一起的肉體享受是獸性的。事過之後,一個人體驗的不是許多高貴的情感,而是悔感”。[3]這也是事實,甚至是性偏至的魅力所在。由此也可以認識到性偏至的實質,是應“五四”新文學尊重人性,解放人性需要的放恣。在處理性愛本身的關係問題上,由人性出發;在對待性愛與社會的關係上,也是由人性出發,實現性的自足即可。
首先,在性與愛的關係上,儘管二者結合和諧統一,是人類性愛的終極理想,但現代性愛文學仍執著于人性的自由表達與呈示,不拘於二者的理想化形態。這一點在上面的論述中已經很清楚地顯示出來。不用說,郭沫若、郁達夫爲代表的浪漫激情主義要率性而發,從人性角度無拘地展示性,即便魯迅這樣的人生派大師,多聽“將令”捉筆,也不免要在表達性愛時,走向性的偏至。他的《補天》和《明天》,前者他自己已明確地說明是依了弗洛伊德理論創作的性的偏至;後者施蟄存運用精神分析也作了如是的準確的闡釋,大抵可證明上述觀點;而他的《肥皂》、《高老夫子》以及《阿Q正傳》中阿Q的性愛也並沒有統一,是一種偏至,揭示的是病態的性愛。《肥皂》中的四銘,在街上見到一位十八九歲的女乞丐,雖沒有馬上産生肉欲的邪念,但旁人的一句“不要看這貨色髒,你只要買兩塊肥皂來,喀支喀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不但刺激起了他的欲念,而且這位衛道士還馬上神遊於“情幻想”與“性幻想”的世界。更有甚者,爲了遮羞,他還把自己所要面對的事實僞裝成別人的罪過,讓別人去做“替罪羔羊”,自己以此得到一些安慰。他大罵“學生”、“剪發女子”與“新文化”如何的不道德,潛意識中把自己真正的“不道德”掩蓋起來。他還提出要以《孝女引》爲題賦詩表彰女乞丐,將女乞丐說成“孝女”,以將自己潛意識裏的欲念拔到正統地位。這一切還似乎出於真誠,其實正是性欲潛意識在支配他作秀。這是一種典型的道學家的病態性愛心理。高老夫子以“正人君子”自居,卻完全受著性欲支配,到賢良女校作教師,目的是想“看看女學生”,認真備課,也只是爲了讓學生看得起,內心深處一肚子壞水,卻偏又披著道家外衣正襟危坐,虛僞、萎縮和卑鄙無恥之至。阿Q也算得上是個下等人,對尼姑、吳媽單相思,八字還沒有一撇,卻居然無限膨脹起性欲望,做起“妻妾成群”的夢,“要什麽就是什麽,我喜歡誰就是誰”。他對末莊的女人悉數進行檢閱:“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腳太大”。
就整個從人性角度表現性愛看,是由兩方面構成的,一是從正面寫性的自然與自由,反抗現實社會對性的壓抑,再是從反面寫性的存在,針砭傳統性文化的負面。郭沫若等人是從正面放歌,魯迅則是從反面述說。總之,不必拘束於愛與性的統一,而以性的獨至和性的偏至,其文化意義是不可低估的。錢理群先生曾經將“自然人性在情感、道德甚至審判意義上的正當性”,“尋求人的解放”(包括思想道德意義的和情感的審美意義的)“基於人的解放之上的”性愛至上主義,“求樂的人生觀”以及“各種各樣的反禁欲主義”等等作爲“五四”個性主義的內涵的重要組成部分[4],現代性愛文學的性偏至正是這些內涵的充分體現。它充分表達了人性的“放恣”,對無所阻攔的生命自由作最大張揚。魯迅對於傳統文化下的性愛的深沈、冷峻的剖析和批判,郭沫若對於性的自然和個體精神的肆意擴張,郁達夫對於性的生命本能的深刻透視,施蟄存對性愛心理的科學解析,沈從文對性愛的歌哭與批判,張愛玲對於性愛的人生化的深刻揭示和思考,都是作家生命情緒和自我意識深化的表現,也是新文學作家追求精神自由和獨立價值的外化形式。梁實秋一語中的:“所謂新文學運動,處處要求擴張,要求自由。到這時候,情感就如同鐵籠裏的猛虎一般,不但把禮教的桎梏重重地打破,把監視情感的理性也撲倒了”。[5]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現代性愛文學家們並不讚賞冰心只寫愛不涉性的“閨秀派”創作,[6]而廬隱和淦女士則備受激賞:廬隱“在感情的發抒上較之冰心遠爲熱烈,而其描寫兩性間的愛,則尤爲大膽”。淦女土“有著比同時代的女作家更大的膽量,敢於掙脫一切舊禮教的束縛,也敢於揭開一切虛僞的面目,赤裸裸地把女性的心理和隱秘,于小說中和盤端出”。[7]
同樣的道理,當人們指責性偏至時,也有不少理直氣壯的捍衛,如周作人、郭沫若、黎錦明等對指責郁達夫性偏至的辯護和反駁;蘇青對張愛玲,張愛玲對蘇青遭受指責時的維護與辯駁等等,都是現代性愛文學史上的佳話。 其次,從性愛文學與社會革命的關係而言,理性論者極力要求二者統一偕行,要服從社會的需要,但現代性愛文學同樣自決地堅持性愛的自足,社會革命可以不看重它甚至抛棄它,但它寵辱雖驚,卻仍然堅執地自足發展。這從“五四”性愛文學與社會功利相統一時代結束之日起即開始顯現此特徵。“左翼文學”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取代了“五四”時期性愛文學與社會革命的統一關係,而與新形勢下的社會革命結成同盟;或徑直作爲文化載體。這些文學也曾試圖再振性愛文學精神,將性愛與革命結合,創立“革命加戀愛”模式,結果當革命者在享受性愛時,又覺著有負革命,於是産生靈肉衝突,呈水火不容狀,二者失去了統一的基礎,扭不到一塊。另一方面,性愛文學由熱鬧走向寂寞,默默地自我發展著,到抗戰文學時代,“左翼”文學沿著正向達到頂峰時代,文學與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出現高度一致狀態,“延座講話”應是這一文學與革命高度一致的理論總結與昇華。但同時,性愛文學火種不熄,就在“孤島”上海,也能有聲有色、像模像樣地存在與發展,並創造了張愛玲這樣燦爛奪目的星辰,充分體現了性愛文學的自足。幾乎可以說,就時代背景而論,“孤島”性愛文學已經卸下了爲抗戰鼓呼的社會革命擔子,是在全力爲人性歌哭。這方面的性偏至,是一種宏觀上的偏至。從整個現代的歷史看,性愛文學順著歷史向前延伸,只要精神分析學不被徹底撲殺(精神分析學被撲殺之時,性愛話語同樣也會消失,文革時期就是極例),性愛還會重演現代的一幕,事實證明,新時期東山再起的性愛文學的確將性的偏至推向了新的階段。
(二)
透視現代性愛文學的這一品質,明確地反映了西方全新的性愛觀與中國傳統文化中性道德觀與性價值觀的兩極悖進的衝突。一方面顯現的是嶄新的性愛觀,充分表達著人本主義思想,一方面是對傳統文化中兩極悖逆的憎惡與反感。兩者的反差造就了偏至的性愛觀,導致了對性的歌哭無拘,實現了人性的狂歡。這種情形甚至已經超過了西方“文藝復興”文學和十八世紀啓蒙文學的人本主義表現——至少在性愛這一題材上。啓蒙文學繼承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本主義思想,強調表現個人的精神生活,執著人的內心,關注人的自身價值,追求人性的自由和解放,但是他們也不泛濫情感,強調以理性的精神去觀照人類,狄更斯是如此,斐爾丁也不例外,盧梭甚至在提出“自然人”論(強調“天賦人權”)的基礎上仍然強調道德教化,狄德羅強調真善美的統一,絕沒有像中國現代性愛文學作這樣的人性放恣。正如黃子平先生評贊魯迅先生當年的片面(偏至)一樣,是一種“深刻的片面”。它抓住了人性的原點,結束了性與人性分離的中國傳統性愛文學歷史。
性屬於人的本能層,是人性的原點,正如福柯所引用的一句俗語:“有真理處便有性,關鍵在你見不見”。凡大作家無不研究性,將之作爲審視人性本質的起點。大詩人惠·特曼在《野草集》中常常深人到人性深層,爲性愛而歌;文學大師托爾斯泰將性苦悶與對人性的探尋結合在一起,寫出了一系列傳世之作;戴·赫·勞倫斯則是活畫人性性愛精魂的巨匠。中國現代文學家們將性和人性聯繫起來,由表及裏,追本溯源,無疑是有深刻意義的。
完善的性愛是性欲、愛情、道德構成的穩定的三角形,即所謂欲、情、理三者合一的“性愛結構”。中國現代文學將這一結構打破了,發生了傾斜,但這既不是它們的罪過和不足,反而是它具有思想衝力的應有形態。中國傳統文化倫理體系原本就是破裂的,性道德觀與性價值觀尖銳衝突,性道德領域對性愛的畸形壓抑,必然會把男女之真正的愛情擠壓掉,只剩下性這一赤裸裸的外殼,而性生活領域對性愛的變態崇尚和放縱,又必然會喚起人性中的獸性,這就是“道德的強化而引起道德的異化,人性的抑制而變爲獸性的膨脹”,造成有性無愛、有理無情、極度禁欲與無度縱欲並行的畸形現象的産生。這是導致主流文學(文人文學)不敢涉性,而非主流文學的民間通俗文學之流爲寫性而寫性的根源所在。中國現代性愛文學沒有在缺失的結構中將其補全,而是將之打碎,以“欲”爲中心構建人性的圓,用性的偏至宣示人性的復蘇和對舊禮教的反叛,因而它不僅具有深刻的批判意義,也寓示著重建健全的性愛結構的文化意義。
[參考文獻]
[1]弗洛伊德,性愛與文明[M],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12.32.
[2][美]卡倫·霍妮,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M],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221.
[3]愛言情語[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181.
[4]錢理群.論“五四”埋藏人的覺醒[J].文學評論.1989(3)
[5]梁啓超論文學.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M].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1.11.
[6]陳敬之.現代文學早期的女作家[M].臺灣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90.17.18.
[7]福柯.性史[M].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