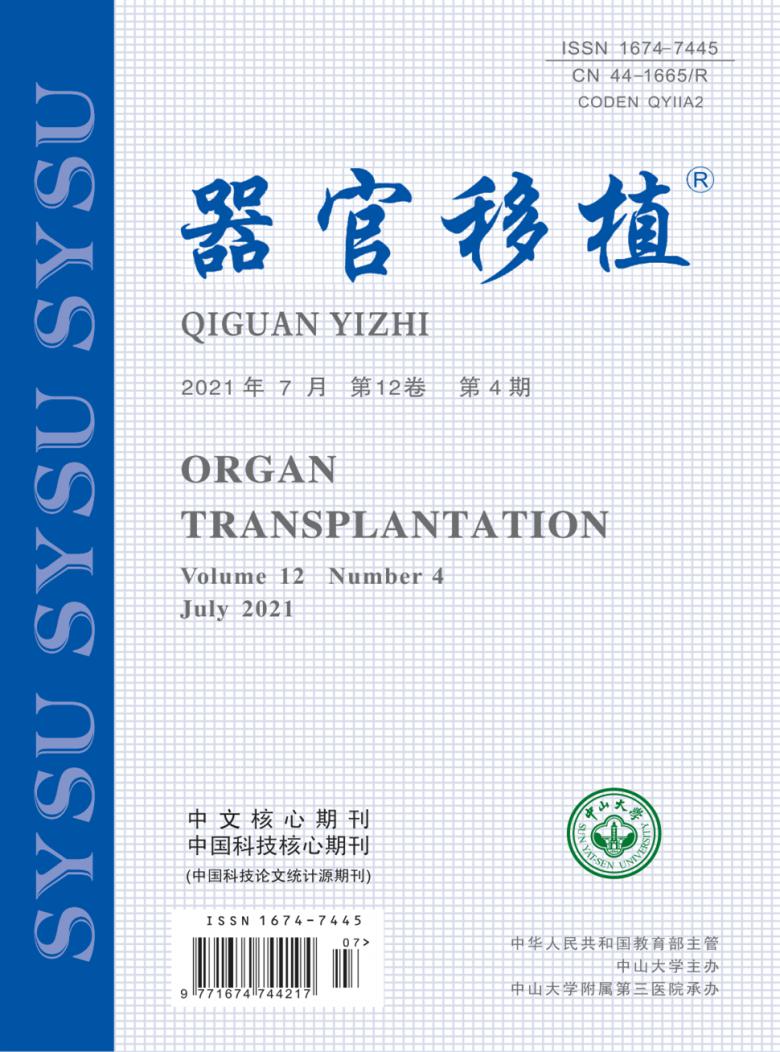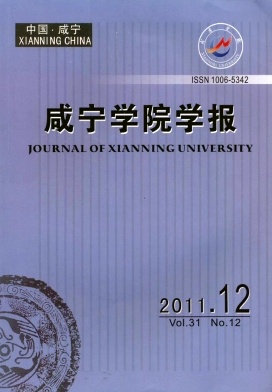理论与经验:介入大众文化的两种路径[1]——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比较研究
杨击
[内容简介]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辨证方法论,英国文化研究则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法兰克福学派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的“异化”思路批判和解析大众文化,而英国文化研究则采用历史主义的现实态度,凸显了工人阶级对英国社会“共同文化”的贡献;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采取的是抵制和超越的态度,英国文化研究则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救赎与正名;法兰克福学派对“精英文化”被褫夺表现出了极其的不情愿,大有用“应然”反对“实然”的意蕴,而英国文化研究则小心翼翼地求证工人阶级文化现实的合法性,更多地是要为“实然”争取“应然”的地位;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文化因为达不到他们的审美趣味而必然招致政治上的无能,而英国文化研究则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不但在政治上是合法的,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经验。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介入大众文化的路径所发生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代文化批评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其中,以审美趣味还是现实政治作为出发点,是这一变化发生的重要契机。
[关 键 词] 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 英国文化研究 审美 政治
本文试图讨论的是两种欧洲背景的思想方法针对大众文化现实所作出的反应,虽然这两种思想方法是不同时代和不同语言的产物,它们所面对的具体的大众文化对象非常不同,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传承关系,但是,两种思想方法均已成为西方大学或其他学术机构中主流的学术传统,并对当今学界的大众文化研究发生着持续的、无法绕开的影响力(当然,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大众文化研究的范围),无论欧美,还是中国。值得警醒的是,这两个学术传统的不断引介和吸纳过程,也是不断被工具化的过程,其原因不外乎两种:贪图学术生产的便当,或担心学术立场的偏差[2]。本文旨在体会两种思想方法的不同出发点和旨趣,反对简单化地将它们用作某种现实的批判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共享“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y)之名,前者通常被认为是批判理论的始作俑者,后者被视为传播批判理论的重镇,而事实上,从学术渊源上看,两者之间的联系或者传承都是不显著或者不重要的[3];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动服膺者,然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或继承是相当不同的。粗略地讲,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辨证方法论,英国文化研究则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在面对各自的大众文化现实之时,各自都从自己的身份本能出发作出了反应,法兰克福学派是以文化精英的口吻,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的“异化”思路批判和解析大众文化,而英国文化研究则采用历史主义的现实态度,凸显了工人阶级对英国社会“共同文化”的贡献;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采取的是抵制和超越的态度,英国文化研究则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救赎与正名;法兰克福学派对“精英文化”被褫夺表现出了极其的不情愿,大有用“应然”反对“实然”的意蕴,而英国文化研究则小心翼翼地求证工人阶级文化现实的合法性,更多地是要为“实然”争取“应然”的地位;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文化因为达不到他们的审美趣味而必然招致政治上的无能,而英国文化研究则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不但在政治上是合法的,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经验。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介入大众文化的路径所发生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代文化批评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其中,以审美趣味还是现实政治作为出发点,是这一变化发生的重要契机。
从审美批判开始
如果我们可以从血统和家庭背景的角度来考察,那么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立场几乎命定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重要成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的共同特征,即,他们都来自于家境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霍克海姆、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无不如此。按照汉娜·阿伦特的说法,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来自这类家庭的犹太青年,很多都“声称成为一个天才,或者致力于人类幸福,像那些为数甚多的来自富裕家庭的共产主义者一样——总之立志做高于挣钱的事业”,而他们的父亲,通常只接受这一类借口,原谅他们并没有一个像自己所走过的那种成功的人生,并继续在财力上帮助他们[4]。
虽然这是阿伦特针对富裕犹太家庭中父子之间解决关于人生目标冲突时写下这段话的,我们从中不难看出,犹太血统中对耽于理想、超越现实的气质的推崇与服从。阿多诺,法兰克福群星中年龄最小,也是最自负、精英意识表现得最充分的一位,她的外祖母和母亲都是德国有名的歌唱家,他的出生地法兰克福给他从小就提供了传统的音乐训练。可以说,阿多诺一出生就浸淫于“高超的音乐环境”之中[5]。可以想见,阿多诺这样的学者,他对于流行音乐的蔑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早在1936年,阿多诺尚未到过美国,尚未成为法兰克福学术团体的成员,就已经发表了批评爵士乐的论文《论爵士乐》。阿多诺不无轻蔑地否定了爵士乐也有表达解放的可能性,“爵士乐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只能给人以虚假的回归自然的感觉,其实是彻头彻尾的社会技巧的产物。阿多诺后来承认,他对爵士乐的厌恶,来自于“第一次读到‘爵士乐’(Jazz)这个词时感到的恐惧”,因为和德文中Hatz一词相象,而Hatz在德文中表示一群猎狗的意思,这就使阿多诺产生了否定性的联想——“张开血盆大口的猎犬追赶行动迟缓的动物”[6]。
1930年代后期,作为一个流亡美国的学术团体,法兰克福学派与当时负责哥伦比亚大学广播研究所工作的、同样是讲德语的拉扎斯菲尔德进行合作,显然更多是出于生存上的考虑,而非学术上的志趣。1941年,在法兰克福学派主持的刊物《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上,同时发表了霍克海姆、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论述大众传播的一些文章,其中有霍克海姆的《艺术和大众文化》(Art and Mass Culture),阿多诺的《论流行音乐》(On Popular Music)。值得一提的是,拉扎斯菲尔德《论行政的传播研究和批判的传播研究》(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的发表,已经预示了两者之间了然的分别。事实上,在整个1940年代,霍克海姆、阿多诺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他们是在充满紧张的生存空间和学术氛围中展开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的。
在《论流行音乐》中,阿多诺延续了早年对爵士乐的批评。他认为“标准化和假个性是流行音乐的显著特点”,而大众听觉的本质恰好是对熟悉的东西的亲近,这种本质只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是导向更深入欣赏的手段”,“一旦某些程式取得成功,工业就会反复鼓吹或大肆渲染某种同样的东西,通过令人神魂颠倒的、移植了的愿望满足和被动的强化,最终使音乐成为一种社会的黏合剂”[7]。
在为拉扎斯菲尔德所写的第三篇文章《电台中的交响乐》(The Radio Symphony)(1941)中,阿多诺之矛指向了艺术作品的生产和消费空间。针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音乐欣赏一小时》节目,阿多诺指出,这种所谓的电台交响乐,对听众来说,音乐已经失去了“现场”,与此同时,艺术品的“灵光”[8](aura)一同失却。在阿多诺看来,电台摧毁了交响乐的生成“空间”,那种类似大教堂的空间,在真实的音乐会上,听众是被这一空间紧紧环绕的。也只有在这种空间中,才有可能实现“时间意识的悬置”[9],而这种悬置恰恰是贝多芬交响乐的接受特质。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阿多诺对技术进步所持有的冷淡态度。
以政治批判落脚
对大众文化的审美批判从来就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终极目标。法兰克福学派感兴趣的问题是对西方启蒙理性的把握与反思,和二十世纪其他重要的德语思想家(譬如韦伯)一样,他们所诉求的是解除对启蒙理性所具有的解放人类能力的迷信,所谓“祛魅”,尤其让他们深感不安的就是所谓“工具理性”的反戈一击,无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还是技术的进步,这种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异化”后果,使他们看到人类尊奉理性之后自取其辱的一面。尤其令法兰克福学派痛心疾首的是,工人阶级居然非常温顺地与这个“异化” 社会整合到一起去了。而大众文化的种种特征,恰好是表达他们这一思想的种种佐证。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播研究真正产生影响,是从1947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开始的。《启蒙辩证法》虽然还是沿着法兰克福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道路前行,但是与1941年的写作明显不同的是,他们是从西方社会启蒙与理性的发展悖论的角度进入大众文化的批判的:
如果公众社会达到了,思想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商品、语言变成了对这种情况的颂扬,那么,必须在这种质变的世界历史结果完全发生破坏作用以前,努力发现这种质变,批判尾随流行的通过语言和思想表达出来的要求。[10]
阿多诺后来说,在《启蒙辩证法》中,他们有意识地用“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一词代替了他们往常一直使用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因为“大众文化似乎是从大众(masses)自身当中自发地出现的一种文化,是流行艺术(popular art)的当代形式。”而“文化工业”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它同时损害了曾经并存的高级艺术(high art)和低级艺术(low art)的严肃性:“它把分离了几千年的高级艺术和低级艺术强行撮合到一起,使两者都受到了损害。高级艺术的严肃性因为追求功效而被毁;低级艺术的严肃性则随着其内在固有的反抗性抵制受到文明的限制而消失。”[11]这里,阿多诺有把大众文化、低级艺术以及民间艺术(folk art)放到同一范畴中的倾向,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审美上和政治上都毫无顾忌地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了。
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关于大众传播和流行文化的批判的一些经典命题都是来自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最重要的认识就是艺术作品的商品化,这种商品化贯穿了整个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创作”已经不能用来描述“文化工业”了。这种商品化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艺术作品的同质化,艺术的个人主义和对抗性彻底消失;第二,艺术作品的消费是维护社会权威和现有体制的最好手段。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同质化显然是艺术的天敌,它结束了艺术的个人主义时代,消弭了艺术的反叛性。过去的艺术,比如悲剧,要表达的是像尼采所说的那种“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严酷的厄运、一个招致困境的问题所具有的勇敢精神和要求自由的感情”,[12]而“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电影、收音机和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出现了“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虚假的一致性。”这是因为“文化工业的技术,只不过用于标准化和系列生产,而放弃了作品的逻辑与社会体系的区别”[13]。在文化工业面前,人失去了真正的本质,而只能体现为一种“类本质”:“每个人只是因为他可以代替别人,才能体现他的作用,表明他是一个人。”[14]
文化工业是通过剥夺艺术作品的对抗性和反叛性而将它驯服为既有秩序的一部分的。文化工业生产的文化产品致力于使工人阶级非政治化,并且把生活中所有的矛盾都表征为通过现有体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的实现都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一旦“革命的倾向不论在何时羞涩地露出一定的苗头来,都将被一种大体上类似于财富、冒险、热情似火的爱、权力以及肉欲主义一样的愿望—梦想式的虚假满足所平息和遏止”。15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可以提供满足除革命以外的任何欲望的手段的地步了,而正是文化工业成功地阻碍了政治想象力的生成。对于文化工业是如何操纵消费者的思想与行为的,马尔库塞有如下的分析:
娱乐和信息工业不可抗拒的产品所带来的是各种定式的态度和习惯以及精神和情感方面的某些反应,这种反应使消费者在不同程度上愉快地与生产者紧密结合起来,并通过后者与整个娱乐和信息工业紧密结合起来。这些产品向消费者灌输某些思想并操纵他们的行为;它们提倡一种不受其虚伪影响的虚伪意识……这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比以前的生活方式要好得多的生活方式—而且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对质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单面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在内容上超然存在于已经建立的话语和行动领域之外的各种理念、抱负和目标,要么被排斥在这个领域之外,要么被限制在这个领域之内。[16]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的一个初始目的是寻找马克思的预言在二十世纪遭到失败的原因。俄国革命证明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爆发的预言是错误的,而美国的现实则证明工人阶级不但没有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反过来几乎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维护者了,哪怕是不自觉的。“历史看来是‘误入歧途’了,因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变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了,尤其是通过在工人群众当中推行一种‘假意识’,使得他们被同化到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去了,而普遍的、商业化的大众文化被看作是这种垄断资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一种重要手段了。”[17]
从对启蒙理性悖论的发现到对文化工业意识形态操纵的揭示,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批判理论。他们用“文化工业”来表述大众传播活动中媒介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开了当代大众传播和文化批判的先河;他们敏锐地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度组织化的阶段,大众文化和传播不仅仅是人们的闲暇活动的中心,更是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效果的一种基本的社会机构了。但是,法兰克福学派那种强烈的悲观色彩,那种用理论超越现实的态度,使他们的理论失去了解释现实的能力,使他们的批判失去了实践的指向,他们也许是用哲学思辩用审美精神抗拒现实的最后代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干脆放弃将理论转变为实践去改造世界的想法,认为理论的目的就是用它的否定力量与世界相对抗。[18]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批判态度也只能让一切事物保持原状:“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被严厉批评为‘坏现实’(bad reality),实在是坏得无可救药,但是这样的说法也使这个现实被哲学式地不朽化。”[19]
灵光(aura)消失之后:批判理论转向的重要契机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进行的批判,无论是审美的还是政治的,如果不从理论层面下降到经验层面之上,其批判精神就无法承继。而完成这一下降的恰恰是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中略显边缘的成员瓦尔特·本雅明。
上面我们分析了阿多诺试图将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与低级艺术(low art)和民间艺术(folk art)放在同一范畴中考察,阿多诺承认低级艺术的严肃性等等事实,可以看出他对文化工业化之前的流行艺术(popular art)的态度的。但是,似乎以前的大众文化一旦成了文化工业以后,文化产品连同它的消费者都是一无是处的。这里面他犯了两个历史错误,第一,文化工业并非在某一个历史时刻突然降生的,它和过去的所谓高级艺术和低级艺术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它不可能完全取代这两种艺术形式,况且所谓高级艺术和低级艺术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楚,历史上的低级艺术很有可能就是后来的高级艺术。第二,工人阶级,文化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发展和演变的整个过程的,他们也是整个文化现实和生活方式的制造者。工人阶级以及少数民族或者青年文化等其他亚文化群体不仅仅是文化工业中的艺术作品的被动消费者,有时也是积极生产者,并且在不同于过去的低级艺术或民间艺术的新的艺术作品中,仍然实现着对抗性,比如被阿多诺贬损至极的爵士乐明显就带有黑人反叛特色。事实上,正如阿多诺想用所谓理论的否定力量与他们永远也不会满意的现状相对抗之外,法兰克福学派从来不曾想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当代历史中拯救出任何东西,至于工人阶级和他们所热衷的文化商品肯定是乏善可陈的,从这点来看,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是相当可疑的[20]。但是,“只有被救赎的人类才知道它的过去的完满性……只有对被救赎的人类来说,它的过去才变成了随时都可引用的东西。”[21]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无是处的时候,只有让现实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新的审美批判才有可能。提出这一论点的不是别人,正是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沃尔特·本雅明,一个早逝的、曾经是默默无闻的边缘成员,而在当代,法兰克福学派中被公认最值得援引的两个作家,一个是阿多诺,另一个就是本雅明。
本雅明所要实现的这一转换是从对艺术作品“灵光” (aura)[22]消失的积极态度开始的。在阿多诺那里,真正的艺术作品是无法改编的,而文化工业的所有产品,却无情地将“本性严肃的文艺作品改变成讽刺体裁”。他痛恨爵士音乐家在演奏贝多芬的“极为朴素的小步舞曲时,任意进行了省略,并且粗暴武断地加进去了滑稽可笑的节奏。”[23]于是,艺术作品为了获得普遍的可得性而丧失了它的审美意义。马尔库塞进一步论述了这种“灵光”同样是艺术作品的批判性得以维系的关键所在:
新保守派的批评家嘲笑左派的大众文化批评家,因为后者反对巴赫被当作厨房的背景音乐,反对柏拉图和黑格尔、雪莱和波德莱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被陈列在杂货店里。反之,前者接受经典作品已经离开陵墓而再度进入生活的事实,这能使人们变得更有教养。没错,可是走入生活的经典作品已经不再是它们自己,而是别的东西;它们被夺去了那股反抗的力量,它们本体中的那种真正向度—疏离(estrangement),也消失无踪。这些作品的意图与功能因此根本地改变了,如果它们从前是与现状(status quo)处于矛盾对立的局面,这个矛盾现在已被抚平了。[24]
而本雅明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电子技术成为艺术的生产力之后,过去存在于自给自足的艺术作品中的生产关系已经瓦解了。要建立一种与大众文化时代相适应的美学,必须承认新的电子媒介的解放潜能。本雅明深深体会到机械复制艺术作品的行为后果超出了艺术的审美意义的范畴:
在机械复制时代所消失的东西是艺术作品的“灵光”。这是一种征兆式的过程,它的意义超出了艺术领域。人们可以这样来总结:复制技术将复制对象从传统的领域中分离了出来。通过制造许多复制品,一系列拷贝代替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同时,允许复制品符合观者和听者的具体情境,又激活了被复制物。……两个过程都和当代的大众运动(mass movements)有密切的关系。它们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就是电影。电影的社会意义,尤其是以它的最积极的形式出现的社会意义,不可能不伴有破坏性和宣泄性的另一面,即对文化遗产的传统价值所进行的清算。[25]
本雅明在辨证地看到电影这种新的艺术手段的两面性之后,进一步强调技术潜能的进步意义,而这种进步意义是直接体现为政治实践的。他说,“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机械复制把艺术作品从其对(宗教式的)仪规的寄生虫般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了,”由于“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标准不再适用于艺术生产,艺术的总的功能就颠倒过来了。代之以以(宗教式的)仪规为基础,艺术开始基于另一种实践—政治。”[26]本雅明可能是从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当中悟出这种技术潜能的积极意义的。本雅明看到了法西斯主义是通过把美学引入到政治生活中,让德国大众通过战争表达了他们想要改变社会的财产结构的愿望,而实际上是并没有改变这种财产结构。[27]德国大众在法西斯主义的引领底下参与了一场以战争为形式的审美暴力活动之后,不但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反而更糟糕。所以本雅明反其道而行之,倡导通过审美活动政治化,首先拯救大众,随后拯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大众被救赎了,大众得以欣赏的艺术也才能有地位,这和法西斯主义的态度正好倒了个个。[28]
从理论到经验:大众文化研究的现实转机
英国文化研究在实现从审美到政治的转换当中,既没有犹太人那种灾难深重的历史包袱,也没有德国人那种幽深曲折的理论负担。非常相象的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两位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他们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本能来介入大众文化的,只是他们要做的是救赎而不是抵制。面对英国文化思想史当中维护精英文化的所谓文化-文明传统,英国文化研究采取的不是超越的态度,而是改造的手段。如果说,雷蒙•威廉斯是通过置换利维斯主义的政治立场从英国文学史当中解读出他的文化观念的话[29],理查德•霍加特倒更是一厢情愿地将工人阶级文化,尤其是二战前的他所熟悉的英格兰北部地区的工人阶级的“活文化”纳入到文化-文明传统中的有机社会当中去。霍加特在他的那本稍早于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出版的成名作《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1957)中,试图证明二战前的英国工人阶级社区是具有传统的有机社会的色彩的,其中有一种典型的工人阶级的“十分丰富多彩的生活”(the full rich life)。大众娱乐的形式以及邻里和家庭关系的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的公共价值和私人实践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30]
《识字的用途》的第一部分题为“‘旧式’的秩序”(an ‘older’ order),通过对霍加特早年生活的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的社区生活的社会人类学似的回顾,展现了一种和谐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公共文化。这种公共文化体现在酒吧、工人俱乐部、报刊杂志和体育运动甚至个体日常生活的结构之中,而家庭角色、性别关系和语言型式中都能透出一个社区的共识(common sense)[31]。后来有一部反映英格兰北部社区生活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加冕典礼街》(Coronation Street)(从1960年开始一直播映到今天)就是以霍加特所描摹的二战前的工人阶级社区生活为蓝本的。在这个工人阶级的有机社会中,普通百姓人人各有所属,贫富差距、文化差异和社会矛盾都不是非常显著。[32]霍加特把这种工人阶级早期的文化版本的失却,看作是一种文化上的衰落,口吻和利维斯对十九世纪的文化衰落极其相似,不自觉地落入了文化-文明传统的窠臼,难怪霍加特把民间文化(folk culture)的所有优点都加到了那个时期的工人阶级文化头上,而在《识字的用途》的第二部分,他则抨击式地解读了二战后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霍加特在第二部分“让位于新文化”(yielding place to new)中一屁股坐回到了利维斯主义的立场上去,否认二战后的工人阶级社区文化同样也是植根于普通人的活文化的。他把这一时期的现代流行音乐、美国的电视节目、通俗的犯罪小说和浪漫小说以及和着自动唱机的音乐边饮酒边跳舞的青年行为方式,都看作是一种内在地假文化,被悬置的文化-文明的审美标准又开始发挥作用了。格雷默•特纳批评霍加特“虽然很好地描述了他的青年时代所处的文化领域的构造的复杂性,但是对当代工人阶级青年的‘十分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复杂性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33]霍加特对当时出现在英国街头的、带有自动投币唱机的牛奶厅的描述,丝毫都不掩饰他的深恶痛绝:
和我前面描述过的快餐店(café)一样,用假摩登的小玩意儿装饰的牛奶亭(milk-bar)那种低俗的耀眼的卖弄,马上就显示出审美趣味的完全垮掉。与这些牛奶亭相比,某些房舍简陋的顾客家中的客厅的布置看起来倒更具有十八世纪排屋的平衡和教化的传统……牛奶亭的“自动投币唱机”(nickelodeon)发出的刺耳的嘈杂声更象是给一个有一定规模的舞厅的而不是一条主要街道上的一个小商店所能承受的。一帮年轻人有的歪歪扭扭地耸着肩膀……目光茫然地穿过那一张张廉价的铁管椅子。
即使与街角的酒吧相比,这也全然是一种无意义玩闹的单薄而苍白的形式,一种弥漫在煮沸的牛奶味中的精神上的干腐气。[34]
霍加特随后把这些年轻人描写成“一个听从机器的阶级”,是“没有方向、被驯服了的奴隶”,是一种“享乐主义的但又是消极的野蛮人”,整天乘坐“票价三便士、五十马力的公共汽车,观看票价一镑八便士、投资五百万美圆的电影”,这不单单是一种“社会怪癖”,而是一种“不祥之兆”。[35]
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的第二部分之所以又回到了利维斯主义的立场上,是因为他在第一部分就试图把他年轻时所具有的工人阶级社区的生活经验硬是往文化-文明传统当中的有机社会身上靠,也就是说,从一开始霍加特就没有特别理直气壮地为工人阶级文化找到自己的立足点,那么,在霍加特眼里,把二战前民间文化(folk culture)和二战后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看成是泾渭分明的也就不奇怪了。从霍加特的身上再次看到,如果一定要在工人阶级文化当中寻找传统的审美合法性,是无法从根本上拯救工人阶级文化的。
真正完成从文化-文明的审美传统向文化政治学转向的还是雷蒙·威廉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前期,威廉斯已经开始建构他的文化政治学了。威廉斯是第一批把电影认同为创造性艺术的学者中的一个。之前的绝大多数文学评论家都把电影毫不犹豫地归入低级文化的范畴中。利维斯曾经批评电影追求的是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是一种消极的消遣手段。事实上,利维斯认为电影对高级文化的威胁要比那些低俗的小报来得大得多[36]。而相类似的,是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在《启蒙辩证法》中对电影的态度,他们把电影看作是“文化工业”的一部分,使观众产生错觉,“认为外面的世界是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情况的不断的延伸”,因此,电影“约束了观众的能动的思维”。[37]早到1953年,威廉斯在牛津大学从事成人教育工作时已经提出电影可以“作为一种主要的教学科目给(文学)评论提供许多机会”,并强调“电影研究作为一种机制不可避免要成为我们的社会学的一个部分”。[38]到了1958年,雷蒙•威廉斯在一篇宣言式的文章《文化是平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中直接挑战那种把文化区分成一方面是“超然的、自我得体的高级尖端的东西”,另一方面是“麻木不仁的大多数”的做法[39]。当然,最终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为所谓的“群众”(masses)争得地位的还是《文化与社会》。按照现在的传播理论来看,威廉斯梳理的英国文化观念史,就是一部关于“文化”应该是什么的话语霸权的争夺史,而要颠覆传统的文化-文明的文化观念,首要地是要消除那少数人和群氓之间的界线。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的结论部分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威廉斯通过把“群众”一词的意义返回到经验当中,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群众往往是他者,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他者。然而,在我们这种社会中,我们一直都看到这些他者,看到无数形形色色的他者;我们的身体就站在他们的身边。他们就在这里,我们就和他们在一起。……对于他者来说,我们也是群众,群众就是他者。
实际上没有群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群众的那种看法。[40]
雷蒙•威廉斯对文化批评所做出的贡献,始终是通过把观念返回到经验中完成的。通过历史主义的情境化,他采用的文化或者群众定义和表征获得合法性,然后与这些定义和表征相对应的主体也具有了合法性。威廉斯最中意的“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是从T.S.艾略特那里挖掘来的,而放到文化人类学的语境中来看,这种定义毫无新意。威廉斯对文化人类学的超越,就是通过对上述“他者”经验的超越实现的。文化人类学从来研究的是“他者”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在研究“他者”时,他们才敢于用相对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一个整体,而他们是没有勇气将自身当作“他者”看待的。和本雅明一样,威廉斯通过消除少数和群众的界线,消除我们和他者的界线,目的不仅仅是救赎工人阶级或者群众,而是救赎人类,这也是他的“共同文化”的旨趣所在。
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文化对欧洲的侵袭,以及英国本土那种被霍加特称为“新的大众艺术”(newer mass art)影响的扩大,如何评定大众文化以及如何使用新的大众媒介的问题在英国教育界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关于大众文化的鉴别和使用的研究在主流的教学和学术体制内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与此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越来越重视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使用问题。当然,官方和主流,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般立场都是指望把新的媒介当作手段,去传播所谓的高级文化。英国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斯图亚特•霍尔,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跻身于大众文化的研究行列的。1964年,还在中学任教的霍尔,在他和英国电影研究所(the British Film Institute)的教育官员帕迪•华奈尔合作出版的《通俗艺术》(The Popular Arts)一书中已经显示出和利维斯式的怀旧和有机主义越来越大的距离,同时对大众文化有了越来越现实的态度。霍尔和华奈尔首先要拒绝的就是所谓的“前工业时代英格兰的有机文化与今天的批量生产的文化之间”的传统的对抗:
旧时的文化已经逝去,因为产生它们的生活方式已经逝去。工作的节奏已经永久性地改变,封闭的小范围的社区正在消失。抵制社区的不必要的扩张、重建地方独创性也许很重要。但是,假如我们想要重新创造一种真正的通俗文化的话,我们只能在现存的社会之内寻找生长点。[41]
正是基于这种对通俗文化的既历史又现实的态度,霍尔在后来给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拒绝了该组织给各位提交报告者的预设立场,即电视应该普及和传播高级艺术,这种立场仍然是把文化当作少数遗产的传统立场。霍尔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误解了媒介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霍尔的结论是:“电视赋予我们的,并非更有效地端出文化的传统大餐,而是实现出现在1968年巴黎大学墙头的那句乌托邦式的口号:‘艺术已经死亡。让我们创造日常生活吧’”。[42]面向“日常生活”已经成了霍尔研究通俗文化的有意识的策略,预示了霍尔及其伯明翰中心从事的文化研究事业的方向。
小结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始终是站在精英立场上的批判,他们是用传统的审美文化来批判当下的文化工业产品的,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有两项不可饶恕的罪过:不但剥夺了真正的艺术品的“灵光”,而且成了统治阶级操控劳工阶级的帮凶。至于劳工阶级,非但没有成为马克思所预言的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反而心甘情愿地丢弃了以往同样具有反抗性的民间艺术,俯首帖耳地欣赏起文化工业的假艺术。于是,文化工业和劳工阶级一样是无可救药的了。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手中不过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它的立场是可以弃之不顾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边缘成员的沃尔特•本雅明,却通过把法西斯主义将政治审美化的手段颠倒为将审美政治化,承继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理论上救赎了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化以及“无产阶级化的大众”[43],但终因缺乏实践土壤而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英国文化研究介入大众文化的路径与本雅明几乎神合,但是它却是完全来自英国本土的社会主义传统和工人阶级的经验。根据雷蒙•威廉斯的分析,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工人阶级一直自觉地以避免普遍暴力的方式追求合法的政治地位,这本身就是对“追求完美”的文化的一种贡献。[44]在这种语境中,救赎工人阶级及其文化几乎是一种天然合法的立场。于是,在英国摆脱文化-文明传统的束缚,实现从审美到政治的转向的现实阻力要小得多。随着霍尔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主将,随着伯明翰中心对亚文化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经由欧洲结构主义理论的葛兰西式的运用,英国文化研究在对媒介文化的批判和救赎两个方面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注释:
[1] 三年前,笔者写作有关英国大众传播理论的博士论文,试图梳理文化研究学统的来龙去脉,不得不介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之后,便以为谙熟两个学术流派把握大众文化的切入口和脉络。去年八月,为参加在丽江召开的传播学大会,旧文新用,把比较两个流派的一段文字抽出来,润色修订,分段,赋摘要与关键词,单独成篇。在命名时颇费思量,最后决定以两个流派把握大众文化旨趣上的差异作为比较的切入点,遂得“理论与经验: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批判策略解读”之名。说实话,以“策略”这样的名目来安置这两个流派的思想努力,一定有违先贤们的本意,笔者能够体会到把思想当作权宜之计的紧张,仍明目张胆使用,心中不安自不待言。然而,更让笔者感到犹豫的是,以“理论”与“经验”作为对研究旨趣的描述和把握,其准确性有多少?把它们作为两相对应的“术语”放在一起考察,其合法性又几何?果不其然,在大会小组发言之后,点评专家黄旦教授提出两个疑问:其一,所谓批判策略的流变和对应关系,并不清晰了然;其二,“理论”与“经验”两顶帽子无所覆加,无的放矢,更进一步,哪怕两顶帽子合适,又有什么意义?到了今年现在,笔者修改这篇旧文并试图发表,针对的是第二个层面的疑问。如果放到我们所处的新闻传播学界的语境中来看,这种疑问不巧就可以还原成两个所谓的学术问题:第一,在引介西方理论之时,是把它们演绎提炼成某种工具(无论是用作学术方法论的、还是所谓指导现实实践的)呢?还是描述、阐释它们的生成状况?第二,如果从工具理性出发,批判理论于我何干?应该说,这种学术张力在更广泛的人文、社科语境中已经经历了某种凸显与消解过程,然而,在新闻传播学界,这种紧张状态连显现的机会都是微乎其微的,原因中的原因,仍然是那种“开药方”式的研究旨趣,其惯性之强劲仍然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另,为减弱笔者些须的不安,试将题目改为“介入大众文化的两种路径”,approach之谓也。
[2] 在一次非正式的、短暂的课题讨论会上,北京广播学院的陈卫星教授对批判理论的引介显露出一定的担忧,认为在我们目前传播体制尚未完善,媒体自主自律远远不足的情形之中过多地介绍对大众文化(包括大众传媒)的批判性论述,会不会抑制了我国媒体的发展。这应该是代表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相当一批学者专家的意见和看法。
[3]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学统之内,无论是以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和E.P.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主义还是霍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都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有政治经济学派的尼古拉斯·加纳姆直接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创造的术语“文化工业”的概念基础上开始其理论工作的。到了九十年代,仍然主要是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派中的人物(还有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重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和威廉斯“文化共同体”的含义的内在联系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媒介和民主、公共领域和公民身份的讨论。参见詹姆斯·库兰,《对媒介与民主的再思考》,彼得·达尔格伦,《媒介,公民身份和市民文化》,均收录于詹姆斯·库兰和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和社会》,第三版,伦敦:阿诺德出版社,2000年。
[4]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中译本,P44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5] 同上,P29-30
[6] 同上,P214
[7] 同上,P220-21
[8] 这是本雅明创造性使用的一个比喻性概念,稍后详述。
[9]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中译本,P221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10]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译本,导言第2页,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
[11] 阿多诺,《再论文化工业》,收录于保罗•莫利斯和苏•索纳姆,《媒介研究读本》,第31-37页,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 尼采,《朦胧的偶像》,载于《尼采全集》,第8卷,第136页。转引自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译本,第144-145页。
[13]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译本,第113页。
[14]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译本,第137页。
[15] 利奥·洛文太尔(法兰克福学派中一个不太出名的成员),《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第11页,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图书出版社,1961年。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14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6]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面人》,第26-27页,伦敦:斯菲尔出版社,1968年。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146页。
[17] 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第95页,伦敦:圣贤出版社,2000年。
[18] 参见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导论,张峄译,收录于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卷》,第182-23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19] 引自托尼·贝尼特,《媒体理论与社会理论》,见米切尔·古尔维奇等编,《文化、社会与媒体》中译本,第59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20] 其实这种精英式的态度始自马克思本人。格雷厄姆·莫多克在《重建倾圮之塔:当代传播和阶级问题》一文中,引述了一段有关马克思的文化趣味的逸事,原文如下:“马克思一位志趣相投者的妻子是这样逗弄马克思的,说她不能把一个具有如此贵族趣味的人和他在著作中所预测的平等社会很贴切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则足够真诚地回答道:‘我也不能’。马克思说他虽然确信‘那样的时刻会到来……届时我们离得远远的就是了’。详见詹姆斯·库兰和米切尔·古尔维奇合编的论文集《大众媒介和社会》,第11页,伦敦,阿诺德出版社,2000年。
[21] 出自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文集》。转引自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中译本,第17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22] 原意为“气味”“气氛”,本雅明用来描述过去的艺术作品诞生时的具体时空所赋予艺术作品的原生性、独一无二性和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术语。详见,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收录于达勒姆和凯尔纳,《媒介和文化研究:关键著作选》,第48-70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1年。
[23]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译本,第120页。
[24] 赫伯特•马尔库塞,《五个讲座》,第64页,伦敦:阿兰巷出版社。转引自托尼·贝尼特,《媒体理论与社会理论》,见米切尔·古尔维奇等编,《文化、社会与媒体》中译本,第56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25]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见达勒姆和凯尔纳,《媒介和文化研究:关键著作选》,第51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1年。
[26] 同上,第53页。
[27] 参见达勒姆和凯尔纳,《媒介和文化研究:关键著作选》,第63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1年。
[28] 本雅明的拯救对象是人类,因为他认为“现代人的不断无产阶级化和大众的不断形成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所以不论阶级,群众已经是当代社会的主体了。因而,他的“政治”,也非存在阶级和集团之间的,而是与审美阶段相对立的一个新的人类阶段,这种新的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大众的生活方式取得合法性。与雷蒙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真是不谋而合。见达勒姆和凯尔纳,《媒介和文化研究:关键著作选》,第63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1年。
[29] 有关英国的文化-文明传统以及威廉斯和利维斯主义之间的关系,详见杨击,《雷蒙·威廉斯和英国文化研究》,《现代传播》2002/3。
[30]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第132-1688页,伦敦:企鹅出版社,1958年版,1992年重印。
[31] 同上
[32] 参见杰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中译本,第57页,桂万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3] 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46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34]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第247-248页,伦敦:企鹅出版社,1958年版,1992年重印。
[35] 同上,第250页
[36] 参见杨击,,《雷蒙·威廉斯和英国文化研究》,《现代传播》2002/3。
[37]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译本,第118页。
[38] 引自雷蒙•威廉斯,《作为一个教学科目的电影》,1953。转引自约翰·西金斯,《雷蒙•威廉斯读本》,第5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1年。
[39] 引自雷蒙•威廉斯,《文化是平常的》,1958,见约翰·西金斯,《雷蒙•威廉斯读本》,第24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1年。
[49] 《文化与社会》中译本,第378-379页,译文略有改动。
[41] 斯图亚特•霍尔和帕迪•华奈尔,《通俗艺术》,第38页。转引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67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42] 斯图亚特•霍尔,《作为媒介的电视及其和文化的关系》,1971年,第113页。转引自格雷默•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第69页,伦敦和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
[43] 参见注28。
[44] 《文化与社会》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