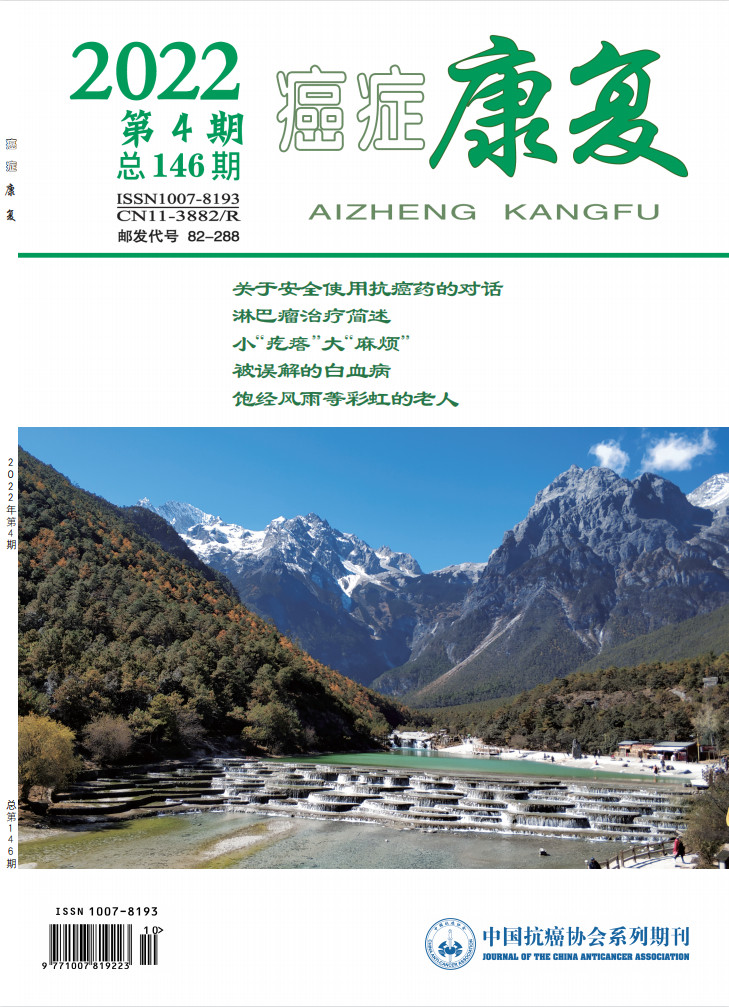转轨前中东欧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可放弃性”问题
佚名
「内容提要」对经济转轨后出现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最大的论题之一,论者在概念上似乎都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在改革前都是“计划经济”,两者的差异只在于对“计划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式。其实,中国与中东欧在改革前的经济体制差异更大,中国具有更多的“命令经济”的成分,而中东欧则较多的“理性计划经济”的成分,后者的绩效显然优于前者。但在迈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后者注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英文标题」“Abandonability”of the Central &East European and Chinese EconomicSt ructures Before the Transformation
「英文摘要」Interpretations of the“Chinese wonder”and “East European predicament ”after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themes of the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al economic community.Conceptually ,sc holars seemto believe that pre-reform China and Central East Europe lived under planned economy,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being the diff erent modes of reform over plannedeconomy.As a matter of fact,great dif ferences existed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East Europe in their economic s tructures before the reforms.The Chinese economyhad more elements of“o rder economy”,while the Central &East European economyhad more elemen ts of “rational planned economy”with obviously better achievementsthan the former.However,the latter had to pay a greater cost on the way to market economy.
「关键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性计划经济/“命令经济”
reform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structure/rational planned economy/“order economy”
“走出……”之别,还是“走向……”之别?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即所谓“中国之谜”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似乎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因而经济(根本性的或暂时的)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因而经济(根本性的蛟菔钡模┧ネ恕?br>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地以加入欧盟为目标,欧盟多数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剧变”后的东欧——前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相差悬殊之大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之差异来得大。
国际上的转轨经济学争论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两大传统即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在转轨问题上的延伸。在中东欧转轨10年间它们分别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并各自对中国与中东欧转轨战略的异同作出了解释。但他们在概念上似乎都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在改革前都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计划经济”,两者的差异只在于对这同一个“计划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式。人们很少反过来想:也许中国与中东欧的“改造方式”差异不是那么大(就经济改革的方向而言),而改造前的经济体制倒是差异更大些,由此可以更有效地解释后来的改造绩效?换句话说,中国与中东欧如今的转轨绩效之别也许更多地属于“走出……”之别,而不是“走向……”之别?
以往的转轨经济讨论中已谈到过“走出……”之别,尤其出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华盛顿共识”派学者如萨克斯等,都侧重于以“初始条件”来解释“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但他们通常强调的是发展水平不同(中国更不发达),产业结构不同(中国是农业国),乃至计划经济的惯性不同(中国只搞了30年而苏联搞了70年)。这些不同当然有影响,但仅此而已说服力是不大的。因为这样说来,最能摆脱困境创造奇迹的应当是更穷、更农业化、“计划”历史也更短的非洲国家了。
我现在强调的是,在“走出……”方面更重要的是经济机制的不同。在这方面,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外的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倒是谈到过。崔之元先生大讲“鞍钢宪法”就是一例。他把这个“宪法”说成是“后福特主义”的种种褒评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并就此提出过批评。但“鞍钢宪法”之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大异其趣,的确不可忽视。作为转轨过程的起点,这种差异对后来进程所起的路径依赖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恰恰与崔之元讲的相反)十分重要。而西方左右两派经济学家把转轨前体制大而化之都视为“计划经济”、只重视走出这种体制后在民主福利国家与公民自由交易两者间进行选择与搭配(中国与中东欧恰恰不是这种区别),这就很难真正理解所谓“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的产生机制。
事实上,无论古典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强调的市场机制优越性,还是凯恩斯—罗斯福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强调的国家调控必要性,都不足以解释这种“奇迹”。在笔者看来,这个“奇迹”的形成机制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由于中国式的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它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负帕累托过程”(不同于中东欧的束缚—保障协调型体制)而导致的条件:“走出负帕累托过程即帕累托过程(即人人受益过程)”。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只能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
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非现代性与异化的现代性
过去人们认为,传统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资本主义以广泛的交换打破了自给自足,于是有了市场经济。同时启蒙运动造成的“理性的自负”和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又使人追求人为设计的经济资源最优化配置,于是有了计划经济。但历史并非如此简单。马克思当年就谈到过“人的依附性”时代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作为“共同体之现成基础”的“强制劳动”可能包含的协作。[1](p.197,496,517)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 ·希克斯更认为真正无交往无分工的“自给自足”并不存在,传统经济中可能有相当规模的分工与要素流动,只是它并非因市场而起,而是“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2](p.23)他把这称之为“指令经济”。而经济现代化在他看来,就是传统“指令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演变。这种“指令经济”与工业文明无关,它与其说是“理性的自负”不如说是“权力的自负”,与其说是“科学主义”不如说是浪漫主义。正是这种“指令经济”或“排除交换的权力—分配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构成所谓“农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有利于种田人或为种田人所喜)。
而所谓计划经济,无论它的倡导者还是反对者都公认它是一种近代现象或工业文明时代的现象。倡导者如马克思,是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容纳不下的高度生产力”的产物,反对者如哈耶克,也再三指出它渊源于启蒙运动导致的“理性的僭妄”与科学主义扩张,而强调它与中世纪强制制度的区别。众所周知,尽管纯粹作为经济行为的国家强制与自由放任可以分别追溯到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德国历史学派与亚当·斯密学派,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中最主张自由市场的重农学派到亚当·斯密一系关系密切,与强调国家统制的重商学派到德国历史学派一系关系疏远而敌对。这当然不意味着马克思“亲市场经济”,只意味着作为计划经济倡导者的他,与斯密式的市场经济论者同样是敌视命令经济的。总之,赞成者与反对者都肯定计划经济与传统命令经济是不同的——尽管这两者都与市场经济对立,因而也有许多共性。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既可以意味着走出计划经济,也可以意味着走出命令经济,而在传统与现代因素并存的强制体系中这两者的成分往往并存,但毕竟也还有哪种成分为主的问题。
被希克斯称作“命令经济”的类型,是农业文明(但不一定是农业经济)的产物,这种经济可以不需要“工业文明”,不需要“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它不考虑投入产出系数、没有数理逻辑基础上的“计划均衡”概念、不考虑经济过程的最优化原则,而仅以人们对共同体的依附性为基础,以掌权者的长官意志、浪漫心理、个人需要或某种社会激情来支配经济。
一般地说,如果把市场机制下通过供求与价格信息反馈调整经济决策的现代经济看作“即时纠错”的经济,那么上述这种指令制度相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就是一种“无法纠错”的经济。除非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使旧的“命令”者退出,新一代的“命令”者有可能与民更始,它就很少有其他纠错机制。
另一种体制则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计划经济。据认为,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病在于市场“无政府状态”,使其纠错过程滞后并造成效率损失。在这种状态下,生产是盲目的,产品要上市后才能发现决策偏差(过剩或不足),然后根据市场信息进行调整,在一次次调整、一次次试错中达到市场均衡,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自从理性主义兴起后,相信数理逻辑的人们认为,完全可以把一切事先计划好,把均衡关系预先计算出来,以免除接触市场以后才发现的种种错误,即把“市场试错”要解决的问题以模拟经济参数的计算而“预先”得知,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根据资源配置最优化原则设定。
这种经济也可以叫“预先纠错”的经济。它依赖于通过精密的科学计算“预先”建立的“计划均衡”。如果仅仅就实现均衡(即实现最优配置)而言,它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胜于或至少不亚于通过“即时纠错”建立的“市场均衡”。事实上纯从数理逻辑角度看,市场均衡与计划均衡都是合乎“经济理性化”的。因此作为现代数理经济学奠基者的帕累托的如下态度便毫不足怪:他一方面反对贸易保护、支持极端的市场自由,另一方面似乎同样肯定“计划最优化”。这个以效率理论大师著称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计划足够“科学”,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比基于私有财产经济的国家能更好地把经济引向均衡”。即使不说“更好”,至少也可以设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常产生相同的结果,因而社会主义制度和完全自由的制度可能同样的有效率”[3](p.863)。数理经济学“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与理想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致的相同的经济‘计划’”。[4]在帕累托看来惟一的问题似乎在于:人们的计算技术是否已经能够产生这样的“计划”:“如果我们考虑四千万人口和几千种商品产生的巨额数量的方程,这将不是数学帮助了经济学,而是经济学帮助了数学。”[3](p.863)
这种“预先纠错”的经济在理论上似乎很理想,而从物质生产(不是效用生产)的效率看它也许比市场经济好,当然比瞎指挥的“命令经济”更好。这洋一种设想最大的问题,与其说在于它没有效率,不如说在于它不人道。它的设计无论如何“科学”,也是完全排除了消费者主权或更广义的个人效用主权,把人当作完全划一、没有生命的物体,当作生产—消费机器上的一个零件看待。例如,这种经济完全可以给一千个人配置出一千双鞋,不多一双,也不少一双。既没有过剩也没有不足。它还可以通过精确计算做到所有的材料部物尽其用。根据这一千双鞋所需要的材料安排皮革、橡胶等的供给,所有经济环节环环紧扣、精确衔接。它完全可以做到每个人都有鞋穿——但惟独不考虑个人的喜好和特点,它把消费者主权与个人效用原则排除在外,给你什么你就得接受什么。
从理论上、从物质生产的效率来说,它可以做到最优化。但我们现在所讲的效率不只是物质生产效率,更主要是讲效用增益效率,就是要满足人们主观福利偏好的效率。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经济就没有效率,至少远不如以个人效用主权为基础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那么有效率。还用上面的例子说,为一千个人生产的这一千双鞋,也许有大半是人们所不喜欢的。如果硬性配给,效用效率谈不上,物质生产效率(以实物即所谓“产品”计量的效率)在理论上还是有保证的。但这种保证必须以“最优化计划”的一元化控制为前提。也就是说它不可能“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按“科学计划”的确可以做到以最高的效率为一千个人提供一千双鞋,但如果还要加一点市场,允许这些人有权选择,那么这一千双鞋就很可能大半卖不出去,这些人就要从另外的途径、在充分市场化以前往往是成本很高的途径(自制或走私等等)来得到鞋子。于是效用生产效率的损失便转化为物质生产效率的损失,反而不如一点市场都没有,通过越来越精密的“科学计划”还可以保证物质生产效率的提高。但计划越科学“。加入市场因素后由效用效率损失转化为物质效率损失的现象就越严重。
两种转轨前体制的逻辑基础:“政治经济学”,还是“计划科学”
这种按“经济方程的最优解”运行的“科学经济”到底能否实现?帕累托提出的这个问题在20世纪20—30年代引起了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和社会主义学者兰格、泰勒等人的长期争议。前者认为由于经济变量的无限性,按预先纠错的理论,把经济过程的所有变量都作为参数代入一个超多元的方程,求出一系列的生产函数,这是“理性不及”,亦即人的能力所不能达到的。而以兰格为首的一派、直到后来的数理经济学家坎托洛维奇等认为是可能的。现在东欧的左派理论家亚当·沙夫仍然认为,以前受科学水平所限,信息处理能力不足造成了计划经济的失败,当今电脑时代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的结论是“新技术革命”是通过“真正计划经济”来达到“新型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但在米塞斯一派的后学看来,人们需求信息的变化永远比人们处理信息的速度更快,所以坎托洛维奇等人的最优化计划只是“电脑乌托邦”,永远不可能实现。对这种争论至少可以说:建立在最优化数理经济模型基础上的经济是不是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可以另当别论,但它比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的“命令经济”效率高是毫无疑问的。
东欧、俄罗斯与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时都处在不发达状态,都有“命令经济”传统。但相对而言,苏东的近代化程度较高,受工业文明影响较早,科学主义、理性计划的成分因而比中国改革前大得多。与苏联东欧相比,改革前大多时间内我们搞的实际上更近似于“无计划的命令经济”。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理论模式最典型的表述就是过去人们经常谈到的“马钢宪法”和“鞍钢宪法”。当年援华苏联专家引入斯大林时代样板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运营管理体制,企业中虽有党组织但基本不设专职党干,强调一长制、科层化管理、专家治厂,严格经济核算与计划平衡。而中国的鞍钢宪法则强调企业中设立强大的专职党政机构,实行群众运动、政治挂帅、党委领导、政工治厂、阶级斗争等。前者主要体现理性计划原则,后者主要体现浪漫命令原则。应该说这两种经济类型在苏东和中国都有,但相比较而言,中国“命令经济”的成分要多得多,苏东“科学计划”的成分要多得多,而且随着其工业化的发展而加深。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诸原则,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实行“最优化模型主义”,“科学计划”体制越来越“理性”了。
一般而言,理性计划经济、命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可表列如下:
表1理性计划经济、命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一)
表2理性计划经济、命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二)
有趣的是在“创新效率”方面,市场经济的均衡永远是动态的,由于竞争与需求的激励、过剩与不足的交替,均衡不断被打破和重建,两者都能推动创新,而市场本身又具有鉴别有效创新、淘汰无效创新和“伪创新”的功能,因而市场经济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实物生产效率,甚至最重要的也不在于效用增益效率,而在于它那无可比拟的创新效率,这是它能淘汰计划经济的直接原因。理性计划经济与命令经济在创新问题上似乎显得“两极化”:理性计划经济由于它那静态均衡和“预先纠错”性质,是最难产生创新激励的。在一个环环相扣的“最优化计划”中如果一个环节出现创新,反而会打破静态均衡,导致来自其他环节的压力。因此理性计划经济的“理性”从另一面看,实为泯灭创新激情的惰性。苏联经济墨守成规、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傻大黑粗而“经久耐用”是出了名的。而命令经济由于既无均衡观念,又不讲究环环相扣,还没有科层化的约束,就显得很不“墨守成规”,它常常能够激励浪漫的“创新”狂想:没有哪个体制能像改革前的中国那样成天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保守”,拔“白旗”,创“奇迹”,“放卫星”,“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砸烂规章制度”,“打破条条框框”……然而,这种体制致命的问题在于没有鉴别有效创新、淘汰无效创新和“伪创新”的机制,因而往往是“伪创新”、“奉旨创新”的效率特别“高”。而这种“伪创新”只会浪费资源、败坏风气,对国民经济的效用增益起负面作用。因此在效率方面,命令经济的“伪创新”通常还不如理性计划经济的不创新。不过,如果就打破体制本身束缚的“创新”而论,命令经济的这种特性倒使它比理性计划经济更容易被“创新”掉。
理性计划经济与命令经济的绩效比较不仅可以在理论上分优劣,而且经验上也十分清楚。工业战线的老同志都知道:如今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成为老大难问题的许多大型国企,尤其是以东北等地为中心的“156个大型项目”在改革前曾长期作为我国工业中的精华,其经济效益与业绩指标大都遥遥领先于我国工业的其余部分。这些企业当年均由苏联、捷克等国一手援建并奠定了其经营管理模式,后来虽然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受到“反修”的冲击,毕竟还有相当影响。而在“反修”中我们“自力更生”搞的那些运动型企业,包括“跃进牌”企业、五小工业、三线工业等等,除了少数像大庆这样的资源型企业与烟草工业这类特殊专营企业外,绝大多数绩效都很差。
但也有人认为,从整体经济指标看,改革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总的来说并不亚于苏联。其中最极端者(如韩德强先生)甚至认为改革前经济绩效高于改革后:虽然那时生活较差,但是高积累高速度奠定了工业化基础,改革后只是在吃老本。如果就发展绩效而言,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尽管经过长期战争与革命后,改革前我国经历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30年和平时代,在这个背景下旧体制与“计划经济”类似的高积累机制也的确对工业化原始积累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原始积累”以外的意义上,这个体制的绩效确实很差。不仅与改革后相比,就是与现在被公认为弊端百出的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相比也是如此。韩德强等先生喜欢用改革前官方统计数字,从这些数字看,即使现在被称为“十年浩劫”、“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文革”时期,发展速度似乎也不比改革后低。国外早就有学者以此为据,说了不少“文革”的好话。本文在这里不打算全面评价这种统计方式存在的问题,只是想以同样口径因而也存在类似问题、但因此反而有相当可比性的苏联时代数字作为对比,看看苏联计划经济与我国改革前经济的发展绩效。
这里必须指出,尽管中苏等国因政治因素决定的统计模式相似,但有一点明显不同:在传统上中国历来以与1949年的比较来统计发展成就,而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是按国际通常的口径与战前和平年代最高水平作比较来统计发展成就的。1949年是个10余年毁灭性战争后的废墟状态,严格地讲不适于用作比较基期,尤其不适于用作评价制度性因素对发展之影响的比较,更不适于与上述苏联式的发展统计相比。近来我国的统计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统计发展成就多改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的当年即1952年为比较基期。“国民经济恢复”后的数字尽管并不完全等于战前最高水平,但由于我国情况特殊,很难确定一个年份代表“战前最高水平”(注:我国农业以1936年为战前最高水平,但抗战时期虽然内地工业破坏惨重,日本在其占领相对稳定的东北等地则靠野蛮手段达致战时经济的一定程度发展,使全国统计的若干工业品产量高峰出现在1942-1943年前后。),因此用1952年数字代表“战前最高水平”还是最为近似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把改革前中苏经济发展的中长期业绩作出如下几项分段比较:苏联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三年大规模内战后,1921年基本恢复和平(当年仍有收复远东、平定伏尔加流域农民起义、乌克兰—中亚地区民族主义抵抗与喀琅施塔得“叛乱”等局部战争),由此至1940年共20年和平建设,到1940年与战前经济最高水平的1913年相比,国民收入达到611%,工业产值达到852%,农业产值达到141%,[5](p.58)农业人口比重由1913年的82.1%降至1939年的67%。[6](p.12)中国1950年基本恢复和平(海南、舟山、西康仍有局部战事,至于抗美援朝则是境外作战,人力损失虽大而物力主要靠苏援,对国内建设影响不大),由此至1969年也是20年和平建设,而1969年与“恢复到战前经济最高水平”的1952年相比,工业产值仅达到477%,“社会总产值”在1952-1971的20年里只增加到339.8%,农业产值则增加到162.9%(注:据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902、888-889页有关数据推算。)。实际上苏联的农业虽然糟糕,主要表现为产量增长慢以及为实现集体化付出的惨重代价,但苏联农民因工业化而明显减少,农业生产率还是颇有提高,而中国农民在此期间仍不断增加,其农业生产率明显下降,农业劳动者年人均净产值从“一五”时期的215.6元降至“三五”时期的182.4元。[7](p.358)
1941-1945年苏联陷入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46年恢复和平建设,历14年至1959年与战前经济最高水平的1940年相比,国民收入达到405%,工业产值达到480%,农业产值达到156%,[5](p.59)农业人口比重由1940年的67%降至1961年的50%。[6](p.12)如果同样以14年的时间看中国,则1950-1963的14年发展使中国在1963年达到相当于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52年工业产值的284.5%,1952-1965年间社会总产值只增加到212.1%,农业产值只增加到137%(注:据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902、888-889页有关数据推算。),而农业人口比重在这14年前后几乎完全没有变化。(注:中国城镇人口在“大跃进”中一度猛增,灾难发生后又大力清退,使1966年底城镇人口总数降至1957年水平。但由于总人口增加,城镇人口比重这时已降至1953年水平,即13.4%。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主编:《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73页。)
经过以上两个阶段共32年的和平建设,1959年苏联工人平均“实际收入”达到革命前最高年份(1913年)的390%。[5](p.76)应当说这个增长速度并不高,可是与中国相比还是很惊人了:同样是32年和平建设,中国经济到1984年工业职工平均“实际工资”仅为1952年(相当于革命前最高年份)的129.4%。而且这点可怜的增长也都是1956年以前“完全学苏联”时期与1977年以后很大程度上是恢复“苏联模式”的那几年的成果。如果以开始大批“一长制”的1957年与结束“文革”的1977年相比,则在这“中国特色”最浓的20年间中国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以1952年为100)竟然从116.3降至92.7,即净减少20.3%
即使在工资有所增长的苏联,国民总体生活水准的提高主要也不是靠这种增长,而是靠大量农民转为城市人口带来的生活水平变化。中国虽然工人农民各自收入水平部很低,两者间的差距却很大,“农转非”更是这一时期中国人生活提高的主要希望。遗憾的是:这一希望在中国比在苏联渺茫得多。在上述同一时期,苏联农业人口比重已由革命前经济最好时的82%降至50%左右,基本达到了进入工业社会时的都市化水平。中国同样是32年和平建设,城镇人口比重仅由1949年的10.6%升至1981年的19.8%,其中非农业人口仅为13.9%。“农民国家”的面貌基本未变。而且同样,这点增加也是1957年以前、1977年以后“苏联模式”还算管点用时的情况,而在1960-1976年间城镇人口从13073万降至11342万,[9](p.272)纯减幅达13.2%。这样的“逆城市化过程”无论在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苏联东欧的所有计划经济国家部没有出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按20年、14年、32年和平发展的绩效分别进行中苏改革前旧模式的比较,得出以下三表:
表320年绩效比较(20年和平发展后与战前最高年份之比)单位:%
表414年绩效比较(14年和平发展后与战前最高年份之比)单位:%
表532年发展绩效(32年和平发展后与革命前最高年份之比)单位:%
这里当然还有一些不可比因素,如苏联在二战前处于“一国社会主义”状态,经济发展基本无法指望外援。而中国在50年代经济发展中得益于苏联援助的成分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即使排除这些因素我们也不难看到:中国改革前的经济发展绩效的确与苏联式计划经济有明显的差异。当然苏联式发展的代价也是骇人听闻的,从今天改革的眼光看,苏联式的体制并不可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区分两种体制的差别。
因此,这两种经济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命令经济与“科学计划经济”一样不人道,一样缺少效用生产效率,但它因“不能纠错”而比“预先纠错”的经济更糟,因为它还严重地损害实物生产效率。而“科学计划”在这方面却有长处,起码它是一种“次优”的选择。但也正因为此,“命令经济”的可逆性较强,它会把经济搞得一团糟(像“文革”、“大跃进”时期)。但从这种“无序的命令”中走出来却相对容易,而“科学计划经济”却是一种严格有序的经济,对它的改革容易产生无序。一般地讲,改掉“命令经济”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放弃命令走向市场,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就能较易实现过渡。二是放弃浪漫命令,约束长官意志,“按科学规律办事”,运用最优化数理方法来实现计划科学化、理性化。对命令经济成分较多的国家来说,无论走哪条路付出的代价都比较小。因为原来的“瞎指挥”本来就不能建立均衡,当然就不存在改革破坏均衡的问题。这时无论通过“最优化”改革来建立“计划均衡”,还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建立市场均衡,都会带来经济上的纯增益。而对于计划经济成分较多的国家来说,问题就复杂得多。它可以通过“科学”手段使计划更加精确、周密、完善,越来越吻合于最优化数理模型。但这种改善有一个悖论,它在科学计划上越走得远,要转到市场就越困难。因如此精确的计划均衡极易被破坏,而市场均衡机制却不那么好建立。如此环环相扣、分工细密、有机联系的经济,只要计划一中断,整个系统就会崩溃,生产就会完全紊乱。
现在有人说:民主造成了混乱,过于激进的经济变革造成了混乱。然而苏联东欧在旧体制时代不是没有试过非民主状态下的渐进改革,但往往就是“一改就乱”。人们就是从中认定政治不改革,经济改不动,或者渐进无效果,必须彻底市场化的。早在60年代,人们就发现了这种两难处境。60年代苏联的利别尔曼建议就是要在体制内局部引进市场激励的。这个潮流传到东欧,东德,捷克、波兰等国都搞过“利润挂帅,市场导向”。然而不久就发现,这么一搞,原有的计划就紊乱,原有的分工协作体系就受干扰以至中断,生产出现下滑。后来中国那种市场因素“引进一点改善一点”的好处,他们没有尝到。于是只好又回头搞计划科学化的模式。最典型的例子是东德。东德在60年代学利别尔曼建议也搞过放权让利、加强经济核算的新经济体制,遵循一些市场选择,结果马上产生混乱,只好更换方向,到70年代走上“计算中心”指挥下的全国“托拉斯”化道路,不断集中不断地搞全行业一体化。捷克在60年代也企图搞市场经济改革,“布拉格之春”是政治先行,在《两千字宣言》和《捷共行动纲领》中都有市场经济的内容。捷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家奥塔·希克就是代表。但经济改革还没来得及实行就被明火执仗的武力卡断了,到了胡萨克时代,捷克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又努力使计划“更加符合最优化方向”,居然还真使经济一度又有起色。
利别尔曼建议的产生地苏联也是如此,赫鲁晓夫后期的改革未能取得效果,这成为他被赶下台的原因之一。在“河”里没有摸到“石头”的苏联人认为退回原处没有出路,因此改而强调优化计划。于是抽调专家到计委,给计划统计部门配置高级计算机,进一步发展数理经济学。但“科学计划”越是“理性”就越不食人间烟火的反人道之弊却不是“最优化”所能消解的,到一定程度人们又会有效用追求、亦即向往市场的追求。7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晚期又一次循环到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阶段,这新的轮回再次重复了60年代的情况:一放就乱,而且越是“科学”的计划,一旦放弃,那“乱”的代价也越大,只好又强化“联合体”制和“经济区”制,把一个行业的生产全部归到一起,实行全国“托拉斯”化,在一个“预先纠错”的体系下按“最优化参数”进行生产。
在这一过程中,数理经济学越来越取代“政治经济学”成为东欧计划经济学的主流。数理经济学是从理性主义的角度以最优化模型来配置资源的一门学问。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是道德判断问题,即证明资本主义是恶而社会主义是善,但它对怎么搞“计划”(这是道义原则无法解决的运算问题)是不加考虑的。所以可以说,与计划经济相应的经济学就是数理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盛行、数理经济学空白则是“命令经济”在学术上的体现。
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里是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但计划经济本身是否有自己的经济学?马克思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后来斯大林署名搞了一本“苏联经济学圣经”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该书传入中国后成为直到改革之初一直垄断经济学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祖本。尽管与苏联相比,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性更浓逻辑性更差,总体学术水平未必能及苏联,但“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之地位却是东欧万不能及的。
然而在苏联本国,即使在斯大林神化最甚时,计划经济学的数理化方向已经大成气候。20年代涅姆钦诺夫的统计分析理论与30年代坎托罗维奇的最优化模型建构,分别为计划经济中的经济信息处理与系统最优化控制奠定了“科学”基础。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长期受冷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布哈林虽被镇压,计划经济下无“政治经济学”而只有“计划科学”的看法在30年代仍然影响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193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改革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决议和后来的斯大林“圣经”虽然都指令要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直到1951年联共(布)中央召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讨论会时,仍然有许多学者尽管承认要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坚持认为它不研究“生产关系”(即不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承担制度褒贬功能),而只应研究“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和国民经济的计划化”问题,实际上还是把它看作非“政治”的“计划科学”。
直到1954年,苏联才出版了包含“社会主义”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这时斯大林已死,苏联也已在没有“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靠“计划科学”完成了工业化。随着理性计划经济的发展与早期命令经济成分的消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从赫鲁晓夫时代逐渐式微,数理经济学、尤其是坎托罗维奇所开创的“最优化计划”成为苏联理论经济学的主流。早期的维恩斯坦、诺沃日洛夫,晚期的阿甘别吉杨、沙塔林直到后来改宗西方经济学而成为剧变后经济转轨理论家的盖达尔、亚夫休斯基等等,这些挂帅人物无不是数理经济学出身的。60年代后对苏联经济决策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经济学研究机构也是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科学城工业经济研究所等数理经济学重镇,而传统上主要承担“批资”、“卫道”意识形态职能的机构如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这时也已突出了数理化色彩。
有趣的是,作为现代性异化的典型体现,科学主义的过分扩张一方面以“理性的僭妄”压抑了人性,另一方面也会冲击中世纪式的“神性”,而不同于仅仅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传统“命令经济”思想。一些数理经济学家由于其强烈的科学主义现代性取向,对掌权政客“反科学”的恣意妄为与瞎指挥深恶痛绝,往往容易发展出离经叛道的异端倾向。早在20世纪60年代,老一代数理经济学家涅姆钦诺夫、维恩斯坦等人就激烈批评“僵化的经济体制”,认为“一个从头到脚被束缚得如此厉害的经济体制,将阻碍社会与技术的进步,并迟早将在经济生活实际进程的压力下走向崩溃”。(注:B ·C ·涅姆钦诺夫:《论进一步完善计划与经济问题》,转引自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6-57页。)当时要求改革的新派经济学家都由他们构成,转轨后最狂热地主张自由市场的也是前数理经济学家。然而,又恰恰是被数理经济学高度“最优化”了的俄国计划经济,成为最难搞市场化转轨的经济体。所谓东欧拥有“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差的经济”这样一种奇怪的景观,说穿了也并不奇怪。
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到改革前夕还是旧体制经济的惟一理论形态。可以说,1978年以前在中国经济学界,既没有人吃西方经济学这碗饭,也没有人搞坎托洛维奇那套东西。这不能以那时政治上“反修”、与苏联学术隔绝来解释。因为苏联经济学的数理化早在斯大林时代已经很明显,那时中国根本没有反修之说,而是事事学苏联的,可是中国并没有引进涅姆钦诺夫、坎托罗维奇之学。这只能理解为当时中国的命令经济还只需要“政治经济学”来为“命令”作道德论证,并不需要什么最优化机制。
我们现在常说,苏联忽视了信息技术革命,这话要看怎么说。苏联人的确压根儿想不到去开发作为市场信息载体的互联网,更不会发展作为新一代市场消费热点的个人电脑及其大批相关商品——正是这些东西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质的飞跃。但若论计算机在要素配置中的应用,从宏观的计划制定到微观的企业管理,苏联在世界上都是最早注意的。早在电脑时代之前,以解复杂数理方程来求得经济参数最优化就成为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核心思想之一。无怪乎东欧人都寄厚望于电脑,数理经济学因而被称为“电脑乌托邦”。早在第二代计算机时代,苏联对电脑的运用已经从一般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发展为使用经济数学模型制定最优化计划。以后苏联的生产越来越朝理性计划发展,越来越强调生产函数最优化设定。早在70年代末,苏联已普遍设立了各专业部计算中心,并在互相联通的基础上建立了全苏计算机中心(ВЦВЦИО)。80年代前期,苏联当局又提出“当今时代的特点之一,是广泛采用计算技术设备来解决复杂的计划—经济、组织和管理课题”。
与宏观经济中的计划最优化相应,苏联企业的微观管理也向“最优化”发展。当时推广的“谢基诺实验”通过优化劳动组织、运用运筹学等科学计划手段,分解经济指标,实行物质刺激而实现减员增效。通过实验,谢基诺化工联合企业产值增加两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三倍,人员减少1570人,平均工资增加46.5%。当时还有所谓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是计划最优化在微观经济中的实践。
走出“命令”与走出“计划”:改革的“效率代价”问题
然而,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其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11](p.607)
在苏联东欧一会儿问津于市场、一会儿又转向琢磨怎么使计划更“理性”的曲蛇形探索的同时,中国却相反地走上一条一边割断市场“尾巴”、一边搞乱计划秩序,越来越走向命令经济之路,如所周知,中国在“大跃进”时代曾搞过“吃饭不要钱”,在“文革”中把农家养鸡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禁止,许多地区一度取消传统农村集市,不但消灭私人经济,把集体企业也当作“集体资本主义”来打击。在理论上不仅大批“等价交换”,甚至连命令经济中的工资制也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痛加贬斥。除这些特殊时段外,一般而言中国在票证、户口控制等“反市场制度”方面也比苏联更极端。但是尽管如此,改革后中国市场关系的恢复与发育却比前经互会国家相对容易,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命令经济至少以与消灭市场同样的程度,消灭了理性计划机制。
本来,正如苏联建国之初在落后农业文明土壤上亦有命令经济成分一样,中国建国之初受工业化苏联的影响也引进了若干理性计划经济的因素。“马钢宪法”尤其是其中的“一长制”等内容,曾在东北等地的一些苏援工厂实行。据薄一波的回忆,1956年前实行苏式厂长负责制的地方,尤其是156项目中较系统地引进苏式管理制度的那些企业,绩效还不错:“东北就是完全学苏联的,成绩显著。”[12](p.963)
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按薄一波的说法,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发动了大批“一长制”的潮头。中国工业从此恢复战争年代“中国特色”的政工治厂(即“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模式。此后,企业管理就日趋混乱,“提倡算政治账”,取消经济核算,“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现象相当普遍”,“无人负责和瞎指挥盛行”,甚至“有些单位把规章制度文件像土改中烧地契那样烧毁”,“车间‘自由生产’;仓库‘门户开放’”,[12](pp.961-982)直到酿成三年“人祸”。以刘少奇、薄一波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后来力图恢复一些“马钢宪法”的东西,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就是经过力争后的产物。薄一波认为它虽然未能恢复“一长制”,但通过拒绝规定“车间、工段实行党总支、党支部领导下的车间主任、工段长负责制”,总算抵制了政工治厂的恶性发展。[12](p.964)从而为中国工业赢得几年喘息时间。然而“四清”开始后,《工业七十条》就“被扔到一边”,不用说恢复“一长制”,“就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受到‘左’的严重干扰”,被说成是“架空党委”、“没有跳出苏联‘一长制’的框框”。1965年“上海座谈会”提出“割去厂长负责制这个尾巴”,学习军队,实行政委制,“企业管理日益‘政治化’”,[12](p.981)终于导致“文革”中彻底的“运动经济”和“无计划的命令经济”。
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所谓路线分歧几乎就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地“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计划经济倾向。
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前者是劣势是支流,在后者的进逼下全无招架之功,何谈“恢复”之力。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了。到了改革前的“文革”时代,薄一波式的“修正主义”实即计划经济派彻底失势,中国经济完全陷入“命令破坏计划”的非理性混乱之中。建设中盛行“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首长工程”、“条子项目”大行其道。计划经济的“规章制度”、“条条框框”都被砸烂,正如改革之初一篇著名社论所说:那时根本不把“计划”当回事,而是“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13].因此不难理解: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仅从引进市场因素中获益,而且实际上也从“恢复”苏式计划经济中获益。在改革初期,后者甚至更为重要。这是东欧人不可能享有的独特“优势”。邓小平后来曾说: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14]众所周知,1975年的“整顿”并没有任何“市场取向”的影子,而只是部分放弃了“运动经济”,部分恢复了被“文革”彻底“砸烂”的“修正主义”的即苏式的经济管理,或者说减少一点“鞍钢宪法”色彩,增加一点“马钢宪法”色彩,减少一点“政治经济学”,增加一点“计划科学”。就这样中国的经济顿时有了明显的起色,“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而苏联东欧当然完全不可能得到这种效果——他们早已是百分之百的“马钢宪法”了,还有什么可“整顿”的?他们已经把理性计划发展到“最优化”的地步,继续发展已无潜力。而要放弃“最优化”,那代价是很大的。正如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所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15]实际上,中国改革同时享有“引进市场”和“优化计划”的双重好处,虽然后者的比重渐小,但迄90年代仍未完全消失。那时中国一定程度上还在用“全国托拉斯化”的思路来解决重复建设、山头经济的问题。例如近来的民航重组就是如此:90年代中期中国一度出现了多达44家独立航空公司,比任何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多,民航总局出面将其“重组”为实力大致均衡的国航、东航、南航三大集团。对此,有人担心行政性重组会开市场化的倒车,有人则誉为国家调节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杰作。实际上,此前的44家公司既非民营企业,亦非按市场规则运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承继“文革”中“山头经济”、“五小工业”、诸侯攀比的命令经济遗风。民航总局的“重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国家调控市场”的凯恩斯式成功,毋宁说是理性计划纠正命令经济的成功。
如上所述,由于作为“现代性异化”的“计划科学”与反现代性的命令经济有矛盾,前者因不满后者而容易产生改革思想,苏联后期的这一逻辑在中国表现得同样明显。早期发动改革的邓小平、薄一波等人基本都属于“文革”前的理性计划派。只是他们远比苏联东欧的同道更不幸——改革前他们被整得无所作为,但因此他们也比苏联东欧的同道更幸运——正因为过去理性计划无所作为,改革后他们无论搞理性计划还是搞市场化都能大有作为。而东欧同道们过去的成功恰恰成了他们如今必须付出“代价”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J·希克斯。经济史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A·P ·柯曼。作为经济学家的帕累托[A].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4]E·罗尔。经济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59[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
[6]李仁峰。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7]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8]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9]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10]G ·I ·马尔丘克。苏联1981-1985年及至1990年170项综合目标规划概况[J].苏联科技参考资料,1983,(总13)。
[11]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94Book of the Year )[Z].Chicago :EncyclopaediaBritannica Inc.,1994.
[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13]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N].人民日报,1980-04-15.
[14]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OL].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
[15]Laszlo Csab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China and EasternEurope Compared[J].Communist Economi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199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