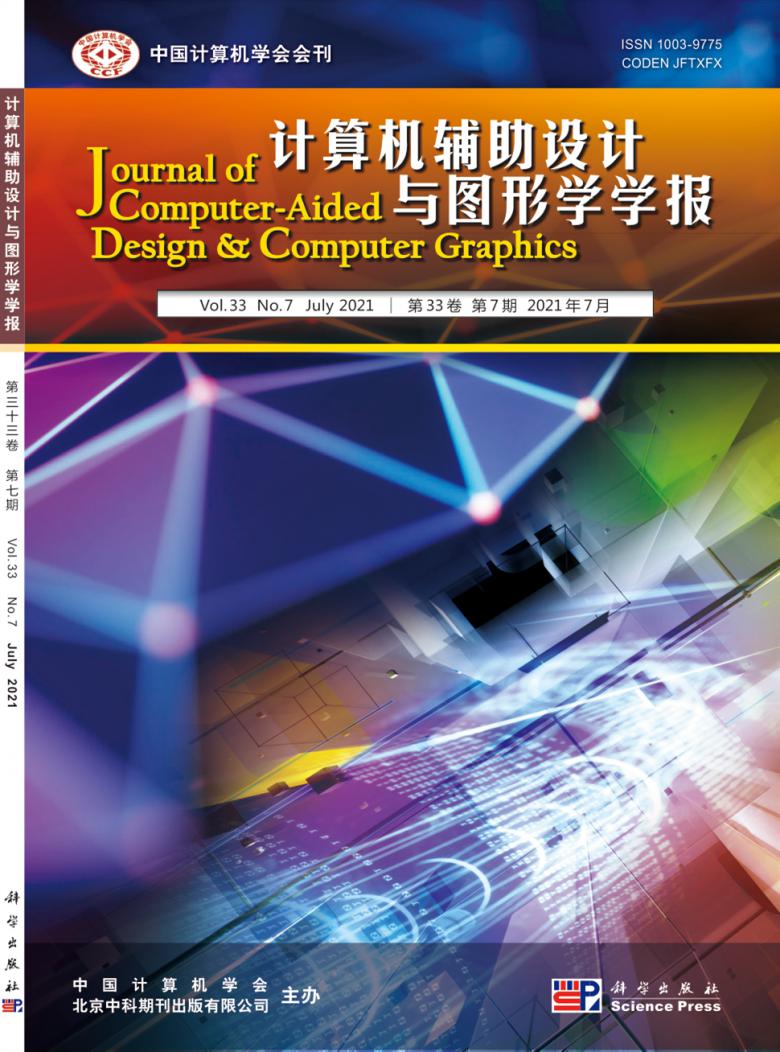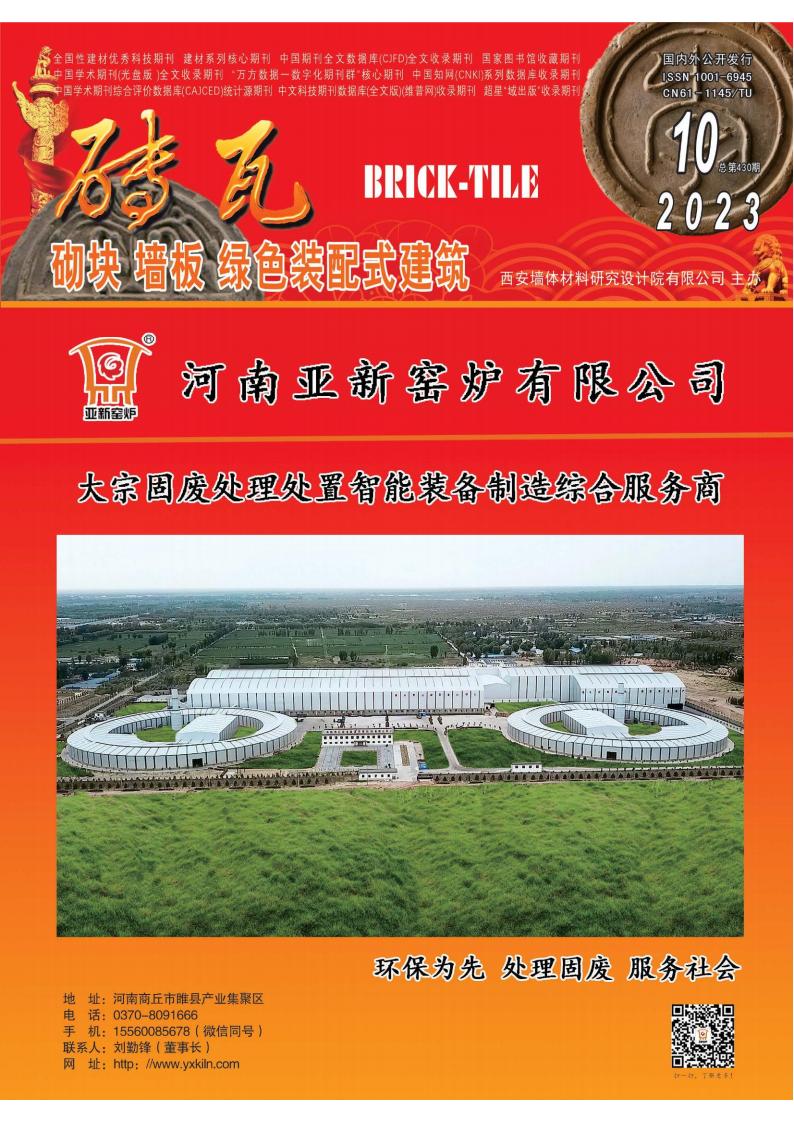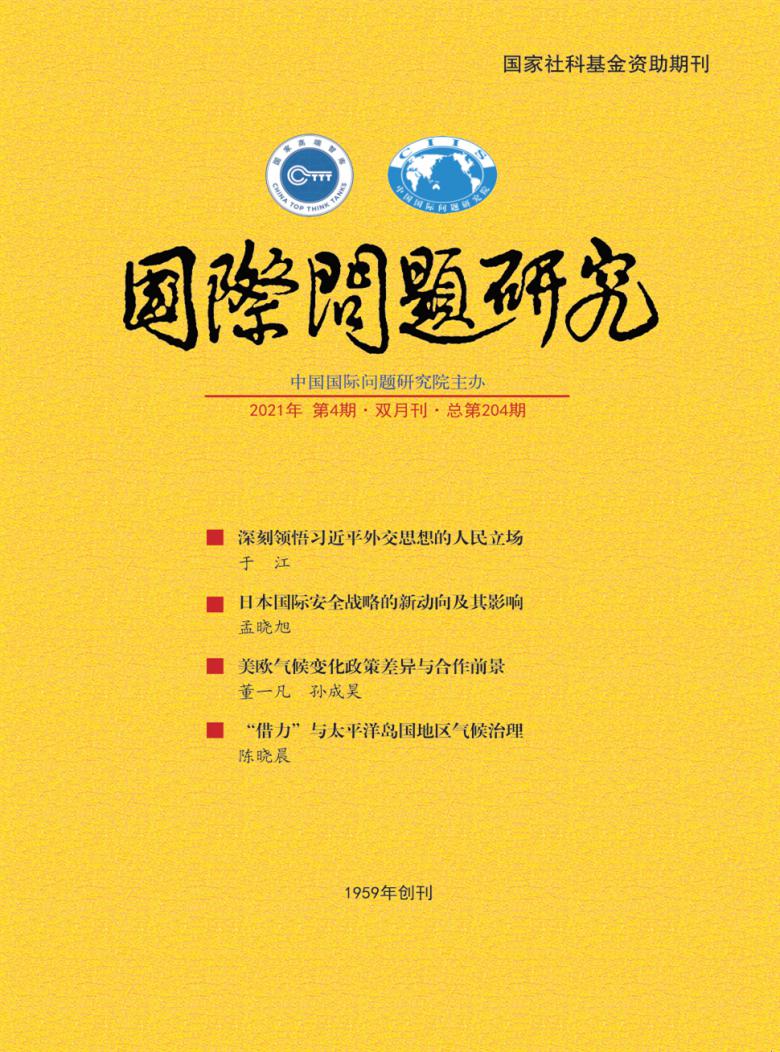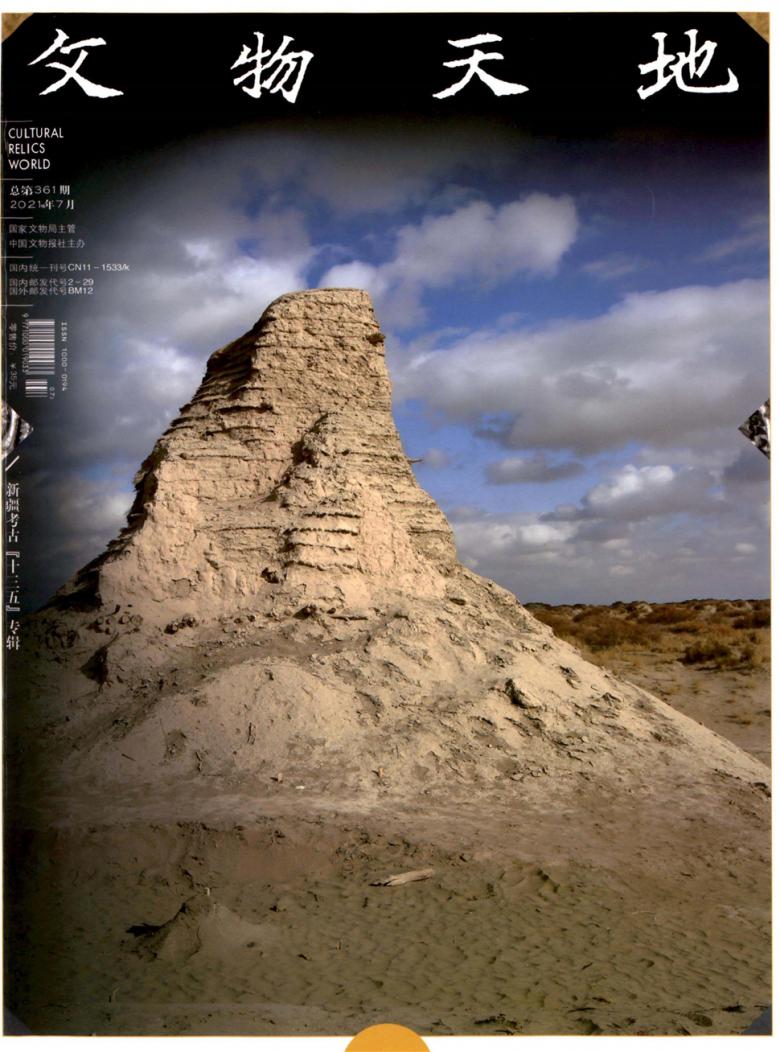关于WTO法中的“冲突规则”——一个相对封闭的WTO争端解决法律适用系统的形成
许楚敬 2011-06-20
关键词: 《WTO协定》/冲突规则/其他国际法
内容提要: 冲突规则的作用在于决定哪些国际法规范应优先适用。但是,《WTO协定》本身没有包含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一般冲突条款,但又不能机械地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且难以有国际公法的冲突规则适用的空间。DSU第3.2和19.2条根本不构成一条冲突规则,而是作为对WTO涵盖协定的过于宽泛的解释的一种制约或限制。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冲突规则隐含在DSU第7.1、7.2、11和19.1条的规定之中。从上述冲突规则可推断,WTO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争端解决法律适用系统,从而排除了实体的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适用。 《WTO协定》对WTO法与其他国际法的关系很少涉及,它没有包含明确规定其与已经存在的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一般冲突条款。由此产生了一些相应的问题,其中有,如果遇到WTO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存在冲突,能否适用国际公法中的冲突规则,比如后法规则和特别法规则解决可能的冲突;WTO法,尤其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中有没有隐含一些处理这类可能的冲突的规则;如果有,哪些DSU条款隐含这类冲突规则,以及这些冲突规则是否排除了其他国际法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适用,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在WTO法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WTO法中明确规定的冲突规则为数不多
冲突规则的作用在于决定哪些国际法规范(除了反映强行法的规范)应优先适用。如果规则的冲突缺乏明确的规则指导,将减少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如果一项条约的规定与另一条约的规定之间存在冲突,关于哪项规定应优先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维也纳公约”)第30条规定了一些指导。该条规定涉及同一事项和相同当事国的条约之间冲突的一个主要的规则是:条约中专门调整与其他条约冲突的具体规定(即冲突条款)必须得到尊重;[1]也就说,如果WTO法中对其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已经作出明确的规定,就必须按照此类冲突规则处理。
但是,《WTO协定》本身对其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冲突很少涉及。[2]它没有明确规定它优先于或者不减损先前存在的其他公约或国际协定。[3]WTO法中明确规定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冲突条款或包含冲突规则的规定大致有: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宪章》的GATT1994第21.3条[4]和关于其他保护知识产权公约的《TRIPS协定》第2.2条,[5]某些有关争端解决的规定,[6]区域贸易安排,[7]以及《WTO与IMF关系的宣言》等。[8]
在WTO争端解决判例中,阿根廷-纺织品和服装案是一个可以用来说明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明确的冲突规则的例子。在该案中,上诉机构审查了专家组认定的违反了GATT1994第8条的一项百分之三的统计税,是否可以借助于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对阿根廷实行的据称冲突的义务予以免除。上诉机构评估了IMF备忘录是否与GATT规则冲突,以及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哪个应优先。上诉机构认为,阿根廷并没有证明其与IMF的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与GATT1994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9]即使有冲突,上诉机构认为,“《IMF与WTO之间的协定》,《WTO与IMF关系的宣言》或者《关于一致性的宣言》中都没有规定……可证明一个成员方对IMF的义务应优先于GATT1994第8条下的义务的结论。[10]上诉机构还认为,仅《WTO与IMF关系的宣言》——构成了《WTO最后文件》一部分的一个部长级会议的决定,而不构成WTO涵盖协定的一部分——规定了WTO与IMF之间的法律关系。该宣言包含一个以GATT规则为准的明确的冲突规则:关于货物贸易,WTO与IMF规则之间的关系应继续由GATT1947的规定管辖,这意味着,只有在这些与IMF有关的措施条款中规定的例外可用于为违反GATT辩解。以这个冲突规则为根据,上诉机构认为,由于在GATT1994本身中,GATT1994第8条下找不到与IMF有关的例外,独立的IMF规则如争论中的备忘录,不能证明阿根廷违反GATT1994第8条是合理的。[11]
总之,WTO法中如果有对其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做了明确规定的,在WTO裁决机构遇到这类冲突问题时,即可做到“有法可依”,按照冲突规则的指引适用法律,使冲突得到及时解决。但是,实际上,WTO法中这类明确规定其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条款为数不多。
二、国际公法中的冲突规则难以有其适用空间
维也纳公约第30条规定涉及同一事项和相同当事国的条约之间冲突的另一个主要规则是:一般情况下,时间上较后的条约应优先于先前关于同一事项的条约,即后法规则。[12]不过,维也纳公约第30条没有提到与条约之间的冲突有关的另一项规则,即特别法规则。虽然这一规则并没有出现在维也纳公约中,但在许多案件中,国际法院已经承认并适用特别法规则。[13]那么,在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上,国际公法的这些冲突规则是否有其适用空间?
(一)后法规则
后法规则(lex posterior rule)到底是否适用于多边条约,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根据维也纳公约第30(3)条,如果后来的所有当事国也是先前条约的当事国,而先前条约并未中止或终止,则仅在其规定符合后来条约规定的范围内适用。因此,当两个争端的国家是涉及同一事项的两项条约的当事国时,应努力调和这两项条约的适用:它们仍然有效,且累积适用,但是应给予后订条约的规定一些优先。如果两项条约存在冲突,而且各当事国显然希望或从两个条约看来当事国显然意图终止先订条约,那么第59(1)条允许第一项条约终止。否则,这两个条约一般继续适用,并且以在后的规定为准,而先前的规定则暂停适用。
对于能否适用后法规则解决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冲突,有学者认为,鉴于在WTO条约本身中没有规定明确的冲突规则,关于如何解决冲突的规则,必须在一般国际法中寻找,例如体现在维也纳公约第30条中的一般国际法。就大多数冲突而言,WTO条约并没有排除这些国际公法的冲突规则,因此,它们也必须适用于WTO规则。如果无法最终确定各当事方的意图,则条约规则之间的冲突必须首先诉诸第30条的后法规则。对于其他冲突(如条约与习惯之间的冲突),这条规则同样适用,因此,任何后来的规则优于先前相抵触的规则。这同样适用于条约与随后的“彼此间协定”之间的冲突,[14]在原先的条约与该彼此间协定的各当事国之间,根据第30(4)(a)条,以后来的规则为准。在受原先条约和彼此间协定约束的一个国家与仅受原先条约约束的另一国家之间,根据第30(4)(b)条,只适用原先的条约,而彼此间协定则不适用。[15]还有学者认为,后法是“国际法的适用规则”,WTO专家组在解释条约,如《WTO协定》时,必须考虑后法规则。后法不仅在条约的规定冲突的情况下使用,而且还在解释条约时,作为规则适用于任何条约的解释,以避免产生冲突的解释。[16]
上述学者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冲突方面,后法规则没有其适用的空间。首先,DSU第3.2条没有提到维也纳公约第30条,因为维也纳公约第30条不是规定条约的解释,而是规定它们的适用规则。在一些争端解决报告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提到了维也纳公约第30条,但并没有适用它。[17]比如,在欧共体-家禽案中,专家组指出,“过去的专家组一直对后法规则适用于关税减让表小心谨慎。”[18]上诉机构也指出,没有必要诉诸维也纳公约第59(1)条或第30(3)条,因为在该案中,《WTO协定》的文本和关于从GATT1947过渡到WTO的法律安排解决了《第80号减让表》与《油籽协定》之间关系的问题。[19]按照维也纳公约第30条,后法优于先法只是在当事国相同的范围内适用。在一个WTO成员方与一个非WTO成员方之间的关系上,只适用它们都受其约束的其他国际法规则。
其次,维也纳公约第30条并没有解决如果一个WTO成员方在履行对第三国义务或者在行使其他条约授予的权利而被迫偏离WTO法时,应适用哪些法律的问题。在WTO范围内,WTO的法律权利或义务不可能让位于源自先订的条约的义务或权利;在WTO争端解决中,不得以行使非WTO法中包含的特权或履行非WTO法中包含的义务,为违反WTO法辩解。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只具有有限的职权,只有在WTO法中有提到或纳入的情况下,它们才被允许适用非WTO法。在WTO争端解决中,绝不能执行非WTO法产生的权利或义务,[20]因为这将导致减少或增加WTO涵盖协定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至于WTO规则提到或纳入的非WTO法,由于它们与WTO法在同一时间生效,因此也没有第30条适用的空间。[21]
最后,维也纳公约第30条也不宜适用于《WTO协定》与在其之后生效的其他条约的关系,其理由有二:其一,维也纳公约第30(4)条由于第30(5)条而可能不适用,因为彼此间修改WTO协定可以被认为是影响其他WTO成员方的权利,而且,根据维也纳公约第41(1)条,这种彼此间修改不符合《WTO协定》的目的和宗旨,因为它是一揽子交易。其二,第30条的适用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一方面,取决于加入WTO的日期;另一方面,取决于时间在后的条约生效或通过的日期。[22]那种认为时间在后的条约将仅在争端各方之间改变WTO协定而不影响到其他方的权利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有悖于WTO法作为一揽子承诺的观念。WTO成员方只有按照《WTO协定》第10条规定的程序才可以这样做。[23]
因此,在国际法中,关于先后规则之间的冲突,后法规则的适用是有限度的。尽管在涉及那些属于有机构性联系或试图促进同样目标的条约(即形成同一制度的一部分)的冲突和重叠的规定方面,后法规则的作用最大,但是,当不同制度的条约之间出现冲突或重叠时,哪一个在时间上靠后的问题不能用来表明它们之间固有的优先顺序。[24]总之,不能机械地适用维也纳公约第30条,在WTO法与非WTO条约之间的关系上,不存在后续的关系,也不存在后法规则适用的空间。
(二)特别法规则
特别法的格言起源于罗马法,它是一个公认的法律解释的格言和解决规则冲突的技术。尽管很难把特别法称为一个有具体内容的规则,但是,该规则背后的理由是明确的:适用最具体的规则是为了落实各当事方的意图,并考虑案件的特殊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同意的表示。因此,特别法的适用把注意力指向各当事方的同意和意图,尤其适合于解决条约冲突。[25]适用特别法,可以有效地减损一般规则,这已被国际法院证实了。[26]
在WTO争端解决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偶尔也借助特别法规则解释WTO协定。[27]但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仅在WTO体制内适用特别法规则,即在涵盖协定的范围内,在两个单独的协定之间或在一项协定的文书内。[28]不过,WTO体制内部的冲突主要通过条约解释得到解决,特别法只是作为解决冲突的一个有限和辅助的解释工具和最后手段。但是,对于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冲突,特别法的适用是令人怀疑的,尽管有学者主张特别法规则可适用于WTO条约与其他条约之间的关系。例如,他们认为,如果WTO条约与作为特别法的其他条约,比如多边环境协定发生冲突,该多边环境协定应优先适用。因为它们构成一项特别法,即使它们在时间上先于有关WTO协定。否则,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将永远无法适用多边环境协定,如果这意味着增加涵盖协定下的义务或减少权利的话。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本来可以适用这些协定中的法律,如果它们与争端的事项是有关的。[29]
也有学者认为,在适用特别法规则时,第三方(是WTO的成员方,而不是多边环境协定的当事国)不能主张违反了WTO规则,以质疑多边环境协定的贸易措施。多边环境协定在有关事项方面显然比关贸总协定更具体。根据特别法规则,通常是假设两项协定中更具体的协定优先,即使更一般的协定时间在后,按照这种规定,每当WTO成员方签署了一项多边环境协定授权其他成员方对其实施贸易限制,WTO的规定就应该让位。签署这样的协定的WTO成员,可以很合理地被视为放弃其反对这种贸易限制的法律权利。[30]还有学者认为,WTO成员方可以缔结可能对WTO条约有影响的新条约。这些新的条约可能只是补充或确认原先的规则,但它们也可能终止或暂停WTO规则,或者与WTO规则相抵触。如果它们与现有WTO规则冲突,新的条约规则可以优于相抵触的WTO规则,反之亦然。一切将取决于一般国际法中规定的冲突规则。当然,只有同意新条约的WTO成员才受其约束。不是新条约缔约国的WTO成员方的权利和义务不得受到影响(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由于WTO条约没有规定排除关于彼此间修改的一般国际法规则,比如特别法。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依赖于”这些一般国际法规则。如果环境规则与WTO规则(例如,GATT第3条和第20条)之间相冲突,适用一般国际法的有关冲突规则解决;如果可适用的冲突规则(例如特别法)确定环境规则优先,上诉机构有责任不适用相冲突的WTO规则。[31]
然而,将特别法适用于规范关系往往不明确的国际法律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在国际法中,一项条约明确规定其与先前的、当前的和将来的所有条约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少见的;确定其与其他国际法的关系,更为罕见。虽然特别法规则非常适合于一个单一的条约内或具有相互关系的条约之间的规则冲突的解决,例如由《欧洲人权公约》及其议定书或WTO管辖的条约制度。这是因为在一个条约内或同一制度内的若干协定,在两个规则之间存在逻辑关系:一个为一般的规则,另一个是具体的规则。[32]但是,特别法的适用也是有限度的,它不适于解决彼此独立的规范秩序之间的冲突,如贸易法、海洋法、人权法、环境法等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的“危险的冲突”。它几乎没有独立的“规范力量”,无法提供任何标准以决定一个法律领域是否比另一法律领域更重要或更特别,更难以建立一个优先顺序。[33]此外,特别法并不是一项实体的国际法规则,可能无助于确定相对于更一般的规则哪项规则是特别的。在确定来自不同法律领域的规则,如环境规则与贸易规则之间的关系上,特别法难以发挥其作用。这个问题已经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被提出了,该案的上诉机构认为,预防原则并没有凌驾于有关条约的明确规定,其对WTO也不具有约束力,不论该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处于什么地位。[34]
总之,尽管特别法规则在解决WTO体制内部不同规则之间冲突时具有有限的作用,但是,在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冲突方面,特别法规则却难以发挥其作用,因为这种跨体制的冲突本身关系复杂和混乱,难以用特别法确定哪些规则是特别的。
三、DSU中隐含的“冲突规则”排除其他国际法的适用
在WTO法与其他国际法发生冲突的场合,哪个规则优先,或者说哪个最终必须适用?当有明确的冲突规则存在时,比如,《联合国宪章》第103条、[35]NAFTA第103条,[36]这个问题最容易回答。但是,如前所述,在WTO法中这类明确的冲突规则为数不多。不过,在DSU中还可找到一些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隐含的“冲突规则”,而且,在WTO争端解决中适用这些冲突规则的结果是排除了实体的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适用。
(一)DSU第3.2和19.2条并非冲突规则
DSU并没有对WTO涵盖协定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的、直接的规定,但一些学者还是试图从DSU的一些规定中“挖掘”出有用的冲突规则,比如,DSU第3.2条和第19.2条。按照这些条款,争端解决机构(DSB)、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建议、裁决或调查结果不能增加或减少涵盖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上述规定被这些学者认为是一条限制WTO裁决机构适用法律的冲突规则。有学者认为,在WTO涵盖协定的规定与任何其他可适用的法律之间冲突的情况下,该规则的功能是确保以涵盖协定的规定为准。其结果与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3(1)条是相同的,[37]尽管其也认为这一规定并不是一条正常的冲突规则,但是这一规则以这种间接的方式起作用,而不是直接确定WTO争端解决中可适用的实体法,它达到了实际的冲突规则确保某些协定规定的“法律”优先的目的。该学者还指出,第3.2和19.2条规定的“冲突规则”至今已在WTO的许多案件中适用了,尽管还没有提到其在这些规定中的来源。例如,该冲突规则可用来处理涵盖协定与习惯国际法、其他国际协定之间的潜在冲突。[38]一旦一项WTO义务已被确定,第3.2和19.2条中的冲突规则将起到排除非WTO的权利和义务适用的作用。此外,基于这条“冲突规则”的存在,甚至都不必援引维也纳公约第30条了,如果在WTO范围内条约冲突的适用规则已规定在第3.2和19.2条中的这个主张被接受了的话。[39]
不过,对于DSU第3.2和19.2条,另有学者做了不同的解读。其认为,DSU第3.2和19.2条的目的并不在于限制专家组可适用的法律,也不在于处理WTO涵盖协定与所有过去和未来的法律之间的关系。相反,它们处理WTO专家组在解释WTO涵盖协定时必须遵守的固有的限制。在行使解释的司法功能时,专家组可以澄清WTO涵盖协定的规定,但它们不能“增加或减少涵盖协定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换一种说法,作为司法机关,专家组不可以创设新的权利和义务,而必须适用WTO成员方同意的法律。而且,关于专家组职能的这个限制是为格外谨慎起见而规定的。即使没有这项规定,专家组仍将受到一般国际法规定的司法职能固有的限制。一个国际法的法院不可以一般和事先排除考虑除了那些被请求执行的法律以外的国际法规则。在1994年以前或以后的其他法律与WTO规则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不必始终以WTO规则为准。DSU第3.2和19.2条的这些规定不应该被解释为专家组、上诉机构和DSB在适用非WTO的其他国际法时,始终都不能增加或减少WTO涵盖协定明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40]规定司法机构怎样对待法律与规定立法机关(即WTO成员方)怎样对待法律相去甚远。第3.2条规定,WTO司法机构,像任何其他司法机构一样,不能“改变”WTO条约。但是,这并不限制WTO成员可以缔结的或已经缔结的影响它们相互的WTO权利和义务的其他条约的范围。[41]
对此,笔者认为,在第3.2和19.2条中的这项规定,连一条“不正常的冲突规则”都谈不上。它根本就不是一条冲突规则,它只是起到限制WTO裁决机构司法能动的作用而已,而非一项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冲突的规则。实际上,“增加或减少涵盖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禁止应被解读为限制WTO裁决机构澄清涵盖协定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不得逾越职权,或者说,是作为对涵盖协定的过于宽泛的解释的一种制约或限制。在WTO争端解决中适用和解释涵盖协定的现有规定时,第3.2和19.2条可用来防止WTO裁决机构解释法律时逾越权限,使WTO成员方精心构筑的权利义务平衡受到破坏。因此,把第3.2和19.2条的规定“上升”为拒绝适用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冲突规则的“高度”,实乃牵强附会。此外,一方面认为,DSU第3.2和19.2条中的规定应被解释为在澄清WTO涵盖协定的现有规定时,专家组、上诉机构和DSB不能增加或减少WTO涵盖协定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又认为,WTO裁决机构可以适用其他国际法,这些非WTO国际法规则可以优先于WTO规则,从而改变WTO成员方在涵盖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这显然是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无论如何,第3.2和19.2条中的规定不应被解读为是一条排除其他国际法适用的冲突规则。
(二)DSU第7.1、7.2、11和19.1条是冲突规则
有些学者认为,WTO争端解决中可适用的法律不只包括WTO涵盖协定,并且解决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冲突的冲突规则来源很广泛。这些冲突规则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找到:非WTO条约、WTO条约本身,以及一般国际法。DSU不能被解读为排除援引WTO涵盖协定以外的国际法,也不能被解读为包括一个始终以WTO涵盖协定为准的一般和自动的冲突条款。[42]WTO条约的起草者们本来可以插入一个类似于《联合国宪章》第103条的冲突条款,规定WTO条约优于所有过去和未来的国际法。如果起草者希望WTO条约优于所有其他法律,它们不会这样做吗?例如,它们不会在《WTO协定》中设置一个“不减损条款”,反而要在技术文书DSU中作出规定吗?而且,DSU或任何其他WTO规则都没有规定排除专家组处理并视情况而定适用其他国际法规则。WTO条约和DSU不需要明确提到或确认所有其他可能适用的有关国际法规则,无论它们是在1994年以前或以后。基于DSU是在更广泛的国际法背景下创制和继续存在这个简单事实,这种引用或确认自动发生,其他国际法规则自动适用,除非DSU或任何其他WTO规则已排除了它们。[43]从DSU第7条第1和2款明确提到一些法律(即WTO涵盖协定)推断所有其他法律因而被暗示地排除,是错误的。相反,第7.1和11条暗示在审查WTO申诉时专家组可能被要求援引和适用其他国际法规则。DSU中提到的诉诸涵盖协定不能被理解为排除其他法律。[44]另有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立场,其认为,在DSU下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可以由WTO裁决机构适用和执行;[45]这么多次具体提到涵盖协定作为WTO争端解决中可适用的法律,如果成员方还希望非WTO法是可适用的,将是很奇怪的。[46]
笔者认为,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潜在冲突的冲突规则,除了前述提到的WTO法中为数不多的规定以外,在DSU第7.1、7.2、11和19.1条的规定中还隐含着冲突规则。尽管DSU并没有对“可适用的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DSU第7.1条规定了专家组的职权范围,并指示其“按照”争端各方引用的涵盖协定的“有关规定”审查提交给它们的事项。第7.2条规定专家组有义务“处理争端各方引用的任何涵盖协定的有关规定”。第11条更是明确规定专家组“应对其审议的事项作出客观评估,包括……有关涵盖协定的适用性和与有关涵盖协定的一致性的客观评估”,该条可谓“白纸黑字”,只提到“有关涵盖协定的适用性”和“与有关涵盖协定的一致性的客观评估”,因此,可将其理解为完全排除了其他国际法的适用性以及与其他国际法的一致性的客观评估。第19.1条也明确规定,如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认定一措施与一涵盖协定不一致”,则应建议有关成员方使该措施符合该协定,这里指向的仍然是“一涵盖协定”,而非其他国际法。上述这些规定从“按照争端各方引用的涵盖协定的‘有关规定’审查”,到“处理争端各方引用的任何涵盖协定的有关规定”,最后落到“评估(或认定)与有关涵盖协定的一致性(或不一致)”上,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WTO争端解决法律适用系统就形成了。
总之,DSU第7.1、7.2、11和19.1条中的规定应该被解读为是避免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潜在冲突的隐含的冲突规则。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它们明确地完全排除了来自国际法其他领域的实体规则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适用,也就是说,在WTO争端解决中唯一可适用的实体法是WTO涵盖协定的规定。
四、结语
冲突规则的作用在于决定哪些国际法规范应优先适用。但是,《WTO协定》本身没有包含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一般的冲突条款。在WTO法与非WTO国际条约之间的关系上,不存在后续的关系,也不存在后法优先的问题。即使是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也不能适用其他国际法。对于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冲突,特别法规则的适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法规则不适于解决彼此独立的规范秩序之间可能存在的“危险的冲突”。也就是说,在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冲突方面,难以有国际公法的冲突规则适用的空间。在WTO法中,用于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除了明确规定的冲突条款以外,在DSU中还可找到一些隐含的“冲突规则”。不过,第3.2和19.2条并不是一条冲突规则,它只是起到限制WTO裁决机构司法能动的作用而已。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冲突规则隐含在DSU第7.1、7.2、11和19.1条的规定中。从上述规定可以推断,WTO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争端解决法律适用系统,而这个法律适用系统主要是由上述冲突规则构建起来的。 注释: [1]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2条规定:“本公约的规定不得影响任何缔约国在任何现行国际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除非行使这些权利和义务将严重破坏或威胁生物多样性。” [2]WTO体制内部的不同规则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不过,当WTO各涵盖协定中的两个规则发生冲突时,WTO条约有一系列应以何者为准的规定。例如,《WTO协定》与任何多边贸易协定(如GATT、GATS、《TRIPS协定》和DSU)之间产生抵触时,必须以《WTO协定》为准。在GATT1994与《WTO协定》附件1A中的货物贸易的另一协定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以另一附件1A的协定为准。 [3]与之相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11条明确规定了公约与其他公约和国际协定的关系。 [4]GATT1994第21.3条规定:“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3.阻止任一缔约方为履行其在《联合国宪章》项下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而采取的任何行动。” [5]《TRIPS协定》第2.2条规定:“本协定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的任何规定不得背离各成员可能在《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和《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条约》项下相互承担的现有义务。” [6]《SPS协定》第11.3条规定:“本协定中的任何内容不得损害各成员在其他国际协定项下的权利,包括援用其他国际组织或根据任何国际协定设立的斡旋或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利。” [7]GATT1994第25条;GATS第5条。 [8]该宣言规定,GATT1994的规则优先于IMF规则,除非GATT1994本身另有规定。 [9]See Argentina–Textiles and Apparel,WT/DS56/AB/R,para.69. [10]Id.,para.70. [11]Id.,paras.69-74. [12]参见维也纳公约第30(3)、30(4)和59条。 [13]See Mav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s,PCIJ(ser.A),No.2,pp.30-31;Chorzow Factory,PCIJ(ser.A),No.9,p.30;European Commission of the Danube,PCIJ(ser.B),No.14,p.23;Rights of Passage Case[1960]ICJ Rep.,p.6. [14]所谓彼此间协定(inter se agreement),是指多边条约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国(而不是在所有条约当事国之间)缔结的在它们彼此间修改条约的某些规定的协定。 [15]Joost Pauwelyn,The Rol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WTO:How Far Can We Go?,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5,No.3,2001,p.545. [16]Gabrielle Marceau,Conflicts of Norms and Conflicts of Jurisdiction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TO Agreement and MEAs and other Treaties,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35,No.6,2001,p.1095. [17]See US-Section 110(5)Copyright Act,WT/DS160/R,para.6.41;Japan–Film,WT/DS44/R,para.10.65;EC–Poultry,WT/DS69/AB/R,para.79. [18]See EC-Poultry,WT/DS69/R,para.206. [19]Id.,para.79. [20]See EC-Hormones(US)(Article 22.6–EC),WT/DS26/ARB,para.50. [21]Wolfgang Weiss,Security and Predictability under WTO Law,World Trade Review,Vol.2,Issue 2,2003,pp.213-214. [22]例如,A国在1999年签署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随后加入了WTO,以WTO规则为准;而对B国来说,作为WTO创始成员方,却以该议定书为准?或者反过来,比如,对C国来说,一个只在1997年加入了《气候变化公约》的WTO成员方,该公约优先于WTO规则;而对D国而言,一个在1992年《气候变化公约》缔结时同意它的WTO成员方,以WTO规则为准吗?这岂不是荒谬的结论?参见前注[15],Joost Pauwelyn文。 [23]参见前注[21],Wolfgang Weiss文。 [24]See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the ILC,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U.N.Doc.A/CN.4/L.702,18 July 2006,paras.25-26. [25]See Paul Reuter,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reaties,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5,pp.132-133;Ian Sinclair,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2nd.ed.),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pp.114-115. [26]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我们十分理解,在实践中,可以通过协定,在特定情况下或特定当事方之间,减损(一般)国际法的规则。”See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s(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Denmark and Federal Republic ofGermany v.Netherlands),ICJ Reports 1969,para.472.在大陆架(突尼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案中,国际法院指出,“在特别协定中各当事方确定海洋法的某些具体发展,无疑是可能的。在特定情况下,在它们的双边关系中,这些规则应作为特别法具有约束力。”See 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Tunisia v.Libyan Arab Jamahiriya),ICJ Reports 1982,para.24. [27]See Brazil-Aircraft,WT/DS46/R,para.7.40;Turkey-Textiles,WT/DS34/R,para.9.92;Indonesia-Autos,WT/DS54/R,WT/DS55/R,WT/DS59/R,WT/DS64/R,paras.14.28-14.34. [28]在欧共体—香蕉案(三)中,上诉机构指出,专家组应在审查一般规定之前审查特别规定。See EC-Bananas III,WT/DS27/AB/R,para.204.美国-反倾销法(日本投诉)案的专家组则认为,欧共体-香蕉案的上诉机构适用了特别法规则。See US–1916 Act(Japan),WT/DS162/R,para.6.269. [29]Lorand Bartels,Applicable Law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edings,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35,No.3,2001,p.500. [30]See R.Hudec,GATT Legal Restraints on the Use of Trade Measures against Foreign Environmental Practices,in J.Bhagwati&R.Hudec,Fair Trade and Harmonization:Prerequisites for Free Trade?,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Vol.2,1996,p.121. [31]参见前注[15],Joost Pauwelyn文。 [32]See Anja Lindroos,Addressing Norm Conflicts in a Fragmented Legal System:The Doctrine of Lex Specialis,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74,2005,p.41. [33]Id.,pp.65-66. [34]See EC-Hormones,WT/DS26/AB/R,WT/DS48/AB/R,paras.123-125. [35]《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 [36]NAFTA第103条规定:“……2.如果本协定与其他协定不一致,本协定优先,除非另有规定。” [37]该条规定国际海洋法法庭适用“与本公约不抵触的其他国际法规则”。 [38]比如,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上诉机构认为,“预防原则并不优先于《SPS协定》第5.1和5.2条的规定”。See EC–Hormones,WT/DS26/AB/R,WT/DS48/AB/R,para.125.同样,在危地马拉-反倾销案中,专家组指出,在WTO范围内,被申诉方主张的国际公法习惯规则中的“无害的过错”是非法的。See Guatemala–Cement I,WT/DS60/R,paras.7.40-7.41. [39]参见前注[29],Larand Bartels文。 [40]参见前注[15],Joost Pauwelyn文。 [41]Joost Pauwelyn,How to Win 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ispute Based on Non-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aw?Questionsof Jurisdictions and Merits,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37,No.6,2003,p.1003. [42]参见前注[15],Joost Pauwelyn文。 [43]参见前注[15],Joost Pauwelyn文。 [44]See Lorand Bartels,supra note 29,pp.499-519;David Palmeter&Petros C.Mavroidis,The WTO Legal System:Sourcesof Law,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2,No.3,1998,p.399. [45]Gabrielle Marceau,A Call for Coher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Praises for the Prohibition Against“Clinical Isolation”inWTO Dispute Settlement,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33,No.5,1999,p.87,110. [46]Joel P.Trachtman,The Domain of WTO Dispute Resolution,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40,No.2,1999,p.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