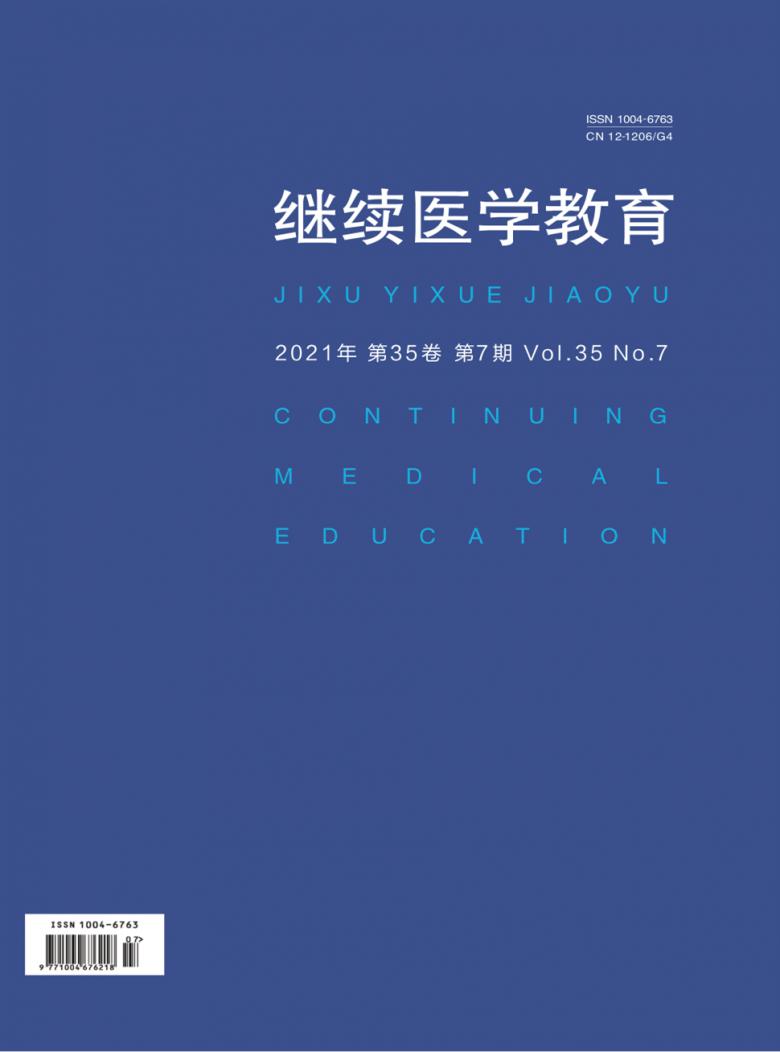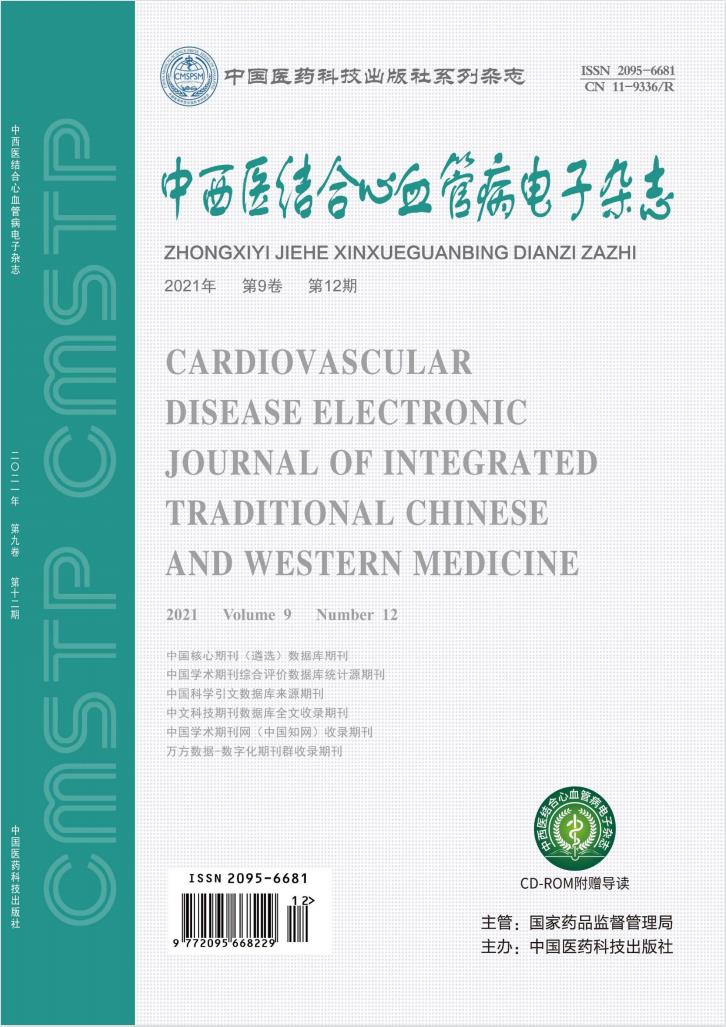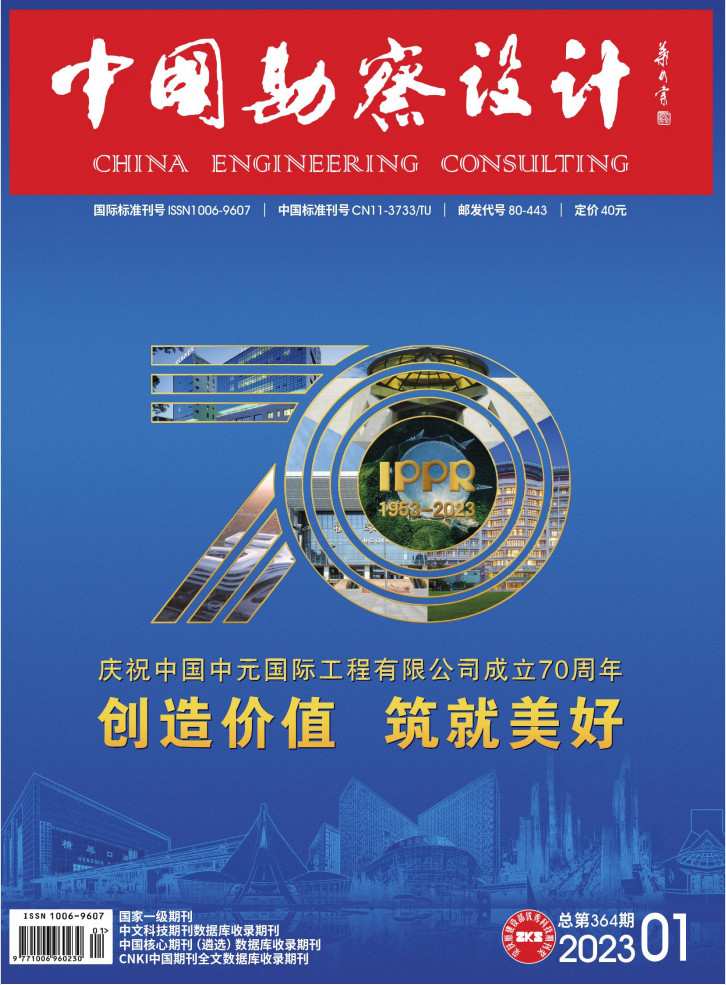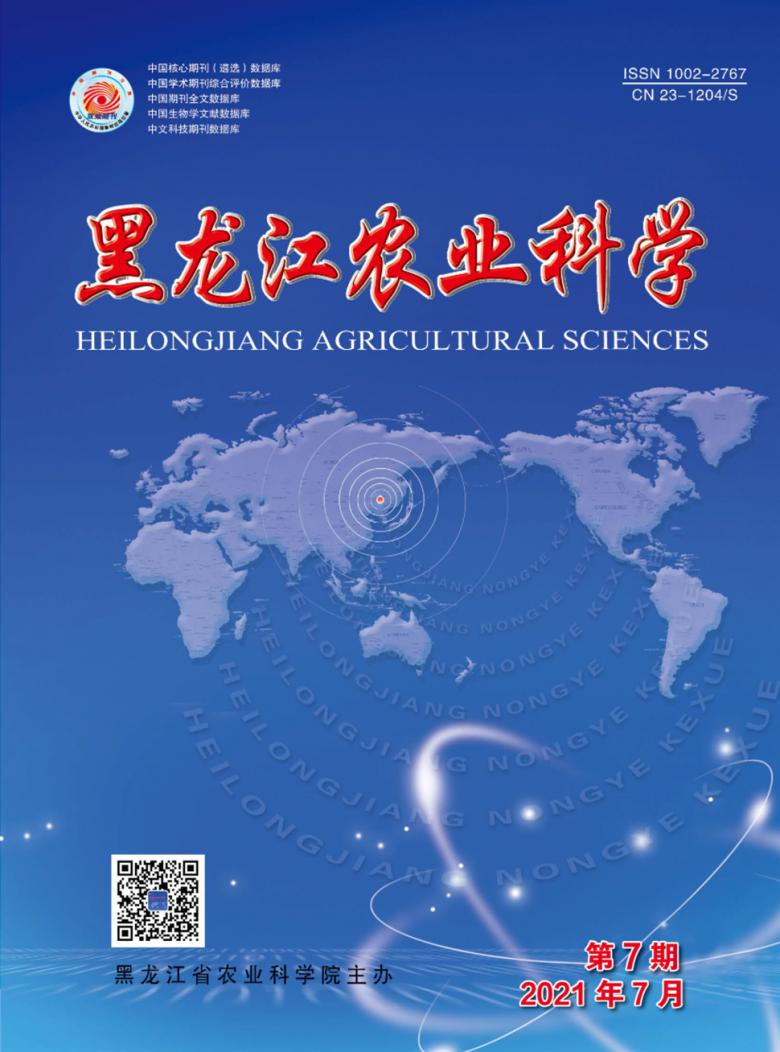协商民主:执政党主导的民主化进程的选择性亲和
黄晗 2009-09-09
[论文关键词]协商民主 执政党 选择性亲和
[论文摘 要]通过从民主化理论的微观视角来研究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从执政党应对转型时期的重叠危机,探索民主的程序化价值以实现体制内渐进民主化以及发挥组织化治理资源优势增进有效治理几个方面论证执政党在推动协商民主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协商民主是执政党主导民主化进程的选择性亲和,协商民主的发展是执政党主导的渐进、可控的民主化思路。
协商民主是这样一种民主:在共同体中的各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议来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审视他人的偏好及其相关理由,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及普遍利益的实现。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的壮大及批判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于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达到了高潮。我国目前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做规范性阐释,或者把协商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得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乐观派认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日益发育,公民政治意识逐步觉醒,协商民主将会成为中国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些人则基于对公民参政意识、公民社会成长的制度空间等的质疑得出悲观的结论。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还是基于对协商民主的规范性理解,对政治转型的功能性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没有深刻得理解和把握协商民主的实质内涵,因而也就不能准确预测其发展前景。本文力图对协商民主进行经验研究,用“选择性亲和”来定位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从而透视转型时期执政党主导的民主化进程的基本逻辑和理路。
一、协商民主:执政党应对转型时期重叠危机的民主机制
美国学者卢西恩·W·派伊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不稳定状态概括为六大危机:一是认同的危机,即刚取得独立的国家还没有形成政治一体化。二是合法性危机,即政府权威与职责合法性由上认同危机的存在而经常遭到质疑。三是贯彻危机,即政治体制不健全,政策难以实现。四是参与危机,即政治体制不健全,制度化水平低新生政治集团很难通过制度化渠道进入政治;五是一体化危机,即整合危机,指难以将民众参与与政府绩效统一起来,以解决参与危机及贯彻危机。六是分配危机,即政权无力解决转变时期的分配问题[1]。我国学者吴辉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以上危机可集中概括为整合危机、参与危机和合法性危机。
有效解决参与危机,关键的是要建立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亨廷顿认为:“任何一种政体的稳定性都取决于参政水平与政治制度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要想维持政治稳定性,必须在参政扩大的同时,使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连续性随之增长。”[2]他将政治制度化水平低而参政水平高的政治体系形容为各种社会力量都按自己的方法直接在政治领域内活动的政治体系,即“执政官体系”;将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高于参政水平的政治体系称之为公民政体。“在大众社会中,参政是非结构性的不规则的、零乱多样的,每一种社会力量都试图通过自己最擅长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冷漠与愤慨情绪交替出现,而在参政型政体内,高水平的群众参与是通过政治体制而组织起来的,是结构性的,各社会力量必须将它的力量来源和行动方式转变为这一政治体系中的合法制度化力量来源及行动方式,参政必定是广泛的,而且是通过合法渠道组织起来的结构化了的。”[3]为此,亨廷顿提出了其著名的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制度的确立往往滞后于现实社会的变革,体制内提供的渠道很难满足新的问题及要求,由于体制渠道的封闭,民众通常利用反体制、反现行政策的社会运动形式来表达其要求。近年来,城市社区组织及农村村民越来越多地运用上访、请愿、游说,甚至游行、静坐、示威、围堵党政机关等激烈手段,要求有关职能部门解决与本地居民的切身利益相关的拆迁、治安、环境、就业、服务等政策问题,这是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于政治参与度的典型表现,这种状况如果长期积累就容易导致参与危机的弥散。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为公民参与开辟了一条结构化的途径,通过信访制度、听政会制度、民主恳谈会制度、工青妇系统等各种形式,民意得到了有效的疏导和传递。
同时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权威的树立,权力的积累是十分重要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经济上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在政治上则需要高度的共同性、一致性,因此,它在政治民主上的取向主要是效率的而不是政治的。事实上不仅是一党制国家要么继承了一个政治化了的社会,要么促进了一个社会的政治化,和多元制政治实体相比,它们更需要一个普遍政治化了的社会,一党制是排它的,因而它更尖锐地面临自我辩护及自我肯定的难题,故而一党政体不能简单指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获得合法性,它们必须表明它们能够比多党政体做得更多、更好、更快。因此指政党和国家必须具备超强的整合能力,有效地实现价值观念的整合,化解冲突,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协商民主强调在充分深入的参与和讨论之上形成偏好的转换和社会共识性的达成,因而在整合社会意识,实现政治共同性,从而降低政治改革和公共政策的成本上具有强大的功效。
二、协商民主:治理资源约束下的理性选择
如何进行民主而有效的社会治理是执政党在社会层面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应该是一个规范化、法治化的社会,国家对社会的治理遵循的是制度化的渠道。然而目前我国执政党面临的一个基本现状是制度性治理资源的贫弱。如果全部依靠制度化的治理则容易导致对有限的制度资源大量的消耗,一旦超出制度的承载力,则会导致治理危机的爆发。因而理性的选择是通过组织化的治理对治理对象进行一定的拦截,减少制度化治理的压力,实现有效治理。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建立和扩大自身的组织网络及建立自身的组织体系,夺取国家政权并彻底改造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政权进而构建国家的治理体系的。执政党拥有完善的组织网络体系、深厚的社会基础,党组织网络渗透至基层各个角落,覆盖了各个政府层级,各个社会领域及行业,国家全部的治理空间,整个社会都被纳入这样一个组织网络之中。可见,组织化治理资源是执政党治理的最大优势资源。协商民主实际上为执政党释放其强大的组织功能,进行对社会的组织化调控、组织化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协商民主在社会层面的各种制度如上访、听证、调解等虽然是一种结构化的民主渠道,但它们又具有散点式、机动性、细致性、亲和性等一些特点,协商民主提供一个协商场所供各利益主体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协商,最后实现由执政党主导局部性地消解问题,而不是诉诸制度化治理渠道,避免社会矛盾的固化和分歧的弥散。因而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执政党发挥其组织治理优势,避免制度化治理资源劣势的一种理性选择。
同时,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执政党组织及其外围组织对社会各种利益主体的一种“说服”。通过协商民主的各种形式,执政党的各种政策被给予修正,但更重要的是政策获得了更牢固的合法性。执政党组织对大众的说服是通过其对协商民主议程的掌握和其知识、技术、信息的显著强势地位实现的。2002年1月12日铁路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这次听证会上,固定代表中市各政府部门代表占10人,专家占5人,他们全部来自人大或政协,群众占4人。政府人员比例高达51%,当选代表33人,其中消费者占12人,来自工人、农民、外出务工人员、教师、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等各个民主体。经营者代表7人,来自各省铁路局。此外是来自国务院发展中心、国务院法制办、经贸委、交通部、社科院、大学等的专家代表。[4]听证会上群众甚至没有全部发言,听证会实质变成了专家的论证会。同时政府在选择代表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意愿,在该听证会上,河北律师乔占祥在春节期间因火车票上涨的行政议程状告铁道部,他也报名参加这次听证会,但被消费者协会以某些理由排除。林尚立评价听证会制度时认为:“听证会制度从产生的社会根源来看,其实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的一种权衡过程,主要功能应是通过相关者的民主参与来引起社会强势对社会弱势利益的关注,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的限制,听证会也许从根本上不能解决问题,但通过它可以使一定历史阶段的利益分配得以顺利实现,为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赢得有利条件。要赢得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最为关键的是要使社会成员对利益冲突得以接受。[5] 三、协商民主:执政党主导的民主化进程的程序价值亲和
林尚立认为:“作为一种政治形式,民主政治实际上由三大要素构成,即价值、制度、程序。价值决定民主的政治目标和合法性取向,制度决定民主政治的结构及功能,程序决定民主政治运行的方式及手段。”[6]价值、制度、程序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价值与制度确定的情况下,程序的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价值和制度的实现程度。他继而认为在多元化已成事实非竞争性民主已无立足之地的当今社会,竞争和协商是民主程序的两种主要价值取向。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民主的程序性价值总是要受到其价值、制度的规定性限制。其中国家的政党制度架构对民主程序性价值的限定尤为明显。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制度架构是竞争性政党制度,它假定政党只有在竞争性选举制度中才获得其合法性,并且将自身的行为限定在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范围内从而实现民主宪政的。这种制度的竞争性取向决定了其民主程序的竞争性。而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架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强调执政党的主导地位,其民主更多的体现为执政党一元化集中领导及权威统合下的咨询式的民主。不主张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形式。 从民主化进程的视角看,协商民主的发展表现出其对于政治协商制度的一种“路径依赖”。陈尧认为:历史上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结构或限制或助成可供选择的民主方案,它们可能决定了可供决策者去考虑的选择方案,也即显示出一定的“路径依赖”,正确的战略选择只能在过去、现在的客观情势相结合中才能进行,在客观条件中所创造的各种可能性或社会中去选择。”[7]然而,这种“路径依赖”背后蕴涵的却是执政党主导的体制内渐进民主化的思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协商民主从本质上讲是主体政治力量与次主体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体现为执政党的权威性统合和对各参政党的咨询性协商。它是一种国家政治架构层面上的力量协商机制。
四、基本结论
中国协商民主生长、发育的生态环境与协商民主应然的环境呈现出巨大的不对称性,因而,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不能用功能主义方法来理解。中国协商民主一方面强调民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并作为一种结构化渠道缓解了转型时期执政党面临的参与危机及决策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协商过程中的公共理性及协商结果的共识性,契合了转型时期执政党进行社会整合的需求,因而它是有效应对转型时期重叠危机的有效民主形式;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程序性价值的一种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制度架构,决定了中国民主的程序性价值取向不是竞争性的,而是协商性的,从政治协商向协商民主的过渡和推进体现了执政党体制内渐进民主化的道路选择;而在社会治理层面,协商民主为执政党发挥其组织化治理资源优势对社会进行有效民主治理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它是执政党制度性治理资源薄弱而组织性治理资源雄厚的条件限制下的理性选择。
[1] Cf.Lucian W·pye,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Little,Brown and Company ,Inc,1966,pp.62-7
[2] [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 北京:三联书店, 1989第43页
[3]同2 第97页
[4]林尚立,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 :中国的探索[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第187页
[5] 同4 第194页
[6]林尚立,协商民主:对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一种思考[C] 学术月刊 2003年第4期
[7]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