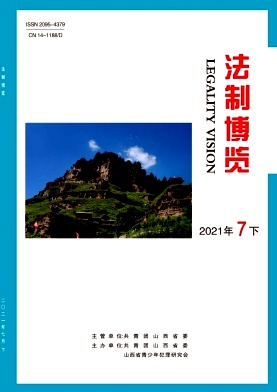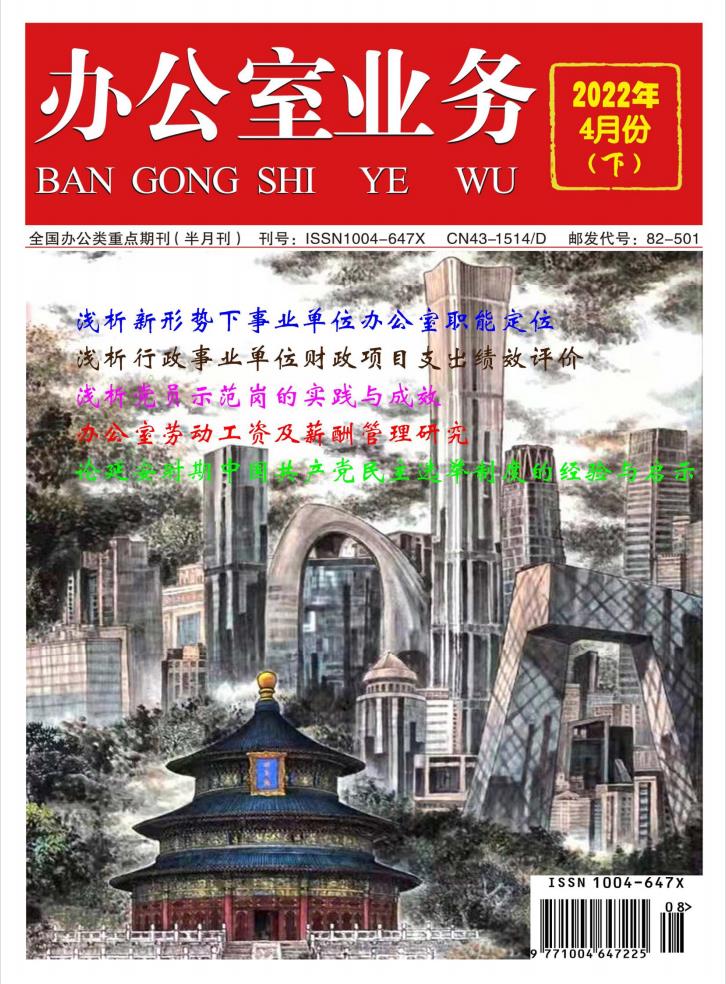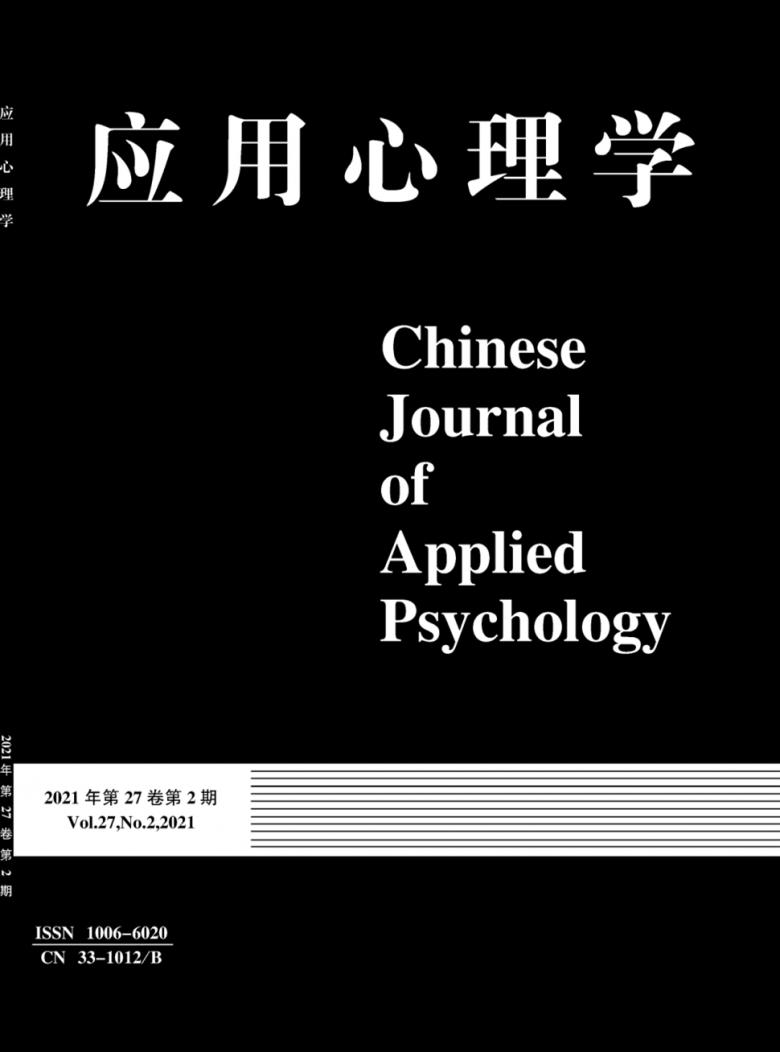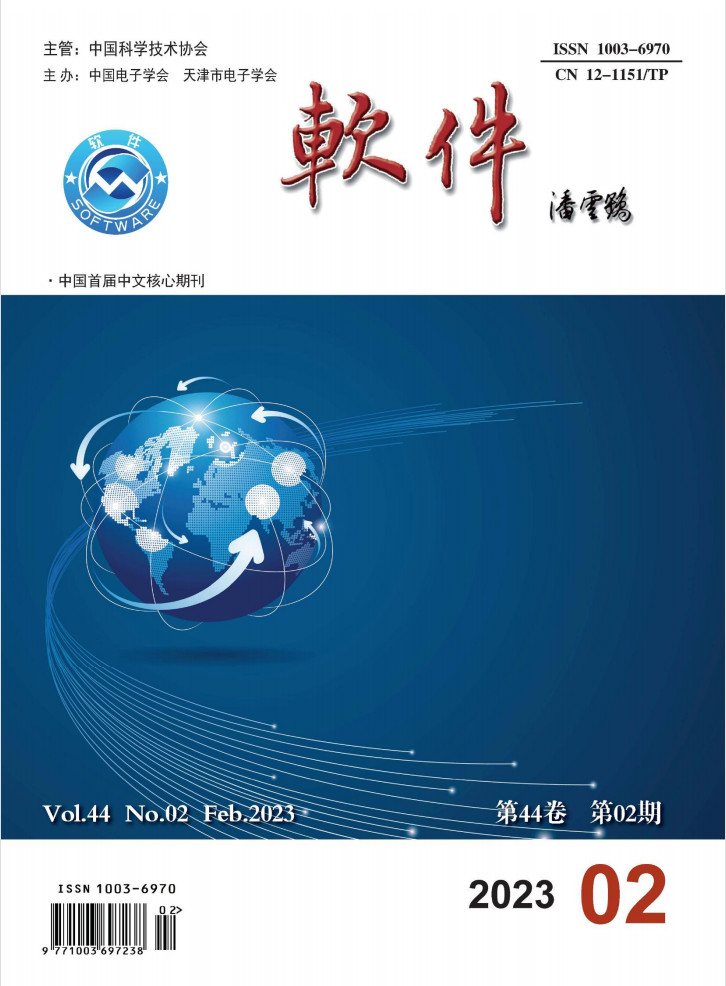法院的公共政策形成功能:比较与定位
佚名
关键词:法院 公共政策 司法解释 判例 违宪审查
按哈耶克的理解,立法面向未来、行政立足于当下、而司法着眼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欧陆国家的法官谨慎地行使其解决纠纷的权力。这主要因为欧陆国家的制度是按照洛克与卢梭的议会至上的理念设计的,人民普选产生的立法机关——议会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机关,也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曾任法官的孟德斯鸠敏锐地认识到议会至上与人民主权思想之不足,提出了权力制约的三权分立。孟德斯鸠的政治理念最终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开花结果。不仅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得以实现,而且自马歇尔法官始,经过几代法官们前赴后继的努力,司法权得到空前的扩张,司法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战后德国,开始注重以其他权力制约和约束立法权、行政权,并因此设立了宪法法院。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中最早实现法典化的法国,在原来成立的撤消法院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宪法委员会,并在较大程度上介入国家的公共政策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不能仅仅满足于个案的纠纷解决,同时应当在公共政策形成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力图在对法院参与政策形成方面的域外比较的基础上,反思性地探讨中国法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时,面临的诸多限制,并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法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之方式。
一 域外比较——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
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处,作为两大法系代表的美国和德国都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治体系,法院都在较大程度上参与公共政策的形成。不过由于德国和美国在历史、文化方面存在较大的不同,两国法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模式也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法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方式不同。美国是比较典型的普通法国家,判例是其重要的渊源,由是建立权威判例便成为美国法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方式。在美国,判例首先表现为对具体案件的处理,表现为对具体纠纷的裁判意见。但判例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它具有超出个案的效力。判例的扩张效力表现在判例中所涉及的法律理由,不仅可以成为公众调整其生活关系和民事往来的基本的生活规范,同时也可以成为法院处理以后的案件的基本依据,可以为法官裁判案件直接引用,即是说法院的判例对法院以后处理纠纷有法的约束力。正是因为对法院处理以后的类似的案例有指导意义和法律约束力,其才成为法律的渊源。这样,法官不仅是法律的实施者,同时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法官在法律的创制和法律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立法作出贡献并名垂青史的均是法官。“英国的所谓司法经验和睿智都记载在报告法官具体判决的判例集中,极少采用理论性著作的形式表现出来。”[1]这样的概括不仅适用于英国,同样适用于美国。尽管自Blackstone在大学中讲授罗马法开始,美国和其他普通法国家、地区的司法以及立法中开始注重学者和立法机关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判例仍然在美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埋葬了普通法,但他却从坟墓中走出来,和支配我们的生活。”[2]也正因为此,撰写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之判决书的马歇尔,也成了美国司法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3]
在德国也有判例和判例编撰制度,其判例也不是没有约束力,美国斯坦福大学梅利曼将大陆法系判例发生作用的原因归纳为三点:一是法官深受先前法院判例的权威的影响;二是法官懒于独立思考;三是不愿冒自己所做的判决被上诉审撤消的风险。[4]但与英美国家、地区的判例相比,德国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具有以下特点:(1)法院的判例不能作为法律渊源,由法院在案件裁判时直接引用。法院判例的效力主要是通过上诉制度实现的,即是说与上级法院判例相反的裁判,有可能在上诉审被推翻。有学者在论及德国的判例时认为,德国宪法法院的判例可以作为法律渊源,并能在裁判中直接引用。实际上德国宪法法院判决的功能是宣告某项有争议的法律或者法规违宪与否,并由之决定该有争议的法律或者法规在以后争议的案件中能否适用。因此法院后续案件的审理直接引用的并不是宪法法院判例,而是宪法法院宣告合宪的法律或者法规;(2)德国的判例编撰还不能产生广泛的波及效力。德国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成册判例,主要流传于法院系统内部,判例一般不能成为学者的对象和学生的基本材料。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关注最高法院的判例,并以此理解最高法院在争议法律问题上的态度。但这并不能因此在实质上提高判例的波及效力,一方面最高法院的判例在整个法院判例中仅属于冰山一角,另一方面更多的学者和学生关注的仍然是法学理论的探讨和学习;(3)与美国相比,德国的判例总体上质量不是特别高。导致这一状况的基本原因是德国缺乏美国民事诉讼中的发达的审前程序,大部分案件无论难、易,最终都会进入审理程序,裁判者没有充分的时间撰写判决书;同时因判例的地位和影响也无法与美国媲美,裁判者呕心沥血撰写的判决书,对裁判者的回报不大,裁判者故此也缺乏撰写判决书的基本激励。[5]
可以说,违宪审查是两国法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共同方式,不过违宪审查在两国却表现出质的差别,有学者将这些差别概括为审查形式等方面的不同。[6]美国的违宪审查不是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而是附属于普通诉讼程序中,在具体审理上,法院不仅要对作为个案裁判依据的法律是否违反宪法、是否有效,同时还要对案件的事实问题进行审查,并适用有效的法律对当事人的具体诉讼请求作出裁判。德国的违宪审查是一种独立的程序,表现为普通法院在审理当事人的具体纠纷时,如果发现当事人对法律的合宪性存在争议时,应立即中止普通程序,将案件“移交”给宪法法院审理[①].宪法法院接到移送过来的案件后,只对其中的法律问题进行裁判,“而不审理发生于当事人之间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7] “不能干预原适用该法律所审理的具体的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更不得代替原审的一般法院所审理的民事、刑事案件”,[8]宪法法院审查完毕后,将审查结果告知提交违宪审查的法院,该法院再继续其审判,根据宪法法院的审查结论确定该案的法律依据并对该案作出终审裁决。如果当事人违宪审查的建议不被法院接受,当事人“则可以直接依据该法律作出法律裁判。在普通法院作出终审法律裁判后,公民可以就作为普通法院所作的终审法律裁判依据的法律的合宪性,直接向宪法法院提出诉讼”。[9]
第二,审查主体不同。在美国,法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渠道虽然有违宪审查和判例两种方式,但由于违宪审查不是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而且法院对法律合宪与否的宣告也是通过具体判例实现的,因此两种方式具有形式上的一致性。在美国的判例制度中,创建权威判例的权力并不专属于某一具体的法院,而是由多个法院分享,没有任何一个法院享有违宪审查方面的专属管辖权。有学者称美国的这种违宪审查模式为分散型的违宪审查模式,并以之与德国的集中型违宪审查模式相区别。“违宪审查存在于整个司法体系,它与一般司法管辖并无显著分别。一切争议,无论性质如何,都以同样的程序,在基本上差不多的环境下,由同一法律裁夺。任何案件都可能出现宪法问题,其中并无特殊对待。说到底,美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宪法诉讼,没有理由把在同一法院提起的案件或争端作一专门的分类。”[10]“司宪权与司法权合为一体,将司宪权视同为一种司法权。”[11]]在美国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因为无论是违宪审查还是普通判例的形成,都是法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重要方式,具有目的上的一致性。通过前者决定立法机关创制的法律是否违反宪法、是否有效,通过后者填补立法的空白,修正既往判例中不适合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要求的法律理由,以引导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违宪审查和一般判例在形式与目的上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美国法院都分享政策形成功能。判例制度的主要表现为判例的拘束力,这种拘束力表现为上级法院的裁判对下级法院以及本法院以后的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约束力,他们一般不能作出与既往判决相异的判决。这样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判具有最高的法律约束力,其次是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判一般情况下不能作为判例被引用。事实上,在普通法的历史上作为法律渊源的主要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和上诉法院的判例,普通法上,名垂青史的法官也多是最高法院的法官。
在德国,不仅一般的下级法院不享有违宪审查权,而且联邦最高法院也不享有违宪审查权,违宪审查的权力专属于联邦宪法法院。联邦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虽然采用了诉讼的形式,但宪法法院本质上不是一个司法机关,而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一项独立权力。宪法法院设置的背景是,历经法西斯独裁统治之苦的德国人民特别重视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宪法法院的性质就是一个法律监督机关,其在剥离了传统三个国家机关的部分权力的基础上对这些权力机关进行监督。所以如果说美国的违宪审查权隶属于法院,体现了三权分立格局的话,那么,德国宪法法院的设计则是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之外的一个机关,是三权之外的权力,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所有国家权力。
两国法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主体虽然不同,但对代表这些法院行使公共政策形成的法官的素质都有严格的要求,以保证法院在公共政策形成方面有充分权威和广泛的可接受性。在美国法官是从律师中选拔出来的,法律首先采取了较高标准的律师职业准入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