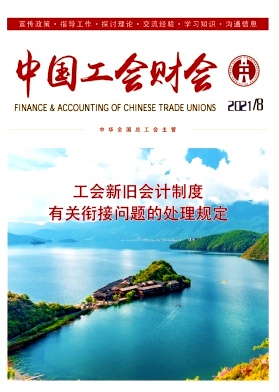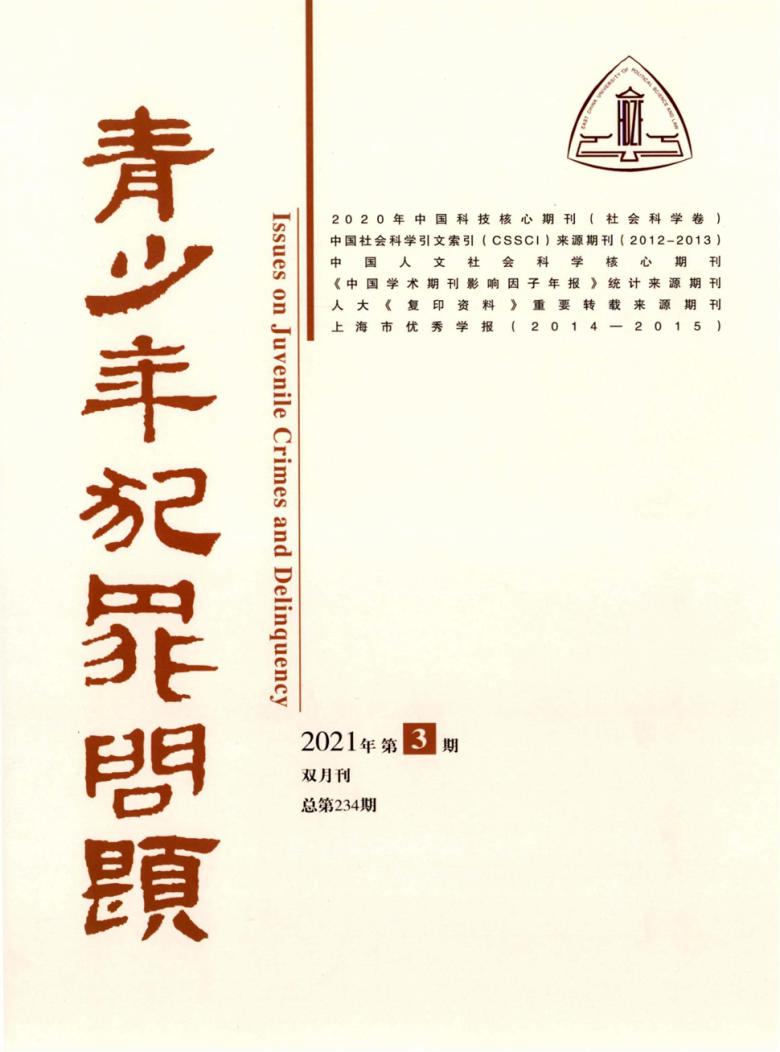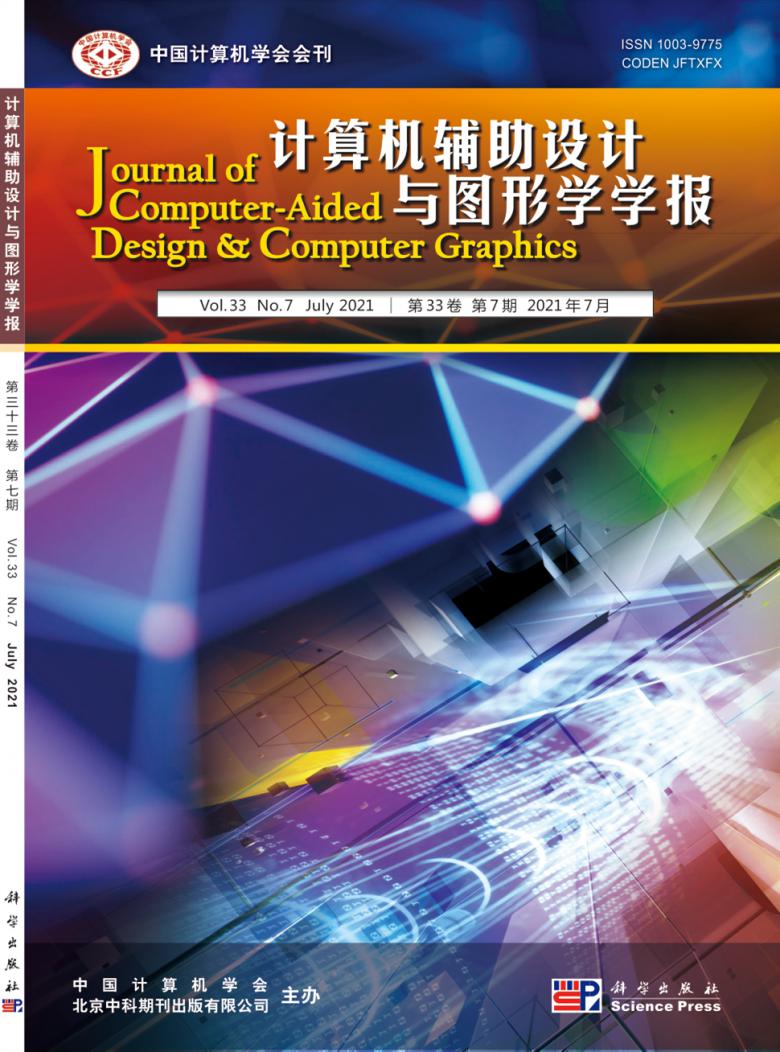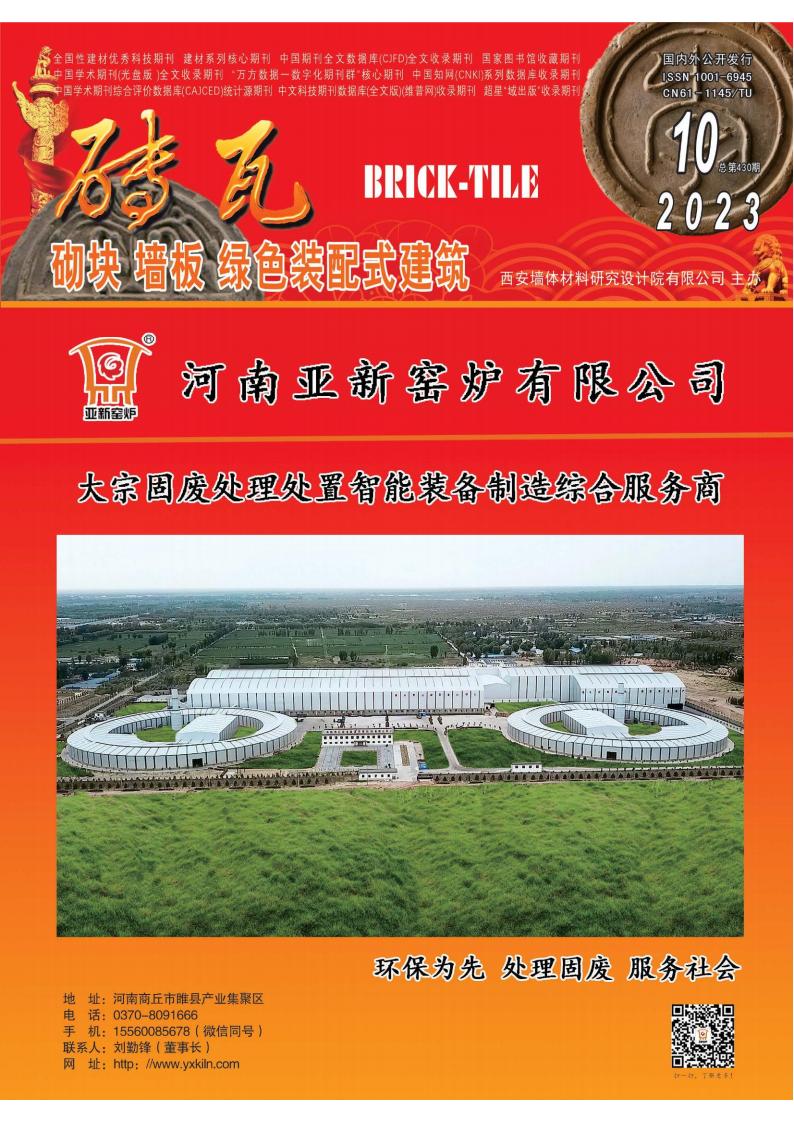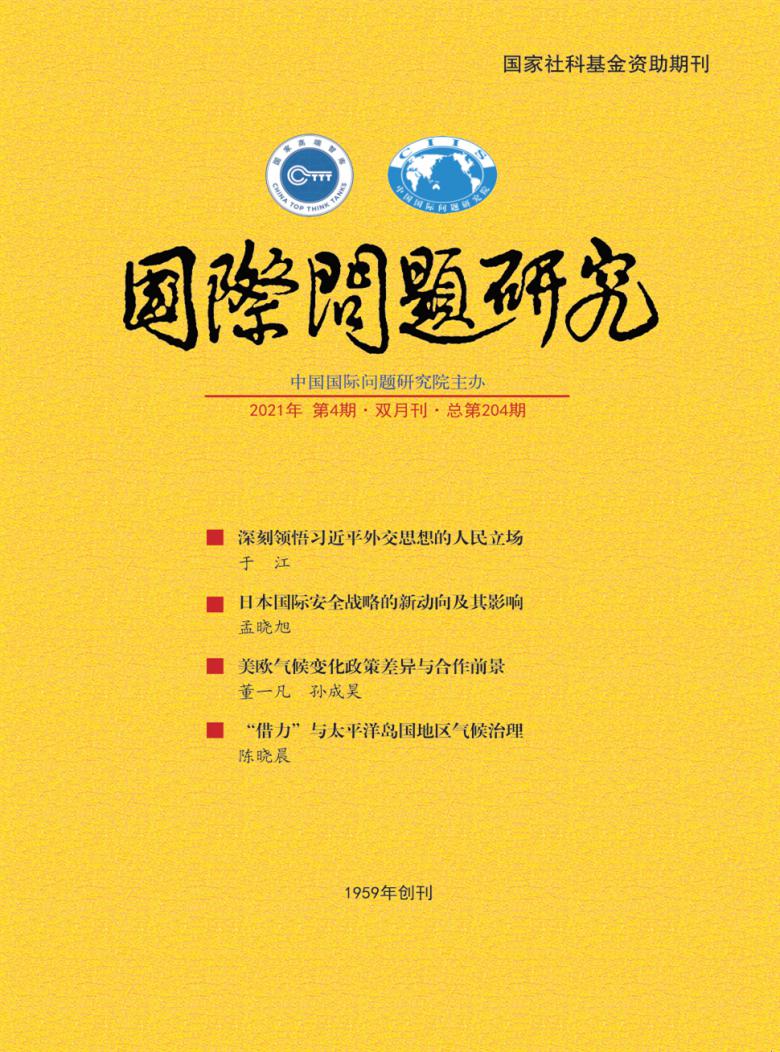试析从污点证人的角度看行贿人的司法处理
张耀军 2013-06-21
论文摘要为了重点打击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中的行贿人给予了“有条件从轻处理”的立法待遇。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形成了“重查受贿、轻办行贿”的办案格局,然而这一办案格局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有效打击贿赂犯罪,而且司法实践中对行贿人的处理方式也极不规范,难以纳入侦查监督的视野,与现代刑事诉讼法律理念相悖。本文主要从有效打击贿赂腐败犯罪的角度出发,对行受贿犯罪中行贿人的处理方式进行探讨,并认为将实践中对行贿人的司法处理从程序法角度加以规范应是立法改进的方向,而进而明确给予行贿人以“污点证人”的刑事诉讼地位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论文关键词贿赂犯罪行贿人污点证人
在贿赂犯罪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受贿的犯罪在新时期呈现出许多新特征的同时,市场交易中“非国家工作人员”为谋取私利而受贿的商业贿赂犯罪也愈演愈烈。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作为一种“权力寻租”的腐败犯罪,对党的威信和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严重危害,从长期看会威胁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商业贿赂则严重破坏商业信用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若不有效打击使之成为了不良的“商业潜规则”,会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贿赂犯罪作为一种“交易型”的对合犯罪,行贿人与受贿人由于都从这笔“交易”中获取了一定利益,犯罪之后双方即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恰如“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这就使得贿赂犯罪变得极为隐秘不容易被发现,即使被发现也由于过于依赖口供使得案件不易突破。因此,贿赂犯罪一直是腐败犯罪中的“痼疾”。
一、“重查受贿、轻办行贿”办案格局下对行贿人的司法处理
长期以来,贿赂犯罪虽然是典型的对合犯,但是由于受贿一方是公权力“寻租”的行为,所以一直是反腐败打击的重点。加之出于诸多法律层面和办案策略的原因,以至在查处贿赂犯罪时形成了“重查受贿、轻办行贿”的办案格局。大体来看,“重查受贿、轻办行贿”办案格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因。 首先,这乃是由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引起的。贿赂犯罪由于极为隐秘,还日趋复杂化和智能化,物证与书证极难获取,这就导致查处贿赂犯罪对言词证据尤其是口供的依赖性非常高。而由于贿赂犯罪往往当事人极少,一般只有行贿人和受贿人在场,行贿人和受贿人又因共同利益容易形成“攻守同盟”,要想获取贿赂犯罪的口供极为艰难,“分化瓦解”便成了主要的策略。现实办案中,从打击腐败行为的办案重点出发,经常采取先突破行贿后突破受贿的模式,而突破行贿人口供时,为了解除行贿人的顾虑,给行贿人以免于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政策承诺”遂成了重要手段之一。 其次,这是由我国刑法实体法律的相关规定决定的。根据我国《刑法》第390条第二款的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乃是刑法为了瓦解贿赂对合犯罪、鼓励行贿人如实交代的重要规定,也是办案实务对行贿人“从宽处理”的唯一法律依据。从另一个方面讲,根据我国《刑法》第389条的规定,行贿人构成行贿犯罪,需要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构成要件,而实践中“不正当利益”的内涵与外延十分不易界定,容易引发分歧,从而影响对行贿罪的处理,这也是“轻办行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轻办行贿”及其方式的问题
就成因来看,“重查受贿、轻办行贿”办案格局的形成具有一定必然性,这乃是贿赂犯罪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但是就长远来看,一味地“重查受贿、轻办行贿”却无法有效打击贿赂犯罪,不利于遏制腐败现象。毕竟贿赂犯罪是一种对合犯罪,只有对受贿方和行贿方都给予有效打击,才能有效发挥法律的威慑功能。 而且在“重查受贿、轻办行贿”的办案格局下,侦查机关出于分化瓦解的考虑,以“政策承诺”的形式换取行贿人的口供并对行贿人直接作不立案处理,这种广泛存在的处理方式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侦查机关的“政策承诺”并无可靠的法律制度保障,是否兑现承诺具有较强的恣意性,这就使得行贿人对于“政策承诺”顾虑重重,分化瓦解的策略经常难以奏效;一旦侦查机关失信,从长远来看也会影响查办贿赂犯罪的办案环境。其次,虽然根据《刑法》第390条第二款,如果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但是刑事诉讼法却缺乏明确的程序性规定。根据现代刑事诉讼理念,只有法院才拥有定罪量刑权,那么如果对行贿人进行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理论上也应当由法院进行宣告,侦查机关直接对行贿人作不立案处理则与这一理念相悖。最后,侦查机关为换取行贿人的口供,而对配合调查的行贿人不予立案,有与行贿人进行“交易”之嫌;而且由于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善,侦查机关的这种行为需要接受侦查监督部门的立案监督,一旦侦查监督机关要求侦查机关对已经作出“政策承诺”的行贿人进行立案,侦查机关将面临“有苦难言”的窘境。
三、《刑法》第390条第二款的“尴尬处境”
应该说,侦查机关在向行贿人进行“政策承诺”时,其法律依据主要是《刑法》第390条第二款。但是如前所述,侦查机关对行贿人配合调查交代行贿行为的行贿人直接作不立案处理,则有重大问题。如果肯定《刑法》第390条第二款的立法价值,那么对于这一实体法规定如何在程序法层面进行规范则是立法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根据我国《刑法》第390条第二款,“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对其性质,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以前,学界存在不同见解。具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三种:(1)特别自首论,这类见解认为,该条款是一项“提示性”条款,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其行贿行为实质上是就是“自首”情节,其可以“免除处罚”的功能也只有“自首”;(2)重大立功论,由于贿赂犯罪隐蔽性极强,行贿人主动交代自身行贿行为,实质上是对受贿人的检举揭发,属于立功表现,其量刑幅度也与“重大立功”相同;(3)坦白制度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实质上是被动到案后对自己犯罪行为的“坦白”,但是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以前我国刑法中并无“坦白”这一量刑情节。
笔者认为,《刑法》第390条第二款不能笼统地认定为我国刑法规定的“自首”、“立功”和“坦白”(“坦白”系刑法修正案(八)所新增),而应进一步区分。《刑法》第390条第二款将行贿人主动交代自己的行贿行为的时间点定为“被追诉前”,那么无论是行贿人主动到案、被动到案只要最终交代了其行贿行为,那么均可以就该行为获得“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如果行贿人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其行贿行为,那么构成“普通自首”;如果行贿人因其他犯罪行为被动到案,但是供述了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行贿行为,则构成“特殊自首”;如果行贿人因为其行贿行为被动到案,后主动供述了其行贿行为的,则构成“坦白”。而由于贿赂犯罪对合犯罪的性质,行贿人无论主动到案还是被动到案,在其供述其行贿行为时虽然貌似也是对受贿人的检举揭发,但实质上均无法构成“立功”,因为究其实质如实交代自身行贿行为虽然相当于交代受贿人的受贿行为,但是一项行为在法律上却不能重复评价。 因此,笔者认为《刑法》第390条第二款乃是专门针对贿赂犯罪中行贿人的一项特殊规定,就其“减轻处罚”、“免除处罚”的立法用语来看,其乃是一项量刑规定,但是其却不同于刑法设置的“自首”、“立功”和“坦白”三类量刑情节。其立法初衷应旨在分化瓦解贿赂对合犯罪中行贿人与受贿人的“攻守同盟”,鼓励行贿人“倒戈”,但是其关于“主动性”的规定颇显理想化。加之该条款缺乏相应的程序性制度予以保障,最终导致了这一条款在司法实务中被侦查机关的“变相适用”。
四、结语:行贿人的“污点证人”地位应从事实进入规范
从某种程度而言,司法实务与法律规范之间应当存在一个良性的互动。虽然严格来说,司法实务作为法律规范实施的过程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范进行,这也是法治实现的基本保障,但是如果司法实务长期存在“脱法”现象,那么或许法律规范本身也应进行适度反思。正如哲人黑格尔所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当事实与规范长期脱节的时候,如果事实具有合理性,那么应当改变的必然是规范。 以此来看我国司法实务中“变相适用”,《刑法》第390条第二款这一现象,便能得到很多启示。其实,司法机关对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行贿人给予“不立案处理”后,行贿人在贿赂案件中的地位便是“污点证人”,而“污点证人”作为一个法律名词在法律实务中也并不陌生。只是在法律规范和法学研究中,“污点证人”一直得不到承认,虽然它在法律实践中广泛存在。 细究之,“污点证人”之所以不被承认,从根本上讲,仍是我国法律文化中“绝对正义”的理念在作祟。让所有的犯罪都得到惩罚,这是法律严肃性的体现,其反映的刑罚必罚性也是刑罚发挥职能的关键。但是随着法律实务研究的深入,任何一个理性务实的人都必须承认,“犯罪黑数”是大量存在的,绝对正义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树立“相对正义”的正义理念只是更为理性的选择,承认“相对正义”并非就是对正义理想的背叛,也不会动摇对法律权威的确信。在“相对正义”的视野下,接受“污点证人”也就不会显得那么困难。 退而言之,如果广泛承认刑事司法中“污点证人”的存在仍有困难,毕竟实务中操作有被滥用的风险,那么承认贿赂犯罪中行贿人的“污点证人”地位则显得十分可行,且对于惩治贿赂犯罪来讲具有极大的制度价值。从法律规范层面讲,我国《刑法》第390条第二款的规定本身已经体现了法律对贿赂犯罪特殊性的关照;从司法实务的角度看,当下打击贿赂犯罪的司法实务也体现了这方面的制度需求。只有承认行贿人“污点证人”的可能性地位,才能弥合对行贿人司法处理方面司法实务与法律规范的紧张关系。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当首先借鉴《刑法》第390条第二款的立法模式,即仍从实体法角度对被动到案后坦白交代自身行贿行为的行贿人给予特殊规定,但是特殊规定的性质应当进行修正。对于《刑法》第390条第二款规定的行贿人交代其行贿行为“主动性”的要求,应当删去,淡化该条政策性质的倡导性,强化其作为法律规范的操作性。至于对《刑法》第390条第二款“量刑情节”的性质,也应当修正为直接对刑事责任的“审查性豁免”,其在效果上的差别是:如果是“量刑情节”,那么对行贿人就是定罪而免于处罚;如果是对刑事责任的“审查性豁免”,那么对行贿人即是由法院在审查后作无罪宣告。只有从实体法角度进行规定,才能免却执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与行贿人就行贿人的刑事责任进行交易的嫌疑;只有直接对被动到案后坦白交代自身行贿行为的行贿人的刑事责任给予“审查性豁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商业贿赂中,才能完全解除行贿人顾虑,从而最大限度发挥该制度分化瓦解的立法价值。 在实体法修正的基础上,对现在司法实践中“变相适用”法律的现象从程序法角度进行规范也显得极为重要。这一方面体现在,侦查机关不能对被动到案后交代自身行贿行为的行贿人直接即作“不立案处理”,毕竟这与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相悖,而应由法院在对行贿人的行为进行评价后对其刑事责任作进行豁免,即“审查性豁免”。另一方面,对于被动到案后交代自身行贿行为的行贿人应当有相对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保证其此次行贿犯罪行为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保证其可以享受证人的保护待遇,包括侦查机关特殊的立案程序、侦查终结、审查起诉时提请豁免其刑事责任的意见文书、对其作证的保护措施应该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