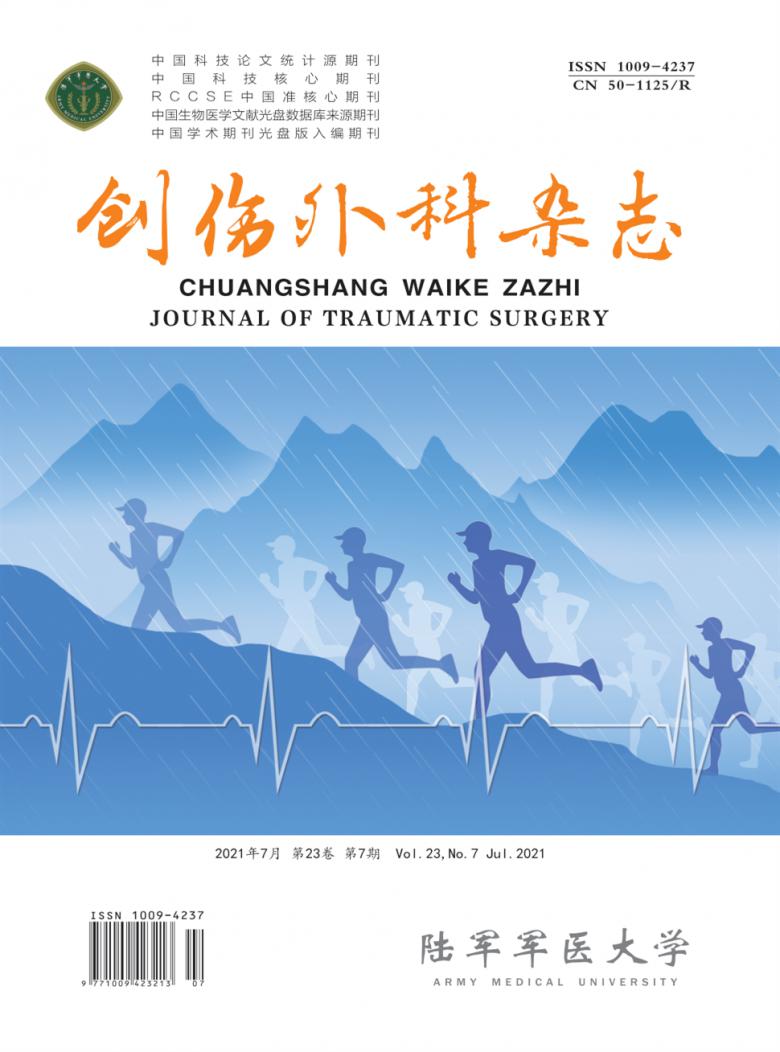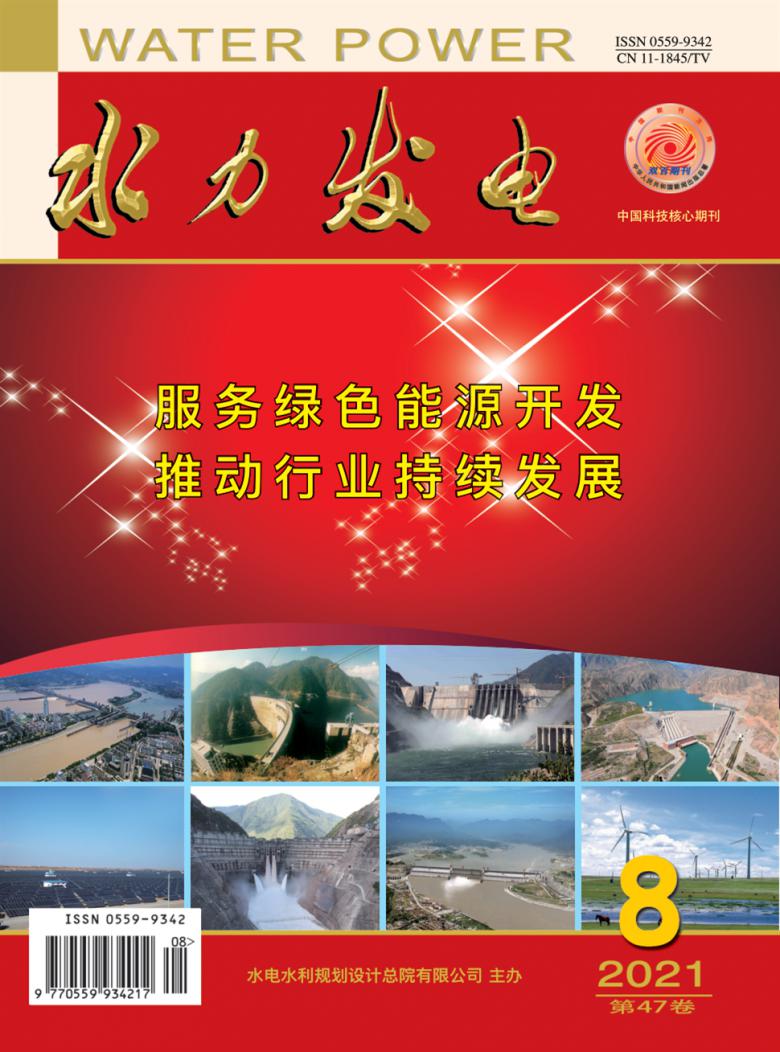苦难叙事、“人民性”与国族认同——对当前“地震诗歌”的一种价值描述
李祖德 2008-08-28
【内容提要】 自5·12汶川大地震以来,媒体上涌现了众多的“地震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表达了民众对自然灾难、民族苦难和生命价值的追索。从诗与史的关系出发,本文描述的正是当前“地震诗歌”的价值蕴含,即其中表达的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
【关键词】 “地震诗歌”;苦难叙事;“人民性”;国族认同:诗史互证
如何重建诗歌与历史、时代和现实的精神关系,这是困扰当代诗歌甚至是整个新诗史的问题。对于当下的诗歌写作而言,当诗歌(文学)“绝望地回到文学自身”之后,我们又如何让诗歌(文学)“重返”时代和社会,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或理论问题了,而是已经成为一个写作态度和价值诉求的问题。
自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媒体上涌现出了许多的相关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表达了诗人及民众对大地震所带来的灾难、中华民族面临的苦难考验的哀伤和追索。一方面,有论者认为“大地震震出了一个复苏的诗歌界”,地震“引发了全民诗歌热潮”,另一方面,也有论者认为,这些诗歌作品具有大众化、口语化、即时性甚至是“战时性”的特点,并不具有特别的“艺术水准”。
这些不同评价都涉及到了“地震诗歌”[①]的艺术价值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都未能充分呈现“地震诗歌”所表达的价值诉求。“地震诗歌”也会为时间和历史(或者某种“文学史”)所选择和清理。基于这些考虑,本文并不是要从诗歌(内部)艺术的意义上来讨论“地震诗歌”这一文学事件,而是针对这些诗歌作品与历史、时代和现实的关系,也即是在“诗”与“史”的关系结构中来描述其价值蕴含。在本文看来,“地震诗歌”中所蕴含的民族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诸多意义指向正是其价值表征。从这一角度来看,尽管作为一种“战时性”(暂时性)的诗歌现象而且颇多雷同化的倾向,“地震诗歌”仍然为当代新诗写作如何“重返”时代和社会提供了一种深刻启示。
一、价值的关联:地震与诗歌
仅以2008年6月号《诗刊·上半月刊》“抗震救灾”诗专号为例,关于5·12大地震的诗歌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自然灾难、民族苦难和民族国家主体性等诸多内容,其他媒体上涌现的诗歌作品也同样在这些层面上多有表现。诸如李瑛《生命的尊严如此美丽》组诗、商泽军《阿特拉斯的脊梁》、徐必常《国家的眼泪》、蒋同《国哀:那一朵小白花》、白连春《整整一个地球的痛》、北塔《生命的物证》、叶舟《祖国在上》以及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宝贝啊,不要沉睡》、《妈妈的呼唤》、《孩子,天堂路上别走太急》、《最近我常常含着泪水》、《开往天堂的火车》、《爸爸妈妈,别为我们难过》等作品[②]都展示了在抗震救灾的“战时性”状态下,诗人和民众对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民族苦难的哀伤和痛惜,同时也传达出了一个民族在灾难和苦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团结。
在这里,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大地震和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就建立起了一种价值的关联。也就是说,这些诗歌作品之于大地震并不仅仅是一种反映关系,其中还存着在一种意义关系。“地震诗歌”一方面记录了大地震这一民族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战时性”状态下呈现出来的苦难叙事、“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诸多价值内涵。
如果说“启蒙”与“救亡”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双重变奏[③]的话,那么,从整个现代文学史来看,“地震诗歌”则同时兼具了“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主题。大地震及其灾难,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民族危亡”的历史想象,现实的危难从我们的历史经验中获取了苦难的精神内涵。而“地震诗歌”同样也从文学史(诗歌史)的经验中获取了“民族救亡”的写作动力。从众多“地震诗歌”作品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这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④]的历史图景,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⑤]了的历史形象。“地震诗歌”仿佛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在对现实灾难和民族生存苦难的观照中,我们仿佛回到了臧克家、田间、艾青等人歌唱的时代,同时又回到了“中国新诗派”和“七月诗派”等人沉咏的情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地震诗歌”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文化事件,在现实的语境(自然灾难与民族苦难)中获得了“民族救亡”和情感与精神启蒙的意义。
可以说,在对地震灾难、人性磨难和民族悲怆的苦难想象与叙述中,众多“地震诗歌”作品交织着生命、死亡、苦难、大爱与民族精神的繁复旋律,这些繁复旋律正演绎着“启蒙”与“救亡”的复调叙事,而非一种声音压倒另一种声音的“双重变奏”。因此,在“诗”与“史”的关系结构中来看,并在价值和意义的维度上进行考察,“地震诗歌”既体现出了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同时也蕴含着一种民族国家的集体情感和认同。作为自然灾难的大地震因此而具有了精神苦难和价值重塑的意义和功能,诗歌对苦难的书写加强了现代新诗“人民性”的文学品质,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族和身份认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与诗歌再次确立了“诗”与“史”的关系,并缔结了多重的意义关系。“地震诗歌”的出现既是对难以抗拒的自然灾难——大地震的历史书写,也是对隐秘的民族心灵史——国族认同的一种情感(文学)呈现。
二、题旨一:灾难考验与“人民性”
当下的“地震诗歌”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达了大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及考验,以及国家和人民抗震救灾的信心和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性”是“地震诗歌”的基本情感和价值意向。在这里,“人民性”指涉的并非是单纯的政治和阶级含义,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共同的民族情感、经验和精神。在全民抗震救灾——“民族救亡”的历史时期,“地震诗歌”体现出的这种“人民性”的文学品质,既是现实的呈现,也是民族情感、力量和信心的汇集。
从众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诗歌的抒情主体再一次回归到时代的“大我”。如《这时候——写在5.12四川汶川震灾之后》:“当十三亿同胞伸出了温暖的手/当泪水打湿了一张张善良的面容/这时候,我们挺直了沧桑的腰板/我们昂起了高贵的头颅——/为了抵抗这无法避免的天灾/我们变成了热血沸腾的英雄 /这时候,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看到了中国的强大”。在这样的诗歌里,抒情主体“我”和“我们”并不存在什么情感、价值、观念和意图的差异,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地震灾难和民族精神进行反复的叙说。在诗歌里,“我”是作为一种视点而存在的,而“我们”才真正是诗歌情感扩张的辐射源,或者真正的抒情主体。因而,作为诗歌叙述者的个人和作为诗歌抒情主人公的集体——“我们”、“十三亿人”在这里达成了情感和意向的统一性。再如一首《我们的心——献给汶川的血肉同胞》,在“地震诗歌”中颇具代表性,它直接以“我们”进行诗歌的抒情和叙事:
我们的心朝向汶川/我们的双手朝向汶川/我们阳光般的心朝向汶川/我们旗帜般的双手朝向汶川/我们十三亿双手向汶川去!/……/让我们的心朝向汶川/让我们的双手朝向汶川/让我们阳光般的心朝向汶川/让我们旗帜般的双手朝向汶川/让我们十三亿双手向汶川去!/汶川流泪/夜,很安静/往日的喧嚣也缄默了言语/俨若战后的城市/荒芜且退去原有的色彩/满街道的灰土/和坍塌楼道里的死亡气息/埋没了花草昨日的鲜艳/掩埋了螟虫昔日的笙歌/飞鸟也远离了故土/不忍视/汶川流泪/四川流泪/中国流泪
自然灾难的考验和民族国家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汇集了。正如诗人艾青在70年前的那首《我爱这土地》所描绘的历史图景和民族苦难一样,国家和民族正面临着灾难的考验,诗歌抒情主体也转变成为一个时代的歌手,传达出了一个集体的声音。“故土”、“家园”、“战后的城市”和“灾难”等诸多形象都具有了一种精神的意义,而“我们”则成为“地震诗歌”普遍的抒情方式。可以说,诗歌抒情主体的包容性使“地震诗歌”不仅仅起着一种集体代言的作用,而且还有效地传达出一种共同的和普遍的情感。在“地震诗歌”里,“人民”和“人民性”再次显现,使得诗歌再一次恢复了它应有的功能。
书写民族的灾难和民族的重生是这些“地震诗歌”最基本的意义倾向。其他相关作品如郭文斌《中国,你为什么泪流满面》、刘继明《哀悼日》、鲁文咏《地泣与国殇》等作品都直接书写了民族和国家在面临地震灾难时的艰难和信心。这些诗歌尚未能直接深入对灾难和苦难的思考和剖析,而是直接展现“人民”和“人民性”的时代主体。因此,重塑一种新的时代主体和主体精神也是“地震诗歌”最普遍的主题之一。作为当代新诗的核心命题,“人民”和“人民性”在“地震诗歌”里被再次激活。
当代诗歌在经历了“政治抒情诗”、“朦胧诗”、“第三代诗”、“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后,作为一个诗学话题,诗歌的抒情主体从“大我”“回归”“小我”已经为当代诗歌史所确认,但我们会发现,当下诗歌写作的思想和审美空间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如何在现代诗歌写作中重新恢复“我们”——另一种抒情主体的价值和权利,或者如何在表达个人体验的同时融入民族国家的情感和命运的内容,这是在当下诗歌写作中一直被忽略的问题。在这次大地震和“地震诗歌”事件中,诗人们及民众暂时放弃了理论上的成见和分歧,灾难、苦难、生命与爱、国家与民族成为当下诗歌的共同话语,这也许正寓示着诗歌写作应有的一种品质和良知:“我们”如何表达“人民”与“人民性”?
“地震诗歌”作为一种现象,它给我们的启示恰恰在于:诗歌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同样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诗学命题。当“地震诗歌”让“我们”重新成为诗歌的抒情主体时候,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也复活了。因此,可以说,作为历史事件的地震在激活诗歌,作为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也在激活诗歌的主体——“人民性”。从“地震诗歌”的写作者来看,众多“非专业”作者的参与也为当下诗歌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正如批评家谢有顺在评价“地震诗歌”时所说,“诗人和作家要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众人,面对现实;他写的作品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⑥]当“我们”成为当下诗歌的主人公时,诗歌、诗人、民众与国家民族、时代和社会才再次达成了情感和价值的沟通。因此,“地震诗歌”所展现的“人民性”,给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呈现了一种新的方向。
三、题旨二:苦难叙事与国族认同
对苦难和灾难的“历史化”书写也是“地震诗歌”的基本题旨之一。对“历史”(现实)的“历史化”叙述是建构一个国家和民族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尽管大地震依然是我们当下的现实,作为一种“战时性”文学表现手段,“地震诗歌”则已经提前将大地震“历史化”了。在对大地震的“历史化”书写中,“地震诗歌”容纳了“苦难”叙事的成分,甚至带有某种民族寓言和神话的特征。在许多“地震诗歌”的叙述里,大地震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一种历史记忆。也正是这种集体的“苦难记忆”成为我们国族身份认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地震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苦难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苦难。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诗歌”已成为建构和强化我们国族身份认同的历史叙事。
如在媒体上流传甚广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一诗这样写到:“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妈妈/怕天堂的路太黑/我看不见你的手 /自从倒塌的墙/把阳光夺走/我再也看不见/你柔情的眸……”在这样的诗性言说里,个人作为叙述者,在对苦难的叙述中,容纳了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体验。“妈妈”和“孩子”穿越时空和生死界限的对白,将苦难化作生命和希望的祷告。苦难让我们反观和照亮现世的生存。再如《开往天堂的火车》一诗,是将生命与死亡、告别与归家、苦难与幸福表现得最让人痛切心扉的作品之一:
这是开往天堂的火车/注定有一条河流清澈的流向/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他们的告别乖得没有一点声响/我第一次看见/我们的孩子/变得像大人一样坚强/他们行将离去的站台/也不再需要爸爸妈妈与奶奶的/送行//这是开往天堂的火车/注定会穿过一片鲜花的海洋/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我知道他们来自神灵的家乡
这些作品从苦难、人性的角度将灾难、生命的罹难和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的叙述,对大地震带来的“苦难”进行“历史化”的书写。“火车”、“告别”、“站台”、“天堂”和“家乡”等种种意象都无不意味着生命的归宿和幸福。这样的苦难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审美化的倾向,灾难、苦难和死亡被赋予了一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有某种神话和寓言的意义功能。
在这些充满“个人化”的苦难叙述中,苦难已不仅仅是个体和生命、死亡的意义关系,而是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阅读者的苦难记忆。“告别”与“归家”、“离开”与“寻找乐土”的意义结构是诗歌史上一直都存在的“神话写作”的基本模式,而这一类“地震诗歌”则在这一向度上体现了生命、人性与苦难的意义关系。应该说,这样的苦难叙事是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它们所表达的是苦难和对苦难的意义追索。“谁点燃了这烛。并且,让烛光成了中国铺满阳光的午后最痛的伤口/一只叫做汶川的陶罐,一只被舜用宽仁的手指/就着厚厚的黄土与泪一般透明的水焙制成的陶罐/被黑色的烛光击中,然后/碎了……”(龚学敏《汶川断章》)在这样的苦难叙述里,“汶川”、“地震”、“舜”、“陶罐”和“黑色的烛光”等意象实现了跨越历史时空的碰撞,地震灾难与民族传说一起呈现了人性、生命、个人和民族国家共同的心理原型,这种“神话写作”恰恰是有关人性和苦难的,这里面容纳的意义和价值正隐藏着一个民族国家潜在的精神结构。
与苦难同时传达出来的,还有关于爱的内容。苦难与爱作为诗歌(文学)写作中的一种原型或母题,同样在大地震这一历史事件中找到了表现的空间。许多“地震诗歌”直接以爱为题,将自然的灾难、人性的苦难以及生命救赎等复杂的情感体验融合到一起。苦难、爱与生命本身结为一体,苦难因此而多了一层悲悯的宗教色彩,爱也超越了世俗的理解上升成为一种“大爱”。地震灾难带来的“恐惧与颤栗”背后是对苦难的担当和爱的力量。有诗句这样写到:“这不是诗歌,我只是如此呼喊/愿以一个死难者的声音/此刻醒来,就要永远醒来/因为我们还在经受更为严重的灾难/它来自我们自身,来自阴谋和战争/来自掠夺、杀戮、膨胀的私欲和勾心斗角/你甚至还来不及发现/灵魂已离去好多年……”(东荡子《来不及向你们告别》),还有诗句这样表达了对苦难和爱的悲悯:“当我写下/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在诗人的话语叙述里,有对自然、苦难和生命的敬畏,有失却家园的悲伤,也有对自我的责问,苦难与爱被赋予了忏悔和救赎、生命归宿与精神家园的意味。
尽管这些诗歌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化”和“神话写作”写作的痕迹,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诗歌作品仍然从“个人化”的苦难记忆里表达了一种集体的苦难历史。很多“地震诗歌”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将“我”或“我们”这一诗歌的抒情主体导向“汶川人”、“四川人”和“中国人”,正如有一首诗这样写到:“此刻/我们都是汶川人/我们都是四川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汶川人”与“四川人”作为一种地方性情感、知识和经验的主体,在“地震诗歌”里则获得了更高的意义,作为诗歌的抒情主体,它正是一种情感反射,它所投射的是一个更大的主体性——“中国人”。其他诗歌如《国家的眼泪》、《国哀:那一朵小白花》、《14时28分的祖国》等作品则直接从时代“大我”的角度展开了对民族苦难记忆的“历史化”书写。
“历史化”意味着对记忆的整理,记忆则保存一个民族的共同的心理和情感。在对地震与灾难、生命与死亡、苦难与幸福、爱与担当的“神话写作”中,诗歌的抒情主体、国家、政府、社会和民众已经结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诗歌”的苦难叙事,强化或者凸显了一直隐藏于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心灵深处的身份认同。
四、诗史互证:苦难记忆及其意义
随着灾难的过去,“地震诗歌”的热潮也会逐渐趋于平淡,“地震诗歌”作品也会经由时间的选择和淘汰而去粗取精。但与过去的几次诗歌事件(如“梨花体”等事件)决然不同,这一次的“地震诗歌”事件则激活了“诗”与“史”的互动关系。地震与诗歌发生意义的碰撞,也正是“诗”与“史”实现价值传递的历史契机。在“地震诗歌”热潮中,凸现出来的是“史”的意义,而“诗”的意义则已经退居其次。对于我们而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5·12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伤痛,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则让我们在灾难考验和苦难记忆中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形象和精神品质。关于大地震的苦难叙事让当代诗歌写作寻找到自我升华的机会,也让我们从诗歌写作和历史叙事中看到一个人、一个民族隐秘的心灵史。这也许正是“诗史互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这也正如谢有顺所评价的那样,“这(地震诗歌)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它向我们重申了诗歌和情感之间的永恒关系;二是诗歌并未退出公共生活,只是,诗人要重新寻找诗歌介入公共生活、向公共领域说话的有效方式。国难过后,未必就会出现诗歌繁荣的景象,但这一次的诗歌勃兴,为诗歌重返现实敞开了新的可能性。”[⑦]诗歌与时代和现实的意义关系,同时也意味着诗人对时代的态度或价值取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地震诗歌”既体现了现实对诗歌的情感激发,也体现了在长久的“个人化”写作之后,诗歌对介入现实和公共生活的精神需要。
作为一种文学事件,“地震诗歌”现象已超越了单纯的诗学(诗歌文体)理论的阐释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地震诗歌”写作也是“组织中国‘历史’的过程,是一种对‘历史’的写作”。[⑧]因此,在文学史的视阈中,“地震诗歌”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即“诗”与“史”的辩证关系及其意义给我们当下诗歌写作提供的可能性。“诗”与“史”的互证,以及其中容纳的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价值因素为我们正确认识诗歌的作用和功能提供了理论的和历史的依据。
[①] 作为一种描述和概括,“地震诗歌”是针对这些诗歌作品的题材和内容而言的,尚未成为一个诗学概念或文学史概念。
[②] 本文所涉及到的相关作品来源于《诗刊》2008年6月上半月刊、“左岸文化网”及其他网络媒体,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③]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49页。
[④] 出自艾青1938年的诗作《我爱这土地》。
[⑤] 出自穆旦1941年的诗作《赞美》。
[⑥] 参见《南方日报·文化周刊》,2008年6月1日。
[⑦] 参见《南方日报·文化周刊》,2008年6月1日。
[⑧] 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