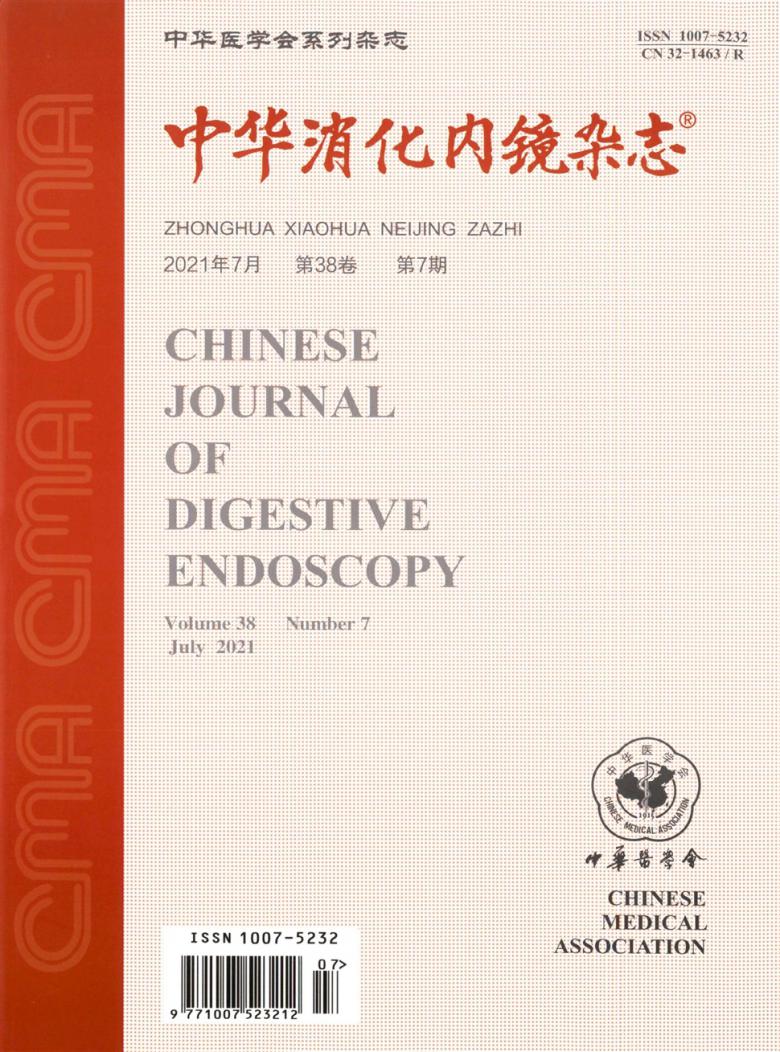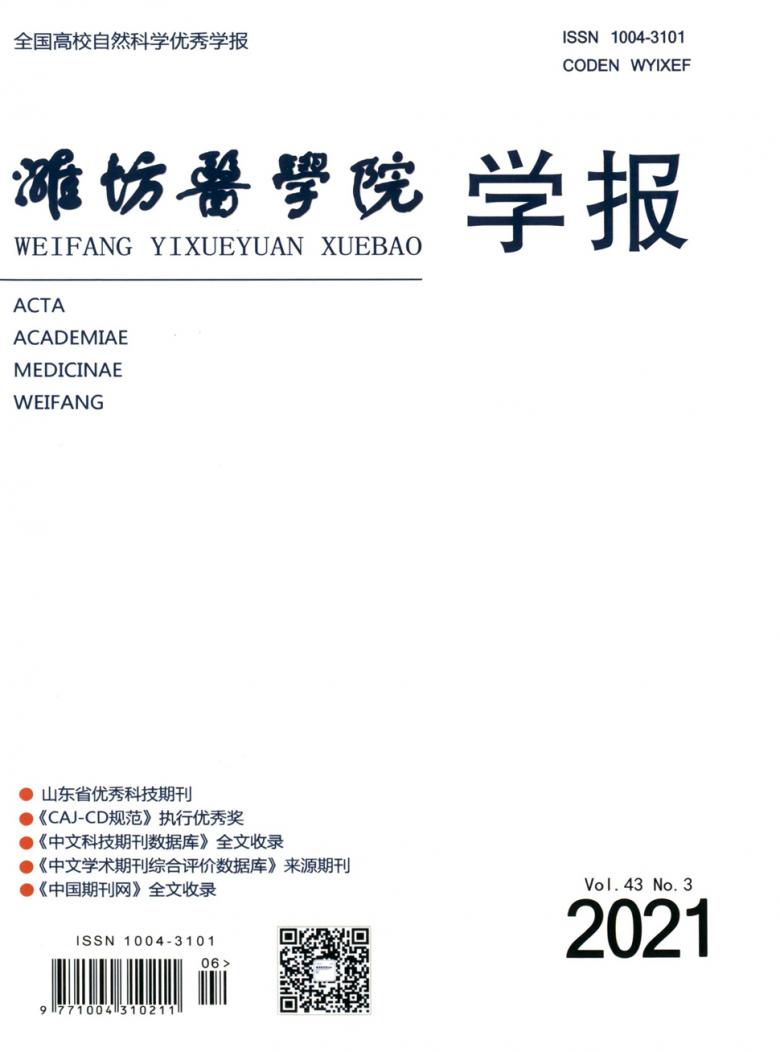浅谈“监狱行刑悖论”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邹晓玫 2013-03-30
论文摘要 “监狱行刑悖论”是指监狱的隔离监禁手段与实现犯罪人重返社会的目的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福柯在其独特的“微观权力”视角之下,以“规训”话语重构了“监狱行刑悖论”的本质、生成机理和社会功能。以新颖的思维进路揭示出“监狱行刑悖论”根源于被行刑人“主体性”的减损和丧失;提示研究者避免“监狱成为自身补救措施”的理论死循环;并要求重视行刑过程中“多元权力”的运行对行刑效果的重要影响。福柯以后现代风格的观察视角为研究和克服“监狱行刑悖论”提供了法律社会学意义上理论参照。
论文关键词 监狱行刑悖论 规训 微观权力 主体性
随着监狱行刑实践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法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研究者不约而同的关注到,在各国各时期的监狱行刑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监狱行刑悖论”。这一现象从根本上影响着现代刑罚理念的实现。现代学者们从恢复性司法、行刑方式社会化等角度出发,试图解决或缓解“监狱行刑悖论”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但所有这些努力和尝试都并未突破“人道主义”的价值和解释框架,因而取得多是功能改良意义上的成果,并未能揭示“监狱行刑悖论”的根本生成机制。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规训与惩罚》一书中,通过对刑罚的演变及监狱的功能所进行的颠覆性分析,表达了对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其微观权力(规训权力)理论为我们跳出现有的理论惯习,重新审视和解读“监狱行刑悖论”的症结所在,以及寻求根本性的解决之道提供了全新的思维进路。其理论和观点虽有个别失于极端激进之处,但也确实以“他者”的视角,敏锐的揭示出“监狱行刑悖论”中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福柯对“监狱行刑悖论”的另类表达
当代占主流地位的教育刑论者认为刑罚的目的并不在于简单的实施报复,而是将犯罪人作为一个可塑性主体看待,主张通过特定的训练或改造,矫正犯罪人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方式,使其能够重新回归社会,再次成为享有自由的权利主体。现代的监狱行刑实践,也以这种刑罚哲学作为指导性理念。“监狱行刑悻论”是指监狱的隔离监禁手段与其实现犯罪人重返社会的目的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两大矛盾:其一是罪犯监狱化与罪犯再社会化的矛盾;其二是封闭的监狱与开放的社会的矛盾。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书,在回顾了西方君主时代以来的刑罚发展史之后,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说监狱的作用在于(如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样)教育、矫正那些不能够正确驾驭自由的个体(犯罪人),使其能够重返社会,重新获得与其他主体一样的自主性,那么监狱并没有达成他的目标。因为经过监狱规训的人们很少因此变成通常意义上的“好人”,反而有些进监狱时不那么“坏”的人,因此变成了彻底的“坏人”。从社会角度看,“监狱并没有降低犯罪率”,“拘留造成了累犯”,“监狱必然制造过失犯”。 在这个意义上讲,监狱是“失败”的。然而自监狱产生以来,无数的改革者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和多种改进,监狱却一直保留下来了,而其核心的规训机制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是为什么?这一问题构成了福柯对“监狱行刑悖论”敏锐而独特的表达,也是他展开讨论的逻辑起点。 更有价值的在于,福柯并没有陷于应对该悖论的两种惯常路径(实际上,它们也是当代的众多相关研究依然沿用的路径):其一,认为监狱的改造作用不充分,教养技术仍然粗糙、落后,因而不能够完成教育、改造之使命;其二,认为监狱在力图成为改造场所的过程中,失去了惩罚的威力,同时造成了监狱在双重意义上的“不经济”——一方面它导致维持监狱运转的直接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它致使累犯增加(部分犯罪人因留恋监狱良好的物质保障而主动重新犯罪)福柯认为上述两种路径只能回到唯一的一种解决方案:进一步强化、细化、精致化现行的教养技术,从而导致“监狱总是被当做自身的补救办法”。只有跳出上述思维逻辑,才有可能发掘“监狱行刑悖论”的真正生成过程。而福柯正是以此为起点,在更广阔的社会科学论域下,发掘出了全然不同的“规训”世界。
二、福柯对“监狱行刑悖论”生成机制之重构
(一)现代刑罚理论和行刑实践中“监狱行刑悖论”的生成机制 从现代刑罚学立场出发,“监狱行刑悖论”是“报复刑主义”向“教育刑主义”理念转换的产物。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对犯罪人进行社会性报复,因而监狱必须通过对罪犯进行隔离、监禁、强制劳动等方式实现这种报复性惩罚。教育刑论者认为刑罚的目的并不在于简单的实施报复,主张通过特定的训练或改造,矫正犯罪人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方式,使其能够重新回归社会,再次成为享有自由的权利主体。这是刑罚学领域中“人道主义”理念的深层次胜利。监狱以其“更少的残忍,更少的痛苦,更多的仁爱,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取代酷刑是历史进步的体现,是值得称道和赞美的事情。然而,教育刑论者在否定刑罚的惩罚、报复目的同时,却并未否定监狱的隔离、集中教育等功能,甚至在以强制劳动为手段实现行为矫正过程中,使得监狱在社会中的经济功能较“报复刑”时代有所增强。因而,在教育刑理念主导之下,隔离、监禁方式仍然是自由刑实施的主要方式。这就必然导致奇特的三重悖论: (1)对犯罪人个体而言:通过剥夺犯罪人的自由来教导他如何更好的驾驭自由;(2)对犯罪人群体而言:使其隔绝于社会,却期待以这种方式完成其再社会化过程;(3)对其他社会成员而言:犯罪人因越轨行为进入了一个普通公民难于了解的、完全不同的秩序之下,之后带着特有的烙印(监狱化人格)归来,却要求被视为完全无异于其他社会成员的个体。 人道主义理念和教育刑哲学造就了上述悖论,却无法从根本上解释其生成机理,而只能将其视为一种“手段”对“目标”的背离。在这个逻辑之下,只有改良“手段”以适应“目的”的需求,监狱行刑社会化的讨论热潮即由此而起。
(二)“监狱行刑悖论”生成机制的后现代重构 福柯对监狱所代表的刑罚方式的独特理解却为解释上述的三重悖论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路径。在他看来,上述悖论的症结不在于监狱行刑方式,而在于人道主义刑罚哲学未能(甚至是未敢)揭示出监狱所代表的刑罚方式之根本目的,而监狱的行刑实践恰恰将这种目的表露无遗,那就是:监狱及现代自由刑的根本目在于创造“驯顺的肉体”,而远非人道主义者所表达的“恢复权利人主体资格”。 从表面上看,刑罚史经历了一个“从炫耀的酷刑到沉闷的规训”的发展过程。最终,监狱所代表的规训方式不可思议的取代了之前所有的刑罚方式而成为了现代刑罚的主导形式。监狱行刑方式虽自确立之时起即饱受争议,但历经了几个世纪的多方抨击与诟病、不绝于耳的改革呼声和改良尝试,监狱行刑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在福柯看来,正是其“规训”本质,使得监狱监禁这一看似并不成功的刑罚方式,恰恰成为了最能满足统治者需要的行刑方式。因而它能够取代酷刑和“惩罚剧场”而成为现代社会执行刑罚的主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狱是最成功的刑罚实施场所:权力者希望能够通过监狱实现对犯罪人的规训,进而通过监狱规训的产物——“过失犯”实现对整个社会的“规训”控制;而监狱的各项行刑实践非常完美的达成了权力者期待其达成的目标。至此,福柯揭示出:所谓“监狱行刑悖论”其实有着非常顺畅统一的内在逻辑结构,只不过在福柯看来,是权力者(规训者)不肯或不敢承认监狱的规训目的而已。监狱行刑目的与效果间“悖论”式的表象,充其量只是规训者希望达成并借以掩盖其真实的规训目的“障眼法”。
三、现代监狱功能之重构——“规训”话语下“监狱行刑悖论”的三重展开
在福柯看来,监狱的“成功”实际上是“规训”的胜利。监狱是最彻底的规训体系,权力通过刑罚控制犯罪人的身体进而形塑其思想。监狱是权力的表达者,是彻底的规训者,也是社会控制的枢纽。监狱无论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实体,还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都是“规训权力”的象征: (一)微观意义上,监狱是规训机制的最典型代表机构,也是“监狱行刑悖论”的策源地和直接操作领域 “规训(discipline)”是福柯创用的一个新术语,在英文里,“discipline”这个词可以作名词使用,也可以作动词使用;它具有纪律、教育、训练、训诫等多种释义,还有‘学科’的释义。该词在福柯理论中用来指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规训即规范化训练,社会组织通过监视、训练、检查等手段按照规范塑造个人。这其实是现代社会无处不在、人们习焉不察的现象。监狱的隔离性、封闭性和控制性,决定了其必然是一个典型的规训场所。规训者在这里创制出一个在一切意义上不同于社会的生存环境,从而决定了在这个环境下接受规训的个体,必定被打上独特的思想和行为烙印,即形成我们通常所说的“监狱化人格”。“监狱化人格”为上文所述监狱行刑“三重悖论”的形成准备好了一切条件;同时也为监狱在中观和宏观意义上的规训使命之实现,奠定了基础。 (二)中观意义上,监狱是实现社会意义上规训机制的重要枢纽,也是“监狱行刑悖论”得以社会化展现的中间途径 通过对非法活动中“过失犯罪”的独特性论述,福柯“天才”的解释了监狱的在其机构之外的社会功能。过失犯(delinquent)是福柯本作中的又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因环境恶劣或性格缺陷而有犯罪倾向的人(这一概念完全不同于刑罚法学上的规范界定豍)。监狱特定的规训环境使得监狱根本上不能减少过失犯,甚至必然产生过失犯。一方面,监狱的隔离、强制训练使得经过监狱规训的人具有了独特的“监狱化人格”,难以适应开放的社会生活,没有足以在社会上维持生存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监狱生活的烙印及其“监狱服刑人员”的特殊身份,对犯罪人必然产生“标签化”效应,使得其他社会成员很难接纳其为普通的共同体成员。上述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犯罪人很难在实质意义上重返社会。在福柯看来,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道路即:沦为“过失犯”,为了生存而成为规训者监视、控制其他社会成员的工具——从规训的直接对象转变为进行社会规训的武器。 由上述逻辑不难推知,福柯认为所谓的“监狱行刑悖论”实质上是一个“过失犯”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该过程不是监狱行刑机制力图避免的,而恰恰是监狱的隐性追求,甚至是它的根本社会功能。福柯否认法律的任务在于确定“正当—非正当”,认为法律和监狱的目的不在于“保护好人惩罚坏人”,而在于区别不同类型的人:接受常规控制的人和不接受常规控制的人。对于不接受常规控制的人,即以“监狱”这一特殊机构进行严厉的规训,将其打造成有特殊用途的工具。监狱造就的过失犯的最重要用途是:帮助统治者实现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全景敞视”,担当无孔不入、亦此亦彼的监视者和信息提供者。从这个角度讲,监狱是非常成功的社会控制枢纽,而“监狱行刑悖论”是监狱的这一中观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机制保障。
(三)宏观意义上,监狱象征着无所不在的规训之下的社会,也将“监狱行刑悖论”在社会化层面放大 福柯的学术倾向与风格带有很深的个人生活与经历的烙印,有学者认为“从一定角度上看,他的全部著作都反映了一个被社会认为不正常的人对所谓‘正常’的反抗,要为不正常寻求一个生存的空间,为使那些被压抑的声音能为人们所听见”。福柯认为,现代社会中,规训权力已经扩展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个个体时时处处都处于微观权力的规训之下。人的主体性在这种严格的规训之下窒息。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监狱、工厂、军营、医院、学校等规训单位连续统一而构成的“监狱群岛”。社会总体像一个巨大而没有围墙的监狱。这里,“监狱行刑悖论”在反身意义上被放大:人们将那些被认为“不正当(或不正常)”的成员投入(微观意义上的)监狱,实施隔离、监视、训练和控制,从而保护自身主体地位。然而在这种“正当”且“正常”的话语之下,监狱实际上不停地制造“过失犯”,反过来通过他们对社会实施隔离、监视、训练和控制。各种类型的“监狱”通过制造各个领域中“驯顺的肉体”,将现代人从真实意义上的“人”转化为所谓的“主体”。福柯一生,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行动上,都在挑战和反抗这个处处制造着“悖论”、又以“正常”来掩饰“悖论”的巨型监狱,寻求真正意义上的“自我”。 四、福柯之“他者视角”的法律社会学价值
福柯对历史资料的诠释总是“天马行空而发人深省”。他以颠覆性的视角重构了“监狱行刑悖论”的生成机理和社会功能,在带来理论惊骇的同时,揭示出现代刑罚学理论框架之内被忽视的一些重要论题。笔者并不想借此文讨论刑罚或刑法学领域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甚至并不认为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潮在当下中国法学领域中有超越人文主义和启蒙精神的可能和必要,但它们确实为反观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困境提供了一面镜子,提示我们在熟稔的现实资料中发掘多元化的理论径迹。就“监狱行刑悖论”问题而然,福柯的“他者视角”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法律社会学价值: (一)“监狱行刑悖论”的存在,根源于被行刑人主体性的弱化或丧失 福柯总结自己毕生理论研究的核心在于对“主体问题”的讨论。他反对人文主义的“主体”观念,认为作为现代权利“主体”的“人”不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知识概念,是现代人文科学的知识建构。他认为是无处不在的“规训”扼杀了人的自然本性,而在对肉体的操纵中将“人”改造为“主体”,并使被规训者内化的接受了这一异化的“主体身份”。在现代监狱的行刑实践中,这些已经被“异化”了的“主体”,再次经历监狱中的特殊“规训”,而再次深度异化为“犯罪人”。刑罚剥夺了犯罪人自由的同时,要求犯罪人在监狱中必须按照既定的程式和秩序行为,甚至必须接受特定的价值体系才能被认定为“改造效果良好”。然而“改造良好”的服刑人回归社会之后,其在监狱中被形塑的“监狱化人格”却成为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这种“监狱化人格”,是“服刑罪犯在封闭、隔离的刑罚执行条件下,在长期严格、单调、刻板的监禁生活中,通过对罪犯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对监狱当局制定的正式规则和制度的学习与接受,对监狱普通文化的学习与内化”,逐渐形成依赖性增强、受暗示性增强、思考能力下降、惰性增强等特质。虽然这一效应并不见得如福柯所言,是监狱管理者的主观追求,但从现实来看,“监狱化人格”的确突出表现为个体的主体性意识弱化甚至丧失。任何寻求克服“监狱行刑悖论”的努力,都必须正视这一症结。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和实践尝试,找到使被行刑人恢复“人格自主”节点,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监狱行刑悖论”。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社区矫正为代表的一些非监禁行刑方式,在方法论意义上有助于更好的恢复被行刑人主体性特征。 (二)多元视角考察“监狱行刑悖论”,避免陷入“监狱总是被当做自身的补救办法”的理论怪圈 “监狱行刑悖论”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现象。教育刑理论、犯罪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甚至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都可能、也仅仅是可能解释了其成因的一个侧面。福柯一贯反对宏大叙事和元叙事、反对构建一元的“真理”性话语。他对“监狱行刑悖论”的独特讨论,至少从两个层面提示研究者拓展思路:其一,不仅要从“操作—功能”角度检讨监狱行刑理论和实践,同时应当对监狱体系和相关制度的设计目标进行反思;其二,避免一味追求线性意义上的“进步”,对监狱行刑实践开展真正多元化的尝试和探索。 从福柯的视角来观察,监狱中的被行刑者实际上经历了“双重异化”过程:人——作为主体的人——监狱化的人。现代监狱管理理论、刑罚理论旨在寻求如何使“监狱化的人”回归为“作为主体的人”;而福柯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远,力图寻求使“作为主体的人”回归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虽然在理论立足点上有差异,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以下有价值的提示: 1.社会的“规训”使“人”变成了“主体”,监狱的“规训”又再次使“主体”变成了“罪犯”。因而,主体性的获得和丧失都可以通过特定的“规训”方式予以达成。通过适当的“规训”方式的创制和实施,可以实现“主体性”的恢复。 2.克服“监狱行刑悖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脱离监狱的“规训”环境。 3.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使犯罪人“回归社会”。 (三)重视行刑过程中多元化、分散化的“权力”及其作用 福柯认为,权力并不源于某个中心,权力是多元的,来自于各个地方。虽然他因完全无视现实意义上国家权力在多元权力中的特殊的地位和主导作用而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但他也确实敏锐的发现了国家权力理论之外,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微观权力。当代监狱行刑的相关研究也印证了多元化权力存在的现实:犯罪人在监狱环境中的习得和养成,不仅来源于官方(国家)的价值和规训,也来源于犯罪人群体中的各种亚文化,甚至管教人员的价值体系、具体监狱的特定物质环境和管理传统都会对犯罪人的改造状况产生影响。因此,“监狱行刑悖论”的克服,必须重视多元化权力的作用,将多元“微观权力”运作的过程纳入到监狱行刑研究的视野中来。
五、结论
“监狱行刑悖论”是当代刑事法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以微观权力之“规训”为核心,重构了“监狱行刑悖论”的生成机制和社会功能。其独树一帜的理论风格和敏锐、深刻的洞察力,提供了反观已有研究成果的理论参照,为“监狱行刑悖论”的克服,提供了具有法律社会学价值的思维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