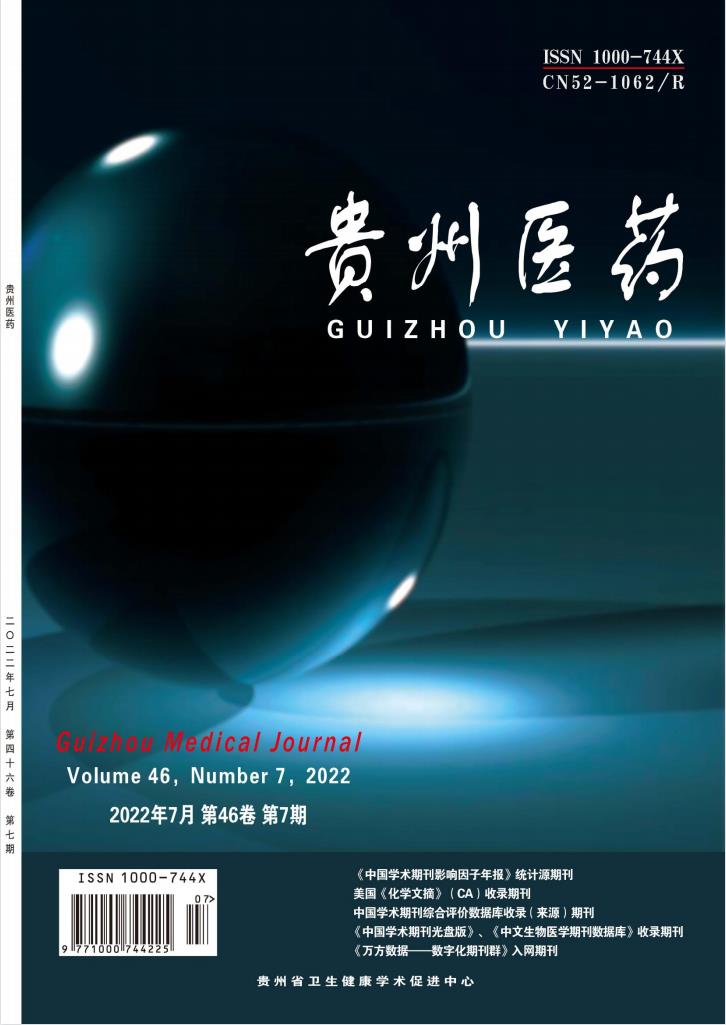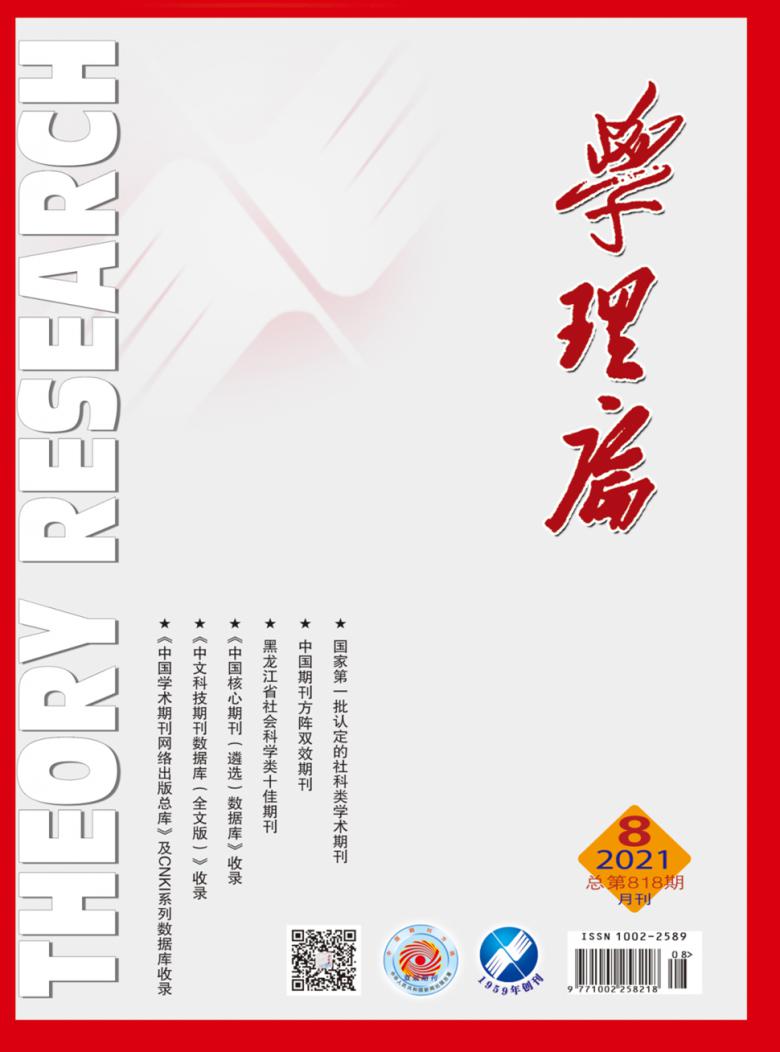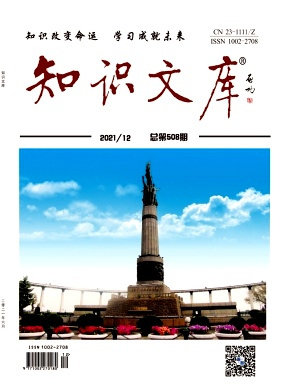我国监狱行政处罚形式的历史演进与适用程序
佚名
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应执行《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形式宜为警告、禁闭、罚款、没收非法财物、责令赔偿或科以某种作为的义务。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过程中,监狱规范执法活动,保障罪犯合法权利必须依据法定程序,必须用一套程序制度保障实施。
一、我国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的历史演进。
我国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监狱对罪犯违反监规纪律的处罚形式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处遇限制和禁闭,行政处罚没有单列。但是,受惩罚过程中罪犯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处罚形式也有逐渐趋向人道、文明的趋势。建国以后,在有关监狱的法律、法规中,行政处罚才从对罪犯日常生活处遇的限制、制裁中分离、单列出来。但是,在行政处罚的方式中却列出了一个不规范的“记过”。
1、清朝末年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监狱规则》
清朝末年是早期监狱立法的雏形期,监狱改良运动是北洋军阀政府正式颁布《监狱规则》的前奏。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监狱法典是《大清监狱律草案》。1904年清政府设立修订法律馆,沈家本任修订法律大臣。他同武廷芳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狱制改良的立法活动。1908年,清政府聘请了日本监狱学家小河兹次郎出任狱务顾问,起草监狱律及设计改建监狱的规划。同年《大清监狱律草案》递交法律馆审查,于1910年上奏,但未颁布实施。据《大清监狱律草案》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惩罚之种类如下:一、叱责;二、三月以内停止赏遇;三、废止赏遇;四、三次以内禁止接见;五、三次以内禁止发受书信;六、三月以内禁止阅读书籍;七、十五日以内停止陈请作业;八、一月以内停止使用自备之衣类卧具及杂具;九、一月以内停止自备粮食;十、七日以内 停止运动;十一、削减作业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十二、七日以内之减食;十三、二月以内之独慎;十四、七日以内之屏禁。独慎令受罚人昼夜屏居于罚室内,其课作业与否得斟酌情形定之。屏禁令受罚人昼夜屏居于罚室内,暗其罚室,禁用卧具。”
《大清监狱律草案》第十二条规定了在监人不服的申诉权、申诉方式、监狱官员的回避及申诉裁决的效力。
《大清监狱律草案》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的监狱法,基本上照搬了日本的监狱法。虽然没有颁布施行,但是却成为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颁布的《监狱规则》的蓝本。
北洋军阀统治前后持续了16年,从1912年起到1928年起到1928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洋军阀政权宣告覆灭。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是袁世凯统治时期,1916年6月至1920年、1920年至1924年、1924年至1928年分别为皖系、直系、奉系军阀统治阶段。由于政权更迭,连年战争,虽然全国创办了80座新式监狱,颁布了一些监狱法规,但是,由于国库空虚、监狱经费拮据,新监难以维持,受战乱影响较大。这一时期的《监狱规则》规定:在监者违反监规纪律时处以面责,停止发受书信、接见及阅读书籍,减食、停止运动,减削赏与金,慎独、暗室监禁,酌减赏与金等惩罚。受罚者有疾病及其他特别事由时得停止惩罚。受惩罚者,有悛悔情状时免除处罚。以上条款与《大清监狱律》的内容大同小异。
2、民国时期的监狱和监狱法规。
民国时期1927年至1949年的监狱,一方面基本上承袭清末、北洋军阀政府的狱制,同时又吸取了资本主义国家监狱立法的一些内容,监狱法规比较完备、严密。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于公布了《监狱规则》和《监狱处务规则》(1928年10月),《监狱行刑法》和《监狱条例》(1946年1月19日)。军政部公布了《军人监狱规则》(1930年8月)。监狱的内部机构设置、各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等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至今没有规定,可见其详细和完备。
民国十七年十月国民政府司法部公布的《监狱规则》第八十六条规定:“在监者违反监狱纪律时得处以下各种之惩罚:一、面责;二、三月以内停止赏遇;三、撤消赏遇;四、三次以内停止发受书信及接见;五、三月以内停止阅读书籍;六、七日以内停止运动;七、减削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八、二月以内之慎独;九、五日以内之暗室禁闭。前列一与各种惩罚得并科之。”
民国十九年八月军政部公布的《军人监狱规则》增加了“掌责”(由监狱长酌量情节轻重得施以四十板以下之掌责)。
康德四年十一月公布的《伪满洲国监狱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惩罚之种类如下:一、叱责;二、七日内停止运动;三、二月内禁止阅读书籍;四、二月内禁止使用笔墨;五、削减作业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六、七日以内之屏禁;七、二月内停止赏遇;八、废止赏遇;九、十五日以内停止著用自备之衣类、寝具;十、十五日以内停止自备饮食。第一项各款之惩罚得并科之。”
台湾监狱,罪犯受行政处罚时,其权利较以往已有所扩大。
台湾现行的《监狱行刑法》是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公布三十六年六月十日开始施行的。以后经过多次修订。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受刑人违背纪律时,得施以下列一款或数款之惩罚:一训诫。二停止接见一至三次。三强制劳动一至五日,每日以2小时为限。四停止购买物品。五减少劳作金。六停止户外活动一至七日。”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告知与辩解权,第七十九条规定了撤消惩罚的情形。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监狱和监狱法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建立的监狱溯源于1927年11月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期间,早期是在各地工农武装暴动的过程中,各地肃反机关建立的拘留所、看守所。关押对象主要是各种反革命犯和部分刑事犯。由于政权不稳,经常处于游击状态,因而以看管住犯人不逃跑为主,管理简单,没有制定专门的监狱法规。1932年8月10日,中华苏维埃司法人民委员会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这是工农民主政权的第一部监狱法规,监狱管理初步有法可依。劳动感化院既是改造机关又是生产单位,是后来人民民主政权监狱机关的雏形,这时除看守所关押未决犯外,还设立了苦工队 用以关押短刑犯。这一时期曾出现了左倾错误,如:1934年5月人民委员会发布训令,在战争地区对地主全部编入永久劳役队,富农编入临时劳役队,强制劳动。后来随着南方根据地的丧失,监狱数量逐渐减少。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抗战时期。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各根据地的监狱陆续产生。抗日民主政权的监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37年至1940年时期缺乏监狱管理经验和统一的监狱管理制度以及旧的监狱管理制度和思想的影响,各监狱不同程度的出现过管理方面的偏差。1941年至1943年期间,监狱形态由单一的看守所发展为专门的刑罚执行机关-------自新习艺所和监狱,1937年7月12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并建立了高等法院看守所,1941年后,县级看守所设立。1942年9月陕甘宁高等法院监狱建立。1943年至1945年,颁布一系列监狱法规和监狱管理制度。
陕甘宁边区的监狱规定了罪犯不服处罚的申诉权。
1944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押人犯服刑奖惩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如人犯服役有消极怠工或其他不良行为者,得按情节之轻重给予下列惩罚:“(一)批评(包括个人及小组批评);(二)全体讨论斗争;(三)停止或撤消奖金之一部或全部(此项所称一部或全部分月季年三种,视其情节轻重定之)”。第十六条规定了不服惩罚的申诉权。即:“实施第十三条第三款惩罚应经各部门会议通过,如被惩罚人不服,得向本院申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监狱管理规则》第十三条规定:“守法人如有违反规则,按情节轻重予以下列各种处分:一、打扫公共卫生;二、于工作时间外加工或分配较苦的工作;三、扣除应得奖励或红利之全部或一部;四、刑事处分。”
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刑事处分”与不属于同一层面的内容混列在一起,反映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立法的局限性。
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管训队以收押俘虏为主,劳动改造队以生产为主、半军事化管理,这一时期主要是专项打击的文件、政策,没有产生专门的监狱法规。
4、建国以后的监狱和监狱法规
建国初期的监狱主要是关押土改、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1951年5月在全国第三次公安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示“为了改造这些犯人,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于是,全国的县、专署、省、大行政区、中央各级均设立了劳动改造管理部门,开始劳动改造罪犯。1954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以下简称《劳改条例》)。
1966年至1976年十年动乱时期,监狱工作受严重破坏。全国监狱数量减少百分之六十,法规、正常秩序被践踏,制造了以一大批冤假错案。
行政处罚的名称和形式是在建国以后的监狱法规中开始出现的,这是监狱立法的进步,但是,在行政处罚的形式中却出现了不规范的“记过”这一“罚种”。清末至建国前成文的监狱法均没有“记过”之规定。正式出现“记过”规定的是《劳改条例》第六十九条:“犯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记过或者禁闭等惩罚:(一)有妨碍其他犯人改造的行为的;(二)不爱惜和损坏生产工具的;(三)在劳动中懒惰怠工的;(四)有其他违反管理规则行为的。”第七十条规定奖励和惩罚“经过劳动改造机关负责人审核批准后,宣布执行。”
从“监狱负责人审核批准”到“中队队务会集体讨论”,经历了二十八年。
1982年,法条中开始出现“行政处罚”字样。但是在这以后,内容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和发展。
改革开放后的第十四年,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1954年的劳改条例已不适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国际人权组织激烈地攻击我国的监狱人权问题,制定适合新形势发展的监狱法典已势在必行。1994年12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部监狱法典。它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对监狱的客观要求,标志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确立和完善。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仍保留了记过,在“禁闭”之后取消了“等处罚”字样,对“下列情形”限制了其他种类的行政处罚,在我国的监狱的劳动改造史上,“记过”迄今已经有四十八年的历史。
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狱法多以前苏联的监狱法为蓝本。1969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公布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劳动改造立法纲要》对于违反服刑管束制度要求的被判刑人的处罚措施种类中,有警告、禁闭,却没有记过。看来,前苏联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狱法的行政处罚形式也多仿造前苏联。只有我国监狱法有记过,与前苏联的监狱法不同。
二、我国监狱法有关行政处罚条款存在的问题及适用行政处罚的内容及形式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出台是为了适应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回应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对我国监狱人权问题的攻击,因而,监狱法的内容多规定的比较原则。这样的好处是不易受人以柄,不足是具体操作难以适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纰漏,行政处罚也不例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行政处罚有关法条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罪犯有下列破坏监管秩序情形之一,监狱可以给予警告、记过或者禁闭……”这里,列出的所谓警告、记过或者禁闭,是行政处分还是行政处罚呢?归于行政处分显然是不合法的,因为行政处分是国家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根据行政隶属关系,依据有关法规或内部规章,对其系统内部违法失职的内部工作人员实施的一种惩戒措施。罪犯当然不具有国家公务员或企业、事业在编职工的主体资格。那么是否可以算作行政处罚呢?我国行政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形式中,不包括记过。记过是行政处分的一种。警告是行政处罚形式中声誉罚的一种。禁闭也未列入我国行政处罚法的罚种,但是,从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的具体执行方式、内容上看,实质上接近于人身自由罚。因此,可以视为一种行政处罚。由于罪犯不具有国家公务员或企业职工的主体资格,不能适用行政处分,那么,监狱法前款规定的只能是行政处罚。
2、行政处罚内容的分类及适用对象
行政处罚按照内容可以分为四类。一、人身自由罚:1、行政拘留;2、劳动教养。二、行为罚:1、责令停产停业;2、吊销、暂扣许可证、执照;3、科以相对方某种作为的义务。三、财产罚:1、罚款;2、没收财物(非法所得,非法财物);3、责令金钱、物质赔偿。四、声誉罚:1、警告;2、通报批评。以上四类10种行政处罚中,行政拘留,劳动教养,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暂扣许可证、执照通报批评这五种不适用于罪犯,其他五种可以适用。修订监狱法时,应当明确规定,对罪犯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适用《行政处罚法》。“记过”作为行政处分的一种,不能列入监狱法的法条,应当在修订监狱法时,予以删除。
3、我国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的内容及形式
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的形式可以分为警告、禁闭、罚款、没收非法财物、责令金钱、物质赔偿、科以某种作为的义务等6种。《行政处罚法》设定的行政拘留、劳动教养、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暂扣许可证、执照4种处罚,因罪犯刑罚执行的监禁方式和相应的行为能力限制而不能适用。通报批评只适用于法人或其他组织而不适用于自然人。因此,前款所列的6种处罚,监狱依据《行政处罚法》应当是可行的。即罪犯有监狱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监狱可以给予警告、禁闭、罚款、没收非法财物、责令金钱、物质赔偿或者科以某种作为的义务。例如,“盗窃、赌博”产生的“非法财物”可以予以没收。“故意破坏生产工具的”可以责令金钱、物质赔偿或科以修理完好、恢复原状的义务。这样设定、实施行政处罚,更切合实际,更具有针对性。新增设定的罚款、没收非法财物、责令金钱物质赔偿、科以某种作为的义务这4种行政处罚,符合我国市场经济法治条件下公民的经济义务、作为义务逐渐增加的趋势。实质上,是增加了罪犯行政违法行为承担责任的义务内涵,使监狱对罪犯不同的具体违法行为,能够根据具体情形设定相适应的行政处罚方式。这样,将丰富监狱法行政处罚的内涵,使监狱法行政处罚这一块,趋于合理、完善。这样才符合处罚法定和过罚相当的原则。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皈依处罚法定原则,公正、公开原则,处罚救济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和一事不再罚原则,有助于增强监狱人民警察的法治意识和促进监狱整体工作的社会化。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必须要注意的是:罪犯的违法行为客观存在并且未超过追究责任的时效;必须是行政违法;实施处罚权的必须是适格主体,符合法定程序和审批权限。具体适用行政处罚的形式、条件,参照《行政处罚法》可以在修订监狱法或制定监狱法实施条例时,用相应的法条予以明确规定。
三、我国监狱适用行政处罚涉及权利保障的司法实践状况
按照我国行政法的法理原则和《行政处罚法》适用行政处罚必须遵守法定的程序。行政程序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即指行政行为所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以及时限的总和。然而,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还是《劳改条例》以及《管教工作细则》,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的程序,均无明文规定。这是我国刑罚执行立法的一个重要欠缺。
1、罪犯受行政处罚时享有的法定权利
监狱对罪犯科以行政处罚,在具体适用监狱法第五十八条时,在适用程序上无法律依据。直接后果是,易造成监狱对罪犯的行政处罚的随意性,执法失去规范;罪犯受行政处罚时,应当具有的基本权利,在法律程序上缺乏保障。罪犯是特殊的公民权利主体。依据我国宪法,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是中国公民。罪犯服刑后,并未失去国籍。而且,罪犯作为公民,仍然享有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其他权利。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并不因为犯罪服刑而丧失公民这一主体资格。与普通公民(非犯罪公民)相比,罪犯权利主体带有一定的特殊性,表现在罪犯权利主体局限性,期限性和不完整性。一定的特殊性是指法律赋予罪犯的某些特殊权利以及罪犯行使权利的某些行为能力被依法剥夺或限制。同时,《监狱法》第十七条规定:“罪犯……未被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明确以法律规定,保护罪犯的权利能力不受侵犯和行为能力的行使。即,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凡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罪犯都享有。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已于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这一条,列举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适用行政处罚时的权利。即:陈述权、申辩权、申请复议权、提请行政诉讼权、以及依法请求赔偿权。对于罪犯,这些权利并未被依法剥夺。相反,是应当依法保护的权利。
2、罪犯受行政处罚时权利保障的法定程序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行政处罚适用过程中的罪犯权利保障,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固定下来。行政处罚程序合法,是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是行政处罚有效的必要条件。《行政处罚法》第五章,专门规定适用行政处罚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该法总则第三条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律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然而,监狱在适用监狱法第五十八条时,往往是另一种情况。例如:2000年1月,某监狱一罪犯陈某因“用玻璃在手腕上划了两下,逃避劳动”,“态度恶劣,不服管教,气焰十分嚣张,依据监狱法第五十八条,予以警告处分”。经了解,陈犯“受处分”后一个月,竟茫茫然不知道自己已经受行政处罚。分监区既未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罪犯本人,也未通知公布。分监区未依法制作法定格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而是用“罪犯奖惩审批表”取而代之。在这个实例中。分监区对陈某适用行政处罚,依据《行政处罚法》显然是违法的,是无效的。然而,在现实中,却是有效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国监狱法法条对行政处罚种类、形式及适用程序上,存在着严重问题。监狱法并没有规定监狱在对罪犯进行行政处罚时适用《行政处罚法》。分监区干部讲的,乍一看也不错呀,无法可依嘛。其实不然。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五章,规定了适用行政处罚条件、范围、程序种类及应遵循的程序步骤。在行政处罚的简易程序中,行政主体的执法人员在进行当场处罚时,应当遵循的程序是:一表明身份;二说明处罚的理由;三给予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四制作笔录;五制作当场处罚决定书;六备案;七执行。在行政处罚的一般(普通)程序中,包括以下几个步骤:一立案;二调查取证;三听取申辩与听证;四作出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以上程序步骤显而易见。对于一般程序,需注意的是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一个行政处罚决定必须适用一般处罚程序。
四、我国监狱具体适用行政处罚过程中罪犯权利保障的程序制度
徒法不能自行。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仅仅依据《行政处罚法》是不够的。必须依法结合监狱工作的具体操作步骤,将法定的程序分解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罪犯权利保障应当是通过行政处罚程序中监狱的严格依法办事来实现的,即在行政处罚程序环节中,使罪犯的陈述权、申辩权、申请复议权、提请行政诉讼权以及依法请求赔偿权等,能够由程序制度保障行使。
1、立案及调查取证阶段
监狱在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时,发现罪犯的违法行为符合立案条件,首先应当立案。立案是行政处罚的启动程序。应当填写《立案报告表》,经监狱长审查批准后即完成了法律上的立案程序。被指定的办案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办案公正的,应当予以回避。监狱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和监狱长对立案报告不予批准的,应当制作《不予立案报告书》。如果案件涉及利害关系人的,应当将不予立案报告书送达利害关系人,该人如不服此决定,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监狱在对罪犯的违法行为立案后,应当客观、全面、公正地调查、搜集有关证据。监狱在进行调查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监狱传唤罪犯进行讯问时,应当制作笔录。笔录须经罪犯核对认为无误后,罪犯应当在笔录上签名、画押。监狱在调查取证时,对罪犯违法行为的有关物证,书证可以依法扣押。但是,监狱执法人员必须查点清楚,开具暂扣单一式两份。由执法人员,见证人、罪犯签名后,一份由监狱办案部门收存,一份交罪犯。监狱在调查过程中,根据需要进行鉴定、勘验,可以委托有关法定的机构、组织进行。对勘验情况和结果应当制作笔录,由执法人员,见证人,当事人签名、盖章。鉴定人、勘验人于罪犯有直接利害关系,应当申请回避。
2、告知权利阶段
监狱在调查取证之后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罪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罪犯依法享有的权利(《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罪犯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监狱必须充分听取罪犯的意见,对罪犯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罪犯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监狱应当采纳。监狱不得因为罪犯的申辩而加重处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监狱在向罪犯履行告知权利程序时,应当告知罪犯适用行政处罚法的权利、种类及期限。除申辩权、陈述权,罪犯还具有申请复议权,提起行政诉讼权和依法请求赔偿权(见《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涉及数额较大的罚款以及“收缴”、暂扣财物去向不明等案件,罪犯主张权利要求的,还应当适用听证程序。
3、提出处罚建议和作出处罚决定阶段
经过以上程序,监狱如果确认违法事实确实存在,并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处罚建议书报上级监狱管理局。如果监狱管理局发现罪犯违法行为不存在或者事实不能成立的,则不能给予行政处罚,而应制作撤销案件决定。如果罪犯有违法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应作出免予处罚的决定。如果认为罪犯不仅有违法行为,而且该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则应将有关材料移送有权机关处理。其中,给予行政处罚,应当由监狱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报监狱管理局加盖公章予以公布(《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罪犯的姓名、地址;违犯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与证据;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复议或起诉的途径和期限;作出处罚决定的监狱管理局名称和决定日期。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罪犯本人;罪犯不在场的,监狱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罪犯本人(《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同时,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关驻监狱检察院(室)备案。
4、侵权责任追究及损害的赔偿、救济阶段
199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罪犯在人身权、财产权受到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法侵害时,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并规定了取得国家赔偿的程序和方式。1995年9月司法部四十号令《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办法》第四章第七条,规定赔偿请求人的申请复议权。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了行政复议的适用范围和程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作为行政处罚的补救程序,在立法上已经完成。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时启动补救程序,是符合行政法的法理原则的。即符合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
监狱只有依照法定的程序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才是合法的,合理的。才符合行政程序法的程序公正原则,相对方参与原则和效率原则。反之,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显然,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已在追究法律责任之列。
监狱依法通过立案及调查取证,经过向罪犯告知权利程序,提出行政处罚建议,作出处罚决定。经过一定的权利主张期间,处罚决定生效后,还有侵权责任追究及损害赔偿的救济程序,以上各环节必须通过一套程序制度,保障行政处罚的公平、公正、合理。
综上所述,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各环节构成一个系统的整体,环环相扣。其中,重要的作用是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规范和制约;是对被处罚当事人合法权利的程序制度保障;确保行政处罚的公正、合法、合理。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只有皈依法定程序,才能避免实际工作中的盲目处罚,违法处罚。罪犯的合法权益才能依法得到保障。否则,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不分,主体资格不具备,程序无限制,则不符合依法治国、依法冶监的法理内涵。对此问题,有待于修订监狱法时予以匡正。
(1) 董元虎、刘武萍编著。世界人权约法总览。[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2) 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 曹沛霖等主编。外国政治制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192。
(4) 魏定仁主编。宪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5)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6) 金鉴主编。监狱学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7) 梁立民主编。简明中国监狱史。北京:群众出版社,1994。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编。中国监狱史料汇编(上、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