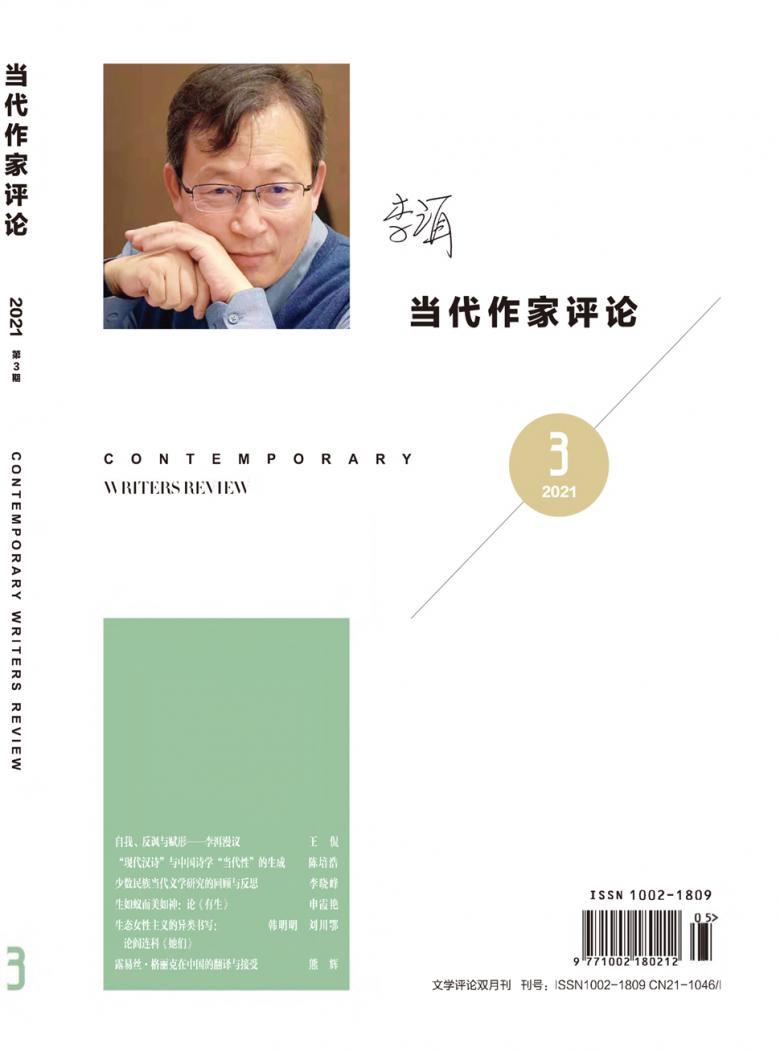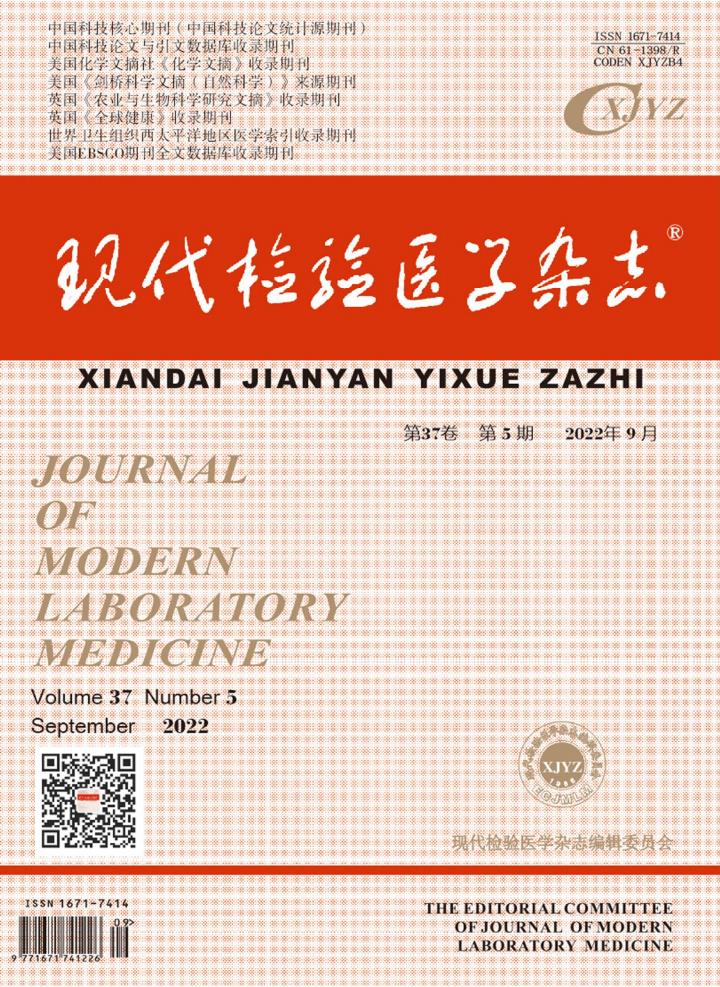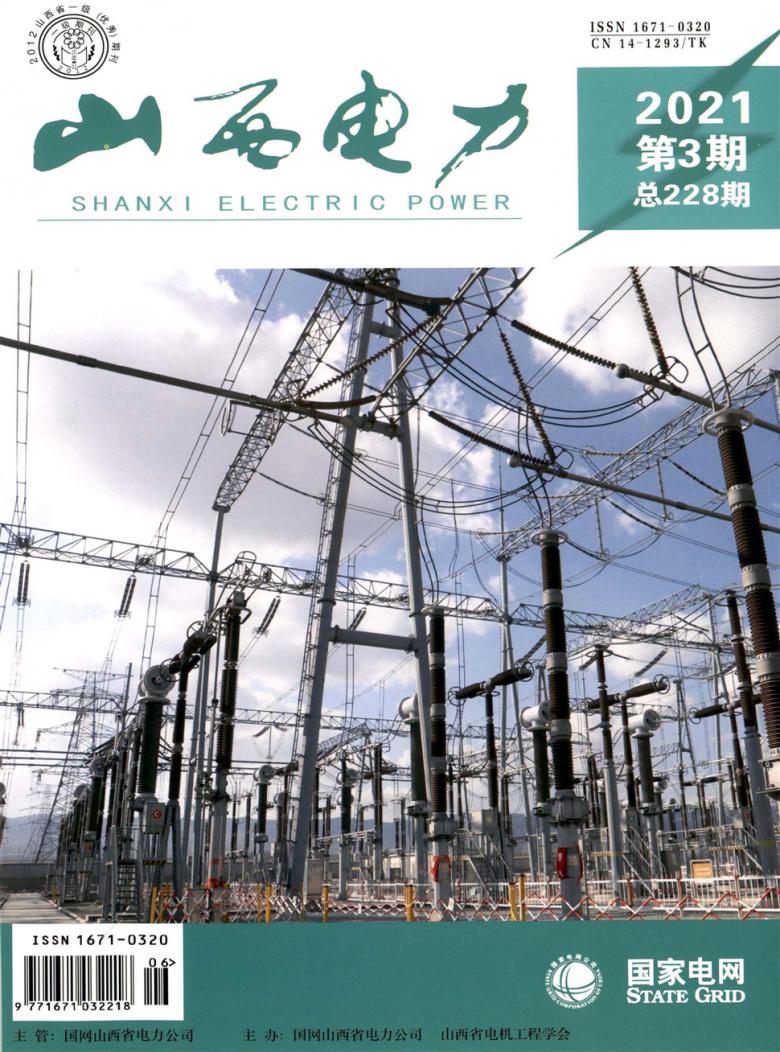抗战时期中共群众动员的组织机制论析——以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
张孝芳 2010-12-15
[论文关键词]正式组织;社会网络;政治动员
[论文摘要]本文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阐释了正式组织和社会关系网络在党的群众动员中所发挥的功能及其互补作用。为了有效地动员民众,中国共产党首先以正式组织为起点,将动员对象最大范围地吸纳进来。在正式组织的框架下,以“革命道德”标准确定各个不同的群体在组织中的位置。在寻求行为一致、目标认同的基础上,党利用非正式组织来推动和促进集体行动,将湮没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激活。
1935年秋,随着中共长征落脚陕北,陕北成为中国革命新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进行着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革命和改造工作,力图使共产党的影响渗透到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以便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打下基础。而一种社会秩序基础的稳固性在于创造有效的社会关系。正如社会学家所揭示的,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但带来了行动动员的条件,也提供了适当的环境以形塑特定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中国共产党在陕北乡村社会的诸多举措,正是通过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过程,在边区乡村民众中间建立起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来塑造一个惯于集体行动的乡村社会,从而为党的群众动员提供结构性的条件。本文即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共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阐释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在中共群众动员中的作用。
一、正式组织的建立与乡村社会的组织化
将社会各群体组织起来是共产党的一贯工作方针。1939年,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明确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据一项统计,在陕甘宁边区,各类群众团体达25个之多。概括起来,在边区,一个普通的乡村社会大致可以分为3类群众性组织,一类是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如农会、减租会、变工队或扎工队、妇纺小组、合作社、运输队等;一类是群众性的文化教育组织,如小学、冬学、村学、识字组、夜校、民教馆、读报组、黑板报、秧歌队、卫生小组等;一类是群众性的军事组织,如自卫军、民兵、少先队及儿童团等。众多的组织将乡村各个不同的群体吸纳进来。经常的情形是一个农民可能参加七、八个组织,尽管许多人在有些组织中只是挂个名而已。
这些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产生,为执行党的政策展开工作。因此,尽管这3类组织性质不同、功能各异,但在人员构成上彼此交叉、重叠,使农民个体与组织都带有多重性特征。比如,在组织变工队时,往往先利用学校、读报小组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酝酿,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在开展社会教育运动过程中,也会借助生产组织来进行。经常的做法是直接将变工队、妇纺小组等生产单位变成识字小组、读报小组,利用生产之暇进行识字扫盲的社教工作。而自卫军组织也被认为是“最便利于进行社教活动的场所”。许多地方的民兵组、担架组同时也是识字组、读报组。在边区,每个小学的学生都要参加当地少先队,而教员则成为自卫军、少先队的文化政治教员,经常去给他们教字或政治课。李公朴在华北就观察到,在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儿童团里,妇女自卫队里经常有人报告时事,或是讲解当前重要的政治问题。他评论说,这并不是什么别的工作,而正是没有折扣的教育工作。
在社教运动开展的实践中,农民还发明出一种叫做“变工教学”的方式,将识字与生产的劳动力进行交换,使识字与生产两不误。1944年,《解放日报》就登载了这样的事例:在米脂县印斗区第七乡高家沟村,由于村子贫困而又分散,全村仅有村民高怀山读过4年书,全村人几乎都是文盲,乡里的指示经常被耽误。因此,当地民众便想出了“变工教学”办法,设立民众学校,由教员承担教育全村娃娃的任务,教员的地则由众人分工合作来负责。教员还组织成立妇女识字班、变工队读报组,这样既不耽误生产又开展了学习运动,两头不误。
在组织化的方针之下,边区社会的民众很快被纳入到各种组织中去。“各业工人百分之九十五加人了工会,农民全体加入了农民会,边区青年绝大多数加人了青年救国会,边区妇女百分之七十以上加人了妇女救国会”。在社会教育运动中,据称,在建立新延安之后,仅仅五六个月的时间,文盲和半文盲全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便已经过着有组织的教育生活了。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化的生产、生活成为社会民众所熟悉的状态。这正是党所期待的。毛泽东在关于农民被组织到劳动互助合作社问题上曾有这样评论:“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提高,文化也会进步,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因此,正如外界人士所观察到的,真正的权力并不属于选举出来的议会或政府,而属于革命本身的机构,即群众团体,如青年团、妇女会、农民协会等。这些群众组织的革命职能即在于提供一种手段,或创造一种气氛,使新政权能够扎根、成长。换言之,这些组织抑或组织化了的民众是革命进程中的一环。尽管这一环可能只是革命奠基工作中的一部分,但这种集体劳动、合作互助方式“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感受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浪潮”,从而为乡村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动力。
二、组织框架下的乡村社会分层
如果说,“组织起来”是党的群众工作方针之起始点,那么,接下来的工作步骤即是在群众内部划分类型,对他们进行归类定位。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对这一工作方法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根据这一“三分法”,乡村社会的群体被划分为积极分子(如英雄模范)、落后分子(如二流子、巫神等)、中间分子等类型。随后的工作即是针对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从而实现以分进合击的方式改造并整合所有群体,并将他们纳人革命航道的目标。
首先,对积极分子,如英雄模范、优秀典型等,党给予充分的礼遇。他们是党所倚赖的对象,因为党的政策之推行与贯彻需要他们的首先响应、率先行动并组织其他人随后跟进。毛泽东总结说,劳动英雄的作用就体现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因此,他高度重视通过活生生的榜样对民众的示范和引导。为了推动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应即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和当地情况发出指示,并亲手检查几个乡村,发现模范,推动他处。同时,应在报纸上发表关于减租的社论和关于减租的模范经验的报道”;他批评说,“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上粪)推行于各地……是错误的”。他出席边区的各种劳动英雄大会,和各个领域的模范们交谈,颁发奖章,表扬他们。
其次,对落后分子的问题上,则是打击和改造双管齐下。如为了推进“二流子”改造工作,党的各级组织者首先对二流子进行了归类划分。完全无业而靠不良行为为生者,如巫神娟妓、贩卖鸦片烟的,是正式的二流子;有正当职业而兼靠不良行为维持生活者,是半二流子;如只有不良嗜好,就不能算二流子。查清了这些,然后将他们编成二流子小组,采用不同的方式区别对待。对于巫神等落后分子,也先对他们所犯错误程度轻重进行划分,采取不同处置方式,“巫神之以酷刑治病死亡者,应以法究办。至于一般的反迷信活动,则应依靠青年站的觉悟与自愿进行之,以免与群众相对立”。
再次,对于中间分子,包括旧社会遗留分子,比如旧绅士、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等,也包括那些在态度上游移不决、处于冷漠或观望态度的广大中间化民众,党的政策倾向于改造和教育。以社会教育为例,在对待私塾先生、民间教育家问题上,党的政策一方面是团结他们,充分发挥他们在扫除文盲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施以新的教育和改造,帮助他们提高。同时对他们即使是微小的改变和进步,也加以表扬。
显然,这种社会分层不同于传统乡村社区以士绅与大众二元格局为基础的划分,而代之以“革命道德”对乡村民众进行的重新划分。“革命道德”在乡村社会设置了一种选择性机制,凡是对革命贡献大的,对革命工作积极的,就是值得肯定的,是依赖对象。反之,则是否定的,被批判对象。依据不同的群体类型,对其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态度,或是激励他们、帮助他们;或是改造他们、纠正他们。这是一个联合和排除的双向过程,既可以划分出那些被认可的行为规范,也可摈弃那些为革命所不容的意识和行为。通过这种划分,党的精英试图使民众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得到鼓励的。正是这样一种“革命道德”的设置,使民众分散的选择或力量得以集中,同时也为使他们的目光从个人的天地聚集到革命的动员目标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三、社会关系网络下的群众动员
为了形成持续的动员力量,还需要更加耐心和细致的工作环节,这就是作为非正式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举措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和频繁沟通来传递信息,传播革命,并以积极分子的范例来引导民众接受和认同革命,从而把同情革命的旁观者吸收到革命中来。
人际互动的第一支力量就是乡村社会的儿童,尤其是上学的小学生们。1942年2月1日,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这一文件指出,小学学生应于课外参加破除迷信、讲究卫生等项宣传和社会教育及生产劳动,以补助其课内学习……边区各小学应利用假期、星期天、课外活动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如进行抗战宣传,帮助自卫军放哨、送信、探消息、查路条、捉汉奸,参加春耕秋收、优待抗属、动员新兵、读报、扫盲等。在有关冬学的经验总结中也指出,“我们应把平时的小学教育和普通的社会教育联系起来。采取适当办法来(进行)普遍的社会教育和训练小学生,提高每个小学生的责任心,将他们培养成为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传播者,即训练与实行小先生制,经过他们来影响与教育他们成年、老年或失学的父、母、伯、叔、兄、嫂、姐、妹等,将抗战知识广泛深人的传达到广大民众中去。”负责社会教育的组织机构—各县三科和社教指导团也都被明确要求每逢市镇大的集会都要领导小学生到会举行识字教育宣传工作,或小学组织宣传队,每礼拜到附近乡村去宣传识字教育工作,并在市镇交通要道张贴关于识字的标语。。
在边区社教运动的开展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在教育厅下发冬学计划到各乡后,各乡的小学就开始了冬学宣传周,小学生跑到家家户户作深人的冬学宣传。“娃娃儿童劝着爸爸妈妈读书,常成为最有力的动员方式”。“每个小先生都是清洁卫生、妇女纺织、劳动生产的宣传与组织者。小先生们教给每一个妇女儿童要好好劳动生产。”⑥绥德六区有个安家婆姨不讲卫生,徽得不愿生产,坤元(小学生)整天给她讲二流子变英雄等实际例子,现在安家婆姨家里常打扫好让坤元检查,几天来捻了一斤多好线卖了。这些小学生还帮助区上做事:区上每开会,他们便是基本队伍,去唱歌、表演秧歌,分头去动员到会的人。读报时他们也参加,还动员自己的爸妈去听报。他们还分工进行街道和家庭的卫生检查工作函。各学校还配有宣传队组织,每逢礼拜日到农村去进行宣传。宣传的内容均联系到抗战动员工作;还宣传禁烟,帮助军队放哨,检查路条、盘问逃兵、优待抗属、给她们挑水砍柴。还有的小学生督促家庭努力生产,劝说父亲戒烟,或说服二流子父亲转变。他们成为“学校和家庭的一个争辩的桥梁,情报的传达者和分析者”函。他们如同共产党进人乡村的导管,活跃在家庭、近邻和乡村社区。 人际互动的另一支中坚力量是地方干部,比如劳动英雄、变工队长、妇纺组长等。在社教运动中,通常的做法是让这些人首先站出来说话,宣传识字的好处,然后让他们推动和组织所在地的识字运动,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如华池城壕村劳动英雄张振财,不但自己识字,而且领导全村的识字运动。华池白马庙劳动英雄石怀玉除了自己学字,“还推动和领导变工队的读报组和识字组”。庆阳三十里铺的社火头黄润努力自修,编写新社火剧本,描写减租斗争、防奸斗争、识字运动、合作社方针等新事物,还推动陇东分区的民间新秧歌运动。在米脂高家沟,村民推举全村唯一识字的高怀山当教员,自办、自管、自教。学制分全日班、半日班,还有拦羊娃的早班,不固定年限,能写会算就可以毕业。“学校同时也是本村文化建设中心,成立了变工队员读报识字组,妇女纺织识字组,并与村、乡政府配合,开展卫生运动和文化活动。”这些人从社会基层产生,来自于普通民众。他们实际上成为一个村、一个区县的群众领袖者。他们表现积极,被誉为“新型文化战士”,在民众中拥有一定的威望。作为共产党开展工作的支点,他们支撑着革命运动的基本构架。
此外,还有一种人际互动的重要力量是由党直接选派的外来干部。在社教运动中,就是公派教员。比如在延安杨家湾,首先是教员到村里,帮助群众修理纺车,与群众建立感情和联系;随后教员进行家访,了解群众意见。在适应地方方言和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编著教材,开设语文、算术、卫生、常识、习字等课程。还教儿童学写便条,学珠算、记帐,“教育儿童民主与遵守纪律的习惯”,“讲礼貌、团结友爱,讲究卫生,尊重父母,家庭和睦的道德风尚”等。在教员的组织和领导下,这里还开展成人教育,推动全村卫生运动。在志丹县七区一乡则形成以教员为中心的巡回式学校。其特点是选定4个较大的村子作为巡回教学范围,教员每天轮教两个村子。教员轮到哪个村子,就将学生集合在一起教学。这样既解决了就地上学的问题又不误生产@。作为社会教育运动的主要承担者和党组织的权威代表,教员的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这一运动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也关系到革命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关系到乡村民众对新秩序接受和认同的程度。因此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各农家的常年顾问。“如分布在每一个角落的文化据点,把延安的号令贯注到一家一家去。”。
四、讨论与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有效地动员民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的群众工作方式,即首先以正式组织为起点,将动员对象最大范围地吸纳进来。党在乡村社会塑造了一个新的空间环境,将动员对象置于一个新的组织化的场景之中。这一组织化政策把相似的群体—无论是基于生产上的互助,还是生活上的合作而相似—集中在同一生态环境下。这样的生态环境加强了各组织之间、各群体之间的联系,将乡村社会纳人到一个巨大的组织化的关系网络中。因此,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不仅促进了组织和网络的形成,也有利于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农民们经过集体劳动和组织化的生活,不仅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生活得到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也起了变化……他们不独对经济有了兴趣,对政治文化生活同样有了兴趣……合作社是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核心,同时对农村中其他各种政治、武装的工作,起配合和推动作用。”同时,以集体、互助方式组织起来的乡村社会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活动场所,比如学校。大多数的革命活动和党的工作都通过这里传达、完成。它区别于乡村社会传统的宗庙祠堂、祭台神坛,开创了一个大众化的、广阔的、革命化的公共空间。正是这些公共空间提供了更多动员民众、联络情感的巨大舞台。此外,这种组织化改变了乡村社会人群的分布状态和聚集模式,促进了人际交往和融合。显然,这里的正式组织成为一种重要的动员资源。
在正式组织的框架下,还需要确定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因此接下来的工作便是以“革命道德”标准确定各个不同的群体在这个组织中的位置。它将对人的行为选择进行限定,也包含了对人们行为的塑造。因为这样的划分与归类极大地缩小了他们自我选择的空间和领域。在相互关系密切的群体内,意识形态或文化规范会使封闭的群体内成员之间出现模仿、跟进行为。再加上号召中心的存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这种相互感染,相互影响会日益强化。群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模仿,甚至通过对某些群体动用强制性手段,会使目标更加凝练、集中,会产生更多的认同感。“变工队使农活干得更愉快,更有效率,同时由于创造了新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他们对克服众所周知的农民的个人主义和氏族性质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换言之,随着农民被组织化的程度提高,农民集体化的倾向逐渐显著,已然引起若干心理上的变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以农民为主体的根据地民众被充分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之后,他们便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次生政治团体(即为了明确的社会目的自觉地组织起来的、形成科层结构的团体)之中,并通过这种团体与国家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团体生活中,他们的眼光开始突破家庭的小天地,他们开始普遍地形成强烈的政治认同,公民意识和国家观念也迅速长成。”
在寻求行为一致、目标认同的基础上,还需要将湮没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激活。因此,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工作,这就是利用非正式组织,即社会关系网络来推动和促进。以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可资利用的动员手段。这里的关键是信息的交换与传播。通过同一居住和活动空间下的人际交往和相互接触,经过交谈、讨论、解释和评价,革命的信息被理解并随后被运用,从而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进来。新的观点、信息首先在那些最先受到感化的乡村民众那里引起共鸣,而后在非正式圈子、初级群体和朋友网络中传播和加工。由于农民处在复杂场域中,因此,其他的群体或多或少也都会卷人其中。在这一过程中,集体信仰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建构和重建,整个乡村社会也日益趋向同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