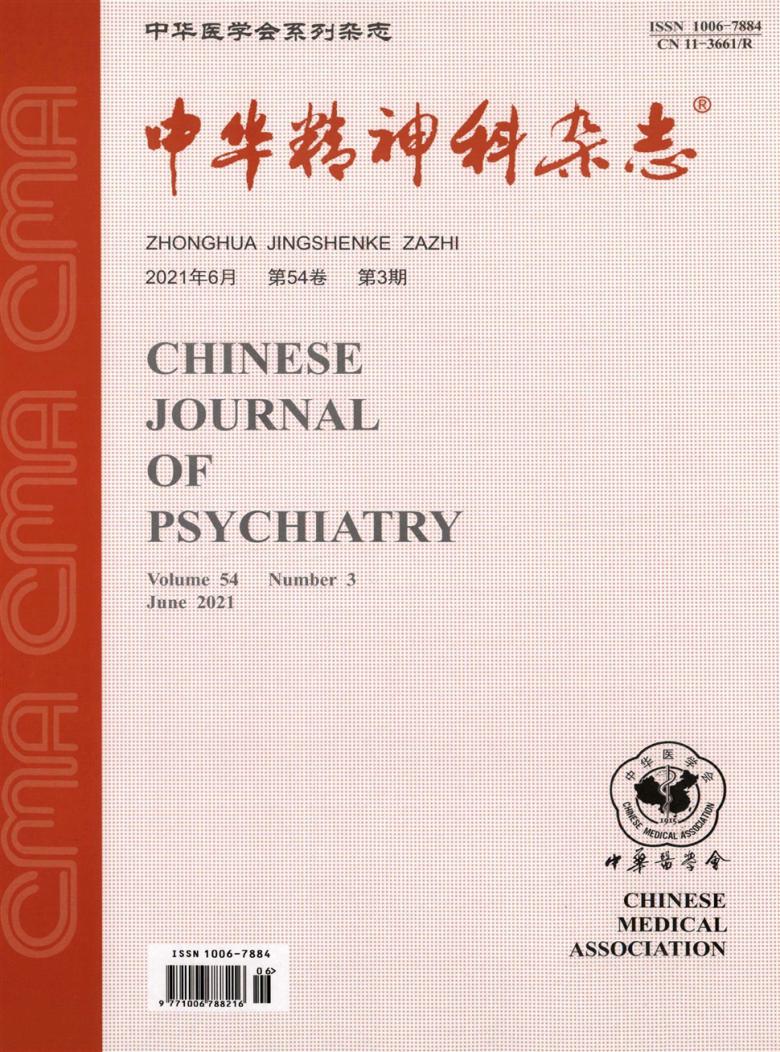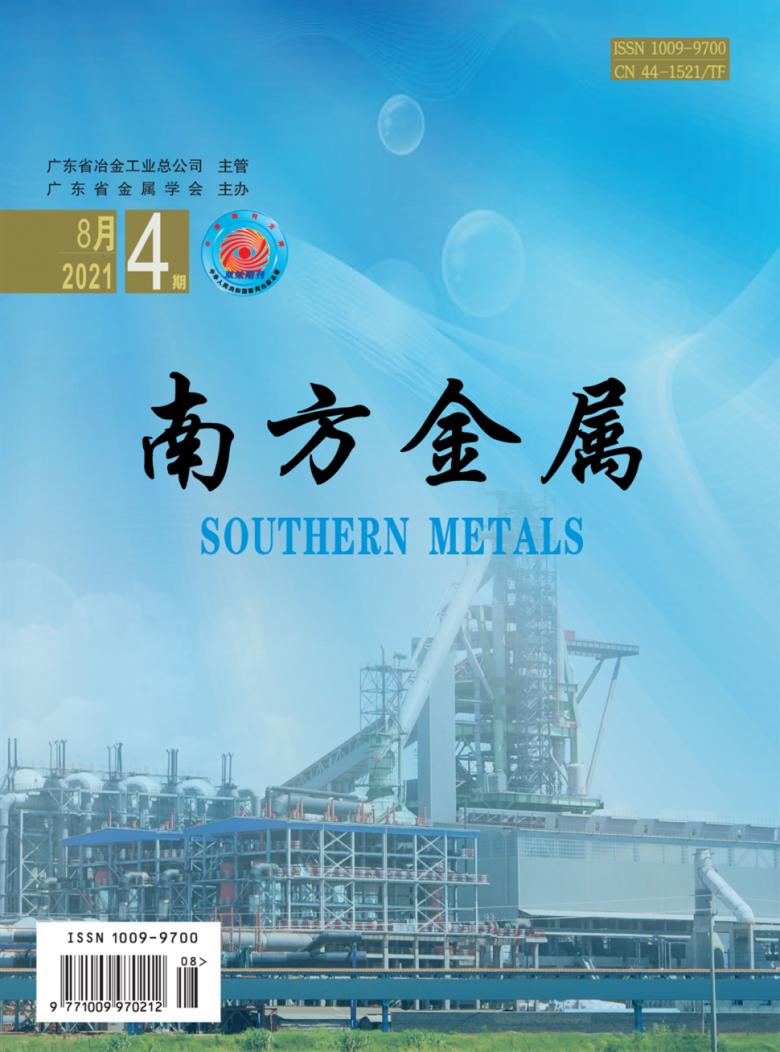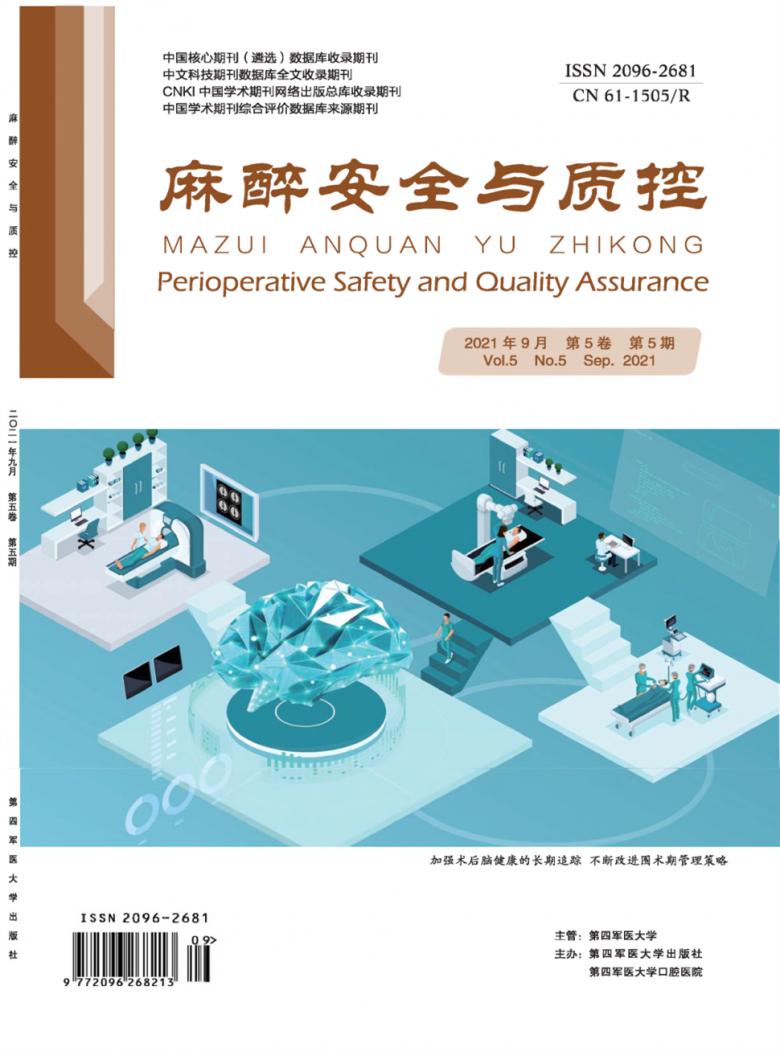重构母语教育的创新途径
佚名 2013-02-02
无论是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界,还是“五四”时期国语、国文教育的先贤们,都高度重视通过母语教育使学生习得由心灵所主宰的语用能力。因此,比主动归正母语课程名称更为重要的是:在深入反思新中国成立后母语教育弊端的基础上重构其发展性和语用性目标,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确立顺应国家汉语文化建设之需的积极语用教育观[1]。
长期以来,母语教育界陷入了一种非常狭隘的窘境之中。一方面,就教学的实然形态而言,本应由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三位一体的课程模块窄化为以阅读教学为本的封闭小圈。写作教学沦为阅读教学的附庸:既没有研制相对独立、自成系统的教材,又无尊重学生语用心理发展的教学序列。口语交际教学则被边缘化:既不进入实际的教学流程,更遑论开发自身特色鲜明、形成自足内容的体系化教材。而且,所谓的阅读教学又囿于内容有限的“公共教本”,将五彩斑斓的汉语读物拒斥在课堂之外,即人为地将学习生涯分离甚至对立为所谓“课内”与“课外”,从而严重束缚了学习者的精神视野:内存的词汇量贫乏,词汇的组合更是惊人同质化。久之,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言语表达能力滞后于自身生命的成长,桎梏了其未来文化使命的践行和社会角色的担当。正因如此,那位被我国80后一代尊奉为“代言人”并被美国《时代周刊》票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的韩寒,坚定地认为惯常被视作行之有效的背诵和默写毫无意义,并无情判决语文“完全是一个束缚人想象力的课程”,甚至尖锐地怀疑语文课存在的价值:它“在教会人认字以及遣词造句以后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2](pp.39-54)“韩寒们”的感受是具有普遍性的。
另一方面,就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育理论界曾出现过“思政中心说”、“语文工具说”、“知识中心说”、“语感中心说”等多种“接受为本”的片面观念。1949年到十年“文革”,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语文教育的中心,异化了语文课程的本体性质。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叶圣陶等先生的“工具论”渐成主流观点,虽有回归语文本体的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模糊了作为“思想现实”的言语行为之本质,因其在客观上淡化了学生作为语用主体本应有的积极主动的表达功能而在历史新时期受到了语文教育界清醒的反思性批评①。与此同时,注重讲授系统化和静态化的语文知识、配以训练语言技能的“知识中心论”颇为流行,语文课误入语义教学、语法教学、语形教学的歧途。20世纪末,王尚文为代表的“语感中心论”异军突起,虽有纠偏贡献,但终因语感与语识分隔、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剥离、限于阅读本位等三大缺陷而遭到理论界质疑[3](pp.168~175)。总之,这些在我国母语教育研究中曾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主流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偏颇的教育目标观:母语学习就是凭借“公共教本”使学生“接受”某些预设或既定的东西——或是某种政治观念,或是某种知识系统,或是某种役使工具,或是某种实用技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产生这种不约而同的“接受性思维”,根因于母语教育的理论研究不自觉地笼罩在其后的一种更为深广的教育学思维背景中,即教育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相“适应”,学校要培养“适应”既有社会伦理和文明规范的具有某些统一规格的建设者②。这种“适应论”的教育目的观其实是“前喻文化”的派生物,反映在语文教育领域内就是进一步助长了“以本为本”的“接受性学习”倾向,即表现为以公共的“母语范本”为中心、教与学双方围绕着它而展开以授受为特点的所谓“语文教育”活动,最后将本应由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三模块构成、相辅相成的母语教育应然形态,人为地窄化为、固化为自我封闭、日见狭小的接受性实然形态。
虽然传统语文教学也强调培养学生在认知和理解基础上“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但实际上这种模糊的“运用说”后面隐含着明确的教育指向,其实是一种接受为本的“窄语用”。上个世纪60年代,理论界一位前辈的著名观点就颇值得琢磨:“语文教育”就是要养成学生“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要把“训练学生运用字、词、句、篇、章的能力”与“训练学生理解语文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相结合。[4]这与“五四”时期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所提出的“表达说”形成鲜明对比:“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表达思想”[5](p.303)。显然,与后者基于生命本位的“表达说”(上文已述,“五四”时期的叶圣陶也持此说)相比,前者留有明显的“被理解”、“被运用”的痕迹。这种涵盖言语的输入性和输出性两大功能的所谓“运用”,模糊了源于心灵“自由表达”的鲜明的个性特征,模糊了母语教育的终极指向即以“自由表达”为内核的言语表现力;而且,在当时我国的教育语境中,“训练”说隐含着学生是“被操控的学习工具”这种“适应论”的负面倾向。由此推论,传统“语文”课程与教学信奉的是偏颇的目标观。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学生对公共“母语范本”的认知、理解、鉴赏乃至全盘背诵和默写,但是这些接受性的言语实践活动理应无一例外指向其输出性的言语表达力,只有后者才是母语教育的目标所在——使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学会表达自己,并通过这种规范得体、明晰晓畅的表达来实现与世界的联系、达成一己的生命价值。最重要的是,生命本位的言语表达必然是富有个性特色和审美品格的,其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是以表现性语用为价值取向的,故“言语表达”的终极指向是“言语表现”——以“汉语”为名称的中国人的母语课程与教学旨在培养的就应然是基于接受的言语表达力、基于规范表达而超越其上的言语表现力。
详而言之,以“汉语”指称的母语课程,其显性目标囊括以“思”为中枢,以“听、读、视”为基础,以“说、写、评”为指向的七字能力体系。显然,这个被重构的能力体系,不仅拓宽了学习者语用的广度,而且拓展了其语用的深度;不仅关注到学习者的输入型语用能力,而且重在强化其输出型语用能力;不仅重视诉之于眼、耳、口等感官的外部语用能力,而且高度强调心灵思维、想象、体验等内部语用能力(见图3)。 而所谓积极语用是指表达主体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而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因而富于创造活力的自觉完整的表现性言语行为。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积极语用=自觉语用(语用动机、激情)×全语用(完整语用能力)×深度语用(表现性语用)
这种母语教育的新观念和新思维是基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外语用学的理论视角,更是源自上文所述对偏狭表浅的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批判性反思,同时,也是基于对全球化背景下未来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前瞻性考量。积极语用教育观不是将输出型语用平面化地对应于输入型语用,而是强调“说写评”不能仅仅止步于语用主体的再现性复述,更不是从众化和同质化的“公共表达”,就价值取向而言,“说写评”的最高境界是基于规范表达的表现性语用——从言语内容到言语形式双重意义上的个性化、审美化和创意化。特别是将“评”与“说写”并列,是为了凸显语用主体在评论活动中所迸发出来的独立的思想力量,虽然“评”可以凭借“说写”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说写”未必就是一种有品味、有内涵的精彩评论。而且,受制于全预设、全封闭和全垄断的指令性课程范式,我国传统“语文”教学长期偏废对学习者思辨性语用能力的培养。这表现为:从输入型的阅读教学到输出型的写作教学和口语交际教学,普遍“缺席”洋溢个体生命语用活力和智慧的独立评论。与此同时,环顾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高度重视培养未来公民必备的自我选择、自主判断和自由评说之能力——以致中外母语教育两相比较,不仅顿生究竟培养“语用人”抑或“语用工具”的深长感喟。仅以当前教育界高度关注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进行的“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价项目”)大型研究项目为例,就其中阅读素养的测评而言,着眼于阅读素养的核心即基于书面和电子媒体的理解、运用和判断能力,鲜明指向语用主体的独立表达,既不要求从俗于主流观点,也不苛求面面俱到。③该项目已有整整十年研究进展,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对基于“深度阅读”、超越纯技术性认知、理解和复述的思辨性表达力的价值引导,无疑对我国母语教育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新具有深远的警示:PISA将阅读精重号为引者所加)。直言之,母语教育欲接轨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亟须言语表达的高级形式“独立评论”之回归——由此而全面启动中国母语教育的范式转换:从型塑“被表达”的“语用工具”到培育基于阅读后开悟、想象和创思而善于独立判断、自主表达的“语用主体”。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欣赏高中语文新课标所力倡的“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之基本精神[6](p.17)。即使是阅读教学,也要按照新课标那样来接轨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充分关注学生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应鼓励学生批评质疑,发表不同意见。”[6](p.16)从而使阅读真正成为蓄养学习者母语表达力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由传统“语文”课程名称回归到名正言顺的“汉语”,这实质上是:唤醒中华民族的母语意识并使之更趋自觉,坚定母语教育界宏伟的使命感并使之日臻理性;进而促使母语教育价值重心发生一次革命性的深刻位移,即从机械、单一和偏狭的“接受本位观”转换到“表达本位观”乃至“表现本位观”,促使母语教育目标开始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升华,即由重在养成认知、记忆、复述和平面化再现的语用能力提升到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审美表达直至创意表达为目标指向的表现性语用能力。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传统“语文”教育从名到实的蜕旧更新,也是其独立设科百余年来名归实至的质的跃升。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向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国外学界已提出以充满活力的“核心英语(Nuclear English)”新概念作为全球多元文化博弈之核心竞争力的背景下④,我国母语教育以“汉语”重命名为逻辑起点和历史契机,将获得与世界各国母语教育的和谐同步:不仅仅是作为课程名称的一次形式归正,而且深层次上共享全球母语教育的普世价值,即通过养成表现性语用的“立言”来达成人格独立、思维开放之“立人”目标;而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而言,我国以“汉语”为标志的母语教育,将开启一个新的教育历史时期,即以深刻、创新和高迈的目标意识为引领来炼就未来公民以“表现力”为内核的“言语童子功”,最终汇聚成象征东方大国空前文化创造力的强势汉语——这是全球化背景下语言强国战略的应然之义!
注解:
①对“工具论”的反思性批评甚多,意见甚丰富。代表性意见有李海林的《言语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30页~170页)、潘新和的《语文:表现与存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06页~111页)等。
②“适应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流行。90年代后,遭到教育理论界强烈的质疑和批评。详见鲁洁所著《超越与创新》,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页~393页。相关论文有:鲁洁《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载《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项贤明《关于“教育之适应与超越”问题的讨论》(载《教育研究与实验》1997年第3期),庞学光《论教育之超越》(载《教育研究》1998年第11期),李雁冰《教育的最高追求在于超越》(载《教育改革》1998年第2期)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强调实践主体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创造,而不是简单满足于复制既有文明、适应现实社会需求。因此,可以推论:教育的超越性特征就体现在它能够培养出改造现实世界、创造理想世界的新人,换言之,赋予未来人以超越性的实践本质,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这样,教育并不是单纯使新人满足于“接受”人类积淀下来的既定文明,“适应”前人所早已预制的社会规范,更是在“接受”、“适应”的基础上为“超越”和“创新”而自主性学习。
③陆璟《PISA如何测评阅读素养》,见《中国教育报》2011年3月17日,《读书》专刊第5至第8版。“PISA”隐含着以“立言”来“立人”的重要价值导向,应该引起母语教育理论界和一线教师的高度关注。
④[德]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著、吕淑君译《世界语言简史》(第十七版),山东画报社2009年6月,第303页。更有代表性的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以语言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谋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靡世界,成为政界关注、学界追踪且跨文化、高含量的国际学术话题。而在我国,复旦大学教授王沪宁早在1993年就发表《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将以语言为载体和象征的文化纳入国家“软权力战略”。2006年11月,胡锦涛在中国文联八大和作协七大上首度完整表述以母语为载体和象征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并在2007年10月,通过十七大政治报告正式将“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创造活力”等并置同一语境,从党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高度赋予这一新概念深远的内涵。至此,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题中要义之一。由此,作为母语的汉语表达活力问题承载着新的文化使命而重新纳入研究者深度关注的视野。
原标题:论汉语文课程名称的归正与我国母语教育目标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