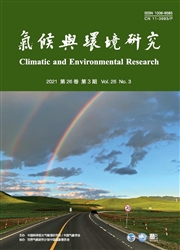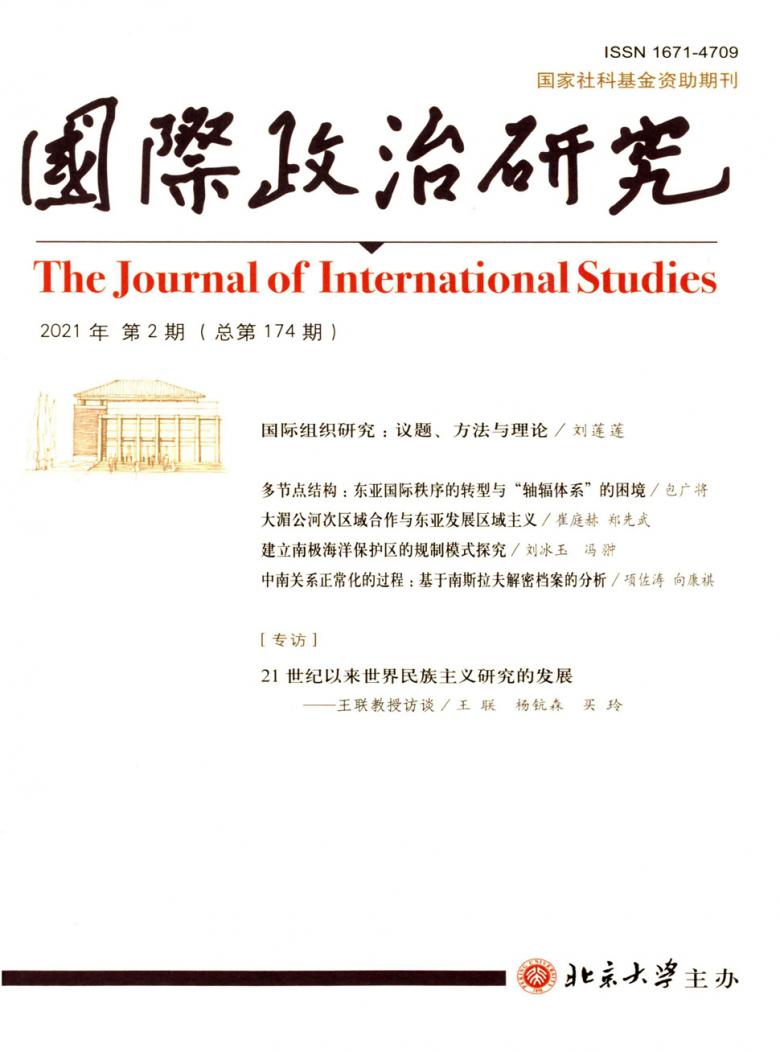从儒家思想看《水浒传》妇女观
周俊玲
【内容提要】
《水浒传》从民间传说到成书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在有限的对于女性的叙述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妇女观,留下鲜明的儒家思想的烙印,主要体现在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禁锢和蔑视,然而,另一方面宋元之际又是中国古代城市经济空前发展的时代,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意识增强,反映到作品中的妇女观也鲜明地显示了一些进步,冲破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流露出些许的民主思想。
【关键词】 《水浒传》 儒家思想 妇女观
《水浒传》从民间传说到成书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所写人物有七八百人,其中女性人数仅为全书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在有限的对于女性的叙述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妇女观。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形成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基本观念。尤其是南宋时程朱理学兴盛,理学把封建伦理道德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存天理、灭人欲、三从四德,进一步加强了对女性的禁锢。元朝统治者推崇理学,明初,朱元璋更是大力提倡理学。《水浒传》的作者,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不可能摆脱这些束缚而超然存在,所以作者在描写女性时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一种传统的儒家思想要求的妇女观。然而,另一方面宋元之际又是中国古代城市经济空前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出现,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意识带着时代的清新空气,强烈地冲击着作者,反映到作品中的妇女观也鲜明地显示了一些进步,冲破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流露出些许的民主思想。
一、作品妇女观的积极方面
(一)小说塑造了勇敢机智的女杰形象,展露出男女平等民主思想的一线曙光
《水浒传》难能可贵地将三位女性列入着力表现与赞美的一百零八将之中,塑造了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三位绿林女杰形象。她们不仅有粗豪、勇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更有临危不惧的胆识、谋划周全的精细、善于应变的机敏。武松在孟州杀人,逃到张青酒店,孙二娘巧妙地把武松化装成行者,从而免除了一场灾祸;顾大嫂软硬兼施劫牢救二解、混入敌牢救史进更显机智细心;扈三娘不仅貌美,而且武艺超群。聚义后,她们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利用女性特有的身份,常假扮艄婆、贵妇、农妇混入敌方,偷袭、接应,起到了男子不可替代的作用。作者在塑造三位女英雄时冲破了一般的封建妇女观,使她们也和其他男英雄一样,铲奸除暴,武艺高强,她们也和其他好汉一样平起平坐,在梁山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用再像花木兰那样乔装打扮,可以说这些女性真正走出了家庭,走上了社会,而且参与到男性的政治活动中来,发挥着她们作为女性的胆识和才干,成了“女人中的强者”。三位女主角摆脱了“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藩篱,作为农民起义军的成员,男女同上战场,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深受皇权、父权、夫权、族权四条绳索束缚的时代,能够描写出这样一群女性无疑是一种创举,无疑展现了一线“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的曙光,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儒家思想倡导的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模式,反映了作者妇女观中积极进步的一面。
(二)小说表达了对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的同情
小说除了歌颂梁山女英雄,鞭笞淫妇虔婆,还塑造了一批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形象,反映了那个年代女性悲惨的命运,不禁令人同情和感叹。北宋末年,奸臣当道,恶霸横行,鱼肉乡里,民不聊生。林娘子是上层社会的贵妇,因美貌过人,遭来一场横祸,最后自缢殉情;李师师是个烟花名妓,才色双全,理解、同情梁山好汉,甘愿冒险接受“招安”信息的传递任务,而李师师对燕青的“嘲惹”示爱,燕青与之姐弟之拜的拒绝,则充分揭示出这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内心的追求和痛苦;金翠莲曾被恶霸霸占;张太公的女儿遭强人蹂躏……作者对这类妇女倾注了怜悯的爱,字里行间溢满真切的同情,反映出作者对造成弱女子不幸的黑暗现实的不满,是作者妇女观中进步一面的表现。
二、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与小说妇女观的局限性
毋庸讳言,一部伟大的作品在超越时代的同时,也必然受到时代思想意识的束缚,《水浒传》在展露妇女观积极一面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根深蒂固的儒家妇女观的消极影响。《礼记·郊特牲》中说:“男先乎女”,“妇人,从人者也。”这已经有了“夫为妻纲”“出嫁从夫”的味道。《论语·阳货》中写道:“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足见对女性的鄙夷和贱视;孟子在《滕文公下》中写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认为女性应该依附男性而生存。在儒家思想看来,女性必须自甘卑弱,恪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服从男人的意志,受父系文化意识的支配,女人只有安于社会指定的位置,才会受人尊敬。《水浒传》宣传了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念,其妇女观必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一)女性自我意识缺失,缺乏独立人格
细读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无法摆脱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三位女英雄虽在水泊梁山占有一席之地,但却无法不受制于男人们。
首先,从扈三娘的个人境遇来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扈三娘,扈太公之女,祝彪之未婚妻。水泊梁山攻打祝家庄,祝扈李三家联盟抗敌。扈方以一丈青为首,挥刀跃马,驰骋战场,直扑宋江,生擒王英,勇猛无比。扈三娘不仅武艺高超,而且还拥有海棠花似的美貌,她的未婚夫祝彪也英俊潇洒,武艺高强,可称得上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可是三庄被攻破后,祝彪被杀,扈三娘被擒,一屈为宋太公之女,再屈为身材矮小、丑陋好色的王英之妻,低首伏心,了无一语,与前面英勇的扈三娘判若两人,在自己人生的大事上,她木然处之,任由命运摆布,其话语权根本失语,我们听不到她心底的任何声音,缺少人性的流露。出现这样的结局,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作者落后的妇女观:扈三娘无家可归,而宋太公是义父,宋江就是义兄,依照“三从四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伦理,宋江便义气地将扈三娘许配给了王英。扈三娘成了宋江实现承诺的一个筹码,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是一个被弱化的、没有个性的人。扈三娘的悲剧表明:即使她再高贵、英勇,即使她可以将须眉打下马来,但却冲不破男性强权的压迫和禁锢。
其次,从三位女英雄的结局来看,她们走得是一条与那个时代的妇女殊途同归之路——“夫唱妇随”、“夫死妇随”。尽管她们武艺高强,分别居于其夫之上,但上梁山后每每出征,她们又都随夫而行;排座次时,只能列于其夫之下;当她们的丈夫在沙场一一战死时,除顾大嫂侥幸存活外,其余都随夫战死沙场。三位女英雄的命运,显然受到夫权思想的主导,这无疑是“夫为妻纲”封建伦理道德观对作者思想的束缚。
(二)作品中婚姻常属爱情代名词,忽视压抑了女性的感情需求与思想意识
在儒家文化的字典中没有爱情的概念,婚姻常常是爱情的代名词,“儒家学说之所以在众多学说中获胜,以后成为中国长期的统治思想和行为规范,绝非偶然,它的以血缘关系为轴心的伦理政治学说完全适合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政治的需要,而血缘关系必须藉男女交合来实现,这就是宗法制度所要求男女关系所遵循的伦理的根本契机。”小说描写的婚姻多属不幸的,它忽视压抑了女性的感情需求与思想意识。
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都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城市妇女,在《水浒传》中她们被描写成不守妇道,寡廉鲜耻的淫妇,她们的被杀是替天行道,维护道德的必然结果。但是仔细分析三位女性的“淫荡”,是与她们不幸的婚姻紧密相连的。做人使女,颇有几分姿色的潘金莲因“不肯依从”那个大户的纠缠,被“倒贴些房奁”,白白嫁与了“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爱”的武大,她不满意这样一个丈夫,心中苦闷,西门庆的出现,王婆的唆使,同时也是出于女子本身对美好爱情(在潘身上由于情感的不幸变化为一种性欲)的追求才祸起萧墙,酿成千古恨,可以说,潘的不幸直接根源于地主大户的残酷报复。只因阎婆得了一口棺材,十两银子的救济而“无可报答”,就用女儿阎婆惜与宋江“做个亲眷来往”,宋江却是“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他一没把阎婆惜平等看待,二没给她爱情,仅使她保持衣食无缺的生活,这种情感只能说是同情而不是爱情,宋江没有娘子,可他并没有把阎婆惜娶作正妻,因为门不当,户不对,作者是根据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来处理二人关系的。作为一名下层妇女,张文远的出现激起了她对爱情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如此的强烈,致使她的行为偏激,理想和追求变得畸形,可以说,阎婆惜的不幸源于廉价的买卖。潘巧云和杨雄之间谈不上什么感情,杨雄爱的只是舞枪弄棒,不善嘘寒问暖,而且一个月内有二十几天不在家,潘巧云实际上是在守活寡,成了家庭的一件摆设。而潘巧云与后来出家的裴如海可谓青梅竹马,较之杨雄,潘裴二人的感情成分较多一些,潘的红杏出墙也实属必然。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几位女性该去通奸、杀夫、讹诈、堕落,她们的结局只是封建时代只追求个性、只追求所谓个人幸福的妇女的必然结局。即使按照现在的道德标准,她们的所作所为同样是被认为犯罪的。问题的关键是,作者在铺陈这些故事情节时,始终抱着“万恶淫为首”“妇女是祸端”的封建观念,字里行间渗满了这样的女性就是罪恶源泉的说教。“红颜祸水”的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历史记载上往往将亡国殒命归咎于女子,对女子尤其是漂亮女子进行种种非难。如殷商的灭亡不是纣王昏庸无道造成的,而是由妲己的美貌所致;东周的灭亡源自褒姒的嫣然一笑;中唐王朝的衰乱起因于杨贵妃……美丽的女子是败家亡国的罪魁祸首,人人得而诛之,《水浒传》在叙事中更是强化了这种看法,所以在作者的笔下,潘金莲们所受的惩罚要比男的严重得多。比如说,西门庆是被武松斗杀的,而潘金莲就被挖出心肝;潘巧云和裴如海私通,裴如海是被杀,而潘巧云却被肢解。作者没有给她们一丝惋惜、一点同情,只是一片咬牙切齿的憎恨,将她们的死归于违背贞节操守无疑是受到封建礼教影响所造成的,这也充分体现出了作者落后的妇女观。
(三)回避英雄豪杰感情世界的描写,看不到英雄们立体的多层次性格
儒家思想注重人的群体意识,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个人属性,所谓“内圣外王”是说男人应当看重道德修养与功名心,放弃个人欲求与发展。所谓“食色性也”是说饮食之欲、色欲是人的本性,尤其好色的本性不易改变,渔色无度之辈层出不穷。《论语》孔子慨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儒家经典所阐述的鲜明观点之一就是压抑人的色欲,否则危害性极大。《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又说:“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还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意思是圣人的职责就是治理人的七情,使之在正常范围内发展,尤其要贬抑“饮食男女”之大欲。《礼记·坊记》说:“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宣布“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故男女授受不亲”。这一系列论述发展成为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
生活在北宋末年的梁山好汉们只“好德”“重友”,他们绝大多数不娶、不近女色,即便是一些有家室的好汉,也不沉湎于男欢女爱。“好色”的梁山好汉屈指可数,王英是典型的好色之徒,他在第32回捉住去坟头化纸的刘高夫人“自抬到山后房中去了”,对此,宋江道:“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燕顺道:“这个兄弟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这些毛病。”他的这一“嗜好”被梁山好汉嗤之以鼻,暗中耻笑。
《水浒传》好汉们不爱女色,究其原因,其一,如前文所言,“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影响。其二,儒家倡导的禁欲主义观念影响。在中国古代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女色是斫伤生命的斧子,行欲会耗损男子的精元之气,而禁欲则会使人精力充沛。《水浒传》好汉大都崇尚超人的体力和高强的武艺,疏远女色被认为是保持这种体力的重要措施。《水浒》中提到某人喜爱习武,往往同时附上一句“不爱女色”之类的话。如晁盖“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体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卢俊义“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其三,就男女地位而言,儒家力倡男尊女卑,友与色往往被放在互相对立、排斥的地位,《三国演义》中刘备的言论极具代表性:“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重色轻友”者会遭到人们的蔑视和贬斥。《水浒传》作者笔下的好汉们看重的是朋友义气,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倘若陷于情爱之中,当然就会“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所以,在《水浒传》中崇尚这样的观念:英雄必过美人关,真正的英雄不会“好色”,否则就有悖于儒家伦理道德的要求。“相貌堂堂强壮士”的武松、燕青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身躯凛凛、相貌堂堂”的武松对潘金莲极具诱惑力,任其挑逗、引诱,不为之所动,尽显“顶天立地啮齿带发男子汉”的风格。面对京城名妓李师师的言语撩拨,英俊聪明、百般伶俐的燕青心生一计,拜她为姐姐,抵住了美色的诱惑。而这些女人却用姿色和性命成就了英雄好汉。
有趣的是,西方国家文学作品中的好汉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好汉完全不同。在西方,那些行侠仗义的好汉一般被称为骑士。一个理想的骑士总有着缠绵的爱情,他们是女子的仰慕者和保护者,而不懂爱情、践踏女性的人则被称作恶棍。这种对骑士的看法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一个没有情人的骑士不配被称作骑士。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想成为一名骑士,却苦于没有情人。无奈之下,他只得在想象中将他见到的一名村姑当做他的情人而大写情书。这当然是一种幽默,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不同而导致作者笔下人物形象的差异。
通读《水浒传》,我们不难发现,整部作品回避英雄豪杰感情世界的描写,显得阳刚之气有余而阴柔之美不足,水浒英雄们漠视女性、仇视女性,以其冰冷的理智扼杀了自己的情感,把英雄斗志与儿女情长截然分开。“内圣外王”的要求,使《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决“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他们恪守封建伦常,感情世界一片荒芜。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避开女性世界的描写,我们看不到英雄们立体的多层次的性格,英雄的生命色彩亦随之暗淡。
参考文献:
[1] 何满子.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 (战国)子思.礼记[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
[4] (春秋战国)孟子.孟子[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
[5] 刘琦译评.论语[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6] 王学泰.水浒与江湖[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7] 董连祥.论梁山好汉的共性及成因[J].辽宁大学学报,2005,(5).
[8] 马成生.水浒通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