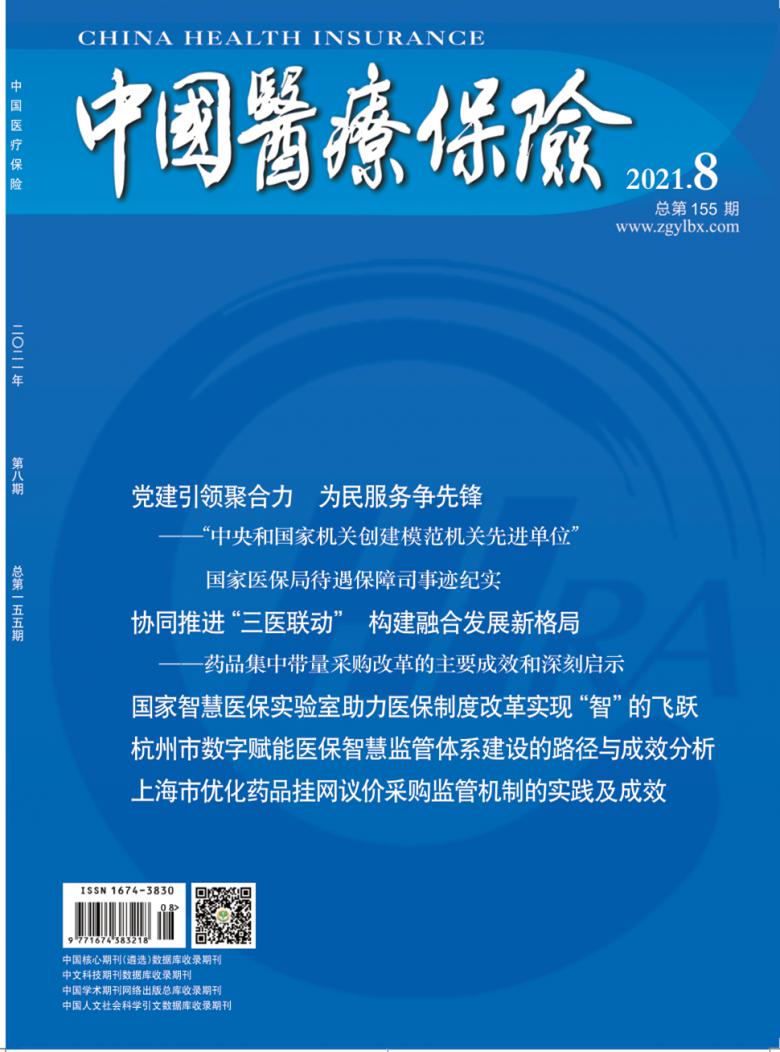佛光幻影中世俗女性的映象--《西游记》女性形象解读
李赴军 2008-07-23
明代的小说创作,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出现之后,沉寂了一百多年。明中叶以后,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发展壮大,为了适应他们的文化需求,通俗文学又趋繁荣。随着《西游记》的出现,一大批长篇小说相继问世。《西游记》最早感受时代剧变前的气息,因而在体现新的时代精神上有异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形象,是社会的投影,而女性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她们的艺术形象尤其负载着复杂多样的社会因子。《西游记》的女性世界十分驳杂,作品的魔幻色彩、宗教意识遮蔽了人们的目光,因而绝少有人留意那些女仙佛神怪以及她们身上所透射出的曙色。
《西游记》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女妖魔、女神仙及俗世女子三类。作者借这些世俗凡人和神佛形象对人情人性的渴求,对生命长存的期望,对世俗生活的向往,传导出渐趋时俗、复归人性的时代趋向。
一
《西游记》并非描写世情之作,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它与史实距离更远。但是怪诞离奇的神魔争斗中隐寓着世态人情,折射出丰富的社会内容与时代风貌。玉面公主、树精杏仙及女童丹桂腊梅、盘丝洞的蜘蛛精、黑松林的老鼠精、天竺国假公主玉兔精等。这些女妖,有的是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有的是想与唐僧成亲,破其真阳;有的是真心想与唐僧作夫妻。她们都以美貌诱人,考验师徒四人真心向佛的心志,都在九九八十一难之中。她们虽为妖魔却有着世俗中人的人情人性,正是“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铁扇公主的形象塑造十分成功,活脱脱世俗中人。身为翠云山芭蕉洞主,凭其稀世珍宝芭蕉扇称霸一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她的丈夫牛魔王为贪图美色与百万家私,又讨玉面公主为妾,到摩云洞做了“倒插门的女婿”。铁扇公主过着被遗弃、被冷落的凄苦生活。她渴望夫妻长相厮守,因此,当孙悟空假扮牛魔王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喜出望外,俏语温存,试图以情以义感化夫君,人世间夫妻之情之状在她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现。透过这一形象,我们可以感受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给女性带来的内心痛苦。
白骨精的出现,反映了家庭观念与佛教理性的矛盾冲突,出家求佛,必须与社会和家庭脱离,做到“六根俱净”。要真正修成正果,必须抛舍家庭观念的影响。琵琶洞的母蝎精对唐僧流连不舍,想与他结为夫妻,声言“黄金未为贵,安乐值钱多”;木仙庵的树精个个清奇风雅,锦心绣口,他们慎重其事地做媒、保亲、主婚,欲成全杏仙与唐僧的婚配。……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些妖魔鬼怪当然都是罪恶的,但另一方面,她们的所作所为却表现了人类渴求无拘无束享受生活的愿望,以及永世长生的生存欲求。作者通过这些由妖魔、精灵变幻出的女性,对人类的生理本能寄寓宽容理解,又通过她们欲望的落空,表明了自己的理性选择。
《西游记》中出现的女仙佛有观世音菩萨、黎山老母、普贤、文殊、毗蓝婆菩萨、嫦娥仙子等,除观音外,其他几位较少出场,她们最轰动的行动是在二十三回,集体上演了一“四圣试禅心”的热闹喜剧。取经路上的魔障绝大多数是险恶的自然环境生成的山精水怪与不服管束的仙佛奴仆幻化而成,而由众神佛出面考验取经者意志唯此而已。四圣幻化为林间庄院的平民女子,所采用的富贵、美色诱惑方式甚至女儿的命名,都涂抹了一层浓厚的世俗色彩,标示着庄严神圣的仙佛从神坛走向凡间。作者倾心打造的观世音形象更是世俗化的典型代表。
在佛教经卷中,观音只是佛法神力的抽象体现,其身相不定,更难分性别。观音最终成为一位端庄秀美、大慈大悲的女性,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演变,大致在宋代基本定型。在元末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观音已介入取经故事,但仍有很重的宗教色彩,主要还是观音神力的体现。由于缺乏生动、细致的描写,其性格特点不够鲜明,甚至也看不出女性特征。
小说《西游记》尽管未能汰尽这一形象的宗教色彩,但作者基本上是按照人间女性来描写的,变庄严为亲切,化神力为人力,使观音形象成为《西游记》世俗化倾向的生动体现。对她的容貌形态、衣着服饰,作品在第八、十二、四十九回等处有浓墨重彩的描绘,她不再是云缭雾绕中面貌朦胧的神秘仙班,而是一位具体可感、和善可亲的女菩萨。四十九回,观音为收伏河怪,褪尽妆饰赤脚光臂、手执钢刀削竹织篮的场景,充分世俗化了,真是美不可言,观音的可亲可爱凸现得淋漓尽致。从悟空咒“该她一世无夫”,八戒称她为“一个未梳妆的菩萨”,以及观音本人的一些村言俗语,我们也看到了作者赋予观世音形象的现实意味。有别于佛经中观音的宗教劝化寓意,《西游记》突出的是观音在取经事业中的收妖除怪、救苦救难。她奉如来佛旨察访取经之人,是取经队伍的真正组织者。在取经途中,观音更是频频出阵,亲临黑风山、五庄观、枯松涧、通天河等处,常常是“未及梳妆”,便纵上祥云赶去救难,成为唐僧师徒的释厄者、民间信仰中救苦救难的化身。观音慈悲为怀、扶正祛邪正是俗世中平民百姓善良美好愿望的形象体现。
二
《西游记》构筑的是一个变幻奇诡的幻想世界,所涉俗世女性少而又少,仅西梁女国、唐僧母可以列入。但无论是工笔细描的女儿国,还是简笔勾画的唐僧母,在反映时代精神以及传统道德观念的变异上,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女儿国”并非吴承恩独创。《山海经·海外西经》有关于女子国名目的最早记载:“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 郭璞注曰:“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妊矣。若生男子,三岁辄死。”唐三藏西天取经所过女儿国,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末《西游记》杂剧、明初《西游记平话》都有记述。《西游记平话》,今无传本,有关女人国的具体情节不详。《诗话》中的女人国是文殊、普贤为验试法师的禅心而幻化出来的;杂剧中“女人国”的女王淫邪毒,硬逼成亲。小说作者对情节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保留“女王招赘”模式,却将《诗话》中的部分情节另写为“四圣试禅心”,将杂剧中“女
王逼配”一节移入琵琶洞蝎子精身上,从而赋予“女儿国”新的意义内涵与理想色彩。
佛经传说中的“女人国”故事,旨在传播佛理,把“女人国”喻为人生之苦海,人必须抛开俗世的情欲,方能度出苦海臻于圣境。小说《西游记》则有意淡化“女儿国”的宗教色彩,把西梁女国作为一个人间国度来描写,把西梁女王作为凡俗女子来塑造。尽管“女王招赘”也是考验唐僧西行取经诚意的一“难”,但它与蝎子精、蜘蛛精、老鼠精、玉兔精等由妖魔制造的女色之难有着根本的区别,女王是向唐僧求婚配的唯一的活生生的人。通过这一形象,作者对人情、人欲表现出大胆的肯定和由衷的赞美。
女儿国王是一个有情有欲的凡尘女子形象,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高洁圣徒。她美丽多情,聪慧灵秀,毫不掩饰自己对爱情婚姻的热烈渴盼。当唐僧师徒来到女儿国倒换关文时,女王立即表示,愿舍弃九重之尊、一国之富招唐僧为王,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传帝业。当见到丰姿英伟、相貌轩昂的唐僧,心欢意美之下,“不觉淫情汲汲,爱欲态态,展放樱桃小口,呼道:‘大唐御弟,还不来占凤乘弯也?”,大胆真率之言,令唐僧耳红面赤,羞答答不敢把头抬。接着,“那女王走近前来,一把扯住三藏,俏语娇声,叫道:
‘御弟哥哥,请上龙车,和我同上金奎宝殿,匹配夫妇去来。”,其娇媚、温情、执着,让唐僧战战兢兢,止不住落下泪来。在这里,唐僧似乎成了违反人的本性的标本;女王则是者所肯定的积极、大胆追求爱情婚姻的正面形象。而且,女王对唐僧的情,是以性爱之欲为前提的,换言之,是压抑已久的自然欲求被焕发而萌生“指望和谐同到老”的“真情”(54回),它与《牡丹亭》中杜丽娘因自然涌发的生命冲动引向梦中的欢会意义一样,包含着人性解放的时代精神。
唐僧母亲,作品着墨极少,仅在叙述唐僧身世时有一简要交代。她仍属传统的节妇形象,但父亲的宽容劝阻,代表了作者对妇女处境、行为的理解与同情,表明在时代声息的感应下,传统的道德观念有所松动。唐僧母殷温娇是巫相的千金小姐,婚后随夫陈光蕊去江州赴任。在洪江渡口,稍水刘洪、李彪谋害其夫,刘洪强占温娇为妻,并冒充陈光蕊赴江州上任,殷小姐痛恨刘贼,恨不能食肉寝皮,只因身怀有孕,“权且勉强相从”,后生下遗腹子,为免遭谋害抛入江中。十八年后,儿子长大成人,父亲提兵报仇,丈夫还魂再生,全家团聚。最终,唐僧母因羞见父亲、丈夫,“从容自尽”。唐僧母所信奉的仍是“妇人从一而终”的传统道德观,但他父亲的劝解之语,让我们感受到新的时代气息正拂面而来。殷巫相说:“此非我儿以盛衰改节,皆因出乎不得已,何得为耻!”虽然仍以妇女应当守节为前提,但可以看出,在对待女子贞操的态度上,他主张应视具体情形而定。这种通达的贞节观,多少给妇女留下了一点生存的空间。
三
《西游记》的女性描写,有别于此前的两部章回小说。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再到神魔小说,女性世界的精神内涵是有差异的,作者对待女性的态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三国演义》、《水浒传》张扬的是豪杰英雄图王霸业、角逐江湖的历史感和征服欲,是一个典型的雄性群体。女性被视为男性附庸,女性形象被政治、伦理化;或者视女性为事业的羁绊,将两性世界对立起来。《西游记》作者对待女性的态度表现得较为复杂。一方面,受佛教理性的制约,视人欲、女色为灾难的渊数,人必须摒斥一切俗世的欲念才能终成正果;另一方面,作者又淡化豪迈的历史感与神圣的责任感,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了女性的处境,以赞赏的笔墨写女性对情感、家庭的渴求。较《三国演义》、《水浒传》以理性原则统摄复杂的人性内涵,《西游记》更多一些对人类感性生命的关注。这一变化包蕴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它是时代风云激荡的必然产物,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思潮的急剧变化,也表明作家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
《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也属世代累积型小说,但作家个人创作的成分更多一些,作家主体意识有了更大自由的发挥。“全书以诙谐滑稽为宗旨”,即便涉笔很少的女性人物也体现了真幻相生、幽默戏谑的艺术风趣。云中四圣为试禅心联袂上演的闹剧,女儿国国王为求匹配所引发的喜剧,还有观音菩萨的村言俗语及与孙悟空的幽默调侃等,都抹上了作者“性敏多慧”、“复善谐剧”的个性色彩。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西游记》虽未摆脱类型化的模式,作品中女性人物仍分几种类群,但道德化色彩明显淡化,个性化风采开始显露。作品中的女性,无论仙女、人女还是妖女,都富有较
强的“人情”色彩。
明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单一的封建人格模式受到冲击,个体价值广受关注。李蛰明确提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认为每个人的存在都有他自己的价值,都应让其“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李蛰还从“童心说”出发,鼓励人们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生活,这种以人为本的朴素的人本主义是思想界的一大革命,并给当时的文艺创作吹进了一股个性解放的新鲜空气。它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着极相似的地方,都是把人从附属于某种政治、宗教法律或道德伦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尊重个体的人生价值。
与时代思潮合拍,这一时期的小说敏感地捕捉人的自我意识的萌动,表现出迥异于传统规制的价值取向。《西游记》《金瓶梅》对传统的价值体系做了大幅度的修正。《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所体现的挣脱外界束缚、尊重人的个性、追求平等独立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传统的的价值观。那些女妖,若剥离其宗教目的上的吃人本性与人类并无多大区别,她们都各自为政,凭自己的能耐过活。她们对生命长存与享乐的追求,不也是人类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吗?女儿国王愿舍弃九重之尊以求得情感的满足,更使得注重事功的社会价值相形之下黯然失色。
新的经济形态对封建宗法制也构成了较大威胁,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尊卑上下的等级秩序。孙悟空大闹天庭就是为了求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尊卑秩序也不再那么森严可怖,难以跨越。由于作品很少涉笔夫妻家庭生活,我们仅能从非夫妻关系中去考察。观音与孙悟空的关系如同人间母子,观音对待悟空就象一位慈爱的母亲,即便骂他“泼猴”,也充满爱意。虽为悟空戴上紧箍儿,意在让他一路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观音却未曾念动过咒语。悟空对观音也十分信赖,一遇困难便请求援助,虽然有时出言不逊,但对两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并无大碍。在女儿国,师徒四人中唐僧因相貌英俊被招赘成亲,内心受着痛苦的煎熬,惟有偷偷落泪。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婚姻是不能自主的,稍有姿色的女子常有飞来横祸。而在女儿国中,这幕悲剧却由男子来上演。作者借唐僧的疲困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进行了辛辣的鞭挞。
在哲学领域,宋明理学的一统局面受到强大冲击。以左派王学为嗜矢的异端思潮风靡一时,王守仁“心学”从理学的反面论证了人的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大胆反拨了程朱理学对人性的禁锢。他的弟子王民在王学基础上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发展到万历时期,李蛰针对禁锢人性的虚伪道德提出“好货”、“好色”的口号,不仅在思想界、哲学界引起震惊,更渗透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引起了一场观念的变革。
《西游记》最早刊本是在万历二十年,创作时间更早,未逢晚明浪漫思潮的汹涌期,但是它得时代风气之先,提前感受到了时代狂潮到来前的微澜。可以说,《西游记》正处在新旧交替的链接点上,既有对前期思想文化的脉承,又初步显露出人文主义启蒙思潮的曙光。所以,作者在时代思潮与传统伦理观念的夹缝中左冲右突,对女性表现出既渴求又排斥的矛盾。唐僧、悟空都是“铁打的心肠朝佛去”,女妖又专以色害人,这些描写虽不无题材的规定性,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对传统伦理观念的认同。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作者通过猪八戒对“食色”的拼命追求,肯定了世俗凡人的人生欲望。作品中的女仙、女妖对尘世生活的向往,对人欲的渴求,都折射出呼唤、期待人性回归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