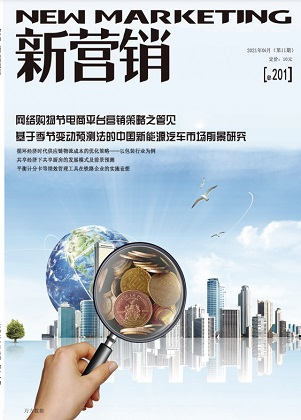《西游记》的儒释道文化解读
黄卉 2008-07-23
【内容提要】
灵魂的自救与人格的修炼。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和以造福人类为目的不畏艰险的追求探索精神。个性的整合与重塑。
【关键词】 《西游记》 人格 修炼 人性 重塑
《西游记》作为文人创作神魔小说,与古代的中国神话和外国神话相比,其神话思维是自觉的,而不是朦胧的;是系统的,而不是零散的;是文学的,而不是神话的。但它们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寓言性质。因而,透过小说的神话外衣,挖掘其蕴涵的文化意义,即所寓之“言”,应是我们解读《西游记》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将文本切分为三个层面来解读。
灵魂的自救与人格的修炼是表层意义
西天取经是《西游记》故事的主体部分。所谓表层意义,是就取经过程而言的。由取经队伍组成人员的出身、经历、遭遇和结果等事件序列所构成的意义,是直接浮于故事表层一望即知的,也是故事直接明示的部分,故而将其视为文本的表层意义。
首先,取经之于取经人而言,是一个由仙界——凡间——回归仙界的历程。这一历程,恰好画出一个起点与终点相重合的圆形图式:降落——出发——回归。这种图式在带有道教神话色彩的故事中,屡见不鲜。仙界之神因触犯天条而被贬谪人间,历经一番磨难后,又重返天界,再度成为仙界的一员。《西游记》对取经人物及过程的设计,是将一个原本佛教的故事道教化了。
这一过程,用小说中惯用的语言来表述,是一个从“放心”到“归心”,从“有心”到“无心”,从“多心”到“一心”的“炼魔”的过程。这套术语,与晚明时期“心学”的普及有很大的关系,也与故事在流传演变过程中受“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小说虽然讲的是一个西天取经的佛教故事,但在叙事中却同时使用了儒、释、道三套话语。
对于取经人来说,取经之事既是一个灵魂的救赎过程,又是一个人格修炼的过程。取经队伍的一师三徒一马,本系神佛之界的人物,兹因误犯禁令而被贬落人间。玄奘原是佛界的金禅子,“只为无心听佛讲”而被打入尘凡;孙悟空则因大闹天宫而被压五行山下;猪八戒原为天蓬元帅,因调戏嫦娥而遭贬;沙僧原本天上的卷帘大将,因“打破玉玻璃”而被贬流沙河;白龙马原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因触犯天条被贬鹰愁陡涧。他们均是蒙受菩萨的“劝化”、“戒行”而踏上西行之路的,所以取经对他们而言,便是一种“将功折罪”、“改邪归正”的灵魂自救行为,“了悟真如”、“顿开尘锁”的“务本”之道,跳出“性海流沙”,达到“浑无挂碍”的超越之路。只有历经这样的磨难与提升,方能达成“正果”。将此换成儒家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让他们“务必迁善改过,以底于至善而后已”。
灵魂自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人格修炼的过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这一修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为苦志弘毅,一为去念正心。而这两个层面又可以一言以蔽之曰:苦行精神的锻造与发扬。因为任何宗教都倡导苦行主义,只有当一个人学会了抛弃凡俗,勇敢地面对痛苦,他才能出“类”拔萃;只有克制自己的本性,反向而行,才能超“凡”入“圣”。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甚至只有热爱痛苦,才能欣然履行他的各项责任,所以锻造这种“苦行精神”的最好途径是让他们遭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和痛苦。小说的九九八十一难,就是专门为此而设置的。
西天取经是一项救民水火的神圣使命和普度众生的崇高事业。它虽是以宗教的形式出场,而内在精神却深深契合着儒家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事业心、责任心、使命感和意志力,彰显的是坚定不移的价值信仰、坚忍不拔的人格毅力和不改其志的理性自觉。而八十一难的设置,就是要让他们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受难考验中,做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最终树立起“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因为“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要“心性归正”,就首先必须“灭心中贼”,因为王阳明说过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为了制伏“心猿”,小说还设计一个紧箍咒来规范和约束他的行动,紧箍咒的真名是“定心真言”。做到所有这些,用儒家《大学》的话就是“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和以造福人类为目的不畏艰险的追求探索精神
这是《西游记》的另一层意义。以孙悟空这一主体形象的塑造看,《西游记》中包含了具有人类普遍精神的两大母题: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和以造福人类为目的不畏艰险的追求探索精神。
第一母题: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向往和追求个性的自由应当是人类共有的天性,所以在古代中国和外国的早期神话中,出现了像普罗米修斯和鲧这样命运极为相似、能量巨大却遭受个性屈辱和压抑的神祇。孙悟空的形象正是一个神通广大而又遭受镇压的不幸角色。从这个意义上看,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塑造,应当被视为普罗米修斯和鲧这种神祇从神话向文学“移位”的产物。那么这种文学移位现象为什么出现在十五世纪的中国?这就需要从个性自由的精神在中国和外国所遇到的不同土壤及其萌发时间上,来深入理解它的内在动因。
与西方相比,汉民族的氏族解体极不充分,血缘纽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牢牢地将中国人的亲族关系缠在一起。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以父系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的家庭和家族延续数千年之久,构成社会的继承单位。这种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华夏社会,只承认血缘族类,而不承认个人的独立价值。与之大相径庭的是,解脱了血缘羁绊的城邦化的希腊人,则承认个人的独立的原则,进而承认个人之间的后天契约原则,并将这两点认作国家的基石。这种以血缘纽带为基础,以道德伦理为价值准绳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因此,这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或封建集体主义的“人学”,它与近代社会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精神大异其趣。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尽管向往个性自由的集体无意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不乏存在,但人们在意识形态中对它的评价却一直持否定的态度。直到明代中后期,以王学左派的异端李贽为代表的具有早期启蒙主义倾向的进步社会思潮弥漫于中国大地之后,追求个性自由的“童心说”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对这种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的评价才有了明显的转变。如果我们将《西游记》和此前的各种《西游记》题材的小说和戏曲故事的内容、人物加以对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曲折反映。
同样是表现人类个性自由精神的孙悟空的故事,在吴承恩之前的故事中基本上都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宗法集体主义不能接受像孙悟空这样的具有很大能量而又桀骜不驯的叛逆。所以明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个性解放的思潮,不仅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冲击,同时也对受到儒家思想大背景影响之下的诸多问题发起了挑战,对孙悟空形象的认识、改变,便是其中之一。
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的身份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们知道,“铜头铁额”是神话传说中蚩尤兄弟的外貌特征,而蚩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最典型的凶神恶煞。更能发人深省的是,书中写到当年具有叛逆精神的猴行者曾经偷吃过十颗仙桃,被王母捉住打了三千八百铁棒,发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而当他二万七千年后保护唐僧取经再次路过此地,法师让他再去偷,他不敢了。这一转变,正是宋明理学将伦理价值和道德自律上升为本体这一最高目的的鲜明而具体的体现。但是在《西游记》中,孙悟空身上这种人类普遍的个性自由精神开始得到充分的张扬,而且是作为一种善的化身而受到作者的充分肯定,这与当时作为社会主流思潮的“童心”说的深入人心是具有因果关系的,也与当时的狂禅之风不无关系。
第二母题:以造福人类为目的的探索追求精神。从中国的夸父追日,到西方的浮士德,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较之前者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因此随着孙悟空头上紧箍咒的出现,他的自由意志就受到极大的限制,小说的第一母题就退到从属地位。如果说第一母题体现的是对人的个性价值的尊重和体认的话,那么第二母题则体现了对人的个性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认识,或者说是提出了个性价值如何在社会价值中得到实现的问题。如来让玄奘西天取经是因为“那南赡部州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所以要传唐僧真经“劝人为善”。真经即大乘经典,就是以普救众生为目的。因此取经也就成为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的精神的象征,成了为人类冒险和牺牲的正义和壮丽的事业。师徒四人超越了对个人自由价值的执著,而把“普济人生”作为更高的人生追求,在追求真理的宏伟事业中,求得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这也正是夸父和浮士德的神话精神。
两大母题的深刻蕴含:取经故事并不意味着对个性价值的取缔,而是在充分肯定个性价值基础上对个性的升华——由对个人自我解放的渴望而上升到对全人类利益和价值的追求,即将个人的解放扩大为全人类的解放,那才是最彻底的解放。所以在孙悟空被封为“斗战胜佛”时才又想起个人自由解放的事情来,然而奇怪的是,紧箍咒自动没有了,大乘佛教讲“自未度先度他”,上求菩萨,下化人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宏伟目标,都在这个风趣幽默的故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说明。这样《西游记》这两大精神原形不仅不是矛盾的,而是具有深刻内在含义的有机神话精神体系。
个性的整合与重塑
前面两层意义实际上均是为了完成一件事情——人性的整合与重塑。希腊有一个著名的神话:双轮马车的驭手理性,手里挽着白色骏马和黑色骏马的缰绳,白色骏马代表着人的精神饱满或充满热情的一面,比较顺从于理性的指挥,而不听话的黑马代表着嗜好或欲望,驭手必须不时地挥鞭才肯就范。马鞭和缰绳不过表达了强迫和限制的概念,只有理性这个驭手才具有人的面孔,而人的其他非理性的部分则用动物的形象来代表。理性,作为人的神圣的一面,从人身上的兽性分离开来。于是就有了一师三徒一马的艺术造型:孙悟空是心“猿”,“意马”则是小白龙。人的贪婪与惰性化身而为猪八戒,人的平庸无识则是沙和尚。所以,一个寻求真理并献身崇高事业的唐僧,必须驾驭着“意马”,约束着“心猿”,催进着“懒猪”,开启引导着平庸唯诺的和尚,在生死、金钱、美色的诱惑中去磨练心性,修炼人格。若变换一个寓言角度,以孙悟空为主体来解读,那么这个形象展示的是一个人艰难的成长过程。孙悟空是个天生的石猴,用玉帝的话说:“乃天地精华所生”。这一生成境域揭示出孙悟空实乃一个自然的存在,充满了不受文明教化和理性熏染的野性。所以他一出世,就要求绝对的自由,不但要突破空间限制(上天入地),还要突破时间限制(将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上勾掉),这是人的天然禀性和天赋本能,是应该保留和尊重的。但是,人还是需要接受教化的,而人的第一任启蒙老师就是自己的父母。所以,当孙悟空“漂洋过海”找到师父后,师父问他姓什么,他说:“我无性。人若骂我,我也不恼;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个礼儿罢了,一生无性。”一生无性,正是未受教化的说明。菩提祖师听他答非所问,便纠正道:“不是这个性,你父母姓什么。”回答无父无母,就是没有家,一个没有受到文明熏染的存在。因而对他来说,什么父母尊严和权力,一概不知,当然不必遵守。所以他才会大闹天宫。无父无母,即没有父亲代表的权力和秩序,母亲代表的同情慈爱和帮助。玉帝代表父亲,菩萨则代表母亲,家庭的教育是一个人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因此,必须让他知道什么是尊严不可冒犯,什么是秩序不可打乱。一旦触犯了规则,就将受到惩罚,并在惩罚的过程中学会自觉地遵守。所以佛祖就把孙悟空押在五行山下,巨手代表权力,五行代表秩序。因此这一节的回目就是“五行山下定心猿”。玉帝代表社会的外在的权力至尊,佛祖象征人类的精神信仰。一个人的成长,必须有精神信仰,即有精神的提升和畏惧,行为才不会放荡不羁而道德失范。
在人类发展史上,接受文化(紧箍)的规训是必要而且必须的,是保障文明得以发展的前提,是人之为人的必由之路,我们每一个人头上都戴着无数的紧箍咒,只不过我们习焉不察而已。《西游记》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很巧妙地把它作了形象化的呈现,使我们由此而看到了人文教化的本质,这是庄子“混沌凿窍”故事的一个正面阐释。但应该看到作者在这里提倡的是一种文明教化的最高最理想的境界,那就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和谐的兼容并举。既保留人的原始生命的创造力,又具有智慧的理性。如六耳猕猴就是孙悟空潜意识中的魔性,这是连菩萨也不能识破的,如来佛祖就说,这是二心相战,其实也就是人格的分裂。因此,取经修炼的过程就是寻求双重人格的一个美好和谐整合的过程,重返仙界的师徒,其人格自然也就完成一次重塑。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冯文楼:《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罗宗强:《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章培恒:《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