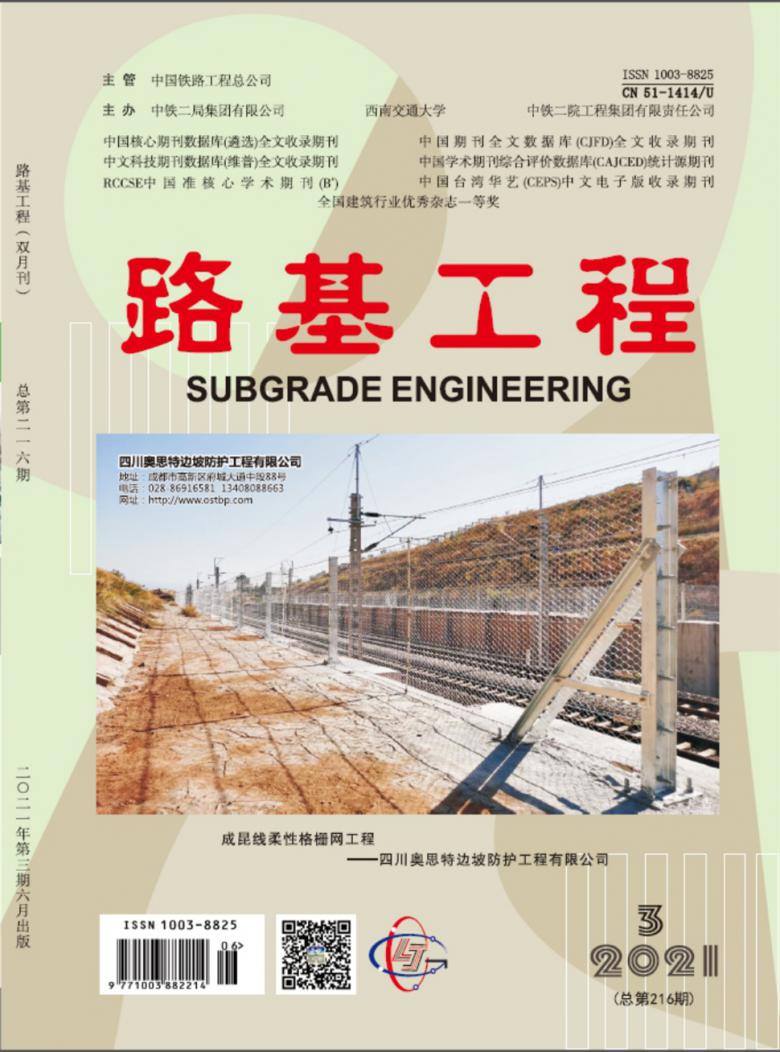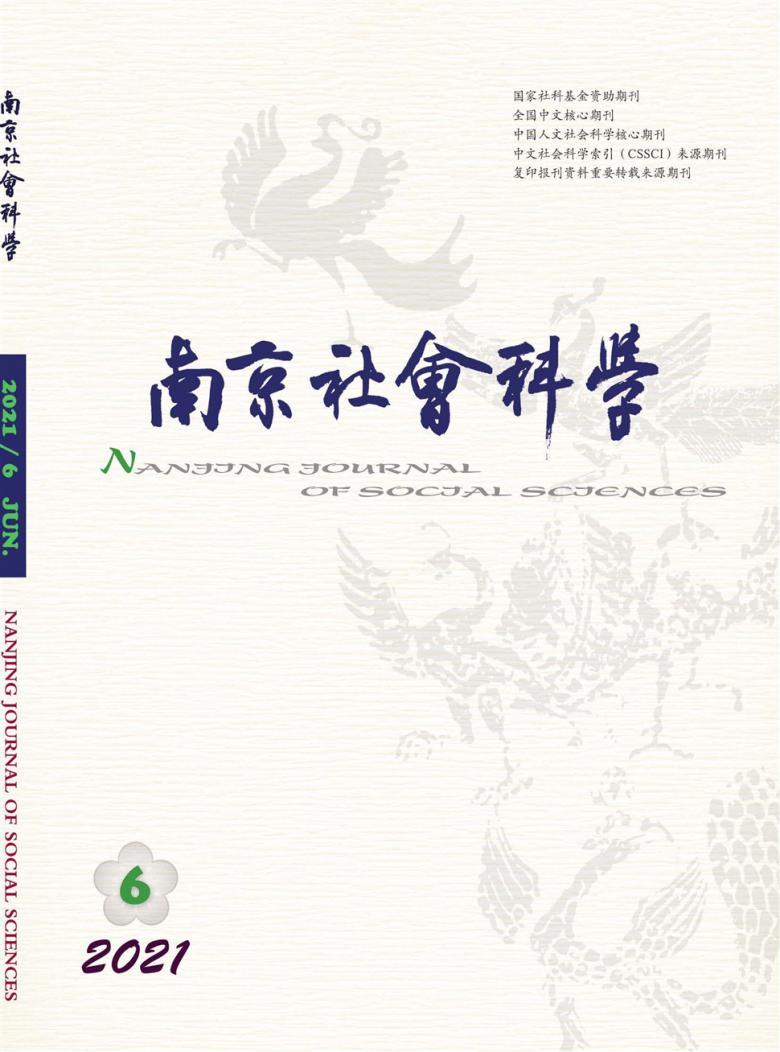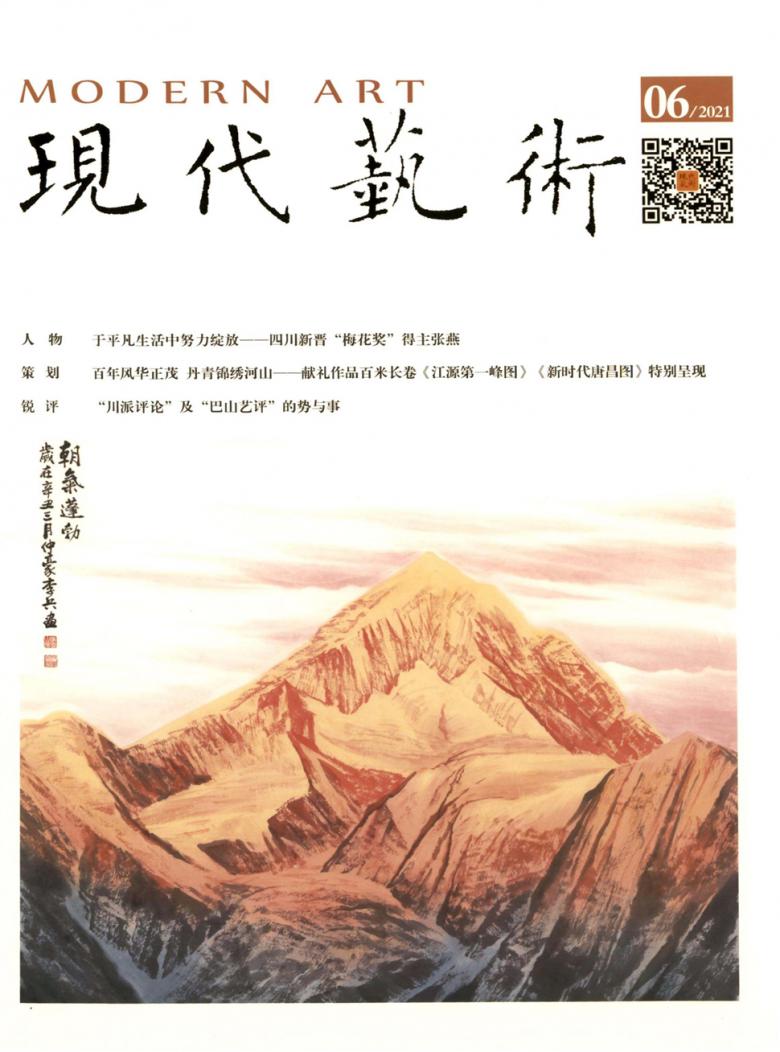论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态及其文学创作
未知 2009-07-09
摘要
元祐年间,是一个政争不断,诗祸不断的敏感时期。作为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和学术主体的元祐士人,呈现的是“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和“渴望自由却深陷其中”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心态的形成,有诸多原因,譬如社会环境,历史及政治原因等。矛盾心态的直接表现在元祐士人对新党和新法的态度以及内部的思想斗争中。此外,矛盾心态更主要的表现在士人的文学创作,对文学内容、文学形式和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元祐士人 矛盾心态 文学创作
引言
谈及元祐,专家和学者们研究的主题不外乎“元祐诗”和元祐党争这两个方面。“元祐诗”作为一个诗体概念,是南宋严羽首先提出来的,被认为是宋代诗歌的最高峰,此论题为后人争论不休。元祐党争,是北宋党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因元祐党人(即“旧党”)的情绪化、意气化,而具有“分水岭”的作用。论及这两个方面,专家和学者们都要触及到元祐时期的士人心态。因为士人的心态能影响到其文学创作,而士人的心态是源于生活的,那么处于复杂政治环境的元祐士人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笔者认为用明人王夫之的一段评价宋人的论述,即可辨明。“宋人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然以此受祸者不少,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则虽无所诽诮,亦可加以罗织。观苏子瞻乌台诗案,其远谪穷荒,诚自取之矣”[1] 。由此可以推断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态是“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且这种的矛盾心态直接影响了元祐士人的文学创作。本文从此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态入手,深入探讨其成因、表现及这种矛盾心态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在这里,需要表明的一点是:这里所讲的“元祐士人”是旧党分子,因为他们才是元祐时期的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和学术主体。
一、元祐士人矛盾心态的成因
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态是“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那么这种矛盾心态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总结出来有四点:(1)新旧党争的仇怨;(2)前人从政后果的影响;(3)宋代特殊的统治政策所致;(4)宋代文人尚党盟的风气。此四点,乃元祐士人矛盾心态的成因,详细论述如下:
(一)新旧党争 仇怨甚深
这是此矛盾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自北宋中期以来,就本着“三冗”问题的如何解决,北宋统治阶层中就一直存在着两种意见:守制和变法,当然不排除一些持中间意见者如苏轼。王安石上台主持变法十七年,是他所代表的新党占上风。新党在变法期间,曾利用台谏制造一些冤假错案,著名的如乌台诗案,来挤兑旧党分子,这难免使旧党分子心生怨愤。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继位,主张守静的高太后掌握权柄。旧党分子纷纷返朝,重新执掌朝政,对新法除一些保留外一概否定,对新党通过控制台谏一一铲除。由于这次“铲除”,不像是变法期间的“乌台诗案”时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整个群体,公开化,使元祐年间一时出现朝中无新党的现象,这更使新党分子感觉到倍感忿怒,报复之心更是炽烈,绍述党锢就是例证。新旧两党的这些积怨和倾轧,虽然能使暂时取得胜利的一方喜悦和“博得忠直之名”,但更多促使士人担心和“畏祸及”。
(二)前车之鉴 士人心悸
这是士人矛盾心态产生的历史原因。古代士人的参政热情是很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的出现,汉时的“布衣将相”,三国的“士庶之争”,隋唐的“科举取士”,五代十国的藩镇幕府,那便是例证。在更为提倡儒家经纶济世精神的宋代,士人更是有更高的参政热情,但在前人因参政而身遭其祸的事实前提下,宋人又不禁有了“畏祸及”的心思。秦时的“焚书坑儒”,东汉的“党锢之祸”,三国的“嵇康之死”,南朝时的“谢灵运被害”,唐末的牛李党争,前人的命运或死或贬或隐。在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的面前,元祐士人不禁有了其它的心思,但无奈身陷其中,只能从文人唱和和山水景物里,去畅想自由的天地,寻找心灵的纯净,故有了“诗人酬唱,盛于元祐”[2]的说法。
(三)重文抑武 台谏相混
这是士人矛盾心态形成的社会原因。由于唐朝以来的地方藩镇割据问题,鉴于此等情况,宋代统治者实行重文抑武政策,科举取士的数量明显增多,便是例证。还有宋代娱乐业的发达和士人狎妓成风,又可以从侧面看出宋代士人的生活水平。科举取士的数量明显增多和宋代士人的生活水平之高,极大刺激了宋代知识分子的功利心。“冗官”问题的出现,可以证明当时官员数量之大。台谏是古代君主监察百官和言明君主过失的制度。北宋的台谏有个特点是:台谏相混,合成一势,且享有“风闻言事”,无需查实的奏事特权。因此,台谏官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朝中势力。前面笔者所谈及到“乌台诗案”就是新党控制了台谏所造成的结果,后面所要论及到的“车盖亭诗案”也是台谏势力运行的结果,所以北宋士人在言谈和进行文学创作时,要斟酌再三,才可行之,更何况是元祐这个高度敏感期。词的言志功能,就是这样被“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的北宋士人如苏轼所开发出来。
(四)讲究师承 内讧不断
这是士人矛盾心态形成的思想原因。宋人尚党盟,认为“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3],极力宣扬“君子有党论”,且党同伐异。其实新旧党争就是一场思想之争,各个党派的政治观点的大碰撞,只是擦出了火花,变成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元祐时期,旧党就是基于这种党同伐异的心理,去否定新法,倾轧新党。旧党之间的内讧,尤其是蜀洛之争,其实就是一场思想之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苏轼的两次策题之谤和扬州题诗之谤,就是很好的见证。在这种惧怕新党的卷土重来,元祐士人还得承受来自从没牢固过的内部其它党派的“飞来横祸”,这就更加加剧了元祐士人的畏祸心理。
从以上四点原因看出,元祐士人虽然怀着古时以来的士人参政心,“寄心王室”[4],一心想博忠直之名,但无奈得承受古人前车之鉴、恐新党卷土重来和旧党之间的内讧这“三座大山”的重压,所以只好夹着尾巴做人,转而寄情山水之间,畅想一片自由想象天地。 二、元祐士人矛盾心态的表现
元祐士人矛盾心态的成因,在上述文段中笔者已经详细论述过,那么这种矛盾心态是如何体现在元祐士人的一言一行之中?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新党和新法的态度和元祐党内的内讧来一一分析。元祐士人矛盾心态的表现是:倾轧新党,排斥新法,内部争斗不断,加剧了元祐士人的畏祸心理。
(一)从对新党和新法的态度看士人矛盾心态的表现
对新党的态度,旧党是意气化和情绪化地倾轧,“车盖亭诗案”是一个高峰。“车盖亭诗案”是继“乌台诗案”后北宋又一文字狱案,牵涉面之广,为宋代历史罕见,其处理和做法都为世人和后人不加苟同。这个诗案,源于新党领袖蔡确在元祐二年在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作的名为《夏日车盖亭》的十绝句,本为抒写夏日乘凉之意,元祐四年却被与蔡确有隙知的吴处厚弹劾诬告,说蔡确在这首诗当中用唐上元年间郝处俊谏高宗传位于武后事影射高太后。作为旧党的台谏旧党梁焘、刘安世,接到此一诬告,竟“皆手舞足蹈相庆,不食其肉,不足以餍”。在高太后的纵容下,遂成大狱。同年五月结案,蔡确被贬岭南新州,四年后死于瘴气。该案的结词是“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本来此案就此到头了,但此事只是个开始,对新党大规模的清洗风暴展开了。此案结案后,元祐党人在蔡确被遣新州的同时,一方面将王安石和蔡确新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借此巩固旧党的势力。诗案发生后,各方反应不一。旧党大部分是欢喜的,但宰相范纯仁、刘挚和苏轼曾试图阻止此案的发生和扩大化,哲宗则是沉默抗之。相比上述苏轼的“乌台诗案”,这次旧党对新党的打击扩大化和公开化,实在世人和后人“难于接受”,甚为新党怨恨。
元祐党人虽“寄心王室”,一心“想博忠直之名”,但是意气使然,挟高太后司马光的威势,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清洗,可谓是北宋历史之罕见,这更加加深了自己的畏祸心理,因为新党的怨恨、哲宗的不满和实权人物高太后的去世,使得他们深恐“衣冠之祸”降临及身。其实给元祐党人带来畏祸心理,还不止于此,对新法的态度,更是犯了儒家大忌。
对新法的态度,旧党是除有些保留之外,全盘否定新法。其实,经过十七年的变法实践,利弊得失愈益清楚,新旧党人都颇有感触。司马光曾在元丰八年四月的一封奏章中,亦承认新法有“便民益国”之处,建议“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便民益国存之,病民丧国者去之”。同年六月,吕公著也说“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然而,当元祐党人掌握实权后,在高太后的幕后支持下,就宣布废止变法,彻底恢复“祖宗之制”,史称“元祐更化”,原因在于元祐党人“愤激太深”。南宋施宿也曾指出一点,说元祐党人虽怀有“更张之际,当须有术”和“别定良法”的愿望,但“愤激太深”,早已失去“和平之气”,从而使政见之争变成意气之争。新党领袖蔡确和章惇曾试图阻止,但无奈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依靠高太后的威权,违反“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儒家经训,悉改神宗之政。这种做法,妄图“以母改子”,大大损害了哲宗的皇权自尊心。随着实权人物高太后和司马光的去世,哲宗的成长,再加上内讧的不断升级,元祐党人内心的畏祸心理更是严重,纷纷离朝外任。
(二)从元祐党人的内讧看士人矛盾心态的表现
在上面的论述中,笔者已经指出元祐党人并不是一个牢靠的执政联盟,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政治思想的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蜀、洛两党之争上。蜀党是以苏轼为代表,主张并不强调某种理念,也不认为某种制度独胜,强调中和之法;而洛党的政见,与王安石多有异同,主张以理想来改造现实,他们所本的理想也是唐虞三代所谓的“王道”,偏重于人,两党之间政治观点差异大。再加上宋朝南北士人讲究地域性,且矛盾尖锐。故蜀、洛两党之争是由来已久,元祐时期的内讧,只是个高峰点,主要体现在苏轼的两次策题之谤和扬州题诗之谤。
苏轼的两次策题之谤,都是来源于苏轼为学士院试职官所撰的两次策题,题目分别是《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和《两汉之政治》是洛党门生所为。第一次策题之谤是弹劾苏轼诽谤仁宗和神宗,源于“媮”和“刻”两字的运用,其实苏轼指的是“今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高太后接受了苏轼的自辩,故苏轼解除了一场政治风波。第二次策题之谤,是攻击苏轼策题有损国体,最后以出守杭州而告终。两次策题之谤,都是洛党以文字为奇货,利用台谏势力发动的,以攻击蜀党领袖为目标,最终都不了了之。在旧党还未取得对新党的彻底胜利时,自己的内部就斗得个不亦乐乎,可见当时士人的意气化和情绪化的严重心理,党同伐异的主体性格更加明显,这不免使得一些士人厌倦国事,不愿陷入是非之争,纷纷出任外地。
扬州题诗之谤,是发生在“车盖亭诗案”之后。此时,元祐党人在朝堂上已无敌手,新党已经基本清理出去了,已经稍微平息的蜀、洛两党之争,在这时更加激烈起来。洛党和朔党不知从何处寻觅到苏轼在扬州作的一首题诗。这首题诗是苏轼元丰八年所作,被洛朔两党攻讦为苏轼和苏辙两兄弟“欲兄弟专国,尽纳蜀人,分据要津,复聚群小”等等攻讦之言。苏轼立马上疏自辩,说即使有此意,哪敢拿出来见人呀,这才免去一场大祸,只是被命出守扬州而已。此次诽谤,又是以“文字”为奇货,虽没搞成什么风波,但自车盖亭诗案后士人畏祸心理更加严重,政治功利心已变淡薄,纷纷出任外地,更加专注于文学创作上。
三、元祐士人矛盾心态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宋代士人的身份跟前代不同的是,即大都是集政治家、文章家、经学家于一身,具备了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学术主体三种特征,作为宋代士人的一部分,元祐士人也不例外。元祐士人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也进行创作,那么在此种矛盾心态作祟下,元祐时期的文学会呈现一种怎样的形态?我们可以从对文学内容、文学形式和文学风格这三方面的影响来解析。
(一)矛盾心态对文学内容的影响
矛盾心态对文学内容的影响,应该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更多的是表现元祐士人的政治观点、学术观点,且从中有不少的攻讦他人之文,言辞激烈,带有很浓厚的情绪和意气成分,如司马光在《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一文论及差免优劣时指出:免役于上户不利,但事实上,却是“彼免役钱虽于大户困苦,上户优便。”这是对新法的言论,可以看出,司马光的政治观点的“愤激之深”。再如在《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八月八日,至卷三七零元祐元年闰二月,不到八个月的纪事中,弹劾新党和批评新法之弊,还六十七篇之多,在章惇被逐出朝后,王岩叟如释重负:“余无大奸,皆柔之徒,易为处置,惟在常辨之,便之不可入而已”。
另一方面,表现亦官亦隐的主题居多,唱和酬唱之文不少,内容空洞,应和他人之文居多。依据是元祐士人参政心切,对新党愤激太深,对内部的党同伐异的主体性格明显,又因怕畏祸及身,再加上生活条件的改善,诗人群体性增强等原因。如苏辙的题画诗作《书郭熙横卷》就表现出渴望自由的主题,前十八句可以看出诗人则通过画境怡悦性情,“食罢起爱飞泉清”,从画面上品味“岩头古寺拥云木,沙尾渔舟浮晚晴”的真趣清味,可谓“不下堂筵,坐穷泉壑”,重现出往日的“江海兴”和林泉踪迹。然而,“归来朝中亦何有,包裹观阙围重城”,诗人对山水的美感享受,仅是画饼充饥式的心理满足,自己仍深陷于“意气之争”,虽然有着对自主,自由的美好向往,但被君权和党人的羁绊。再如苏轼的《郭熙画秋山平远》,诗也作于元祐二年。此时,作者正充满激情地参与“元祐更化”,突然因策题之谤遭洛党之攻击,在观赏郭熙《秋山平远图》,顿生归卧秋山之想。“漠漠疏林寄秋晚”,“中流回头望云巘”,是表达在畏祸心理驱使下的一种真实却无法实现的美好理想,只能作一次心灵远游。诗人此时正处于“受国恩深重,不同众人,不敢妄退”的姿态,只能在再次陷入这个“是非之地”,陷入这无法改变的生命悲歌。面对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诗人追求“平地家居仙”的处世模式。 (二)矛盾心态对文学形式的影响
其实,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是一组辩证关系,什么样的文学内容适合用什么样的文学内容,反之,什么样的文学形式能较好的表达什么样的文学内容。矛盾心态对元祐文学形式的影响是:
元祐士人“欲博忠直之名”,寄心于王室,参政热情极高,且为了打击新党和异己者,那么散文中议论类文体(如奏议),就很好地承担了这一重担。据《苏轼文集》统计,奏议凡一百五十篇,其中从元丰八年十二月还朝至绍圣元年被贬之前,苏轼就创作了一百五十九篇;再据《栾城集》,直接议论时事的书、状共一百五十一篇,作于元祐年间的为一百四十篇,可见创作之多。
元祐士人虽“欲博忠直之名”,但又畏祸及,处于政治漩涡中又不能自拔,唯有寄情于生活和与他人吟诗唱和之间,诗歌里的抒情功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元祐时期,以二苏为宗主的文人中,均或多或少地作有题画诗。据《栾城集》,苏辙作有题画诗凡十三题十八首;据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黄庭坚在元祐作题画诗四十五题五十四首;又据孔凡礼校点《苏轼诗集》,苏轼作于元祐的题画诗三十五题四十八首。再看酬唱诗,围绕在两苏为宗主的文人,由于师从的关系,几乎都对当时两苏和黄庭坚的诗进行唱和,有时还对古人的诗进行唱和,如:元祐元年,围绕苏轼《武昌西山》一诗进行唱和者,竟达三十余人之多,再如:元祐七年,苏轼作《和陶饮酒二十首》,晁补之也随之作《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从中可见元祐诗人酬唱之盛。
由此可见,以政论为主的散文和以题画酬唱为主的诗歌,构成了元祐时期的文学形式。
(三)矛盾心态对文学风格的影响
从以上对矛盾心态对文学内容和形式的评述,可以看出矛盾心态对文学风格的影响应该是:
散文说理因素较重,且有情绪化和意气化成分。依据是:奏议文体自身的议论性成分重,讲究说理;元祐士人在散文中更多的是表达政治观点、学术观点和攻讦他人之语,有说服他人之意愿,故文章机构趋向说理;唐宋以来的文学复古之风,强调文学尤其是散文要承担“文以载道”的重任。如苏轼《再乞郡札子》在说明自己自请离朝的原因,一开篇直说:“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此臣刚褊之罪也。而贾易,颐之死党,专欲与颐抱怨,”直接指出是深忧奸人程颐死党贾易必报旧怨,再罹诬谤之罪,为了避弟之嫌,才自请离职。不仅说明了作者自己的畏祸心理,条理清晰,而且更是情绪化、意气化,“加足料”地攻击洛朔两党,极富说理成分,朴实无华。
诗歌趋向隐晦性和雅化,有悠游心理存在。依据是:元祐士人虽有寄心于王室之心,但随着诗案频发,他们的畏祸心理更加加深,诗歌创作自然而然更加趋向隐晦;士人“畏祸及身”,更加寄情于生活和山水之间,一些雅致生活的事物开始进入诗人的创作视野里;士人欲得自由之身,纷纷要求外任,享受短暂而自由的悠游时光。如黄庭坚的《演雅》一诗,咏及蚕,蛛,燕,蝶等43种动物,它们本来是自然意象,但作者却在古代典籍里字里行间去认识它们,全诗充满着典故。这就是刻意雅化的表现。又如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
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磑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
这一诗,将茶变为文人雅致生活的一部分,可见作者的创作风格雅化的倾向。再如苏轼《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独在起居院读〈汉书·儒林传〉,感申公故事,作小诗一绝》云:
寂寞申公谢客时,自言已见穆生机。
绾臧下吏明堂废,又作龙钟病免归。
虽然表达隐然归去之意,但诗咏申公、兰陵王臧与赵绾先后事楚王之子戊,及戊即位,绾、臧下狱自杀,申公以病免归的故事。用典之频繁,可见雅化之势。
四、结束语
元祐年间,是一个政争不断,诗祸不断的时期。作为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和学术主体的元祐士人,参政热情极高,对新法排斥,对新党倾轧,内讧不断,情绪化和意气化的主体性格明显;但恐遭新党的报复和内部的攻讦,希望摆脱此等困局却不得,唯有寄情于生活和山水之间,与亲朋好友进行唱和,这是元祐士人的普遍心态,是矛盾的。此等矛盾心态,被元祐士人反映于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元祐士人的矛盾心态对元祐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文学主题多是表达政治观点和士人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文学形式选择政论性较强的奏议和陶冶情操的题画唱和之诗;文学风格中,散文多呈现说理化趋势,诗词多隐晦,趋向雅化,有悠游心理。
注释:
[1]丁福保.清诗话[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8
[2]邵浩.坡门酬唱集[Z].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
[3]曹枣庄等.全宋文(卷一五一,第4册)[Z].巴蜀书社校点本:440
[4]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