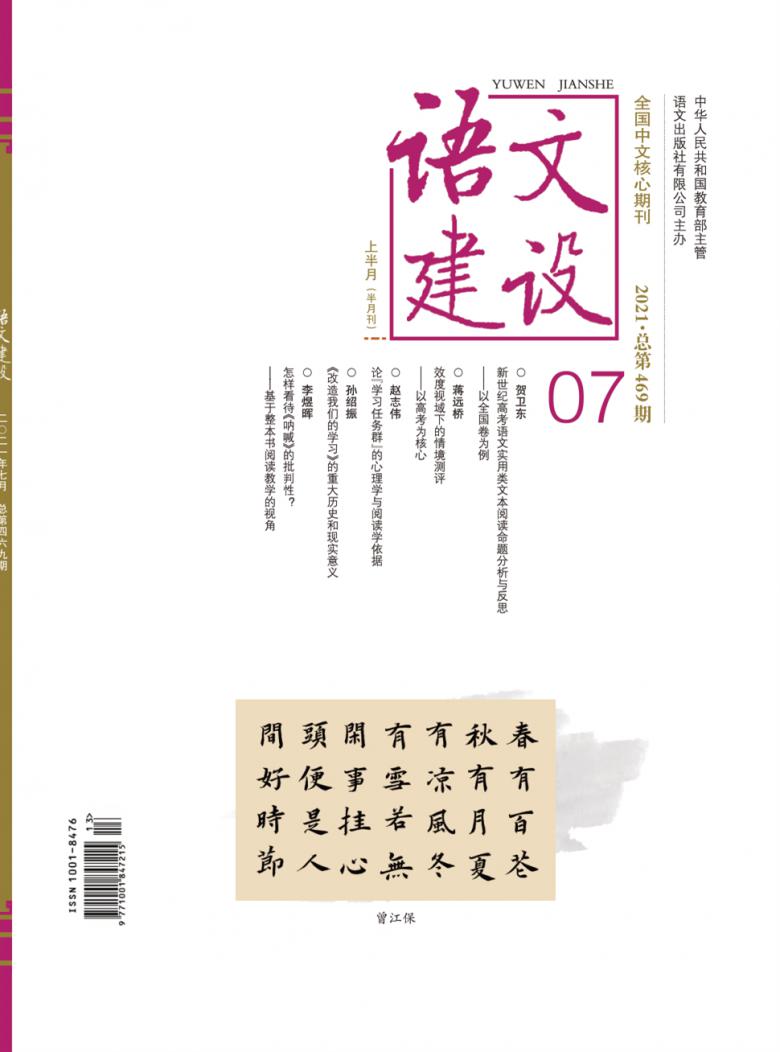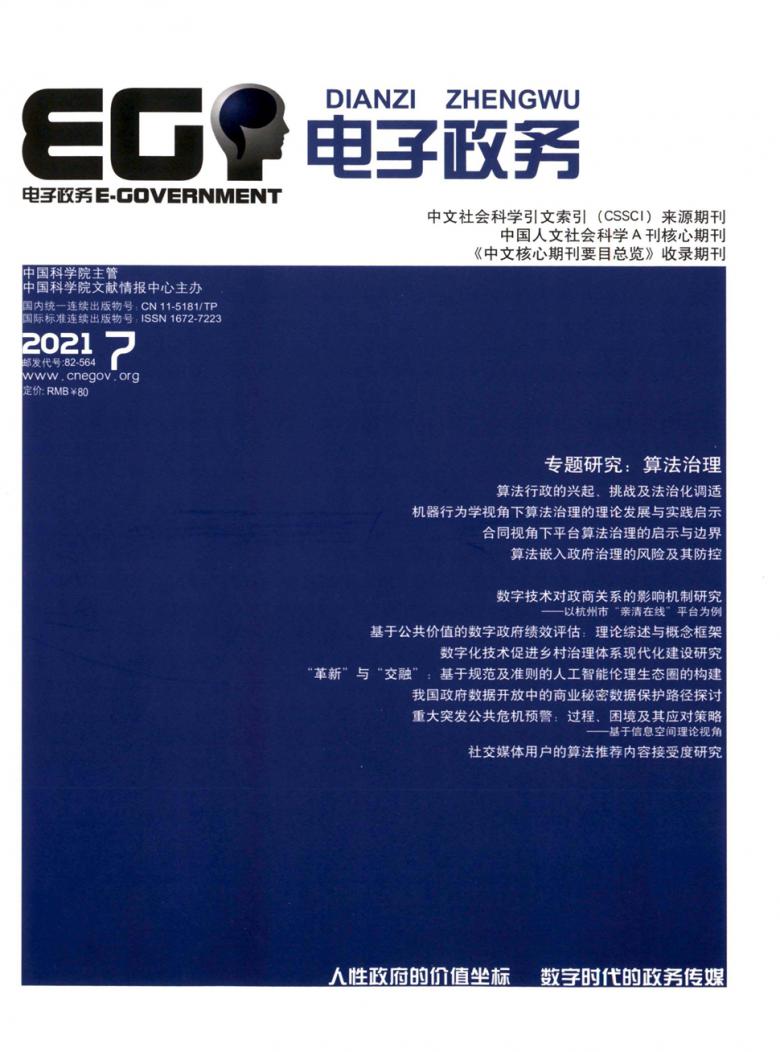关于现代汉语思维的中国当代文学
贺绍俊 2012-01-10
了一次“新写实”的潮流。“新写实”强调零度情感,强调原生态。新时期文学的30年,现实主义基本上仍是文学的主潮。但现实主义经历了一场自我解放的过程,在这之前,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于是现实主义叙述受到偏执意义的严重束缚。新时期文学从拨乱反正开始,拨乱反正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意义偏执的状况,但它并没有改变现实主义叙述与意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后来的发展中,现实主义经历了疏离意义、放逐意义、重建意义的螺旋往复的过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大转型带来中国当代“新的现实”,则是重建意义的必要条件。“新的现实”是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源,“新的现实”变幻莫测的生活万象和前所未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当代作家来说确实也是充满诱惑力的,但由此在对“新的现实”的叙述中也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写作模式和小说样式。20世纪80年代,由知识分子政治精英话语建立起来的新时期文学拨乱反正宏大叙事与现实主义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90年代的中国社会逐渐给市场化加温,经济几乎成为社会的主宰,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和自由竞争原则诱使文学朝着物质主义和欲望化的方向发展,这为现实主义与拨乱反正宏大叙事的亲密关系的松动乃至瓦解创造了最合适的条件。但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摆脱意义约束之后,便朝着形而下的方向沉沦。 三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 中国当代文学是革命胜利者的文学,革命胜利者对它具有当然的领导权。中国革命理论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文学看成是革命的武器和工具,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应该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就召集一批文学艺术界名人在北平商议成立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即以后的中国文联。1949年6月30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正式召开,7月23日,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全国文协的领导成员为:主席茅盾,副主席丁玲、柯仲平。丁玲为文协党组组长,冯雪峰为副组长。全国文协在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大会通过的章程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但实际上它是国家领导和组织文学事业的特别机构,理论上说是群众团体,实际上是被纳入到国家正式编制中的执行国家文化政策的、具有行政性质的机构,其工作列人到国家决策计划之中,是有国家正式编制和相应的政治待遇的。作家协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产物,它不完全等同于其它国家内部的作家协会或作家同盟组织。在20世纪阶级斗争对抗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相似的作家协会机构,随着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这些国家的作家协会也形存实亡,或者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文学的态度,反映了在阶级对垒分明的时代,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文化领导权的愿望。这一愿望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显得更加迫切,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东方专制文化土壤上开展的革命,缺乏资产阶级文明的广泛传播和精英阶层的集结,无产阶级政党以唤醒民众的方式,将启蒙与革命合为一体,这一切决定了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如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前身)成立不久,便创办了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时任主编的茅盾在创刊词中是这样阐述刊物的编辑方针的:“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这一编辑方针更像是在完成一项政治思想任务,而这恰恰说明,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被纳入到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宏伟规划之中的,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但成立中国作家协会等相应的文学组织,只是国家全方位领导文学的方式之一,国家领导文学的方式是多方面的,还表现在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学制度、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方式的确立,等等。总之,国家通过多种方式使其领导和组织文学事业的意图得以实现。这一切,给文学创作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要更为准确、全面地描述当代文学史,就不能忽略对文学制度的考察。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当代文学中的文学制度和文学体制问题,并将其引人到文学史的写作中。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为我们率先做出了一个良好的样板,他在这部著作中注重从文学制度入手去分析一些文学现象的成因,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来文学制度的专著。他在这部专著中阐述了文学制度的现代性意义。 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社会制度,文学制度更为隐性,更多地通过一种社会习惯和精神指令加以实现。不同的社会形态具有不同的文学制度,文学制度是一个社会使文学生产获得良性循环、文学能被广大社会成员接纳的基本保证。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执政者对文学有着明确的政治要求,其文学制度是为了最大化地保证其政治要求的实现,通过相应的文学制度,将文学纳入到政治目标中,这使得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这样一种文学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与文学的自由精神相冲突的,因此文学制度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矛盾就十分的尖锐,这导致了文学制度和文学创作双方的相互妥协和调整。尽管当代文学制度最初明显表现出与文学自由精神的冲突,不利于发挥文学的积极性。但我们在对待这一历史现象时,不应该轻易地从否定文学制度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经验,菲合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