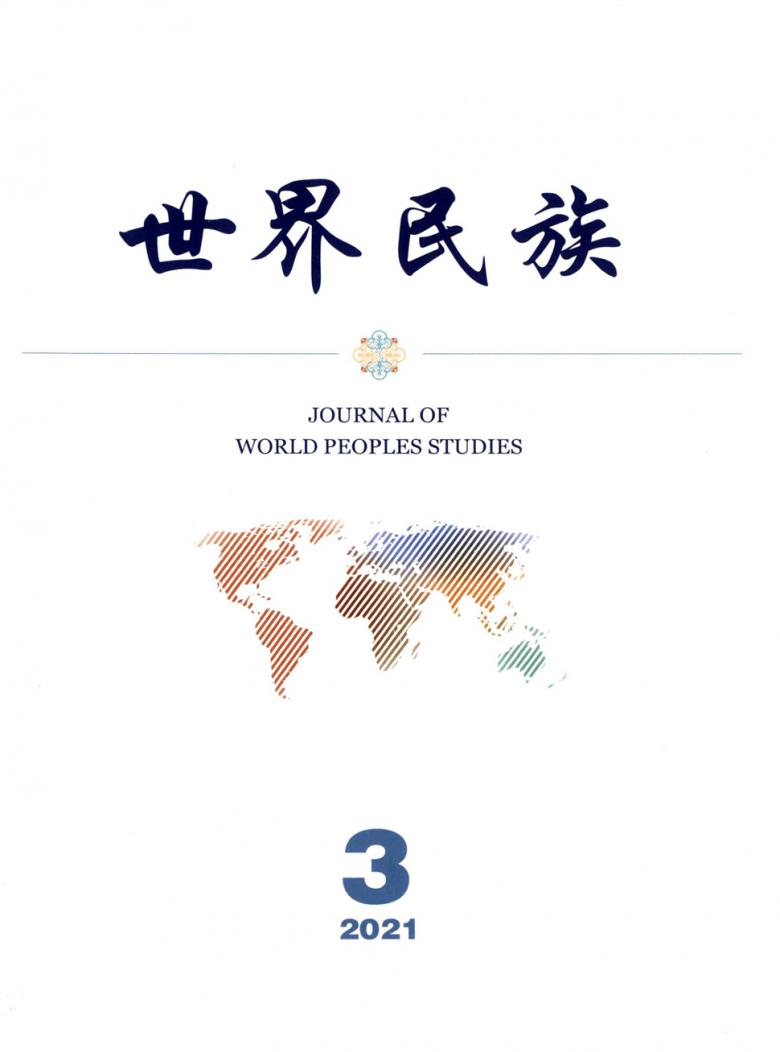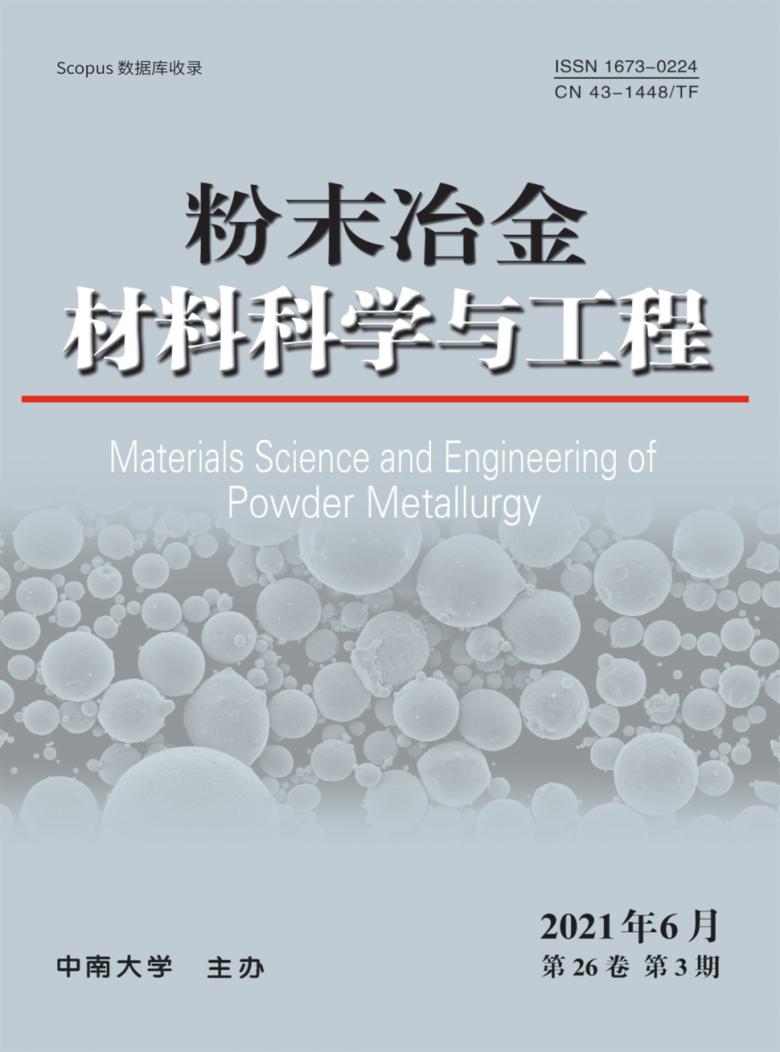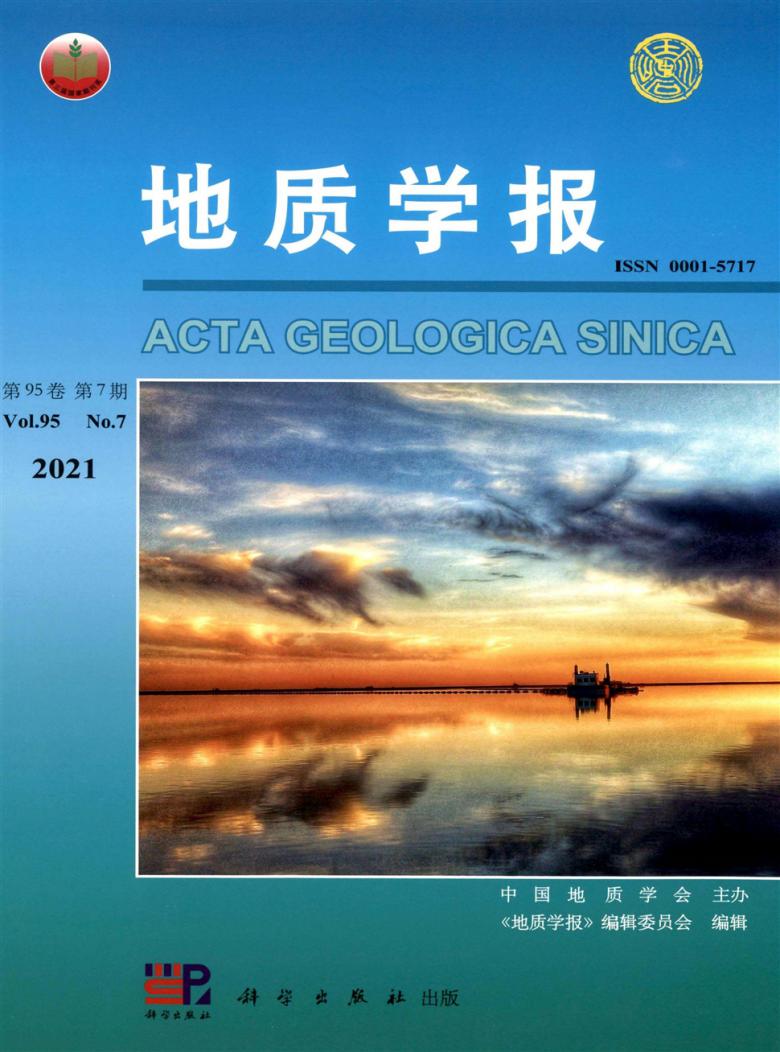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
陈方竞 2008-07-20
【内容提要】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密切相关的。
【摘 要 题】思潮与流派
【关 键 词】穆木天/左翼文学/鲁迅/边缘文化/先锋性/日本体验
【正 文】
一
我与穆木天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不解之缘,近二十年未曾中断,成为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与穆木天的相遇完全是偶然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在吉林师范学院工作。这时候我遇到了索荣昌老师,他是长我近二十岁的老教师。他最初开的课是“鲁迅研究”,但我很快发现他实际上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穆木天的作品和生平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他与穆木天“同乡”,是吉林省伊通县人,研究穆木天自然寄寓着那份别人不具备的“乡情”。但我以为,当时在学术研究受“天时、地利”等诸多限制的情况下,他做出的这种选择是十分明智的。80年代初是所谓“拨乱反正”时期,整个学术界关注穆木天的研究者能有几人?索老师经过中国“传统”的学术训练,对资料极其看重,为搜集资料同时也是为了使这一研究得以更好地展开,他结识了杨占升等老先生,并得到了杨先生的支持。他与当时在学界埋头于学科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且关注穆木天的蔡清富、李伟江、张大明等我素所佩服的先生建立了纯真的友谊,又与穆木天的女儿穆立立始终保持着联系。在他们的努力下,穆木天研究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是极为丰富和完备的,这在当时更关注鲁、郭、茅、巴、老、曹等作家,且又为郁达夫、沈从文等一个个新的研究“热点”所影响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是很难想象的。《吉林师范学院学报》主编黄湛先生与索老师同样有着把研究作为“事业”来做的坚韧品格和甚大气魄,通过省社科重点项目“穆木天研究”的研究,他们在全国扶持了一批穆木天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学报上开辟了“穆木天研究专栏”,持续不断地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既深化了研究又极大地提高了该学报的知名度。于1990年秋,他们主持召开了“全国首届穆木天学术研讨会”,会后又为《穆木天研究论文集》的编辑和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被动”地走进了穆木天研究。所以说“被动”,是因为我这个有着江浙血统的北方人,当初正埋头于鲁迅研究,对穆木天研究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因而有一种“以鲁视穆”心态,这是我的鲁迅研究带来的“陷阱”。应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中任何一位具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世界,都有自己的个性存在的位置。作家研究最重要的是通过他的作品进入到他独有的世界中。对我而言,走近穆木天是需要一个艰难过程的。“文革”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研究者几乎都是从作家研究起步的(这与后来的研究者有些不同),他们第一步的工作又几乎都是从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和阅读作家的作品和生平史料开始的,首先为这个作家编出年谱或生平传略,这是研究的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化,对作家在文学史上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以及研究者“自身”的某种“情结”便不断有所发现。对于研究者来说,他的研究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能够真正走进作家的内心世界,是否能够把作家留下来的文字转化为自己生命的“血肉”,后者可能更为关键。后来,《新文学史料》邀我写《穆木天传略》,索荣昌老师把他多年来搜集到的穆木天的全部作品和生平史料毫无保留地给了我,这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认真地阅读了这些资料,真正地感到了进入穆木天本有世界的艰难,在我的感觉中,这好似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当时,更触动我深入思考的,是关于穆木天对早年生活的回忆及相关材料,阅读过程中不由自主地时时被记忆中的一幅幅画面所打断,那些我熟悉的但又多少感到有些陌生的生活场景在撞击我。那就是我曾经在吉林省的山区经历的五年的“知青”生活,我真的是把自己的“根”扎在了那片土地中,它成为我一生中最能触发思考力和想象力的“经历”之一,成为我后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精神资源之一,当然,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对穆木天的早年生活产生一些感同身受的体验的原因之一,而且,这种使我走近穆木天的“情结”,又是我当时正在思考和写作的《鲁迅与浙东文化》一书的内在推动力之一,即鲁迅作品中再现的他的早年生活,早年生活中蕴含着的贯穿于他的创作并为他有意或无意凸现的“浙东文化”对他的影响。我对这种影响的发现与我走近穆木天的“情结”之间产生了惟有我才能感受到的“同构”。这对我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
二
几乎任何一位学者的学术研究,都不可能将穆木天与鲁迅相提并论而提出他们身上存在着某种一致性,但在我的感觉中就是这样的。首先,穆木天的艺术天分、知识结构、创作成就和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影响及贡献,是远不能与鲁迅相比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现代文学所显现的多元文化内涵中他们没有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要认识这一点,涉及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涉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内涵的认识。
文化是文学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基础,相对于文人的书面文学的人为性特点,文化(主要是民间文化)更多地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性和自然生长性,它确立在发展变化极其缓慢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上。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文化中心的不断转移,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对相对优越的地域性自然生态环境的选择。中国文化中心经历了从中原至西北又不断向江南转移,逐步脱离了它形成之初与中国更广泛地域的多元文化相依存的自然状态。自宋代以后,江南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至清末,虽然帝都北京是政治中心,但文化最发达的地域仍然是江南,主要是江、浙、皖地区,中国文化版图中边缘省份的地域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逐步“边缘”化了。清末中国文化所植根的地域文化的不断缩小,江浙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又促使这种底气明显不足的文化偏于柔弱、纤细发展,这是一种充分“士大夫文人”化的发展趋向,只能依靠充分“经典”化以维持其“主流”位置。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就是这样,到清末已然蜕变成与“边缘文化”相绝缘的贫血儿,蜕变成根本无法自我更新而行将就墓的垂死者。“五四”先驱者就是这种“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学的掘墓人和送葬者,使维系中国文化的固有文化板块破裂了,也就使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主体发展重新获得了与能够赋予它自我更新的血液的“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可能。
王富仁先生近年来站在维护“五四”的立场上对“五四”的反思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区发生的”,“是由那些具有了更广泛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联系的归国留学生具体发动的”,这带来了“五四”新文化和“五四”新文学建构中的“边缘文化”的缺位,这种缺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二十年代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发展趋向性”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特定的发展趋向性”“有它不可能没有的局限性”,使新文化运动仅仅“取得了表面的胜利”,“埋伏下新的文化的或文学的危机”。这种“局限”和“危机”的突出表现是,一方面新文化、新文学形成了“以世界强势国家的强势文化为统一的价值标准”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另一方面则“重新把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提高到一种普遍的、绝对的文化价值标准的高度,将其凌驾在世界各个不同民族文化之上,并自觉不自觉的将其作为统一世界文化的价值标准”,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倾向”。[1](P9)
这就是说,“五四”新文化未能根本改变中国文化发展中“边缘文化”缺位这一顽症。“五四”新文化先驱者主要来自以江、浙、皖籍为主的知识分子,江、浙、皖等地域的文化的文化血脉无疑是前述那个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根基。家族血缘文化背景和早年生活文化氛围使“五四”先驱者难以对“边缘文化”有感同身受的体验,难以通过“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比照来发现中国文化的症结,他们主要依据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根本不同来展开文化变革——对西方文化的借助。在未能引起变革者对中国文化版图中的“边缘文化”的汲取以深化变革时,这种借助是难以使变革者倡导的新文化真正走出他们所攻击的“主流文化”的顽症的。
所谓“边缘文化”,是一种“在人的原初性的存在中,灵和肉、文和武、情感和意志原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是人的这些不同方面还没有被后来的书面文化和西学东渐之所谓“科学”及其创造的物质文化所分解的文化,是一种含有人的“天性”和“血性”的文化,这种文化造就的是“完整的人”,是完整地“表现出自己真实的欲望、情感、意志、理性的人,是所有这些都有机地结合为一个物质精神整体的人”。[1](P12)
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几千年的发展对“边缘文化”的不断沥除,其主流趋向的书面化以致人为化,成熟以致烂熟,导致文化在人的精神建构中使人本有的“天性”丧失。因此,面对这个“古国文明”,“五四”确立的“立人”思想不能不表现出一种“反文化”的特征,这在鲁迅思想和创作中有突出的表现:他留学日本期间,由“日本体验”激活的“中国体验”使他与尼采产生精神共鸣,表现出某种“反文化”的精神倾向,提出的“气禀未失之农人”的“厥心纯白”具有他的生命本源上的意义,[2](P30) 这使他与“一意于禁止赛会之志士”相对抗,在文章中激烈地为他熟悉的故乡农民迎神拜鬼活动辩护;[2](P30) 他1919年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在“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身上,“自然而然”地能发现“一种天性”,并且说,“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3](P133、135)
鲁迅在“五四”退潮后更加明显地表现出超出新文化视阈的追寻:1924年他到西安讲学,在易俗社听秦腔时提笔写出“古调独弹”,他神往的“汉唐气魄”和“魏晋风度”就与这片土地相关;1926年他着手于《朝花夕拾》的写作,该书很快结集出版。逝世前,他又饱含深情地写出《女吊》。这些回忆性散文对自幼就渗入自己灵魂深处的“人与鬼相交融”的民间文化的重现,浓墨重彩地涂抹故乡农民喜爱的“无常”鬼和“女吊”鬼,这自然也是对他生命的精神源泉的再现。鲁迅更进一步表现出对北方的大自然景观的由衷向往。他撰文赞颂“朔方的雪花”,说“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灵”;[4](P181) 他1928年在上海“看司徒乔君的画”,说自己“爱看”作者笔下的与“爽朗的江浙风景,热烈的广东风景”迥异的“北方的景物——人们和天然苦斗而成的景物”,认为其中显现了“中国人”的那种“天然的倔强的灵魂”。[5](P72~73) 这实则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相对恶劣而“边缘”化的北方保留着充满人的生命活力的生命形态的发掘和肯定。所以,鲁迅极其重视来自边缘省份底层社会的青年作家的创作,他竭力帮助因故土沦丧辗转来到上海的萧军、萧红,还有来自湖南的叶紫,自费编辑出版他们的作品,起名《奴隶丛书》,并为他们的作品作序。在他看来,这些作品与那些“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迥异,别有一种意义,属于别一世界。
三
如果我们认识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文学发展中“边缘文化”的缺位,延续并进一步强化了北京尤其是江浙的文化中心位置,认识到这一“文化中心”的文化建构中的“边缘文化”的缺位,是新文化、新文学发展中经“五四”冲击的书面文化的士大夫文人化传统复活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建构中缺位的东北文化、西北文化和西南文化滋养、培育的作家,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之介入“文化中心”,这种介入显然具有突出的“边缘文化”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都市文化”日渐明显地表现出的士大夫文人化的致命缺陷,同时,也构成对造成这种复旧趋向的前述新文化、新文学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和“狭隘民族主义文化倾向”的有力冲击。
沈从文1924年末在《晨报副刊》上以《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出现,几年后写“湘西世界”充满人的“天性”、“血性”和“蛮性”的《柏子》、《野店》、《旅店》等小说,使读者眼睛一亮,心灵为之震动,即是一例。穆木天的情况较之沈从文显然更为复杂:一方面,他始终并不以自己来自东北而自惭形秽,自认是“东北大野的儿子”、“东北大野”、“北国之人”一类词汇经常出现在他笔下,他是最早一位带着东北文化特征进入新文学殿堂的作家;但另一方面,他的“进入”明显有别于沈从文,与后来的东北作家群的出现更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沈从文尤其是后来的东北作家群“介入”新文学,是在与新文化碰撞中凸显他们创作的“边缘文化”特征的,那么,穆木天步入文坛时较多地受到了“边缘文化”缺位的新文化的淫染,使他与东北文化本有的联系显得模糊了,就像雾退而渐渐地亮出湛蓝的晴空本色一样,他是在相关背景下强化了他的创作的“边缘文化”内涵和特征的。
这种状况使穆木天“五四”后的20年代的创作与30年代转向左翼文学后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区别。研究者在“文革”前后曾经过分肯定后者而不屑于瞻顾前者的“靡靡之音”,近十多年来则恰恰相反,充分发掘前者对于(象征)诗歌本体建设的价值,而对后者已经少有人顾及了。穆木天的文章和创作中突出表现出的这种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念的大幅度变形,他的“觉今是而昨非”,在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屡见不鲜。我们需要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具体感受所研究的对象,从中捕捉一些更内在的、在研究对象身上持续性存在的、更富有生命力的因素。我认为贯穿穆木天一生创作的核心“情结”在他的“故土家园”,但他对此的自觉以及从“边缘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是与时代的影响和他投身左翼文学的经历相关的。
穆木天15岁即1915年由吉林一中转学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其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8年至1926年留学日本近8年,这一段时间是新文化、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期,他尽情地汲取新文化的养料,从确立“科学救国”的理想到做出“弃理从文”的选择,启蒙主义思想自然使他对生养他的故乡文化中的愚昧、落后的东西产生反叛倾向,但他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顺应新文化要求中剥蚀着或者改变着故乡文化对他本有的影响。家庭的败落,寄身异域的“弱国子民”的境遇,还有他与创造社同仁一样的浓重的“怀乡病”,以及青春期经不住失恋搅扰的情感波动,都促使他深深地沉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的氛围中,“热烈地爱好着那些象征派、颓废派的诗人”,“追求印象的唯美的陶醉”,自认:“我读了诗人维尼(AIfre de Vigny)的诗集”,“好像是决定了我的作诗人的运命了似的”,[6](P416~418)“在象征主义的空气中住着,越发与现实相隔绝了”。[7](P428) 他选择并认同的是法国19世纪的贵族文学传统,他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法国象征主义鼎盛期地位“隐微”的年轻诗人萨曼,认为萨曼承继了死于法国大革命断头台的贵族诗人安德烈·舍尼埃开创的古典主义传统。穆木天对法国贵族文学古典主义传统的择取,是与《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的法国平民文学取向相矛盾的,这使他1926年回国前后写出的《谭诗——致沫若的一封信》、《写实文学论》等文章较深地触及文学革命倡导的一些症结,他提出的“纯诗”理论有助于“五四”白话新诗切合诗歌自身性质的发展。但是,穆木天的“纯诗”理论及创作,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就他自身而言,这种理论及创作也是“转瞬即逝”的,他不久就宣布自己和这种理论及创作告别,他投身于左翼文学倡导和创作中。我认为,认识穆木天的这种“转向”,必须结合他身上根深蒂固存在的“边缘文化”特征,他始终没有割断与曾经生养他的“东北大野”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被他留日期间的法国贵族文学取向弱化了。这涉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留日知识分子身上的“日本体验”与“中国体验”关系问题。
对于中国的留日学生的“日本体验”,应做出不同层面的分析,但这种分析不可抹杀其主导趋向和核心内涵。首先,日本与中国同在东亚,自古属于同一文化谱系,这一文化谱系的中心无疑在中国。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民族,地理位置又处在东西方之间,这决定了日本文化对于中国固有的汉文化明显具有“边缘”性特征。我认为这种“边缘”性在近现代之交之于中国具有双重内涵:日本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不仅较之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之于汉文化具有更为突出的“边缘化”特征,而且,当“五四”中国开始挣脱“固有文明”的束缚,开始进行自身脱胎换骨的改造时,日本与中国的固有联系以及日本业已形成的与世界的广泛联系,日本文化又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如鲁迅所说:“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日本虽然“并无固有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8](P243~244) 鲁迅同时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认为这些作品“主旨是专在指摘他最爱的母国——日本的缺陷的”,[9](P251) “作者对于他的本国的缺点的猛烈的攻击法,真是一个霹雳手”,[10](P250) 作品“所狙击的要害,我觉得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10](P250) “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尤其是很自负的所谓精神文明”[9](P251)——“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10](P250) 其次,鸦片战争以后,中日两国强弱不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泛滥,自恃强大,甲午海战及“马关条约”,使中国人蒙受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之耻,近现代之交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无一不与日本谋求在华利益相关,这带来两国关系的极度恶化。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对此感受和体验甚深。(注:鲁迅在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中对藤野先生深切的怀念,是与这一感受和体验直接相关的。)所以,留日知识分子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难者,一方面,“日本体验”激活了他们自幼的生命历程中的“中国体验”,同时也深化了他们的“中国体验”,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和症结有更加清晰和深入的感受和认识,批判矛头明确指向“文明古国”的“文化不可更移”之论,主张“改造国民性”。他们的“立人”主张具有明显的“边缘文化”特征;另一方面,正是“日本体验”使他们真正感受到来自这个民族的威胁,他们有着更加突出的民族危机感,变革意识强烈。我认为,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日本体验”在中国现代作家身上的主导趋向和核心内涵。
这就是说,中国现代作家的“日本体验”一旦脱离了与他们身上根深蒂固的“中国体验”,一旦消解了这种体验中深切感受到的民族危机意识,他们的“日本体验”就会发生蜕变。就前期创造社作家而言,他们的“日本体验”应该近于鲁迅,但由于他们自身的特点和境遇又表现出与鲁迅的明显不同。这种不同,一者表现在他们缺乏鲁迅那代人更为深刻的“中国体验”,另者,他们在日本更加突出地感受到民族危机,那种自我生存境遇中“弱国子民”的屈辱心态又弱化了他们的“中国体验”,如郑伯奇所说,他们在日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而使他们“对于祖国便常生起一种怀乡病”,使他们在文学上“走上了反理知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11](P12) 如果说郭沫若和郁达夫在日本所学专业与他们的创作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更主要是在精神上感受“五四”中国,在精神上感受自己在日本的境遇,在这种境遇中感受欧美文学,那么,穆木天的法国文学专业的学习,则不具有这种精神感受特征,由其境遇滋生的“怀乡病”,表现出的是浓重的“传统主义的情绪”,[6](P419) 他由此而对法国贵族古典主义文学传统产生强烈共鸣。他与出生于西北的郑伯奇和王独清,在这种相近的思想倾向中问难于国内的新文学的“反传统”而提倡“国民文学”,反映出他们与自幼生活的那片土地上的“边缘文化”并没有切实的联系。如穆木天的《给郑伯奇的一封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他与钱玄同的争辩文章,他倾诉的爱国主义“情肠”是要求“复活起来祖国的过去”,[6](P419) 这“过去”对远在异国的他是朦胧的。穆木天同时开始的象征诗的创作中也是如此。《旅心集》中的不少诗篇是写他生活过的故乡和日本东京的,但经过他的法国文学取向中的重朦胧、尚音韵、取印象的象征主义表现手法的一番涂抹,很难区分出他的故乡景致与域外风情在外在表现和内在意蕴上有什么不同。如写吉林市的雪花(《落花》)、北山(《北山坡上》)、天主教堂(《苍白的钟声》)等,呈现出的是经他主观变形过滤后的弱质化的物象,反映的是他特有的“日本体验”中的缠绵、沮丧的情绪和那种依恋传统的牧歌调。这些诗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诗歌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探索,被郁达夫推崇,是穆木天借鉴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新诗艺术形式的开拓。但诗中的画面和情调缺乏精神的内涵,明显不是那个根系于“东北大野”的穆木天的性格的体现,你从中感受不到“东北大野”赋予他的精神因素。
穆木天早期诗歌创作中的这种故乡文化“变形走样”的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典型性。这与“五四”后缺乏“边缘文化”支撑的新文化相关。新文化不仅没能为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新文学作家提供认识都市必要的思想文化资源,而且,当这些作家借助新文化而融入现代都市时,他们创作的“边缘文化”特征随之会被消解。我认为沈从文就有这种情况,他的植根于“湘西”而与他所置身的都市文化相撞击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但读他的这些作品也能感到,他缺乏萧红、萧军走进大都市上海后仍保持着与“边缘文化”的联系的那种精神定力,他与“湘西”之间是一种缺乏精神支撑的文化联系,这使他在影响着都市的同时,都市也在影响着他。如他过分迷恋于两性关系的写作就是一个都市新文化所热衷的话题,他主要通过这样一个渠道逐步为都市所接纳。又如何其芳,他走出西南巴文化区到北京求学,创作上一举成名,但从他获奖的散文集《画梦录》中能读出他应该有的那种较少“文明”教化的故乡“边缘文化”特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