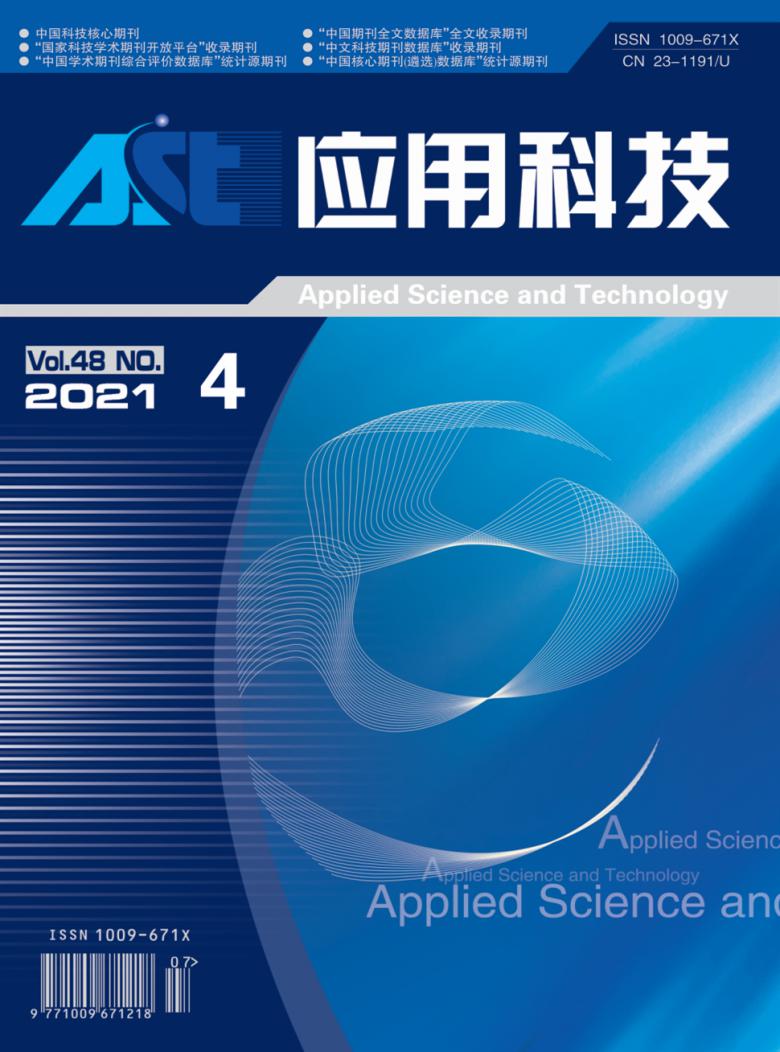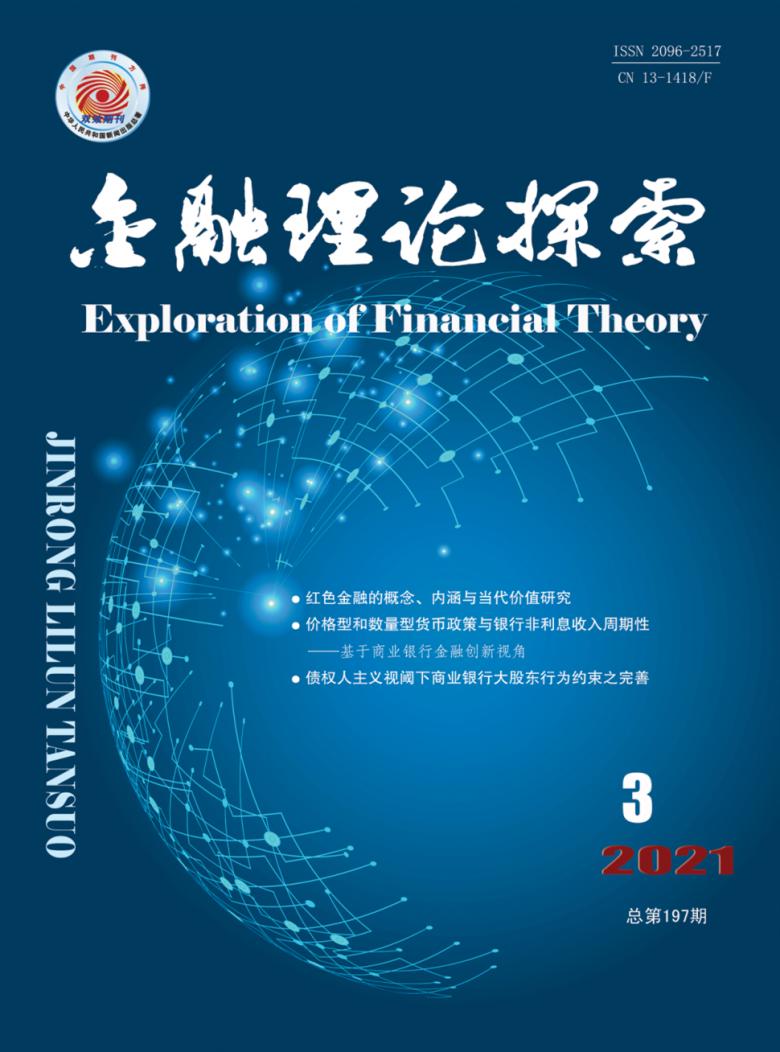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前沿扫描
秦弓
20世纪50年代初,当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进行规划、建设时,曾有历史学权威对其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表示怀疑。的确,当时所理解的现代文学,一则时间短,从1917年文学革命发难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只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与三千多年的古代文学竟有百倍之差;二则那段历史刚刚过去,缺少历史学科所需的时光淘洗。但是,因为现代文学特殊的历史地位──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文学转型,承担了现代精神建构的文化重任,参与并见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所以,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如今,现代文学史不仅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当之无愧,而且不断给整个人文学科提供新鲜的话题。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历史时段的理解向前后延伸。“20世纪文学”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打通了过去壁垒森严的近、现、当代的界限。书名标明20世纪的中国文学通史、文体史、地区文学史著作如雨后春笋。与此相应,许多高等院校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合为一个教研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辟“近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栏目,倡导扩大学术视野。2002年10月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以“四十年代与‘十七年’(1949-1966)文学”为题,探讨现当代文学的转型与发展、差异与联系。会上揭晓的首届王瑶学术奖,九项获奖成果中就有两项属于“打通”之作:刘纳的专著《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洪子诚的论文《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2003年3月评出的唐青年文学研究奖,获一等奖的四篇论文中,也有王枫的《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其视野上溯至晚清。现代文学研究不单单是跨越既有畛域,涉足近代与当代,更为可喜的是无论研究哪一时段的文学现象,都表现出贯通的历史意识。
二是对“现代”指认的范畴有所扩大。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现代文学即等于新文学,而同一时段的旧体诗词则被排除在外,只有特殊场合,譬如鲁迅的《自题小像》才作为崇高人格的例证被引用,而并非作为一种文体予以肯定。通俗小说堪称难兄难弟,要么视若不见,要么作为旧文学的沉渣泛起而大加挞伐,就连与时俱进、并且拥有广大读者的张恨水也未能幸免。其实,新与旧之间的关系,不只有对峙、冲突、阻遏的一面,也有竞争、互渗、互动的另一面。近年来,尽管仍有学者坚持绝对排斥的立场,但将旧体诗词与通俗小说视为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已经趋于成为现代文学界的共识。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开始尝试将旧体诗词纳入视野,多种文学史著作列出专章,梳理通俗小说与新文学小说交织并行与互渗、互动的历史关系,阐释前者或隐或显的现代性因素。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更是以丰赡的史料与多重视角描绘出通俗文学全景图,为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拓展了视野。随着历史主义精神的确立,关于保守派的认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学衡派,不再单纯地视为新文学的对立面,予以全盘否定,而是注意到其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价值,将其看作现代文学建设的共同参与者。整理国故也得到重新评价,被认为是民族文化顽强生命力的内在要求,是文化转型过程中对外来影响与民族传统关系的自行调整。
三是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现代文学发展中外部的文化关联与内涵的文化因子,经多重文化视角的观照,得到颇为开阔而深刻的揭示。制度文化方面,有关于三四十年代政治审查制度的研究,也有关于“十七年”审查内在化──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绿皮书”出版前作家对旧作的修改──的研究;传媒文化方面,有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局、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有《申报》及其《自由谈》副刊、《大公报》文学副刊、《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论语》等报刊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地域文化方面,仅湖南教育出版社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就包括吴越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上海城市文化、东北黑土地文化等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教育方面,有清华、西南联大、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等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宗教方面,涉及道教、萨满教、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民族文化视角,有关于老舍与满族文化、沈从文与苗族、土家族文化等的研究;性别文化,主要是女性主义视角,有对冰心、丁玲、张爱玲等女性作家的解读,也有对男性作家文学世界中的性别歧视的揭露,其次,还有男性性别视角的研究,体察文学所表现的现代生活中男性的种种困境。
文化研究的成绩固然可喜,而且尚有开拓的空间,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毕竟有其自身的审美本质,因此不能以文化研究冲淡甚至取代审美研究。现在中学语文教学通常把文学作品拆解成一个个知识点,要学生死记硬背,以便应付考试。高等院校的文学教学中,作家生平+作品主题+风格特征的陈旧模式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在这种教育模式的制约下,对于意境、声韵、情调、文笔乃至文本艺术结构整体的审美能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培养。难怪在大学生中,有的热中于网络为之推波助澜的快餐文化,迷恋于影视、漫画、书刊中到处充斥的肤浅的感情游戏,有的则超凡脱俗,唯思想史诉求为尊,亟亟探索文本的微言大义或所谓的历史规律,而面对色彩斑斓的审美境界却感觉迟钝、手足无措。大学生中,不知《红楼梦》美在哪里、不解鲁迅杂文魅力者大有人在。无论是为了维护文学研究的立身之本,还是着眼于提高学生乃至全民的审美能力,现代文学都应该加强审美研究。近年来,文本细读已见佳绩,这将推动审美研究深入展开,使之成为一个持续发展的热点。 日益高涨的全球化浪潮,给现代文学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怎样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并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现代文学史上的经验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反思。现代接受了外国影响,由传统的杂文学观变为纯文学观,文学划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体裁,其中的散文又设定了种种框架,除此之外,则逐出文学殿堂。这种观念局限了文学的疆域,连现代文学前驱者鲁迅都无法接受,他编杂文集所遵循的文体原则就是同传统的杂文学观接轨的。其实,外国对文学的认定也有宽泛与狭窄之别。罗素、丘吉尔就分别以其哲学、历史学著述获得1950、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分类并非细枝末节问题,文学搞得纯而又纯,势必将本来可以纵马驰骋的广阔疆域拱手让出,将本应强化的文学生命力大大削弱,使得人们容易得出文学仅仅属于文学圈子的误解,其结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全社会文学素质普遍下降,想象力、创造力大打折扣,连儿童卡通片都要依赖进口;经济学文章干干巴巴,“一块蛋糕”的比喻年深日久,已经快要发了霉;电器说明书枯涩费解,令人望而生畏。
在全球化与民族化冲突与互动的背景下,关于新诗与话剧的得失问题,借助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再次被人们所关注。新诗的成绩及其意义不可否认,但为什么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时光积淀,人们能够背诵下来的新诗仍然寥寥无几呢?当然,人们能够随口吟诵几首古诗,与古诗积淀的时间更长、民族的记忆更深有关,但诗歌的形制、意象、声韵与意境等显然是不应忽略的重要原因。话剧不景气,人们往往从电视与光盘的冲击等外部寻找原因。其实,话剧自身也存在着问题。一是与百姓声息相通的好剧本少,二是在观众与话剧之间至今仍未形成观众对于传统戏曲那种依恋、痴迷的关系。中国戏剧传统是以唱为主的歌舞剧,看戏也称之为听戏,哪怕背对着舞台,只要听得见委婉曲折或高亢激越的旋律声韵,也能进入戏剧情境,发生深深的共鸣。而20世纪初叶引进中国的话剧,截然割断了这种已有几千年审美记忆的戏剧传统,难免遭遇尴尬。话剧确有其长处,但如何从传统汲取养分,使之取得长足进展,真正在广大群众之中生根,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现代文学史上,散文与小说的成绩较之新诗与话剧要大得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散文与小说在传统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近年来,这种追根溯源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的研究将有更加广阔而深入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