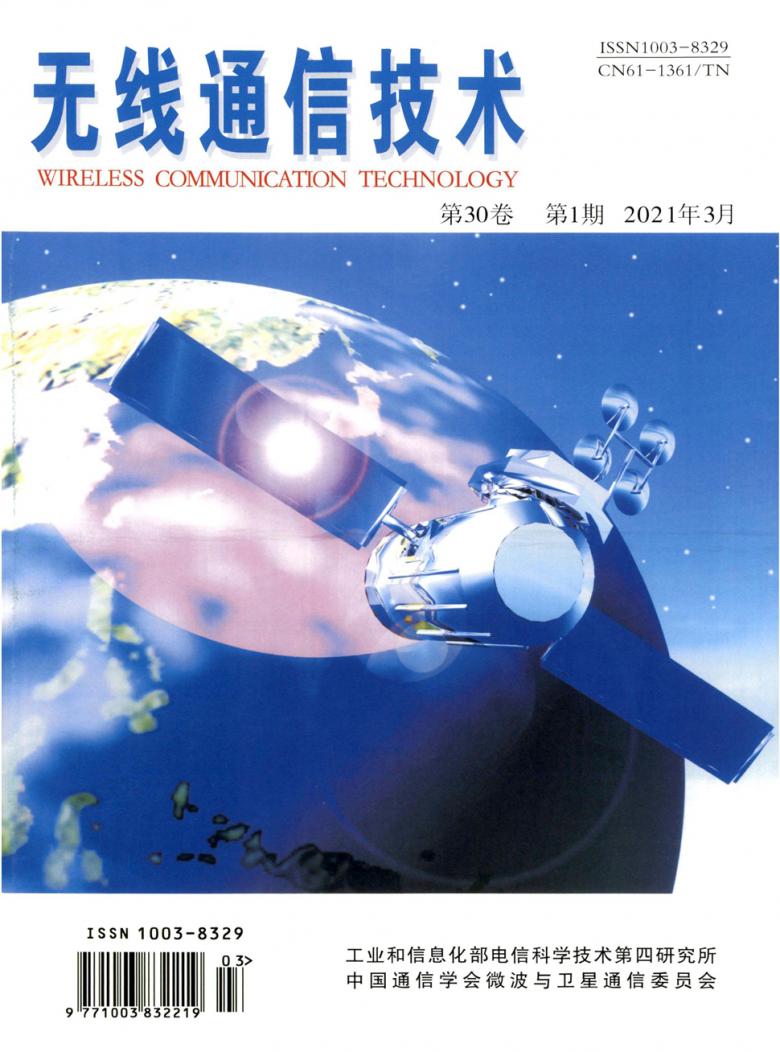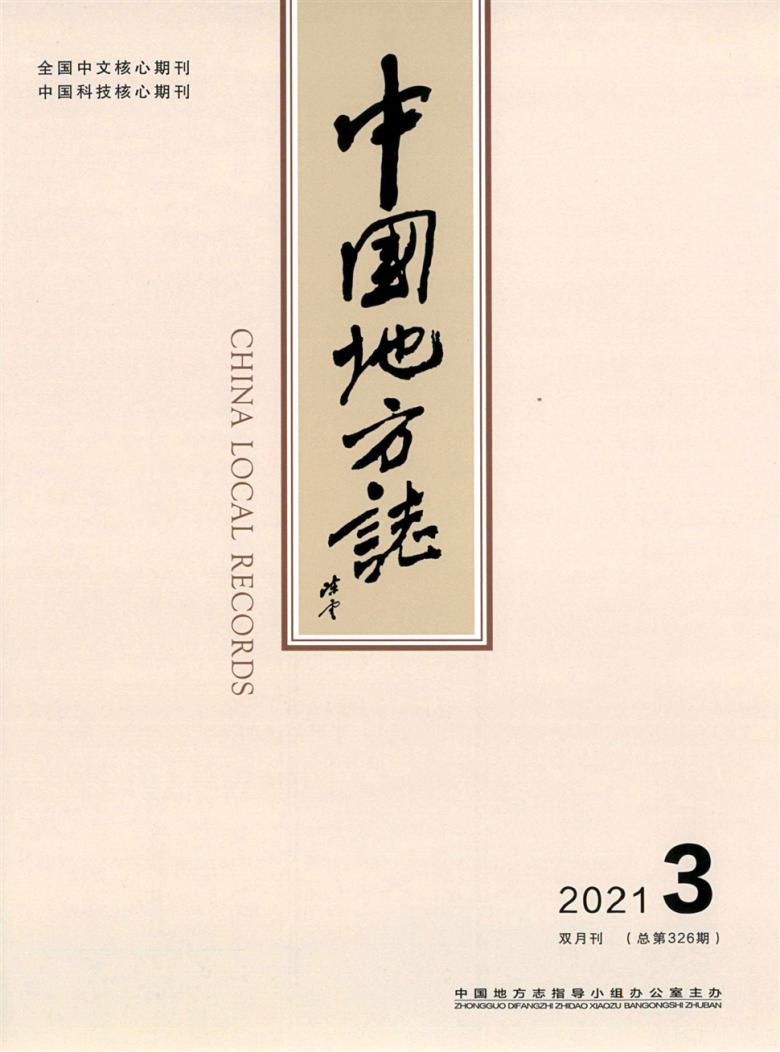邵氏黄梅调电影艺术论
蓝凡 2008-09-08
一、邵氏黄梅调电影:艺术特征缘起 邵氏黄梅调电影虽然仅是戏曲电影片中的一个类型,但却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电影类型。可以这样说,在电影工业理念下的邵氏黄梅调电影,尝试了走现代性格的戏曲电影之途,为传统艺术在现代艺术中的转换做了有益的实验。香港导演张彻说得很深刻:“香港的国语片,第一步‘起飞’便是由于拍摄传统戏曲‘黄梅调’。在邵逸夫主政下的邵氏公司,开始注入大量资金来拍国语片,第一部大成功的是李翰祥导演的《江山美人》。以前国语片在香港的卖座以‘万’为单位,此后才以‘十万’为单位(《江山美人》似是收入四十余万元),而到李翰祥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造成高峰,全香港的影片,成了‘黄梅调’的天下,可说传统戏曲影响最大也最表面化的一个时代。”[1] (P16)张彻的这一描述直接道出了邵氏黄梅调电影的最本质意义:用电影拍摄传统戏曲是因应电影市场的需要,黄梅调电影的艺术特征便也直接与电影的“卖座”挂钩。很显然,邵氏黄梅调电影的艺术特征可以说是一种实用美学的特征,也是一种建筑在电影工业理念/邵氏电影工业理念上的艺术特征。所以,有了邵氏黄梅调电影,我们才知道戏曲电影这一中国/华语电影所特有的电影片种,其中在如何看待戏曲与电影的结合,以及两者如何结合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既造成了不同风格类型的戏曲电影,也是造成今天对戏曲电影的认识仍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的局面。 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视了这一点——因为缺少对邵氏黄梅调电影的关注而最终导致了我们对戏曲电影在类型意义上缺乏完整的认识与科学的把握。其实在中国戏曲电影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倒确实存在“史”(现实)与“诗”(诗意)这两种绝然不同的戏曲电影类型:“将戏就影”——以电影为主导的戏曲电影,及“将影就戏”——以戏曲为主导的戏曲电影,前者是戏曲迁就电影,后者却是电影迁就戏曲。或者又可以说,前者是现代的,后者是古典的。邵氏的黄梅调电影是以电影为主导的戏曲电影,费穆等尝试的戏曲电影和大陆的戏曲电影实践则是后一种以戏曲为主导的戏曲电影。只是邵氏黄梅调电影对戏曲电影类型的铸造历来没有受到重视罢了。 从20世纪50年代戏曲电影的兴起开始,中间经“文化大革命”的“样板戏”阶段,再到20世纪80年代戏曲电影的再次崛起,“将影就戏”几乎成了大陆戏曲电影的主流,如崔嵬、陈怀皑、应云卫等执导的《杨门女将》、《野猪林》、《穆桂英大战洪洲》、《宋士杰》、《武松》、《追鱼》等,全都是因为精确地反映了戏曲电影的这一类理念而成了当时戏曲电影的范本。特别是1960年由崔嵬执导的《杨门女将》,被看作是在大陆拍摄的戏曲电影中没有一部能出其右的精品,以致受到当时政府总理周恩来的推崇。[2] 崔嵬在《拍摄戏曲电影的体会》一文中说,“戏曲片是戏曲与电影这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结合,这种结合并不是谁代替谁的问题”,但“主要应该是电影服从戏曲”,“电影要服从戏曲,不能离开戏曲这个基础,既要保持舞台风格,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要打破舞台框框。要利用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更加发挥戏曲艺术的特点,力求做到虚实结合、情景交融、优美动人”。[3] 显然,“电影服从戏曲”成了大陆戏曲电影的主流观点。 虽然邵氏黄梅调电影乃至香港的戏曲电影是由大陆黄梅戏电影的香港演出而“激发”出来的,但两者的戏曲电影观念并不一致。将内地一个不属香港的地方戏曲剧种与香港的电影产业相结合,其创造的电影类型——黄梅调电影,由于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它不但与早期费穆的戏曲电影理想不相同,而且与其“源头”——大陆黄梅戏电影,在戏曲电影的理念和特征上更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之所以选择黄梅戏而非其他更有传统文化味的京剧、昆剧,说明了其中包含的资讯——对戏曲电影的自身看法。因为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理念。黄梅戏的发生、发展,与京剧、昆剧等戏曲不同,表现出非常的特殊性。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采茶戏,是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以黄梅采茶调为主的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当黄梅采茶在20世纪初逐渐发展成“两小戏”和“三小戏”,并在20世纪30年代因进入上海等城市而最后衍化成戏曲剧种时,它实际上走了一条与中国传统戏曲(京剧、昆剧等)完全不同的路:其时,中国京剧、昆剧和其他声腔剧种(如梆子、秦腔、川剧等)业已成熟,黄梅戏却还刚刚走上它由歌舞向戏曲的嬗变——向中国戏曲和西方话剧两方面借鉴学习的尴尬之路(两种完全不同的舞台表演艺术),所以如果从中国传统戏曲这一角度考察,黄梅戏的“传统”部分并不完整,并且还保留了很多民间歌舞的东西,如剧目《打猪草》、《夫妻观灯》等。黄梅戏的这种特色俨然成了邵氏拍摄戏曲电影的最主要选择依据。 二、艺术特征:邵氏黄梅调电影的艺术亮点 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布烈松曾尖锐地指出,“舞台剧和电影书写结合只会共同毁灭”,“用两种艺术结合而成的手段不可能有力地表现什么,要么全是一种,要么全是另一种”。[4] 他认为舞台艺术和影像艺术在艺术的本质上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融合”的可能。但对中国的戏曲来说可能是个例外,因为我们毕竟有了还算成熟的黄梅调/黄梅戏电影,况且戏曲电影也已经有了这么多年的实践,所以,“对于戏曲来说,影视起先只是摄录手段,渐渐地,它们便以其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和独特的镜头技巧形成了自身的艺术特征”。[5] 然而,布莱松从他导演实践产生的想法,也从另一方面告诉了我们,黄梅戏/戏曲与电影的结合毕竟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这种障碍直接导致了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犹豫”和尝试,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戏曲电影美学观。建筑在电影产业基础上的邵氏黄梅调电影,基于黄梅戏自身独特的发生历史和电影的大众性质,采用了一种非常实用的美学原则:“将戏就影”,一切以电影为主,因此而造就了邵氏黄梅调电影的最本质艺术特征,即它的现代性格,也可说就是黄梅戏的民间性和电影的大众化的双叠后的性格。从这点出发,我们说,邵氏黄梅调电影的艺术特征首先反映在其银幕结构上是以主唱段分割的唱段式结构;其二是它的通俗流传,这是因为其好听易唱的黄梅曲调;其三是它的写实风格,体现在其写实时空与写实动作造型上。 1. 银幕结构:以主唱段分割的唱段式结构 结构就是“叙述”故事的总体框架,银幕结构也就是邵氏黄梅调电影在叙事上的基本态度。它可以分两方面来讲。第一是将传统戏曲的分场结构衍化为以主唱段分割的唱段式结构,从而从基本的结构形态上完成“以戏就影”的构造;第二是将耳熟能详的戏曲故事,尽可能地“塞”进银幕中而非舞台中,从而使故事的“传奇”是银幕般的“奇”而非舞台式的“奇”。 传统戏曲的连场结构形式表现的是点状的矛盾冲突,根据戏剧情节和冲突的要求,分别采用不同的场子,如正场、过场、圆场、转场,以及大场、小场等。在这里,一系列的动作被化成为大大小小的单体动作,按顺序作线性的排列,一个场子基本就是一个中心动作,以完成一次矛盾的冲突。对于传统戏曲结构的这种基本特点,非邵氏戏曲电影一般都“敬之如神”,因为改变了它就等于是动了“戏骨”。以费穆拍摄的梅兰芳主演的戏曲电影《生死恨》为例。《生死恨》是费穆和梅兰芳两位艺术家自觉地“尽量吸收京戏的表现方法而加以巧妙的运用,使电影艺术也有一些新格调”[6] 的力作,前后拍摄时间达半年。梅兰芳事后曾说:“对于舞台艺术进入彩色电影方面的工作,我们打了冲锋,作了大胆的、带有冒险性的尝试,因而是值得加以记述的。”[7] (P234)可见,由于有了梅兰芳的关系,《生死恨》在费穆拍摄的戏曲电影中电影理念是比较“冒险”的,但尽管如此,《生死恨》的连场结构形式在电影中基本没有变动,仅是作了某些删节:“我和费穆都主张拍《生死恨》,因为这出戏是‘九·一八’以后我自己编演的,曾受到观众欢迎,戏剧性也比较强,若根据电影的性能加以发挥,影片可能成功。大家都同意,就决定拍摄《生死恨》。我把剧本拿出来和费穆研究,他说:‘舞台剧搬上银幕,剧本需要经过一些增删裁剪,才能适应电影的要求,我先把它带回去琢磨一下,过几天再来商量。’我说:‘我们共同斟酌修改,彼此有什么意见只管提出来讨论。’我们经过研究,根据舞台剧本进行了修改,台词、场子方面有增有删,有分有并,从舞台剧的二十一场改成十九场。”[7] (P215)对于这样的结构,梅兰芳和费穆都满意,认为是“利用电影的纪录,或者合乎目前的需要”。[8] 梅兰芳甚至说,《生死恨》“在剧本改编方面,在舞台艺术如何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方面……都是有成绩、有收获的”。[9] 与此不同,邵氏黄梅调电影几乎是将戏曲的分场结构完全打碎、推出,用主唱段来作为分割结构的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弱化”了戏曲的色彩而加重了银幕感——电影的结构。如果将邵氏《天仙配》加以比较与大陆拍摄的黄梅戏《天仙配》加以比较,两者在结构上的差异就更是一目了然。特别是《王昭君》,唱段、琵琶曲相继组合,构成了整部电影的结构,所以,这种结构表现出来的电影的节奏,一定不是戏曲舞台的节奏,而是电影节奏,或者说就是音乐的节奏。邵氏《三笑》因是1969年的后期作品,其结构可以说已经完全没有戏曲连场的任何痕迹,而是标准的电影结构——连唱段的结构作用也被推到了银幕之后。邵氏黄梅调电影的这种结构方法也反映在对待传统戏曲的故事叙述上。应该说,无论是邵氏黄梅调电影还是另一种戏曲电影,都是将耳熟能详的戏曲/传说故事当作自己的基本剧目。因为剧目故事的丰富——“唐三千,宋八百”,本来就是中国戏曲的一大优势。而通过中国传统戏曲/传说故事的引入,激发的是它们背后的深广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也是戏曲电影吸引观众的一个主要动因。但由于邵氏黄梅调电影的结构需要,它一般避开舞台式的叙述故事,将戏曲在叙事上的特长——所谓“说书人的嘴,唱戏人的腿”——通过演员的动作表演来讲述故事/推进剧情——推倒不用,以避免“戏曲化”。譬如《江山美人》改编了京剧传统剧目《游龙戏凤》的结尾,李翰祥用文人的视野将大团圆结局改为悲剧,李凤最后死在日思夜想的皇宫前。如果以戏曲思考,这一场电影根本不可能完成,因为巨大的宫殿和人群,会“扼杀”演员的“戏曲”表演。但对邵氏黄梅调电影来说,用不着“腿”,用群唱的“嘴”很自然地表现了人物,推动了剧情,加上庞大华丽的景,一下子就将故事推向高潮。 可见,邵氏黄梅调电影的银幕结构叙事从根本上排斥了戏曲叙事的可能,而使自己成为当时标准的大众娱乐的电影——而不是已日益丧失观众的银幕上的“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