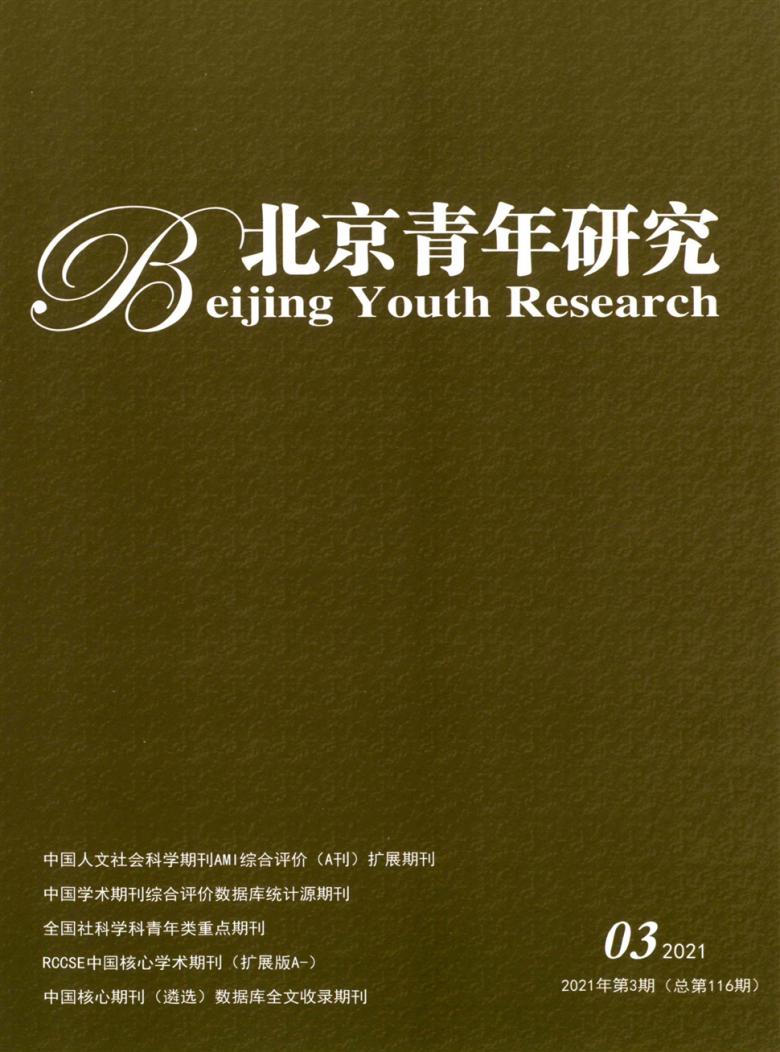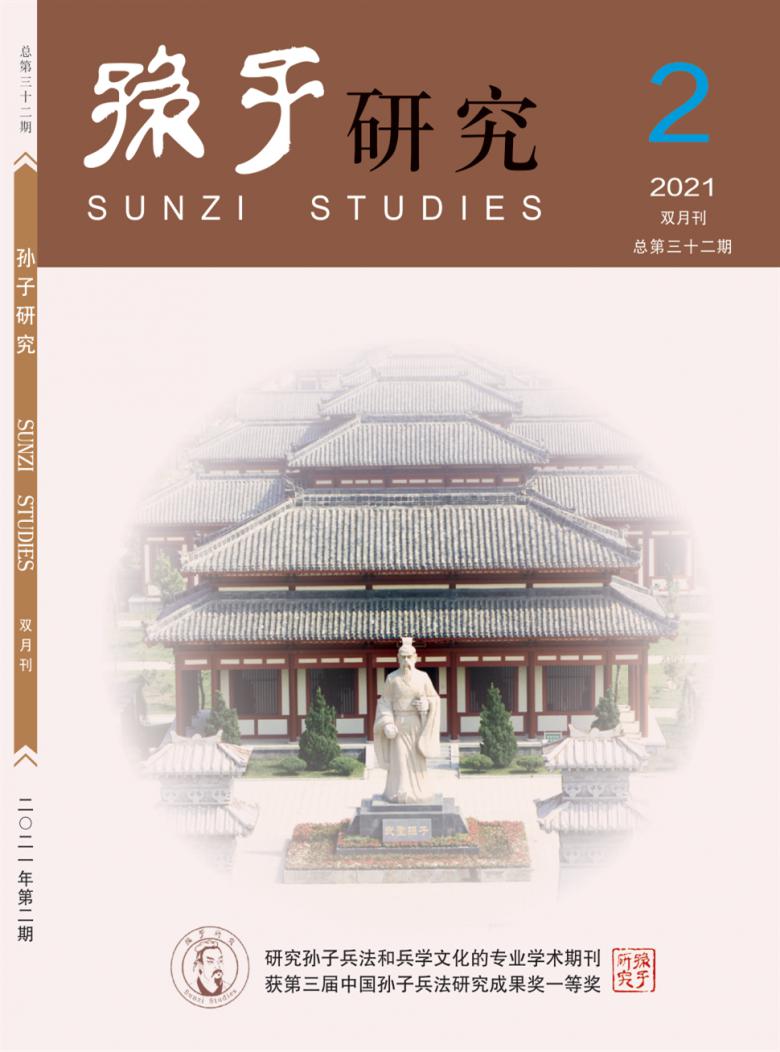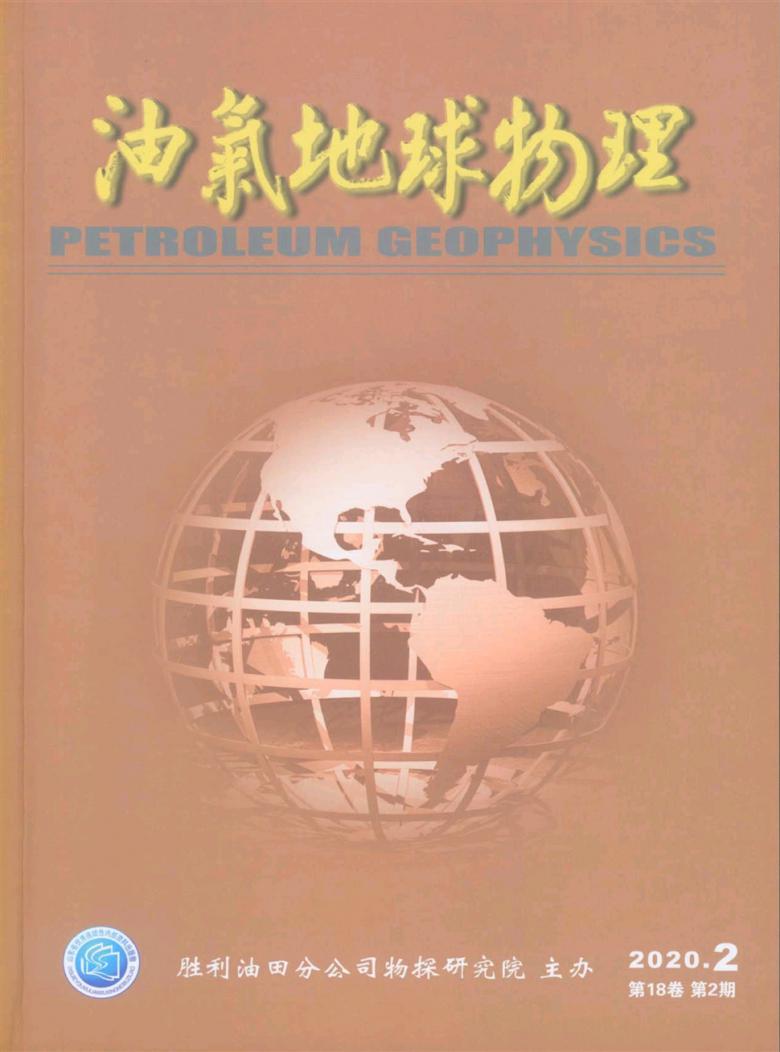三重缘:诗与书法及华文文学分析(评论)
庄伟杰 2011-07-19
二 对于中国书法艺术,在许多人的感觉里,可能如印象中的故乡一样,走在路上已渐行渐远,甚至觉得早已成为“已故”的梦乡,尤其是在电脑化时代,更多的从事写作的人甚至已脱离手中之笔。但我庆幸并且欣慰,即便以毛笔为工具的书写在日常和实用领域几乎已濒临绝迹的当下,书法的文化传统依然没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日趋多元的当代社会,书法显然已失去了固有的尊荣而走向边缘,只能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依愚浅见,这恰恰正是书法作为纯粹艺术的时代真正揭开序幕…… 旁白之二:走向书法,走向作为艺术的书法,只有智者,才能把犀利的目光投向远古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发掘与探索中,才会以鲜活灵动的意象凝定于铺开的宣纸,才会以抽象的艺术线条铸造美的造型,然后把那些属于古朴的灵魂和时代的精神气象,氤氲流淌在历史文化的河道中…… 书法犹如人在跳舞。文字,属于人的语言符号;书法,属于人的情感符号。如果说诗歌是生命的旋律,那么书法则是心灵的舞蹈。是故,诗与书,素来都是中国传统文人修心养性的最佳选择。因为,诗歌使人联想飘逸,直指艺术之内核;书法则让人情感清雅,追求平和与高尚。甚而可以说,书法艺术之于人生,无论是益智、健体、审美、养心和博学等都有着无法言喻的妙处。 纵观刘登翰的书法,文意清淳,流利多情;秀丽风雅如南方山水,飘逸自如中尤见法度。在当代诗人、作家和学者群体中,其书法庶几趋近于上乘,如此笔情墨趣,也是其书法一直让不少人心向往之的缘由。在当代文坛,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部分诗人、作家和学者拥有书法艺术的天赋,又以文学底蕴的支撑使书法变得更为丰富和立体。这种从历史深处传达出来的文化声音,是复合性的才艺体现,多重性的精神交响。刘登翰深谙其中三味。从他切入书法艺术的领地加以观照,他似乎注定要走文人化之路,追求一种精致圆融又不乏神采性灵之气,玲珑清隽而不乏清刚爽健之格的风韵。我像读诗一样读他的字,从一撇一捺、一波一磔中去感受书者的心境。其书的苍与稚、立与依、逸与沉、润与枯,皆尽可让人心领意会。这种从心中涌流而出的线痕墨色,显露其真性情,似是能听能品,其文质彬彬的书卷气息也随之在书作中洋溢,这是一种人书合一的人文对应结构。由是可见,那种鼓翼振动式的逸致驱使他拨动了艺术的触须,那种“空梁落燕泥”式的清雅则使他获得了人生的天籁,既潇洒大方,又自然秀雅。 人之性情常常是先天之铸就,又凭后天之积累。一个艺术家总是要从自身出发,并在不断探求和历练中加以修行。然而,文(诗)心绝非一日可以养成,需要一种沉潜和坚守。刘先生深悟到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对一种传统文化的维护。失去了它的传统和源流,即失去了这门艺术。在这种意念的统摄下,他追踪先贤书家的墨迹神韵。二王、苏轼、鲜于枢、文征明诸大家及唐宋元明时代为我们留下的帖学经典固然是他心仪和竭力追摹的,但他只在于性相投契,即一切服从于他心目中与自己追寻的美学范式相关的逻辑。于是,他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作为一个非专业书家,他不仅逐渐形成了独具的书艺风貌,而且做到了丰盈而不杂驳,腾挪而不失序,仿佛是理性的歌声弥漫于他敞开的丰富的精神世界。作为一门艺术,书法内在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意蕴,总是深藏于创作者的心中,而非刻意追求罗列的表层之物。 三 诚如书法也好、诗歌也罢,都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表达,人生也有太多的东西必须加以面对,你别无选择。 旁白之三: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里,刘登翰可谓开国内学术界之先河,而且筚路蓝缕,辛勤耕耘,一路探索一路垦荒一路收获。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扩大华文文学在海内外学术界乃至世界性的影响,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构成,对于人们关注、走近和理解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学者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一进程中的价值作用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一种突破性的贡献和开拓性的意义。 随着全球多元文化的崛起,随着世界各地华人社区的持续发展和中华文化的进一步深入与张扬,也由于华文文学本身蕴含着丰富内容、文化信息和心灵密码,华文文学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青睐和重视已然成为一种事实。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个有益于中华文化重构的重要学科,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推进堪称迅猛异常。然而,伴随华文文学研究空间的渐次推展和深拓,置身于其中的研究者和学术界,却遭遇了一个学科命名、定位、归属以及学科理论构建等诸多问题的尴尬局势。面对开放的华文文学,如何让其自身在生长壮大中获得合理的依据和定位呢?对此,刘登翰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术自审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但既然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仅仅止步于平面‘空间’的展开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必须有自己学科的理论建构,从学科的范畴(内涵、外延)、性质、特征的界定,到反映学科特质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确立,才能开拓学科研究的深度‘空间’,获得学科独具的‘专业性’。对理论的长期忽视———或者说对本学科理论建构的无暇顾及,是窒碍华文文学研究突破和提高的关键。”面对华文文学世界这个巨大而庞杂的空间,随时都有可能需要一个研究者在学术意识与理论建构思路上进行适时调整,方能更好地把握和确定华文文学的存在价值并就关键性问题及时作出积极回应。因而,保持开放而前瞻的意识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在刘登翰看来,无论华侨、华人和华裔的文学,其主要文字媒介是华文,一般情况下称之为华文文学。但华文文学并不能涵括华人和华裔作家用其它语种创作的文学,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华裔的英语文学受到包括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和广泛关注。其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沟通和改造,是不同地域、不同种族和不同历史之间文化融汇的重要现象和亟待深入探讨的新鲜命题,而且随着华人对所在国社会的参与和融入程度日益加深,华人的异语种书写已渐成一种普遍现象。对此,他表示赞同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张超越语种的局限而立足于族性和文化之上的学术主张。同样的,他又以一种高屋建瓴的学术气势,从目前全球化语境影响学科体系的一些新变动来拓展华文文学诗学体系的学术思考空间。近年来他撰写的一系列学术论文,既有宏观的透视,又有微观的剖析,学术视野开阔,内容有的放矢,锐气不减当年,堪称自成一家之言。其中《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形态与运动方式———关于“一体化”和“多中心”的辨识》一文,则从华文文学形态的某种特殊性出发,针对有的学者以“一体化”和“多中心”来建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和思路提出大胆的质疑,这不仅是对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出深入而透彻的思考,也是对处于流动性状态的、跨文化语境的华文文学态势的清醒认识和极大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华文文学诗学体系构建的一个核心问题。 应该说,刘登翰的学术个性,在于他能把宏阔敏捷的文化视野和缜思求实的研究品格加以结合,从而开辟了自己的研究疆域。从他早期率先提出一个必须面对的文学现实,即文学的“分流与整合”的理论阐释所揭示的新世纪中国文学必将从分流走向整合的必然趋势,到他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去考察和研究台湾文学,并在《台湾文学史》一书里得到的集中体现;从他对香港文学、澳门文学的多元构成和大视角的全方位描述和观照,乃至于对东南亚华文文学、海外新移民文学、尤其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性思考和研究,以及对诸多重要现象与问题的审察和清理,等等,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其声音,可以看到他富有创建性的论述,不仅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同样的为当代华文文学世界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富有价值作用的理论导引、实践范式和诗学体系建构模式。 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是人们在谈论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的关系时经常提起的话题。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史,我们可以从许多文学家的身上获得理论上的依据和支持,恕勿赘言。有人这样描述过,作为学者,刘登翰起步于多元的文学创作;作为作家,他又在文学研究的领地找到归宿,从而展示了一代文人的特殊风采。我想,读者诸君只要走近刘登翰,走向他为生活、时代和文学所思考而凝聚及留下的文字结晶与构筑的精神大厦,自然会有“所见略同”之感,并且,可能获得更多的感染和启迪。 (本文原稿较长,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