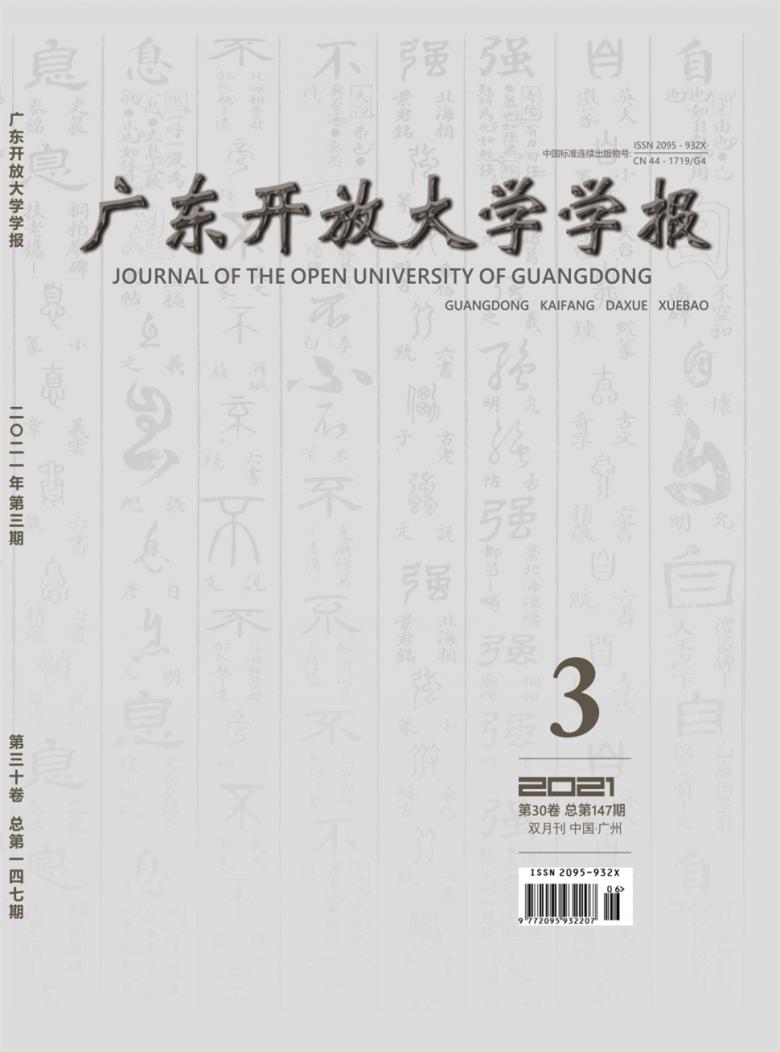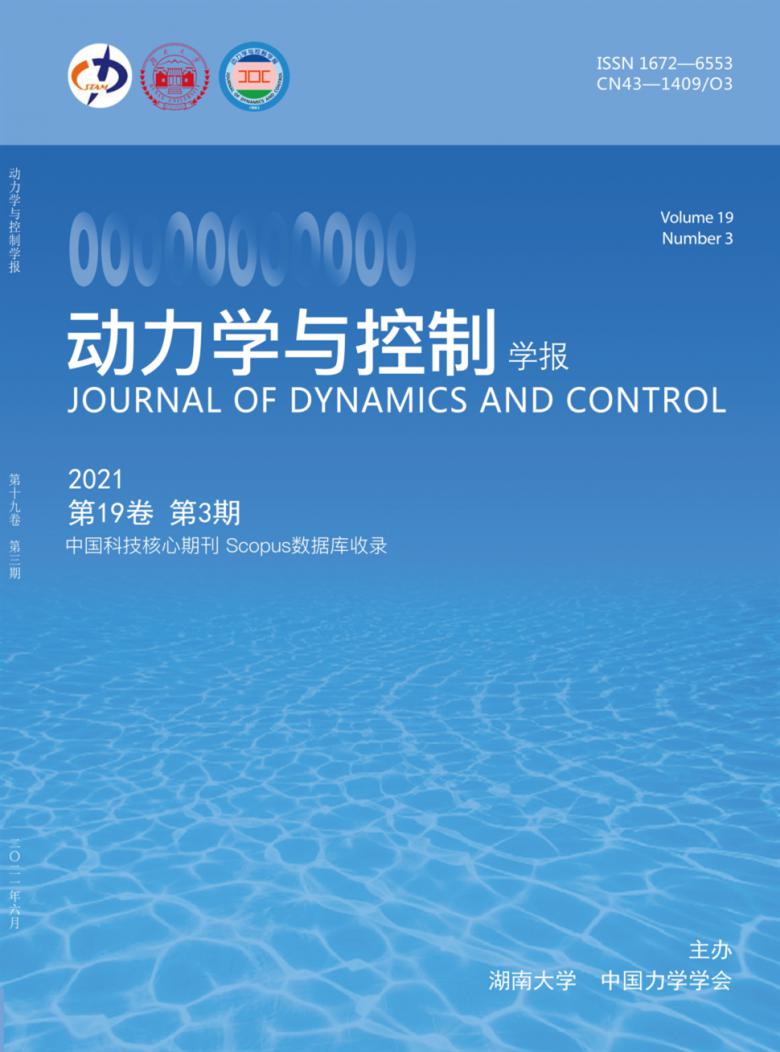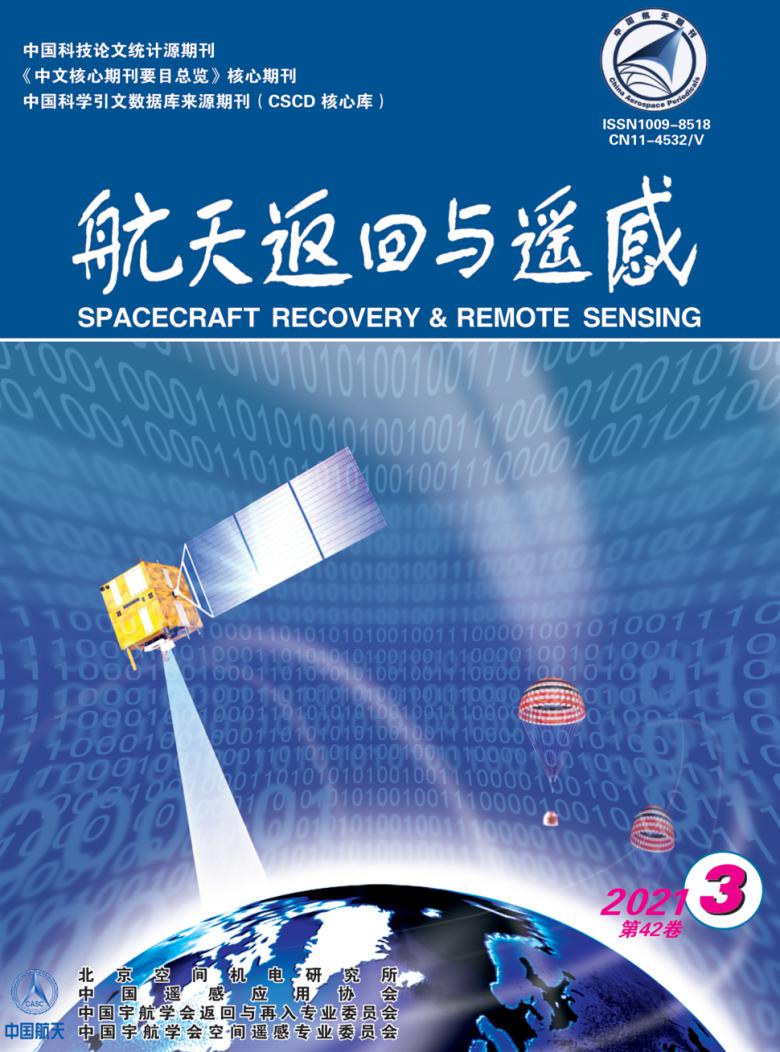关于水粉画《金训华》创作秘闻
佚名 2012-01-11
1969年冬,我与陈逸飞以“逸中”笔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12期上首次发表了水粉画《金训华》。40年来,我们没有向媒体谈过此画创作的过程。不少媒体有关此事的报道,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就连一些中外美术史的研究专著和地方志也有不少错讹。今借《上海滩》一角,将当年的事实真相表述如下,以正视听。 1968年12月起,我被《解放日报》美术编辑洪广文从崇明县前进农场借调到报社,起先是为报社的两幢大楼画毛主席像,接着又画了礼堂、走廊和各楼梯口的领袖像,后来就让我负责每日报纸版面的插图和配画。晚上与陆炳麟等一起值夜班,一旦有新的最高指示发表,就要在—两个小时之内配上一幅主题图,往往要赶画到早上四五点钟。马上制版见报。 我参加了《金训华》组画创作组 1969年9月,《解放日报》记者龚心瀚从黑龙江逊克县兵团采访了金训华事迹回来,写了重点报道。报社领导赵元三极为重视,批示要求各部门配合重点报道。洪广文决定出整版的美术画刊,并与我商量成立创作组,我推荐陈逸飞,因为他是我在少年宫的同学。老洪当即发函邀请陈逸飞、蒋昌一、张嵩祖、秦大虎、丁荣魁与我六人组成创作小组,在报社集中创作。同时,还请工人诗人王森、张鸿喜配写《金训华道路金灿灿》的诗。 龚心瀚几次认真地向大家介绍了金训华的背景资料,讲解金训华奋不顾身抢救国家财产的感人故事。他提供的形象资料,只有一张金训华的正面报名照。老洪要求我们根据这张照片去想象,然后画出六幅画。老洪和我们讨论了几次如何选择画面情节和构思,安排了各人的分工。 最后决定由我画《解放画刊》领头的主题画——《抢救财产》,陈逸飞画《深夜写日记》,蒋昌一画《半夜扣门》,张嵩祖画版画《劳动》,秦大虎画《巡山防火》,丁荣魁画《学习毛选》。各人虽分工明确,但还是要求群策群力,搞好创作。 当年还没有彩印的报纸,所以我们就用黑白两种广告色画黑白水粉画。画都不大,只有25×40厘米左右,使用的是白卡纸。 我与陈逸飞从小就认识了。当年他23岁,我22岁,都是浙江镇海人。我们都觉得,能为党报创作发表作品,机会很难得,所以大家都很谨慎。6个人在汉口路274号二楼一间不到十五平方的房间里画画,虽然拥挤,但有说有笑,非常融洽。 我吸取大家的意见三易画稿 老洪很重视领头主题颐的效果,一直在我边上观察。第二天,我画完了第一稿后,就进行集体讨论。张嵩祖认为我画的金训华抱着木头,给人感觉像落水逃生,而且戴了帽子也不好。于是,我画了第二稿。大家认为这一稿中的金训华在游泳时人太直,看起来洪水显得很浅。后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著名宣传画画家哈琼文见到这两幅草稿,认为第二稿与后来发表的第三稿已非常接近。 两天后,我画出了第三稿,画中的金训华脱了帽子,姿势改成左臂向上,高呼同伴:“跟我来!”集体讨论中,大家对每人的画都提了意见。老洪再三强调:一切为了出效果,分工不分家,领头画是画刊的“报眼”,很重要,要大家都出力,提高画的质量。当时没人在意名利,登报也不登作者名字,更没有稿费,互相改画是常事。老洪希望加强领头主题画的效果,请蒋昌一来帮助我提高。蒋昌一推给陈逸飞来协助,蒋则坐在一边观察,提出不少修改意见。 陈逸飞是我们六个人中画得最好的。此前不久,我还在淮海路上见他画整堵墙的毛主席像。现由他来协助,我非常高兴。逸飞为人谦和,在拿笔修改前,一再问我:“这样改,行不行?”他提出让金训华眉头锁得更紧,嘴张得更大些,伸出的五指改为后三指合并。蒋昌一也提出把湿衣服加深,右边的浪花减弱些,木头减小,推远。就这样,我们互相商量,轮替改着、画着,直到大家满意。讨论陈逸飞画的《写日记》画时,大家认为油灯太亮,会影响同伴睡觉,他就在油灯上加了张穿孔的纸,遮一遮。秦大虎也帮丁荣魁改了画中人的大衣。大家合作得很愉快,没有任何功利心。 四天后,各人的画稿都完成了,由老洪拿去排版、送审。完成了画稿,大家都很高兴。骑自行车回家时,我与逸飞特意到山东路摊头上吃了碗馄饨,还到浙江电影院看了场电影。第二天,画刊见报,我与夜班实习编辑许根荣,一起到评报栏前,看见上面已写了不少对领头主题画的好评,同时见到我的画中多了三条白色水纹线,猜想那一定是老洪连夜加上去的。 “旗手”看中了《金训华》主题画 傍晚,老洪急匆匆找我,说中央首长看了《金训华》主题画,很重视,现在报社领导要与你和陈逸飞谈话。我和逸飞来到总编辑办公室。赵元三总编辑问了画的创作过程,还看了三张变体图,说了句“三易其稿啊”。第二天,市革委会徐景贤、王少庸等找我们谈话。市写作组的朱永嘉还在报社制版房对我与陈逸飞说:你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这幅画受到江青同志(当年被称为“旗手”)的肯定,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今天姚文元已三次来过电话、电报,要3H的彩色反转片送中央的《红旗》杂志发表。但没想到原画只是黑白的。你们不要离开,估计上面还要你们进一步画出彩色稿。 果然,很快上边来了通知,要我们赶画彩色稿。我与陈逸飞一起到上海中华印刷厂,和工厂领导开会讨论,如何把25×40厘米的黑白原稿改成彩色宣传画。此时已是下午两点。 我和逸飞坐着,静静地听大家提的各种方案。因为要放大原黑白画成为彩色画而不走样,两人同时上板画色彩稿又不可能,很有难度。大家一时都很为难。哈琼文很有经验,也极聪明,他提出了当时的最佳方案。他说:先把原画拍照制成版,放大在瑞典进口的水彩画纸上,手工打印成多张有各种层次的淡棕色的画稿,再分别由徐纯中、陈逸飞按原画轮廓上水粉颜色。画完后将这两张彩色稿送到北京,请领导选择、决定发表哪张画稿。哈琼文还说:“不要画太大,对开足够,印刷时可略为放大些。” 傍晚时,才确定下方案。大家都集中在中华印刷厂,连夜赶画稿。很快就请专业师傅手工制版,打印了二十多张不同深浅的棕色画稿,挂在车间的墙上,由我们去选择自己喜欢的棕色稿。然后我和陈逸飞到各自的房间去画,用水粉上色。哈琼文认为这样分别画,可以互不干扰,更好地表现主题和自己的想法。 哈琼文等人足足陪了我们一夜,他不时在我和逸飞的房间里来回地走动,指导我们如何达到出版印刷上的要求。我们整整地画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四点,才完成了上色稿。最后,又请美术编辑陆垒根手写了美术字红色标题:“毛主席的红卫兵——金训华”,附在画后。随即有车将画稿送到市里,再由飞机直送北京。陈逸飞画的上色稿很像油画,色彩丰富。我 上色稿比较忠于原画,只是把画幅拉长了些,人物的头部放到了画面的中央。我对陈逸飞说:“你画得好,上头肯定是要选你的画了。” 谁知第二天,北京送回彩色原稿,并传达了江青的指示:发表徐纯中的上色稿,陈逸飞的画不用。我很惊奇,不知他们是用什么标准来选画的。逸飞不满地轻轻对我说:“这些人到底懂不懂画?”哈琼文轻轻拍了拍陈逸飞的肩表示安慰。接着还传达了上面的指示说,为了宣传好金训华,画作发表时作者不用真名,在我们两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作笔名。我们讨论过用“纯逸”或“纯飞”。后来徐景贤向姚文元电话汇报时,姚传达了江青的话:“我看用‘逸中’吧!”于是《红旗》杂志在刊发这幅画时,署的就是“逸中”笔名。 《红旗》发表了水粉画《金训华》 水粉画《金训华》是发表在当年第12期《红旗》杂志的封底上的。这是《红旗》杂志创办以来首次发表绘画作品。该期杂志上,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说:“作者在三大革命斗争与火热的生活中,努力感受与锻炼,才画出了歌颂英雄的好作品。”文章号召全国艺术工作者向我们学习。不久,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都转载了此画。《金训华》宣传画迅速贴满了全国,前后印制了四千多万张。许多城市还在街口画了大幅《金训华》的宣传画。 《金训华》发表后,对我的画友们很有影响。当时,我的那位在江西插队的师弟陈丹青对我说:他在农村翻了好几座大山,走了几十里路,见山凹凹里的一户农家门上贴了一张金训华的画,就像门神似的。他马上想到我这个大师兄,感到只有坚持画下去,才有出路。 《金训华》一画,被捧为继《毛主席去安源》之后的“样板画”,被印成特种邮票和各种书的封面,也被做成瓷瓶、屏风、刺绣、木刻、玉雕等工艺品,甚至还排了画中造型的朗诵剧。国外不少报刊也转载了这幅画。法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的美术团体还寄来奖状。逸飞与我都被“一夜成名”的浪潮包围了。我们前后参加了多次宣讲团,两人共同作过几十次报告,反复讲述我们受感动和合作的故事。我们都难以理解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只觉得战战兢兢。陈逸飞的爸爸是厚道人,拉着我的手郑重地对我们说:“够了,人爬得越高,跌得越重。” 我拒绝了江青为我改名字 不久,陈逸飞入了党,担任了油雕室负责人和文艺界领导,还被评为标兵。我俩常一起接待外宾,接待过法国共产党书记儒尔盖、印尼领导人等。 我参加了宴会后,还是回崇明农场种地。过了好多年后,逸飞在香港对张正、梁家辉、刘德华等人说:“《金训华》一画对我的一生影响是巨大的。”不久,我被调到国务院文化组。但在讨论我是否当选“四届人大”代表时,很多人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很有意见。我曾说:“江青看过全国很多画,怎么像‘唐伯虎点秋香’似的,居然点中了《金训华》这幅画。”我当时率真幼稚,大概也是从小听了太多苏州评弹,不知深浅吧。 江青曾认为我名字起得不好,要为我改名。我说:我爸起我这名字,意思是“纯粹的中国人”。江青听了不语,过后说:“就这样吧,不改了。” 我调北京一年多,跟国画大师关山月、方增先、杨之光、周思聪、卢沉等人学画国画,也参加“批黑画展”工作。我把要处理掉的大画家作品,一张一张地送还到吴作人、李可染、李苦禅等家中,还拜他们为师。后来给江青、王曼恬知道了,说我与“老朽混在一起”,就把我送回了上海。 由此,逸飞与我有了更多的交往,常常在油雕室(现“新锦江”的地址上)他的小阁楼里听古典音乐,天南地北地畅谈到深夜。他有深厚的艺术修养,精通古典音乐。他说只有哼得出旋律的人,才算懂音乐。他给我解释什么是“赋格”,什么是“卡农”。 我们并没有认为《金训华》一画在艺术上有什么太大的成就,只是时代把画和我们推到了前沿。我们前后画过六张金训华画(三张黑白水粉,两张彩色水粉画,一张油画),没拿过一分钱的稿费。我们觉得从小下功夫学画画,今日能得到社会肯定,就是自己最大的满足了。 不久,中国历史博物馆通知我们画一张大幅油画《金训华》,作为博物馆收藏品。陈逸飞认为这是纠正以前画的不够好的机会来了,要“扳”回艺术上的“印象分”。他鼓励我说,一定要画出真正的水平。我们从图书馆、美协借了不少俄国画家艾瓦尔素夫斯基的海浪画来做参考,并以我作姿势参考拍照。陈逸飞信心很足,说这次要完成“为内行人都称赞”的作品。 在油雕室画这幅油画的过程中,俞云阶、王大进、张隆基、魏景山、邱瑞敏、夏葆元、秦大虎都给我们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画好后,送北京历史博物馆收藏至今。 “贫下中农”始于何时 “贫下中农”一词,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可谓家喻户晓,它表明一个人的“阶级成分”,该词最早始于何时呢? 1957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这里谈一个社员成分问题。我以为在目前一两年内,在一切合作社还在开始推广或者推广不久的地区,即日前的大多数地区,应当是:(1)贫农,(2)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3)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首先组织起来。”这是在党的重要文献中首次出现“下中农”这个“阶级成分”。1955年9月7日,《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员团员和贫农下中农》文件发布后,“贫下中农”一词在各新闻媒体频繁出现,“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