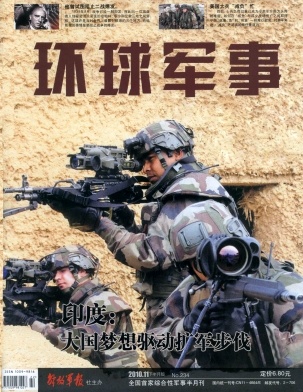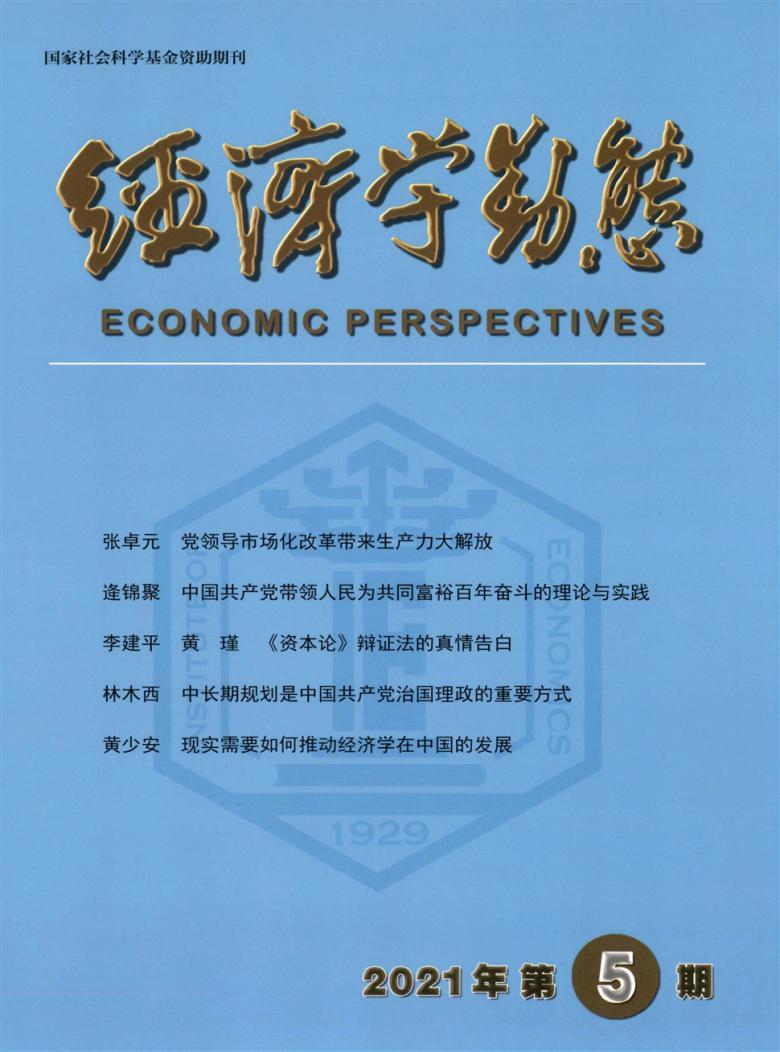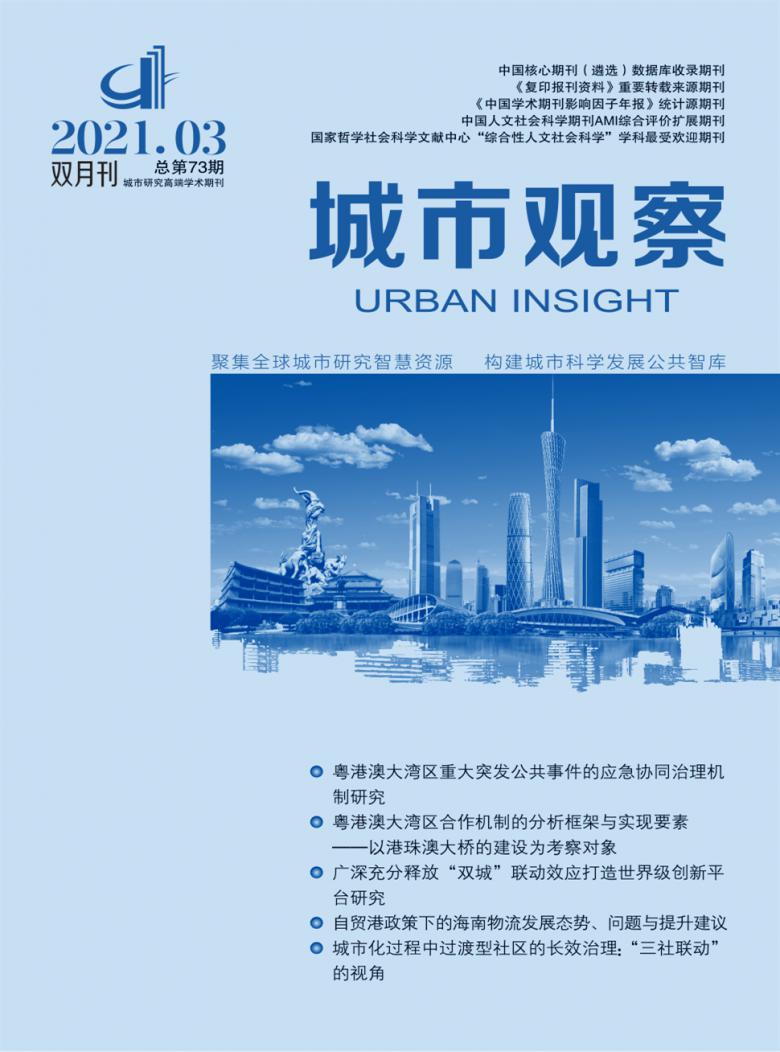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
刘保昌 2008-02-28
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在中外文学史上早就有人运用,而作为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却是人类文化史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它发端于18世纪末的西欧,在西欧各国流行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又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它地方。而作为文学观念形态上的现代浪漫主义,则是二者的融合。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一方面,浪漫主义诗学对自由的张扬、对个体的关注、对自然的归依、对异化的敌视等与道家诗学发生着遥远的呼应;另一方面,现代浪漫主义坚决反对“不撄人心”,它在个体与社众之间所保持的紧张战斗姿态与决绝反叛精神尤其是主体的焦灼感又完全不符合道家主张。
(一)
鲁迅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与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都有密切关联,他既以面向西方思潮大幅度的开放姿态出现,又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现实与时代需求,显示出世纪初一代文化巨子面对现代世界文化时的从容宽阔心胸及其从本土现实出发的积极建构心态。现代化与民族化是鲁迅构建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双重方向。代表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的论著计有《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等等。
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的核心表述是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就显示出鲁迅作为文化巨子的对于前辈学人的飞跃式超越精神与整体性推动浪漫主义建构步履的功勋。
鲁迅在“物质”与“灵明”的冲突中坚守“灵明”;在“个人”与“众数”之间选择“个人”,这就超越了“短视”型的现实功利价值,而立意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强盛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建构浪漫主义诗学时对道家文化的借鉴途径,其一是老庄的反异化精神;其二是道家文化的“物物而不物于物”的主体自由诉求。二者都着眼于“物”与“我”的关系。
鲁迅对社会、科技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物”对“人”的压抑、物质文明对主体精神的挤压、美感的丧失、人的灵性的失落、道德的堕落等时时抱有警怵之心。这种浪漫主义思想主张就与道家文化中的反异化思想资源极为契近。《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既讲人与天一,同时又讲人与天两不相胜。人与天不相胜而相合,这是道家的“自然”“道”、“以天合天”观。而整部西方近现代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则是“将人看作自然界的全部和最高本质”,“把整个自然界看作人的生成过程”,认为人本主义才是真正彻底的自然主义。这就将主体的地位超擢在主宰层面,“人”不仅为自然立法,也应该为“万物”立法。历史实践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论点的虚妄,人类业已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而道家视域中的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却与此大相径庭,天大、地大、人大,天地并不大于人,人也不大于天地。天道自然,人道无为,道家反对以人灭天,以故灭命,这并不是要取消人的意志和欲望,恰恰是从当时社会、时代的“大有作为”的“战争”中发现了人为力量对人自身所造成的祸害与痛苦而得出的结论。道家独特的“物我”观也在全球生态日趋恶化的当下,重新受到了重视。
鲁迅追求理想的人性,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既对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批判起来不遗余力,又对道家文化中的“不撄人心”深为不满。他主张通过无功利性的审美达成人性的完整,最终实现文学的大功利。由此,他超越了康德的超功利、无利害观念,认为创作者只有在无先在动机、无先设情绪以后,才能在审美直观中实现自我与世界的融通为一,才能在“万物与我为一”之中达成精神的怡悦。在他看来,尼采的疯狂执迷的生命过程,本身就是一首富于起落回旋感的诗。“去除成见”、“物我为一”,以“赤子”之心投身创造,“随物赋形”、“自由自为”,等等,这些浪漫主义诗学主张属于典型的道家文化系统。
道家美学中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与庄子的“无用之用”观念,都诉求于主体的精神自由,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自然而然”、“天马行空”的美学精神不仅成就了鲁迅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同时也是鲁迅浪漫主义诗学的核心。
鲁迅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带有鲜明的道家文化特征,而明显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从博克到康德,从黑格尔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无不认为主体受到了外在异己力量的残害,因此,在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过程中,往往伴随有恐怖、痛感与神秘惊悸的成份在内。而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中并不包含这种惊悸恐怖成份,看不到恐怖和神秘的宗教意味。在《破恶声论》中他反而认为中国“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中国人之所崇拜者,不在无形而在实体,不在一宰而在百昌”,可见他对中国道家文化一脉中浓厚的泛神论主张在总体上是予以肯定的,对“顾瞻百昌、审谛万物,若无不有灵觉妙义”的泛神主义艺术亦是肯定、赞扬的。
中国古典浪漫主义从“自然而然”的道家(尤其是庄子)到注重个性自由、主张感官享受的明季市民浪漫潮流,再到近代人文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都用意于打破等级森严的社会壁垒,在平凡人生中寻找生存的快乐与满足,追求个人的解放与精神的飞腾自由。其中,庄子的泛神论对浪漫主义美学影响深远,它以自身雄奇奔放、绚丽无羁的艺术风格标示出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黑格尔认为道家文化中的泛神主义艺术“强调的是在一切现象里观照太一实体和抛舍主体自我。主体通过抛舍自我,意识就伸展得最广阔”,个人“消融在一切高尚优美的事物中”,“诗人……忘却了他的自我,同时也体会到神性内在于他自己的被解放和扩张的内心世界;这就在他心里产生了东方人所特有的那种心情开朗,那种自由幸福,那种魂游大悦”。这就从艺术发生学角度强调了道家泛神主义的创造性功能,其核心就是“物我交融”。
鲁迅的浪漫主义文学观虽然也包含了个体与自然、宇宙、社会的交融交汇特征,但他与古典形态的泛神论(以道家文化为代表)的区别也十分明显,因为老庄一脉哲学思想的总体特征是“静态”地“消极性”地融入自然、宇宙、社会之中,而鲁迅则是以强调个性、主体情感的飞扬为基础,最终达成主客体的统一。这种区别既预设了鲁迅以后的向现实斗争层面的“转向”,也注定了鲁迅终究要走出道家式浪漫主义的必然命运。
(二)
创造社作为20世纪2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性社团,其创作的典型特征便是主情主义。我认为这种主情主义写作的根源可以一直上溯到晚明性灵心学、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直至先秦诸子中的老庄一脉。从精神价值取向而言,张扬个性旗帜,尊崇感性人生,敢于歌哭笑骂,对于自己的真实感受不加丝毫掩饰,这种新鲜活泼的生存方式的确令深受儒学规范束缚的奉“奴隶性人格”为处世圭臬的传统中国人瞠目结舌。即使到了思想空前解放、西学观念汹涌而入的20年代,创造社的离经叛道仍然为当时的主流社会、群体以异眼视之。创造社正是从这一文统中吸取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从而为己所用,刮起了“狂飙”式的性灵文学的风暴。
就浪漫主义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广度、在读者社群中产生的轰动指数而言,毫无疑问,创造社诸子的创作达到了成功的巅峰;而如果从文学史角度来评价其影响的深度及其艺术造诣所达到的高度而言,三四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则超过了20年代的创造社。如果说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是一种富有反抗精神的“狂飙突进”式的浪漫主义的话,那么,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写作则是一种“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而后者更加贴近于“效果史”意义上的道家文化,因为其体现的是道家式的“静”态的欣赏与玩味。
郁达夫曾说:“自己大约因为从小的教养和成人以后的习惯的关系,所嗜读的,多是些静如水似的遁世文学。现在佗傺无聊,明知道时势已经改变,非活动不足以图存,这一种嗜好应该克服扬弃了,但一到书室,拿起来读的,总仍旧是二十年前曾经麻醉过我的,那些毫无实用的书。”从《沉沦》的惊世骇俗到《迟桂花》的“向往闲静”,郁达夫成功地在浪漫主义文学领地实现了从激情冲动到田园慢歌的战略转移,而田园牧歌与有节制的感伤、去欲后的冲淡、平静的抒情写意,共同构成了三四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主流。
事实上,早在20年代就有废名在抗争呐喊型的创造社式的浪漫主义写作之外另辟了一方“世外桃源”,他把古老的农村当作理想中的伊甸园,以怡然自适的心态导引读者认同与欣赏原始、朴讷、静谧、封闭的乡村文明,从而在文学史家那里获得了“素雅的浪漫主义者”的称誉。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在30年代,经由沈从文达到了艺术美的巅峰,其中“固然融汇着哈代、艾略特、莫泊桑、契诃夫等‘多而杂’的外国文学韵味,但它的基本格调却植根在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和陶渊明型的传统文化积淀的沃土里”。或者可以说,在废名、沈从文所受“综合性”影响中,道家文化充当了他们会解中西诗学时博兰霓在《知识论》中所说的“支援意识”的重要支柱。如废名在其自传体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就反对、质疑现代知识界流行的进化论:“什么叫做进化呢?你们为什么不从道德说话而从耳目见闻呢?你们敢说你们的道德高于孔夫子吗?高于释迦吗?如果道德不足算,要夸耳目见闻,要夸知识,须知世界的大乱便根源于此了,知识只不过使得杀人的武器更加厉害而已。进化论是现代战争之源,而世人不知。”这种论述,不惟不难从道家经典中寻绎出其思想来源,就是废名所使用的“道”、“知”等二元对立的概念亦是道家经典中的常用词语。反进化论的思想与飞扬的浪漫主义格格不入,这也是废名的创作有别于早期创造社小说的重要原因。在反对过分“知识”化以及由过分的“知”导致的“智诈”等方面,废名与老庄选择了相同的阐释路径。这就决定了废名小说的平淡的诗意、寂静的浪漫主义的美学特征。
(三)
徐言于小说《鬼恋》中的“女鬼”;《风萧萧》里的白苹、海伦、梅瀛子;《吉卜赛的诱惑》中的潘蕊和罗拉;《阿拉伯海的女神》里的女巫;《荒谬的英法海峡》中的培因斯;《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里的海兰与白蒂等等,这些女主人公莫不在外表上“楚楚动人”、气质高雅;在内在修养上拥有渊博的知识、别致的谈吐,而且具有西洋社会女子的现代平等意识,敢于大胆地追求爱情,敢于为了幸福的生活搏击人生。而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则多为才子、作家、哲学家,经常处于被多个优秀女性所“围剿”的地位,在人物结构上属于“一男多女”、“众星捧月”模式。他们在性格结构上往往不如女主人公大胆、明朗,大多具有道家式的退缩“出世”人格,而缺乏进取、顽强、拚搏的“入世”精神。
在《吉卜赛的诱惑》中,徐言于提出了解决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方法———回归自然,这种思路属于典型的道家。潘蕊从声色犬马的马赛投入蓝天白云下的平静的南美洲的怀抱,并从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安稳所带来的幸福与自由,这在某种意义上不正是对道家“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的认同与遥远的呼应?在老庄经典中,天、地、自然等与“道”一起,都是人类的存在家园,这种存在家园既是肉身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精神层面上的。徐言于的《荒谬的英法海峡》也描写了一处世外桃源,即海盗所居住的化外之地: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没有官僚阶级;没有商品、货币;食物是各取所需;劳动是完全尽义务型的;每周休息三天;首领由全民选举,随时可以更换。桃源梦想,古今中外都存在。道家经典中描述的“往古之世”也是桃源世界:“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这正是人类厌倦了战乱频仍、过度智诈所造成的恶果之后的梦想。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40年代的抗日战争大背景使得一切“隐私性”、“个人性”都带上了罪恶的纸冠,在全民抗战的口号下,个人必须牺牲“隐私性”以“顺应”时代主潮。因此,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性本质就受到了主流价值的深刻质疑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声批判,无名氏就不得不为他小说人物的个人化选择———“出家”、“隐遁”作这样的自我辩解:“对于抗战,过去五、六年,我也总算尽过一点个人责任了。看世界大局,盟军胜利,已是决定性的了。我为我的隐遁,感到歉疚。然而,像我这样的畸人畸行,世间极少,我的生灭,对社会只是沧海一粟。尽管如此,我仍为我的扮演闲云野鹤表示遗憾。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万事万物,不能完全按道义的钢模子去浇铸,例外的怪事总免不了的。”虽然已经感受到了“道义的钢模子”的“浇铸”伟力对大时代下个体的无情威压,但无名氏还是为自己的“畸人畸行”寻找到了一个存在的理由———“例外的怪事总免不了的”,从而表达了对个体多样性的尊重与对“畸人畸行”的理解。
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魏晋时代多有对“脱俗之士”的赞誉,多有对“落拓不羁”人格的标举,当时的名士多以对礼法的悖违互相标榜,以至于“王猛扪虱”、“坦腹东床”传为佳话,究其根源仍在于先秦道家。《庄子·人间世》、《庄子·德充符》、《庄子·齐物论》中就多有对畸人畸行的推崇。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容忍伟大的畸人畸行,只有伟大的思想才能欣赏与主流价值冲突剧烈的畸情畸思。在美学形态上,那已不再是秀美,而是崇高!
(四)
以个人抒情小说与田园抒情小说来划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小说类型是大体合理的,但我不同意“个人抒情小说与西方浪漫主义关系比较密切”、“田园抒情小说是传统自然审美观念的产物”的观点。应该说,处于历史长河下游的具有巨大开阔胸怀的现代文学巨子们,综合性地吸收人类已有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在他们身上并不存在单向度的文化择取路径。如果说“个人抒情小说”与“卢梭的孤独”、“维特的感伤”、“拜伦的反叛”存在着密切关联尚可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到证据的话,那么,将“华滋华斯、雪莱等人对大自然和爱情的咏叹”视为“个人抒情小说”的特点并与“田园抒情小说”由此作出划分则显然是不太恰当的。无论是个人抒情小说(文学),还是田园抒情小说(文学),都是在本土传统文化视域下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创造性择取。这种本土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精神主体就是以庄子为代表的艺术精神与美学思想。
郭沫若推崇歌德、雪莱的理论基础是“自然”,诗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这显然并非歌德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全部,而只是歌德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之中的一部分,也正是郭沫若所愿意接受、发挥的“一部分”!其基础正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老庄道家。
对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歌德,在1827-1829年间提出了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成熟的思想。他首先注意到的是中西民族在思想与情感方面的相似之处,强调了人类世界中不同种族、人群的可沟通、可理解性。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持欣赏的态度,特别是对作品的民族特点和写作技巧更表示出作为“同行者”的理解与赞美。他在《〈百美新咏〉中的中国材料》一文中说,在中国作品中,“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房屋内部和中国画一样整洁雅致。例如‘我听到美妙的姑娘们在笑,等我见到她们时,她们正躺在藤椅上’,这就是一个顶美妙的情景。藤椅令人想到极轻极雅。故事里穿插着无数的典故,援用起来很像格言,例如说有一个姑娘脚步轻盈,站在一朵花上,花也没有损伤……”这种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中国文学的欣赏,其实就是对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流溢出来的道家情趣的沉醉与流连。
但歌德的中国文化观中本身包含着很大一部分“道德理性”因素,或者说,他对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德传统同样表示钦佩。他依据他所读到的中国传奇《好逑传》断言,在中国人那里,一切都比西方“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举中国小说中常见的描写为例:“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显然,他对由于这种“严格的节制”所产生的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缺乏认识,而这一点,正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所极力批判的。对于歌德的“道德理性”的那一部分,郭沫若是捐弃不取的。可见,他所接受、理解的歌德是“道家”式的,以追求“自然”为矢的的歌德。或者,我们可以说,郭沫若选择歌德的富含“道家”内容的那一部分加以接受,其“先设”知识基础正是他对庄子文化的喜爱。
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家们对卢梭的接受与阐释过程之中。如果说歌德在人格风范上尚带有几分魏玛王国臣民的奴气的话,那么,卢梭在反对“文明”、“体制”方面则毫无疑问地走得更远,并因其激烈地攻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体制而更容易引起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作家的精神共鸣。卢梭的早期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以“自然”对抗“文明”,进而否定“文明”。自然是美好的,出自自然的人才是生来自由平等、道德高尚的,文明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相反只带来了道德的堕落和风俗的败坏。因此,科学和艺术是与人民相矛盾的。唯有平民“纯朴的灵魂”才具有深挚的情感和高尚的道德,人类应该以自然的美好来清除“文明”的罪恶。他在论文中批判了中国文化中的儒家传统,批判了“文化的过度发达”所造成的主体脆弱,精致的“文”化让帝国丧失了“反抗”的冲动与实力。与此相对应,卢梭对那些“前文明”时代的野蛮、蒙昧、贫穷的民族寄予厚望。在卢梭笔下,发达的中华儒家文化是作为野蛮民族文化的对应物存在的,其间的价值判断非常明显。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接受了卢梭的与老庄一脉思想贴近的“返朴归真”思想。卢梭的返归自然的思想,在他的教育学著作《爱弥儿》及小说《新爱洛绮丝》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述。卢梭开始接触老子是以狄德罗为中介的,他把老子写成Rossi,他的返朴归真思想明显受到过老庄道家的影响。庄子的自然观建立在宇宙论之上,体现的是人的生命精神与宇宙精神的交流化合。这种自然观虽然想要解决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解决宇宙秩序与道德秩序的悖乱,但总体上仍是一种主观的心灵省悟,是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中构筑自己所憧憬的自由的精神家园。而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黑格尔在论述浪漫型艺术的真正内涵时说:“浪漫型艺术的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相应的形式是精神的主体性,亦即主体对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认识。”为了保留主体心灵的精神家园不被现实侵蚀、毁灭;为了保持事物的自然本性,反对人为的异化,老庄愿意以牺牲常人眼中的富贵权势作为代价。《庄子·让王》中说:“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功名、利禄,而以劳心损形为代价,在庄子看来不啻于“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是“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
卢梭与老庄在反对异化、追崇自然方面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我们越积累新的知识,便越失掉获得最重要知识的途径。”与原始人安宁自由的生活相比较,近代社会的人类生活令人不忍目睹耳闻:“社会中的公民则终日勤劳,而且他们往往为了寻求更加勤劳的工作而不断地流汗、奔波和焦虑。他们一直劳苦到死,甚至有时宁愿去冒死的危险,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或者舍弃生命以求永生。”如此的“进步”,完全得不偿失,背弃了幸福的本义。
也正是在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幸福的达成方面,正是在对近代资本主义发达物质文明的批判方面,卢梭思想被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并予以了高度评价:“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否定的否定。”这就是说,恩格斯已经注意到了卢梭否定文明、返朴归真的批判性意义及其寻找更高级文明形态以救偏补缺的精神性努力的可贵价值。在批判性、思辨性层面上存在着相似性的卢梭与老庄思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分道扬镳:卢梭对“未来”显然充满信心;老庄却只是怀持循环史观,看不到温暖的光明,他们永远在“眺望故乡,咀嚼旧梦”。
如何解决人为物役的主体异化?如何安妥个体的巨大心灵孤独?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给出的答案是回归自然。这显然是一种东方化色彩十分强烈的答案。因为西方文化的主体精神是“有为”。作为西方文化主体精神的典型形象的浮士德就将《新约》中的一句话译为“太初有为”,“投身到时间的洪涛之中,投身到世事的无常之中!不管安逸和痛苦,不管厌烦和成功,怎样互相循环交替,大丈夫唯有活动不息”(《浮士德》)。“活动不息”的征服精神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随处可见,如阿耳戈的英雄们历尽艰难杀死毒龙去寻获金羊毛;在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厄》中主人公在颠沛流离中被女神导引去寻找“金枝”,等等。在这种征服活动中,主体一旦从自然中分离,一旦将自然视为对象性存在,人就会体验和意识到孤独的可怕,随之展开的主体心理矛盾便愈演愈烈,而老庄的道家思想已经解决了人类的这一心理矛盾。解决的途径便是道家的回返自然、清净无为,回到“道”的怀抱,回到自然之中去。在哲学思辨的层面上,老庄文化显然更为成熟深刻。
当然,由于中西历史、经济、文化、社会背景的迥异,浪漫主义文学所反对、批判的对象也不尽相同。中国本土的现代浪漫主义更多的是对封建体制、人性压抑、经济不发达、政治不开明、人身不自由等“异化”现象的批判,带有鲜明的时代性、本土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