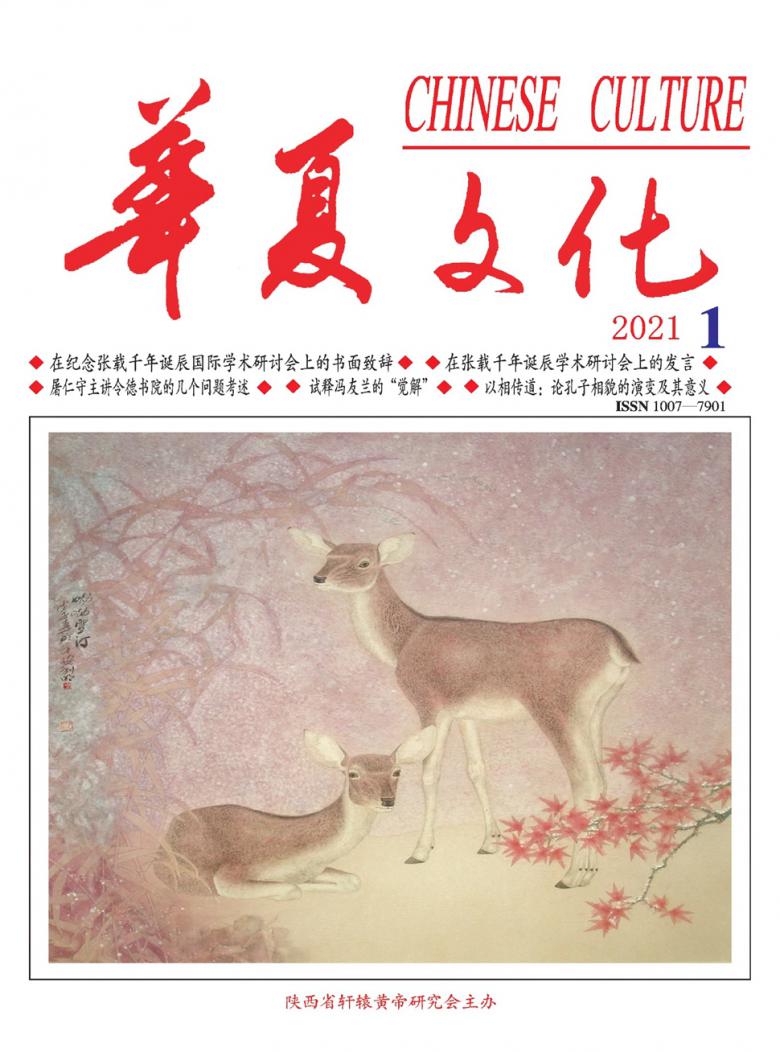沈从文·浪漫主义·生态批评
覃新菊 2008-07-23
笔者曾从心态的角度解读了沈从文自我标榜的“最后一个浪漫派”所蕴涵的美学特征以及这一心态与创作生态景观之间的关联①。余尤未尽,本文想进一步从浪漫主义思潮演变史的角度再来看看沈从文关于“最后一个浪漫派”的美学意义,以及浪漫主义与大自然,与生态之间的关联。
一、浪漫主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运演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端的五四“文学革命”,被公认为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由于中国现代化启蒙的需要,也由于现实斗争功利性的束缚,再加上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积淀,在实行“拿来主义”,“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开放氛围之中,现实主义是倍受青睐,一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主潮,他们对浪漫主义不以为然,认为浪漫派惯于用冥想意绘的种种不确切的方法,作心灵的幻想与逍遥,不敢面对现实,其共同倾向是“浪漫主义对客观现实的拒绝”(霍依德)。尽管如此,依然抵挡不了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现代世界性的文学潮流对中国文坛的诱人呼唤,首先在五四这个大变革、大动荡、大冲撞的浪漫时代中神采飞扬,大放光彩。第一阶段,以郭沫若的《女神》与郁达夫的《沉沦》为代表,树立起了浪漫主义在中国运演的两种不同的范式,刘增杰教授将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文化特征概括为“自尊与自卑的共存”、“真诚与伪饰的交织”、“清醒与迷茫的渗透”②。可能是反抗封建的精神过于急切而缺少一种从容自如的气度,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的印记,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具有相当的悬殊,在文艺表现上,则是极端的崇尚主观,极端的张扬主观自我,而放逐了一切形式规范,蔑视任何艺术技巧。因此,回观五四初期的浪漫主义思潮,可以说,影响很大,影响也很坏。陈国恩教授打了个形象的比方③,说这好像一个人长期受到束缚,一朝获得自由,因缺乏思想准备和适应过程,反而会行动过火,举止失措。
浪漫主义这一“醉舟”(诺思普·弗莱)在语言文学的海洋里风雨飘摇,忽起忽落。1925年的“五卅”使浪漫主义思潮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分化趋向:最主流的是寻找联盟,与革命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成为最有“中国特色”也最具有时代特色的“革命浪漫主义”;另一类则主动退守边缘,对种种苦难采取“看淡”了的姿态,用一种达观宽容的心态面对现实人生,重在对人类远景的凝眸,如沈从文、废名;或干脆扭回头,闭了眼,在幻想和朦胧中寻求情感的寄托与艺术的独立,像新月派徐志摩。这是浪漫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时期的浪漫主义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重在自然的抒写、心灵的解放、艺术的纯美方面达到了共鸣,对五四那种天马行空式的浪漫主义起到了纠偏的效用,成为中国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可见中国文艺理论界在接受西方浪漫主义概念上可分为两个时期,界分点约在1930年左右。之前所接受的是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之后则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了。④郭沫若与沈从文就分别代表这两类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不同命运。政治学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比较代表“中国特色”,也是因为时代与国情使然,自然的,沈从文所赖以生存的美学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控中处境唯艰,当边缘也被主流疯狂的侵占,不复存在之时,这种形态的浪漫主义只能归于寂灭。难怪到四十年代战火纷飞的时局下,沈从文感叹到自己是“最后一个浪漫派”,他是洞察到了美学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在主流话语的冲击下必然销声匿迹的命运。浪漫主义在三四十年代的衰落,主要是因为:1. 现实主义“惟我独尊”以及“左”的文学思潮的纷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本来是一对既存在着差异和对立,又互相渗透和补充的“孪生姊妹”,结果在“左”的文学思潮的纷扰之下,不仅割断了之间的天然联系,而且把浪漫主义放到了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位置上而加以全盘否定,或者巧妙地整合到现实主义的屋檐下,降格为一种创作方法而存在着。2. 时代的冷淡。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对于刚刚从“铁屋子”里苏醒过来的人们来说,宇外来风正好与国内的大骚动相契合,使五四成为一个浪漫的时代,“西方的个性主义与传统的名士风流在浪漫主义作家身上得到融汇的结果,就构建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深层文化结构”⑤,这是一种十分独特、又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的文化模式,到三四十年代战火纷飞的时局下,浪漫主义被现实主义所整合,抒情被放逐,“轰炸”炸死了许多人,也炸死了抒情。在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处于最残酷、最激烈的年代,作者和读者选择的,往往是短兵相接的利器,他们关注眼前的胜利,期待文学给他们提供战斗的宣传器械,而无暇聆听个人私语的心灵感伤。文学思潮的起伏涨落,有着历史时代的严格选择。
在当时如火如荼的年代里,浪漫主义被整合在现实主义的麾下,自身也迫不及待的转向政治,以它包罗万象的胸怀,由“赋予诗以生命力和社会精神”向“赋予生命和社会以诗的性质”了,如此一来,生活与艺术的界限悄然打破。现代中国的浪漫派作家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即从审美的非功利实现向审美政治化的转化,耐人寻味的是浪漫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结合,产生“革命的浪漫谛克”,这一“浪漫”结合应该是现实的促动,可是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强大的社会能量简直就像一股滔天洪流,把个本来就势单力薄、缺陷十足的美学意义上的个体心灵解放冲刷得荡然无存。在以后的新中国建立的“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之中继续任凭这股“革命浪漫主义”泛滥,浪漫主义扭曲了,变形了,社会疯狂了,荒诞了。80年代后,痛定思痛,浪漫主义又才和着血泪的感悟“回来”了。陈国恩总结道:“这不是天马行空的浪漫主义,也不是怡然自得的浪漫主义,而是承担着历史重负的铭心刻骨的浪漫主义”⑥,成为“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的喊叫”(郭沫若),这可以称得上是浪漫主义在中国运演的第三个阶段。
综观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演变,可以肯定地认为,它不是中国古典式的浪漫主义在现代的承续,古典式的浪漫主义主要以艺术形态上的瑰丽奇谲为主要特征而没能触及到人的自由、个性解放的清醒认识和不懈追求,因此我们坚持认为它是世界性的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回响。艰难曲折,难以纯粹自立,三个阶段犹如少年的狂歌、青年的忧郁、中年的沧桑,是各有魅力,也各有缺失。然后,到90年代,以其情感的深化与深层挖掘而滑向现代主义,整体性的被现代主义所收容,结束了它作为思潮的历史使命。我觉得,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是志趣相投的渗透与融合,比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结合,还有特定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要健康得多,有文化底蕴得多。
二、沈从文与“最后一个浪漫派”
一种潮流,一种气候,作为个体的人要抵挡是极其艰难的,不为时风所动的品格又有几人能够做到?跟住时风,这是大多数文人的一种心态。沈从文自称是30年代“最后一个浪漫派”,就是决心在这股洪流面前,以一个保守主义的姿态立意摆脱“这一个现代社会”,这种精神的逃离与后退,对当时疯狂“拿来”,急切跟上西方现代化的国人心里,不亚于是“唱反调”,被视为历史逆流而打入冷宫。人们将政治与美学混为一谈,并且直接用政治取代了美学。他不会对一些时事性的东西过于冷漠,他在政治化的浪漫洪流中有过质疑、顾盼与迷惑,但这一切构不成他思维的核心,他关注的始终是人类和生存的最大奥秘,这是其文本一代又一代持续不断的延续、积淀成经典的接力。
他选择了一种与五四迥然不同的浪漫叙事。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基本是把西方的形形色色的思潮、主义统统“拿来”以镜鉴,与陈旧的、落后的传统文化抗衡,结果导致情绪化的反对传统,正如泼洗脚水,把盆里的婴儿也泼掉了。虽然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试图“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中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借以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郑振铎)⑦ 。但呼声在那个不纯正的火热的年代是那样的难以落实,而且本身走向病态。沈从文针对此种现象,由衷的走向了传统——“乡土抒情”,不是还原传统,更多的是对传统作诗意解释。从他混合着多种感情的自述中,我们可以隐约辨别得出他的写作意向——“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我的妄想在生活中就见得与社会隔阂,在写作上自然更容易与社会需要脱节”(《水云》)。一方是坚守,一方是质疑,主体的矛盾心理——源于主观的执着与现实强大的解构——使得他也只是荣获瞬间的美丽而没能坚持到最后。
远离尘嚣与现代文明的烦扰,向着心中的神与诗意挺进,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主观意图所在,而在客观上,却让人产生“逃离”与“落伍”的印象。孤独的拼杀,奋力的突围,没有阵营,没有同盟,个体性的“独家经营”着浪漫、乡土、田园、抒情的世界,自然的,难以与常态规范相融合,时间久了,能量也为之耗尽。因此在他功成名就、新婚燕尔之际,他要“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因为“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朽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而写下《边城》之后,痛快的说“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水云》)这“最后一个浪漫派”便在《边城》里最后尽情的浪漫了一次,也便喑哑了牧歌歌喉。
云南几年创作的所谓哲理散文或曰心迹散文,分明表迹着一个步入绝境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心境:“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面前反而消灭”(《七色魇》)。诗的想象与情感的浪漫在现实中找不到原型,找不到!浪漫主义应该“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不仅是一种精神寄寓,更是一种人生追求”⑧ 。沈从文在对事物形态的特征与主观自我的情感特征两者之间试做糅合处理时,在“求差”与“求同”的权衡之中丧失了分寸与尺度,只是在小心翼翼的维护着一块方寸之地,让精神之树在夜色里成长,这让他如何做精神的飞翔?一个步入绝境的创作心理只有依靠这种隐蔽才能生存下来,他不是使自己的面目清晰显露,而是尽力使之模糊含混。当作家失去了可供耕作的土地的时候,唯一顽强的维护方式就是退守心灵一隅,以心灵的解剖掩盖外事的纷杂,在心灵殿园里保存和延长它那纷乱着的、敏感着的、鲜活着的感应。而文学向来就以传递心灵的感动为己任,他把那一刻,那一瞬中的震颤用文字固定下来以后,我们今天的读者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怦怦心跳,那份微微脉动。
他之所以感叹自己是“最后一个浪漫派”,他是洞察到了美学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在主流话语的冲击下必然销声匿迹的命运,炮火也提醒着告诉他,这是“神”之解体的时代,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之路上,是“后不见来者”的了。虽然他曾不无庄严的宣称要“保留神性在人间”,可终究寡不敌众,连这“最后一个浪漫派”自己都难以为继,没能坚持到“最后”。想当初,在两种浪漫主义交相更替、此涨彼消的相持阶段,他是继废名之后成为影响最大的具有田园风味的浪漫主义者,这既不是五四时期如郭沫若式的狂歌与傲视,也不是如郁达夫式的沉沦与感伤,更与四十年代弥漫文坛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区别开来,为此,他成为了中国国土上比较纯正的浪漫主义作家。
之所以说他是中国国土上比较纯正的浪漫主义作家,那是将他与西方比较纯正的浪漫主义作家如卢梭、歌德、雨果、华兹华斯等相比较而言的,西方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认为回归自然环境与回归人的自然天性,是人类健康生存的必需,从而提倡物质生活的简单化、物质需要的有限化和精神生活的无限丰富化。凌宇曾问过沈从文是否接受过卢梭的影响,沈从文肯定的回答“没有”,说他不曾读过卢梭的书⑨,他是从神秘奇丽的湘西这块乡土上吸取的精神营养,沈从文与“湘西”这一对概念的组合,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作家与地域文化联系的模式,而是作为一种独特的价值选择—— 一种边缘性的文化价值选择而存在,体现了沈从文在五四思潮的基础上开辟了“另一种”现代性:五四奠定了以进步为指向的社会文化发展图式和将西方文化作为还魂草的现代性,而沈从文始终以自然观照生命,是从人的精神层面关怀着人的现代性,主要是通过城乡对比,对乡村灵魂的赞美中呼唤一种健全的民族生活方式,以安置一个个漂泊无定的现代灵魂,进而实现民族文化人格的再造;五四更多的借鉴西方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现代性如同一性、理性,像鲁迅以一个知识者的理性和先驱者的觉悟,立意要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性转型的需要,能够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轻装前进,而沈从文宣扬的则是审美意义上的现代性如多元化、非理性,意在防止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行进中只剩下一只躯壳,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重要工作。于是便有了沈从文式的另类:“五四唾弃野蛮,呼唤文明,沈从文却崇拜野蛮,嘲笑文明;五四文明对乡土的描写,永远在批判愚昧的思想启蒙模式中进行,沈从文的乡土,却是自由理想的境界。五四讴歌‘新’和‘变’,沈从文却耽于‘旧’和‘常’。”⑩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另类”与“独立”是相对于当时流行文坛的西方话语而言的,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他同样是有依附的。他的哲学观念,不是来自学校教育或域外熏染,而是在自然之中长养而成,是“无师自通”的取自中国老子的返归自然,将自然作为宇宙的最高法则,又在文明批判的领域内与欧洲浪漫主义惊人的“暗合”。
需要申明的是,沈从文揭示都市之丑,是丑在人事,而没有提到科技文明。这一澄清为他洗刷了反科技、落伍的罪名,呈现出一种对现存文明秩序的“修补性批判”,可是,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来看,又表现出力度的不足。这是可以理解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充分发展之后主动的运用现代思考与能力去“求全责备”、“完善”是迥然不同的语境,面对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神化,也不能圣化。落后是一种脱节,超前也是一种脱节,脱离了中国社会的现实,脱离了审美的传统习惯,因此,沈从文的“浪漫主义”被冷落是可以理解的。而今,在城市文明大受污染,生态环保的呼声日益高涨,回归自然的美学命题又一次郑重的复出,沈从文的价值也重新显现出来。真正的艺术和深刻的思想总是有一种奇特的命运,接受他们,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悟想思辨的过程,不同的思路和理解就在这个过程里冲撞和衔接,从而激扬出新的语境下方可出现的全新的东西——如果作家本人有幸见识,他也会为之一惊的。
三、浪漫主义与生态批评
在西方,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首先是从浪漫主义的研究开始的。最早将“浪漫主义”与“生态学”联系起来的,是英国乔纳森·贝特《浪漫主义的生态学》(1991),这部著作使得“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词广为传布,并获得了文学与文化的意义,这一“概念”包含两层涵义:1. 浪漫主义具有生态性,正是本文挖掘的要点;2. 生态主义具有浪漫色彩,这在“作为活动的生态批评”一文里有专述。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布依尔《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文学和美国文化的形成》(1995)一书,则为生态批评的操作找到了理想的范本。浪漫主义与生态主义的携手,成为二者互生互惠的“友好交往”。
1.浪漫主义与大自然
浪漫主义在文学长林之中被公认为是最具生态性的文学,其原因就是其中介:“自然情结”。浪漫主义队伍庞杂,涉及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涵义又难以界定,被各自张扬的主观自我所抵制;历史进程中也难以独立行进,对其他主义与流派存在着依附。但几乎所有资料都证实了浪漫主义的这样一个显著特征:着力歌颂大自然,对大自然的景仰和趋同。可是追根索源,询问: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为什么与自然结下家园情结?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对公认的现象进行“寻根”式的探究,似乎有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嫌疑,也有可能被指责染上了有意作难的毛病,然而,当我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沈从文时,乡土、浪漫主义、大自然,都是必须正面应对的话题,而且,无论是主体,还是对象,都潜藏着生态特质以待挖掘、品味。
在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看来,自然不单是感官觉察的景物,更是隐藏于自然之中或其背后的事物的象征里的某种感悟和神启,诗人通过想象,通过倾听与诉说,寻找与美化,就是把心灵与大自然之间的象征性神性诠释出来,然后将其双手捧起来,献给新的时代和需要它的人们。在自然——心灵——文明的三维结构中,主体心灵与自然结成联盟,共同抵制文明的侵蚀,因此,自然是家园,现实是浊世,是排污场,形成了“回归自然、心灵解放、文明批判”的经典模式。在沈从文的美学观中,进一步将“自然”安放在他的乡土湘西,把“文明”置放在城市,于是,形成了他的“乡土抒情,城市批判”的创作模式,究其根本,这种模式原来是浪漫主义美学观的结构原型,这一发现为他的二元对立模式剔除了情绪化的东西。由于国情、时代以及自身的原因,这种浪漫主义没能在中国形成思潮效应,只是沈从文个体式的接应,而且是短暂的接应,当然也是一个美丽的接应。之所以难以被人们认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西方浪漫主义主要是诗歌,小说家们是不以为然的,而沈从文偏偏把浪漫主义运用于小说创作,你说叫人如何理解?
在浪漫主义者的怀中,他们紧紧的将人与自然搂抱在一起,提出消除人与自然的敌对的或冷漠的异他与异己关系,重建一种联合的、快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借助家园感和亲情感,让人在与自然的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从而剔除人在与社会的交往中产生的统治欲、占有欲以及压抑感、分裂感。无疑,浪漫主义者调动着他们“寻找”的眼睛,因为他们坚信大地之上“存在”着理想,这一“存在”,就是“大自然”,当然他们找到了,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完善”的工作,于是世界诗化了,建立在大地之上的家园是可以尽可能美妙的,有别于乌托邦的空中楼阁。可见,“浪漫”这个字眼所隐含的主体性涵义,非常适用于描述新兴文学中大量存在的主体意味和追求,生态文学与浪漫主义就这样自然而然的结缘了,无论是梭罗在瓦尔登湖畔“找到了”的亲身体验,还是徐刚在长江“不见了”的忧心呼唤,都以浪漫的情怀抒写出多主题、多变奏的大自然情怀;无论是卡森在春天的“寂静”,还是沈从文在边城的“逗留”,都勾画出了责任感极强的作家对大自然的隐忧,进而连锁的引带出人类生存的困境。这就是浪漫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关联,而其关联的中介,就是大自然。
2.浪漫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这个话题挺是微妙。按说,浪漫主义把世界诗意化了,在一片赞美与崇尚中体现了主体意识的合融,也体现了对自然的呵护,与以践踏、掠夺、征服为特征的人类中心主义简直是风牛马不相及。然而,用生态理念来考察,也真是个问题:既然世界是人类对真实世界诗意化的产物,那么,浪漫派心中的世界依然与人类有关,浪漫主义标志着现代主观性原则的颠峰,当然脱不了人类中心的干系。当代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理论教授沃尔夫冈·韦尔施{11} 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中心透视法、浪漫主义诗意化艺术与20世纪现代艺术的“非人性化”的比较分析,认为浪漫主义“这种有悖自然常理的诗化世界只是夸大了的独特体验,人类中心论并没有消除,只是变得更微妙而已”。“诗意化”遍布于自然之中,我们的视野仍然过分地专注于人类自身;而现代艺术通过对“非人性化”的追求,“引导我们超越这个为人类包围的、处处充斥着人类的世界”,力图争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结果以“对人性的逆向思维”导致对人性的否定,为其自身的桎梏所羁绊而“转变失败”。从而提醒我们:人类始终是深刻的世上的存在,“仅仅背离人类是无法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当代艺术的当务之急是将注意力从自我中心转向人与世界的联系”。是的,“美在关系”(狄德罗),间性理论成为改造中心理论的试金石。生态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剔除人类中心主义,说实话,人类中心主义确实有着存在的某种合理性,它对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创造性、主动进取性,从而使人们从自然界的严酷压迫和绝对支配下“提升”出来,实现人的应有价值,具有深远的意义,需要提醒的是,这种提升必须以尊重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其前提条件,但是人类盲目无度的“发展”已经违背了这一根本的生态规律,时代呼唤并敦促人类应该而且必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坚持主张“为了人”,也必须“通过人”,但绝不是为了“人类”这个“中心”;而主张“为了人”,也“通过人”,只不过是一种“高阶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偏向于某种微妙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为此,包庆德提出“扬弃人类中心主义”{12} 的观点,也许“改造”、“扬弃”与“重返”的思路比“剔除”更能行之有效,而这一切,只有在“批判”中才能获得。生态主义本身,也是形形色色,在人类中心主义的面前,位于“走出与走进之间”,如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批评还在筹划着。浪漫主义中所蕴涵的微妙的人类色彩,具有启示性。
3.浪漫主义与生态批评
在社会工业文明和科技理性阔步前进的现代化背景下,浪漫主义是危机四伏,不亚于沈从文当年的困窘。主要表现为:1. 从康德浪漫哲学中淘选的主体自我以其先验存在、自我欣赏而切断了与人类文明的整体生存状况的联系,无法统摄现实的纷繁复杂,无法对现实人生作出积极的应答;观念中的自我天然的具有“逆动精神”,具有“灾难性”的迷向,容易使人“机械性反对”任何外部权威,而与世不相容,也使人对自由放任的过分耽迷而放弃了真正的追求与修养,许多人生悲剧都是浪漫主义惹的祸;2. 诗化中的自然固然美好,可是不是对现实自然的描摹,使真实自然处于一种遮蔽、无知的状态,不利于科学常识的普及与宣传,以至于常德动物园的狮子吃掉一个八岁的男孩,而记者采访同龄人时,他们都以童话、动画片中的印象回答:狮子很可爱!3. 艺术上主张以人的感性存在和真实生命活动为本体,以其对主观自我的偏执痴迷容易导致主体在日益膨胀的现代性面前遮蔽重重,陷入尴尬的网络而难以与现代化接轨,使艺术难以担当历史使命。{13}
浪漫主义之祸,生态主义来纠偏。在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兴盛是针对古典主义的程式与规约,使得回归自然、心灵解放、文明批判三大指标得以奠定,而今,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绿色风暴,赋予浪漫主义以崭新的内涵与形式。浪漫主义这一醉舟在生态主义热的21世纪,重新升起桅帆,舵手不再只是诗人,他们常常是些生态主义者;不再是以诗人为中心,而是带着“以大地为中心的观点进行文学研究”(格罗特费尔蒂)。在自然——心灵——文明的三维结构中,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是自然观的变化。蓝仁哲教授将生态批评与浪漫主义相比,认为:
与浪漫主义自然观相比,生态批评超出了静态地对自然的崇尚、默契与神交,被动地以“回归自然”来抗议科学主义和现代文明带来的恶果。相反, 生态批评采取一种实际的干预姿态,力图以抵制的行动来拯救自然,制止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重要的是,必须维护自然而不止于赞美自然,自然不只是现实中的景物、描写对象、阅读与批评的审美观照和心目中的精神导师,而且自然本身被视为批评的观念或手段。一方面诉诸自然及其法则以挑战工业文明的逻辑,不仅为自然的环境惨遭掠夺破坏而呼吁警示,还以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活力对照人类生命的短暂,以大地母亲的忍辱负重的厚实鄙夷人为的机巧;另一方面,坚持浪漫主义的有机整体的自然观,批判人类中心、人定胜天之类的妄想,宣扬万物齐一、物类平等的哲学理念,斥责万物皆备于我、任我宰割征服的傲慢凶残。{14}
其次,是情感的超度。如果浪漫主义主张人的“自然情感”的释放,“情”作为沟通现实生存与精神神性的中介,把世界纯化了,经验的现象界与超验的彼岸趋近了,人的有限性生存与无限性的期盼沟通了,使人类“自然而然地”,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那么,浪漫主义托生而出的生态批评运用的是一种超理性,这种超理性既不是理性,也不是非理性,它是一种体验,一种智慧,一种“亲证”,崇尚的是“大地伦理”、“生态情怀”,真正的实现高尔基所云:“倾听世界的回声”。
再者,是文明的求全。如果浪漫主义在反对工业文明时不可避免的带有情绪化的色彩与反现代化的论调,那么生态批评则是以“求全”的心理“责备”现代文明对自然对心灵的伤害,并且坚信自身具有纠正这一“异化”的“现代能力”,能够引领科技走向生态化之路。在环境危机日窘的背景下,生态批评更多的受到“问题的驱使”(劳伦斯·布依尔),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挥着自己应有的独特作用:“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阐释文学作品,挖掘生态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批判渗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生态文学作品,重新建构文学经典,促成生态文学的繁荣,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重新铸就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人文精神,并担负起引领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重任”{15}。以干预现实的姿态言说现代化进程中潜伏的危机,起着“提醒”、“警示”、“修补”与“设计”的作用,对现代文明是批判而不是反对。
在文学“绿色化”的进程中,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挖掘浪漫主义的自然观,探讨浪漫主义文学在自然之中寄寓的种种理想与追求,可以发现一个悄然变更的趋势:浪漫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合流,这一趋势算不算浪漫主义被现代主义收容后所做的积极突围与自我调节?预示着浪漫主义的新动向,21世纪文化界的新景观?
注释
①覃新菊:《“最后一个浪漫派”心态论——沈从文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吉首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②⑤刘增杰等:《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7-102页。
③陈国恩:《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概观》(上),《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④俞兆平:《美学的浪漫主义与政治学的浪漫主义》,《学术月刊》2004年第4期。俞兆平的这一划分为笔者的研究增加了思维的明晰性。本文正是立足此划分,对沈从文所属的“美学的浪漫主义”以及他的“最后”性、浪漫主义与生态的关联进行思考的。
⑥陈国恩:《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概观》(下),《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⑦刘增杰等:《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⑧刘增杰等:《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⑨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孙冰编:《沈从文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⑩杨联芬:《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温奉桥:《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另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社会文化的现代性”与“审美的现代性”的划分,为我进行五四与沈从文的比较提供了思路。
{11}[德国]沃尔夫冈·韦尔施著,朱林译:《如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第5期。另见《文艺理论》2005年第3期。
{12}包庆德,王志宏:《走出与走进之间:人类中心主义研究述评》,《科学技术辩证法》2003年第2期。
{13}王作:《浪漫主义的缘起与危机》,《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14}蓝仁哲:《浪漫主义·大自然·生态批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15}陈茂林:《质疑和解构人类中心主义——论生态批评在文学实践中的策略》,《当代文坛》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