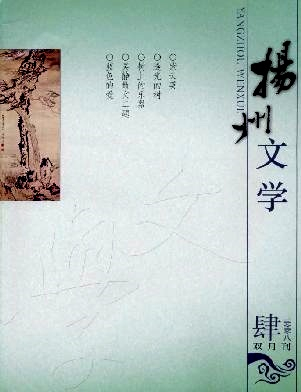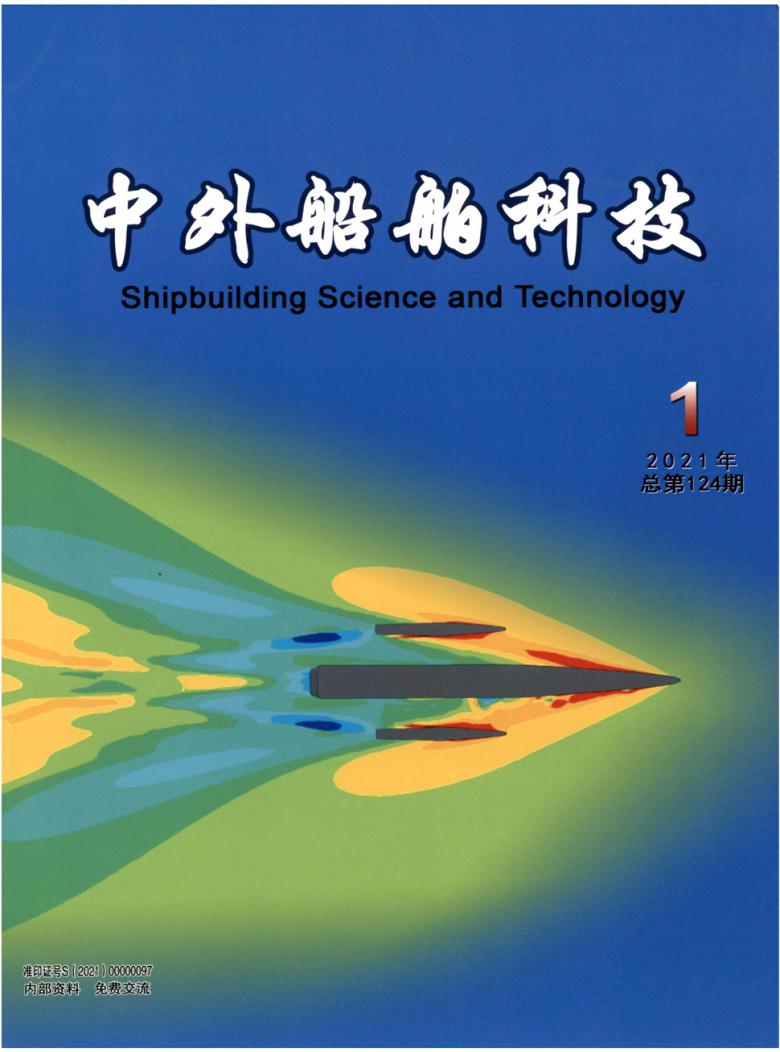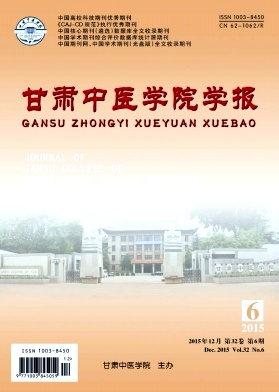1998—1999年文学各学科研究新书评介·《古典主义的终结》
关爱和 2008-08-14
350年前,几乎在八旗铁骑厘定天下的司时,一个新的古文流派在安徽中部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偏远小县悄然崛起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桐城之名震于天下,桐城派古文也成为雄踞文坛的主流文派。它几乎经历了清王朝由乱而治,又由治而乱以至灭亡的全部过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延续最久的一个散文流派,又是最后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古典文学流派。当“五四”风暴席卷北京之后,桐城派的末代传人又黯然返回桐城,使桐城派的发源之地戏剧性地最终成为这一流派的圆寂之处。
桐城派向以道统、文统自居,所以它不仅是一个散文流派,而且代表着程朱理学的文化祈向,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统治者的文化意志。在桐城派的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的漫长发展进程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潜藏着文学发展的丰厚底蕴。解读这些信息,探寻这种底蕴,已经成为文化史学者和文学史学者的一项任务。
如果从1905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发表《文章源始》一文算起,桐城派研究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在近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桐城派古文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所谓“一文(桐城派古文)一诗(宋诗派)一社(南社)”,构筑起近代诗文研究的基本框架。但是,也许是因为近代文学研究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理论积淀还不够丰厚,学术视野还不够开阔,因此不少有关桐城派研究的成果,还停留在“就人论文”、“就文论文”的层面上,未能深入开掘桐城派的文化蕴含。现在,关爱和教授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一书弥补了这一学术缺憾。
脱出习惯的线性思维模式,在较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分析桐城派的兴衰衍变,将文学研究与文化阐释结合起来,通过文学分析来解读重要的历史文化息息,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使这部学术专著在不乏精彩的同时,也拥有了坚实与凝重,代表了20世纪末桐城派研究的学术水平。该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似乎在不经意之间深入探讨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问题,例如,政治文化氛围对文学流派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流派领袖人物的个人际遇和性格学养对该流派发展的主导性作用,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相互激荡,等等,而这些问题又被此前的学者长期忽略,由此显示了作者的敏锐缜密的学术洞察力和宏博丰厚的学养。
该书以桐城派标榜的“道统——文统”为中轴线,作纵向的学术展开。作者首先追溯了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认为韩愈、柳宗元的“文道合一,文以明道”的文道观被北宋古文家所继承,但朱熹等理学家却轻诋韩、柳“裂道与文以为两途”,主张“心统性情”,“文从道出”,以语录体代替古文,导致了中唐以来思想与文学联盟的破裂。明初,宋濂提倡“辞达而道明”,唐宋派重提文道并重与韩、欧传统,主张古文家必须从“明道”中显示出文章家的本色。清初,侯方域、魏禧、汪琬皆推崇韩、欧之学,批评理学家重道轻文,主张“汇文道源流而一”,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下,遂成为古文一派的思想旗帜。而以道统、文统承继者自认的,就是继侯、魏、汪之后而崛起的桐城派。
在分析桐城派的源起时,作者认为,方苞“以古文义法用为制举之文,以清真古雅为正途楷模,实际上是依古文家的宗尚在为科举文确立一种写作与评价的规范。当方苞有关以古文义法旁通于制举之文的两篇序言随着《四书文选》、《古文约选》颁行天下时,已因它所具有的官方色彩,而在无形中大大扩展了方苞义法说的影响和覆盖范围”。所以,“义法说的植被地带在古文,也在时文”。在这里,作者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作为文学主流派的桐城古文所具有官方色彩,以及桐城古文与科举文化的密切联系。桐城古文之所以被誉为“文章正宗”而长盛不衰,与此大有关系。
在论述嘉道之际士风时,作者首先对明清两代士风作出了比较,认为“明代之士言官争竞,清议讲学,士风喧嚣骄盛,不可一世。清代矫正明代弊端,以严厉之策治士,不许聚徒讲学,不许清谈议政,从而造成士风委靡,言路堵塞,慷慨忠义之士无所用其智慧,官场士林中则弥漫着苟且偷安、推诿因循、好谀嗜利的风气”。作者进一步分析道,正是由于嘉道之际的变局和政府控驭力的减弱,才激活了姚门弟子被压抑已久的政治热情,使他们热心于立德、立功、立言的话题,而姚门弟子对程朱义理之学的虔诚信赖,也有更加切实丰富的内涵。 作者认为,桐城派传人特别强调道统、文统的承传接续,注意编制传承系统,极力维护桐城派古文的嫡传地位与师道尊严,不失时机地推出新的领袖与传人。作者写道:“浓烈的道统、文统意识,是桐城派发展过程中的精神信仰支柱及向心力、凝聚力的所在。它使散在的作家个体,在准宗教化情绪的支配下,以准宗法制衣钵传承的关系而结盟。这无疑是桐城派二百余年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桐城派关于道统、文统的阐释与论述,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中极富个性特征的组成部分。”作者同时又指出,桐城派托道统、文统而自尊,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宗派情绪,划地为牢,自我封闭,形成了虚幻色彩极浓的“统系理想主义”,从而逐渐失去了理论创新的锐气,也压抑了作家的创作个性。至曾国藩出,主“坚车行远”之说,于古文之学孜孜以求,“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于一途”,始有桐城派之中兴。
关于桐城派的生存与发展,作者提出了两个空间的观点,认为桐城派文人设定了两个生存空间,一个是社会空间,即桐城派以道统、文统的传人自居,以艺术之文的作者自任,以力延古文一线作为历史使命。这种必然而自觉的集体行为,又营造出第二个空间——艺术空间。桐城派通过对古代散文的理论成果、阅读体悟及创作经验的总结,形成了独具特色、风格鲜明的古文理论体系,从而别开之境,卓然不群。
对于中兴桐城派的领袖人物曾国藩,作者用功颇深,不乏精彩之处。作者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处在传统与现实的夹缝之中,充满极大思想矛盾和人格分裂的复杂人物。特殊的政治际遇,把他推上了中兴名臣的地位;他又凭此煊赫的政治地位,着意强化文事辞章的社会功能,在桐城派趋于山穷水尽之时,援之以手,对桐城派予以改造,将桐城派纳入其中兴大业之中。曾氏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识度,是桐城派中兴的基础。他对雄奇瑰玮风格的崇尚,他于义理、辞章、考据之外又特别标出经济,为桐城派古文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曾国藩主张以文见道,坚车行远,重在讲求经世要务,记叙当代掌故,铺叙文治武功,重义而不轻诋于法,求雅而不拘泥不洁,取方姚之流畅而去其柔弱,辅以汉赋之气体而脱其板重,义必相浦,气不孤伸,词必己出,简要有序,以政治家、经世家之文取代文学家之文,由此形成了湘乡派。
作者认为,曾氏之文,“较为全面地体现出宏大卓然的气质和举重若轻的才力”,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圣哲画像记》。作者对比文有精彩的点评:曾氏“在对32贤哲心仪柱香、顶礼膜拜中,传达出纷乱之世士儒阶层文能坐而论道,武能决胜千里,从政能驭将率民,闲逸则登高能赋的人生理想,及承先启后、全面继承学术文化传统的精神面貌。文中所贯穿始终的‘沙场秋点兵’的豪侠气魄,既有书生意气的成分,也有舍我其谁的底蕴,令读者心驰神往”。而曾文的‘敛退气象”,则体现在《欧阳生文集序》诸文中。与姚鼐、梅曾亮相比,曾国藩气度过之而精微不及,但立言谨慎,措语熨贴,却是一脉相承。但是,作者同时也指出,曾氏生古文理论上的改革倡导之功,远远大于他的创作实践。
关于桐城派消亡的原因,除了桐城派自身艺术创造力的衰竭之外,作者特别强调了历史文化因素,认为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桐城派依附于封建政治之上,而封建政治的垮台,使桐城派挟道统、文统自重的优势轰然坍塌;桐城派古文自方苞起,便与科举制有不解之缘,士人缘桐城义法而敲开仕途之门,但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桐城古文失去了往日功利性的诱惑;桐城派古文的盛行,与一直受到清政府的保护、提倡有关,一旦清朝灭亡,失去这种官方支持,桐城派必然要陷于穷途末路。相反地,白话文由于得到国民的认同,1920年又被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为法定国语,其优势地位才得以巩固。
当然,这部著作也给人留下了些许遗憾。从体例上看,该书的所有古籍引文都未能注明卷数,正文之后也未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从全书篇章设计来看,第一章为桐城派的总论,第二、三章分别论述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及古文创作,第四章论述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其思路可谓清晰,但在具体论述时,第一、二、三章的内容偶有互相重复之处;从论证上看,曾国藩崛起与桐城派中兴,除了其他因素以外,似与湘乡的历史人文环境及湖南理学集团有关,惜作者于此着力不多;从行文上看,出现了个别笔误,如第357页:“咸丰元年,已入垂暮之境的曾国藩……”。“咸丰”显然为“同治”之误,因为咸丰元年时,曾国藩才40岁,正当英壮之时,在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而同治元年时曾国藩已51岁,十年后下世。所以,如果再稍加磨砺,这部学术著作也许会更加精洁完美。然而,小瑕不掩大美,《古典主义的终结》仍然不失为近年来近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少见的一部力作。它是作者近20年来潜心于桐城派研究的学术结晶,展示了比较独特的学术风格,拥有精醇的学术品位,与那些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学术复制品有质的不同。就桐城派而言,《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可以说为20世纪的研究划上了句号,也为21世纪的研究奠定了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