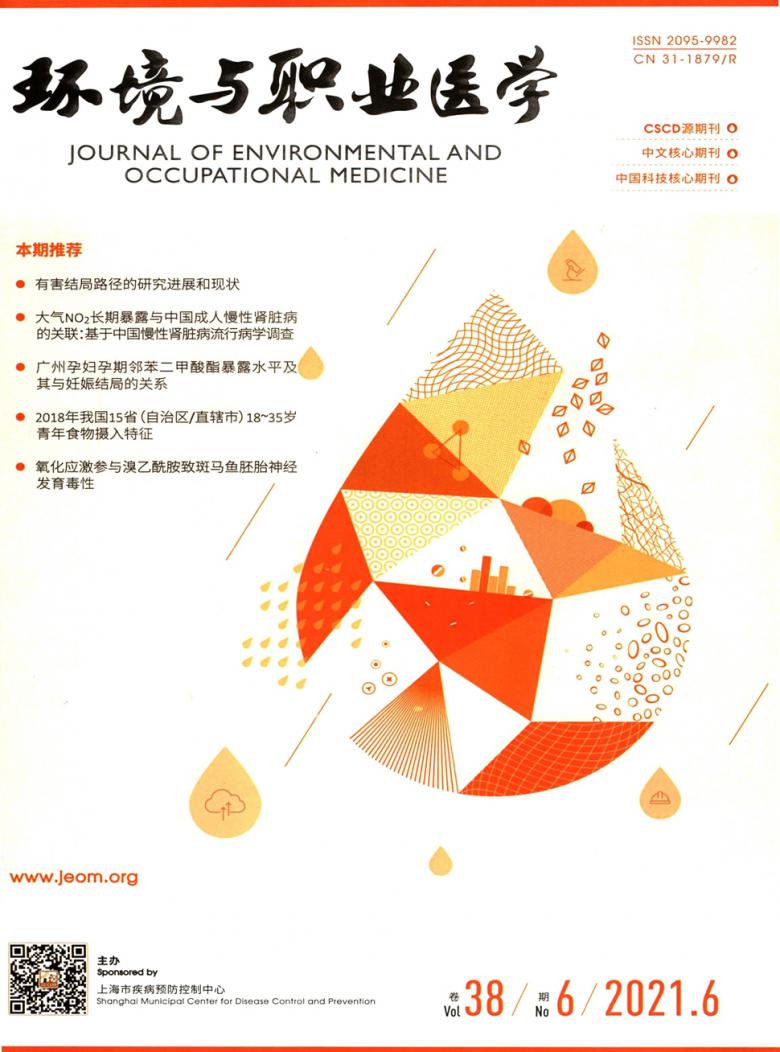想象力:艺术创作的本体精神
刘辉 2008-11-11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始终闪烁着璀璨的光芒,历久而弥新,靠的是作家、艺术家奇崛而丰赡的想象力。也就是说,文学艺术赖以生存的精神力量是生命中的想象力,“没有想象,便没有艺术”。所谓想象力是人所特有的具有生命活力、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心理功能,主要是在审美过程中通过联想、想象、幻想将各种相关形象、记忆表象加以整合以认识对象和创造新形象的能力。
古往今来,许多哲学家、文论家都对这种奇异的能力做过精辟论述和精彩阐发。意大利启蒙运动时期的文论家维柯曾把想象当作诗性智慧的主要推动力,认为如果没有想象就不会有诗人的创作,更不会有诗性智慧的诞生。维柯解放了想象力,他认为,想象力不是其他任何之物的女儿或仆人、侍从,而是一种独立存在、拥有独立价值的能力。黑格尔认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力”。[1]马克思在《路易士•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这时候已经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并且给予了人类以强大的影响。”[2]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希腊神话时又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马克思的这些话,适用于一切文学艺术。文学艺术的创作正是借助于想象,把客观的现实生活形象化。正因为这样,所以高尔基直接把想象看成是艺术的思维,说:“想象在其本质上也是对于世界的思维,但它主要是用形象来思维,是‘艺术的’思维。”“想象是创造形象的文学技巧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3]因此,我们认为想象力是一个人精神的灵魂和艺术创作得以产生的精神力量,即艺术创作的本体精神。它是文学艺术给人以诗性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强有力地揭示文学艺术的情感体验与文化意蕴,并不断努力超越庸常的社会现实,是体现作家艺术家精神深度与思索广度及其艺术意念与品位的核心素养。
想象力的本质属性是情感性、自由性与生命性,就是挣脱一切现实秩序对人类精神束缚羁绊,为恢复生命内在的自由活动而努力。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艺术家或作家正是以这种艺术想象力作为主要而且是基本的思维模式,通过想象力的发挥和延展,来推进积极自觉的表象活动,催生作家内在的形象系统不断急剧变化和生成,从而创作出真实而深刻的艺术作品来。创作中的想象力作为一种极富创造精神的心理活动,具有高度的自由性和任意性,突出体现在对客观时空局限的完美超越和对情感对象的“身与物化”。在艺术创作实践中,艺术家或作家的想象力逸出心灵的束缚,在广袤的大地上纵横驰骋,完全不受客观物质形态的限制,可以灵活地消解空间阻碍,自由地跨越时间距离,奔突驰骋,无拘无束。我国古代的文论家对创作想象力也有过隽永含蓄而又精辟的论述,陆机曾经在《文赋》中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生动地形容了艺术想象力超越时空的特性。最为人乐道的乃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艺术构思中对想象机制的生动描绘:“文之思,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由于艺术想象不受时间空间阻隔与限制,艺术家可以在无限的时空中自由联想,任意驰骋想象的翅膀,以便能达到与天地万物符应契合的自由境界。无论是想象奇特的《山海经》,如“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之类的描述,还是家喻户晓的《西游记》,历来都被看作想象力表现尤为突出的典范性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孙悟空大闹天宫、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故事,“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诗句,“六月飞雪”“春花冬开”的传说,都不必受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与约束,不必符合客观世界的真实,因为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法则,也是想象力的功用使艺术的精神魅力得以呈现和拓展。法国著名作家乔治•桑在《印象与回忆》中曾坦言:“当创作活动展开后,想象力高度活跃起来,我有时逃开自我,俨然变成一棵植物,我觉得自己是草,是飞鸟,是树顶,是云,是流水,是天地相接的那一条水平线,觉得自己是这种颜色或是那种形体,瞬息万变,去来无碍……总而言之,我所栖息的天地仿佛全是我自由伸展出来的。”在这种艺术想象的自由天地中,主体的心灵得以充分舒展,创造性思维得以充分释放,充分发挥,其结果则是一个个令人惊异的艺术形象系统的诞生。所以说,想象力确实是最自由的创造性想象,是文学艺术创作中最活跃的心理机能。想象力并非只是一种话语表达的方式和展现手段,而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创造形式,它的创造性与生命性特征也正体现在作家艺术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自由重构之中。想象力的生命性、情感性与“物我同一”的境界同艺术活动形成契合无间的同构关系,它作为赋予作品以美学意义的重要手段,在凸显人类生存的情意状态或独立品格和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此,我们可以概括指出,创作想象力主要表现为形象想象力、意象想象力和情感想象力。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是须臾也离不开形象的加工、意象的浓缩、情感的升华的。形象激起想象的风帆,意象鼓起想象的翅膀,想象又促使情感的升腾和变化,形象、意象、情感与想象交织在一起不断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一股合力,推动着艺术创作活动顺利地向前进行。因此可以说文学艺术赖以生存的精神力量是奇特的想象力,质言之,想象力是艺术创作的一种本体精神。想象力始终灌注着创作主体的丰富情感,是在情感力量的催动下展现的,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并通过凝铸而成的形象和意象展示在作品中。因此缺乏想象力的艺术创作是不可能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的。
然而,当我们厘定清新健康的文明坐标重新审视当下的艺术创作时,不难发现在艺术领域里想象力的日渐匮乏和作家艺术家对想象力的忘却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工具理性的控制下,文学作品、电影、相声等艺术门类越来越远离必要的想象空间,失去诗性的审美质感与诗意智慧,这不仅彰显着作家艺术家在艺术思维上的苍白无力,暴露出作家艺术家对商业利益积极迎合的姿态,同时还表现出他们对心灵自由这一艺术理念的淡化与漠视。想象的思维特点日渐程序、化单一化的趋势,因此,当下的想象世界呈现出一片荒芜而苍凉的景象。诚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日益受制于理性的想象力,一方面,在无数概念的指导下,获得了精致的逻辑秩序,并有了新的流动方向,一方面又被概念所缠绕所束缚乃至被窒息了。”[4]缺乏想象力不仅使文学艺术变得索然无味毫无魅力可言,也使原本充满诗意的生活陷于一种彼此模仿的单调重复之中。无疑地,缺乏想象力,就会使我们的生命不但没有必要的更动和新鲜感,而且连最为日常的运作都显得特别慵懒乏味。一旦缺乏想象力,艺术作品的延展性和审美趣味就会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失去生命律动感。想象力之于艺术犹如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之于生命。事实上,想象力不仅是一种综合能力,更是一种生命意识,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做前提,就没有旷世作品的出现和个性流派的诞生,更没有文学艺术的总体发展和欣欣向荣。
鉴于当前文学艺术发展不景气的局面,致力于呼唤想象力的回归,是当今所有艺术创造者都应该首先思考的问题。优秀的艺术家总是以奇特的想象力密切地观察、分析、感悟着自己所身处的大千世界,揭示出生命的存在状态与本体精神。想象力的回归可以有效地遏制当下艺术创作的衰败颓废之势,增强艺术作品的内涵和表现力,提升大众的艺术品味和审美水平。同样,想象力对当下的社会文化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正如被誉为“当代美国文明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的米尔斯所说:“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5]
[1]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3] 高尔基:《论文学技巧》,《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17页。
[4] 曹文轩:《小说家:准造物者》,小说选刊,2001年第5期。
[5] (美)米尔斯:《社会的想像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