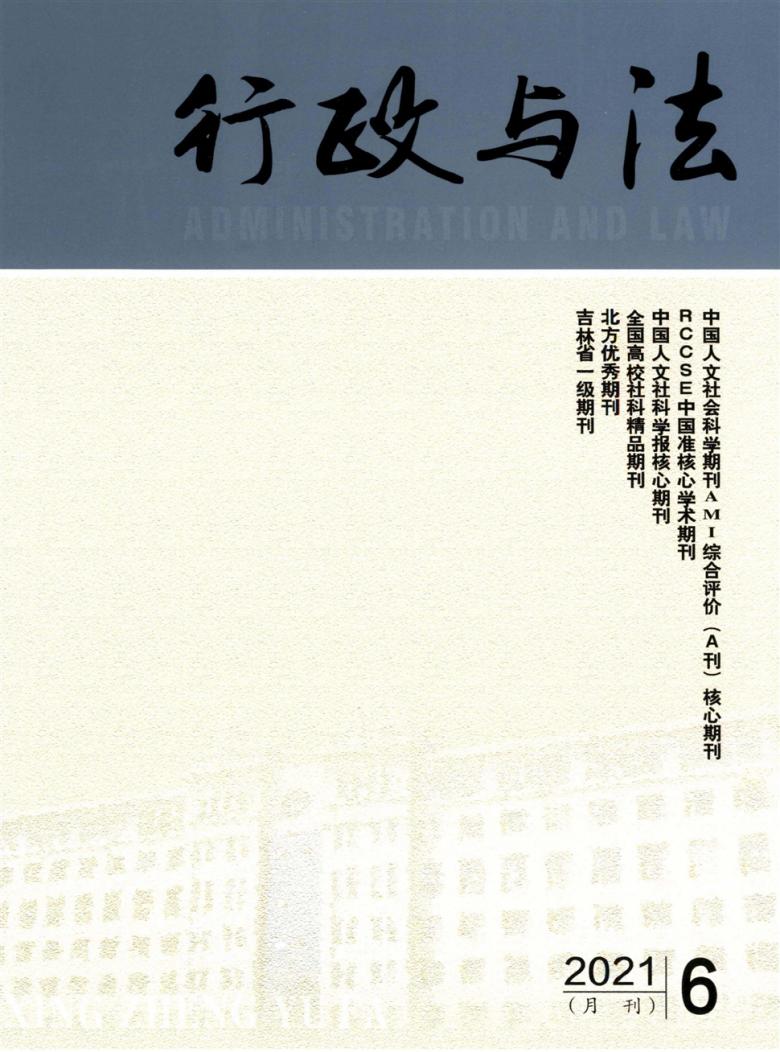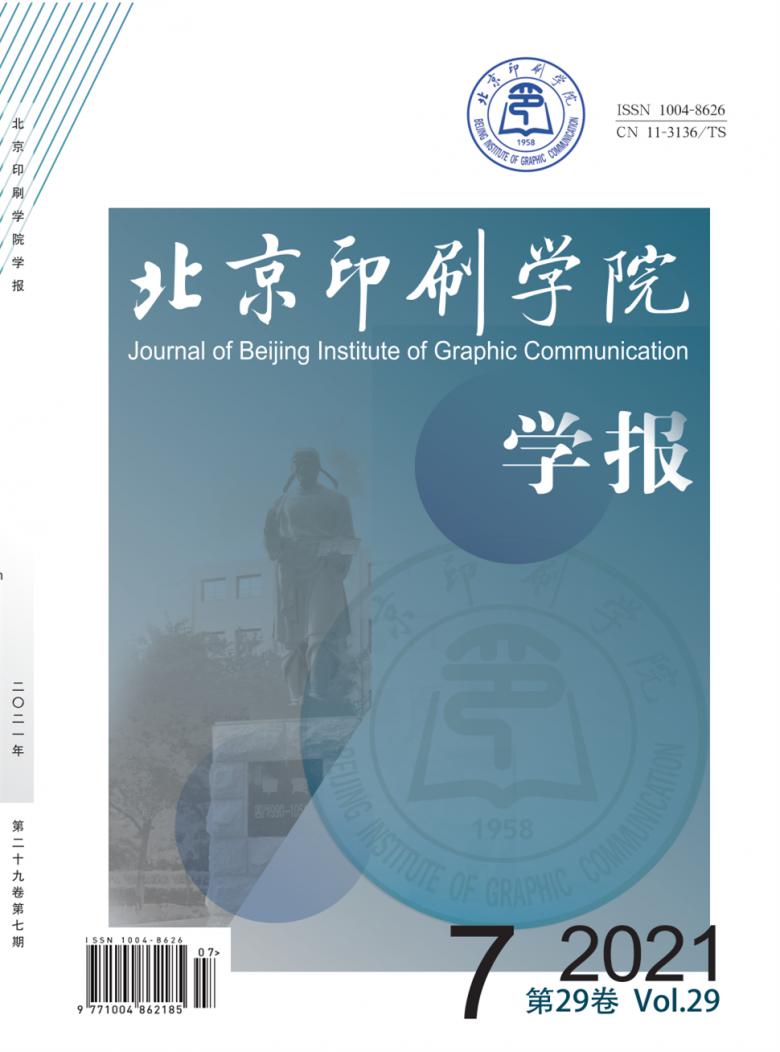五四女性叙事文学的叙事节奏分析
王志萍 2009-07-03
关键词:五四女性叙事文学 叙事节奏 策略 意义 摘 要:五四女作家们用节奏变换的策略去取舍剪裁故事,不仅是技巧的展示,还隐含着意义。五四女作家在讲述“价值微小的事件”、自己比较隔膜的社会历史事件或出现“话语空白”时,倾向于快节奏的叙事;而描摹日常生活场景和女性人生情状及抒写自己对自我、对时代、对社会的女性切身感悟时,倾向于用慢节奏的叙事。叙事节奏的变化,与女作家的经验及视野相关,因此表现出与男性作家的某些不同。 叙事文学中的时间是一种经过扭曲、变形的时间,叙述者对时间进行压缩或膨胀,从而使生活中摸不着看不见,以年、月、日、时、分、秒等计算长度的物理时间空间化,变成以页数、行数、字数为计量单位的“叙事时间”,故事中事件的时间长度与“叙事时间”的长度之间参差对照的关系就形成了各种叙事“节奏”(Rhythm)。叙事“节奏”的控制不仅产生了叙事作品的审美特色——张弛之度,也产生了意义——叙事者对故事的详略剪裁隐含着他对事件本身的理解和评价。节奏是通过叙事的快慢变化,也即速度呈现出来的,荷兰米克·巴尔教授在《叙述学:叙事理论悖论》一书中区分了省略、概略、场景、减缓、停顿五种不同的叙事速度,这五种速度在五四女性文学的叙事节奏中的具体表现是本文探讨的对象。 “省略”“概略”的故事时间长于叙事时间,通常情况下,事件推进速度很快,没有细节,只有概况,其表现的叙事节奏便是“快节奏”;“场景”的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大体相等,事件发展比较缓慢,“减缓”和“停顿”的故事时间短于叙事时间,事件的正常进展被拖延或中断,这三种叙事速度可统称为“慢速”,其表现的节奏则是“慢节奏”。在五四女性叙事文本中,“快节奏”和“慢节奏”交替出现,如石评梅的小说《只有梅花知此恨》开头描绘主人公潜虬灯下抄录公文的场景,交织着减缓与停顿,几乎无事却用了三段文字,而接下来,潜虬接到薏蕙的电话,以省略和概略的方式追忆往昔,八年前的爱情故事和八年中各自的经历化作寥寥数语,简约之至。故事转入现在,薏蕙约潜虬见面,潜虬以“社会礼教造成的爱,是一般人承认的爱,它的势力压伏着我们心灵上燃烧的真爱”为由,拒绝相见,故事戛然而止。主人公爱情故事的快节奏讲述和收束,衬出开头部分慢节奏叙事中人物生活的沉滞和无聊,社会积习的难以抗拒。两种节奏参差错落,既完整地讲述了事件的发展,又运笔细致地描写了人物生活状况。 女作家在节奏的自由调度中表现出自然天成的美的感悟力,更重要的是她们也知道如何用节奏变换的策略去取舍剪裁故事。节奏不仅是叙事技巧,也是叙事策略。 “省略”和“概略”这样的快节奏,在五四女性叙事文学中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所谓“价值微小的事件”,这类事件对故事的发展进程没有太大影响,对作者表达自己的女性经验、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也没有多少作用,在叙事过程中被放弃或不予详述,如冯沅君小说《贞妇》,从弃妇何姑娘与姑姑商量要去拜祭她曾经的婆母的场景,到“慕老太太开吊的第二天”,老姑娘陪何姑娘到慕家,这段故事时间在叙述中被省略,这期间可能发生许多的事,如何索要衣裳工钱?如何筹办体面的祭礼?何三奶又会如何为难何姑娘等等,这些琐事对故事的推进没有直接影响,对表达谴责男性薄情寡义的主题无足轻重,因此被完全省略。再如冯沅君《旅行》的结尾,男女主人公越轨而富有激情的旅行结束了,回来后要调整心态,要掩人耳目,也要深化二人关系,女主人公“心乱”时如何排遣,对待别人如何“不能似从前那样的专”,这些对表现女性的处境和女性的时代心理未必无用,但过于琐屑,因此用概略述之,三天的纷乱总结于男主人公的一句“往事不堪回首”中。 第二种情况中,所述故事是“展开型素材”,即“在其中显示出一种发展的较长时期”。有些故事时间覆盖十数年或数十年,涉及历史变迁、社会革命、人事沧桑的内容,五四时期的女作家明显表现出由于不能介入其中而导致的经验匮乏,只能将自己不甚了了的事件快速略记,快节奏成为女作家掩饰自己经验不足的叙事策略。如石评梅的《红鬃马》,关于郝梦雄的从戎经历和两次革命,均是快节奏的概略。再如,她的另一篇小说《白云庵》,“刘伯伯”叙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时,几个重要的时间阶段的事件都是概略陈述,各时间段之间则用省略,二十几年的人生经历被浓缩在不到五页纸的篇幅中,叙事节奏非常之快。一方面,石评梅并未亲身经历这些历史阶段,让自己的叙述者用慢节奏去真实再现历史风云比较困难,另一方面,大跨度的时间变换,更利于表达时间流逝带给人的无限伤感,作品的女性叙事者“我”感到“我们一生的精力只是一小点,光阴只是一刹那,自然我们幸福愿望便永远是个不能实现的梦了”。在这里,快节奏的叙事时间框架,与女性主体对时间消逝的悲剧性体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第三种快节奏的情况出现在“话语空白”的情境中。男权社会中,整个话语体系由男性建构,是用以确立和加强男性权威的一套表意系统,它是压抑女性经验的表达的,女性几千年的沉默,不仅是不能说,同时也是无法说,“恰如克莉斯特娃(法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当代著名女作家)已指出的那样,女性若想进入这种为男性把持为男性服务的话语体系,只有两种途径,要么,她借用他的口吻、承袭他的概念、站在他的立场,用他规定的符号系统所认可的方式发言,即作为男性的同性进入话语;要么,用不言来‘言说’,用异常语言来‘言说’,用话语体系中的空白、缝隙及异常的排列方式来‘言说’。”凌叔华的《绣枕》就是用快节奏的策略,用空白,“用不言来‘言说’”。开篇慢节奏的“绣枕”场景之后,笔锋一转,“光阴一晃便是两年”,从女佣妞儿的话中读者了解到靠垫被男性无视并糟蹋的际遇,至于两年中,大小姐是怎样在对幸福婚姻的热望中一天天心灰意冷下来,发生过多少骄傲、尴尬的事,叙述者只用大小姐自己的心理概略告知。“结婚,是社会传统赋予女人的命运。”为得到婚姻这一女性“有利的职业”,大小姐两年中可能会付出多倍于绣枕的辛劳,可能会寻找与其他男性联姻的机会,可能会受到多次的打击,可能会受到闺中女友的讥讽……各种可能已经发生的事对“高门巨族的精魂”而言,既难以启齿,也无以言表,女性的经验没有相应的话语体系足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概略的快节奏,能传达出言外之旨。 冯沅君的小说《缘法》中,叙事者用大半篇幅极写雄东在爱妻死后的悲痛和父母要为他包办亲事时他的抗拒及对爱情的忠诚,在结尾两段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迫于家庭压力再娶的雄东新婚不到三天,就已忘却旧情,并且“红光满面得意洋洋”,这近三天的故事时间里发生的事,在叙事时间里是完全缺失的,这种缺失,当然不是没有任何事件发生,而是没有言语可以说出女性对男性情感迁移之快的理解和评价。 相比较而言,慢节奏能更充分地表达女性作家的女性体验,在对话和一系列动作构成的场景中,女性对人生的观察之细、对人性的理解之深格外引人注目。受传统、环境、教育等的影响,女性对世界、对宇宙的宏观把握也许暂时逊色于男性,但这并不表明女性对世界对宇宙的认识肤浅于男性,女性是通过身边诸多细枝末节的东西去升华出对世界的认识,所谓“一粒沙中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 五四女性叙事文学中,“场景”是最为常用的一种慢节奏叙事,很经典的是凌叔华《绣枕》中大小姐绣靠枕的场景,静态的摹写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对故事的线性讲述,但对中国旧式闺秀的人生境况的揭示却再真实不过了——青春美貌、心灵手巧和温柔贤淑都不能保证幸福,中国旧女性永远只能是绣在靠枕上的鸟,艳丽照人,却不能飞翔,她们的命运如自己绣出的靠枕一样,只能任人践踏!慢节奏的场景可能比“事”更符合旧女性生活状态,囿于深闺的处境决定了她们很难有“事”发生,她们的生命就在类似的一个个场景中消磨而消逝。这里女作家对女性人生中时间停滞感的领悟是极其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