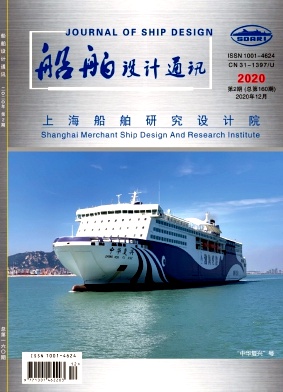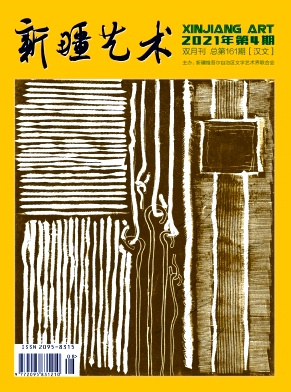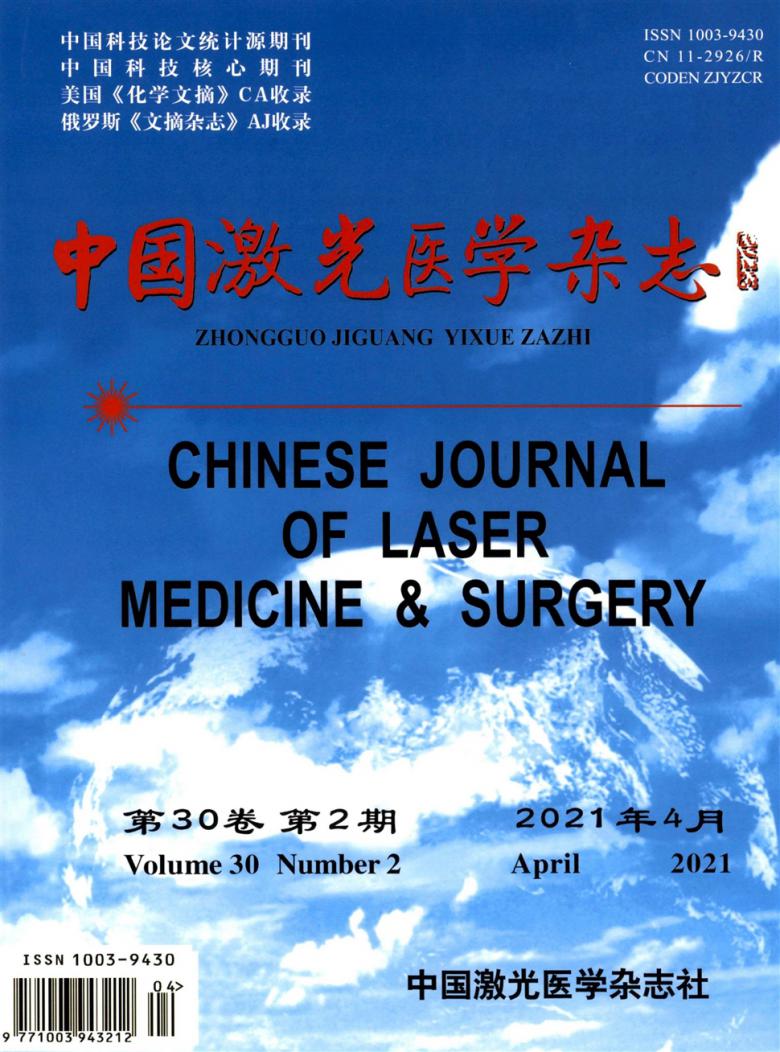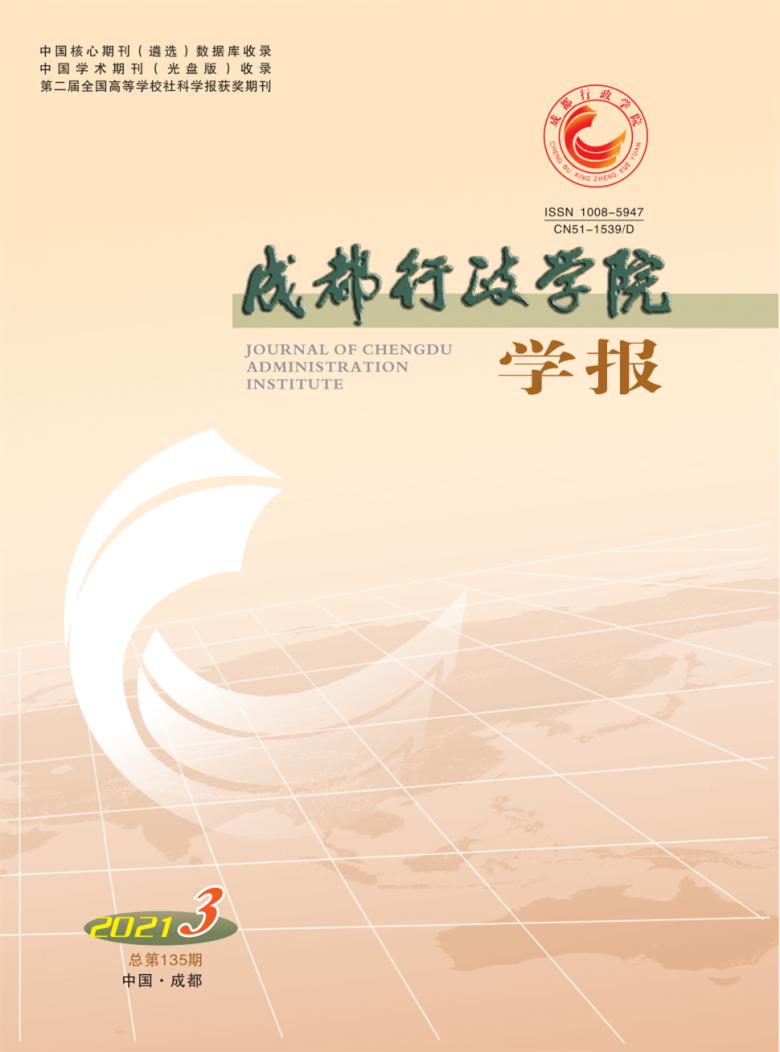新编京剧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
张宏梁
摘 要:新编京剧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话剧舞台的改革创新推动的。蒙太奇手法在京剧舞台上的运用已非个别现象,而且闪现出多种形式,使新编京剧增添了时空切换和形象拓展上的自由度,焕发出新的审美气息。对于新编京剧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仍然需要以积极的态度给予支持。当然,蒙太奇手法在新编京剧中毕竟只是辅助手段,京剧更应该充分发挥自身所独有的特长,以它特有的“唱做念打”来与影视抗衡。
关键词:新编京剧;蒙太奇;辅助手段
Abstract:The application of montage in the new Beijing Opera is,to a large extent,promoted by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the drama stage. Montage practice in the Beijing Opera stage is not unique,but has come out in various forms,added space-time switch and freedom of image expansion to the Opera,filling it with new aesthetic atmosphere. We should adopt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it. Meanwhile we should also know that the montage practice is only a supplementary means,and to contend with the film,Beijing Opera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its ownunique traditional expertise singing,performing,explaining and martial arts.
Key words:new Beijing Opera;montage;supplementary means
一
新编京剧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话剧舞台的改革创新推动的。
以影视为代表的物质技术力量的进步和发展的需要,使观众对话剧的审美也发生了变化,迫使话剧的创作和演出跳出某些传统的圈子,展开一种全新的自由,正如俄国戏剧大师梅耶荷德所感叹的那样,舞台从此就变成了“充满了种种奇迹与魅力的一个世界,具有了令人喘不过气来的乐趣和奇异的魅力”[1]。戏剧吸收多种艺术的长处并将它融为一体,为舞台演出服务,已成为当今戏剧发展的一大趋势,其中一个种类就是电影。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对电影情有独钟的梅耶荷德就对已确立了独立艺术品格的电影赞赏有加,大胆提出了“戏剧与电影相结合”的口号,他在排演《森林》、《拿下欧洲》、《射击》等剧时,都曾在戏剧演出的过程中直接穿插电影片段,包括在舞台银幕上配合剧情放映电影、采用电影字幕的表现手法等等。在1926年演出《钦差大臣》时,梅耶荷德更将电影里的特写镜头、蒙太奇用来处理一些重要场面,这给舞台形象带来了饶有趣味的清晰性。与此相应,尤金·奥尼尔、布莱希特、田纳西·威廉斯等人也都从电影艺术中吸取了大量技巧,极大地丰富了戏剧的表现力。戏剧要真正实现“电影式”的时空自由,而又不破坏观赏感受,就得在时空切换时快速剪辑,以做到像布莱希特所说的那样“迅速变换场景”。它可以采用“化入化出”形式,以电影化的速度出现在观众面前,也可以在视点上进行互无关系的画面的突然结合,借助蒙太奇等电影手法创造出流畅的戏剧舞台进程。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戏剧“电影化”的探索始于军事题材的突破,其始创者是1980年北京军区政治部话剧团演出的《平津决战》和军委总政话剧团演出的《原子与爱情》。它们在当时较为普遍的“高调”戏剧、“观念”戏剧中,开始重视活生生的戏剧性格的塑造,力图通过蕴涵悲剧精神的英雄主义情怀,诠释一种道德崇高。它们对电影手法的借用,基本上处于不自觉的状态,与题材本身的展示性特征密切相关。《平津决战》直接在每幕(场)戏前插入电影片段,目的是帮助观众了解“平津决战”的历史背景;在《原子与爱情》中,银幕的作用既体现在事件背景的解说上,也体现在诱发人物进入回忆,推出闪回镜头上。它们在空间上与戏剧的叙事空间拼接在一起,虽显得有些突兀,但在当时却也不失为大胆的创新。
话剧的演出除了直接加入银幕(近年来利用舞台上的大型电子显示屏显示时空变化的亦非少数)还广泛运用特写、闪回并间接使用叠化等电影技法,扩展话剧的感召力、增强故事的阐释力和性格的揭示力。话剧的观众尽管还不很理想,但话剧界所做的努力,确实是艰苦卓著的。电影与戏剧相比,虽同为“直观”,但电影语言有更强的可选择性,更为自由,这也就是说,在“形象化”方面,电影作品有它特殊的审美心理对应。戏剧借鉴电影手法,正是为了扩大戏剧艺术的自由度。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戏剧中电影手法的运用,无疑是以话剧的改革为先行的。这种改革是艺术生产力和艺术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以影视为代表的物质技术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瓦莱里在《美学》中所言:“技术上惊人的进步,它们所达到的适应性和精确性,它们正在形成的观念和习惯,确定无疑地使古代美妙的艺术面临一场深刻的变化。在一切艺术中,有一种再也不能被惯常考虑或对待的物质成分,一种不能被我们时代的知识和力量所影响的物质成分。近20年来,无论是物质还是空间和时间,都不复是太古时代的那个样子。我们将会有更伟大的革新以改造整个的艺术技巧并因而影响艺术创作本身,也许甚至实现一种我们在艺术见解方面的惊人改变。”[2]科技手段在艺术中的加盟,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发展艺术的表现形式,扩大艺术的表现空间,让观众获得新的美的形式的观照。有了这种艺术形式方面的自由度,才能更好地表达它的内容意义,使欣赏者的审美意识进入李泽厚所说的那种意味层。
话剧的改革也推动了长期固守自己程式规范的京剧的创作和演出。新编京剧中电影手法的运用使新编京剧增添了时空切换和形象拓展上的自由度,给观众新的审美享受。比如于魁智李胜素联袂主演的大型新编历史京剧《走西口》,在光影氛围和照明切换上吸收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整个舞台显得扑朔迷离,渲染出人物命运的悲剧气氛。中国京剧院根据《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为素材改编的《泸水彝山》,在场景的处理上,既有鲜明的程式,又有借鉴电影蒙太奇手法和时空交错的舞台调度。导演高牧坤对“火烧藤甲兵”的场面调度和武打、布景、设计、灯光均有新意。这场戏中,通过化用电影中的“平行蒙太奇”手法,表现出蜀军与藤甲兵在同一时间里的不同空间中进行的多重厮杀,尤其是利用灯光映射出的火焚场面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湖北省京剧院新编京剧《樊姬夫人》在一片声色绚烂中拉开序幕,光影与布景融合了现实与想像、虚与实结合等多种手法,最特别的是场上6块颇具楚文化风情的大盾牌,既是换场的“幕布”,又是表现剧情的背景,还成为了战争场面的道具。沈阳京剧院新编现代戏《法官妈妈》充分调动了戏曲艺术的表现手法,将唱、念、做、舞、翻与戏剧情节、情感的宣泄、人物的性格刻画有机而较为完美地融为了一体。在布景、灯光的设计方面,则着力运用现代手法,创造出美轮美奂、引发深远联想的舞台意境,十几个场景变换自然,还在舞台空间上使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这些信息充分说明了新编京剧中运用蒙太奇手法,已非个别现象,这使京剧这种传统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
二
追溯起来,京剧舞台上运用蒙太奇手法早已有先例或雏形。
在一次关于京剧的研讨会上,武汉大学教授邹元江提出了“梅兰芳不懂京剧美学”这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他举了《汾河湾》中的一幕作为例子:薛仁贵(谭鑫培饰)在寒窑外面诉说往事,梅兰芳演的柳迎春在里面倾听,按照传统的演法,梅兰芳是背对着观众声色不动的。然而,当时的剧评家齐如山看了十分不满,写信给梅兰芳说,柳迎春应当配合薛仁贵的诉说做出各种表情。这显然是把西方戏剧的标准强加给了京剧,因为中国的戏曲讲究虚实相生,当谭鑫培表演的时候,是不允许梅兰芳表演以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的。但令人吃惊的是,梅兰芳居然听了齐的话,在以后的演出中加入了各种丰富的表情。
笔者认为,梅兰芳吸取了齐如山的建议,确实打破了传统的框框,使京剧表演中具有了两个不同空间画面的组接感觉。有专家认为:按照电影一般的拍摄手段,两人对话,一般先来一个人的“正打”画面,也就是先拍一段说话者之一的正面形象,接着便是另一个人的“反打”,以表示他(她)的反应,再接着是一个交代环境的双人镜头。这种蒙太奇手段现在已经被电影广泛运用,它的用意是很明显的:第一个“正打”镜头是为了突出说话主体,此时的倾听者往往只有一个背影或者干脆淡出画面;而“反打”则是为了突出倾听者。在这一正一反的组合中,电影通过空间的变化,把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切割成了先后发生,实质上是用技术来弥补人眼的局限,满足了人类对于全方位了解“真相”的欲望。由此来反观中国的戏曲,在《汾河湾》中,谭鑫培唱、梅兰芳倾听相当于一个“正打”镜头,“反打”被移到了下一唱段,同样采用了对时间的解构—─这其中的微妙对应不是正好说明两个艺术门类的一线相通吗?观众不会运用所谓精确的思维,去责难寒窑里面的人如何能对寒窑外的人所进行的心理活动(这里不同于有意无意地、比较近距离地听隔壁的人讲话)作出表情反应。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无懈可击地解决问题,而在于促进人们热爱丰富的永不枯竭的生活[3]。鲁迅先生也说过,倘若苛求作品的事实真实,那不如去看通讯报道。列夫·托尔斯泰和鲁迅先生的意思都是说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结合梅兰芳在扮演柳迎春这个角色时的改革来看,这其实是使两个人在不同区间的表演具有了背躬戏的味道。而京剧中的背躬戏与电影中的架话式蒙太奇,是具有相似因素的。梅兰芳在寒窑里面对寒窑外的人进行的心理活动所作出的表情反应,不过是一种表情语言(态势语言、身体语言、动作语言)。一些著名的背躬戏,比如《沙家浜》“智斗”中阿庆嫂、刁德一、胡传魁三者之间的背躬唱,不就包含着应答、架话的形式吗?他们三人站的是实的位置,背躬的心理应答空间则是虚拟的。上海京剧院新编京剧《贞观盛事》中亦有一个蒙太奇画面的处理,饰魏征者(尚长荣)所安排的位置则完全是虚拟的:魏征再谏后不被采纳,李世民独步庭院,心理正进行斗争,后面出现魏征身影,这个身影完全属于李世民心理上的联想。舞台灯光人员利用追光,使观众迅速意识到这是李世民进行心理斗争时头脑中涌现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融入电影手法的背躬戏中,李与魏的“二重唱”中出现了“轮唱”成分。笔者在其他新编京剧中也偶或见过,这种包含着“轮唱”成分的唱腔,大大增强了人物心灵交错的气氛。正如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所说:“上下镜头一经联结,原来潜藏在各个镜头里的异常丰富的含义便像电火花似的发射出来”[4]。
一些鄙薄京剧等戏曲的人,往往嫌戏曲节奏太慢,这实在有失偏颇。从情节进展来看,舞台剧恰恰是最讲究情节集中、紧凑的。当然,新编京剧也已注意尽量加快节奏,适应现代观众的观赏心理。譬如沈阳京剧院的大型新编神话京剧《无底洞》,大胆借鉴了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使戏剧节奏更加紧凑,避免了冗长拖沓的情节,多次于无形中完成了场次转换。获得高度好评的上海京剧院创作的京剧《廉吏于成龙》在编导上也是创意迭出,剧本采取的是“散点式结构”,只有中心人物(于成龙),没有“起承转合”的中心事件。这台戏打破了场次的限制,在京剧舞台上大胆运用了意识流、电影蒙太奇等手法,使戏剧结构很紧凑。普多夫金说:“凡是影片中断的地方,凡是在需要连接的地方——无论这些片段是胶片的各个片段或是动作的各个部分,都必须考虑到节奏这个因素,这倒不是因为‘节奏’是一个现代的时髦用词,而是因为受导演意志支配的节奏能够是而且必须是一个有力的和可靠的造成效果的手段。”(注:普多夫金《论电影编剧、导演和演员》,转自免费杂志在线阅读《新闻爱好者》2007年第22期王红霞《漫论影视节奏》。)而要造成效果,则又必须以观众的理解为验证。 架话式蒙太奇等蒙太奇手段不仅可以使戏剧的情节变得更加紧凑,而且可能产生幽默机智、富有情趣等审美效果。湖北省京剧院演出的大型新编古装京剧《曾侯乙》有这样一场戏:曾侯乙为制造大型编钟,与王后钟玉及公主妩女句均化装成普通人,带优丹(由武生饰矮丑)去找铸钟专家钟颖。舞台上,近台边处,优丹抓住一只鸟(以虚拟动作表示),问曾:“此是何鸟?”曾答:“是南方的一种鸟,叫玄鸟。把它放了!”而在舞台另一头,即舞美设置为上坡处,妩女句正抓住钟颖:“不能把他放了。”指的又是不能把钟颖放了,构成了阴错阳差的架话式蒙太奇,既显出妩女句活泼的性格,也增添了语言嫁接的特殊情趣。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常常运用到对比手法,比如在杜甫的诗中就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等诗句,在电影蒙太奇中也有一种“对比式蒙太奇”。富与穷、强与弱、文明与粗暴、伟大与渺小、进步与落后等等的对比,在影片中是常见的。
在京剧《杨门女将》中我们似乎已经看到对比式蒙太奇。当天波府内喜气洋洋,红烛高烧映寿幛为宗保庆寿的时候,孟怀远与焦廷贵却送来了宗保元帅为国捐躯的噩耗,使舞台气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比。在北京京剧院新编历史京剧《武则天》中,通过权倾天下的武则天与文人骆宾王之间的一段恩怨来折射女皇的一生。全剧围绕“讨武檄文”的传奇故事展开,以正说的姿态讲述历史,唱词、念白具有盛唐气象的诗化风格。剧中人的唱词、念白和身段动作都融入了大量的新鲜元素,受到了戏迷观众的热烈回应。武则天在要求诗人骆宾王为她篆写墓志铭被拒绝的时候,才恍然明白原来她当了女皇依然不可能被社会世俗所承认。该剧出现了这样一组画面:武则天在台前思考,为什么像骆宾王这样的人要骂她、声讨她,社会上有很多人不能接受她;而在武则天扮演者的身后,在“横线构图”上展现出一组画面,意图则是表现结婚、丰收等方面的黎民生活。这里也包含着对比式蒙太奇的因素。
蒙太奇是叫板式蒙太奇。这种结构方法在故事影片中能承上启下,上下呼应,而且节奏明快。有的资料上认为,叫板式蒙太奇就像京剧中的叫板或叫头。这样类比等同是欠妥当的。实际上,电影中的“叫板式蒙太奇”只是借用了戏剧中“叫板”这一名称,其内涵则与京剧中的“叫板”有所区别。要解释叫板式蒙太奇,最贴切的比喻是俗语“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京剧《武则天》中,有一场结尾处,武则天心理活动想到骆宾王,骆出,属于心理想像,接下去一场即回到监狱场面,仍然是骆的表演。这里就构成了叫板式蒙太奇。
蒙太奇的设计,符合人的视觉感受规律。人在观察事物时,根据视觉和心理的需要,总是不断地调整视线和视点,将注意力依次集中在不同的空间范围,以便全面地认识事物。有时候,甚至在同一时间内,人的视觉很可能同时注意到两个不同方面。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看电视,在注意到屏幕上主要画面的同时,也可能注意到电视台在屏幕下方所播放的“过条通知”。观众看戏剧或电影电视的时候,进入视野的虽然是整体画面,而注意中心又常常是有所选择的。如果观众有意注意某个人物,某个细部,则可能将其变成视觉上的“特写”,而让其他人物、景物、场面、画面暂时变为注意边缘。戏剧运用电影手法,强化了画面的分割、切块,将某些人物、细部同时特写出来或分别特写出来。电影蒙太奇的功能就是在镜头的组接中,使镜头之间产生连贯、转接、对比、衬托、联想等关系,赋予画面以新的意义,增加电影的表现力。新编京剧《武则天》在这方面也较为典型,该剧利用众多既古老又新鲜的元素打造了视觉听觉盛宴。比如有一场戏,武则天、骆宾王、裴炎、上官婉儿4人4个位置,既是背躬戏状态,也是画面上的切割、叠化。再如京剧《梅兰芳》中采用了电影蒙太奇手法,让史实中本不在一个空间的人物相见、对话,虚与实都做到了极致,比如与武生泰斗杨小楼告别,与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交往等等用时空概念来衡量都近乎荒诞,但这又都是梅先生亲身经历的,为他以后蓄须明志,息影舞台做了铺垫。这些电影手法的加入在传统京剧中都是很难看到的。
三
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认为电影一定会将取之于戏剧的一切,毫不吝啬地奉还给戏剧。京剧的诞生固然早于电影,但电影吸收了戏剧某些特点后,又反过来推动了戏剧与电影的某些融合,京剧的创作当然也不能不与时俱进。这需要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灯光等演职人员的通力合作。比如我们在新编京剧《华子良》中清楚地感受到利用灯光“暗转”切换、淡出淡入而构成“蒙太奇”的效果。过去戏剧场次利用闭合开启幕子或暗转的时空转接,有暗合蒙太奇的,但不多,一般也不明显。而京剧《华子良》不仅频率高,而且较为明显。如有一场次结尾处,华子良跑步“淡出”,下面则是双枪老太婆带华蓥山游击队队员跑步“淡入”,属于“相似性蒙太奇转接”;此剧还有其他几处“蒙太奇”转接值得研究,编导人员真的是把电影取之于戏剧的一切,毫不吝啬地奉还给戏剧了。
京剧发展的过程是革新─规范─革新的过程。我们无疑需要强调京剧姓“京”,强调京剧的规范,强调其质的规定性。但也有些人借强调京剧的本质特点为名而对京剧的改革表示怀疑,对京剧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也颇有微词。他们认为,京剧有其程式,而且它的生命力更在于唱腔,运用蒙太奇等电影手法,就违背了京剧的本质特点,使这一国粹艺术变得不伦不类。
确实,电影电视可以更多地拥有“视觉合一”的效果,戏剧毕竟不同于影视,即使在新编京剧中,蒙太奇等电影手法毕竟也只是辅助手段,京剧更应该充分发挥自身所独有的特长,以它特有的“唱做念打”来与影视抗衡。当然,京剧因为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也有些蒙太奇手法不宜生吞活剥地插入。比如电影中有“复现式蒙太奇”:从内容到性质完全一致的镜头画面,重复出现(例如张艺谋执导的《我的父亲母亲》中复现“父亲”生前在小学教书的镜头)以至反复出现(比如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地球仪的多次转动,表示时光的推进)叫做复现式蒙太奇。这种蒙太奇总是在剧情发展的关键时刻出现,意在加强影片主题思想或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折。但反复出现的镜头必须在关键人物的动作线上,只有这样,才能够突出主题,感染观众。笔者认为,京剧里的人物回忆或补充交代过去的事情,大都通过唱腔或道白,由于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唱念做打上,因此,一般说来,除了心理视像上再现某个人物外,很难安排重复性的具有情节因素的“闪回”场面,京剧的场面如开弓之箭,一般是有“去”无“回”的。
对于新编京剧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我们仍然需要以积极的态度给予支持。鲁迅先生当年谈到创作中新的尝试时说:“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注:鲁迅《且介亭杂文》(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卷6第16页。)。
京剧的特点也不应该神圣化。京剧的改革要符合规范,但这个规范是发展着的、变化着的规范,不应是凝固不变的规范。现代戏剧观众对旧的传统模式可能产生审美疲劳,希望有新的技法,希望形象的丰富性,他们对于舞台上一些新的手段的插入,视觉的敏感性及其识辨力、理解力已远远超过过去。
创造学的原理告诉我们,新的创造往往是根据信息的切割与结合来展开。在作为创造方法之一的创造工程理论中,戈登认为创造过程是由“把不熟悉的东西变成熟悉的东西”和“把熟悉的东西变成不熟悉的东西”两部分组成的。前者重视分析,后者重视结合。在创造过程中,分析与综合两方面都是重要的,尤其是综合更重要。创造是对可能性的挑战。从通常的思考过程中飞跃产生的思想,一般来讲是独创的东西,也有的是深度思考的延长。创造是异质素材的新组合,是人类智慧行为的一种,通过对储存的信息资料做出选择和判别产生的有价值的东西。参照遗传学的原理来看,戏曲改革是个“转基因工程”。其中本质的特点是遗传因素,但又有变异因素。在遗传学上,变异是指同种生物世代之间或同代之间的性状差异。变异有遗传的变异和不遗传的变异之分。前者必须通过遗传物质的改变,包括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一般是不定向的,称不定变异。后者仅由环境条件直接引起的变化。新编京剧是从旧的价值体系向新的价值体系的变异,是将异质的信息或事物用至今未有的方法结合起来,产生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的过程。好像阿尔米达(西方神话中的女巫之名)的魔杖,从不毛的荒野里召唤出一个花香鸟语的春天。
在我们这个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更加多元化的时代,戏剧的改革也必然是不断流动变化的。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推进力量,那就是人类审美观的演变和科学技术的催化。一些新的艺术形式、新的表现手法、新的传播媒介、新的艺术产品,有可能在它刚一出现的时候,就得到赞美和认可,也有可能从不太习惯逐渐变得习惯,转而变为欣赏品味了。
参考文献:
[1]J·L·斯泰恩.梅耶荷德论戏剧[M]//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3.象禺武文,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116.
[2]许诗焱.影视时代西方戏剧的演变[J].艺术百家,2000(2):75.
[3]列夫·托尔斯泰.致彼·德·波波雷金[M]//文艺理论译丛:第1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224.
[4]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