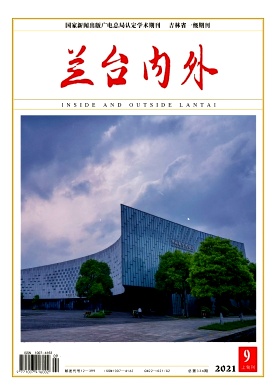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与出路
张玉林 2006-01-22
1,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后的问题
自两年前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许多担心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透过表面的“达标”我们会发现,农村的教育状况并没有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在并没有根除导致问题的根源而又遭遇农村税费改革等新的制度环境时,它变得似乎更加突出了。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这一含糊的语义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是,在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区域还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少年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充分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来看,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10万人。这庞大人群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在农村,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普及”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冲刺”的结果,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弄虚作假”这一经典式的法宝。而不择手段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后遗症,比如许多乡镇所背负的沉重的“教育债务”,此外还包括入学率的下降和失学率的反弹。两年前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已经通过“普九”验收的1242个县中,失学率超过5%的有209个县,超过10%的有63个。在中西部,初中生辍学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而湖南省有关部门今年夏天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
第三,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3791.5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67.6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这些事实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员们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镜子。
2,城乡教育对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农村教育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同城市的比较。这方面的直观感受往往会让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从北京市某所花费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小学,到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存在的“危险校舍”;从城市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去培养其子女的“综合素质”,到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要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一筹莫展;从城里重点小学或“实验小学”的教师们到“新马泰”去度假旅游,到广大农村里的多数教师领不全他们每月的薪水……新世纪的天空下“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两幅图景,的确显得“光怪陆离”,让我们看到城市教育的虚假的繁荣和农村教育的真实的危机。
不过,仅凭直观感受来评说城乡教育差距可能会被一些“权威人士”指斥为以偏概全。为此我这里提供两个系列的重要数据,即城乡各教育阶段升学率的差距和城乡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以此来进行全面的观照。
就教育机会的差距而言,在小学阶段,除了因高度残疾而无法入学的极少数情况之外,几乎100%的城市学龄儿童都进入了小学,而农村每年尚有100万左右的儿童没有入学。在初中阶段,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与城市的小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率为101%)升入初中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只有64%,其中贵州、广西和西藏三省区农村不到50%.到1999年,农村的升学率上升到了91%,但低于90%的省区仍有15个,其中贵州和内蒙分别为72.4%和75.7%,西藏更只有38.1%.全国则有130万的农村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成为“劳动力”。
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农村则从22.3%降到18.6%,两者的倍数差从1.8倍扩大到3倍,绝对差从17.7个百分点扩大到36.8个百分点。而许多省区内部的城乡差距要大于全国的情况:1999年,城乡差距超过3倍的省区达15个,超过4倍的有5个。安徽和贵州省的城乡差距都在3.6倍(分别为55.7%:15.4%56.2%:15.4%),湖北达到3.9倍(71.4%:18.4%),山东(72.3%:16.8%)和河南(57.4%:12.9%)则分别达到4.4倍和4.5倍。在上述省区,城市的升学率都超过了全国城市的平均数,而农村的升学率则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数。
关于大学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可以用学生的城乡分布来对比。据对1989全国高校录取的61.9万名新生的统计,来自农村的学生占总数的44%,城市的占56%.以各自出身的人口母体为基数来换算,可知当年大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为4.9倍。而随着高中阶段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和近年来高等教育“高收费”的影响,相信这种差距90年代末之后进一步扩大了。不过,由于缺少全国的数据,我们难以给予量化。而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99年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的情况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只有902人,占总数的17.8%,这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计算可知,在这两所生产“精英中的精英”的著名学府,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差距,若以城乡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为基数,可以量化到7.7倍;如果以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为基数,则可以量化到10.3倍!
让我们再来看看城乡之间因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在校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它在相当程度上涉及教育质量问题。
就全国范围而言,1993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为476.1元,农村为250.4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941.7元,农村为472.8元。差距分别为1.9倍和2倍。到1999年,两者的差距都扩大到3.1倍,绝对金额分别为1492.2元:476.1元和2671.2元:861.6元。
如果将比较的单元下放到省级行政区,城乡之间的极差将更加突出。1993年,上海市(包括所属郊区)小学生的人均经费高达879.2元,而安徽农村只有125.6元,相差7倍;北京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2157.7元,贵州农村仅为214.1元,相差10倍以上。至1999年,极差进一步拉大,小学生的城乡差距扩大到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生的城乡差距则扩大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农村416.7元)。
而同一省区内部城乡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巨大差距。以贵州为例,在整个90年代,其城乡小学生的人均经费差距都在3倍,初中生都在4.2倍。郑州市1999年小学生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河南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滑县农村的14.7倍;关于初中生的情况,最高的新乡市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 3,教育财政改革:“以县为主”的局限
应当看到,城乡之间的巨大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城乡经济差距的结果。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是教育资源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即“分级办学”制度的必然归结。
自1985年实行的以乡镇为主的“分级办学”制度,作为一项至为重要的公共政策,未能起到统一调配资源以确保全体适龄人口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作用,而是在单纯强调发挥地方“办学积极性”的逻辑下,将应该由政府、社会和家长共同承担的义务教育的“义务”主要转嫁给了农民,将理应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主要转嫁给了乡镇和村。其结果是,不仅给广大的农村和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985—1999年间向农民提取的“教育费附加”总额超过1100亿元,1993~1999年间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超过516亿元;乡镇财政则普遍成了“教育财政”——,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它不是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教育层面上缩小,而是将其扩散和放大,从而造成了农村教育的迟滞和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农村少年儿童的失学和教师工资的大面积拖欠也随之变成了几乎不可逃脱的“宿命”。
所幸的是,在“分级办学”制度运行了16年之后,它的弊端终于得到了承认——虽然是一种谁也不负责任的默认——。去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今年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强调要实现两个转变,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又在相关文件中对“以县为主”作了详细规定,其核心是县级政府负有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即通过调整本级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经费预算,合理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做好“三个确保”(即工资发放、公用经费、危房改造及校舍建设),而乡镇不再承担义务教育投资责任的重压。新体制运行一年之后,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全国已有75%的县市实行统一发放教师工资,今年内则要求全部推行到位。
上述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改进。在县这一级更大的行政区域内调度教育资源,较原来的制度有利于提供农村教育资金,有利于减轻乡镇政府和农民的负担,也有助于缓和乡镇政权因向农民摊派教育经费而造成的紧张和冲突。不过,进一步的分析会使我们发现,县一级财政的实力决定了这一新的制度的先天缺陷,由此不能抱过大的期望。
在现有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财政所占份额很小,加上乡(镇)级财政也只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20%(中央政府占51%,省和地市两级占27%)。在现有的2109个县级行政区域中,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不足600,包括574个国家级贫困县在内,财政补贴县多达1036个(均为1999年数据)。大部分县连维持“吃饭财政”的水准都困难,一些县全年的财政收入甚至不够用于教育的支出。
基于此,绝大多数县级财政显然无法担当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责任。进而言之,“以县为主”仍然没有摆脱教育上城乡分割的格局,因为县级行政区域仍然属于“农村”,从乡镇为主到“以县为主”,只是在农村内部调整教育资金的汲取和分配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教育的基础条件,缩小近20年来越拉越大的城乡教育差距。从对这项制度的最大预期来说,“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可能缓解一县之内教育上“贫富不均”的情况,但却难以改变一个市或地区内部、一个省区内部、以及全国范围内极端“贫富不均”的局面,无法消除城乡之间教育的天壤之别。
中央政府似乎试图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对贫困地区教育援助的力度来解决“以县为主”后农村教育财源不足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努力远远不够:“十五”期间总的投入额度只有330亿元,包括总计50亿元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资金;每年50亿元用于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的专项资金;30亿元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资金(2001-2002年)。这些资金只相当于数年之前国家和地方政府一年内对农民收取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的收入。而即便将所有资金——不再出现中途截留——都用于国家级贫困县,每县每年能够分得的部分也只有1000多万元,最多能解决“吃饭”问题。有鉴于此,有必要采取更大的举措来加以调整。
一是从教育平等和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理念出发,限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水平和生均公用经费、教学设备的最大差距,以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条件的改善和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差距的缩小。参照目前的现状,生均公用经费差距在全国范围内不应超过2倍,在同一省区内不应超过1倍,教师工资水平也应以不大于上述倍数为宜。当然,确定最大差距并非要将城市中小学的现有条件和教师收入砍下来,而是大幅度提高和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
二是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将过去十多年间颠倒了的权利义务关系彻底扭转过来,明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作为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以县为主”。中央应承担义务教育投入的50%左右,省和地市两级承担30%,县乡两级承担20%(其中县承担15%,乡镇承担5%)。中央政府承担的份额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省和地市两级也是就各自管辖的行政区域整体而言,并不意味着平均分配,而是结合前述第一条原则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
应该承认,在传统的城乡分治的思维和制度空间内,并不容易做到这两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调整城乡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依然在老框框里做小幅度调整,也就难以彻底改变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以及它同城市之间的令人感到残酷的差别,并且有可能拖垮普遍贫弱的县级财政——就象已经“拖垮”了的乡级财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