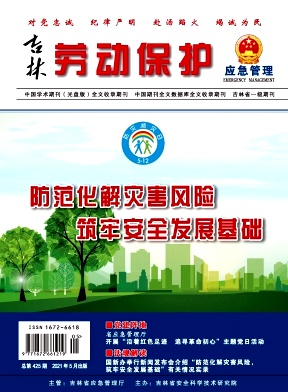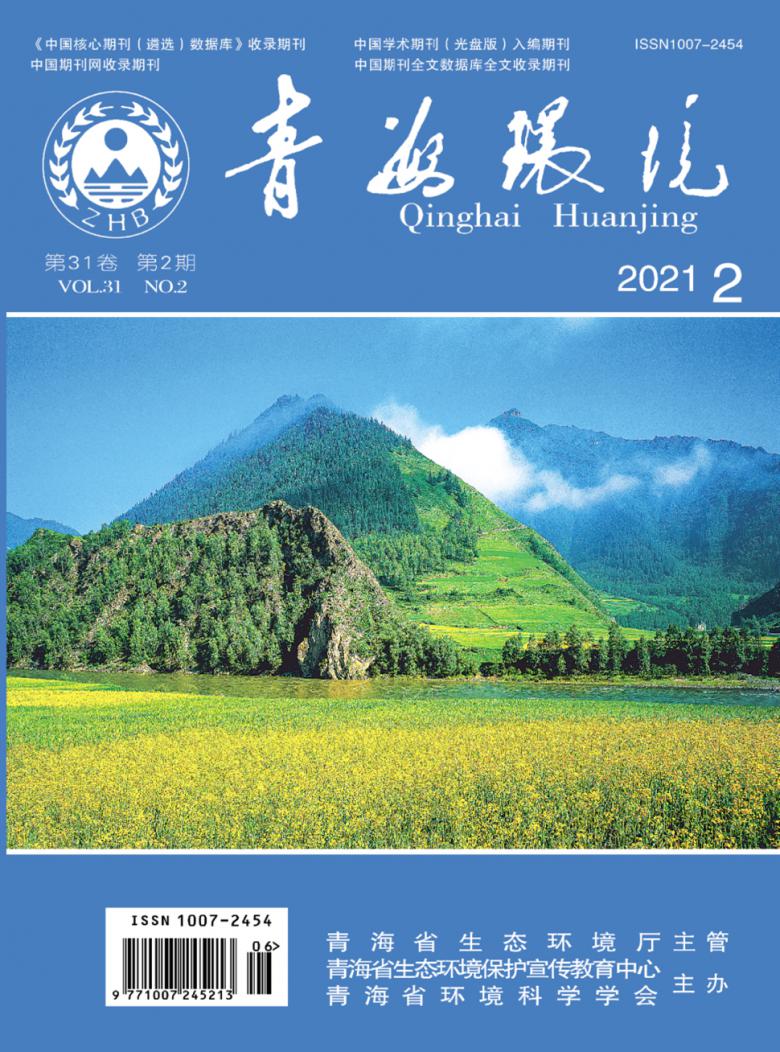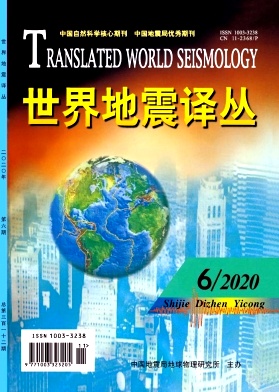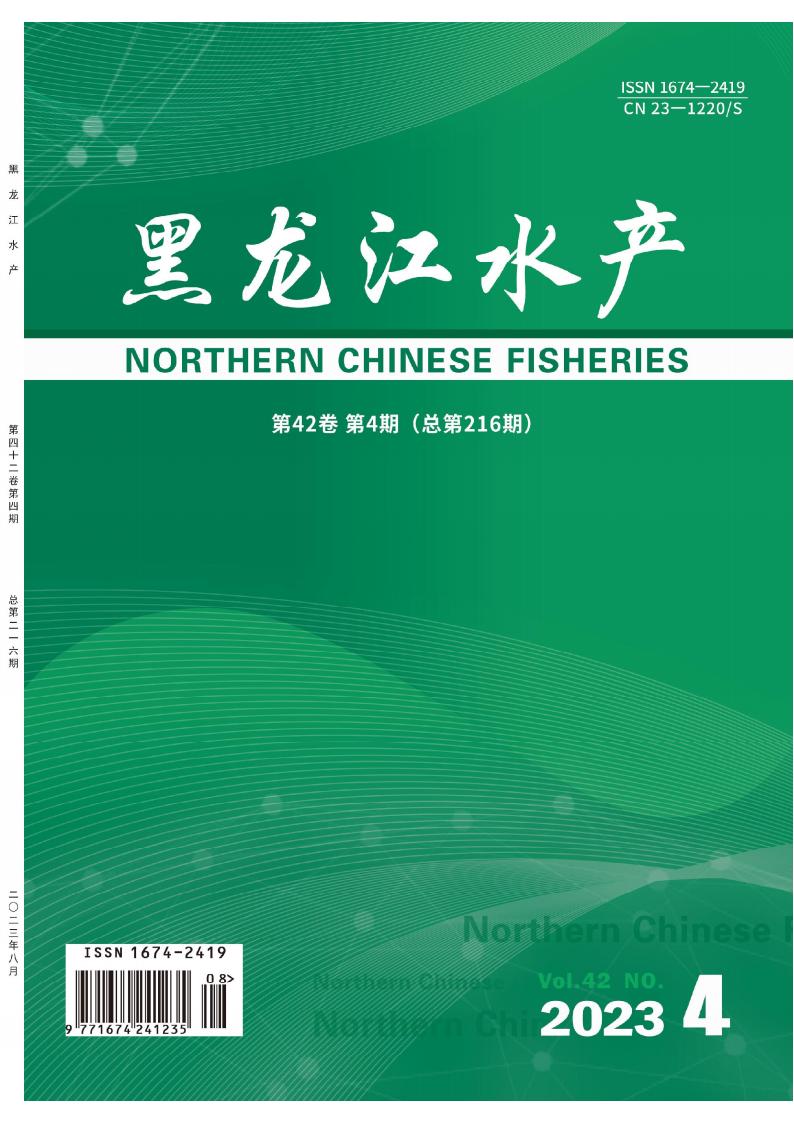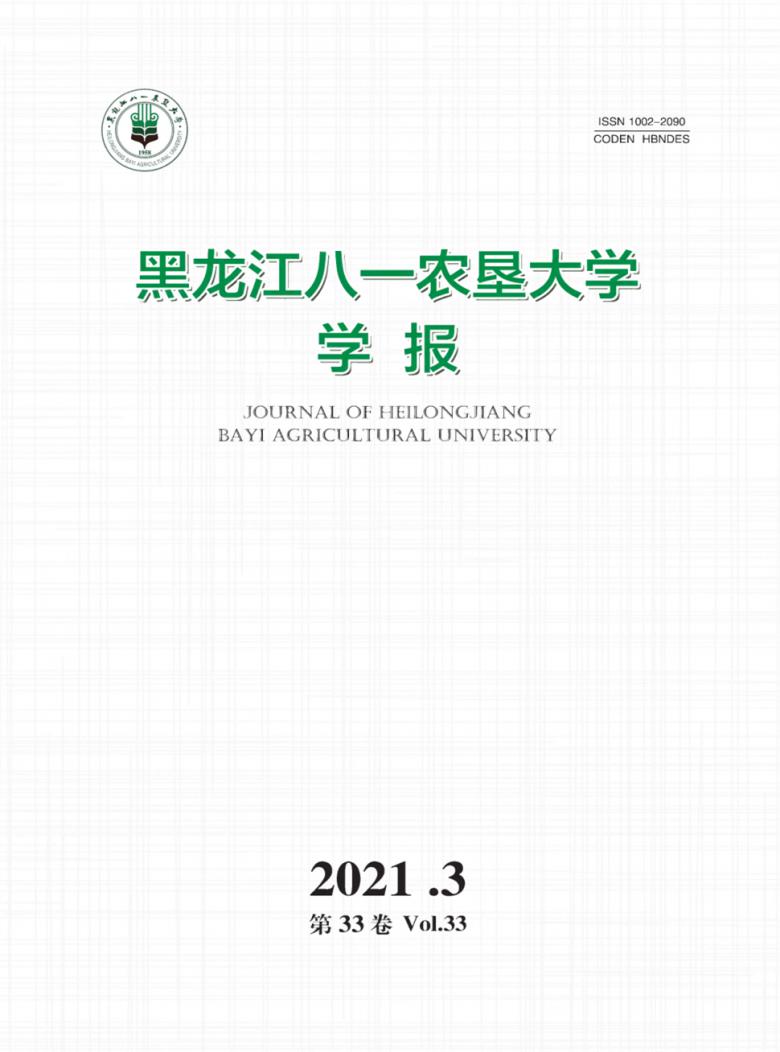中国近代宪政的文化基点:儒家群己观
未知 2010-08-12
关键词: 儒家/仁/群/正
内容提要: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内在超越的,因而,“己”与“人”之间是均衡关联的反向性关系结构。从“人”的视角看群己关系,即“仁”。“二”加之于“人”表明,“仁”就是个体拓展并融入整体,而且这一融合只能通过共同语境下的人际交往才可获得。从“民”的视角看群己关系,即(被君)“群”。民可以“学”为介,通过修齐治平而成人、成圣;不然,民亦可被君主教化,通过“安身”与“交心”的共赢交易,群聚于君之下。从“政”的视角看群己关系,即“正”。其中,民、人、君都是“大一统”政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借助“学”(习)和“修”(养)可以实现从民到人到君的转化,但无论是民、人还是君,都不需要也不应该有明确的“自我”疆界,而应通过心与心、身与心的交换融合成一个统一体,并在其中各安其位。
每一种文化都要解决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的来源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在于,没有泾渭分明的超验世界与现实世界,因此与二元的、外在超越的西方文化不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内在超越的。进而,一个内在性宇宙观,在认识论上所使用的一定不是西方的分离性概念,而是反向性概念。该反向性表明有重大关联的概念实际上是均衡地关联着的,彼此都要求充分的接合。举如“阴阳”就是一对相互内在性和均衡关联的概念。反向性概念表明了这样一种关系:每一方的实现都需要以另一方为必要条件。“左”需要“右”,“上”需要“下”,“己”需要“人”[ 1 ] ( P119 - 21) 。这便是传统文化界定“人”以及“人与群体”关系的哲学背景。
一、人者,仁也
中西文化对“人”的理解和设计是不同的,这里不可能也不需要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比较。我想借助一个简单的例子,获得对中西文化中人的观念的印象主义式的把握。先看看弗拉斯托斯呈现的西方文化中的“人”:
如果我看到一个陌生人面临淹死的危险,我在去救援他之前,不大可能向自己提出有关他的道德品质如何的问题,在这里我的义务是把他作为人对待,把他当作处于这种境遇中任何一个人一样来对待,而不是要把他作为一个善人来对待。(转引自[美] J. 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现代社会哲学》,王守昌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值得玩味的是,孟子以一个非常类似的例子,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了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人”: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仁义礼智,非由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弗拉斯托斯是从面临淹死的被救助者的角度来理解“人”的,“人的价值”是绝对的、去道德性的。因此“‘人的价值’本身,并不标志什么属性,有如用‘力量’来标名力量,用‘红色’来标名红色一样。这样就可以对‘人的价值’作出最佳的解释。在赋予每个人以人的价值时,我们并没有把什么属性或系列的性质归因于他,而不过是表明一种态度———尊重的态度———就是对每一个人里面的人性的尊重态度。”相反,孟子说的“人”并不是将入于井的孺子,孺子是用来型塑有着“四端”之心的救助者的,后者才是孟子理解的“人”,即作为道德性存在的“仁人”。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先有我而后有孺子,我是通过救助孺子而成就的,并因“仁”而与孺子合为一体。这即是所谓的“人者,仁也”。与弗拉斯托斯绝对的、去道德性的个人泾渭分明。
作为道德性的存在,“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和特征[ 2 ] 。从文字发展史看,“仁”字出现较晚,至《诗经·国风》时代方才成形,因此是先有“人”而后有“仁”,“人”是“仁”的母体,“仁”为“人”所派生[ 3 ] ( P1390) 。而且,在包括《论语》在内的古籍中,“仁”、“人”常混而不分[ 4 ] 。从字形结构分析,“仁”作“[人二] ”,通常理解为,仁是由“人”和“二”组合而成,就是“二”个人之间,是相互内在性、相互关联的人和人之间的统一体。但也有研究认为,两横是金文中常用以作为重文合写的符号,并非表示数目的“二”,因此仁是“人”的复体字,即“人人”,其中前一个“人”用作动词,整个意思就是“使人成人”。而且,“人人”中的“人”是与非人相对而言,并非与“己”相对[ 3 ] 。
郭店竹简的出土,为“仁”的字源学说引入了新的信息。在郭店竹简中,仁字均写作“[身心] ”,表明“从人从二”并非仁字的最初构形。“[身心] ”的构形“从身从心”,与“身”是指“(他)人的身(体) ”还是“己身”对应,有两种解释:前者认为,“[身心] ”是指将他人放在心上,也就是“心中思人”,与“仁者,爱人”同义[ 5 ] ,表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后者认为,“从身从心”是指思考和反省自身,表现为“克己”、“修己”、“成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成就自己、实现自己、完成自己[ 2 ] 。
“[身心] ”是对“[人二] ”涵义更为具体和形象的描述,二者包含的两层涵义——— (1)反省己身,以使人成人; (2)心中思人,并在人与人的相互内在、相互关联中达成人我融合、人我一体,乃至“万物一体”之仁———都不是对立的,而是展示了“仁”的涵义的两个方面:内在的德性与外在的践行。克己与修身并不是真正地要让“自我”成为对象,而是具有更为远大的目标:“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 。可见,个人没有,也不需要有牢固的自我疆界,而是处在一个人与我相互渗透,彼此依赖的场境中。在这个场境中,你的心有多大,你的世界就有多宽广。
修身是一段追求德性存在的“任重道远”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从另一个方面说就是一个去“我”的过程[ 6 ] ( P1105 - 117) ,而且去“我”是为了从自我走出来,走到一个家族、国家乃至天下的广阔空间中去,是“舍”我而“得”天下。因此,去“我”得越彻底,拥有的回馈就越多,这正是“仁者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的真谛。也就是在这“舍”与“得”之间,体现了以“仁”来理解的“人”的吊诡之处:个体虽然不是独立的,但也没有被完全消解。这就是内在超越的中国文化的体现。“我”与“他者”也是一组反向性的概念。一方面,“二”加之于“人”表明,“仁”只能通过共同语境下的人际交往才可获得。“仁”是自我的转化:从只顾一己私利的“小人”锻造为领悟深刻关系性的“人”。因此说,“仁”是一种整体化过程,超越了人的自我疆界。不过,这种超越不是西方式的外在超越,而是内在的,是人的自我超越。于是,另一方面,个体在“仁”中不是简单地接受他人而放弃自我,而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在“二人”的语境中做出反应[ 1 ] ( P1136 - 138) 。通过将自我投射到他人的境遇中,克服或者说超越了自我的疆界和局限性,因此,个体不是消解了,而是延展了。在这个意义上,“仁”即成人,就是个体拓展并融入整体———一个人与人之间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与自然的人通过社会契约和自然法则构建的社会秩序有着根本的差异[ 6 ] ( P16、65 - 66) 。
当“将‘仁’定义为某种整体化的成人过程,其中,个体将他人切身之事完全视为己所关心之事,且以一种为整体的善服务的方式行事”时,我们便进入了“公”的世界———一个“仁人”与“仁性社群”共存共生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这就是《礼记·礼运》中最理想、最浪漫的表达: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这里的“公”脱离了政府、朝廷的范畴,是关怀普遍、全体的价值观,也是平等对待事物的心态,更暗指着天下为天下人所有的观念。在这个涵义的映照下,“私”便失去了正当性,成为应当压抑、去除的对象。在公私的对立中,中国人将心灵安顿在了“大公无私”之上。根据陈弱水的梳理,这个意义上的“公”的具体所指可以大到指称天地所负载的一切,小到指称个别邦国或君主的意志与利益,常指的则是儒者心目中的一般人民的福祉。而且,“公”虽然是人人都应该追求的价值,但是它主要是对君主和官员的要求[ 7 ] ( P177 - 83) 。
每个人都秉持着“克己奉公”、“推己及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训导,因此,在结构上就决定了“个人”不应该有明确的“自我”疆界。自然,在“大公无私”的领域以外也很难有合法的“私”范围[ 8 ] ( P1303) 。通过“仁”与“公”,人与人之间,即“二人”(集体)之间“身心交换”,实现了人我不分的交融与协合。
二、君者,群也
就像在古希腊城邦中,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的人仅指“公民”,而不包括奴隶和女性一样,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人”也是特指拥有文化的士大夫阶层,而不是普通的“民”。因此,人与人之间利益的互融协合,并没有整合进“民”的利益。“民”的利益的整合是在两条线上展开的:一是,以“学”为介,实现“民”向“人”的转化;二是,以“民本”为介,达成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
“民”指的是未脱离蒙昧、愚昧因而未能“成人”的人,即所谓:
民之号,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则何故以瞑为号? 以霣者言,弗扶将,则颠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而不可谓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善质,而未可谓善,与目之瞑而觉,一概之比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民”所处的是一种“卧幽待觉”的蒙昧状态,它保留着通过“觉”而一跃为“人”的可能性。儒家还为此设计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学。以《学而》开篇到《尧曰》结束的《论语》指示的就是学以至圣之道。现实中贫寒子弟通过寒窗苦读而出“人”头地的鲜活例证,更为从“民”向“人”的转化架起了一条虽不宽阔却很结实的桥梁。此外,“民”能向“人”转化,也是因为儒家所设计的“人”的开放性。与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天生的政治动物的人,所构建的封闭的公民社会不同,儒家的“人”不是天生的,人之为“人”是自我修身和社会化的结果。人之为“人”是人“为”的而不是即“是”的;它是现实的而非赋予的[ 1 ] ( P1169) 。而且,“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可见“为仁由己”(《论语·颜渊》) ,不假外求。“民”若通过修养功夫而成“人”了,便进入了人与人之间的互融协合;若未能成“人”,责任也主要在自己,于是自然会放低对统治者的要求,这便是民本和民生思想的缘起。
此外,“民之为言也,瞑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新书·大政下》)如果“民”没有通过自学成人,那就只能成为被教化的对象了。实施这种教化的便是“政教合一”的君主。为君之道的一个根本就是善于使民“群”: 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篇》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春秋繁露·灭国》)
众不亲安,则离散不群;离散不群,则不全于君。(《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君要使民众亲安并群聚在其周围,关键在于“群生皆得其命”之后的民心归往。君主必须“得民心”,因为,根据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民本主义思想,通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的“天”与“民”的转化,得不到“民心”就意味着丧失政权的合法性,就会成为革命的对象,这即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如何“得民心”呢? 答案仍然是“仁”,即为政以德。德就是仁德,也就是施仁政。如何施仁政呢? 以心换心,即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 。百姓心系何处? “民”是未能转化成“人”的蒙昧之人,非纯粹的道德性存在,因此对于“民”来说更为主要的是一个“身”的存在,主要关心的便是于生存必需的衣食住行。故此,对于君主来说,心系百姓就是要关爱他们的疾苦,使饥者得其食,寒者得其衣。如此,安顿了民众的“身”,也就笼络了民众的“心”;笼络了民众的“心”,也就得到了“天下”。可见君民之间,与其说是以心交心,不如说是在民生主义思想下的,民众的“身”与“心”的交换。这就是儒家圣贤一直教导的“民本”思想,或许也正是早期将“仁”字写作“[身心] ”的深刻用意所在吧。君主以民为本,对民来说“身”得到了安顿和照顾,对于君主来说得到了“民心”,并进而得到了天下。民与君相互补强,各得其所,是一种真正的和谐统一,因此说“民本与尊君是‘一对’( double)而非‘两个’( two)的关系”[ 9 ] ( P110) 。遵循民本的思想,君与民的利益一合两美,恰似鱼与水、水与舟、骨与肉的依赖关系。
三、政者,正也
通过人与人之间、君与民之间的“交心”,以及民以“交心”给君主获得君主对自己“身”的照顾和安顿,君主基于民本的思想以关怀民生为策略,为代价,获得民心,进而得天下,利益在这样的交织、互惠中得到了整合。在此基础上,传统儒家所规划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形态必然是强化自下而上的利益整合,达成自上而下控制的权力结构。而且,因为利益是整合的,所以权力结构必定是一元化的,否则,便只能称为“乱世”,必须拨乱反正,甚至不惜借助革命的手段,使政治由多元化向一元化回归,利益复又得以整合。赫伯特·芬格莱特将儒家“对于一元的、肯定的秩序的信守”形象地比喻为“一条没有十字路口的大道”[ 6 ] ( P118) 。这就是儒家传统文化提供给我们的政治图景:治乱循环的“大一统”。
“大”是动词“尊大”的意思,即“推崇”,大一统就是“推崇一统”[ 10 ] ( P1327) 。“一统”就是“政”的本义和精髓。
首先,从一系列的“问政”中,可以得知“政”与“正”相通:
(鲁哀)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政者,正也。关于“正”的涵义,《说文解字》曰:“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徐锴《说文系传》曰:“守一从止也。”就是说,“正”有两重涵义:一是守一,二是从止。意思是,只有在“定于一”的局面下,“乱”才会止,乱止即治,治即正,正即政。于是便有梁襄王卒然问孟子:
问曰:“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又问:“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再问:“孰能与之?”对曰:“??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定于一”就是基于利益整合的“一统天下”,而要达成“一统”的政治,既非单纯的从上而下的强权控制,也不仅是自下而上的立元正始,(举如孙隆基认为“一统”是从上而下控制的权力结构,相反,蒋庆认为“一统”是自下而上的立元正始。其实都有失片面。中国的哲学是反向性概念之间的相互内在性和相互依赖、相互转换。参见[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页;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28页。)而是上下相互内在性的交织:君主自上而下的福泽广被,民心自下而上的归集,共同成就了自上而下的权力统治。利益和权力都达成“一统”之后,对于每一个参与者来说,其责任就是“拥有自己适当的‘位’”[ 1 ] ( P1102) ,并担当好这个角色。
“从一而止”也好,“一统”也好,这“一”要从哪里寻找呢? 从理想的王政来说,“一”就是“仁”,“天下归一”实质上也就是“天下归仁”(《论语·颜渊》) 。而“仁”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意象化的德性,它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一个象征或载体,这就是君主的仁德之心。君主以心存德,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照顾民生(身) ,则众心归往,天下定于一,这便是为政之道。可见,无论是原生态的( raw)人通过“克己复礼”而成“人”,还是为君、为政之道,“仁”都是一以贯之的轴心意识和行为。
借助“仁”,己与群建立起了一个动态平衡的有机体,每个人通过“学”和“修”寻找自己的序位。儒家对此有更直白的说法:“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普通的人,即民,就是器,是被使用的人;而道德上获得了自我实现的仁人,即君,则具有统御或使用他人的能力。如此,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被巧妙地转化为了“仁”德有无或多寡的关系,是蒙昧之民向被视为“仁”的象征和载体的君的归往。加之,“为仁由己”,那么一个人在“民- 人- 君”的序列中处于什么位置,是统治人还是被人统治,关键都在于自己对“仁”践行的程度,因此整个为政之道便是在对“仁”的向往、践行、膜拜和归往中,达成了整合与统一。这样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智慧为近代所传承,不管近代学人对传统文化抱持的是接受还是批判的态度。
结语
关于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艾宾斯坦(W. Ebenstein)认为:“虽然去论辩某种类型的哲学体系总是反映某种相应类型之政治体系,也许是困难的;然而在基本的哲学观与政治观之间,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相应性(parallelism) ,此种相应性部分是逻辑的,部分是心理的,而部分是历史的。”(转引自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我想,中国的哲学同样规定了中国政治形态的特质。
近代中国百年宪政之路,也关怀并致力于促进个人自由的实现。何谓个人自由? 有两个理解维度:一是,“人”这个概念或种属本身,即人之为人所应有的德性和价值;二是,“人”与人、社会、国家的关系,即广义的群己观。由此,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对个人自由的理解和界定,不是只有西方一个标准。中国的哲学、文化、历史,对“人”以及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独特塑造,是中国近代宪政的理论基点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宪政理念的一个显要特质。
注释:
[ 1 ] [美]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2 ] 梁涛:“郭店竹简‘[身心] ’字与孔子仁学”,载《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2005年第5辑。
[ 3 ] 李景明:《“仁”辨释》,载《孔子儒学与当代社会文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会、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编,齐鲁书社1991年版。
[ 4 ]《经传考证•论语》。
[ 5 ] 白奚:“‘仁’字古文考辨”,载《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
[ 6 ] [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7 ] 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 8 ] [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9 ] 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10 ]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