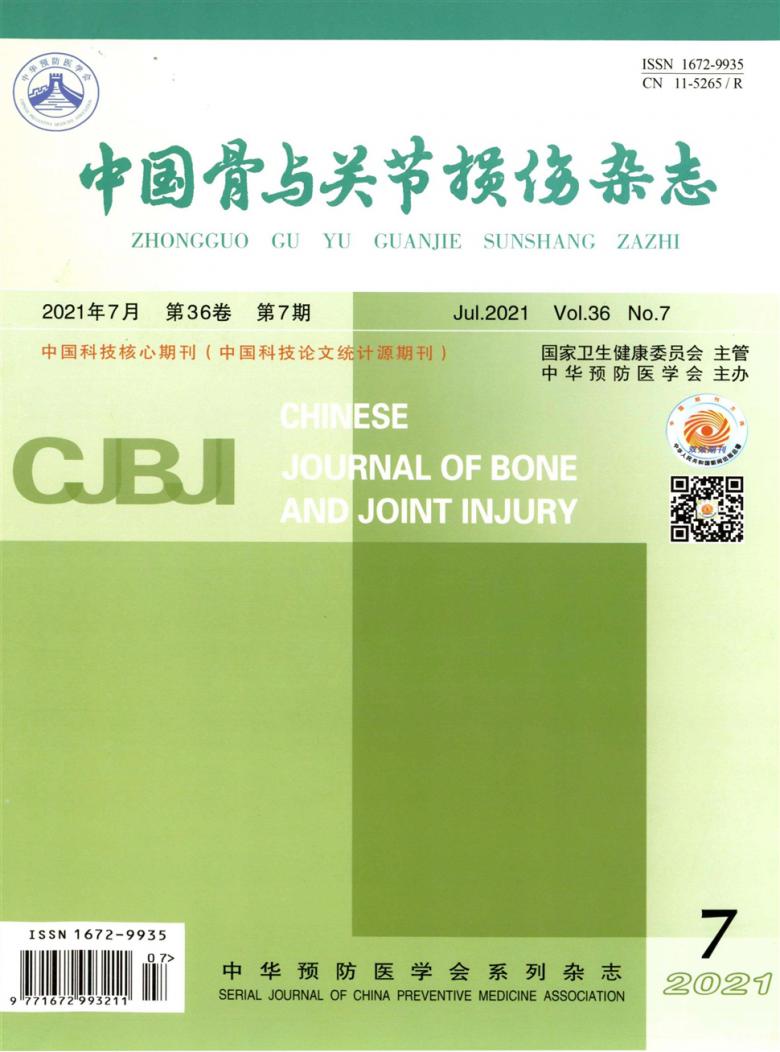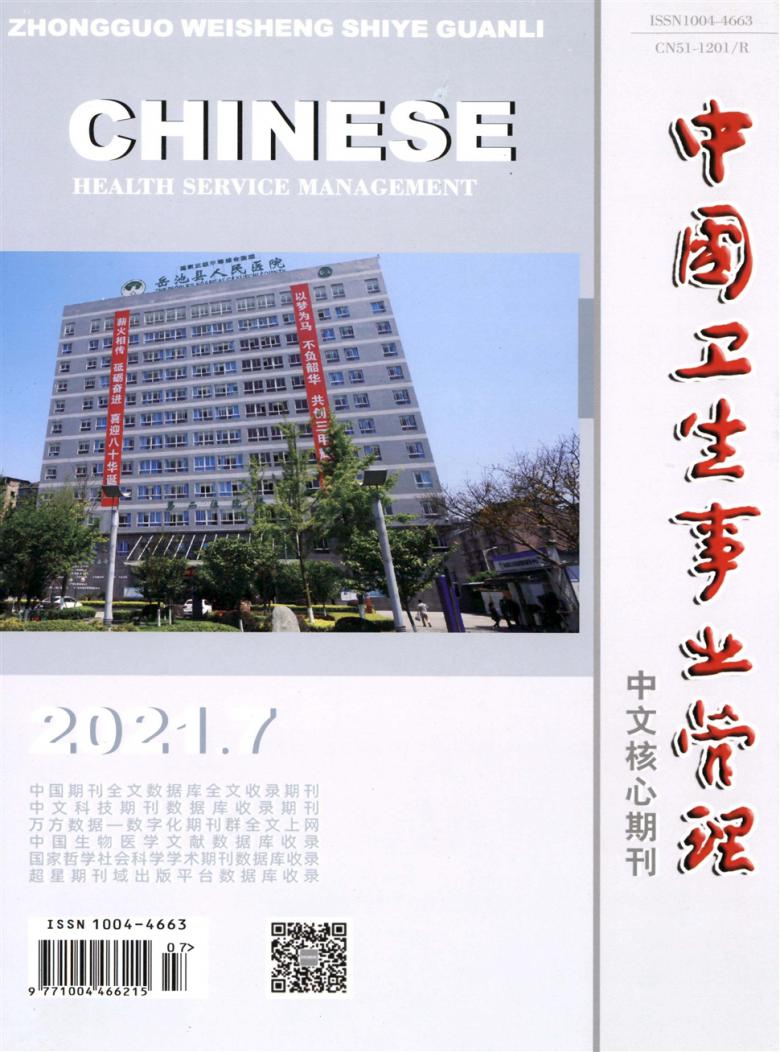关于反思“国民性”:儒家政治哲学与“国民性"论题的产生
韩明港 2012-01-18
摘要:“国民性”论题本质上是对“强国之路”的设想,是以改造“国民性”的方式通达“现代强国”、摆脱民族危机的路径规划,因而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古老的思想的指引下,沿着“立人”而“立国”,“新民”而“新国”的思维定式,“国民性”论题被生产出来。认真清理“国民性”论题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关系,对我们反恩百年来的“国民性”论题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民性”论题是一个贯穿了百年文学史、思想史的重要命题,对这一命题的思考、反省也一直是学界重要的致思方向。但是在众多的相关探讨中,“国民性”论题的生成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关系还没有被深入而有效地清理,对二者深层次关联的理解与辨析,却真切地影响着对“国民性”及相关问题的思考,无论是思考深度还是判断的有效性。
一、“国民性”问题的浮现与延续
戊戌变法前后,对国家积弱积贫之原因的分析开始集中到“国民性”上。1895年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认为“国之贫富强弱治乱者,其民智、民力、民德三者之征验也”,直接把国家“贫”、“弱”、“乱”的现状归凶于民智、民力、民德之低下,“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要救国图强,则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强”这一标题明确地标示着严复的撰文指向:分析国家贫富、强弱、治乱之原因,寻求国富、国强、国治的路径,
1902年,粱启超的《新民说》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也就是“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提倡公德品质,尚武精神,权利与自由,民族主义和国家等思想,试图“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寻求立国之道,进而得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结论,并且,梁启超毫不隐晦地说是源自“大学新民主义”。梁启超的论说影响极大,郭沫若在“五四”之后回忆说:“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弟子——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时经常思考三个相关联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后来鲁迅明确提出“立人”的解决办法:“根柢在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只要“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认为,当由“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的“摩罗”诗人“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诗人”握拨一弹”,国民“心弦立应”,“灵府朗然”,“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以此“先觉之声”,“破中国之萧条”,终“国民精神发扬”,“大其国于天下”。同时鲁迅反对不察“根柢”,误以为“黄金黑铁”、“托言众治”可以强国的观点和做法,认为这些皆是“现象之末”脱离了事情的根本,甚至为害尤烈,因为“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性而排众数”。精神张,自觉至,内曜外华,是第一位的。因此,鲁迅呼唤“强力意志”和“摩罗诗人”,“震吾人之耳鼓”,“启人生之閟机”,使“内曜”明华,“人各有己”,人皆获此“自性”,必“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知人类曼衍之大故,暨人生价值之所存……而张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与时劫同其无穷”。鲁迅通往“雄厉无前”的人国的思路也是从“新民”开始的,在鲁迅的设想中,“人立”则“事举”,人为真人,国为人国,自然“雄厉无前”,人生价值得立,国家根本得固。
清末民初,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远不止严复、梁启超、鲁迅,而是一时思潮,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等政治、思想界主将,周作人、沈从文、老舍等文学界大家,蔡元培、张伯苓、晏阳初等教育界志士都进行过严肃的思考和真诚的实践。这一思潮不但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界、思想界,甚至直到当代,仍能听到其响亮的回音。
二、“国民性”论题与“国家想象”
“国民性”论题产生于深陷内忧外患的中国,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的存亡续绝之关键。问题思考的重心和终极,是如何走出民族危亡的困境,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欲其国安富尊荣”,这就是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所说的“中华大帝国”和鲁迅所说的“屹然独见于天下”的“人国”。虽然对“国”的具体理解或有差异,但是建“国”的目标指向却无不同。所以说“国民性”论题的产生,立足点是政治的,是国族的,虽然后来“国民性”批判更多地具有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味道,但其中寻求中国富强昌盛的底色却是显见的。这一论题在本质上,是对强国路径的思考,是对弱国的批判和对强国的企望,故而,“国民性”论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国族问题,是政治哲学而非单纯的文化思潮。而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无不持有政治理想和国族责任,严复、鲁迅、老舍、沈从文、蔡元培、张伯苓、晏阳初等政治、文化、文学、教育主张,也浸润着深深的民族忧思。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理解“国民性”论题,将其看作对于强国的想象和通达强国之路设计,会给我们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思路。
鸦片战争,第一次把中外摆在了弱小与强大、落后与先进的对峙格局之下。对于“列强”的想象,最初是基于“炮舰”的,于是才会有“洋务运动”,兴洋务被想象成强国之路——炮舰,是对英式强国的想象,是基于“鸦片战争”的直接体认;甲午战后,日本的胜利大大触动了中国人的思想,自古为“中国”学生辈的“撮尔小国”居然战胜强大的中华帝国,给国人极其强烈的震撼。于是认为船炮不是根本,关键在于政体。似乎政体维新是日本强大的根源,至此国人的目光开始聚焦于“明治维新”——维新政治,源于对于日式强国的想象。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国民性改造”为核心的强国之路逐渐明确而且广被接纳,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有:(1)想象“强国之路”的主体多是身处庙堂之外的“草根”一族,如去职后的梁启超和作为普通一民的鲁迅,与身处庙堂、手握重权的朝廷重臣所拥有的资源和所持的视角自然不同:(2)中外交流增加,尤其是出洋留学人员的激增可以让人获得远距审视本国的机会以及对中外国民的直观比对和异域生活的切实体验;(3)国外尤其是日本社会相关问题讨论的话语情境。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思维方法对人们理解“国家”、“强国”和对强国之路设计的影响,这也正是理解“国民性”论题品格的关键。事实上,正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直接促动了 国民性问题的产生。这种影响不一定表现为当时的论者在表面上征用了多少儒家话语,而是看他的思维方法、思想进路、方案设计与儒家哲学思维方式的深层关系,并且,一定要注意的是这种关联,也不应因当时的思考者可能有意避免使用儒家话语甚至声明反对儒家思想而被忽略。
三、“国民性”论题与儒家政治哲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一篇《大学》,道出了儒家政治哲学的精义。
要“治平天下”,必从“修身”入手,定治国之大本,本乱则国不治。修身重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而这里的“知”,更多的是天人之理,社会伦常,是儒家的“礼”,而非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知识。先修己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平天下的方法也非经济、法制,而是“明明德”,是道德、文化的教化。这是就是儒家的政治哲学,由“修身”而至“天下平”。
儒家思想首先是政治哲学。儒者所面对的是礼崩乐坏、天下失序的社会状态,其责任是秩序重建,其目的是重回西周盛世,其理想是“天下大同”。通达儒家“理想国”的途径是由“修身”为始,至“平天下”而终;其方法“明德”、“新民”。儒家的政治哲学显然是遵照“个人”而“国家”的路径,试图建立以个人德行为基础的君子之国。其治理策略是以“道德教化”和“新民”为旨,其本质是建立在“新民”基础上的“国民性改造”理论。人性是这一国家理想的基础,决定了“修身”理论是否可能。在儒家理论中,不论人性是孟子所说的“善”还是荀子所说的“恶”,通过学习、教化,或张其“本心”或“改恶迁善”都可成君子之德,为贤为圣,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所以“修身”的可行性是没有疑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人为“君子”;“学而优则仕”,而官为“君子”;“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王为“君子”。于是民为良民,官为贤臣,王为圣君,天下熙熙。
还要注意,在儒家的“理想国”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不是利益的,而是情感的、伦理的联结。儒家把“孝”规定为人性的基础和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视为人之为人的天然“自性”,进而由“父慈子孝”推演出“君明臣忠”,“官仁民敬”,并把父母子女之间的“慈”、“孝”,泛化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法则,把兄弟之间的情谊“悌”泛化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世友爱。“百行孝当先”,“孝”不但是人性之基础、伦理之基础更是国家之基础。可见,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国家”是以“人性”为始基,以“修齐治平”为路径,以“亲情”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家国同构”的伦理实体。国家秩序由修身成德,具有仁义礼智“四端”和忠孝礼义信悌廉耻品格的民、官、君来共同维系。
这种以人性为基、修身为术、教化为法、伦常为纲的立国方案,必然重人性改造、道德教育,伦常建设。而一旦国家与社会秩序失范,自然由重修人性、重整伦常人手,以道德批判、精神导引、文化批评、教育振兴为法来力挽危局。所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士人的最高理想,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文苑的深深感叹。
但是,纲常立国的背后依然是利益法则。国家,本质上是利益的生产、交换、分配机制。在阶级社会里表现为阶级利益维护与冲突。事实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与社会利益的生产与分配密切相关。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社会财富有限。由于农业文明这种生产方式无法使社会财富迅速增加,是典型的低生产、高需求的经济形态,所以有限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是社会的首要问题。社会失范,多由利益分配失衡造成,要重建社会秩序,就要重设合理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格局。儒家哲学,一方面提倡生产,认为这是“王道”之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另一方面更重视财富的分配,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不言利,如孟子所说“工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儒家的“义”正是对“利”的约束,所以言“义”,本质上还是说“利”,只是不是以“利”来鼓动社会,而是否定“利”以压制社会的利益欲求,代之以“道…‘德…‘义”,以伦理法度为先,建立伦理秩序的价值优先性,再以此来建立整个的社会秩序,进而以“义”为法则进行利益分配。这和法家哲学讲究“刑”(罚)“德”(赏)“二柄”和今天的宪政哲学大异其趣。同时,为广播这种思想与维系这种秩序,教化必不可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推而广之,“明明德于天下”也是治国、威远的基本策略,“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远人不服”,不是大动干戈,而是“修文德以来之”。儒家重教育,孔子为教育家绝非偶然。
文明只有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才能维系,秩序是国家的第一要义,所谓“争则乱,乱则离”。儒家构想的以“义”制“利”的社会生产、分配法则,以“立人”(修身)为基础的“立国”方案则是这种秩序的保证,同时也是皇权的理论基础。反过来这种伦理秩序,也需要王权作为最高权威予以支撑。传统社会在理论上由儒家学说论证,在经济上有农业文明支撑,在政治上与帝王专制互为表里,故而得以维系两千年不溃。
儒家政治哲学在两千年的传承、阐释、重塑中深深融入了中国文化,由“人”而“国”的立国思维模式成为中国人政治思维习惯,也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当我们遇到家、国难题时,会不自觉地沿着这一古老的思维路径达到“新民”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国民性”改造及以此为基点的教育改造和文化革新。
四、“国家想象”中的“国民性”误会 中国政治历来是外儒而内法,或先兵、法,而后儒化。儒家的政治哲学没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撑,无法立身,这就是为什么不是儒学而是法学盛行于战国,最后秦用法家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原因。而国家建立之后又非儒学无以稳定秩序,这就是为何王朝建立之后总是以儒学作为正统意识形态。但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局面与历史上的王朝困境根本不同。中国要摆脱列强的威胁,就必须使自己成为现代强国。
什么是现代强国,什么是真正的强国之路?
对强国的想象先以“炮舰”开始,而后继之以“政体”。炮舰之梦碎于甲午,政体之变止于戊戌。洋务不成,立宪不成,共和艰难,根源何在?于是在古老的思维牵引下,在中外国民气质的对比中,“国民性”论题浮出水面。现代列强的强大,被归为“国民性”的差异;中国之颓败,归为“国民性”的不振。“振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成为时代的主题。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一条路径与两千年来儒家由“立人”而“兴国”的治国思路并无二致,并且也沿袭了儒家树民德、兴教育、新文化(革风俗)的理路。当政治界、教育界、文化界真诚地投入到“国民性”改造的热潮之中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走在两千年前孔子设计的老路上。
现代资本主义列强的强大,在于生产方式。国家强大与否首先决定于其对国内外之资源的动员及组织能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现代大工业生产:动力以矿物燃料及电力为主;材料以金属、橡胶等人工生成物为主;工具为大型机械;组织方式为企业内的现代管理和社会的市场化运作。显然,这与中国农业文明以人力、畜力为主的动力;竹、木、石、棉、革等为主的原料;手工生产、自然经济为组织方式的生产相较,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国力强弱不言而喻。而资本主义政体,或立宪或共和正是这一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的产物。马克思说得好:“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社会。更重要的是,现代国家的组织不是依照伦理法则,而是遵从利益原则。从外观看,见到的是宪政政体,而宪政政治本身,却是社会利益协调的工具。社会的生产方式、利益关系是这种政体的内在支撑。这才是中国近代的立宪政治不能成功的原因:中国近代没有英法的社会利益结构,也没有日本政治上层变革求强的决心。
从长远来看,任何没有切实利益格局支撑的社会法则终会变异乃至解体。因为一切制度,从根本上说,无非是利益原则,是利益生产、交换、分配法则的外现。中国的儒家政治法则,本质上也是一套利益法则,不过是一套与农业文明、王权政治相适应的,以伦理法则为先,又先利后的社会利益生产、分配制度。
中国的贫弱,不在于“同民性”。国民性情、思维、品格究其根本决定于文明形态,虽然也受遗传、地域、气候等的影响。从文化改造和精神启蒙人手,未必能改变国民秉性。启蒙者的血,都未能震动平民的心,更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式的心灵感应。生活首先是俗常的,是物质的,也就是利益的,尤其是在中国大多数国民求温饱尚不得的时代。
近现代“国民性”改造的思路,虽然目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但其路线,却是与农业文明相配适的传统的伦理国家的设计。儒家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误导着人们应对危局的思考,“国民性”论题的产生与“国民性改造”方案的提出,正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光影返照。虽然社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和“国民性改造”的运动之中,然而实则是建立在对“现代国家”和“现实民生”的双重误解之上的:国家——即便传统的中国式伦理国家——本质上是利益结合体,而不是道德、情感的结合体;民生问题,首先是物质问题而不是道德、精神问题。道德更新、精神启蒙,无法真正通向现代强国的建立。国家、民生的现实性、物质性、利益性决定了“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和“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的理想,只是一种文人的浪漫,也表明儒家政治哲学的伦理、精神表象对知识者的误导。“国民性”论者所期望的结果与其所设计的路线无疑南辕北辙。发达国家的国民性特征,与其说是秉性的不同,不如说是不同文明形态下思维、行为、情感习惯的不同。希望通过“国民性改造”的路径通达国族复兴的设计,引发得更多的是对国民的道德期望和道德苛责,是文人的道德自许和精神自恋,却未必能通向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