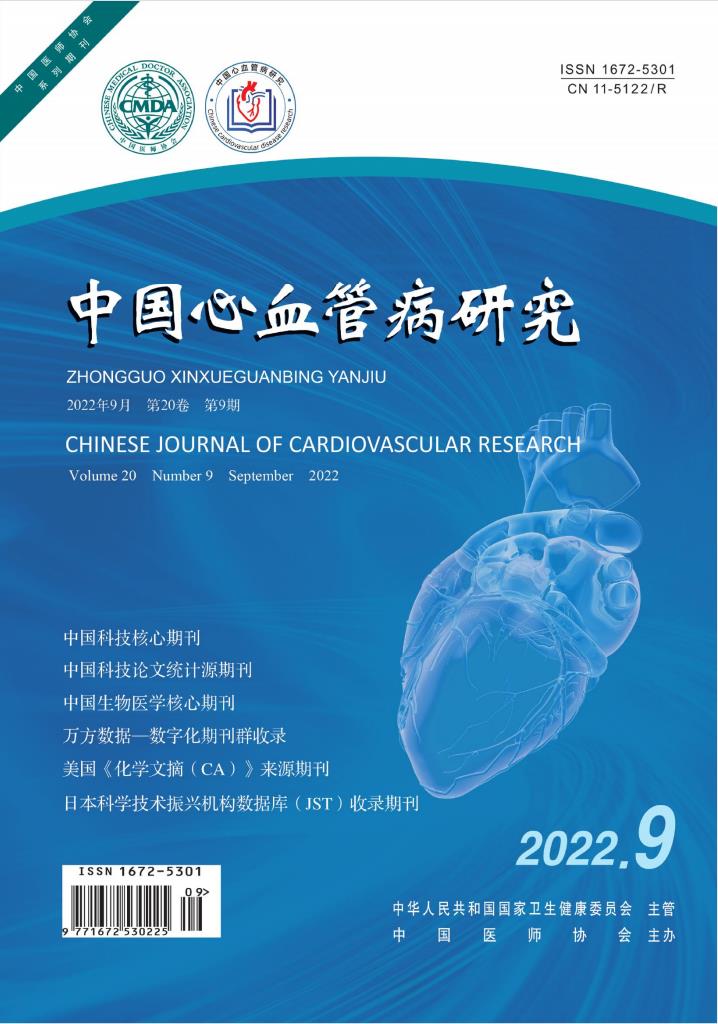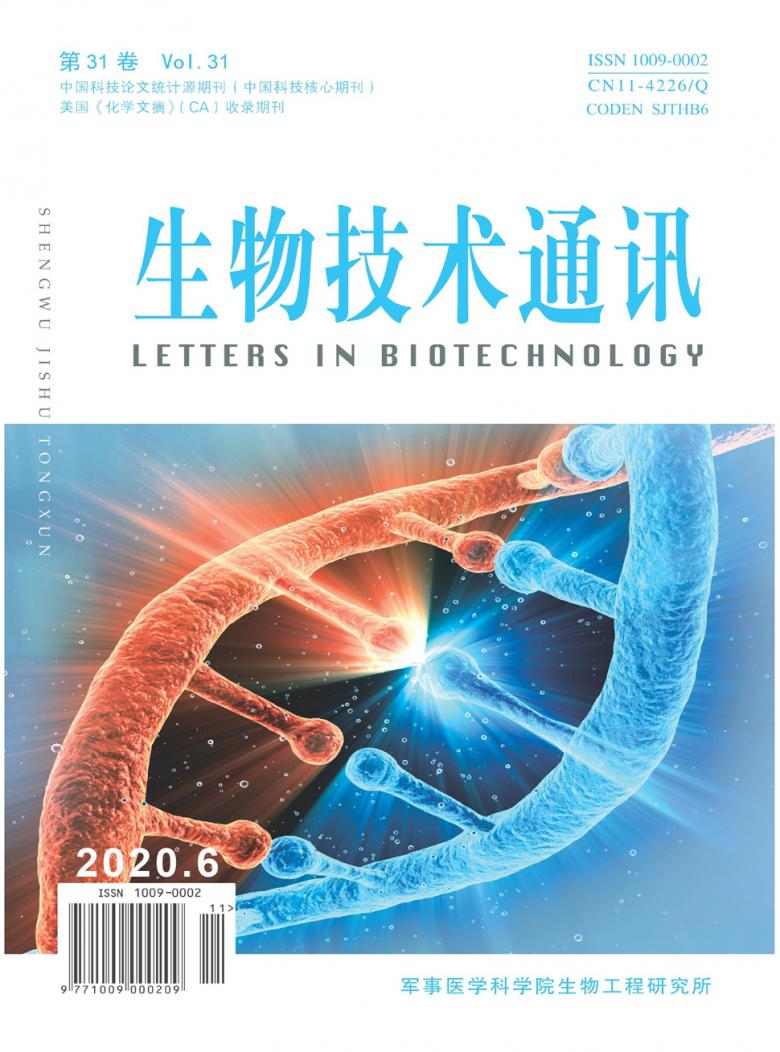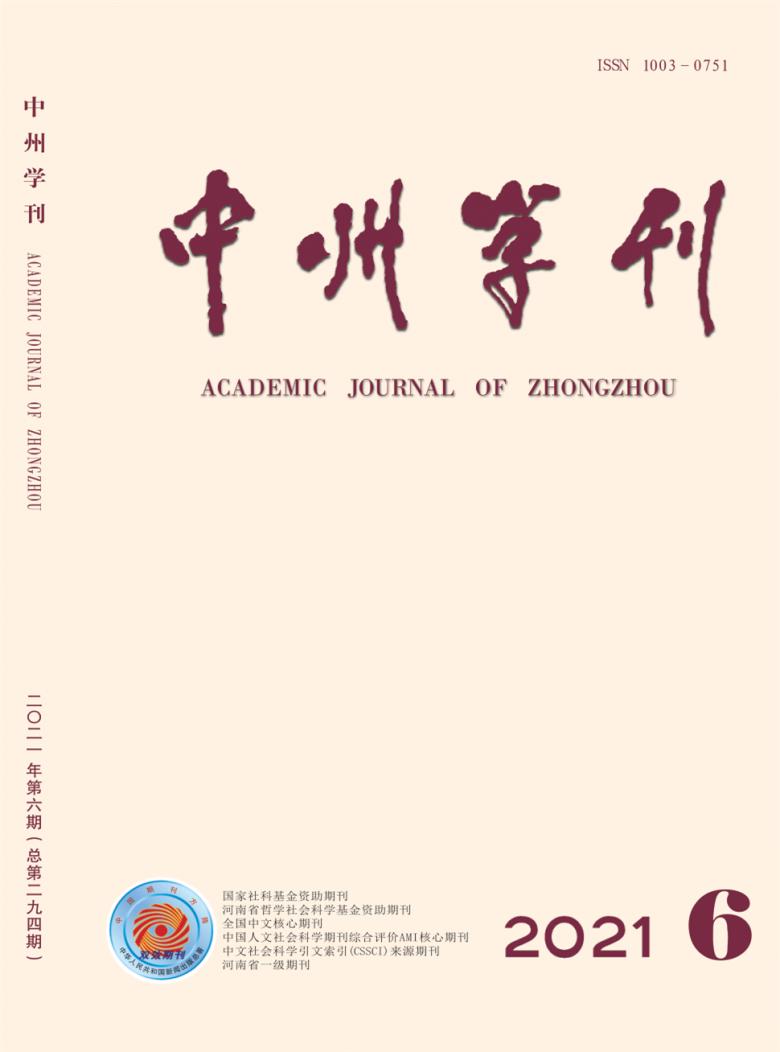唐代“拟判”考
张建成 2010-12-28
如果说,汉代的“文景之治”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兴盛时期,那么,唐代则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全盛时期。至于唐代全盛的理由,后人列举很多,比如,唐朝开国皇帝李世民为“一代明君”,唐代的全盛与他为国家在各个方面打好的坚实的基础有关,等等。但是我们认为,在众多唐代全盛的理由里面,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唐代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非常重要的一项制度—科举制度—即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治理国家;而科举制度也成就了唐代判词的最初形式—“拟判”。
一、“拟判”产生背景考
判词在我国古已有之。据考证,最早的判词叫“书”、“鞠”;之后又有“判”、“判词”等叫法,它与今天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称呼是一脉相承的,主要是指由官方制作的、对案件作结论性的文字记录。中国古代判词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虞舜时代我国就有了刑法;相传在夏商时期诉讼法规即出现;到了周代,李悝著法经六篇,诉讼断狱相继形成。然而,与诉讼相伴随的判词究竟起源于什么年代,至今还难以有确切定论。从现有的历史资料、古代遗留的典籍和出土的文物去考察,我国古代判词的历史最起码可以向上一直追溯到西周时期。[1]但判词真正成为一种成熟完备的文体却是在唐代。这一时期无论是司法意义上的以实用为主的判词,还是文学意义上的以欣赏为主的判词,都相当地成熟完备。唐代之前,虽然也有判词的写作和流传,但其数量较少,形式不一,没有形成制度和规范,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自觉的、有意识的写作判词的情况也还没有形成。
唐代是中国古代判词的成熟兴盛期。唐代最初的判词从“拟判”开始。从其形成发展的文化机制及其历史背景来看,判词在唐代这一时期的成熟并非偶然,是唐代诸多制度、法律、文化等因素共同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是与当时的法制状况及选官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2]
第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为唐代判词提供了制度土壤。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但真正把它发扬光大、形成一种制度并对后世造成重大和历史性影响的还是唐朝。据史料记载,唐朝的科举制度非常完善,考试的内容和程序也非常繁琐。在礼部所举行的科举考试中,有明法一科,属每年都举行的常科,这种制度是唐朝所独有的。它虽然没有进士、明经等科受读书人的重视,但它毕竟是仕进的途径之一,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律学的重视,因为对法律的通晓熟悉正是制判的前提条件之一。明法一科专门考察应试者对国家律令的掌握程度。“凡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3]唐代应明法一科者多从学馆中培养,如唐代隶属国子监的六学中就有律学一科。
读书人在礼部考试及第,获得出身后,还要经过吏部的关试。“关试,吏部试也。进士放榜敕下后,礼部始关吏部,吏部试判两节,授春关,谓之关试。始属吏部守选”。[4]“试判”成为走向仕途的重要一关。另外,在吏部所举办的科举考试中,还有拔萃一科,科为制科,不同于每年一次的常科。在唐朝,一个人想进入仕途,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考中以后,才有可能进入仕途。而参加科举考试又必须过以下四关,这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身、言、书、判”。即所谓的:“一日身,体貌丰伟;二日言,言辞辩证;三日书,楷法优美;四曰判,文理优长”。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进京赶考”之前,必须经过相貌关、口才表达关、书法关,这三关都过了,才允许过第四关,即“进京赶考”;而“进京赶考”具体考试的内容则是“试文三篇,试判三篇”。这里所讲的“判”,就是判词;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国家把由官方制作的法律文书统一固定称之为“判”或“判词”,这个称呼一直沿用至今(今天,我们仍把决断是非、明确罪责、确定权利和义务的人民法院的各类文书称为判决书)。可见在唐朝,没有较高的判词写作水平,很难在仕途上有所作为。[5]
第二,唐代为判词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法律土壤。
唐代时期,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立法的原则理念以及各项法律制度均已确立和完备,并且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这是判词得以成熟的法律土壤。一般来讲,判词的成熟和完备首先应得益于法律制度的相对完善和健全,这样才能使得判词成为司法制度的固有形式之一,从而使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规范性。
第三,唐代为判词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文化土壤。
一般来讲,判词的成熟和完备应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历史背景。这也就是说,判词的成熟和完备有赖于整个社会的文字表达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度。中国古代判词在唐代的成熟,与当时文学上的繁荣是一致的。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唐朝文学应该占有浓墨重彩的一席之地。根据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有关史料记载,在唐代,有名有姓的诗人不下3000人,他们写作的文学作品仅诗歌一项,流传下来的就不下10万首!这样一种写作氛围,为唐朝判词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
从上可见,在读书人走向仕宦的层层关卡中,几乎每一关都有试判这一项。判词写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故判词的制作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其写作也就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风尚。制作判词已成为文人学士仕进为宦所必备的一项基本文化素质,从而成为他们政治乃至文化生活中的组成部分。据说当时写不好判词要受到嘲讽,并被有识之士耻笑。[6]可见当时判词写作普及之广,整体写作水平之高,写作判词氛围之浓。
在这种历史文化环境中,判词的写作水平必然会有整体上的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便逐渐得以完备成熟。随着后世历代王朝政治体制、科举选官制度的更迭变化,人们对判词的重视程度再也没有超过唐朝的。因此,唐朝是我国判词发展过程中一次仅有的兴盛和辉煌。
当然,这一切都是从制作“拟判”开始的。
二、“拟判”之与“甲乙判”、“骄判”名字考
(一)“拟判”名字考
“拟”指“虚拟”、“虚构”;“拟判”,顾名思义,就是虚拟、虚构的判词。“拟判”的名字到底从何而来,由谁所起,现在无从可考。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拟判’是虚构的、不具法律效力的判词。它包括一般的模拟之作和文学作品中根据情节需要而撰写的判词’,[7]“‘拟判’是为了应试而准备的模拟判词”。[8]
“拟判”在唐朝主要是用来参加科举考试或者是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的。所以,唐朝“拟判”的虚拟、虚构笔者以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案情虚拟虚构:作为“拟判”裁判的对象,案件的案情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也可能在实践中发生过,但不是本朝、本代、本地的,或者虽然是本朝、本代、本地的,但是改变了其中的某些时间、地点、人物。
2.人物虚拟虚构:由于案件的案情可能是子虚乌有的,或者案件在实践中发生过,但经过了“改头换面”,所以,人物的虚拟虚构也在情理之中。
作为唐朝“拟判”最著名的两个大手笔张和白居易,其中张的“拟判”绝大部分是当朝、当代发生过的案件,不过经其手改变了其中的某些时间、地点、人物,笔者暂且称其“拟判”为“真实的虚构”;而白居易的“拟判”则自始至终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具体的时间、地点,而出现在案件中的人物也统统以“甲”、“乙”、“丙”、“丁”来称呼,属于典型的“虚构的真实”。
总之,因为这些“拟判”的内容是虚拟的,所以,后人把这一时期的判词称之为“拟判”。
(二)“甲乙判”名字考
“甲乙判”是“拟判”的另外一个名字。“拟判”之所以又叫“甲乙判”,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
1.“熟能生巧”说:毕竟科举考试不是每天都举行的,而读书人制作判词的水平也不是短时间内就一定能够提高的,他们需要平时不断地练习书写判词;时间长了,练习写的多了,给判词的主人公(也就是案件的参与者)不断地起名字就成为“拟判”制作者之累。后来,写的多了,熟能生巧,就把案件一方的参与者称之为“甲”,把案件另一方的参与者称之为“乙”。这就是“熟能生巧”说。[9]
2.“天干地支”说:该说的起因与“熟能生巧”说相同,都是被起名字所累,判词的制作者干脆选取了中国古代“天干地支”中最为常用、书写也最为简单的“甲乙丙丁”几个字、尤其是“甲乙”两个字作为案件参与者的姓名:因为一个案件最起码要有对立的两方当事人。这样以来,制作者就不必再为给判词的主人公起一个优雅而又别致的名字而受累为难了。[10]
其实,仔细分析上述两种说法就会发现,两种说法是有内在联系的,只不过说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罢了,“熟能生巧”说重在名字的结果,而“天干地支”说重在找寻名字的过程。
这一时期判词的制作高手很多,其中就有后来与李白、杜甫齐名的、被称作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晚年的白居易退职以后,把自己早年为应试而制作的“拟判”从中挑选了一部分写得比较好的辑录成书,这就是如今流传下来的《白居易甲乙判》(见《白氏长庆集》卷49和卷50),其中共收录白居易的早年判词佳作一百多篇。[11]
(三)“骈判”名字考
唐朝的“拟判”基本上都是用“骄体文”写成的。因为这些判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参加科举考试,想让考官大人在芸芸众生中发现自己是一个人才。因此,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竭尽所能想把自己文采、学识方面的才华表现出来,而只有骈体文才能最为充分地发挥应考者的文采方面的特长,所以,采用骄体文写作“拟判”成为首选,即所谓的“语必骄俪、文必四六”,因此,后人又把这些用骄体文写作的判词称作之为“骄判”。[12]
三、“拟判”形式考
唐代是中国古代判词的成熟期,这与该时期中华法系的成型及其在文学上的繁盛是一致的。唐代以前虽然也有判词,但多为一种零星的存在,没有形成制度和规范。并且,由于传统的杂文学观念,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即使以现代文学的观念加以衡量,中国古代许多文体都不属于纯文学的范畴,在学科属性上属于边缘性质,如书信、奏章、碑铭和作为法律文书的判词等;但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在撰写这类文章的时候,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文学的视角,从而模糊了其本身的文体意义。所以,这类文体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文学性的内涵;它们的发展演进既有本身发展变化的规律,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文学发展变化的规律。判词也是一种边缘文体,但同时也是一种应用性质的法律文书,二者的结合必然使法律文书文学化倾向成为一种必然。所以,有学者指出:判词的形式研究应该放在唐朝文学与文化的双重背景下进行。
唐朝的“拟判”已经有了固定的体例和格式。“拟判”分为“题”与“对”两个部分,其中“题”的部分提出需要判断的案件和事情的原委,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些文书中的简要的案情介绍,古人称之为“假题”;“对”即为判词,即根据前面所给的“题”的内容引经据典地进行正面的论述与分析,最后简单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因为是“拟判”,所以当时的判词大多都不引用具体的法律条文。[13]
下面列举一篇《白居易甲乙判》中的实例及其分析:
原题
得甲将死,命其子以嬖妾为殉,其子嫁子。或非其违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于恶。”
原判
观行慰心,则禀父命;辩惑执礼,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没齿归乱。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爱妾为殉,死而有害于人。违则弃言,顺为陷恶。三年子道,虽奉先而无改;一言以失,难致亲于不义。诚宜嫁是,岂可顺非?况孝在于慎终,有同魏颗理(治也,唐避高宗讳)命;事殊改正,未伤庄子难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见因心之孝。
译题
查某甲临终的时候,嘱咐儿子把自己的爱妾殉葬,儿子却让父亲的妾出嫁,有人非议儿子违背了父亲的命令,儿子说:“我不敢使父亲陷入罪恶。”
译判
观察父亲的善行,安慰父亲的心愿,就是听从父命。遇到父亲言行有疑虑难解之处,应当遵循礼仪,顾全儿子应尽的孝道。
某甲的立身处世失却正规,临死仍然提出荒谬的嘱咐,命令儿子顺从他的邪恶行为,他活着的时候不能正确对待女色,企图将爱妾殉葬,死去还要加害于人。作儿子的,违背了就是废弃父亲的话,顺从了就是陷父亲于罪恶。三年之中,儿子尊奉先人合乎常规的遗命,不要改变;但如听从临死讲错的话,就不免使父亲陷于不义。确实应当让她改嫁,怎么可以顺从父亲的错误嘱咐呢?况且孝道在于审慎处理父亲身后的事,有如春秋时魏颗遵从父亲合乎道理的遗命一样,让父亲的妾出嫁,改正了父亲神志昏迷时讲错的话。叫活人殉葬的事极应改正,这样做没有违背庄子那种难于办到的主张。
应该忘掉听到的荒谬的嘱咐,才能表现出发乎内心的大孝。
实际上,“拟判”的“题”就相当于我们今天高考中的命题作文中事先所给的“已知条件”,“对”则是根据“已知条件”所写的“命题作文”。这样说来,唐朝的“拟判”应该可以算作是我们现代高考“命题作文”这种考试形式的鼻祖。
四、“拟判”内容考
判词本身的功能就是裁定事理,辨明是非,既用于司法,也用于处理公务甚至日常生活琐事。因为唐朝制作“拟判”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所以其中反映的内容非常庞杂。总结一下,主要反映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反映唐代当朝历史
唐代制判所考察的内容是有所变化的,起初是“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也就是说,唐代制判所考察的内容最初是取之于唐代当朝“州县案牍”中有疑议义的案件,并且通过这些案件考察考生,“试其断割”、“观其能否”,这些判词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唐朝的历史。现存唐代的判词主要见于当时的文集、类书以及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书,其内容也主要为这一类。王维的《王右丞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又叫《白居易甲乙判》)等文集都收录了这样一些判词,张的《龙筋凤髓判》则为这类内容的判词专集。保存这类判词最多的当数《全唐文》和《文苑英华》二书,据查,前者所收判词主要从后者中移录,而《文苑英华》一书中,所收的判词种类繁多,非常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乾象、律历、岁时、雨雪、仇、水旱、灾荒、礼乐等多类,洋洋大观,这些判词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唐朝的历史,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唐朝历史的珍贵史料。 (二)取之典籍
唐代制判所考察的内容最初取之于唐代当朝一些有疑义的案件,并且通过这些案件来考察考生,但是,后来因参加考试的人太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14]但是“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于是就“征辟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15]也就是说,随着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来越多,制判的选题越来越难,最后不得不从典籍、甚至艰僻生涩的辟书曲学隐伏之处去找题目,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惟惧人之能知”,判词写作的考察到了以刁难人为目的的份上,说明判词写作已近乎歧途。这有些类似于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由于科举考试出题的范围不外乎四书五经,当时的读书人早已将其背得滚瓜烂熟,于是,出题者就以各种各样的偏题怪题来刁难他们。唐代制判考察内容的变迁,尽管有的偏离原来考察的本意,但由此我们也可看出当时判词写作的普及以及其整体水平之高。
五、“拟判”表达特色考
(一)内容虚拟
唐朝“拟判”中的时间、地点、人物、案件及其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基本都是虚构的。正是由于唐朝的科举考试里面判词占了一半的分量(“文三判三”),所以,唐朝的文人想进入仕途,就必须把法律文书写好,这就在唐朝形成了一种文人竞相练习、写作判词的局面。而写作判词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那时候的文人,无暇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需要参加社会实践,所以,只能是闭门造车,编造大量有出处或没有出处的案例,然后据此下判,以达到练习写作判词的目的。这种局面沿袭时间之长、制作文书之多,世所罕见。
(二)语必骈俪、文必四六
唐朝“拟判”基本上采用的都是骄体文的形式所写,其特点是语句整齐对仗、音韵和谐,风格典雅华丽。因为唐朝“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也就是说,只要判词写得文辞优美,就可“不拘限而授职”,所以自然有不少人要在判词的文辞上下工夫,这就在客观上加重了判词的文学意味。如现存唐代的《龙筋凤髓判》一书,其所收七十九则判词皆为骄判。骄判长于抒情状物,但缺少司法裁决所要求的精确性,不切于实用,故多为“拟判”,文学意味浓;句式呆板不长叙事说理。其中有的可能千篇一律,质木无文;有的则会妙笔生花,富有文才,极见才情,这全在制判者的文学水平和文字功力。如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古代判词皆可认为是由四字、六字所组成的文采华丽的诗歌的集合。
(三)注重用典、文采华丽
唐朝“拟判”基本上采用的都是骄体文的形式所写,而大量用典是骄体文写作的又一大特点。纵观唐朝的“拟判”,其用典的篇幅之重、数量之多,令人吃惊!有的“拟判”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字,但其中竟然可以用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典故!“拟判”虽虚构案情,用典较多,但也注重词藻,斟字酌句而富有文采。唐代以后各朝在科举选官时,虽也考察判词的写作,但重视程度已无法和唐代相比,不过审判时的制判制度却保留了下来,判词的写作也就一直不断,屡有判词集的编排、刊刻。一般来说,这种判词在司法实务中不会出现,纯属游戏之笔,仅具有文学欣赏价值。从今天所能见到的唐代判词看,多数作品文辞华丽,讲究对仗,音韵和谐,句式整齐,撇开其特定的内容不讲,仅从文本形态看,其表现技法和手段都是纯文学性的,和当时的诗赋杂文没有多大差别。不管是所谓“征引赅洽”,还是所谓“使人不厌”,都是通过判词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品格,而能表现出个人风格,这些正说明判词作为文学体式的确立。判词工整对仗,铿锵节律与浓郁诗词味的融合,这正是古代判词的一个普遍性的特征。
(四)重文学轻理、法
唐朝时期,我国的封建法律已经比较完善,按理说,“拟判”中应该重法、重理—即在重视法律的前提下进行入情入理的分析判断才对,文字、文学性的东西应该退居次席。但纵观“拟判”中文、理、法的表达,会发现三者的比重差别很大。几乎所有的“拟判”都沿袭一种固定的比例分配方式,即“文—大于—理、理—大于—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第一,前面已经提到,唐代科举选官在考察制判时,特别重视判词本身的文采,要求“词美”、“文理优长”,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使判词偏离其原有的实用目的,走向讲究辞藻、音韵、用典一途,其写作日趋文学化。故可以说,唐代既是判词在法律意义上的成熟期,也是其在文学意义上的成熟期。中央政府这种制度上的明显“导向”,必然会影响到当时读书人的写作风气,影响到判词本身的形态和风格,“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骄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这是政策影响的直接结果。在如今存世的上千篇唐代判词中,大多数为骄判。这种注重骄俪、注重判词文学色彩的趋向,除了政府的有意引导外,与唐代当时的文学风气也是一致的。
第二,唐代和我国古代的其他朝代在判词制作时的引用法律是一致的。一般来说在适用法律的问题上所采用的规则是有现成法律则引现有法律,如果没有现成的法律可以援引,则可采用董仲舒“春秋决狱”的方式,通过历史经典故事或者孔孟的经典语句来作判词。这样,判词不仅能够以法律为依据,而且把情理与法相融合,不仅具有时代特色,而且富含文学品格。
第三,这些判词皆出自文人,所以判词均写得文采飞扬。人们经常认为法律语言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法律文学传统在法律语言方面的特色各有不同。在语言的各个使用领域中,法律活动和法学研究对语言的准确性风格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具有严肃性的司法判决书,其语言必须规范,其所表达的意思必须准确无误,其文字结构必须严谨周密,其遣词造句必须朴实无华,而无论是文辞晦涩模糊还是辞藻华丽都是司法语言的大忌。但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的一些判词却完全背离了这些基本的法言法语原则。许多判词写得词情并茂,引人入胜。这些判词通过历史经典故事或者孔孟的经典语句来做论据进行论证。这样,判词不仅能够以法律为依据,而且把情、理与法相融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六、结语
可以说,唐代“拟判”是世界范围内最特殊时期最特殊的判词,它不仅在唐朝当时影响很大,而且对它之后的历朝历代的判词也影响深远。及至宋、明、清以及民国时期(包括当时的解放区),中国判词写得词情并茂,引人入胜,文学色彩突出,可阅读性强,都和唐代“拟判”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注释:
[1]赵朝琴:《法律文书通论》,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2]苗怀明:《唐代选官制度与中国古代判词文体的成熟》,载《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3]《新唐书》(卷三十四)。
[4]胡震亨:《唐音签》(卷一八)。
[5]杜福磊、赵朝琴:《法律文书写作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6]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七),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7]蒋先福、彭中礼:《论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8]陈宝琳:《中国古代判词的发展演变和特点分析》,载《襄樊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9]汪世荣:《中国古代判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10]前注[8],陈宝琳文。
[11]前注[5],杜福磊、赵朝琴书,第18页。
[12]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
[13]前注[1],赵朝琴书,第25页。
[14]前注[2],苗怀明文。
[15]杜佑:《通典》(卷一五),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