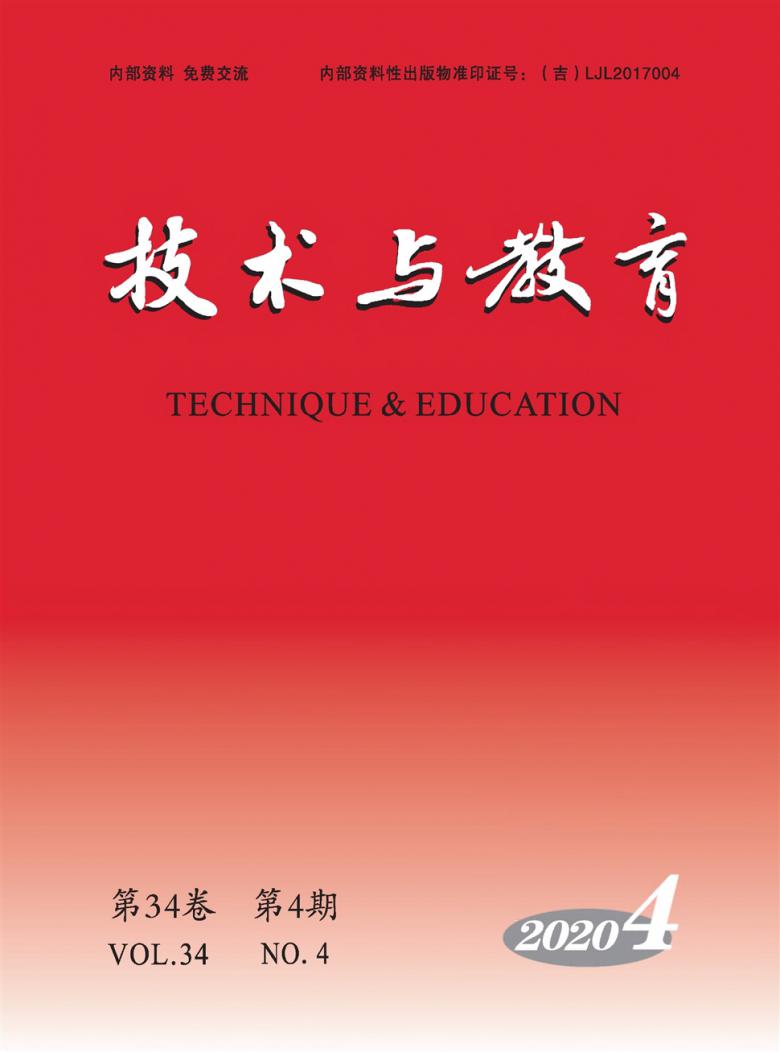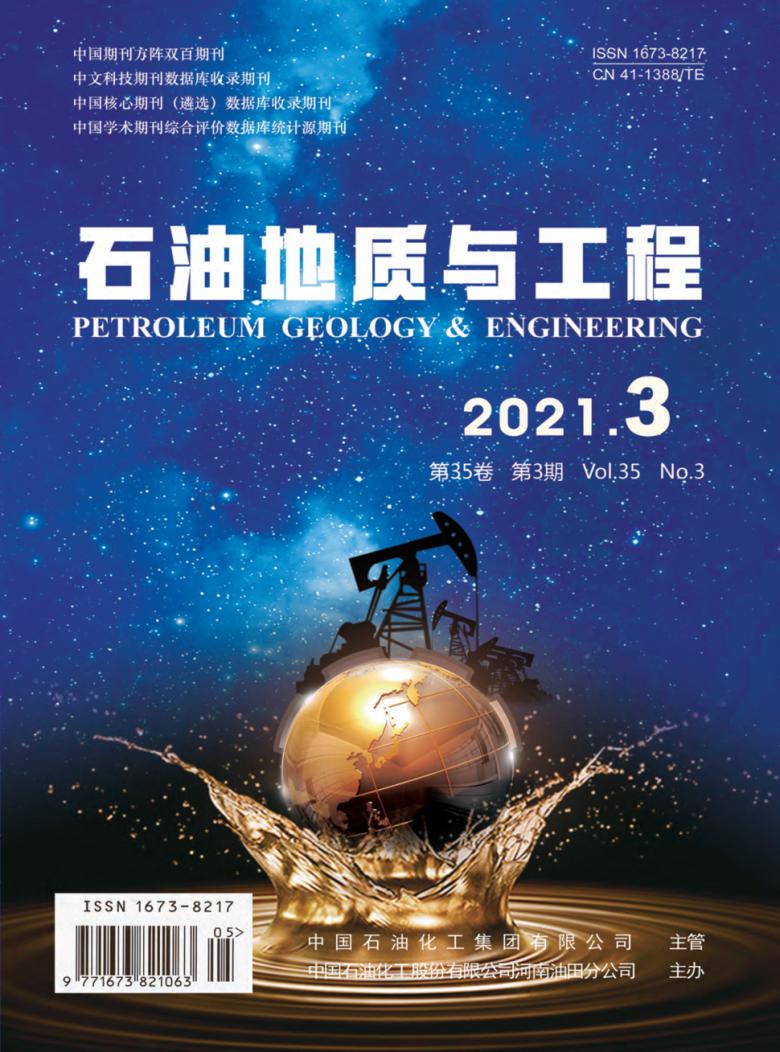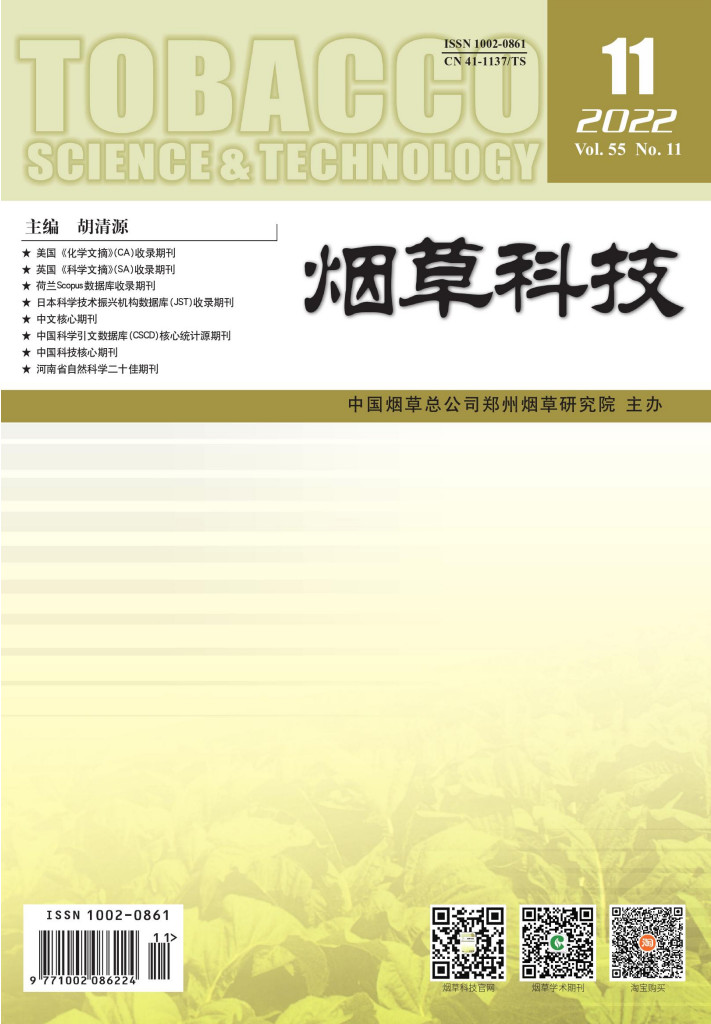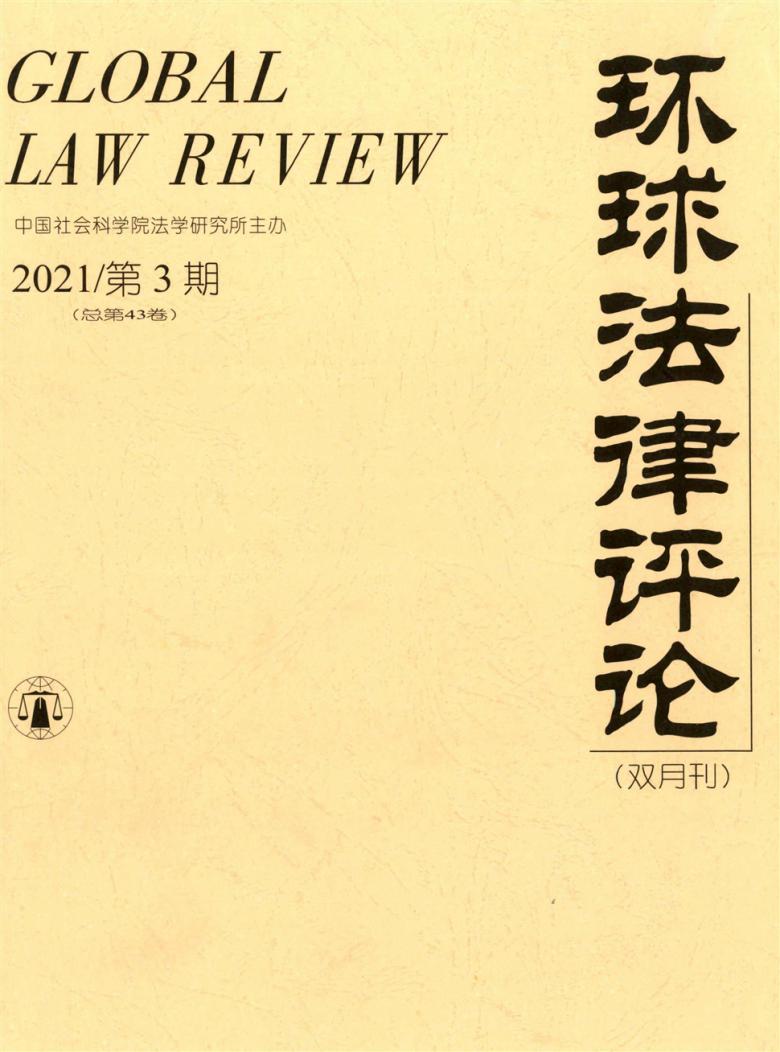20世纪前半叶唐代经济史研究回顾
刘玉峰 2008-09-23
摘 要:20世纪前半叶,中外学术界关于唐代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原创性地提出并论证了唐代经济史的许多重要课题和基本范畴,并一直走着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道路,形成一个研究高潮,基本建构起了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框架和学术体系,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和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唐代;经济史研究;学术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进化史观的传播,近代历史学学科产生,中外学术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纳入研究视野。日本史学界起步稍早,内藤湖南于1910年在《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①],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宏观的时代分期,东汉中叶以前是“上古”,经东汉末年到西晋的一段过渡期,到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再经唐末到五代的另一段过渡期,到宋元明清时期为“近世”。指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革,首倡“唐宋变革”说。其中,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一是唐中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使得大量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开始摆脱贵族政治控制下奴隶、佃农的地位,后经王安石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二是唐代时期货币钱帛兼行,而铜钱流通量相对较少,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银亦在此时开始慢慢得到作为货币的重要地位,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两者交替之际。1923年,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出版[②],将中国历史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周代以前为上古史,从秦朝统一起到唐朝全盛时代止为中古史,从唐朝中叶以后藩镇割据起到南宋止为近古史,从元、明到清中叶以前为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著书当时)为最近世史。全书十分重视研究社会的经济组织和生计状况,重视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对唐代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论述较多,并将“安史之乱”作为“中古史”与“近古史”的分界线。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的社会史大论战,我国史学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作为唐史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③]。自此以后,唐代经济史研究一直是中外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迄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学术历程,学术积累坚实丰厚。
大体说来,近百年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为第二阶段,80年代以后迄今为第三阶段。限于篇幅,本文拟对第一阶段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做一回顾。由于本人的见闻和学识所限,所作回顾只能是简略的,且以介绍中国学术界的成果为主。
一
唐代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一是陶希圣、鞠清远、全汉升、傅安华、何兹全及日本学者加藤繁、铃木俊、藤田丰八等学者,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创新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唐代经济史的若干重要问题和基本范畴。二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指导,开始创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系统地梳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及其阶段,其中关于唐代经济形态和唐代社会性质的研究,也取得了开创性和革命性的重要成果,并奠定了后来研究的科学路径。
重要论文有:黄谷仙《天宝乱后农村崩溃之实况》一文(《食货》1卷1期,1934年),从政府征重税、官吏苛虐、兵祸、经济为政府或商人所操纵四个方面,探讨了安史之乱后农村崩溃的原因和情形;《天宝乱后唐人如何救济农村》(《食货》1卷10-11期,1935年),是一篇长文,挖掘史料丰富,对有关的救济策略和救济方法分析精详;《唐代人口的流转》(《食货》2卷7期,1935年)则专门探讨唐代人口的流动情形。加藤繁《唐代绢帛之货币的用途》(《食货》1卷2期,傅安华译,1934年),从公私经济两方面系统考察了唐代绢帛的多方面用途,并对绢帛的货币职能和货币地位做了评价。杨中一《唐代的贱民》(《食货》1卷4期,1935年),论述了官户、奴婢、杂户、太常音声人等“贱民”的身份地位问题。傅安华《唐玄宗以前的户口逃亡》(《食货》1卷4期,1935年),对户口逃亡的原因、事实、影响及政府制止逃亡的诸多方案,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唐代官僚地主的商人化》(《食货》1卷6期,1935年),则从与商人勾结、自己做商人、商业发展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何兹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2卷9期,1934年),分引言、佛教输入与寺院之兴起、寺院的发展及兴强、寺院的组织、寺院对国家及社会的服务、寺院生活之堕落与俗化、寺院与君主的三次大冲突、寺院的衰落几个部分,对三国到唐代中叶的寺院与寺院经济做了系统论述,是这一课题的奠基之作;《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食货》3卷4期,1936年),分引言、大族寺院户口领有的方式、大族寺院户口领有的发展、大族寺院与领户间的关系、大族寺院与国家之领户的争夺、尾语,研究了三国至中唐时期寺院经济中的依附关系和人口分割。刘兴唐《唐代之高利贷事业》(《食货》1卷10期,1935年),考察了民营、寺院经营、官府经营的三种高利贷活动;《唐代商品经济之发展》(《文化批判》2卷5期,1935年),则考察了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状况。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4卷7期,1936年),分小引、水流管理官吏、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硙的管理、河上交通的管理(一)航行法、河上交通的管理(二)津渡法、河上交通的管理(三)桥梁法、海上运输之规定、结语几个部分,征引文献资料充分详实,论述深入全面;《唐代管理“市”的法令》(《食货》4卷8期,1936年),分市是什么、市的官吏、行与肆的标牓、斛斗称度的平校、物价的评定、把持及诈欺的禁止、立券的限制、不合规程的货物的禁卖等方面,详细搜集并分类征引了有关文献资料,论述清晰完整。《盛唐户口较多的州郡》(《食货》2卷10期,1935年)、《唐代处理客商及蕃客遗产的法令》(《食货》4卷9期,1936年)、《唐代官私贷借与利息限制法》(《社会科学》2卷1期,1936年)、《唐代经济景况的变动》[④]等,也是陶希圣发表的重要论文。鞠清远《唐代的户税》(《食货》1卷8期,1935年),研究了户税的名称、税率、用途和意义等。鞠清远还发表有《唐代的两税法》(《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6卷3期,1936年)和《唐宋时代四川的蚕市》(《食货》3卷6期,1936年)等。黄君默《唐代的货币》(《食货》4卷11期,1936年),从货币的特质、货币的铸造、物价变迁与货币政策、货币理论及其批判、结论,多方面地进行了探讨;《唐代租税论》(《食货》4卷12期,1936年),则包括总论、租税的分析、租庸调及两税之检讨、结论几个部分。铃木俊《唐代官吏蓄积之研究》(《食货》4卷8期,王怀中译,1936年),分序说、从制度上观察官僚之经济的基础、官僚之蓄积、蓄积之用途、结语等部分,考察深入,论说独到。易曼晖《唐代农耕的灌溉作用》(《食货》3卷5期,1936年),包括前论、灌溉工具、灌溉方式、政府对于灌溉的注重、灌溉的封建剥削作用、灌溉之障碍、结论等部分,其中关于灌溉封建剥削作用的见解可谓慧眼独具;《唐代的人口》(《食货》3卷6期,1936年),则包括绪论、初唐人口之凋耗及其对策、唐代中期人口之流亡、唐天宝后人口之南移、结语,论证精审,善于抓住关键。曾了若《隋唐的均田》(《食货》4卷2期,1936年),认为“隋唐两代之所谓均田制度,仅属具文,自开国以迄败亡,始终未尝实行”,见解独到。武仙卿《隋唐时代扬州的轮廓》(《食货》5卷1期,1937年),包括江淮一带的富饶、以扬州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以扬州为中心的转运、扬州商业的兴盛与扬州繁荣的素描、制造业的一斑、中唐以降江淮一带及扬州的破坏等,视野开阔,论述全面系统,是关于扬州区域经济的奠基之作。全汉升发表了多篇长文巨制,成绩尤为突出:《中古自然经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2年),论及唐代的实物货币、实物租税与徭役、实物工资,以及安史之乱前后自然经济的衰落与货币经济的兴起、实物货币的废弃与金属货币(钱)使用的发达、货币租税的征收与雇役制度的萌芽、货币地租的萌芽、货币工资的盛行等,认为安史之乱前后,是中古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型时期,实际上是持唐宋变革论的,或者准确地说是持中唐变革论的[⑤];《唐代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包括引言、唐初物价的上涨、太宗高宗间物价的下落、武周前后物价的上涨、开元天宝间的物价的下落、安史乱后物价的上涨、两税法实行后物价的下落、唐末物价的上涨、结论,系统探讨了唐代数次物价变动的情形及原因;《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分绪论、唐代扬州繁荣状况、唐代扬州繁荣的因素、唐末以后扬州衰落状况、唐末以后扬州衰落的因素、结论等部分,全面论述了唐宋时代扬州经济的变迁兴衰;《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8年)包括引言、唐代的岁入、北宋的岁入、北宋岁入钱币金银较唐激增的原因、结论几部分,将财政收入与货币经济联系起来考察,识见非凡。王永兴《中晚唐的估法和钱币问题》(《社会科学》5卷2期,1949年),征引较多史料,探讨了由于产铜少,因而铸币少以及佛教盛行而大量销钱铸器,对中晚唐估法和财政、经济、政治、军事等的影响,论述全面。
万国鼎《北朝隋唐之均田制度》(《金陵学报》1卷2期,1931年),董家遵《唐末经济恐慌与农民》(《现代史学》1卷3-4期,1933年),华芷荪《隋唐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2卷6期,1934年),邓嗣禹《唐代矿物产地表》(《禹贡》1卷11期,1934年),铁丸《隋唐矿业之史的考察》(《文化批判》1卷4-5期,1934年),秦璋《唐代之交通与商业》(《中国经济》2卷12期,1934年),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籴”之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1935年),恍然《唐代官民借贷考略》(《清华周刊》43卷7-8期,1935年),一良《隋唐时代的义仓》(《食货》2卷6期,1935年),何格恩《唐代岭南的虚市》(《食货》5卷2期,1937年),森庆来《唐代均田法中僧尼的给田》(《食货》5卷7期,1937年)等,也是这一时期发表的有价值的专题论文。
代表性的论文集和著作有: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⑥],收录研究唐宋经济史的多篇论文,论及唐代庄园、市、草市、车坊、居停、柜房及行会等。作者在日本初次发表这些论文的时间很早,《唐代庄园及其性质由来》一文发表于1917年,余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多属拓荒之作,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⑦],论述了官私工业的组织、私工业成品的销售方式及资本流动、工业种类与生产地域、工业行会等重要问题,立论新颖,论述综合。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⑧]第三章《隋唐时代的行会》,分行的发达、行与政府的关系、行的组织、徒弟制度、行的习惯、余论,探讨了唐代行会的一些情况,但过于简要。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⑨],简略论及唐代海外贸易情况。藤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⑩]第一章《市舶源流》,对唐代海外贸易情形论述充分。陶希圣、鞠清远合著《唐代经济史》[11],是第一部唐代断代经济史专著,包括第一章《前代的遗产与隋末之丧乱》、第二章《田制与农业(上)》、第三章《田制与农业(下)》、第四章《水陆商路与都市之发展》、第五章《工商业之发展》、第六章《财政制度(上)》、第七章《财政制度(下)》、第八章《结论》,搜集文献资料丰富,讨论了国有土地、均田制、租庸调制、户税、地税、两税、庄田、庄墅、交通与都市、市、草市、庙会、行会、工匠、色役、资课、商税、茶税、酒税、青苗钱、柜房、邸店、飞钱与便换、高利贷、雇佣、客户、漕运、盐铁转运、东南财库等众多问题,论述广泛、全面、综合,是高水平的奠基著作。鞠清远个人专著两部:《唐代财政史》[12],分两税法以前之赋税、两税法、专卖收入、官业收入与税商、特种收支、财务行政六章,体例严整,纲目清晰地论述了唐代的财政收支与财政管理,是高水平的开山之做;《刘晏评传》[13],分家世、时代背景、传略、转运盐法税制改革、常平铸钱、经济思想与战时财政、政治观念与属吏登庸、秩事与遗文几部分,并附有刘晏年谱,详细探讨了刘晏的理财背景及成就。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14],是第一部唐代社会史研究专著,分阶级、风俗、借贷、交通四章,均与唐代经济史有关。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15],其中隋唐经济史部分包括第八章《隋唐总叙》,第九章《唐代统一后产业进展的新倾向》,第十章《唐代统一后商品货币关系之发展》,第十一章《均田制之没落及私庄之发达》,第十二章《唐代赋税制度之演变——由租庸调到两税》,第十三章《唐代后期社会经济之崩溃》,共计六章,征引文献资料丰富又典型,行文谨严精练,条理清晰,擅长宏观考察,综合分析,以动态和联系的眼光阐述隋唐时期的制度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并多与汉魏南北朝及五代两宋时期史实相比较,视野开阔,上下贯通,多有卓越识见和重要发现。如第八章对均田制和赋役制自北魏北齐北周至隋唐期间之损益沿革的阐述,极为精要,所论已成为学界共识。如第九章论述唐代统一后产业进展的新倾向,阐明了“唐代东南,已成为农业生产之重要区域”、“入唐以后,长江流域之丝织品,上自川蜀,下至吴越,皆已臻于极发达之境。蜀锦在汉时已驰名,兹不必论,由荆襄而下至吴越,则属后起之业,江南东道一隅,尤呈冠绝一时之象。”第十章则从货币、交通、商业都会、市场形制和商业资本诸方面,综合论述了唐代商业“皆表显向上发展之倾向”。其他各章所阐述,如“私人田庄之自始存在”、“制度本身上所存在之矛盾”为均田制废弛之两大重要原因;均田制破坏之经历,“为唐代经济转变之重要问题”;“自唐代中期,计口授田之制无形消灭后,自此历宋、元、明诸代,土地私有之制继续发展,即一部分为国家或皇室所保有者,亦以私有之形式出之,以征收佃租为目的”;“两税制,实为一种苟且应付时势之制度”、“两税法及各种杂征课之产生发展,但以整理财政收入为目的,非以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对于旧日促进经济衰落之因素,非但不能消泯,且因顾虑收入短绌之故,采用苟简应付政策,致令社会经济崩溃之因素益增”;“唐代社会经济崩溃之主要原因,为土地财富分配之失调,致令贫富悬绝,更益以租税负担之失均,贫者负担奇重,不能维持生存,因而流亡者聚为盗贼,遂至于政权解体”,等等,均为精审、深刻之结论。该书隋唐部分可视为20世纪前半叶唐代经济史研究最具水平的综合之作,其动态考察、宏观论析的研究方法极具科学意义,也是符合唯物史观原则的。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6],辟有“财政”一节,指出李唐建国后承继北朝以来之财政制度系统,但是随着武周特别是玄宗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财政制度随之而演进——“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及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陈先生注重探究制度渊源流变的方法和具体观点,对后来的唐代财政制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17],分绪论、高宗以后的东都与运河、大唐帝国的极盛与运河、大唐帝国的中衰与运河、大唐帝国的中兴与运河、大唐帝国的崩溃与运河、北宋的立国与运河、北宋帝国的崩溃与运河、宋金的对立与运河、结论,共十章,深入论证了运河是否通畅对唐宋帝国盛衰以及经济地理变化的影响,迄今仍是这一领域最高水平的著作。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8],论及唐代金银货币在私经济方面和官经济方面的用途、唐宋时代金银之种类及形制、金银钱、金银器饰、金银价格、金银出产地及其输入输出问题等。万斯年辑译《唐代文献丛考》[19],辑译了日本学者玉井是博、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羽田亨等人关于敦煌户籍残卷考释、唐代过所文书、沙洲伊州地志残卷考释的论文,并在《译者后记》中对辑译诸文进行评介,对某些问题也做了进一步的申论。
朱伯康、祝慈寿《中国经济史纲》[20],是当时的大学教材,分自序、导论和上古经济、中古经济(上)、中古经济(下)、近代经济四编,在第三编中谈及隋唐经济概论、隋唐经济之特色、隋唐之国际贸易及工商业和唐代之交通及都市、经济政策、货币制度、工商组织、隋唐之庄园制度及农业、租庸调与两税等,广泛吸收学界成果,所述相当系统完整。当时,还出版了其他一些教材和概述性的经济史著述,对唐代经济史均有述论。如欧宗祐《中国盐政小史》[21]第五章专述隋唐五代之盐政;曾仰丰《中国盐政史》[22]述及唐代盐官、盐禁问题;陈登原《中国田赋史》[23]述及唐代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吴兆莘《中国税制史》[24]第五章述及唐代田赋、关市之税、盐铁之税、酒税、茶税、其他杂税、力役、常平及义仓制度等;王孝通《中国商业史》[25]第七章述及唐代都市、市政、商事之法律、各地之商业、商人之种类、官吏之经商、商业之发达、重要商埠、唐代交通、唐代关禁、唐代币制、高利贷、茶叶之兴盛、茶盐之税、病商之政、理财家;陈安仁《中国农业经济史》[26]第九章《唐代之农业状况》,述及唐代均田制之演变、均田制之破坏与其挽救之法、官吏之职分田、唐代之税制、唐代之庄田制度、唐代之屯田制度、唐代之水利制度、高利贷的剥削等。这些教材和概述性著述学术价值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也有不少深刻的通识和见解,对传播唐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1934年12月创刊,1937年7月停刊),“网罗了全国各地150多位作者,发表了345篇文章。……作为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食货》半月刊在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7],有力推动了包括唐代经济史在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食货》4卷5期还是“唐户籍簿丛辑”专刊,把当时“中日文书籍杂志里辑录的敦煌户籍丁籍收罗在一起”,直接推动了唐代籍帐制度的研究。陶希圣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印《唐代经济史料丛编》,共印刷出《土地问题》、《寺院经济》、《唐代之交通》三种,《土地法令》、《唐代之都市》、《工商业与货币》、《动荡中的唐代经济》、《财政制度》五种正在印刷之中,由于“七七事变”爆发,日寇侵占北平,没有能够印刷出来。1971年,《食货》在台湾复刊,才最终印出。
二
在这一时期,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理论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揭示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揭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唐代经济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奠基性成就,并奠定了后来研究的正确路径。
郭沫若的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28],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根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来阐明中国古代的历史,第一次把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历史叙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种生产方式有规律递替的历史,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阶段作了一个勾画——“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的进入了封建时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第一部重要著作[29]。吕振羽发表《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创刊号,1934年),专门论述了“中国经济发展之阶段的划分”,认为中国经历原始社会之后,殷商时期进入奴隶制社会和青铜器时代,西周时期进入初期封建社会即领主制封建社会,“在生产领域,奴隶经济已退出支配的地位,而让渡给了农奴经济;原来的奴隶主,也已如实的让位给了封建领主。”东周时期即春秋时期,是领主制封建制“发育完成的时代,而且最典型。无论在阶级剥削关系的内容上所表现的,抑其上层建筑之诸形态上所表现的,均系如此。”到了“战国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所包含的一种变化,已开始成长。一方面,新兴地主经济之暂时确立,和商业资本的抬头,一方面原来的封建贵族之大批的没落。因而直到周秦之际,这种内部的变化的因素已经存在,旧封建领主所支配的农奴经济,不能不让渡到新兴地主的农奴经济;因而建筑于其上层的封建领主的政权,当然不能完全符合新兴地主的要求。秦始皇的地主支配之封建国家政权,便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秦代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地主制的封建社会,“系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由秦代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夜,这种经济性质的内容,并不曾改变,只在封建经济的体制内连续的发展,但并不曾中断。”也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所经历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吕振羽还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30]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31],阐述了中国原始社会、殷商奴隶制社会和西周封建制社会理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32],虽未论及唐代,但也明确使用了原始公社时代、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时代、封建制度时代、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等概念。其它重要成果,有翦伯赞《关于历史发展中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3期,1936年秋季号)、《殷代奴隶制度研究之批判》(《劳动季报》第6期,1935年)和邓云特《论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新世纪》第1卷3期,1936年)等。郭沫若和吕振羽的论著,“不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33]。
具体到唐代经济史研究,吕振羽发表长篇论文《隋唐五代经济概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4期,1935年冬季号),该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观点,考察了隋唐五代直至宋朝王安石变法期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政治变动,分析了这一期间社会经济的构成、性质、生产组织形式及其剥削关系,着重论述了农民经济(包括佃农经济)、小地主经济和大地主经济之间的利益冲突、矛盾斗争和消长变化,阐述了经济因素在这一时期政治变动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唐代经济形态和政治变动的最早论文之一。该文指出:“‘安史之乱’为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地主利益冲突之爆发。天宝以后,大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之猛烈的进行,和小土地所有者农民之不断的无产化,以及小土地所有者偏倚的负担,于是引出了小地主与大地主之间利益的冲突,农民与地主间之阶级的仇视,均呈剧烈化;同时在唐代地主经济复兴的基础上,而随来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以及海外贸易的扩大,招来了外国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和中国地主阶级的商业——高利贷资本相勾结联合,来宰割本国的佃农和小土地所有者。因而便引发王仙芝、黄巢等所领导的农民的大叛乱,由于地主阶级本身对农民的叛乱镇压之无力,于是便去引进沙陀和突厥(东土耳其)来为其平定叛乱。然而结果上,农民的大集团势力虽在这本国地主阶级和引进的外国势力的联合袭击之下而归于消灭了,却不曾解除了矛盾;同时地主阶级只有能力去引进外国的势力,却没有力量去排出外国势力,从而在斗争的局势中反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从此便引进了所谓‘五代’的‘纷乱’。‘宋代’的统一以后,到‘王安石变法’,为此一长期‘混乱’的一个结束点,小地主经济的优势,于此得到确立。这直到宋的没落,历史的运动本身又跃进了一步。” 谷霁光《秦汉隋唐间之田制》(《南开政治经济学报》第3卷3期,1938年)[34],不仅考察秦汉隋唐之间土地制度的具体内容,且以发展的眼光阐述期间的变化情形,又以联系的观点注重从政治需要、财政考虑和社会组织各方面说明土地制度的产生、内容及演变。由于以唯物史观做指导,所论“北魏均田制的颁布,系在迁就事实,兼救时弊,于是成为一富有伸缩性而不彻底的空泛法令。实行结果,自不免发生事实上的困难,而制度本身亦不免引起其它弊病,终于未能解决国计与民生两大问题。”到隋唐时期,“均田制随政治而走入另一阶段”,“仍然未能达到制度所期望的目标”,实为精辟之卓见。该文最后指出:“封建国家本身构成为一大地主,又节级成为大中地主,官吏和豪富亦然。大小官吏和豪族富家,一般均享受等差田数。这种封建经济机构组成以后,农民只能得到小块耕地,许多人无地而为佃农或者浮游在外,饥饿死亡,一向被封建文人歌颂的几种田制,其实情不过如此。”又可谓一针见血。王亚南《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时与文》第2卷11期,1947年)[35],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两税法,把两税法改革与封建社会经济权力变化、官僚政治变化等联系起来研究,认为:“封建社会的经济权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收上”,在封建社会中,“田制税法不但体现着支配阶级对被支配阶级之间的剥削榨取深度,同时也体现着支配阶级内部对那种榨取物分配的实况”。指出“均田制度及其伴行的租税制度的失败,不仅说明流通经济相当发达的官僚社会,不可能再把土地与农民束缚定着起来,不使变卖,不使移转;并还说明这种社会由长期因缘积累所逐渐形成的门阀及其有关的社会政治势力,再不会允许把他们已经领有或将要取得的土地所有权力,交由中央政府统制支配。所以,为了适应这两种客观情势,唐代统治者经验到维持统治的最安稳最聪明办法,不在垄断土地分配权,以长期控有赋税源泉,而在承认既成土地所有关系,以改进赋税收入。这即是代替均田制及其租庸调体制而出现的所谓杨炎两税法。”“两税法都分明是建立在一种事实上,即中央政府统制土地所有权的分配为不可能,乃不得已而从赋税方面予以限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先进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唐代经济史的研究迅速取得重要成就,并为建国后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和正确方向。
三
总之,这一时期学术界在唐代经济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理论阐释方面筚路蓝缕,成绩卓著,原创性地提出并论证了许多重要课题,包括唐代社会性质、社会经济形态、经济发展状况及变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赋役制度、财政制度、寺院经济、阶级关系、农村农业农民(三农)、手工业、商业、贸易、都市、市场、货币、交通、漕运、人口等等,为唐代经济史研究提出了众多基本概念和主要范畴,还特别注重唐代三农问题的研究,洵属可贵,影响至今。这一时期,学界展开了社会史大论战,由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而去探讨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由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而去探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问题,就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展开争鸣论难,也就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对各派学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包括唐代经济史研究在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一开始就走上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轨道,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把经济史作为整个社会发展史的一个基础部分,或者说把社会发展视作一个由一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有机整体来研究,并形成了相沿至今的传统[36]。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唐代经济史研究呈现出了十分活跃的局面,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创性探索,从理论方法的探讨到研究领域的拓展,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学术风气和学术领域诸方面都有重要创新,形成一个研究高潮,基本建构起了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框架和学术体系,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和学术史意义,并对后来的继续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当时所提出的许多基本范畴仍是学界探讨的重要课题。
在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也不是没有缺憾。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宁,对学术研究造成了诸多困难,不少论著无论就史料搜集还是理论解释,都显得有些粗疏,对唐代经济思想的研究也注意不够,似乎没有专论成果发表。当然,学术研究和著述是一项永远存有遗憾的活动,尤其是在学术体系的初创阶段,没有缺憾更是不可能的,后来人没有任何理由苛求于拓荒的前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