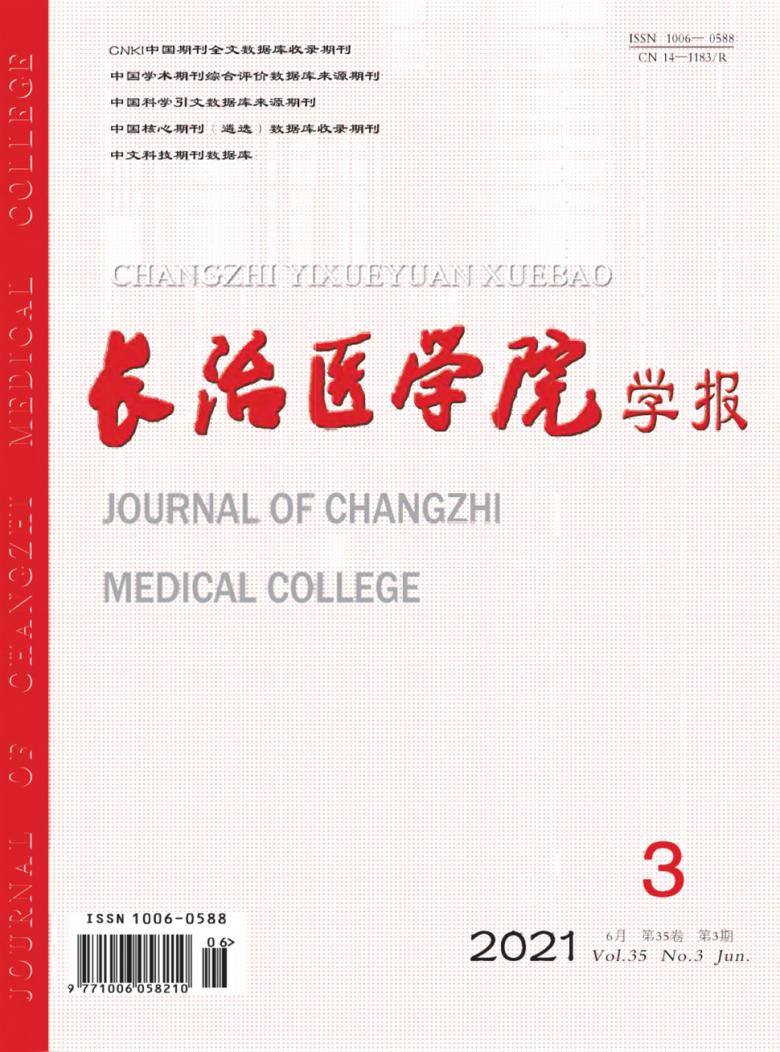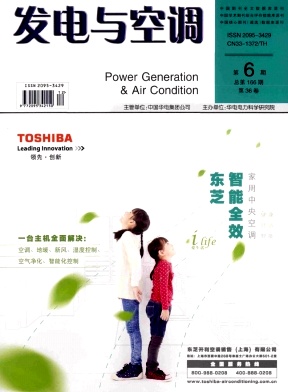元代江南税粮制度新证
陈高华 2006-04-17
税粮是元代重要赋税项目之一。顾名思义,这是一种以征收粮食为内容的税收项目。元代的税粮制度颇为复杂,南、北有很大的不同,官、民田又有明显的差别。过去我写过《元代税粮制度初探》,对此有所论述。由于资料的欠缺,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近年我读到《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一书,其中记载,对于认识元代江南税粮制度,颇有帮助。此书迄今尚未引起治元代经济史者的注意。现将有关记载,结合其他资料,说明如下。
一
关于《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一书,《光绪上虞县志》36《经籍志》有介绍:
《上虞五乡水利本末》二卷,陈恬著。有刘仁本、杨翮二序。嘉靖间邑令张光祖重刊。国朝朱鼎祚续刻。是书分上、下二卷,上卷乃陈恬所著,……。下卷乃朱鼎祚所增刻。历叙三湖兴废事迹暨堰琪成规,足备考镜。近时枕湖楼连氏有重刊本,连蘅又附刊《续水利》一卷。
按,此书刘仁本序云:“县旧有三湖,曰夏盖,曰上妃,曰白马,五乡受田之家实蒙其利,疏治围筑之规,启闭蓄泄之法,自东汉逮今,既详且密。间有擅为覆夺更易者,赖载籍明白,持以证据,于是乎得不泯。乡之人陈恬又惧其久而或讹也,裒集古今沿革兴复事实以及志刻左验公规讼牍,锓梓成帙,将垂不朽,俾谂来者,其用心溥矣。”杨翮序云:“盖夏盖、上妃、白马之为湖于上虞旧矣,幸而不为田则其乡之利甚厚,不幸而不为湖,则其乡之害有不可胜言者,利害之分较然明著。奈何细人之肤见,往往役于小利率倒施之,可为浩叹。此晏如所为夙夜倦倦欲使后世长享厚利而毋蹈遗害焉。”文中“晏如”是陈恬的字。可以看出,陈恬作此书,目的在于保存文献,防止有入围湖造田,破坏当地的水利灌溉。此书所收资料,从时间上看,最晚到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刘仁本、杨翮的序分别作于至正二十二年九月和十二月,当时已“锓梓成帙”。到明代中叶,“其板已坏,其书仅见而损,且将亡之矣”。嘉靖十五年(1536),上虞知县张光祖命人整理,捐俸重刊,见此书张光祖序。清代前期朱鼎祚将明代后期至清康熙年间的五乡水利,辑为一卷,和陈恬的著作合为一书,上卷是陈恬的原作,下卷是朱鼎祚的《续刻三湖水利本末》,全书沿用《上虞五乡水利本末》一名。清光绪十年(1884),上虞人连蘅重刻,后附《水利案卷》,记录清道光、同治年间有关夏盖湖水利的争讼。这就是现在通常见到的枕湖楼连氏刊本,书名《重刻五乡水利本末》。
上虞县在元代属江浙行省绍兴路。全县共十四乡,“大抵九乡在东南,皆绵亘山谷,水利无所预。其西北五乡襟海带江,土多斥卤,雨泽不时,禾受其害①”,主要依靠三湖(夏盖、白马、上妃)之利灌溉。陈恬的《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一书,如名称所示,主要内容便是搜集三湖灌溉的文献资料。因为五乡地处海边,又有海潮之患,所以书中亦有海堤情况的介绍。全书包括“四图”(“夏盖湖图”、“上妃白马湖图”、“三湖源委图”、“五乡承荫图”),十三目(“三湖沿革”、“植利乡都”、“沟门石闸”、“周围塘岸”、“抵界堰坝”、“限水堰闸”、“御海堤塘”、“科粮等则”、“承荫田粮”、“元佃湖田”、“五乡歌谣”、“兴复事迹”、“古今碑记”)。对于研究元代水利和田赋制度,都有重要价值。但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未曾收入,所以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
本书“征粮等则”中说:“田赋之起,因地定则,地有肥硗,赋有轻重,古法然也。并湖之地,虽曰滋饶,地力亦复不同。自宋至今,其法三变,而赋之上下亦第为三焉。”所谓“其法三变”,是指“宋咸淳年间推排时等则”,“国朝至元间抄籍后等则”和“至正十九年归类田粮等则”,也就是南宋末、元初和元末三个时期的不同科征标准。
“咸淳”是宋度宗的年号,共十年(1265—1274)。这时已是南宋亡国的前夕。“推排”即南宋权臣贾似道推行的“公田法”,政府强行收购民间的部分田土作为“公田”,以“公田”收入弥补军饷的亏空②。与此同时,重新确定了田赋的标准。“至元间抄籍”指元灭南宋后在江南推行的人口和资产登记,在登记的基础上确定了田赋的征收标准③。这次确定的“等则”实际上是元代通行的征收标准,因为“至正十九年”(1359)的“归类田粮等则”施行时,距离元朝灭亡(1368)已为时不远。
“咸淳年间推排时等则”和“至元年间抄籍后等则”都是以乡为单位分等征收的,为便于比较,见表一④:
“至正十九年归类田粮则例”,则是以都为单位分等征收的,见表二⑤:
从此二表可以看出,“至元等则”和“至正等则”所记田粮数额,实际上相差不大(后面还要具体讨论),而“至元等则”和“咸淳等则”相比,则减少了一半以上。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变化?原因有两个:一是元朝在计量方式方面的变化,一是忽必烈减免江南租税的决定。
“宋代咸淳年间推排等则”“用文思院园斛”⑧。文思院原是宫廷器物制作场,后来职能扩大,承担度量衡器的制作⑨。“文思院园斛”便是文思院制作的标准量器,在宋代广泛使用。元平江南以后在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⑩。可见文思院园斛仍继续沿用。但没有多久,中书省便另颁量器,称为“省斛”⑾。“省斛”比“文思院园斛”大。过去我们讨论“文思院斛”与“省斛”关系时,曾指出当时有两种比例:一种是文思院斛一石折省斛七斗,亦即十与七之比。一种是文思院斛一斗五升折合省斛一斗,亦即十五与十之比⑿。按照后一种比例折算,文思院斛合省斛六升六合强。本书则提出了另一种比例:“至元年间抄籍后等则”“用省降方斛,假如文思院斛米一斗,展(?)省斛米六升八合五勺。”⒀正好在上述两种比例之间,上虞县通行的这一折合比例,我们在昌国州(今浙江定海)也可看到。昌国州秋税“该征二千八百三十一石六斗八升二合三勺,此文思院斛。以今省降斛折之,止该一千九百三十九石七斗一合”⒁。正好合上虞的比例。这就是说,在江南,征收税粮时,以文思院斛折合省斛,有三种不同的比例,因地区不同而差异。本书所载“至元等则”是按省斛计算的。这样,从具体数额来说,比起南宋的等则来,就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
总起来说,元代前期江南地区两种量器系统同时存在,一种是文思院斛,一种是省斛。但官府征收税粮时,显然都以省斛为准,文思院斛都要折合为省斛。所谓“省斛”,应是元朝政府沿用金代的量器系统,原来行于北方,统一后又逐步推行到南方。元代北方并不存在两种量器系统。《元史·食货志·税粮》说:江南税粮,“其输米者,止用宋斗斛,盖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这段话是很不确切的。江南税粮,在忽必烈时代,作为过渡,两种量器系统并行,但已经以省斛为主。到了元中期,文思院斛系统实际上已逐渐消失。而且,文思院斗斛和“今”斗的折算有三种比例,“一石”当“七斗”只是其中之一。
折合之外,又有减征。本书“至元年间抄籍后等则”下注,当地税粮,“除免三分,实征七分”。另一处说:“世祖皇带悯念越民旧赋之重,岁纳秋粮,以十分为率,永蠲三分。德之至渥,万民感赖。”⒂在现存其他元代文献中,我们看到减免税粮三分的记载,有以下两次:至元二十年(1283)十月,忽必烈颁诏:“江淮百姓生受,至元二十年合征租税,以十分为率,减免三分。”⒃但这次减免,明显仅限于至元二十年。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时颁布的诏书中说:“诸色户计秋粮已减三分,其江淮以南至元三十一年夏税,特免一年,已纳官者,准充下年数目。”⒄“诸色户”应就全国范围而言,减免的秋粮应与夏税相同,亦限于当年。显然,这两条记载都不足以证明元朝政府曾对江南税粮“永蠲三分”。从上引本书记载来看,这是忽必烈“悯念越民旧赋之重”而采取的一项“德政”,很可能是仅限于绍兴路(唐代称越州)范围之内的。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至元等则中各类田的秋粮额和咸淳等则相比,相差很大。南宋末年交纳秋粮一斗(文思院斛),到了至元年间,折合成省斛6升8合5勺。再除免三分,就变成4升7合9勺5抄⒅。以永丰乡民田一等为例,南宋末每亩田税为1斗4升2合7勺,到至元间折合省斛便成为9升7合7勺4抄9撮;再减免三分,打个七折,就成为6升8合4勺2抄5撮了。永丰乡的其他等级和其余四乡各等级的税粮额,都可以此类推。
元代后期,浙东各地普遍实行核田定税⒆。至正十九年(1359),韩谏任上虞县尹,“议履亩以计田定赋而差役,思以均齐其民.其法每田一区,亩至百十,随其广袤高下形势,标其号若干,画为之图曰鱼鳞,以鱼鳞条号第载简册曰流水,每号署图一纸,其四至业佃姓名,俾执为券曰乌由。集各号所载得亩若干曰保总,集各保所积得亩若干曰都总。又自各都流水类攒户第其实管田数日鼠尾,小大相承,多寡分合,有条而不紊,为法可谓密矣”。“由是积弊以革,民瘼以苏,贫富适均,征差有则,民输惟期,岁人用足。”⒇本书所载“至正十九年归类田粮等则”,无疑就是这一次核田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这时包括上虞在内的绍兴地区,已经处于方国珍控制之下。方国珍是浙东台州路黄岩县(今浙江黄岩)人,至正八年(1348)起兵海上,后来归附元朝,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对于方国珍管辖地区内的社会状况,迄今缺乏研究,至正十九年核田定赋之事,可为此提供若干资料。
试以至正十九年等则与至元等则相比较,可以发现有两个明显的区别:一个是以乡为单位分等征收改为以都为单位分等征收,有的甚至以保为单位分等征收。另一个是由四等改为三等。元朝的基层组织,县以下是乡,乡以下是都,都以下有里、保、村。县、乡、都三级各地都是相同的,都以下的设置各地不尽相同。以乡为单位分等征收,改为以都、保为单位分等征收,意味着征收标准更加细致,显然更能反映土地的肥瘠程度。
三
元延祐七年(1320)的一件官方文书中说,江南“田地有高低,纳粮底则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匀一般”[21]。分等征税,是元代江南税粮不同于北方的一大特点。元代北方地税每亩三升,是划一的。江南税粮则各地有不同的等级。如昆山(今江苏昆山)“悉以上中下三等八则计亩起科”[22]。常熟(今江苏常熟)亦同[23]。徽州路(今安徽南部)“一州五县税则,婺源六乡四十都田,但分上中下早晚凡六色,祁门六乡、黟县四乡田,但分上、中、下、次下、次不及凡五色,惟歙县十六乡三十七都田,四色之外,又有所谓天荒田、荒田、沙涨田、众荒田、水冲破田”。徽州路的税粮,是在元朝统一之初,因“无所依据”,用税钱折合的,比较复杂。各县、州每亩税钱不等,秋苗米相差也很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各州、县均分色(等)征收,并不划一。可惜的是,现有文献只有部分县、乡“上田”的秋苗米数额[24]。歙县明德乡上田每亩税钱一百八十文,凡五亩二角为钱一贯,科夏税丝六两三钱一分四厘,绵一两四钱一分七厘,茶租中统钞一百四分二厘,秋苗米三斗三升二合二勺三抄。也就是说五亩二角地纳秋苗米三斗三升多,折算起来,每亩应合六升多。按此类推,婺源州上田每亩不到一升,休宁县忠孝乡上田每亩约三升,祁门县上田每亩约一升六合,绩溪县仁慈乡上田每亩约七升,黟县会昌乡上田二升弱[25]。各州县相差悬殊,虽然有土地肥瘠的因素,但“轻重相悬”,其不合理是很明显的。
相比之下,《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所载至元等则和至正等则,是现在已知元代江南最完整的税粮分等征收的资料。它详细叙述了各乡(至正等则是都、保)分等征收税粮的情况,这是其他同类记载中没有的。而且,它清楚地说明了与南宋粮税的继承关系,这在江南是有代表性的,不像徽州路的秋粮,是元平江南以后新定的。从上虞县五乡的情况来看,至元等则中民田每亩税粮最低为4升3合,最高为6升9合;至正等则最低为4升,最高为7升;上下差别是不大的。《水利本末》一处记载:“邑所垦田大率三十三万亩,公赋一万八千斛。濒湖五乡为田三之一,而粮乃当大半。盖因田为湖,租未尝减,再包湖面不耕之地,故赋视他乡为特重(上山诸乡每亩止科二升、三升,下五乡每亩起科六升、七升)。”[26]可知上虞县其余各乡税粮比濒湖五乡要低得多,但六升、七升应指上等田而言,并非平均数。
与绍兴路毗邻的是庆元路,有民田19 675顷强,交纳秋粮米70 173石强。按此折算,每顷纳米3石5斗强,每亩纳3升5合强。但庆元路各州县情况很不相同,请看下表[27]:
以绍兴路上虞县和庆元路相比较,可以认为,浙东一带每亩民田秋粮额数,自2升至7升不等,其平均数应在3、4升之间。江南其他地区民田秋粮数额,应与此相去不远。当时北方民田每亩税粮三升,南、北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南方民田的亩产量普遍比北方高,看起来南方百姓似乎负担轻些。但元朝政府在江南很多地区另征夏税[28],民田税粮,包括夏、秋二税,这样一来,就比北方重多了。顺便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延祐七年(1320)四月,元朝政府决定增加江南田赋,“除福建、两广外,其余两浙、江东、江西、湖南、湖北、两淮、荆湖这几处,验着纳粮民田见科粮数,一斗上添答二升”[29]。如此则江南税粮应增加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不少论著以此作为元朝政府加重剥削的例子。但是,以上虞五乡的“至元等则”和“至正等则”相比较,显然变化不大,看不出增加百分之二十的迹象。这个决定是否真正贯彻执行,还是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以上讨论的是民田税粮。“至元等则”中只涉及民田,实际上五乡有不少官田。据载,五乡共有土地13.9万余亩,其中官田2 300余亩[30]。“至正等则”中民田之外,有义役官田、官田、万年庄田、湖田、葑田、荡地田。所谓义役官田,应是实行“助役法”时强行从民间抽取的土地。元代差役繁重,应役者往往因此破产。元代中期,政府“命江南民户有田一顷之上者,于所输税外,每顷量出助役之田,具书于册,里正以次掌之,岁收其人,以助充役之费”[31]。“助役”在民间又称“义役”。推行“助役法”后,许多地方“助役之田”实际上“入于官”[32],这就成了义役官田。万年庄田情况不明,疑应是没收入官的土地,设官管理,当然也是官田的一种。至于湖田,指的是围湖造田新得的土地,也属于官田,但与原来官田有别。《水利本末》记载,“三湖官田总计二千二十三亩一角五十五步半”,其中夏盖湖675亩多,白马湖田1 270亩多,上妃湖田77亩多[33]。这就是湖田,不在五乡的官民田数内。葑田又称架田,“以木为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浸”[34]。葑田都在湖田上,为数有限。荡地田应是水荡排水后开垦之地,不过数亩。葑地、荡田都在湖田之列。
将官田、湖田与民田相比较,可以看出,官田、湖田纳税粮,要比民田高得多。官田一般均在2斗以上,最高可达3斗6升多。湖田租额与一般官田差不多,但万年庄田最高达4斗5升。葑田每亩2斗3升,荡地田2斗。总之,官田、湖田的税粮,要高出民田5倍甚至更多。这是因为官田的税粮实际上是租(地租)和税(田赋)合而为一。上虞西北五乡官田与民田的另一区别是,各都、保官田税粮一般不分等,只有个别例外,而民田都是分等的。江南其他地区的官田是否分等,也就是说上虞西北五乡官田的划一不分等是否具有普遍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
在讨论江南税粮时,还必须注意某些田土免征的问题.这是田赋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根据本书的记载[35],上虞县西北五乡共有土地139 748亩2角,名目繁多。除民田(121 399亩强)、官田(2 379亩强)外,还有14种土地,分别是没官田(12亩强)、财赋官田(130亩强)、灶户官田(16亩强)、灶户民田(2 416亩强)、官员职田(537亩强)、站户元签田(10 053亩强)、铺兵免粮田(46亩强)、寺观免粮田(1 272亩强)、本路儒学田(35亩强)、本县儒学田(1 096亩强)、义廪田(42亩强)、稽山书院田(244亩强)、民沙地田(62亩强)、秋租地田(2亩强)。民田、官田要交纳税粮,是没有问题的,其余14类田土中,没官田和民沙地田亦在纳粮之列。田既“没官”,就成为官田的一部分,之所以另立“没官田”一类,应是新近没官的,以示与原有官田的区别。“民沙地田”既以“民”为名,显然属于民田。在本书中,官田、民田、没官田、民沙地田4项有纳粮数额的记载。此外12项田土,则没有纳粮数额的记载,说明它们是不纳税粮的。但这12项田土,情况并不相同,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国家规定可以免交税粮,有站户元签田、铺兵免粮田、寺观免粮田、儒学书院田、义廪田。元代南方签发站户,以税粮七十石出马一匹为则,各户应纳的税粮数额不同,有的一户应当一匹,有的数户出马一匹。也就是说,以税粮七十石作为供养一匹站马的费用。站户的土地,为供应站役所需,便可以不纳税粮,免当差役。但是,有些站户在入站后又购买民户的土地,这部分土地原来要交纳税粮,转入站户之手后仍需交纳。本书记载所说“站户元签田”,就是把免纳税粮的站户原有土地与后来购置的土地分开来。后置的土地,虽然所有权属于站户,但其性质仍属于民田。铺兵就是急递铺兵。元朝设急递铺,专门传递官府的文书,于民户中签发铺兵,承担传递工作。江南铺兵“于三石之下丁多户内差拨,全免各户差役,据各户合该税粮,依弓手例,却令各户均纳,须要不失元额”[36]。也就是说,充当铺兵的人户可以免纳税粮,故称之为“铺兵免粮田”。寺观的土地,原来都可免纳税粮,后来改为宋代旧有的常住土地和朝廷赏赐的田土可以免纳,但入元后新收买的田土照例纳税[37]。“寺观免粮田”即指前一种情况而言,后一种情况仍在民田之列。义廪应即义仓。元朝政府规定,五十家为一社,“每社立义仓,社长主之。如遇丰年收成去处,各家验口数,每口留粟一斗,……以备歉岁就给各人自行食用”[38]。义廪田应是以田土所出供义仓储存之用,故亦可享受免税的优待。学校(路学、县学、书院)的土地,亦可免纳税粮:“江南学田钱粮,……令学校官管领,赡养生徒,官司不为理问。”[39]
另一种田土要纳税粮,但上交其他机构(官员),不归地方政府。如财赋官田,一般指拨赐给贵族、重臣的官田,因设财赋府管理而得名。这类土地的收入归受赐者。灶户是从事盐业生产的人户,他们种的田地,一般是要交纳税粮的[40]。但“盐民苗税各输本场”,不归地方政府[41]。官员职田一般从荒闲田土中拨给,实际上是官田。但职田子粒由佃户直接交给分得职田的官员,与地方政府不发生关系。
还有一种秋租地租地田,在不向地方政府纳粮之列,但情况不详,难以归类。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上虞县西北五乡中,在一般的官、民田土之外,有14种不同隶属关系的土地,其中12种是不向地方政府交纳税粮的,共计田土19 000亩左右,约占全部土地的13%强。也就是说,大约有六分之一田土是不向地方政府交纳税粮的。
江南其他地区的记载可资比较。镇江路共有田地36 611顷强,内纳粮田地27 200顷强,免粮9 410顷强。免粮田土包括财赋府田、王府田、僧道寺院田、职田、赡学田、贡士庄田(学田的一种)、站户田、急递铺田。免粮田占全部田土的四分之一强[42]。庆元路纳粮田土共计23 475顷强,免纳税粮田土3 627顷强,免纳田土包括职田(99顷强)、驿(站)户民田(543顷强)、僧道民田(1 387顷强)、灶户官民田(1 597顷强)。其实还应加上“赡学田土”13 981亩强,折合139顷强,免纳税粮的田土总数应为3 767顷左右。庆元路在元代后期田土总数为27 241顷左右(纳粮田土,免粮的职田、站户民田、僧道民田、灶户官民田,加上学田),而免粮田土为3 767顷左右,占到田土总数的14%弱[43]。根据以上几个统计,可以看出,各地免粮田土比重是相当大的。我们研究国家的田赋收入时,对此是应认真加以考虑,不能忽视的。
还应该提到的是,元代江南税粮分为夏、秋二税。“成宗元贞二年,始定征江南夏税之制。……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粮一石或输钞三贯、二贯、一贯,或一贯五百文、一贯七百文。……输一贯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绍兴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众,酌其中数而取之。”明代绍兴地方志中记载,“泰定籍夏税钞一万九千六百七十贯九文五分九厘”[44],可见当地确是征收夏税的。但是《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中只记“科粮等则”,实则秋粮(税),而没有记载夏税,这应是限于体例造成的疏忽[45],并不是当地田土不征夏税。
五
通过对《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所载资料的分析,并以之与江南其他地区有关记载相比较,可以认为:(1)元代江南田土,从征收税粮角度而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纳粮田土,一类是免粮田土。免粮田土中又有不同的情况。它在全部田土中所占比重各地不等,相当可观。在研究元代江南田赋时,应加考虑。(2)元代江南纳粮田土可以分为官田、民田两大类,每类中又有不同名目。官、民田的比重各地相差很大。(3)江南民田税粮一般均分等征收,或以乡为单位,或以都、保为单位。所分等级各地不同,少的三等,多的六等。数额每亩高的六、七升,低的二、三升,而官田税粮与民田差别很大,要高得多。(4)江南税粮征收时既用省斛,又用文思院斛,而以省斛为主。文思院斛与省斛的折合,各地不同,存在三种不同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