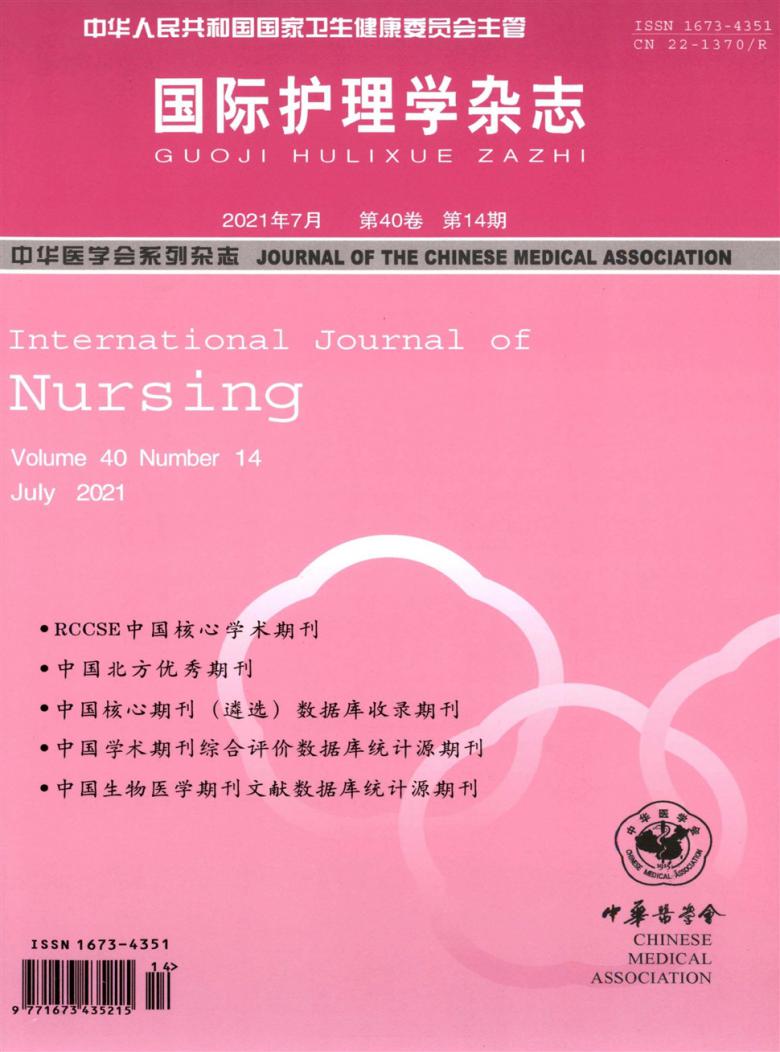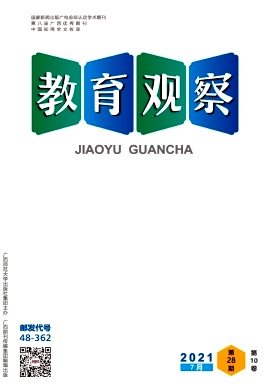元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述略
李治安
秦汉以降,中央与地方的财赋分配关系,随着国家集权统一或分裂割据的发展大势,经历了或聚财于中央,或藏富于地方的曲折变化过程。元王朝的政治体制是蒙古草原游牧君主制与汉地传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融合体,又兼行省、宣慰司、路、府、州、县等地方行政建置多达五、六级,有元一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呈现出与以往封建王朝不尽相同的新情况。关于这个问题,中外学者迄今尚无认真的研究。笔者拟从路府州县的赋税征收和支用,行省在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中的作用等方面,作如下较系统的探讨。
(一)路府州县的赋税征收和支用权限
在元代路府总领逐级科敛的征税体制下,税粮、科差及部分课程等,大都以路府州县为单位,规定数额,强制完成。元廷不仅规定路府州县“非奉朝省明文,不得骚扰科敛百姓,” 各地因水旱等自然灾害蠲免钱粮,通常也是以皇帝诏书等形式颁布的。 田赋增加等,多取决于朝廷的政令。 在行省所辖区域内,行省也有权调整路府州县的赋税数额。行省对所属路府州县的赋税额,或许多半限于高低上下,此增彼减的调整权。 若是蠲免税额,估计行省应咨请中书省批准,才能合理合法地付诸实施。至于路总管府一级的官府,是没有权力减免所辖民户税额的。越权行事,朝廷就会“罪其专檀”。
所谓逐级科敛,就是在路总管府总领的前提下,实行中统初规定的“府科于州,州科于县,县科于民。” 各级地方官府均由“管民正官董其事”。 自中统初,路府州等向下属官署及民户“催督差发”,还要同时颁发信牌、文字作为凭据。官府事先准备带有编号的信牌,遇有“科催差发’时,“随即附簿粘连文字,上明标日时,定立信牌回日”。下属官署接到信牌及文字后,按照规定的期限,“本人赉擎前来赴总管府当厅缴纳。” 路府州县管民官通常以科敛赋税为政务之首。“民户安,差发办,乃为称职。”科税“漏落”不实,要治罪。尤其是“刷出漏籍等户”,“并不申报上司,私下取敛差发”的官吏,更要受到监察官的纠劾处罚。 征税之前,有些地方还“先取管民官甘结文字”。届时不能兑现,依甘结文字问罪受罚。 因“国家两税铢龠不可减,”“每岁将终”,有些路总管府“往往械系县长贰,俾之督税不少贷。民穷无可偿,官至质朝所授书籴粟补完弗惮也。” 下级地方官身受械系,甚至典当官诰补完税额,足见其上逼下困,左右为难之窘态。县和录事司向民户征税,一般要颁发“花名印押由帖,仍于村坊各置粉壁,使民通知。”“差科皆用印押公文,其口传言语科敛者,不得应付”。 县衙科敛文字“下乡如火速”,百姓亏粮欠税,要挨“官棒”。有时不得不鬻卖子女,以偿官税。
需要指出的是,路府总领,逐级科敛的方式,主要适用于税粮、科差及课程中的酒醋课、商税等。课程中的盐课、茶课两项大宗榷卖,除世祖至元二年后的短暂时间外,绝大多数情况下朝廷是委付直属于中书省或行中书省的大都河间、山东东路、河东陕西、江淮、两浙、福建等都转运盐使司等,代表中央直接负责征收或榷卖。据说,各都转运盐使司在所掌盐课及茶课的区域内,“总管府、州若县承命不敢少后。” 相当多的“州县奉盐司甚谨,颐指气使,辄奔走之。” 有些实行盐引制的地区,岁终都转运盐使司将卖不出的食盐强行摊派给附近城乡,“督责州县,临逼百姓,追征食盐课钞。” 有的都转运盐使司下属的提举司“所司办盐裁三分之一,其二分则驱迫州县。” 在实行“计口受盐”的地区,盐课“皆勒有司征办,无分高下,一概给散。”各路州的盐课引额是由都转运盐使司决定的,路及直隶州几乎完全仰其成命办理。 办完后,又如数上缴,不得亏欠。由于都转运盐使司等所办盐课、茶课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宗,直接归中央及行省掌握,由于元代财政高度中央集权,路府州县完全服从于中央而几无独立性,在盐课等办集过程中,路府州县唯都转运盐使司等马首是瞻,就不足为奇了。
唐宋时期,地方官府的财赋支用权限,大体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中唐以后,实行两税“上供、送使、留州”的三分制,不仅规定了中央与地方在财赋占有方面的得益定额划分,而且,“两税之法,悉委郡国。” 地方官府享有较大的制税权或配税权,还可以较机动地支配“送使、留州”的数额,“任于额内方园给用。” 两宋完全改变中唐以后的体制,对地方官府采取“制其钱谷”的政策,各州赋税收入除日常给用外,凡钱帛之类一概“辇送京师”, 致使朝廷“财力雄富”,“外州无留财”,“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各地财赋支用,完全听命于朝廷三司使等。
元朝在路府州县财赋支用权限方面,沿用了与赵宋王朝类似的政策,一直对路府州县经费支出和公帑钱谷出纳等进行严格的管制。通常,路府州县官署日常办公经费,数额固定,多来自本地赋税中的一小部分留成。因诸王部民留驻等,个别路及直隶州赋税收入有限而开销较大,其经费或由朝廷给赐颁发。 其它多数路府州县不能享受此类待遇,日常办公经费严重不足。如世祖至元年间,临潼县衙“经用官给缗钱三可支一。” 在负责征集税粮、科差及一部分课程过程中,路府州县管民官是可以暂时掌握相当可观的一部分财赋的。路总管府所属,也有仓库官的设置。 估计路府州县所征财赋多半是先汇集、储存于路及直隶州所辖仓缴,然后再解运行省或朝廷。但是,正如虞集《平江路重建虹桥记》所言:“今日之制,自一钱以上,郡县毋得擅用府库。” 路府州县官吏对所经办的财赋,对暂时存放在路府仓额中的钱谷,是没有独立支用权的。“经费不赀,帑藏有数”, 地方官不敢擅自动用属于国家的府库帑藏,为满足本衙门费用之需,只得暗中向百姓征敛。世祖至元中期,成都路非法科敛收贮的“羡余米”就多达五千石。 临撞县国家规定的经费仅足三分之一,“余悉赋之民”。为防备上司和监察官的纠劾,官府私自征敛,往往不颁发符信公文。这样一来,胥吏“旁缘为奸,胁持巧取”,又给境内庶民百姓造成很大的骚扰。
路府州县经费缺乏,财赋支用权甚小,使各地水利交通及官衙公廨等兴修的费用筹措,成为十分棘手的事情。元制,“役不可擅举”,若有工役造作,必须事先禀报请示行省,乃至朝廷,获得批准,并拨给经费。 行省在路府州县官吏动用公帑时的批准权,甚为重要。路府州县官吏必须遵照其命令行事。 某些情况下,行省只批准造作项目,“官不给钱”,不拨付经费钱款。地方官府“视公帑一钱莫敢动。” 即使是奉上司撤文兴办工役造作之际,因申请官费“烦文书,迟岁月”,一些路州官不得不自筹款项,命富民出钱粟,贫民出力役。 有的则依赖官营高利贷“规运子钱”解决。 类似这样的工役造作虽然“官无毫米之费”, 但对州县民力耗用颇多,筹措举办并非易事。姚隧曾说,在工役造作方面,庙学容易,官府艰难。庙学兴修,有朝廷诏令严饬,有学田贡庄资助,还可以“责使”儒户出钱“佐力”。官府则不然。“府无公须,山虞泽衡,皆有例禁,财无所于取也,民不敢擅征而役也。” 姚氏的说法,大体反映了当时路府州县财赋支用权微小,受制于人,囊中羞涩的状况。另外,官府经费匿乏和官吏不得擅自动用钱粮,也给各地的灾荒赈济带来了麻烦。灾民“嗷嗷仰给”,官府却“卒无以应之”,“遂至鬻子卖妻,轻则为道路之流民,重则为原野之饿莩”。
元朝廷对路府州县财赋收支的管制,还表现在严格实行岁终上计和钩考理算。
上计,战国官僚制建立之初就已有之。元代财赋高度集中于中央,路府州县支配权甚小。岁终上计,遂被赋予一些新的内容和含义。路府州县的上计,分为中书省直辖区腹里和各行省两种情况: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十二月初一,中书省曾“集诸路计吏类校一岁簿账”,当是较早的腹里路总管府首领官等赴中书省的财赋上计。 而后,各路及直隶州“计吏岁一诣省会之”,成为定制。行省所属路及直隶州的上计,与腹里内容大致相同,只是按规定增加了“各处正官”每季度“照勘”和赴行省上计时行省官吏“稽考”虚实等细节。由于行省接受所属路及直隶州的上计,大体是代中书省行事,所以,上计稽考完毕,行省又需要“总其概,咨都省、台宪官阅实之”。 岁终上计之外,路及直隶州官吏有责任随时将本衙门的财赋收入情况申报行省。发现累年“未申除钱粮,虚作实在,为数巨万”,也申报行省“销破”。 上计和稽考财赋时,行省官员有权适当惩罚路州官吏。
理算和钩考,形异而义近,都是清查检核财赋的意思。蒙元较早的清查检核财赋,当是宪宗七年(1257年)的阿兰答儿钩考。元朝建立以后,经常不定期地派遣官员分赴各地,对路府州县掌管的财赋进行理算钩考。世祖中统初,中书省欲“置局磨勘”“东平路民赋帐册”,“会计前任官侵用财赋”。后因中书省吏员王恽等“力言其不可”,才寝而不行。 至元年间,钩考理算日渐增加。“真定、保定两路钱谷逋负,屡岁不决”,翰林直学士唐仁祖曾受派遣“往阅其牍”。检覆结果,“皆中统旧案,亟还奏罢之”。 在各路总管府与转运司并立之际,各路转运司,也是朝廷理算、钩考的对象。“至元八年,罢诸路转运司,立局考核逋欠。”户部令史刘正“掌其事”。发现“大都运司负课银五百四十七锭”。按照逋欠必须追征包偿的钩考旧例,立即“逮系倪运使等人征之”。后来,刘正“视本路岁入簿籍,实无所负,辞久不决。”又“遍阅吏牍,得至元五年李介甫关领课银文契七纸,适合其数,验其字画,皆司库辛德柔所书”。最终拘捕辛德柔归案,“悉得课银”,洗清了倪运使等四人的冤枉。 不难看出,钩考中既要追究主管官吏逋欠等责任,又需稽察贪赃奸伪等弊病。而派遣和设置专门官吏(“立局”),检覆簿籍帐册,追征逋欠,必要时逮系当事官吏,强制其执行赔偿等,乃是理算钩考的基本程序和内容。
元代路府州县官府经费由朝廷规定,数额甚少,公帑钱谷不得擅自动用,财赋出纳不得留有羡余, 还实行严格的岁终上计和不定期的钩考理算等,所有这些均将路府州县的财赋支用置于朝廷的严格管制之下。路府州县官府在财赋占有和使用方面的权力,与它们承担的征收赋税的繁重义务相比,实在是少得可怜。似乎可以说,元代路府州县的财政职能已很不完整,它们的财赋占有和使用数量很少,而且使用之际又常常秉命于朝廷或行省,无甚自主性。在这方面,元代沿着两宋“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 的路子,走得相当远了。
(二)行省对辖区财赋收支的综领督办
大约在世祖末成宗初,各行省督办的钱粮赋税已有了数额方面的规定。行省官督办钱粮数额,即所谓“合办额”,是以年分 为单位计算的。“合办额”直接向朝廷负责,或增余,或足额,或亏欠,由朝廷逐年检核 。有些场合还履行“自执政以下,皆取认状”之类的“署字”承应程序 。各行省所督办的钱粮数额并不相等,而是高下悬殊,差距很大。以税粮为例,江浙行省最多,达4494783石。甘肃、辽阳二行省最少,仅六、七万石 ,相差六十余倍。就其在全国税粮总数中的比例而言,江浙一省可占到37%左右。按照各行省承担的赋税定额,朝廷予以严格检查和督责,并实行奖励增羡和处分亏空等政策。《元史》卷18《成宗本纪一》元贞元年闰四月庚申条运:“河南行省亏两淮岁办盐十万引,钞五千锭,遣札剌而带往鞫实,命随其罪之轻重治之。陕西行省增羡盐钞一万三千五百余锭,山东都转运使司别思葛等增羡盐钞四千余锭,各赐衣以旌其能。”河南行省下属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所掌盐课居天下之首,世祖末岁额达到六十五万引左右。额重难完,成宗初竟亏欠六分之一以上,折合中统钞五千锭。朝廷遣官鞫问,处罚十分严厉。对监守自盗者,要罚以苦役或罢官。办事迟缓的,也要取招问罪。另一方面,对陕西行省等办课增羡的,则要给行省官“做记验”,并赐以锦衣。运司有功官吏还要添与散官,晋升官阶 。行省在督办赋税过程中,有时掌握的“岁课羡余钞”多达四十七万缗。甚至可以不上缴朝廷,却贡献给食邑在本省境内的皇太子带等,以取悦于权贵 。
行省有权参与议定路府州县所掌的赋税数额、征收方式等事宜。如至元二十八年江南各行省“任钱谷者”及“行省转运司官”曾应召赴朝廷“集议治赋法”等 。湖广行省建立之初,行省长官阿里海牙规定:“税法亩取三升,尽除宋他名征。后征海南,度不足用,始权宜抽户调三之一佐军。”据说,湖广行省赋税较江浙为轻,就是阿里海牙当初确定税率的结果 。后来,湖南宣慰司张国纪建言,欲按唐宋旧例征民间夏税,湖广行省平章哈剌哈孙又“奏止其议”。另,西南建都一带的赋税,也是至元二十三年六月由“云南、陕西二行省籍定”的。
“国计莫重于盐筴“ 。在行省对诸色课程综领的过程中,多以盐课为重点。行省对辖区盐课的管理,具体表现在:某种程度地节制都转盐使司,整顿盐法,掌管榷卖数额等三方面。元世祖以降,腹里地区的都转运盐使司直属中书省,行省辖区的都转运盐使司等则分别隶属于行省。行省对辖区都转运盐使司某种程度的节制,包括了综领盐务过程中的一些统属关系:第一,较重要的事情,都转运盐使司需要随时禀报行省,“照勘议拟”。获得批准后,才付诸实施 。第二,都转运盐使司上奏朝廷,一般需要先申行省,由行省“明白定拟”,然后咨呈中书省参详。中书省作出指示后,也须回咨本省,再转发都转运盐使司等执行 。第三,在实施中书省盐务方面的命令时,朝廷多半要责成行省派官吏赴现场坐镇督察,如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中书省批准拨钞一万锭,供两淮运司“起盖仓房”,即由都省“移咨河南行省”,命其“委官与运司偕往,相视空地,果无违碍,而后行之 。第四,行省可“承制”迁除盐场等下级官吏,事后再申朝廷批准 。
行省可以介入整顿辖区盐法等事宜。这类整顿或与朝廷所遣官一同进行 ,或由行省根据辖区情况,上奏论列利弊,提出建议,如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月,江西行省左丞高兴奏言:当时隶属于江西行省的“福建盐课,既设运司,又设四盐使司,今若设提举司专领盐课,其酒说悉归有司为便”。世祖听从其建议,精简了福建榷盐官署及职事 。他如至元三十年(1293年)河南行省平章伯颜奏言削减两淮都转运盐使司下属盐司建置,改襄阳民户买食两淮盐 ,英宗朝,“湖广盐法废坏已久”行省参政海南携聂以道“榷牢盆,尽除老奸宿蠹,
拔塞本源,无遗余者等 ,均属行省辖区盐法的事例。
行省官还直接负责汇总审核都转运盐使司的岁办盐额。多数时间内,两淮、两浙盐课“直隶行省,宣慰司官勿预” 。行省既管转运司的盐引出售数额,又监督所辖诸盐场的煎盐引额。如世祖末,博罗欢任河南行省平章,足额办集两淮盐课 ;河南行省佥事昔里哈剌“治盐法于淮东,厘革宿弊,增课二十余万” ;武宗朝,河南行省参政某赴两淮都转运盐使司会计盐课收入,且欲以增羡二十五万引作为日后的“岁入常额”,后因都转运使敬俨的极力反对,才未能遂愿 ;仁宗朝陕西行省参政史壎以“陕西岁办盐课良苦,奏减五万缗” ;泰定进士杨维祯担任钱清盐场司令,灶户因赋重困苦不堪,杨“屡白其江浙行中书,弗听”。“乃顿首涕泣于庭,复不听。至欲投印去,讫获减引额三千” ;以上阻止增羡入常额和力请减盐引数事,有些虽然是应都转运使和盐场官请求办理,但行省官对都转运盐使司的岁额增羡,乃至盐场煎盐数所拥有的某种决定权,又是显而易见的。行省得以内掌握和过问都转运盐使司每年输往京师的盐课收入数额。当朝廷在年输京师定额之外临时调拨行省所属盐运司十万钞左右的盐课,用作他省赈济等事时,行省左丞等官可以用‘周岁所入,已输京师“等理由,回答中书省,也可以折合来年输京师盐课数,遵都省命令,“如数与之” 。这类事告诉人们,行省在输入京师之外,尚留部分盐课余额。对后者,行省官员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支配权。
元代地方酒课,通常由路府州县具体掌管。但行省官对辖区的酒课征收方式,有权过问和更动 。还常常派官会计审核路州的酒课数额 。
金银等课,是行省负责的另一项重要的课程。行省对境内各银场提举司等进行检复监督,还派官“体勘”银场经营和收支盈亏 。有关银场役使民夫炼银免其税粮数额等事宜,行省可通过奏报朝廷,予以放宽优待 。行省提调银课的官员,每岁均有固定的数额,必须完成。一些行省官欲减少课额,或须上奏皇帝,获得恩准,才可“从实办之” 。偶尔也有个别行省官妄言增办银课,以邀恩宠。课不及额之际,则“赋民钞市银输官” 。江西行省所属的蒙山银课最为有名。据说,蒙山银课“岁办银五百定之额,始于至元二十一年。后渐次升至七百定”。管理方式也比较特殊:“惟行省相臣一人,瑞州守一人兼领其事,虽宪府不与也 。泰定朝,江西行省平章换住“始减蒙山银课三百定”,“*富民蒙山提举之爵,征赃五十余万缗” 。
行省官还介入商税征收。如辽阳行省左丞亦辇真“薄关市之征,以通商旅” ;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高克恭去“税司或植椼杨于门,以伺匿税者”之弊 ;英宗朝杭州“商税比岁不登”江浙行省掾史孔涛奉命“趋办,旬日而集,时宰以为能” 。商税也是课程的组成部分。行省官督促或改进其征集方法,表明他们对包括商税在内的课程征集的高度重视。元代多数时间内,海外贸易由江南若干行省兼领。如世祖朝江淮行省左丞沙不丁、参政乌马儿奉旨“领泉府、市舶两司”,掌管泉州等处的海外贸易;江西行省参政(遥授)胡颐孙“行泉府司事”,掌管广州等处的海外贸易 。行省提调官多半推行“官本船”制,“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抽分之际,常亲临监督,或“阅商舶南海上” 。
行省掌管辖区财政支出,首先表现于对路府州县财政支出的监督。元制,
路府州县如有工役造作,必须先禀报请示行省,乃至朝廷,获得批准,并拨给经费。如顺帝初婺州路兴建通济桥时,就是由新任中书省参政徐某“白于宰相执政”,“符下”,“江浙行省既给以前所没入之钱二万余缗” 。行省对路府州县动用公帑的品种权,甚为重要。路府州县官吏必须遵照其命令行事 。某些情况下,行省只批准造作项目,“官不给钱”,不拨付经费钱款 。行省所属路及散府、州的上计,与腹里内容大体相同,只是按规定增加了“各处正官”每季度“照勘”和赴行省上计,大体是代中书省行事,所以,上计稽考完毕,行省又需要“总其,咨都省、台宪官阅实之” 。岁终上计之外,路及直隶州官吏有责任随时将本衙门的材赋收入申报行省。发现累年“未申除钱粮,虚作实在,为数巨万”,也申报行省“销破” 。上计和稽考财赋时,行省官员有权适当惩罚路州官吏 。
关于行省的财赋支用权限,程钜夫《论行省》云:“今天下疏远去处,亦列置行省……今江南平定以十五余年,尚自因循不改……凡去行省者,皆以宰相自负……钱粮羡溢,则百端侵隐,如同己物。” 从程氏所言看,行省官员的财赋支用是相当大的。程氏《论行省》一文写于江南平定十五年以后,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左右。至元十七年(1280年)江淮行省阿里伯等“擅支粮四十七万石,”朝廷“屡移文取索”税粮,竟“不以实上”;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湖广行省左丞相阿里海牙因钩考钱粮被逼身亡 ……都印证了程氏之说是真实可信的。不过,它反映的大体只是至元二十八年以前的情况。其后,就大不相同了。瞻思《有元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荣禄公神道碑》云:“旧诸行省之用及千定,必咨都省” 。瞻思所述,系大德三年左右事。表明迄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行省只具有机动支用中统钞一千锭以下的权力,超过一千锭,就必须咨请中书省批准。事实也大体如此。一些数额较小的经费开支,如修建路医学教授厅等,行省可以直接批准支用“官帑” 。但对一些数额较大的开支,元中后期的行省往往需要禀报朝廷了。例如仁宗朝陕西“大饥”,行省参政史寻壎在奏报未获准的情况下,“发另廪以赈民”,事先曾作过“设不从,以私家之产偿之耳”的承诺 ;文宗至顺元年()江浙行省重修拱北楼,“縻钞以锭计,一千七百九十有七,米以石计二百九十”,即由“省具闻中书……不逾时,报可” 。违反此类规则,擅自动用官府材赋,会受到责罚。仁宗时岭北行省官员忻都擅自支用“官钱犒军”,即被“免官”。后来,鉴于他用于‘犒赏“军队,而非据为己有,英宗即位才特意降诏恢复其官职 。
耐人寻味的是,若若干年后由于严格实施上述禀报制度,各行省处理政务
多一味禀命于朝廷,显得消极而不敢负责了。针对这种状况,大德九年()中书省又下达公文,谴责各行省应决不决,“泛滥咨禀”的做法。然而,对“重事并创支钱粮”,仍重申“必合咨禀”的旧制 。换句话说,朝廷虽强调各行省积极承担责任,替行省分办庶务,但仍不允许行省官不经请示而动用较多数量的钱谷。即便是各行省历年按国家制度“应付各投下岁赐缎匹、军器物料等”,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每岁咨禀都省,送部照拟回咨”方能发放。直至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五月,才改为各行省“照勘年额相同,别无增减,就便依例应付,年终通行照算” 。
(三)藏富诸省与上供留用
黄溍说:“昔之有国家者,藏富之所,散于列州。而今也,藏富之所,聚于诸省” 。魏晋隋唐两宋,州是地方高级行政官署,又是相对独立的地方财政单位。地方财赋首先聚集于各州,而后再做上供朝廷和地方留用之类的分配。唐后期实行的两税“上供、送使、留州”的三分法,也是以州之财赋单位所征集的财税为基数进行分割的 。元代则不然。州之上,又有路及宣慰司,还有辖区广、品级高、权利大的行中书省。路总管府及直隶州(府)“言可以专达,事可以专决” ,并能在征收赋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除腹里中书省直辖区外,路及直隶州(府)又是直接听命于行省的。尤其是在财赋方面,路及直隶州(府)需要把所征集的财赋先送往行省,并由行省储藏或转运上供朝廷。在此过程中,行省代表朝廷集中各路州的财赋于行省治所,是元代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的关键。特别是元前期行省多以中书省派出机构出现的情况下,财赋聚集于行省,也就等于朝廷的囊中物了。在这个意义上,“藏富之所,聚于诸省”,已是基本将各地财赋集中于朝廷了。各行省直属的仓库,“所统郡邑岁入上供及经费之出纳,无所不掌”。特别是江浙等江南三省,“岁所入泉币-金玉、织文、它良货贿待用之物,以钜万计。所储为甚厚,所系为甚大” 。由于多数财赋集中各行省,所辖区域内各路州仓廒多半空虚,“有名无实”,有些州甚至“粮不宿仓”。得以保留下来的一些路州仓库,也受到行省所派官吏的清查检核 。需要指出的是,藏富之所,聚于诸省“,行省替朝廷征集赋税,早在元行省雏形的燕京等处三断事官时期业已开始。拉施德《史集》说:“合汗()把全部汉地授予了撒希卜马合木•牙剌瓦赤管理;把从畏兀儿斯坦领地别失八里和哈剌火者,[从]忽炭、合失合儿、阿力麻里、海押立、撒麻耳干和不花剌[一直]到质浑河岸[的地区],授予牙剌瓦赤的儿子马思忽惕•伯;而从呼罗珊到鲁木和迪牙别克儿的[地区],则授予了异密阔儿吉思。凡从所有这些地区征收的全部赋税,他们每年都送到国库来” 。
换言之,燕京等处断事官不仅在组织结构、与朝廷的关系等方面,为元行省制提供了基本模式,而且率先充当了替朝廷征集、转运赋税的重要工具。后者对元行省在中央与地方财赋分
配的角色,颇有影响。
随着行省在成宗初由朝廷中书省派出机构转化为地方最高军政机关,各地财赋集中于行省后,自然出现了解运京师、上供朝廷和各省留用的问题。《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大德十一年九月己丑条云:“晋王也孙铁木儿以诏赐钞万锭,止给八千为言,中书省臣言:‘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臣等虑财用不给,敢以上闻。’帝曰:‘……可给晋王钞千锭,余移陕西省给之’”。这段奏言及武宗谕旨,是迄今所见反映行省征集财赋上供与留用关系的重要资料。其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与成宗初中书省右丞相完泽所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 比较,似不包括金、银及税粮石数收入。而中统钞四十万锭的差额 ,估计是成宗一朝所增加的。即便四百万锭只限于武宗初全国岁钞收入,它与“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句,前后相缀,也能说明如下几点:
第一, 全国岁钞收入四百万锭中,二百八十万锭统统解运、上供京师。上供京师的岁
钞数占全国岁钞收入的70%。各省留用仅占30%。
第二, 上供京师二百八十万锭以外,明确讲是由“各省备用”,而未提路府州县。或者
可以说,由于“藏富之所,聚于诸省‘和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行政建置,元中后期中央与地方的财赋分配已是在朝廷与行省之间进行(腹里地区除外)。地方留用财赋的支配权,主要由行省掌握。
第三, 唐后期两税三分制下各州上供数额只是留州、送使之后的自然余数,通常明显低于全国两税收入总额的一半 。元代由岁钞所反映的中央与地方财赋分割比例,竟高达七比三。显然,元朝廷所占比重高于唐代,某种程度上又是两宋尽收州县财赋于中央政策的继续。据说,明代中央与地方盐税等分割比例是八分起运,二分存留,而且也是在中央与各省之间分割的 。如此看来,迄武宗朝已实行的岁钞上供与留用的比例,又开了元明两代中央与地方省级政权财赋分割的先河。
第四, 由于行省起初是朝廷中书省的派出结构,朝廷行省之间财赋七三分成政策之下,
行省仍然主要充当朝廷简直财权的工具。行省除了上供中央和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和严格控制路府州县的财赋支用,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政支出的不足。武宗海山命令陕西行省在上供之外,代朝廷向晋王支付一千锭赐钞,即属此例。
至于粮食上供,更表现了中央利用行省对江南稻谷主要极力产地的搜刮。世祖朝创立江南之粮海运入京师制度以后,海运粮食由每岁四万余石,逐渐增至三百余万石。这些粮食多取之于平江、嘉兴、松江为中心的江浙行省。然而,元后期江浙行省税粮年收入最高是四百四十九万四千八百八十三石 。显而易见,江浙行省税粮收入的一大半,都要被解运京师。元人陈旅说:江浙行省“土赋居天下十六、七” ,殆非虚语。这种异乎寻常的搜刮,使江浙行省可供民间食用的粮食数额大为减少。成宗大德年间,号称天下粮仓的江浙一带,连年发生严重饥荒,甚至出现了“野无青草树无肤,人腹为棺葬万夫”的悲惨景象 。这或许是元廷对江浙行省肆无忌惮的粮食搜刮所间接产生的恶果之一吧!
各行省的上供与留用虽然在整体上实行七三分成政策,但因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具体执行上述政策时,各省很不平衡,差异相当大。元制,“一岁入粮一千三百五十万八千八百八十四石,而江浙四分强,河南二分强,江西一分强,腹里一分强,湖广、陕西、辽阳一分强,通十分也” 。一般说来,在每年上供朝廷二百八十万锭中统钞等财赋总额内,经济富庶的江浙、江西等江南行省为最多。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岭北、辽阳、甘肃、云南等行省,不仅税粮、课程岁办额较少,而且岭北等行省的经费也主要由朝廷拨赐。这类经费拨赐,少者万余锭,多者几十万锭,几乎达到全国岁钞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盐引、杂彩、粮食、金宝等赐与 。拨赐数额多半远远超过该省年度税课收入。元廷之所以拿出如此大数额的钱谷拨赐上述几个行省,是有缘由的。有元一代,岭北是蒙古肇兴之地,又系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和蒙古大千户所在。自世祖朝,元廷方面长期屯列大军于和林、称海等地,防御叛王骚扰。“朝廷岁出金缯布幣后餱粮以实之,转输之事,月日相继,犹以为未足。又捐数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又可胜计。由是遂为殷富。”岭北行省获取巨额拨赐,主要是用于供给驻屯军队,赏赐诸王及各千户部民 。“甘肃省僻在边陲,城中蓄金谷,以给储王军马”,“仰哺省者十数万人” 。云南行省和河南行省也是蒙古军都万户和万户密集驻屯之处 。元代岭北、甘肃、云南、等少数行省向朝廷上供很少,却能从朝廷得到数量可观的经费拨赐,完全是为着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防御西北叛王和镇遏被征服地区的政治和军事需要而服务的。在某种意义上,岭北、甘肃二行省的设置宗旨,也于其它汉地行省有所差别。供给军需,赏赐和安抚诸王部民,始终是着两个行省的主要使命和职司。
江南三行省担负大部分上供财赋,与岭北、甘肃等行省很少上供、反倒获取朝廷的巨额经费拨赐,造成了元代行省上供与留用,乃至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体制内极不平衡的状况。由于这种不平衡,全国范围内中央与行省间上供与留用的比例虽然大体是七比三,但70%的上供数额绝大多数由江南三省承担。具体到这三个行省向朝廷上供的数额,肯定会高出70%很多。这就使元代中央与地方的财赋分割中,南方北方待遇高下悬殊,北方受优遇,南方受榨取,最终大大加重了江南三省民众的赋役负担。元末“穷极江南,富夸塞北”的怨谣 ,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上述财赋分配不平等的愤*和抗议。值得注意的是,元廷对江南三省的过度榨取,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至大元年()江浙行省绍州、台州、庆元等六路大饥,“死者相枕籍,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有不忍闻” 。但当年十一月朝廷又以“近畿艰食”为由,强令江浙行省“岁运海道粮二百三十万有奇”,较前一年的一百二十四万石增加一百多万石。元廷不用江浙储粮就近赈济濒死之饥民,反而大幅度增加江浙北运京师的漕粮数,真可谓不顾江浙灾民之死活!在这个意义上,至大二年主持江浙行省春运五十八万石至京师的乌马儿平章,显然是元朝廷的大功臣。然而,对江浙一百三十三万流离失所的灾民来说,他又是千古罪人!正如虞集所言:“海运之实京师,国家万世之长策也。然而,东南之民力竭焉,频岁浙西水旱,廪不充数,江淮上流三省数十郡州县之吏、斗升之民,终岁勤动,越江历湖,以助其不足,而争斗无机勿戢,又有深可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