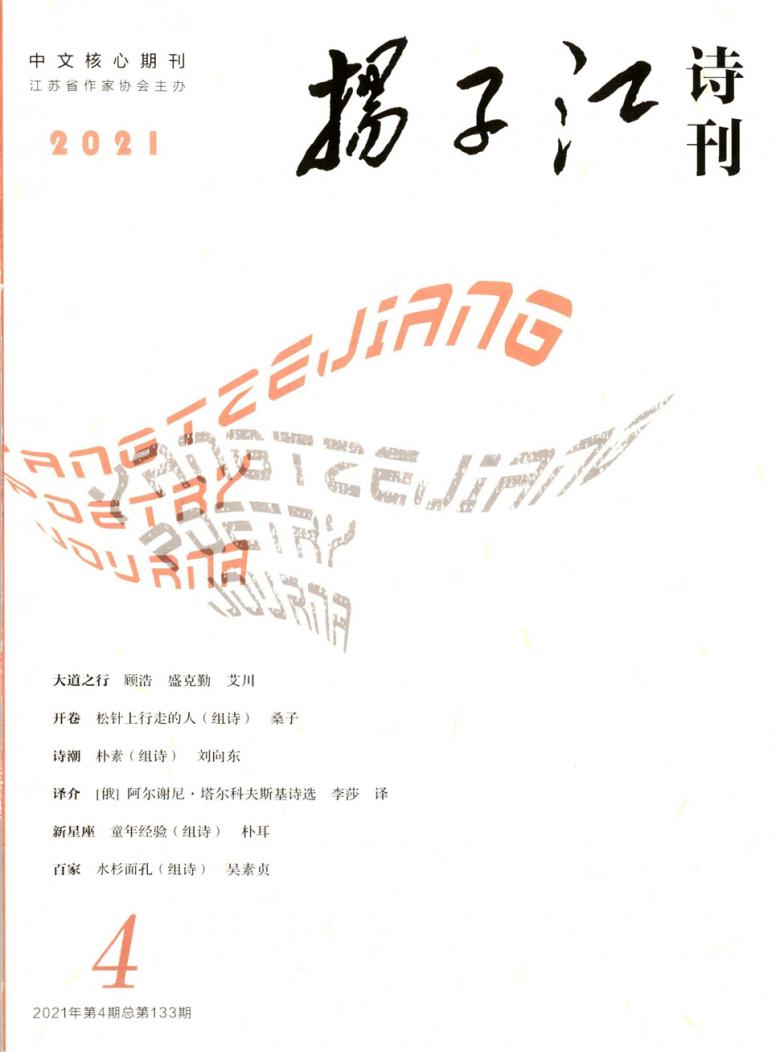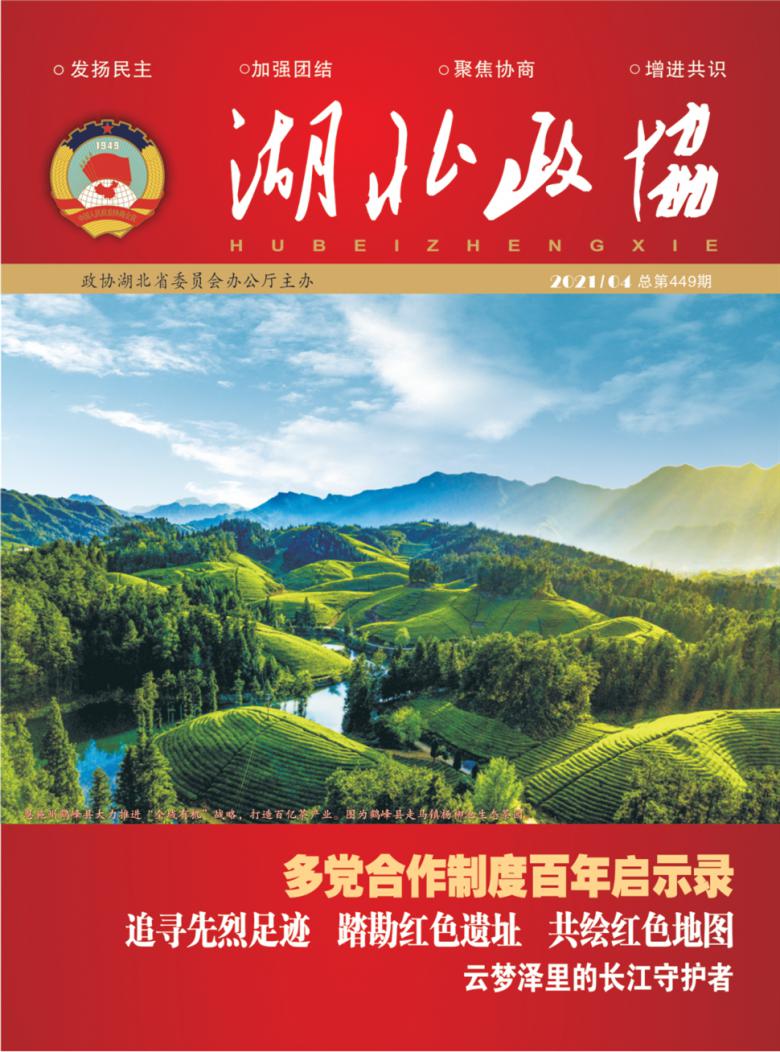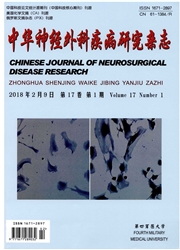试析明代杜诗诗史说分析
王世海 2010-07-15
论文关键词:明代 杜诗 诗史
论文摘要:明代诗论家对杜诗诗史说的阐释有着独特的视点,杨慎首发其论,驳斥诗史合称,认为诗不可兼史;而许学夷等依据杜诗本身特色,虽在理论上同意杨说,但对杜诗诗艺的评价从另一角度肯定了杜诗诗史说;王文禄则从杜甫本人人手,揭示出诗史产生最根本的原因。他们推动了杜诗诗史说的发展。
自孟綮《本事诗·高逸第三》以诗史之称评价杜诗后,这一说法便成为后代诗论家考评杜诗的重要层面。观孟綮所论,“毕陈”、“推见”、“殆无”表明叙事详尽,而“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指明所叙事类,由此而论,诗史意应为杜诗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生活事实,接近似《史记》列传体的诗。晚唐时,李肇的《唐国史补》,郑处诲的《明皇杂录》,康骈《剧谈录》等书多引杜诗以证史事,如《悲陈陶》、《悲青坂》、观水涨》、《草堂》等。及至宋代,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云:“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以时事来申述孟綮语“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已将杜甫个人的历史置换为当时的社会历史,依据是杜诗多处涉及当时事,且多首杜诗直叙时事,或叙议时事。而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云:“……先儒谓韩昌黎文无一字无来处,柳子厚文无两字来处。余谓杜子美诗史亦然。为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姚宽《西溪从语》云:“或谓诗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类,故名诗史。”此解释方法发展到极致,便出现了史注杜诗。刘克庄《再跋陈禹锡杜诗补注》云:“盖杜公歌不过唐事,他人引群书笺释,多不咏着题。禹锡专以新旧唐书为按,诗史为断,故自题其书日:‘史注杜诗’。”在他们的论述里,诗史的意义变为杜诗中语言的实际可考了。诗史中史义的变迁,可视为进一步阐明杜诗的必然结果,然时事与一人之史差别巨大,且以时事义诠释诗史,值得商榷。
明人对宋元诗话,多作省悟、反驳。他们不拘泥于前代论述,多有发明。何景明《明月篇序》以诗“贵情思而轻事实”为理论基点,对杜诗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博涉世故”、多叙时事的杜诗,比、兴少而赋体多,与《风》诗传统相背,不合诗旨。王廷相亦有相近的看法。对“诗史”说辨证尤力的首推杨慎。他紧承二人路数,对诗史说作了更细致的驳斥。《升庵诗话》卷四《诗史》云:“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记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隋句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何谓诗史?“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史记言,纪事,诗多不纪时事,应各司其职,这是体例的区别要求;且诗以含蓄为旨,杜诗直陈时事,怎能含蓄?这两点共同奠定了杨慎“诗不可兼史”的理论基础。虽然在实践中,以韵语纪时事的诗已经存在,由于诗不可兼史,后世就不应用诗史之名来称道和概括这样的诗,此显示着诗学理论的规范。然如胡应麟对杨慎此论指出的一样,诗史不首出宋人,应以孟綮为先。据上分析,孟綮诗史中“史”并非指时事,应指杜甫一人之史,杨慎反驳了宋人之见,但没有反驳孟綮诗史之义;且他没有对杜甫诗史诗作细致分析,缺乏充分而实质的例证;以“韵语纪时事”概括诗史的意义,显其浅陋。继他之后的王世贞对此论述作了修正,《艺苑卮言》卷四云:“其言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称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语荒而日‘周馀黎民,靡有孓遗’,劝乐而日‘宛其死矣,它人人室’,讥失仪而日‘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怨谗而日‘豺虎不受,投界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如何贬剥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之。”“述情切事”与“韵语纪时事”或“直陈时事”区别显明,且赋不以时事发之,以此来驳杨慎“诗不可兼史”不能成立。杨慎论含蓄,《诗史》云:“《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由“未尝有……字也”、“未尝有……句也”可知,杨慎的含蓄意义就是诗中所寓美刺褒贬不应用语言直接说出。这样的观点在评论杜诗中也有表现。《升庵诗话》卷八《不嫁惜娉婷》云:“杜子美诗‘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读者忽之耳。陈后山衍之云:‘当年不嫁惜娉婷,传粉施朱学后生。不惜卷廉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盖士之仕也犹女之嫁也,士不可轻与从仕,女不可轻与许人也”;又云:“‘锦城丝管纷纷,半人江风半人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花卿名敬定,……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含蓄要求诗意多采比兴手法,以达到讽诫的诗教目的。王世贞认为“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反驳杨慎由《三百篇》引出的“诗皆含蓄”的论断,又得出了“诗不皆含蓄”的结论,还不能说明“以韵语纪时事”的诗便可以被称为好诗,且进一步推论为诗可以兼史,诗史之名可以称论杜诗。不能推翻杨慎第一论点,便不能作如此的推论。他在末尾云:“‘慎莫近前丞相嗔’,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之”,能证明诗可以这样写,有历史传统可依,然与诗史无涉。他仅以单例(赋相对比兴言,“语荒”等相对刺淫乱言)反驳杨慎,未能把握杨慎理论核心,故此论还不能为诗史提供深入而恰当的阐释。
及至许学夷,其《诗源辩体》对杜诗诗史说的论述,为诗史说提供了新的阐释意向。许氏云:“愚按:用修之论虽善,而未尽当。夫诗与史,其体、其旨,固不待辩而明矣。即杜之《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哀江头》等,虽若有意纪时事,而抑扬讽刺,悉合诗体,安得以史目之?至于含蓄蕴藉虽子美所长,而感伤乱离、耳目所及,以述情切事为快,是亦变雅之类耳,不足为子美累也。”闭诗与史体旨分辨明晰,诗不可兼史固然正确;杜甫诗史诗抑扬讽刺,虽纪时事,然不离诗体,不应将诗与史合称赞颂杜诗;述情切事为快的杜诗,皆感伤乱离,耳目所及,非史家笔录史实,为变雅体。他肯定了杨慎“诗不可兼史”的理论观点,立论却与其不同:杨慎认为史主纪事,诗不记事,故诗不可兼史;许氏认为诗能抑扬讽刺,史不能抑扬讽刺,故诗不可兼史。可见,许氏更关注杜诗诗的特征。他在《诗源辩体自序》中云:“汉魏六朝,体有未备,而境有未臻,于法宜广;自唐而后,体无弗备,而境无弗臻,于法宜守。易昌:‘拟议以成其变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呜呼,安得起元瑞于地下而证予言乎。夫体制、声调,诗之矩也,日词与意,贵作者自运焉。窃词与意,斯谓之袭;法其体制,仿其声调,未可谓之袭也。”他认为诗应分体与境或体制、声调与词意,在论述杜诗诗史说时,自然也将杜诗的体制和词意区分开来论。“抑扬讽刺”不是诗体,是诗旨,杜甫诗史诗合诗旨,不能以史称;纪时事诗,为诗人亲身所历又出于感伤乱离,不失《毛诗序》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由此而出的诗体可视为变雅体,合诗体,不能以史称,故杜甫这些诗不应以诗史之词命名。许氏集中论述了杜诗本身的特征,从诗的角度完全肯定了杨慎所反对的“以韵语纪时事”的诗,说明它既合诗旨又合诗体,最终认为杜诗不应以诗史来称,可谓与杨慎殊途而同归。然而,此论还不能驳倒诗史之名的成立。许氏承认诗史之义应指杜诗纪时事,其合诗旨,合诗体,对这些诗因纪时事引起的争论作了新的解释。在杜诗评论上,他不囿于宋人观点,对诗史名篇的艺术特征作了尽情的发挥。如“石壕、新安、新婚、垂老、无家等,叙情若诉,皆苦心精思,尽作者之能,非卒然信笔所能办也”,“子美五言古,凡涉叙事,迂回转折,生意不穷,虽间有诘屈之失,而无流易之病”,“子美五言古,如自秦州人蜀诸诗及新安、新婚、垂老、无家洎七言律声调浑纯者,为甚精细”,“如《哀王孙》、《哀江头》等,虽稍人叙事,而气象浑涵,更无有相类者”,“谢茂秦云:‘长篇最忌铺叙,意不可尽,力不可竭,贵有变化之妙。’苏子由云:‘老杜陷贼时有《哀江头》诗,予爱其词其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愚按:子由此论,妙绝千古,然子美歌行,此法甚多,不独《哀江头》也”。杜甫诗史诗多用叙事,涉及时事,但并未伤害诗意的表达,诗艺的创造,其原因一是杜诗皆作者苦心精思所为,非史实录;二是杜诗皆迂回转折,气象浑涵,表现出作者个人高超的艺术技巧和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些论述具体而充分地阐释了杜甫诗史诗的诗学特征,此非史能比,亦非一般诗人能比。纪时事,“不足为子美累也”,不应构成杜诗阐释的中心,杜甫个人的语言创作,杜诗的独特风格才是阐释的重心所在。许氏的这番论述巧妙地回应和深化了孟綮诗史说的本源意义,有关杜诗的具体阐释也证实了“以韵语纪时事”的诗皆是“杜甫个人创造实践”的结论,使杜诗诗史说的讨论本然回归到杜甫本人。然而,因时事人诗而引起的诗与史的辨证,以及诗与史能否合一问题的讨论,许氏没有作深入的阐释。 论述诗史说,必须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吻合,这是许氏留给后人的阐释方向。谢肇浙《小草斋诗话》云:“少陵以史为诗,以非风雅本色,然出于忧时悯俗,牢骚呻吟之声犹不失三百篇遗意焉。至胡曾辈之咏史,直以史断为诗矣。李西淮之乐府,直以史断为乐矣。以史断为诗,读之不过呕哕。以史断为乐,何以合之管舷?野狐恶道,莫此为甚。”嗍“胡曾辈之咏史”中的史,相对胡曾辈,已经是过去的历史,故据上下文可知,“以史为诗”中的史指过去的历史;“忧时悯俗,牢骚呻吟之声”指杜甫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当时的心境和情绪,前后史义显然存在矛盾。谢氏的矛盾述说,透漏出了诗史说阐释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即:“诗史”中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两《唐书》等史书中史,同形而异义。依孟綮所言,诗史之名的核心是诗,在他的论述中,前半为诗之内容,后半为诗之效果。
诗中“推见至隐,殆无遗事”的正是“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之事,诗史中史的含义很明确,指“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的事,史字为此现象的符号标识。然而,这样做在理论上很容易造成意义含混。宋人将诗史中史落实在时事上,使史脱离开诗;杨慎基于宋人论断,完全将诗史分开来论,说明二者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作出“诗不可兼史”的驳论;这些均可视为诗史中史字带来的负面效应。许学夷更关注诗史说名下杜诗自身的特征,多少回避了诗史概念本身存在的矛盾,仅论到“夫诗与史,其体、其旨,固不待辩而明矣”;谢肇浙依循许氏的视角(不注重诗史概念本身,只注重杜甫和杜诗的特征),便将此视角存在的矛盾凸显了出来。论述杜诗诗史说必须首先辨明诗史概念,否则便造成了诗史说与杜甫诗史诗的双向背离:杜甫诗史诗在诗艺上阐释越显明,诗史之义越模糊,混乱。因为对二者的任何阐释都只是为了阐明一个问题:以诗史之名指称这些杜诗特征合适吗?
宋代周辉《清波杂志》云:“叩于汝阴李遐年,李日:‘诗史犹国史也。《春秋》之法,褒贬于一字,则少陵一联一语及梅,正《春秋》法也。”’诗寓讽谏,多褒贬当时,与《春秋》等史以史事纪录来经世资鉴,虽方式不同,社会功能却是相同的。这可为诗史之名的成立寻找到一定根据。此观点在宋代还不昌明,至明代则甚多。如程敏政云《诗》美刺于《春秋》褒贬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后世词人遂有以诗咏世者。唐杜少陵之作妙绝古今,号诗史。第其,且多长篇,读者未能遽了。”闱以诗咏世,求美刺,与史寓褒贬一样,可达到匡正时政,教化子民的目的,这只能说明诗与史在此点上是相同的,不能就此断定诗可以与史合一;以诗咏世,也并不能说明记录时事的诗便可以称为诗史;“所识者皆唐事”和“史记录的唐事”存在本质差异。杜诗诗史说的内涵和诗史中史的内涵不应简单地因诗与史在某点上有相同之处或不同之处就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在这一点上,王文禄则另辟蹊径,为诗史说的成立找到了更为可信的根据。他在《诗的》中云:“杜诗意在前,诗在后,故能感动人。今人诗在前,意在后,不能感动人。盖杜遭乱,以诗遣兴,所以叙事、点景、论心,各各皆真,诵之如见当时气象,故称诗史。”“当时气象”指诗中事景情的接受性再现的景象;以诗遣兴,合《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旨。兴或意才是诗创造的唯一源泉,这样,诗才能做到事景隋真实的表达。诗史中史由“诗应以意为先”、“作真实的表达”这一论断衍出,应为诗中再现出来的过去事实。具体而生动的事景情并非一般的史能够囊括,若用史字统摄它们,难以让他人接受。然而,王文禄明确指出杜甫创作的基本原则,为“意在前,诗在后”、“各各皆真”,这为诗史说的阐释提供了一个重要前提。杜甫意在前,诗在后,故能真实的再现出当时的客观事实,他的诗也因此具有了史的价值,“如见当时气象”。宋人胡宗愈《读杜工部诗集序》所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阿是此论最好的延伸阐释。
综而言之,诗史中史指杜甫“禄山之难,流离陇蜀”真实的生活,指真实再现的当时社会历史,还指“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等杜甫和当时民众真实的思想、情感和愿望。杜诗不仅是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且成为当时人在政治祸乱中哭嚎和呼唤的真实描述,正如浦起龙《读杜提纲》所言“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即使诗史中史有了明确而丰富的内涵,那么能否断定诗史之名在理论上就一定能够成立?这仍待进一步的探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杜诗这些丰富的内涵用一个合适的词来命名。
明人在宋人诗史说基础上进行激烈的反驳与辨证,使诗史说逐渐走向澄明。清人所论视角不出明代,然略为显明。如钱谦益《胡致果诗序》云:“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诗史。”施闰章《江雁草序》云:“杜子美转徙乱离之间,凡天下人物事变,无一不见于诗,故宋人目以诗史”陈玉王基《借竹轩诗序》云:“若为唐人诗尽无撼,何以言诗史者独推一少陵?夫史之可贵者,以其信也,唯真则可信,此昔人所为善论少陵诗也。”
诗史说是杜诗诗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明人对诗史说的探讨,多不集中于概念,往往将概念所及的杜诗及其他杜诗作出品评来辨证诗史;若集中概念,则将杜诗特征忽略,这样做,杜诗与诗史之名发生了分离。诗史之名首先属于杜诗,然其成立必须在中国传统文论中诗与史概念的内涵中得到阐明。诗史中史不仅存在于一般史的范畴中,更直接存在于杜诗的特征里。故杨慎等人诗与史的辨证将诗史之名完全脱离杜诗,以含蓄来反对时事诗,自然有失偏颇,诗史不是诗的概括,而是杜诗特征的描述。许学夷与谢肇浙回避诗史,只论杜诗的艺术特征,与诗史说渐趋远矣;从诗美刺与史褒贬同一的事实来肯定诗史存在的合理性,与杨慎等思维视角相同,忽略了诗与杜诗的区别;王文禄由“真”论杜诗特征,为诗史说的成立提供了重要依据。杜甫诗史诗特征足以证明诗史之名有具体而丰富的内涵,且其真实可信的表达和再现使其完全具有史的价值。这些独特的诗学特征及杜甫独特的诗学风格完全超出了一般诗学理论范畴,因此,后学者必须在诗学理论中确立一个合适的名词来给予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