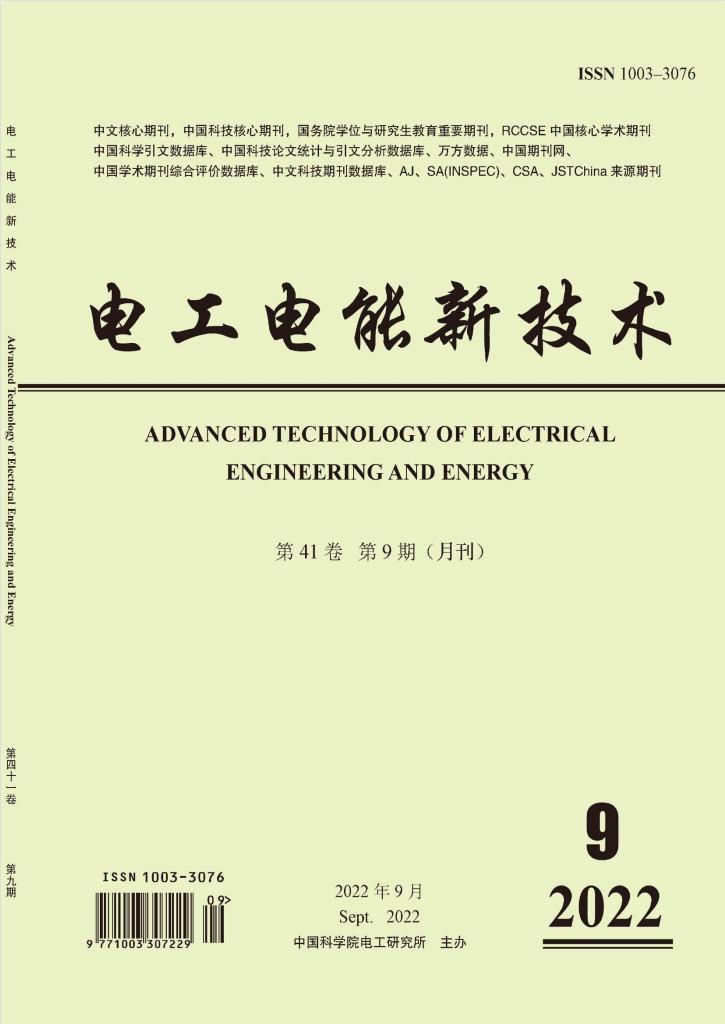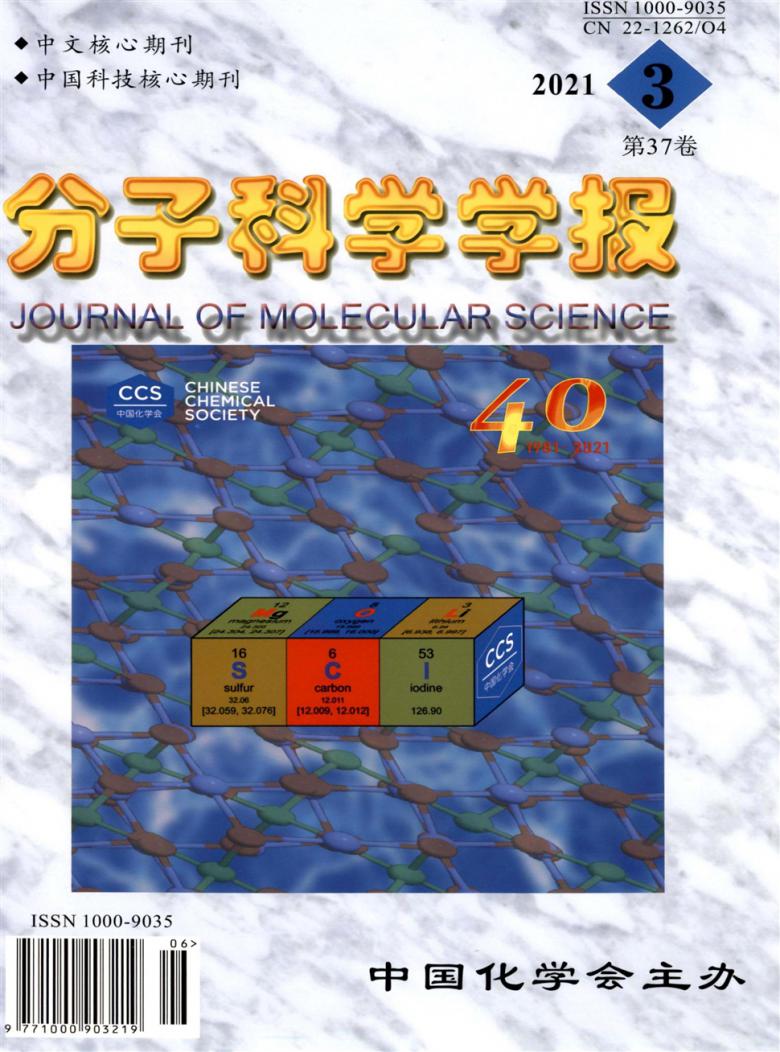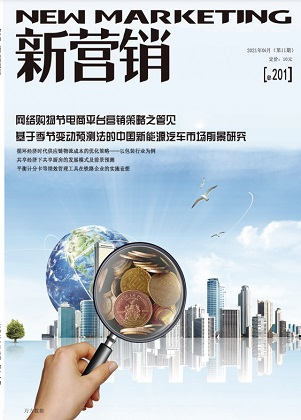关于政治哲学视阈下的儒学人文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刘晗 2011-11-04
摘 要:儒学既重人文,又尊理性,是倡行人文理性的政治哲学。儒学的这种品格是其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它已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和社会生活中积淀下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而今,正确看待这一传统,发掘、借鉴儒学独特而有价值的文化内涵、道德伦理,有助于造就推动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 关键词:儒学;人文精神;道德理性;人类文明
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时,儒学人文思想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根据儒学人文思想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特点,更多地看到其强调人的群体性和塑造理想人格的方面,却忽略了它维护和发展个体的理性及人格尊严的一面。实际上,儒学既重人文,又尊理性,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儒学的这种品格是儒学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它已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和社会生活中积淀下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而今,正确看待这一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对于推动现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此,本文试从政治哲学的视阈对儒学的人文理性及其当代价值进行解读,并请教于方家。 (一)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学问,强调人与人的关系,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是其最根本的特质。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更是注重探讨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实现等问题。儒学的人文思想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逐渐形成的。 儒学的人文思想奠基于孔子“仁”的学说。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在《论语》中出现最多,但其内涵总离不开“人”,如人性、人道、人生价值、人际关系等。孔子主张“爱人”,其基本要求是尊重人,他要求通过“敬”即人格的尊重来凸现人不同于物的人文本质,“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强调爱人、尊重人的仁道原则应以孝悌为基础,从家庭敬爱父母兄长做起,然后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以至于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广大境地,由此定下了儒学重人文的基调。 孟子沿着孔子仁者爱人和能近取譬的思路向前推进人文思想。他强调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即人类的同情心,这就是“性善论”的内容和成人之道。他还把仁爱从人推及于万物,进而发展为“仁政”学说。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不忍人之政亦即所谓仁政。这样,从孔子的仁道到孟子的仁政,儒学人文思想便表现出一个深化的过程:它开始由一般的伦理要求,进一步提升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准则。在孟子这里,儒学人文的价值取向已进一步趋向于定型。 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不仅是孔孟的主张,也是战国至汉唐儒者的共识。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董仲舒也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礼之所为兴也。”(《春秋繁露·服制像》)万物的存在,不过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人具有高于万物的价值,“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人的作用在于使天地所生所养的万物日臻完善,“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唐中期韩愈对孔孟的仁者爱人更作了高度概括,提出“博爱之谓仁”(《原道》),可以说它是对孔孟泛爱说的人文思想的发展。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文化需要,从“天人感应”的角度,强调“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从而将儒家伦理神圣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孔孟儒学执著现实的人文思想路径,也使得儒学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但是,董仲舒所讲的“天人感应”是一种被人格意志化的自然与人之间的感应关系,他所精微论证的“天”仍是为了说明和解决现实的“人”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董仲舒神学化的儒学中所透露出的是“要求君王实行儒家的道德理想,期望借助帝王推行儒家仁政以有助于人的实现这样一种向往”,即便是其后兴起的以名教与自然之辨为核心思想的魏晋玄学,也是“希望建构起一种无违于伦理名教,又能使每个人的自然之性得到充分伸展的理想模式”[1]67-68。虽然思维路向不同,但它们都是希望建立一种能尽量满足人性发展需要的理想的社会秩序,体现了儒学在特定时空下对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所作的理论探索。 魏晋以后,特别是隋唐时期,佛、道二教风行,其间虽有韩愈等人极力捍卫儒家道统的努力,但社会上下对神的膜拜趋向渐渐使人自身的价值变得模糊,儒学的人文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对人自身价值的重新确认,便历史地提到理学的面前。从肯定人文价值出发,理学对仁的内涵作了更多的考察。如张载认为,宇宙是一个大家庭,天地如父母,养育万物,人类如儿女,因而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要求爱一切人如爱同胞手足一样,并进而扩大到“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正蒙·大心》)。他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不仅有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意义,而且有调节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超道德意义,因此人生的最高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包含了人与宇宙、人与人的双重和谐。这种“民胞物与”的观念,上承韩愈的“博爱之谓仁”之说,再现了先秦儒学从亲子伦常关系向外辐射的思路,同时又使儒家的仁道原则获得了更为宽广的内涵,强化了儒学的人文精神。王阳明对这一观念也作过发挥:“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王文成公全书》卷2,《传习录中》)相对于先秦儒家较多地注重亲亲的基础而言,宋儒和明儒则更多地由家庭关系的泛化即民胞物与,而将仁道原则引向天下之人,使儒学的人文精神进一步获得了超越宗法亲缘关系的意义。 (二) 儒学人文思想,起自先秦,历经汉、魏晋、隋唐到宋元明清,延续不断。仁的发展过程,也是儒学理性原则指导下的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实现等问题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重人文,尊理性,是儒学的一贯品质。这里的“理性”,不仅指狭义的认知领域的逻辑思维,而且也指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道德理性及其与这种道德理性相贯通的实践理性。道德理性是儒学理性的抽象形态,也可称之为观念性形态或理想形态,而实践理性则是抽象的具体,或称为道德理性主义的实践。 具体而言,道德理性是指儒学追求理想人格的主体的精神力量,它是以主体对天道的认识和体悟为前提,是主体靠理性认识掌握了“道”与“义”而形成的。理想人格是具体的,而“道”则是超越的、永恒的。
作为一种本体意义的“道”,在先秦儒学里主要讲的是“人道”,即做人的最高准则。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道”、“天道”、“天命”等范畴,其真实的内容就是有相当普遍价值的道德伦理。后来孟子讲“性善”,认为“尽心、尽性、知天”,人类善的内在本质可与天道相通,故《礼记·中庸》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宋儒那里,“道”范畴又被进一步形上化为宇宙的本体,其“天理”的一面又被直接突出。由此可见,儒学中的“道”兼具道德仁义和道理即天理的双重内涵,具有某种信仰色彩的超越层面。
儒学的道德理性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具体化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和价值选择的标准。孔子主张为仕应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道的价值高于一切,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荀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提出了“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的命题,指责那些只知“从君”却“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者为“国贼”(《荀子·臣道》),主张儒者“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荀子·儒效》),儒者必须时刻以道自律,随时保持道的独立价值,从而也就保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宋明理学家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弘道精神,并将其发展为以天理制约权势的道德人文走向。关于这一点,明代理学家吕坤曾作过较为详备的论述:“天地之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之尊之又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既夺焉,而理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以恃以为存亡者也。”(《呻吟语·谈道》)人世间惟理即道与势最尊贵,其中理又尊于势,并且势之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正在于理。而儒者的行为是应当遵循“理”这一最高准则的,故敢于且应当“任斯道之南面”而不屈于帝王之权势。儒学虽然主张儒者应当入仕辅佐人君,但绝不赞成作为人君的驯服工具。所以,儒学所谓的“理想人格”并非是某种纯然主观的东西,因为它有客观的基础和来源,这客观的基础和来源就是天道。这是一种人的理性自觉,这种主体的精神力量,我们称之为道德理性。 所谓实践理性,是指主体修身养性过程中以理智引导情感的自制力量,是以道德理性为导向,以体现和实现天道为特征的理性具体。从根本上说,儒家的实践理性,主要还是道德理性。为了论述方便,这里把“实践理性”区分出来单独论述,主要是为了分析儒家在理想人格概念中如何处理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关系的问题。 中国儒学很早就探讨了理性与情欲、意志的关系问题。应当说,先秦儒学大都强调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要求培养知情意相结合的完美人格,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有了智慧、廉洁、勇敢和才艺,又用礼乐来美化,才是完善的人格;孟子讲人的善的本质包括仁义礼智四端,并说“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荀子也讲“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含有要求人格全面发展的意思。关于“志”,儒学也十分重视。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则有“士尚志”和“持志”之说。不过,孔孟均强调“志向”,注意的是意志的坚韧品格。宋明理学对“志”和“意”作了区分。张载曾指出:“盖志意两言则志公而意私。”(《正蒙·中正》)明儒王夫之在注解《正蒙》时对此说作了进一步发挥:“意之所发或善或恶,因一时感动而成乎私;志则未有事而豫定者也。意发必见诸事,则非政刑所能正之;豫养于先,使其志驯习乎正,悦而安焉。则志定而意不纯,亦自觉而思改矣。”(《张子正蒙注·中正篇》)“志”是预定者,与“天下之公是”即天道、天理相联系,故为“公”;意即意见、动机,因一时的感动而产生,与个体的内在需求相联系,所以是“私”的。王夫之注意到“意”之所发有自主性特点,非政刑所能正之,故强调“教者尤以正志为本”,“志正而后可治其意”,而反对“无志而唯意之所为”,亦在其理想人格中贯彻了理性主义和自觉原则,而否定了意志的自由选择功能。这一点与先秦儒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可见,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宋明理学,在追求理想人格,体现和实现天道的过程中,都注重突出理性的价值和地位,而压制和排斥作为理想人格精神主体的非理性层面,进而逐步凸显了儒学的理性原则。 如果说道德理性表现为道德意识的自我认识和本体意义上的理想状态,那么实践理性则主要表现为实践经验的内心体验。二者在它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天道的汇合处达到一致,是知与行、理想与理性的统一,是“抽象”和“具体”、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统一。正是这种理性精神使儒学摈弃了宗教神秘的玄想和狂热,使人们在日常伦理生活中以理智来引导情感,从而使儒学成为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那样的神权统治人间的宗教化时期,实根源于儒学重人文、尊理性的价值取向。 (三) 如上所述,儒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主体自觉精神的强调,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视,都有其独到之处。固然,儒学在历史上曾经被赋予了神学形式并不断得到政治上的强化,因而使得它的一些主要内容被异化为强制人们接受与遵守的道德戒命和外在规范,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儒学主体的理性自觉和自由选择,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维护了封建统治,扭曲了儒学注重人文的哲学形象。但是,由于儒学的形成深深植根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思想,其基本信仰是“仁”、“礼”、“孝悌”。更何况,儒学士大夫们不惜经受风险与磨难,在千锤百炼中极力寻求适合现世的儒学本身的发展途径与形式,这一过程实际又进一步弘扬了儒学人文主义的道德气质和理性精神。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儒学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解体。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传统儒学赖以存在与生长的社会土壤,其存在形态与社会地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此后,儒学则是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被研究、改造与利用。今天我们研究儒学,就是为了从传统儒学遗产中批判地吸收可取的、有益的思想资料,以重建人类新的精神文明。
特别应当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具有二重性质,它既体现了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趋势,又往往蕴含着负面的文化后果,后者在西方的工业社会已越来越严重地显露出来。由于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被物化,道德失衡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蹈袭西方产业化道路之后,盲目地追求物质利益,因之导致了利益关系上的个体化趋向,个体原则空前突出。个体原则的注重诚然为主体创造性的发挥、个性的多样化,及竞争机制的引入等提供了活动空间,但由此而过分地划定个人权利界线,并以无情的竞争作为实现个体权力的方式,却很容易导向个人主义乃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与普遍的商品化交互作用,使人与人之间只有契约、业务及竞争的关系,而缺乏超功利的、情感的联系纽带,其结果即是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乃至紧张、冲突。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表明:当代欧洲“十分之六的人认为,就他们所经历的十多年的经验而言,人们很少愿意彼此帮助。这是人们不相信他人的原因。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表示,当他们同他人打交道时,从来都相当谨慎。”[2]125这种心态,正是植根于冷淡、紧张的现实人伦。相对于此,中国传统儒学偏重于道德人伦范围,即使是作为政治化儒学所倡导的带有封建性的“三纲五常”,也多少体现出对道德作用和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视。儒学这种重视人伦以及追求崇高人生境界的价值取向,正有助于引导人体认自身的内在价值,避免一味向外逐利,并进而拒斥人的商品化。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的利益越来越趋向于一致性,一利俱利,一毁俱毁。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矛盾、小集团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矛盾。如果只追求个体利益、小集团利益的满足,那么,人类将有可能走向自我的毁灭。所以,我们应该借鉴儒学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弘扬儒学的人文理性精神,从我做起,修身养性,立人、达人,推己及人、推恩及人,积极有效地防止异化,克服异化,使人们在理性情感上走出自我封闭的樊篱,走向宽容、和谐,使人们真正生活在仁爱的环境氛围和理性情感之中。
但是,在现在乃至未来,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的生态环境并不容乐观。现代文明的基本进路是征服与利用自然,它不断地打破人与自然的原始平衡,不断实现对自然的支配。这种原则虽然拒斥了对自然的宿命态度,为改造、利用自然奠定了价值观的基础,然而,它同时也引发了对自然的片面占有,由此造成了天人之间的紧张和随之而来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日益枯竭,环境的污染,土地沙漠化,某些物种的灭绝等等。这种全球性的问题使人类面临严重困境。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忧心忡忡地指出:“一种不停顿的杀戮生机勃勃事物的行为最终将导致全面性的破坏。”[3]121这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天人之间的失衡,在今天确实使人类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为此,人类必须以理性的自觉控制自己的活动,做到既合理地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又能够积极地保护和建设人类生存环境。 儒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保持天人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其人文精神也以自觉追求人的天性到德性的完满为归宿,这种道德理性主义无疑有助于抑制对自然对象的支配和征服意识,特别是宋明理学那种万物一体的天人观,确乎表现了一种博大的胸怀,超越了实际造成现代生存危机的狭隘的人类中心论。这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注重人与自然的区分与对抗的思想,又不同于道家“无为”的自然观和佛教“一切皆空”、“无我”出世的虚幻主张,它坚持“尽性知天”、“生物成物”、“为天地立心”等,流露出强烈的宇宙意识、生态情感、人类责任心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对于合理地调整天人之间的平衡,同时又在总体上不断重建天与人的统一,确实可以成为一种内在的范导原则。 人类文明是全人类自古以来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当今整合与重建人类文明仍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东西方各种不同的文化、信仰各异的多种宗教等等都会在整合与重建人类文明中做出自己的贡献。由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在共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既表现出惊人相似的共同价值、共同理想,又各有自己对人生终极关怀的不同理解、不同追求,因而应该创造条件使不同文化展开对话,相互协调,以讨论发展一种“普世伦理”, “这种伦理必须是全球性的,只有某种西方人的共同伦理,或非洲人的共同伦理,或亚洲人的共同伦理等等,那肯定是不够的”[4]141-142。这是全人类的创新性文化活动,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是人类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生命呼唤,也是为了实现社会现代化或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危机所凸显出来的历史重任。历史在革新中运动,文化在创造中发展。中国儒学的优秀文化遗产,必然在参与解决全球性的伦理问题上,在人类智慧的创造与积累中被更新的文化所吸取和弘扬,因为它有浓厚的人文理性追求,鲜明的道德伦理价值,易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因而有更多的普世性和超越性,必将在人类未来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做出特殊的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1]洪修平.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2][法]让·斯托策尔.当代欧洲人的价值观念[M].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3][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M].文韬,佩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1. [4][德]孔汉思,库舍尔.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M].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