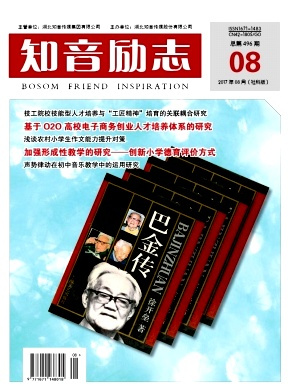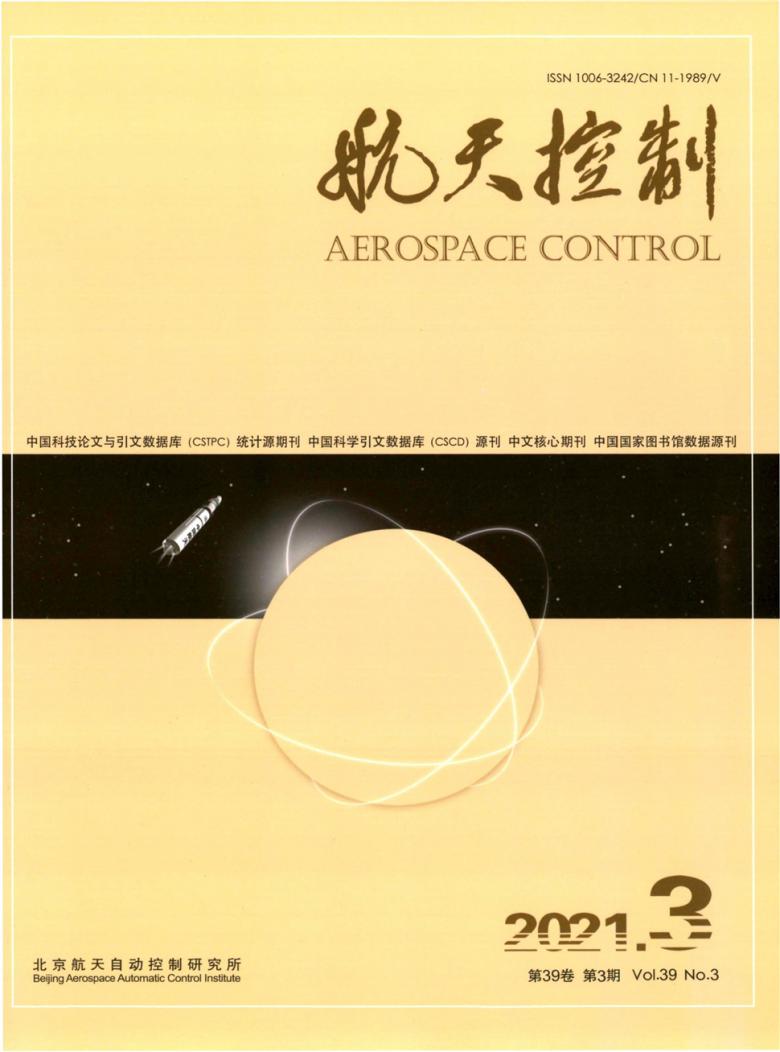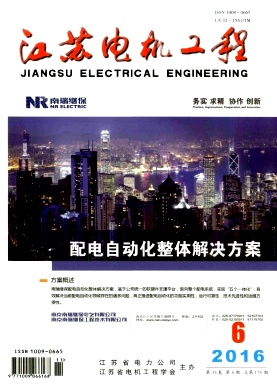主流文化下的独特声音——简论美国华裔女作家水仙花文化意识的发展历程
王戈冰 2011-04-20
论文摘要:作为北美华裔文学的先驱,水仙花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文化意识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其间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从早期的英国妇女“埃迪斯·伊顿”到后来的中国女人“水仙花”,再到最后的“没有国籍”的“欧亚人”——她理想中的“一家人”社会,水仙花的社会文化思想日趋成熟。
论文关键词:水仙花;文化意识;“一家人”社会
水仙花(SuiSinFar),本名埃迪斯·莫德·伊顿(EdithMaudeEaton,1865—1914),是一位具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欧亚裔作家。她是第一位用英文描写在美华人经历的华裔作家。她的代表作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里面收录了她的37篇小说,被公认是第一部反映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经历以及华裔妇女为争取合法权益而斗争的作品。她的作品大多以异族婚姻、文化冲突等为主题,文笔清新雅致,飘逸自然。创作的故事多以华人移民生活为背景,语气亲切,叙述性强,描绘出一幅幅详尽的画面,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华裔社会的方方面面。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而深邃的笔触,以其过人的才华和敏锐的洞察力,塑造了许多丰满逼真的人物形象,为我们讲述了~个个欢笑与泪水交织的海外华人生活的日常故事,获得了当时美国主流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赞赏。随着时光流逝,与她同时代的其他华裔作家都被人们逐渐遗忘,而水仙花的作品,却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然而,水仙花作品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文学艺术上的成功。当时华人在美国属于少数民族,被推向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边缘。184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更是把美国主流文化中对华人的歧视与压迫推向高潮。“黄祸”一词凸显出白人对华人的敌意与排斥心结。北美主流文学中经常出现对华人形象的歪曲描写。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华人野蛮、奸诈、愚蠢、迷信,身上集中了人性最丑陋的品质。在美国主流文化忽略并扭曲华人形象的大背景下,她作为一个具有欧亚裔血统的人本可以装作白人享受白人应有的优越生活,但却选择了捍卫中国人和劳动妇女的事业,用犀利的笔锋发出美国华裔文学的第一声呐喊:“我们需要中国人站来为中国人的事业伸张正义!”。。怀着对母国人民的赤诚爱心,她用朴实无华的文章为华人的权益大声疾呼。
她的作品大多围绕着男女平等、相互尊重、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文化传统的继承等主题,贯穿着作者的爱华情结,突破了当时美国主流文学只描写华人社会“光棍”而忽略为数不多的妇女人口的文学程式,成功地在婚姻、家庭这一主题范围内向读者讲述了她对妇女特别是华人妇女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等的看法,表现了对华人妇女疾苦之关切。对于华裔作家来说,他们由于同时受到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侵染,很难对自己的族裔性——文化身份进行界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何水仙花文化身份的界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如果按时问顺序,结合其生平经历,分析她先后发表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她的文化意识发展经历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正如她在《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书柬》中写道:“我一手伸向东方,手伸向西方,希望他们不会完全破坏这微不足道的桥梁。”…话语表现了作家对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从早期的英国妇女“埃迪斯·伊顿”到后来的中国女人“水仙花”,再到最后的“没有国籍”的“欧亚人”。最终,作家在经历了文化身份上的“东方”与“西方”的痛苦徘徊与游离之后,她眼中的原本对立的“两个世界”逐渐走向融合,其文化意识发展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社会文化思想已经日趋成熟。纵观水仙花的一生,我们把她文化意识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时期来进行分析。
一、早期作品创作时,水仙花认同自己为埃迪斯·莫德·伊顿,在作品的创作中。常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观察东方
水仙花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加拿大蒙特利尔时期(1888—1898)、美国西部时期(1898-1909)和美国东部时期(1909—1914)。水仙花创作早期在自我文化身份的界定上,认同自己为一个英裔加拿大人。她在写作时常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东方,因而作品中不可避免地留有一些“白人眼光”的痕迹。因此她早期发表的作品像《赌徒》、《自由之土》、《坐马车旅行》等署名大多仍使用她的真名“埃迪斯·伊顿”。
水仙花的华人意识源于她和母亲亲密的关系。作为长女,她经常帮助母亲干家务活儿,从母亲那里,她了解到了很多中国的风俗文化知识。但水仙花在北美长大,一生从未去过东方。从童年时代起,她接受的是英式的学校教育。尽管体内涌动着的那一半来自母亲的中国血统使她在文化意识形成之初就与东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水仙花早期作品中对于华人的描写大多处于想象的阶段。对中国及其文化极其有限的了解这个前提决定了这一时期水仙花对东方的认识不可能非常深入,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上她也还并且只能处于“一个英国妇女”的阶段,不可避免地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东方人及其文化。这一立场明显地表现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她早期的作品多多少少表现出来一种倾向:故意营造出强烈的异国情调,以此来吸引读者。比如说她习惯用“quaint”这个词来形容华人,在此影响下,她早期的一些小说,虽都以中国或中国文化为背景,但相比她以后的作品而言,她并非想通过背景来表达某种文化含义,而是源于她对中国文化的新奇与向往。比如像她的两篇小说《东方爱情故事一则》和《中国世仇》的情节设计上很有几分类似西方的经典浪漫爱情故事,将东方文化背景引入西方爱情经典中的创作手法使故事染上了一层神秘的东方色彩。她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水仙花在成年之前一直生活在白人社会,接受的完全是英式教育,就连她身边唯~的中国人——她的母亲也是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她不可避免地会吸收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一些东方主义观念和术语,即便她长大后有了自省能力和批判意识,华裔种族意识日益强烈,其潜意识里也难免存有东方主义的残余。
作为一个欧亚裔混血儿,水仙花仍属于弱势群体的一员,同样遭受着种族歧视与欺凌,生活非常艰辛。尽管这个时期她还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一半的中国血统,潜意识里以“一位英裔加拿大人”自居,但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对母亲的热爱使她在写作中并没有像有些作家那样将东方“妖魔化”,而是对华人抱以同情态度来进行创作,对华人命运非常关切。在作品中,她打破了中国人失语的现象,让华人成为故事中会说话的主人公,通过他们自己的言行展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因此其笔下的华人成了有血有肉会思考的活生生的人,形象要丰满得多。她力图纠正在主流文化的歪曲宣传下,一般人心目中华工的陈腐愚昧,不道德、不自重的刻板形象,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正直、勤劳,强壮、健康”,“他们虽然远离家乡,远离他们的孩子和妻子,但是他们安分守己、自尊自强”。作品中所反映的作者强烈的“中国情结”预示着她自身文化发展中的第一次飞跃即将到来。 二、文化意识发展的第一次飞跃——公开承认自己的华裔血统
1897年的牙买加之行是水仙花文化意识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牙买加的记者生涯加剧了她对白人文化霸权与种族优越感的厌恶,历经一个痛苦的文化身份的探寻与构建过程后,水仙花不再掩饰自己的中国血统,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华裔身份,从而实现了文化意识的第一次飞跃。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她在作品中不再以代表她“英国妇女”身份的“埃迪斯·伊顿”署名,而改用“水仙花”这个中国名字。笔名往往反映了作者的某种目的和关注的某种事物,她以水仙花的英文译音SuiSinFar来作为笔名,强调的是她的华人民族意识。在中国文化中,水仙花代表“高贵典雅”以及“对故土的眷恋”,所以她对水仙花这个笔名的选择,最大程度地表明了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时,她创作的题材也由最初的散文、加拿大浪漫爱情故事等转到华人故事上来,而其中很多是以华人妇女为主人公,讲述她们在爱情、婚姻、家庭等问题上的两难选择。创作题材和署名的变化无疑揭示了水仙花在身份定位和文学诉求上向华人靠拢的过程。
文化身份的这一转变使她的创作态度更加踏实,不再靠刻意地创设异国情调去吸引读者,她想要做的是记录并阐释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因此,她不断深入到唐人街华人日常生活中。在水仙花的笔下,唐人街不再是粗鲁可怕的“单身汉社会”,里面有男人与女人、大人和小孩,有可爱的动物,还有欢笑与歌声,这是一个与其他种族聚居区一样的生气勃勃的社会。
我们看一下她的作品《新世界里的明智之举》中的一段场景描写:
大街上拥挤的人流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女人们的歌声一阵阵地从小巷深处的阁楼里传来,而那些阔太太们却不屑于这些歌女的姓名。肥胖的理发师正开心地看着一个喝醉酒后跌进水沟里的白人;一个干瘪老头提着鸟笼,站在街角处,乞求路人驻足让他算命;几个孩子在路边燃起木块,迎面走过体格健壮的中华会馆老板,正津津有味地与寺院里的黄袍大师聊天。一个穿着新潮美国服装的华人与一个金发女郎放肆地大笑着,一起走进一家中餐馆。在各种各样的喧闹声里,还夹杂着电车的叮当铃声和车轮轧过地面时发出的刺耳声响。
在这段描写里,水仙花试图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文化娱乐、家庭生活等多层面刻画出一个美妙的、崭新的、真实的、人性化的华人生活图景。将美国唐人街的嘈杂拥挤与女主人公广东农村家乡的安宁与静寂形成鲜明的对比,表现出了一个初来乍到的华人妇女在美国感受到的冲击。作者在不同的美国华裔社区生活过,这使得她能够对华人生活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她所刻画的纵横交错的日常生活也为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真实环境。其作品表现出的如临其境的逼真感觉有力地说服了读者,因而读者对她希望表达的思想笃信不疑。
水仙花的思想发展历程可以通过其作品轻易地展示出来。比如在她的小说《一个嫁给中国人的白人妇女的故事》中,她讲述了一个白人女子在遭遇了不幸的婚姻之后,产生了轻生念头,被中国人刘康喜所救,二人因此相识并结合的异族通婚的故事。小说中女主人公梅妮的白人前夫留给她的是“悲伤、苦涩和狭隘”的记忆,刘康喜则带给她的是“幸福、健康与进步”。刘康喜是个典型的正面华人男性形象。女主人公梅妮的话或许道出了水仙花的心声:“我的生活经历告诉我,并非只有白人才具有美德。尽管华人有着一些婚嫁陋习,我认为他们仍然比大多数白人的品德好得多。”小说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刘康喜被同族人的一颗子弹射中了后脑。刘康喜与梅妮的婚姻并不能见容于当时的社会,不仅是白种人的社会,也不能见容于中国人的社会。小说这样的结局,也展示了作者自身文化意识发展历程中经历的思索过程及她的矛盾心理:到底不同种族的人能不能在一起和谐共存?水仙花徘徊并挣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对她而言,两者是撕裂的、对立的。从她的短篇小说来看,混血身份的无所适从和无归属感也浸透于字里行间——既受到自人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也不被华人社区完全接受。作者的文化身份到底该如何定位呢?在经历了徘徊和挣扎的漫长痛苦过程之后,她被迫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进行下一次的新的建构。在这则故事的结尾处,梅妮对其与刘康喜所生的儿子的命运不无担忧:“如果将来白人与华人之间没有友善与理解,那么我们孩子的命运将会怎么样呢?”借小说中人物之口,作者很清晰地展现了她自身在文化身份定位中的种种犹豫、思索过程,她那种期盼?肖除种族沟壑,盼望民族大融合、混血儿能够平等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逐渐在心中扎下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