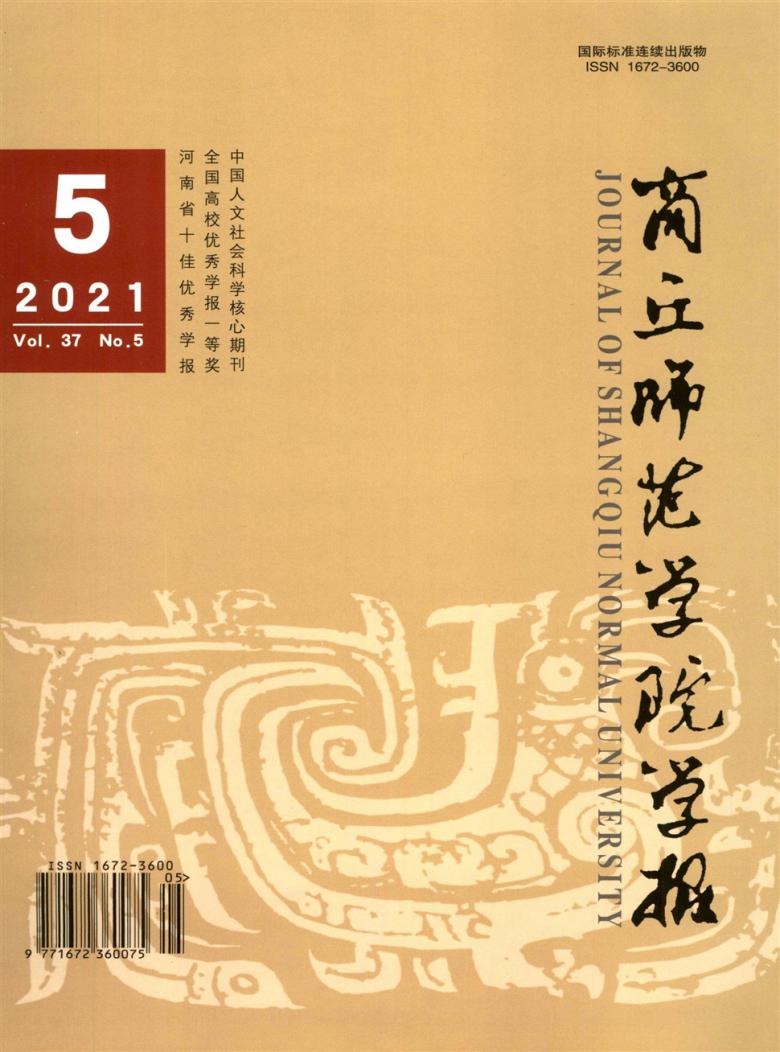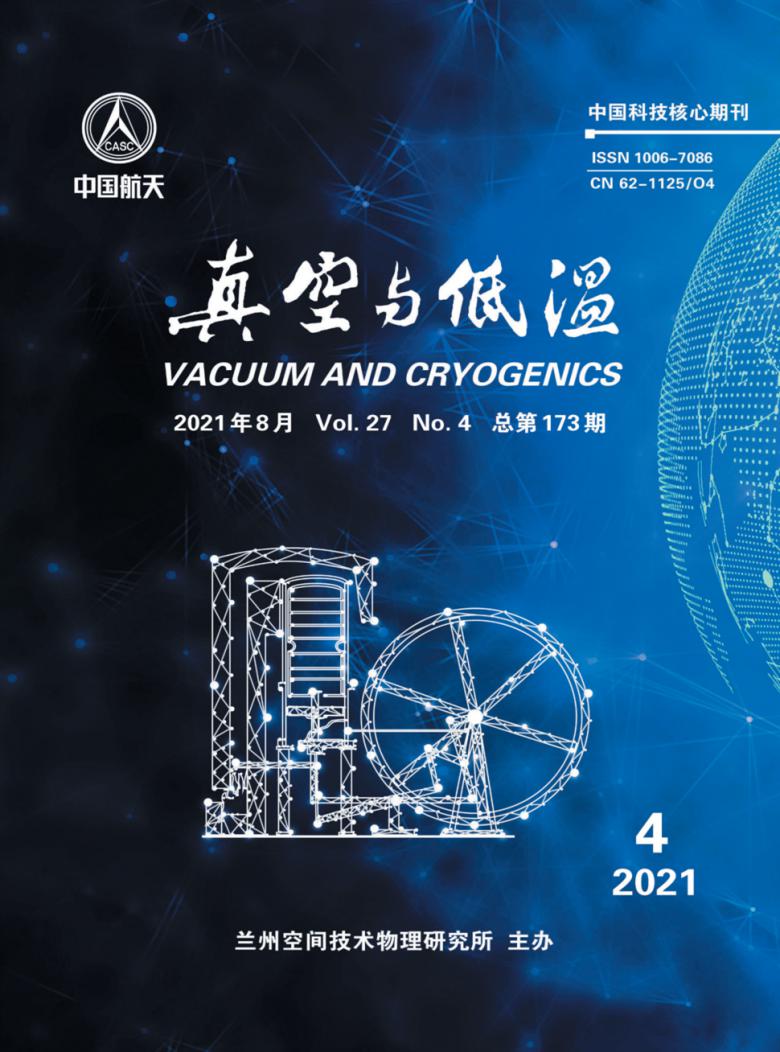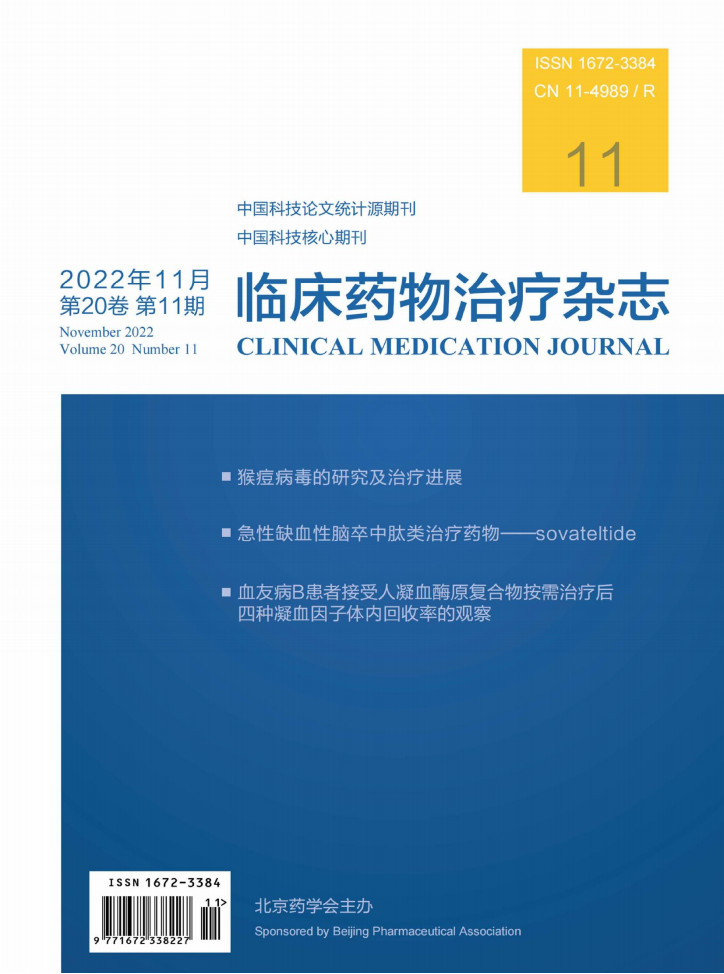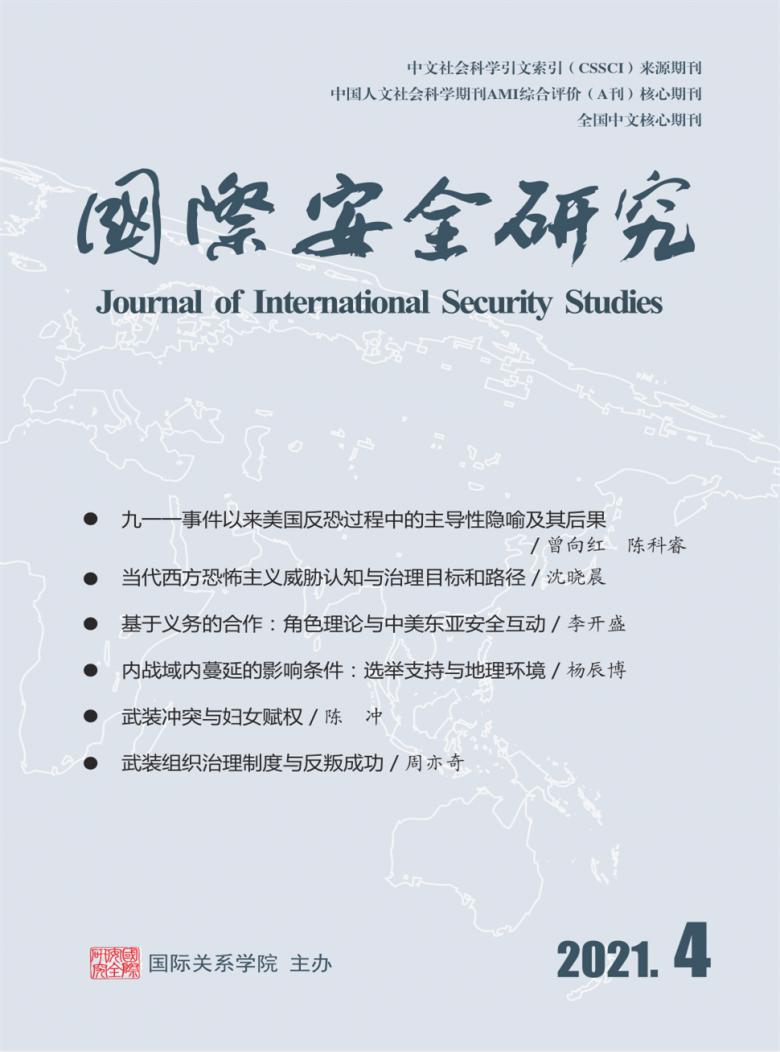传统鬼怪文化与东亚电影的身份认同——以中国、日本、韩国鬼怪类型片为核心
陈林侠 2008-08-01
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