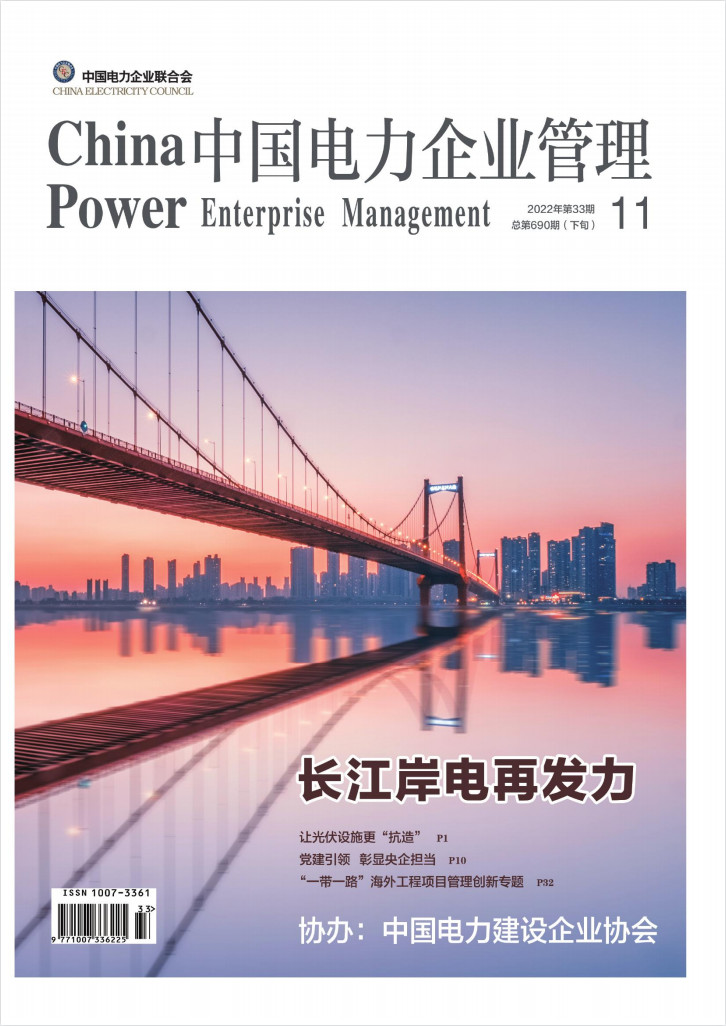唐蕃文化艺术交流
陈崇凯
一、艺 术
当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时,随公主进藏的还有很多杰出的汉族艺术家。这样,也把汉式艺术风格融入了西藏艺术。当时主持大昭寺事务的察巴止奔委托艺术家们根据中原汉族艺术的传统为大昭寺塑造了一些佛像,例如寺内的松赞干布和他两位妃子的塑像以及佛祖释迦牟尼的塑像。
受汉族雕塑艺术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拉萨大昭寺里供奉的四大天王塑像。大昭寺的四大天王像供奉在通向正殿的过道两边,正殿供奉释加牟尼像。据说塑造四大天王的塑像所用的胶泥和建桑耶寺所用的胶泥是完全一样的,就四大天王塑像本身从各方面来说也和汉族雕塑家在内地塑制的佛像几乎完全一样。
后藏江孜的却伦措巴寺所藏的最著名的圣物是两面战旗。人们传说当年王子穆尼赞普(或穆赤赞普)取道雅姆塘前往康区作战的时候,他持有一面战旗,上面绘有护法神朗斯赛钦和八位伴神骑士的画像,这面旗子就是著名的朗斯姜域玛旗。另一位护法神是朗托斯,穆尼赞普可以化作朗托斯的化身。他命令艺术家在一面旗子上画上他的“化身”朗托斯,这面旗子就是朗斯姜产玛旗。意思是:旗面上用八位伴神骑士和各种姿势的武士衬托描绘护法神朗托斯,绘画方法则是采用汉式流派的手法②。
1、雕塑绘画艺术
敦煌石窟的开凿,是书写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的最辉煌的一笔。它与吐蕃有密切关系。敦煌石窟艺术,从前秦起至吐蕃占领沙州之前,不断发展。占领沙州的吐蕃赞普均崇信佛教,因此沙州寺院经济得以空前发展,佛教也渗入沙州地区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敦煌石窟艺术不仅幸免于战祸,而且有了新的重大发展。正是在吐蕃占领沙州期间,敦煌又开凿了四十六个洞窟,而在艺术成就上,其壁画塑像在精致细腻方面,是盛唐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笔墨精湛、线描造型的准确生动,应是唐代艺术的深化。许多石窟艺术还反映了民族的特色,既有唐风,又有藏族特色,许多吐蕃装束的供养人物形象出现在壁画之中,有的壁画直接以吐蕃赞普为中心,如《吐蕃赞普礼佛图》。另外,159窟的《文殊变》、《普贤变》及《维摩诰变》等壁画,帐下听法的诸王子是以吐蕃赞普领先的。总之,在吐蕃近百年统治下的敦煌石窟艺术得以保存并有重大发展,这不能不归功于吐蕃人民。敦煌石窟艺术是无数汉藏劳动人民和艺匠的合作结晶,其间也有其它民族的心血。当然,不难想象,如此繁重浩大的艺术工程给汉藏人民所带来的沉重负担①。
“……至少是在墀松德赞统治之前的那段时期,桑耶寺、昌珠寺和耶巴寺的钟都仿造了中国的式样,他们可能是由生活在西藏的汉族工匠铸造的,因为钟上的铭文是藏文的,在阿里扎仓有一座佛塔,它无疑可以被确认为唐代佛干塔,有可能它是从中亚传入的,还有一幅来自中亚的唐卡,上面画着几个菩提萨垂,每一个菩提萨垂都有一个用汉文书写的名字。”②
杜齐在前藏山南琼结吐蕃赞普王蕃群考察后说:
HE黎吉生刊载了一张石狮像的照片,……这尊石像来自仁波切的墓地,无疑是仿照中国式样雕刻的,我们还见到了一只石雕乌龟,它来自一坐古墓……这种只乌龟雕刻艺术也体现出中国石雕艺术的启迪……我也注意到了桑耶寺西寺的庭院中有一只安放在龙嘴型笕嘴下面的石乌龟。这只乌龟为中国唐代样式,可能是从某个建筑物中移过来的,石碑上常常有一个四角向内折折的中国式塔形碑顶,通常在顶尖上还有圆形或近似圆形的珠子。③
普努沟墓地出土的铜、铁质带扣,据霍巍教授分析,是一种具有一定时代特点的器物,在拉萨澎波农场吐蕃墓地也有出土。普努沟墓地的铁带扣扣环为扁圆形,扣舌较长,以扣舌的后侧带轴“这种类型的带扣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地区,时代从东汉一直延续到辽、金时期”。该墓地的铜带扣“扣环为椭圆形,扣舌为长条形,以扣环的一侧为抽,后接一牌饰形的扣身,此类带扣的流行时代亦为汉至唐代,在我国中原和北方地区都有发现”④。
带钩在中原地区的应用,相传是战国中晚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习自西北游牧民族的服饰习俗。但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中国春秋中晚期,在齐、燕、楚、秦等国的广阔地域内,带钩已开始出现。该如何解释这个矛盾呢?沈从文先生的解释比较合理,即带钩有可能在春秋时已开始用于战士的衣着(因为约束甲衣的需要),而所谓赵武灵王云云,“或许重点应在比较大规模的骑兵应用,影响大而具体”。汉代以后,至魏晋时期,带钩的使用遽减,出土明显减少;南北朝以后铰具(带扣)盛行,所用多为“铰饰革带”,即附有铰具的革带,与当今的皮革腰带已颇为相似,比用带钩扣接革带更为结实、方便,带钩遂逐渐消失①。
2、音乐舞蹈
音乐舞蹈等艺术,在唐代汉藏之间亦有异同之处。相互借鉴而同步发展。前述工艺部分,已提及唐朝曾派音乐家进吐蕃,墀松德赞年幼时的汉人伙伴贾珠嘎勘就是一位舞蹈家。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从藏史记载看,也都是精于音律者。金城公主进藏,皇帝特赐龟兹乐。他们的进入吐蕃,有助于汉藏音乐舞蹈等艺术的交流和了解。
据藏史载,都松芒波杰时(公元676——704年),自汉地得到乐器。《拉达克王统记》载:“自汉地获得多达曼、笛子、布桂、唢呐等”②。吐蕃君臣上下均善歌舞,敦煌文献中的吐蕃君臣对歌就说明这点。据藏史载,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均会操琴。
吐蕃在武则天长安二年,派遣伦弥萨等出使唐朝,武则天宴请他们于麟德殿,并奏百戏于殿廷。伦弥萨说:“臣生于边荒,由来不识中国音乐,乞放臣亲观。”则天答允。伦弥萨等人相视欢笑且激动地说:“臣自归投胜朝,前后礼数优渥,又得亲观奇乐,一生所未见。自顾微琐,何以仰答天恩,区区褊心,唯愿大家万岁。”③此事足以说明吐蕃人对唐乐的倾慕与欣赏。唐中宗时金城公主入蕃,让“杂技诸从,给龟兹乐。” 公元822年,唐大理卿刘元鼎出使吐蕃,吐蕃赞普招待刘元鼎,“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④。据载,唐朝汉地的某些乐器今日仍存西藏,大昭寺内就保存有相传为文成公主带去的几十种乐器,例如箜篌等等。又据劳费尔考证,汉语“琴”字,在《贤愚经》中就有相对的藏文音译词⑤,说明汉地的琴已在唐代传入吐蕃,直到现在,拉萨还保存有许多唐代的乐器,就是在蕃唐人传播中原文化的历史见证。
3、吐蕃杂技与汉地的关系
《贤者喜宴》记载了桑耶寺开光时的杂技表演,译注者黄灏说:“以上记载吐蕃人在开光典礼”上的各种杂技表演很精彩,此为它书所未载者。吐蕃杂技当与汉人有关,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进藏时均有“杂技”随从,“杂技”之中亦包括“百技”(即百戏,亦所谓杂技也)。公元821年,唐朝使臣刘元鼎出使吐蕃,吐蕃赞普特举行文艺表演以示欢迎,据《新唐书·吐蕃传》载,参加演出的人,其中“杂曲、百技,皆中国人也(按此处特指汉人而言)。”可见汉地杂技对吐蕃杂技艺术影响之深。另在敦煌壁画中的百戏图(85窟)及营技图(156窟)也记载了汉地杂技。敦煌曾长期被吐蕃占领,汉地杂技艺术自然会与吐蕃杂技交流⑥。
二、吐蕃学生入唐学习及藏汉语言文字交流
1、吐蕃派学生及使节
据《旧唐书》等汉文史书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为妻,此后因仰慕盛唐文化,派遣酋豪子弟,到唐朝学习语言文字及儒学。到了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又颁诏:“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学习经业,亦附国子学读书。”①
并下敕云:“夫国学者,立教之本,故观文之道,可以成化。痒序爰作,皆分泽于神灵;车书是同,乃范围于天下,近戎狄纳款,日归夕朝,慕我华风,孰先儒礼?由是执于干羽,常不讨而来宾;事于俎豆,庶知几而往学。彼蓬麻之自直,在桑葚之怀音,则仁其远哉,习相近也。自今以后蕃客入朝,并引向国子监,令观礼教。”②国学又称国子监,是唐朝最高学府。“是时,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使之讲论。”当时国学颇负盛名,誉满国内外,“于是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③吐蕃学生十分勤学,深受唐朝臣工赞赏:“吐蕃之性,剽悍果决,每情持锐,善学不回。”④因此,吐蕃人学均有成,吐蕃大臣仲宗就是国子监的学生。“先是,仲宗年少时,尝充质入朝,诣太学生例读书,颇晓文字。”⑤掌握兵权的论钦陵,在“万岁通天二年(696年),四夷多遣子入侍”之时,他“皆因充侍子,遂得遍观中国兵威礼乐”。而且这些年来长安学习的吐蕃人,均“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⑤
吐蕃使臣名悉腊在景龙四年随文成公主离唐前,参加了唐室诗歌联句活动,据《全唐诗》卷二载,堂唐中宗李显《景龙四年正月五日移住蓬莱营御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当将作大匠余晋卿说完一句“铸鼎开岳造明堂”之后,吐蕃名悉腊即席联上一句“玉醴由来献寿觞”⑥。
2、在蕃唐人与汉藏语言文字的交流
在吐蕃占领的河西地区还有一种专门从事蕃汉文教学的在蕃唐人,如此伯希和所藏敦煌卷子第4660号汉文写本附有一位被称作陇西李教授的话肖像,并赞云:“蕃秦耳晓,缁俗齐优……两帮师训,一郡归投。”⑦
吐蕃在河西陇地的 末部中,就有大量没蕃汉人在内,这是因为其部落“百姓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孙,国家却弃掷不收,变成部落。”生活在这一带的汉藏人民,相互影响很大。唐诗形容生活在这里的吐蕃人是:“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⑧而生活在这里的汉人则是:“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胡语。”⑨可见双方风俗语言之间的交流程度。敦煌文献中关于汉藏人民用汉藏对音拼读或译音的办法学习彼此语言文字的记载很多。例如,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⑩、《汉藏对照辞语》⑾、《汉藏对照辞汇》⑿等等,都是至今留存的证明。这些汉藏对音辞汇,很可能是汉藏两族文人共同合作的产品。
语言文字的交流学习促进了唐蕃之间文献、表疏及典籍的翻译与交流。例如,用汉文写的敦煌文献有:《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商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系“大蕃右敦煌郡布衣窦吴撰”①利有《谢赞普支敦煌铁器启》(斯1438号卷子《吐蕃守使书义》)及《吐蕃赞普进沙洲莲花寺舍利骨陈情表》②等等。这些表文、启文、颂词,显然均出于汉人之手,也可能有吐蕃“知书者”的参与撰写。《旧唐书·吐蕃传》载有公元730年吐蕃重臣名悉腊赴长安向唐皇上表,此表文系汉文(也许有藏文原文),行文颇具汉文风格,同时又显示出藏文文书的一些特色。名悉腊的七律之作极佳,汉文造诣非常精深,上述表文很可能出自他手。以上事实可以证明吐蕃入学习汉地“典疏书”已卓有成绩。“长庆唐蕃甥舅会盟碑”的汉藏对照碑文对译十分精确,充分体现了汉藏两族文人的密切合作,也反映出汉藏两族一些文人对汉藏语文之精通。
② 《西藏的魅力》,第245页。
① 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载《敦煌研究文集》,第74至79页。
② (意)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第50页。
③ (意)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第62页。
④ 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108页。
① 《藏族服饰史》,第37页。
② 该书第二册,弗朗克本第32页。
③ 《新唐书·吐蕃传》。
④ 《新唐书·吐蕃传》。
⑤ 《有关文成公主的几件衣物》,载1960年《文物》。
⑥ 黄灏《贤者喜宴》译注[八],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① 《唐会要·附学读书》
② 《全唐文》卷34,P6下。
③ 《通鉴》卷195页23下,贞观十四条。
④ 《旧唐书·吐蕃传》
⑤ 《册府元龟》卷962外臣部。
⑤ 《册府元龟》卷544谏诤部。
⑥ 清康熙间辑《全唐诗》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
⑦ 引自[法]戴密微《吐蕃僧譄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⑧ “陈陶陇西行”,《全唐诗》第十一函,第四册。
⑨ 《张司业诗集》卷七,陇西行。
⑩ 《敦煌藏文文选》巴黎影印本,伯字3419号卷。
⑾ 《敦煌藏文文献》,斯2736号卷子,斯10002号卷子。
⑿ 伯字2762号卷,又编号为1263号。
① 伯字2765号卷子。
② 斯1438号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