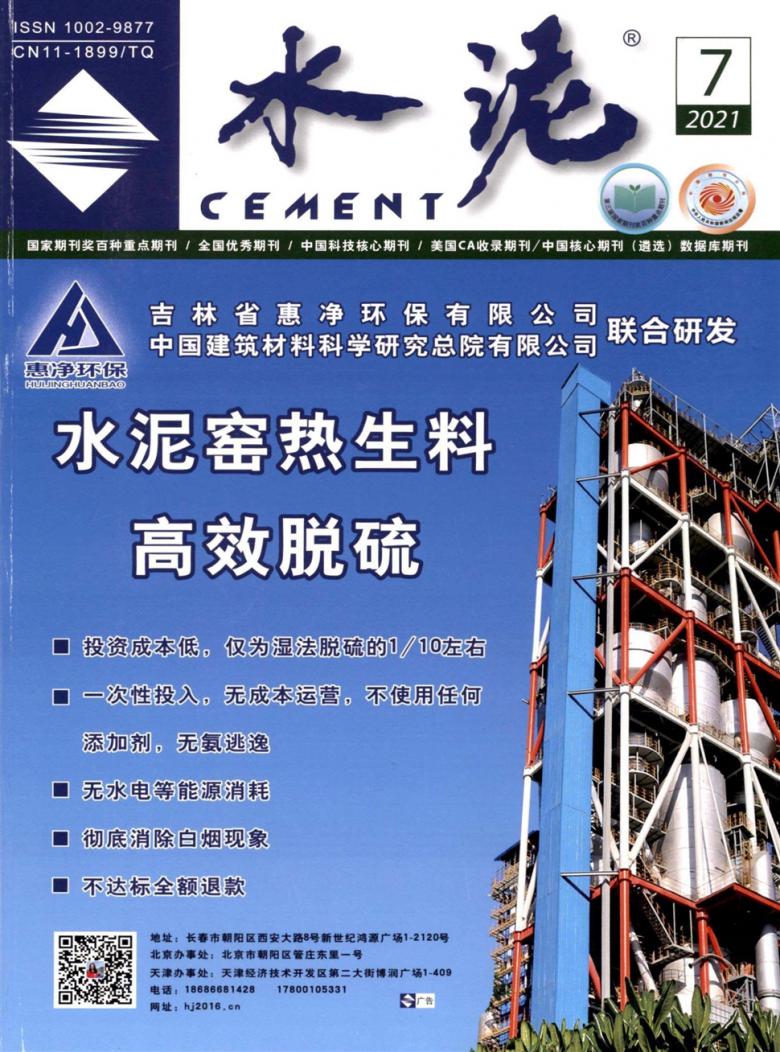试述清代闽人入川与川闽经济文化交流
佚名 2006-04-18
福建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清初福建人民不畏蜀道之难,扶老携幼,辗转于沟壑之中,绵延数千里由闽入川。在这超人的开拓胆识与吃苦耐劳精神的后面,蕴藏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和背景。他们的迁徙动机与目的亦各不相同。嘉道之后直至民初,通过数代乃至十几代入川闽人的努力,对推动闽川两省的文化,均作出突出的贡献。本文拟就明末清初至道光之前,闽人入川的原因与背景、动机与目的,以及对两省经济文化的互动效应作一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对福建与四川人口的有所裨益。
一、福建人民迁徙入川的原因与历史背景
1.长期战乱造成川中人口剧减
明朝之前闽人入川可能是零星的,因而未见史书记载。明末,福建遭受严重的战争祸害,郑成功抗清斗争在闽南进行得十分激烈,顺治九年(1652年)漳州城被围五个多月“饿死男女数余万人”,但到顺治十八年(1660年)统计福建仍有丁145万,口469万;可见总的人口损失不是太大[1]。而四川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明末清初张献忠起义军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起义失败后,南明政权与起义军余部联合抗清;之后平西王吴三桂又联络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以四川为前线与清朝分廷抗礼,川中遂成兵家必争之地。为此清军曾六进成都。饱受长达37年的兵燹战乱,川中地区人口伤亡迨尽;血腥的屠戮之后又是瘟疫流行,号称数百万人口的“天府之国”只剩下区区五万丁税之口,总计不过三、五十万人,不抵明中叶兴盛时人口之10%。以致许多地方官员均无民可治,赋税大省也无产可收。顺治年间四川巡抚张德地到成都走马上任时“行数十里绝无人烟”,只好退驻保宁(今川北阆中县),直至康熙四年(1665年)将衙署搬入成都,康熙五十七年(1778年)才重修毁于战火的成都城。
为解决昔日米粮之仓的川中人烟稀少问题,清初顺治朝下令“湖广(今湖南、湖北)填四川”,一些湖广地方人士“奉旨”入川,实际上这是带有强制性质的性移民。随之康、雍、乾三朝均以比较优惠的移民政策鼓励各省民众迁徙入川,如康熙十年(1671年)下诏“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并开垦者,准其入籍……应准其子弟一体”,康熙五十一年(1772年)“往四川垦地至满五年起征”,每丁给农田30亩或旱田50亩,五年内免征税粮。雍正年间下诏“凡流寓情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户部批准入川垦户“每户给银十二两”用作安家费。[2]这样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川中统一开始,一直到嘉庆年间(1796—1820年)移民才停息,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入川移民以湖广人为主,赣、粤较多,福建较少。据统计福建入川民众仅占移民总数的不及5%。我们从嘉庆年间的《四川通志》“户口”统计,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四川人口净增2516491人,其中约80%是外省移民,即74年中移民总数为201.3万,每年以2.7万人速度移民。加上康熙六年奉诏入川屯垦的12万福建投诚官兵及其家属(后详),福建入川移民总数约在30万人左右。但是,不足移民总数15%的福建入川移民对川闽文化交流却带来了相当深远的。
2.地狭人稠与连年灾荒迫使闽人远徙入川
明清之际我国开始进入第四个灾害宇宙期。[3]随着人口的大幅度增加,灾害的频繁发生,人口流动的规模也不断增大。福建自宋元以来人均耕地即十分有限,入明之后更是大幅减少。谢肇浙《五杂俎》就描述了福建人迫于耕地日减而外出谋生,在广东、广西一带的迁移和开发。他说:闽人“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口则射利之途愈广;什五游食在外”。万历年间“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在广东廉州还有被俗称为“东人”的,“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4]。这些操闽语、有技术而杂处之人,就是流寓粤东的闽人后裔。赣南瑞金一带,明中后期“闽广及各府之人视为乐土,绳绳相引,侨居此地。土著之人,为士为民;而农者、商者、市侩者、衙胥者,皆客籍也”。[5]在江西宁都的6个乡中,“上三乡即土著,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6]。即使是在清政府严密控制之下的满洲腹地,也有数万福建人在当地经营实业,甚至定居。乾隆皇帝闻报后大为惊讶却也十分无奈,他说:“朕闻奉天一带沿海地方,竟有闽人在彼搭寮居住,渐成村落,多至万余房”;“此皆系地方官以闽人在彼贸易营生,藉此多征商税,遂尔任其居住,若不亟行查禁,则呼朋引类,日聚日多”;“但闽人在彼居住,已非一日,且户口较多,亦未便概行驱逐”;且“锦州、盖州、牛庄等处,每年俱有福建商船到彼贸易。即有无业闽人,在该处居住”。[7]这种颇具规模的人口流动,体现了明末清初福建人民向外省迁徙的明显趋势。甚至早至明朝初年即有闽人不畏蜀道的艰险而进入四川谋生,主要集中在资中、新繁、健为等条件较好的地区:“资(中)无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时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闽、赣、粤籍大都清代迁来。明初来者今谓川省人,余则各以其籍相称”。[8]川中新繁县人口主要由湖北、江苏、福建、广东和陕西移民所组成。[9]岷江之滨的《健为县志》专门列出所有由移民按地域建立的会馆。湖广、宝庆、长沙、江西、福建等会馆人数最多。由于移民数量大大超过本籍人,因而在太平天国时期各籍移民自选人员负责为官府征派特捐、收集捐款。[10]
福建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气候炎热,时常爆发大规模的流行性疾病甚至传染病,亦是瘟疫常发之地。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由于漳州潮水突涨5尺,郑成功军队得入海澄。同年漳州城被郑军团团包围,粮尽弹绝,以致“人相食,斗米值五两”。至清军解围之时,在城内收得颅骨73万;于是“疫大作,死者无数”。[11]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汀州永定水灾,漂圯民房无数,冲垮城内卧龙桥;秋季永定“大疫,死者千余人”。[12]乾隆十八年(1753)海澄爆发大规模瘟疫,“死者无算”。同年泉州府也有瘟疫流行,“至明年秋乃止”。[13]道光元年(1821)七月间福建全省瘟疫流行,患者均因吐泻暴卒,“朝人夕鬼”,不可胜数。[14]其实,早在明万历时谢肇浙著《五杂俎》就对福建瘟疫心有余悸:“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付之罔闻。不知此病郁热所致,投以通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煮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纸糊船,送之水际。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闭户避之。余在乡间夜行,遇之辄径行不顾。友人醉者至,随而歌舞之,然亦卒无恙也”[15]。在当时条件下,对瘟疫几乎是束手无策,只好求助于装神弄鬼。为躲避瘟疫等重大传染性疾病,闽人只得远走高飞,包括遥远的四川等地也成为迁徙的目的地。
二、清代福建移民入川的动机与移民的类型
1.为求生存而移民入川
福建移民就其入川动机论之,多属生存型的,即由于福建人多地少,一些少地或无地佃户,兄弟子女多,遇上水旱歉收,生活无着;为求生存而不畏蜀道之难,辗转徒步数月,历经艰辛而入川的闽人家族,在家谱中留下详实的记载。如龙岩万安乡溪口村徐姓《族谱》记载:“启祖原系福建省漳州府龙岩州溪口县万安里,地名庵子脚下老屋基居住,耕种祖父遗留之业。不意年寒欠丰,男繁女众业乏之苦。常言四川耕种贸易之隆,是日弟兄同堂议妥:长么两房仍就福建受业耕春;二房徐美周(入川启祖,号永旭,时年40岁)同缘韩氏(28岁)二人,随带长子良彪,用箩兜挑着次子良凤(6岁),女儿(半岁),与三房美昌(号永镒),于乾隆十七年壬申岁(1752年)九月初四日择取吉良黄道,起身移居四川。长么两房二人送至三十里,弟兄分别泪如雨点,大哭而回。永旭、永镒六人于乾隆十八年癸酉岁三月初二日来川,在大足城西门住座贸为业一载五月。因干旱,贸易不顺,弟兄各寻各居。以至八月内,搬移中敖三板桥,地名刘家沟,佃田耕种三十余年。……嘉庆六年(1801年)男女五人迁移大足茅居子(山乡)屋座几载。承天地之德,至嘉庆十三年(1808年)落业成粮(立为粮户),螽斯千古,永振家邦”[16]。从徐氏家谱中我们发现二个兄弟从龙岩来到川中大足并以此为中心的迁徙轨迹和发展经历。
2.闽人为寻求新的商机入川发展
福建入川民众中也有些原本生活就较为富裕者,其移民性质是属于发展型的。他们随着移民大潮,入川寻求新的商机,发展事业。如“康熙十年(1671年)福建汀州商人曾达一来到四川内江,见三月菜花开放,内江之气候与福建相近,可种甘蔗,遂藉返乡迎亲之际,带来蔗种和制糖工具,延聘了制糖食品的工人,在内江龙门镇梁家坝开设了糖坊。由于种植甘蔗获利高于种粮食,甘蔗种植由内江拓展到资中、资阳和隆昌等地,兴起了种蔗热”[17]。这类发展型的移民大多农商工并举,对清中叶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3.先求生存而后图发展类型
另外一种是始求生存而后图谋发展类型,此类典型代表即如郭沫若的先祖,原籍是福建宁化。郭老在1939年写的《德音录·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说:“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前(1781年,即乾隆四十六年)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铜河者大渡河之俗名,古又称沫水。……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郭沫若祖父),族已昌大”。据郭沫若族弟郭开宇回忆:“我的曾祖父郭贤惠讲,先辈由福建来四川,开始是做苎麻生意。从福建宁化采集野生苎麻,跟着入川的马帮,到了现在的牛华镇,牛华是盐井林立,盛产食盐的地方。苎麻用于盐业生产中缠扎卤水筒。后来也运麻布来卖。赚了钱,自己也办起了马帮,沿途开设了13个驿站”[18]。入川的郭氏家族正是仰赖如此殷实的家业,至其父郭朝沛时才有经济实力在家里办起了家塾专馆—一绥山馆,而后又藉此送郭沫若与其长兄郭开源留学日本成才。
4.入川为宦与军屯入川类型之闽籍移民
此外,还有些福建籍的官员与军人以游宦和军屯的身份入川的,如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记述,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亲政当年就招福建郑成功军事集团的投诚官兵及其家口入川,当时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奏请朝廷:“福建一省投诚一项,除家口外,尚有二万三千八百余名之众,岁支银米除移驻外,尚有三十六万余两、八万余石之多,入伍者骤难补完,垦田则无地可屯。自宜以福建投诚最多之人而垦西川荒芜之地,两利各便,无逾此者……。抵蜀安插之后,一年分田垦地,二年习成土者,三年起科”[19]。这个条件比其他地方招抚投诚官兵更为优惠。如《清实录》载康熙皇帝于六年八月初七日下诏“令河南、山东、山西、江南、浙江见驻投诚官兵开垦荒地,自康熙七年始,每名给五十亩,预支本年俸饷以为牛种,次年停给;三年后照例起科。”安抚在川西屯垦的福建籍官兵,如以每户5口计,则当年入川闽人至少有12万之众。仅此一项即相当可观。再从今天成都等地的“大福建营巷”、“小福建营巷”等地名看,数年中入川屯垦的福建官兵加上眷属的数目相当可观。移屯入川安家立业,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质,但其目的主要是为安置屯戌军人与开发川西经济,仍属经济性移民。
三、清初、中叶福建人民由闽迁徙入川的历史意义与影响
通过清初的移民入川,在较短时间内恢复了天府之国的元气,直至嘉庆朝闽人入川仍络绎于途,因而也促进了川闽两地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其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四川省由于人口迅速增加,劳动力资源渐为充裕,经济得以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康熙五十年(1711年)巡抚年羹尧上奏称:“连年大有,运贩米谷出川者不在少数计,是吴楚歉收资食川米。”雍正初年就有“江浙粮食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之说,四川又恢复了赋贡大省的地位[20]。清代初期,就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口增长情况来看,福建的人口密度已趋饱和状态,可供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包括可垦荒地已臻枯竭。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省有耕地1362万亩,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减少至1345万亩,而人口密度却从乾隆十八年的每平方公里40.38人,增加到咸丰元年(1851年)172.31人[21]。据葛剑雄主编《移民史》统计,四川在清初移民大潮中共接纳移入623万人,其中福建20万人(包括这一百多年中入川定居闽人后裔,笔者以为该数目偏少,如前所述当为30万人),所以清初移民入川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福建本地的人口压力。
第二,两地农业耕作与经济作物栽培、加工技术的交流,促使两省经济的共同发展。早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四川巡抚在奏折中就提倡“须广招在川之闽、粤农民,凿引泉源,或设堰分流,庶灌溉有资,旱涝而无患矣”[22]。说明闽、粤两省农民积累了丰富的引渠灌溉、抗旱保苗的生产经验,四川官员十分注意发挥这些闽粤籍移民的长处。此外,福建移民还引进可收双季的水稻良种及红薯、玉米、烟、甘蔗、木棉等多种经济作物。红薯是在万历年间从吕宋传入福建,藉以抗御灾荒的;经闽粤移民带入四川后,由于红薯十分适宜于川中丘陵和山区种植,又是一种高产耐旱作物,使得四川的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地丘陵山区得到开发利用,移民也可以在那里蕃衍生息。再比如烟草和甘蔗的种植,民国重修《傅氏宗谱》记述入蜀始祖、福建龙岩铜钵人傅荣沐“由瑞金迁居金堂赵家渡。初犹食力于人,继乃自为贸易并佃田,使诸子力农,及迁易家坝,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种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尤所必需,故一时傅姓烟重于锦城(成都),其价过倍他种。又熬蔗糖于赵家渡,发贩四方,获资益厚”[23]。在闽籍移民的影响下,当时沱江、涪江沿岸移民大县遍种烟草、甘蔗。总之,花生、甘蔗、烟草、水稻、柑桔等经济作物的栽培都与当时各地入川移民有关,这在地方志书和族谱中多有记载。从而使四川物产大为丰富,迅速成为粮食输出的省份。明清时期福建长期缺粮,这种粮食与经济作物栽培的交流,可以使两省共同受益。而四川茶叶种植和加工的历史相当悠久,茶文化比较发达,酿酒经验丰富,还有极为丰富的水力资源和资源,闽籍移民作为多元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应当重新评估。
第三,促进闽川两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福建移民把自己的风俗、习惯、方言和民间信仰带进了四川,促进四川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多元一体文化。比如闽人的二次葬俗,敬祖重教的传统在四川得到川人的认同和发扬。在俗神信仰中,福建沿海人民尤重于兴建天后宫(天上宫),广泛信仰妈祖(天后圣母)。遍布四川各地的天后宫一般是由福建籍商人捐建或同乡集资所建,而富顺县城天后宫则是乾隆二十五年(1751年)由该县知县主持修建。这一方面说明官方对福建人的重视,着意团结福建人;另一方面也说明福建商人的数量已十分可观,在当地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据四川各县志及有关材料统计,全川建有天后宫约220座[24]。天后宫主要是入川福建人士聚会议事祭祀酬神之地,并兼有交流工商、农、学各界事务,联络感情,商议互济互助的诸多功能,也祈祷天后妈祖关怀和保佑在川闽人子孙繁衍昌盛。
综上所述,由于闽籍移民入川而建立起闽川两省特有的密切关系。清初福建移民由于本地兵燹灾荒而由闽辗转入川,可分为生存型、发展型、先求生存而后发展型及入川为宦与军屯型等4类。他们均为四川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促进了两省人民之间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典型者如福建的妈祖天后信仰遍及四川大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始,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率领开始经济腾飞。四川、湖北、江西等大量民工开始输入闽、广等地。截至2002年底的统计,在闽务工的内地各省民工有220万人,其中四川籍(含重庆市地区)民工至少有100万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次西南内地人口向东南沿海地区的大迁徙。庞大的民工队伍成为福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并作出了骄人的业绩。四川民工入闽的同时,也带来了浓郁的巴蜀文化,“四川麻辣烫”、“水煮活鱼”、“重庆火锅”等川中饮食文化在福、厦、漳、泉等地举目可见。今天,福建人民也应当发扬当年先辈的奋发开拓精神,积极入川,把人才、资金、技术等带进中国的西南腹地,为我国西部大开发作出应有的贡献,让两地文化交流再创辉煌。:
[1]详见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五“人口”。正谊书院同治二年刻本。
[2]《清圣祖实录》康熙十年、五十一年;《清仁宗实录》雍正六年。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3]这个时期是我国工作者已经发现的三个重大灾害群发期之一。即夏禹宇宙期(约4000年前)、两汉宇宙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20年)、明清宇宙期(公元1500年至1700年)和两个较小的灾害群发期,即清末宇宙期和20世纪60年代末迄今正在进行中的灾害相对频繁期。参见高建国:《灾害学概论》,《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徐道一:《严重自然灾害群发期与》,载马宗晋等编:《灾害与社会》,地震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297页;任振球著:《全球变化---地球四大圈异常变化及其天文成因》,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4]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0页、103页。
[5]同治《瑞金县志》卷十六“兵寇”,引杨兆年“上督府四赋始末”。
[6]魏礼:《魏季子文集》卷八,“与李邑侯书”。
[7]《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六,乾隆五十六年四月庚戌,第26册,第549页。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8]民国《续修资中志》卷八“方言”。第68页。
[9]光绪《新繁县志》卷五“户口”。第2页下。
[10]民国《健为县志》“种族表”,第6页,第51页。
[11][12][13][14]道光《福建通志》卷二七一、二七二“祥异”,同治二年正谊书院刻本。
[15]谢肇浙《五杂俎》卷五“人部”二。第259页。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第三十种,中央书店1935年印本。
[16][23]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17][24]孙晓芬:《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18]详见四川大学《郭沫若集刊》,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1983年。
[19][20]正刚:《清前期闽粤移民四川数量之我见》,《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1]梁方仲:《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有关统计表格,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2]转引自陈世松:《中国西部大开发与客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