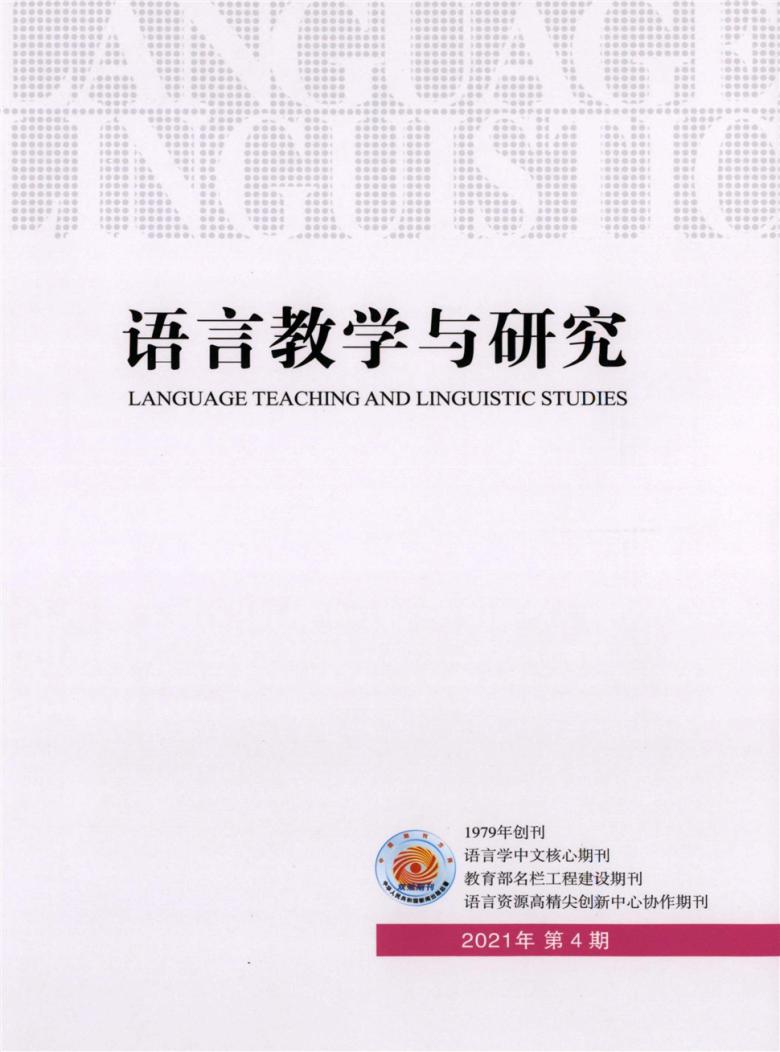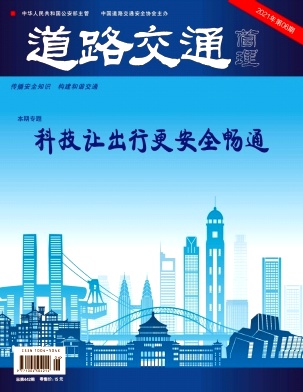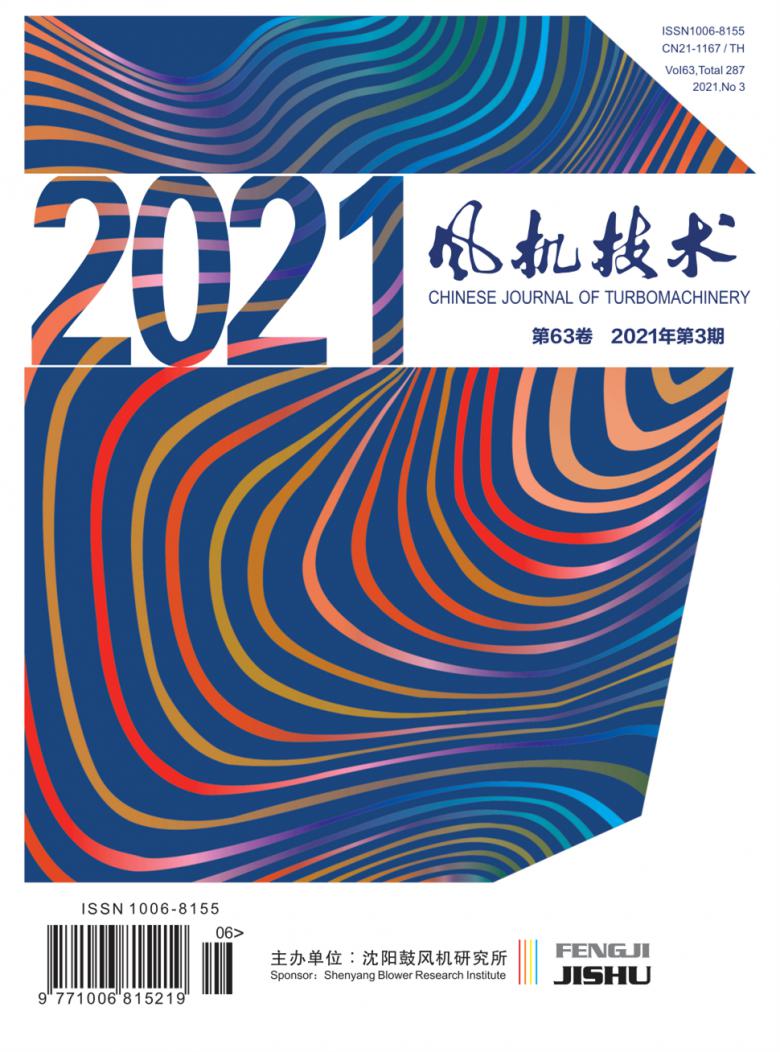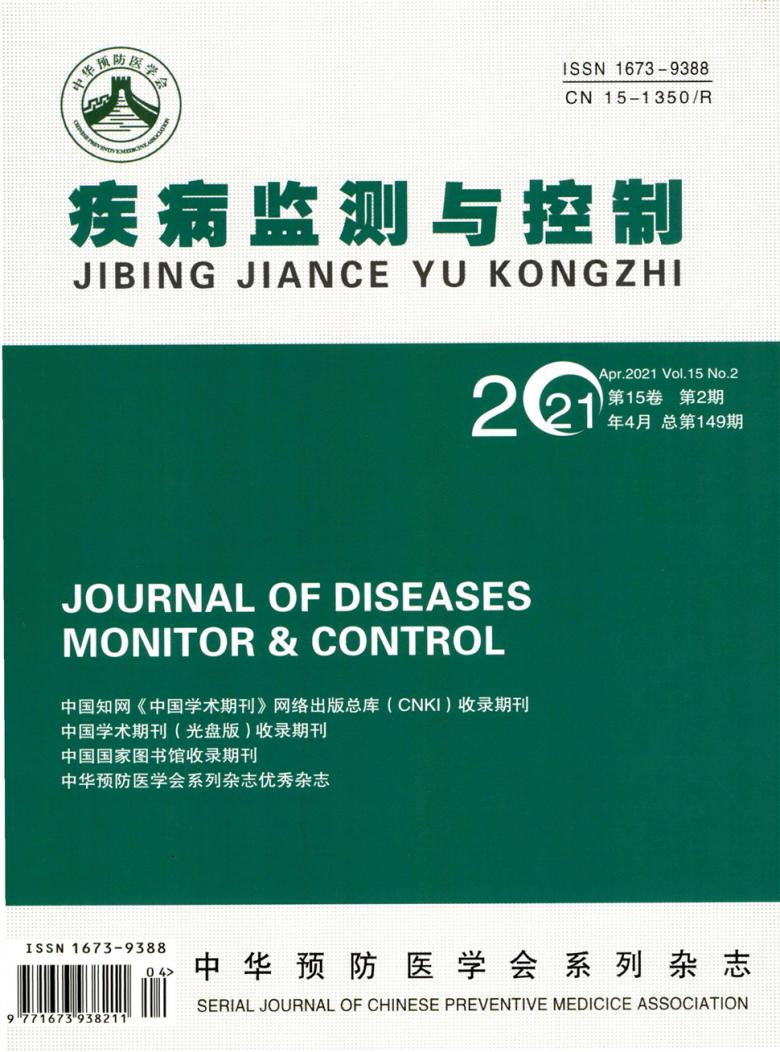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论纲
佚名 2006-01-12
Abstract: The important question in global academia is not to conquer orient but how to "discover orient" again.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edge,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their relationship is very complicated because of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Therefore, there is no nation could break away from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universal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What we can only do is to keep our national character and leave off the unfair relationship of the universal situation. The attitude we hold should be changed from importing our culture to exporting it, which could make ourselves have not only the open image but also the local cultural basement and the internal spirit. 新世纪世界学术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不是权力征服"东方",而是如何重新"发现东方"。这是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起来。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本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关系,使自身既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的"拿来主义",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从而走向文化"输出主义"。
一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问题
全球化成了当大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但是,人们却在全球化中进一步误读东方,甚至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看东方,将全球化理解为:现代化=西化=全球化=美国化=基督教化。这其中,现代化指科技制度层面,西化指后殖民文化层面,美国化则是指霸权化和世俗化层面,而基督化指向宗教层面。如此比附,将科技、经济、军事和文化统统纳入其中,用一串等号来诠释现代化的内涵,似乎全球化就等于世界性的单一化。这里面问题很多,不可轻易放过。 "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历史记忆,但又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语境。[1]当今世界,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代,这意味着各国之间在交换价值和经济制度上认同的逐渐整合为一体,表征为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的趋同,以及保障自由、平等、人权充分实现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化。参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怎样选择时机和方式的问题。 1,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尊重差异性的过程 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最近一位正走红西方的思想家齐泽克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这种观点在西方倍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全球化为什么是一个尊重差异性的过程呢? 在我看来,全球化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即科技层面,制度层面,思想层面,信仰层面: 第一,科技一体化。这种一体化表明中国将尽可能在科技领域同世界同步,中国对西方的科技文明可以百分之百地学习和接受,同时不排除我们可以像"西马"那样反省科技带来的工具理性的弊端。 第二,制度的并轨化。这种并轨的提出只是指证我们的制度轨道可能过窄,应该换成世界通用的宽轨。但是制度并轨应当注意到各个国家的具体环境以及语境,对不同国家需要保留其起码的差异性要求。因而,制度并轨化出现了差异,只可能达到百分之九十。 第三,思想的对话化。这个世界没有中国数学、法国物理、美国化学的说法,但是有中国文学、法国哲学、美国史学的说法,说明在科技领域知识基本是全球通行的,但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差异性向来存在并且正在加大。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不是谁吃掉谁、谁兼并谁、谁垄断谁的问题,而是"对话"与"互动"的问题。这种"对话"大抵从汉代开始到现在两千多年来一直进行着,今后也将永远继续下去。只要是有一定文化身份和价值意识,就会不断地寻求身份的"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中的"对话"表明不同的思想体系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总体上看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 第四,信仰的冲突化。正如齐泽克所说,这是"同一种文明内部之间的冲突"。这种自我冲突化、外部与内部冲突的共同存在已经使差异达到百分之五十。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2]一书中,相当深刻地以鲁迅相信恶的事实力量的绝望体验堵死了儒家的路,以陶渊明植物性的和谐宁静批判了道家的路,以《红楼梦》中价值信仰的虚无化否定了佛家的路,最终抵达"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中国"的理念,强调了只有基督教可以成为真正的信仰。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仍然只能建立在个体信仰上,要把这一观念变成可以普及的全民信仰相当困难,在多元化时代可能也难以要求所有人必得如此。因为信仰的差异性是无可讳言的,哪怕是所谓的全球化时代。 总之,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或者学习尊重差异性的时代,尽管这个多元化的过程将会相当漫长。[3]
二 现代化的最初阶段并非"西化"而是"东化"
地理大发现和东西航路的开通,使得西方人对东方的神奇氛围十分倾倒,同时也想进行东方殖民和文化传教。在几百年以前,有一个叫沙勿略的传教士,到澳门的门口徘徊七年而不得进,他只好去日本,发现日本受到中国文化深刻的影响并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他想,如果要把天主教传到日本,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传到中国,然后辐射亚洲。如果让中国人信奉天主教,连皇帝都成为教徒,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便一帆风顺了,中国就可能变成天主教国家。但是,当时他要想进入中国非常难。由于中国封海,想进入内地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一个传教士,历尽千辛万苦到了中国大门口却几年不得入,1552年12月病死在珠江口外的上川岛上。后来利玛窦等更多的传教士将沙勿略的基本思想继承下来,[9]不断改变传教方式,[10]并逐步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的接触。[11] 这里,有几个问题我们必须面对,并且深究: 首先,现代性与全球化几乎是五百年前同时发生的,至今仍在继续。西方史学家在《大国的兴衰》中认为"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费正清说,"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成就本身"。[12欧洲文明来自东方,古希腊人继承了埃及、巴比伦和东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并加以发扬,并很快达到了奴隶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峰;历史性的西方--包括古希腊的科学民主的西方,古罗马的法制性西方,中世纪神性西方,文艺复兴的西方,近现代的理性的西方,后现代的反理性的西方共时态地被中国接受;地理位置的西方狭义地说是莱茵河以西最早产生资本主义文明的西欧地区,广义地说则是与西欧地区文明有血缘关系的一切地区,如美国、澳大利亚等,日本虽为东方,但在经济政治制度上与英美同属一个类型,也脱亚入欧被看成西方国家。 其次,现代性西方已有五百年的历史,逐步形成两大精神理念:开拓海外市场和谋求经济发展;彰扬人文价值并提倡感性世俗生存。 1,希腊罗马文化理性:15世纪末、16世纪初,拜占廷传来的古希腊文献的手抄本,以其独特的理性力量使人们从神学的蒙昧中清醒过来。文艺复兴时期弘扬的人文主义理想,赞扬人的伟大价值,重视人的尊严,成为西方人觉醒和高速发展的契机。 2,近代缓慢发展的东方古国。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农村社会就出现了一些类似资本主义的现象。《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不少这类描写。中国在近代发展缓慢,而西方拓海开疆,高速增长。如:中国的纺织工具由手摇纺车到多锭纺车的发明经过了一千三百年,而西欧从手摇纺车到多锭纺车自动纺车出现只相距二百多年,少一千一百年。中国从春秋末期公元前600年开始炼生铁,到15世纪冶炼设备同西方相当,中国用了两千一百年,而西欧仅仅用了四百多年。王权在中国存在了两千一百年(从秦始皇到晚清),而西欧存在最长的也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13] 3,遭遇到"他者权力"的中国大国形象:西方人看中国,不仅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东洋镜,还是一个不同立场的人从中找到社会变革的药方或者自己理论依据的思想库。孟德斯鸠从自己的政治理想角度,关注中国思想,希望找到对自身文化范式有用的文化资源。伏尔泰为了抨击天主教教义,从中国儒家尤其是孔子学说中找到新的理论范式,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重塑,莱布尼兹对中国文化多方面研究,为自己的思想蓝图找到了新的背景。无疑,他们在吸收异质文化后的变形中分享了中国思想刚健清新的文化精髓。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一直存在三种种族中心模式或西方中心模式:其一,"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认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主导因素是西方冲击历史作用;其二,"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强调西方的现代性作为世界的通行模式,中国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沿着西方近性道路前进;其三,"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困境的原因。这些模式都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一件促使他国发展的重要事件。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内部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条件,只有西方的殖民才能提供这些条件,中国近代的变化只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是由在西方的冲击下才能产生这些变化。这就将中国本土的历史内因完全抹煞,堵死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哦各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与此相反,美国史学界有学者力倡"中国中心观",反对这种西方中心观,重新阐释中国近代发展的基本模式个中原因。[14] 20世纪的"近东"和"中东",被西方重新阐释并深入到文明内部问题的研究层面,而"远东"问题则落在了西方研究中心视野之外。何况日本已经"脱亚入欧",中国成为一个被不断误读、妖魔化、平面化的国家。谁来阐释中国?中国形象因为什么而"被看"?中国历史究竟应该怎样重新阐释?
三 "发现东方"是当代中国的精神自觉
在新世纪"发现东方",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在于中国自己的言说方式已经全盘中断。 中国文人写了几千年的散文,从《左传》开始,《战国策》,诸子百家等,一直到明清的议论文,达到相当精炼纯熟的高度。近代以降,优美的文言文却突然被西学言说方式所中断。那么,中国在文化思想上是否永远这样下去呢?我们仅仅只有二百多年的落后期,是不是就要变成两千年呢?事实上,在西方中心话语体系中,中国的"经史子集"已经不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也不再具有一般社会教化的意义,而仅仅成为书本性的知识型话语,存在于知识尤其是史学知识的传播中。这段被遗忘的中国言说方式,需要重新考察并做出明晰的价值重审。 今天要做的"发现东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或永远的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的文化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加以整合,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还有那些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一言独霸的一种补充,一种"他者"的言说,一种对西方的置疑和对话? 当然,"发现东方"是要发现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东方,不是要怀旧,也不是要退守,而是要将中国当代新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从而梳理我们的理论范畴、基本命题、核心概念、基本术语和关键词,广泛参照日本、印度、阿拉伯、欧洲和美国五大地区的文化诗学精神,同时借用现代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传播学、文化生态学方法,以重新去解读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诗性的哲学和一些独特理论。 立足于"发现东方"是中国学者的使命,但并不意味着不再关注西方。西方是一个强大的他者,是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一个巨大语境,所以我们不断地要去关注和"拿来","拿来"是几个世纪之内中国学者的一个任务,但任务的核心是开始自己说话。最近西方提出来一种生态批评或生态文化的新理论,其实吸收了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很多好东西,比如说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等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对西方的一种滋养。因此"发现东方"不再是仅仅发现一般的思想,而是发现中国有生命血脉的东西,使其变成我们民族一种活生生的精神。而且,光是"发现"还远远不够,还当有"发现"生命内核以后的"文化输出"与"文化互动"和对话。 在我看来,中国今天的"发现东方"成为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我注意到海外华人学者并没有走向文化虚无主义,而是进行着积极的中国文化重建工作。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多元文化各显精彩的’后现代’社会,儒家应该以不卑不亢的胸怀,不屈不挠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气度,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17]在这一总体思路中,杜维明进一步提出"文明对话"(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策略和"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概念。其中尤以"文化中国"影响最大,引发的争议最多。他认为,"文化中国"是从宏观文化视域来理解广义的中华世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应除儒家传统外还有许多源头,因此儒家传统的意义不能涵盖"文化中国"。杜维明倡导的"文化中国",从深层次看具有相当的文化忧虑,即对中华文化的前景的深层考虑。在他看来,"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如此薄弱,而价值领域如此稀少,和近百年来儒家传统在中华大地时乖命蹇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并不坚持唯有光大儒学才能丰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才能开辟’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但我深信,重新确认儒家传统为凝聚中华民族灵魂的珍贵资源,是学术、知识和文化界的当务之急。"[18] "文化中国"的提出,在当今世界学术界引起普遍的反响,使人们面对中国文化时,关注"文化中国"的多种层次和多种力量的交错,同时对文化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保持关注。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文化中国将研究汉学的洋人也包括进去,使"中国"的含义过于膨胀。但是不管怎样,这位中国文化拓展理解的世界性空间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行动的方略。 中国不可能被他者发现,我们只能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自己发掘出文化的新精神和新生命,从而使中国文化不在新世纪再次被遮蔽。发现东方古国经过现代化洗礼以后的新形态,可以说是中国学界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
四 从"西方"话语播撒到"东方"问题重释
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从五百年前开始的。而五百年前后,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中化""或"东化"。 事实表明,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启蒙精神和人文环境提供了可贵的文化资源。更早一些的西方人像马可·波罗,非常赞赏并学习中国文化。四百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作者门多萨描绘了几近完美的中国形象,其中包含几近神化的对东方文明的喜爱和追随,轰动了整个欧洲。宋明朝代文明的灿烂,使当时欧洲人心目中像天堂一样富丽堂皇和繁荣的巴格达、拜占庭都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中国文化和经济对世界性的现代化曾经有思想资源之功,怎么能说现代化就是西化呢?应该说,在未来的探索中,整个人类需要东方,现代化不是"西化",而且曾经"东化"。起码,应是西化与东化的互相整合。[19] 伏尔泰写于1745年的《人类思想史新提纲》中就认为:"吃着印度、中国等东方古国土地上生产出来的食粮,穿着他们织就的布料,用他们发明出来的游戏娱乐,以他们古老的道德寓言教化习俗,我们为何不注意研究这些民族的思想?而我们欧洲的商人,则是一等找到可行的航路便直奔那里的。当你们作为思想家来学习这个星球的历史时,你们要首先把目光投向东方,那里是百工技艺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东方给与的"。[20]而德国的莱布尼茨博览群书,醉心于中国文化,曾与好几位传教士交谈、通信,甚至想亲自访问中国,同中国学者交谈,甚至还学了些汉语。他的思想与中国思想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尽管有人说他没有受到中国哲学的重大影响,只是得到中国哲学的印证和旁证。[21] 随着中国的衰落,"经济利益几乎把其他一切排之幕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趋于破裂"[22],"随着西欧"中国文化热"的降温,欧洲人不再是中国为人类知识的发源地,而充奉希腊人为人类最伟大的教师,在甚嚣尘上的否定中国文化的言论声中,结束了’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23]当然,也有孟德斯鸠对中华帝国加以抨击的声音:"我不晓得,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24]
五 走出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二元对立
"东方主义"问题的提出,使被长久掩盖的现代中国问题有可能被重新关注和阐释。 尽管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倾向,但他在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了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的明显的二元对立,认为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边缘国往往是仅仅作为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这种强权政治虚设或虚构出一种"东方神话",以此显示其文化的无上优越感。这就是"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 这种重新虚构"东方"的所谓东方主义,使东西方具有了文化价值层面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异己者"。这种"东方主义者"在学术文化上研究产生的异域文化美妙色彩,使得帝国主义权力者就此对"东方"产生征服的利益心或据为己有的"野心",使西方可以从远处居高临下地"看"东方进而剥夺东方。因此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处在西方强势语境的学者个体,应怎样保持个性而不被西方观念所牵引?同时,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又该怎样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在后殖民氛围下同社会和周围环境相联系而又保持个体经验,并对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殖民主义采取批判立场呢?而且,在东方西方、男性女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加以强调强弱的对比,中心和边缘的对峙呢?还是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思维,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后冷战思维得以消解,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冲突""斗争",使得差异性逐渐渗入人们思维的统一认同中呢?而且,在东方主义之后,我们是否就杜撰出"西方主义"来对抗东方主义呢,这种二元对抗又有多少意义呢? 在我看来,"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后冷战时期两种相辅相成、相对立又相统一的重要现象。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二者间差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二者的冲突和融合。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实从来都是彼此依存的,而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自身发展是在冲突中融合而成的。同时又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进而达到更新更高的融合。我主张"多元文化对话论"--既不是完全抹杀各民族自身的特性,走向所谓的"全球化",融合为一体,形成新的单一的文化(西方化);也不是完全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而将人类未来看成一种可怕的互相冲突、彼此殊死搏斗的世界末日图景。我们只能通过对话求同存异,藉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参照系。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当代文化研究有其深化作用,并有可能使我们摆脱一般狭隘的地区意识,以一种新的更大的跨国际语境来看当代西方和中国的文论问题,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29] 在近现代中国,现代身份的"重新书写"首先遭遇到一种"阐释的焦虑",即东方文化在现代化或所谓西化的进程中,成为西方文化凝视(gaze)中的次等文化。在西方虚构出的东方形象中,中国文化被屡屡误读和误解,因此,在对自我身份的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的阐释的"双重焦虑"中,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30]同时,中国文化的"自我镜像"聚焦颇为模糊。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既消除狂妄的"赶超"心理,又避免文化的"自卑"情结,成为清除自我文化镜像焦虑的关键。[31]只有破除这种阐释性焦虑,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可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进一步看,中国学术方式成为非合法,学术言说方式被西方中断。中国传统学术有自己的问思方式,但被西方现代性问题中断。本世纪初,一批理论家,用会通中西的现代性学术方式,将中国的学术思维和写作方式逐渐纳入西方学术模式,从而使"会通中西"成为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基本形态,同时使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方式逐渐丧失了合法性。从此,以西学为参照系的比较性学问成为一种平面式问学方式,有东方色彩的精神和思想似乎难以在中国本土产生和发扬光大。神秘的东方文化已经被"解魅",世界逐渐消失多元文化差异性,而逐步形成一种西式的"同质性文化"。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思想不应该是一种形态,而应是多元文化的对话。可以质疑的是:这种西式同质性文化模式是否是一种本源性模式?一种不再强调多元思想的中心主义话语?这种会通中西的学术角度是否是以一种西学遮蔽中学的运思方式?这种遮蔽今天可不可以质疑?西方学术模式是不是唯一合理的?有没有问思和言说中的独断之处? 这种以西学规范为轴心的局面,使钱钟书先生《管锥编》这类注重感悟的学术模式成为了"另类学术",没有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和合法性(几乎不见任何博士论文敢以这种随笔方式写成并能够通过)。钱先生注重乾嘉学派评点方式与中西会通比较的统一,其学术问思方式强调充分占有资料上的生命悟性和智慧。他是西学功底很好的大学者,但在对待西学模式时,取的是一种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学术本位的立场。这意味着,西方的一些学术形式(譬如现代论文形式),我们不得不借鉴,但在借鉴的过程中,不妨将学术方式与生命智慧相融合,以保存中国文化元气和学术精神。 整体上看,西方学术重逻辑,注重层递性思辨和本质的揭示。西学思辨和东方学术的感悟体验两者都很重要。其实在17、18世纪时,通过一些传教士的文化交通,欧洲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思想受到了明清学术的影响,从德国歌德,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等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单纯从逻辑思辨,而更是从东方生活场景中去体悟或感悟学术,达到一种很高的人文境界。但是现在中国传统学术模式遭到全盘否定,使得"另类学术言说方式"的存在不再具有合法性。这种状况在全球多元对话时代应该有所改观。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学术大抵可以以西学规范为框架,在这一形式框架内注入本土文化生命的内容。东西方有的文化形式是可以通用的,譬如器物层、制度层面的东西大多可以与世界并轨,不必再重头做起。但在思想层面和价值信仰层面则应该保持差异性和多方对话性。西学问思模式有它促进学术推进的历史合法性,但并非永远具有绝对的合法性。任何单一模式的独断和垄断都是可以置疑的。 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价值重建和西方对东方的重新发现是互为表里的。中国文明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保存至今的文明,其中一定有它的合法性。我们可以检讨西方现代性出了什么问题,这一问题发生在西方与中国语境中有什么新的精神走向。我们完全可以坚持开门开窗学习西方现代性中好的精神,并在西方的现代学术框架中,注入中国文化中去除了劣质成分的美好的精神,从而体现出一种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 就学术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能意味着:从事学术需要怀有生命的价值关怀,要对民族、对国家文化有传承和创生新意义的激情。当年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尼采,为的是引进西学悲剧意识和超人哲学,以救国人精神疲弱;其后研究甲骨文,是想借发掘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雄强精神,来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后来他研究敦煌学,是因为看到大量敦煌卷子和文献被运到了大英博物馆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博物馆,研究敦煌学是为了保存古典文化命脉;再后他转而研究蒙古史,也是出于对有分裂的倾向的蒙古的家国时代忧虑。王国维"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32]的学术选择动向与民族国家关系甚密,他的学问推进维度可说是与时代命脉相合拍的。[33]而现在有些人,只关注个人眼前的利益,民族国家的事则置之度外,举世皆惊之事与己无关,切肤之痛之事与我无涉,不去发掘自己的文化,而是抱怨索求多于重建关怀。像这样一种态度和做法是一种"精神自废"。一旦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因为经济振兴而有了文化发言机会时,就会尴尬十分。
六 现代性问题与中国文化身份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滚滚浪潮,中国在科技领域应该进入现代化,但在文化领域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以东方智慧在文化领域发展新世纪社会文化良知。现代化应该是以"人为目的"。而且各国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整个人类体现"东方智慧"。因为人类的未来只能是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和互动。 但是在现代性问题上,不同民族的自我选择变得更加艰难,因为据说杰姆逊说:"早已被超越的现代性幽灵本身,不但没有被超越,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大举登场,比如在拉丁美洲,在第二世界如前苏联等,无处不在。"这次古老的现代性在当代语言里痼疾复发,真正患的其实是一场后现代病。可以说,这是一场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以供它在知识市场的大量生产和重新销售。" [34]可以看出,杰姆逊在无意识中有一种对"现代性"重新登场的复杂暧昧的感受,一方面他觉得可以重新对历史话语获得一种叙事形式,另一方面,现代主义本身变成了"不现代的东西",如今那种能够被肯定的现代性之所以好,是因为它是后现代的。这位认同全球话语权力结构的学者,尽管曾经同情过第三世界,但还是终于将立场移到了西方中心主义上,认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无意识领域广泛传播他们的殖民话语意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无条件地被动接受。我怀疑的是:他所说的"后现代的成就"果真如此吗?而且,在后现代这个充满差异性的时代中,杰姆逊似乎拒绝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做出自己的自由选择,其的基本策略是,不同意区分信息革命、全球化自由市场意义上的现代性和令人厌恶的老现代性,只因为他认为这种区分毫无意义。 他认为,有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式的现代性、非洲式的现代性等等,还有希腊正教或东正教式的现代性、儒家现代性,那么现代性的数目就可以和汤因比所列的宗教一样多。因为在他的心中,全球的现代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现代性只有一种--欧美霸权式的现代性。这一说法委实令人惊讶!其实在我看来,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中心模式的差异是明显的,它也可能不同于日本、韩国、东南亚,或者中东、印度的现代性。杰姆逊认为这种多种多样的现代性都是毫无道理的,只能臣服于标准化、霸权主义的英美模式的现代性,这里隐含的文化霸权问题绝非可以轻轻放过的。 这种观点是西方中心的--后现代状况是一种文化的根本断裂,过去所拥有的经验(前现代经验和现代经验)在当代业已失效,多国资本的新扩张最后完成了对前资本主义飞地的渗透和殖民化,人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非道德化的、令人压抑的、前所未有的新全球技术空间。文化艺术在错位中不断生产着文化话语:"我们忽视了现代性的另一个根本意义,这就是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在讲演结尾的这一西方中心语式的说法,表明了杰姆逊的新世纪立场。这一立场至少有三个维度值得质疑。其一,强调全球化问题,因为所谓"全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可质疑,这一点已经与他早期对资本主义逻辑的批判和质疑南辕北辙;其二,资本主义在发展的高峰期时,有一种标准化的图式,即一体化、同质化,没有区分的模式,使得一切文化多样性成为不可能,这样对多元对话,对解构主义强调的文化差异性,对多元多种多层的可能加以全盘的否定,为这个世界成为整体化、单一化的西方世界张本。其三,在其全称判断中强调,未来世界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这是否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逃离这个普遍的市场秩序的殖民化一元世界?这个世界的多元选择的历史走向真的就此结束了?现代性"幽灵"究竟成为了这个一元世界的"撒旦"还是"上帝"?而且我想追问的是:发现东方和阐释中国的主体究竟是谁?是老外是新老汉学家还是盲人瞎马的技术官僚?中国现代性是否是西方现代性的复制?中国新世纪是否只有被经济文化殖民才能放逐本土性融入全球性? 这种颇有代表性的现代性观点提醒我们,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必须具有自身文化的指纹和身份。如果丧失了这种文化身份,这样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仅仅是后殖民进程而已。当然,立足于东方,并不等于对西方不再关注,相反,正是因为东方的"他者"是西方,只有面对这个他者,面对这个"镜像",中国问题才能真正浮出水面,即不仅看到传统中国的文化形态,而且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形态遭到西方文化中断式挑战,以及中国文化复兴的新的可能性。当代中国需要寻求审美共识,将中国文化的审美内容铸进国际相对具有共识感的审美形式中,进而从不断反传统的怪圈中走出来,从"审传统"走向"审自己",真正地面对决裂与选择。在我看来,中国学术的发展不是一条路、一种声音、一种模式可以决定的。全球化中的思想和学术不应该是一种形态,而是应该有多种形态。 同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注意,这就是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中究竟提出了怎样的理论范畴、命题、概念、术语、关键词?我们是否应该在广泛参照东西方(包括日本、印度、阿拉伯、欧美等五大文化地区)的文化诗学精神中,又广泛吸收现代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传播学的新成果?我们应该怎样总结世界各民族文化积淀的审美经验和文化理论,从各民族思想的交流、碰撞、融合中,研究文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命题,从而使中国式的诗性文化进人世界性和后现代性阶段?中国文论在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中走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由张扬主体的人、倡导启蒙到"寻根",然后反主体、语言游戏、"后"语言游戏,游戏之后则"失语"。中国文化或中国文论是否已经失语?这种失语的内在原因是否仅仅是西方的文化压榨?这些问题,彼此关联,需要综合阐释和具体解答。 在这个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论的反省,使人们注意到东方思维的多层多元性,并对东方思想中一些活生生的东西,诸如:生态文化、绿色和谐精神、辩证思维、综合模糊思想、重视原本性与差异性、文化价值观多样性、以人为目的的"仁者爱人"等等,加以重新体认,以求能纠正西方中心话语霸权之狂。当前的生态文化思想,无疑有着东方文化的精神栖息在其中,说明中国文化输出问题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 然而,一旦考辨西方中心或中国边缘,西方的话语权威和中国的零散和中国的孤独感等问题,这种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的心态这便成为多种思想论战的导火绳,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心态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应该全盘西化,还是半盘西化,还是坚持中国本位,成为百年纠缠不清的政治问题。 在国外曾看过一次电视辩论,深受震撼。NHK电视台邀请了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和在日本的中国人,要求配偶必须是白种人、洋人,同时他们还生了孩子。最妙的是,它分为三方,即甲方、乙方和孩子,甲方即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婚姻不幸"。他们与白种人走到一起,但生活在阴影中,因为对方不愿意说日语、韩语、汉语,因此他们在表达最微妙的感情的时候,最先总是用英语不清楚地说;而乙方认为东方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否则我怎么会娶东方的妻子,或嫁给东方的丈夫呢?但是永远也体会不到他们文化深层的意蕴。最有意思的是第三方--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祖国在哪儿,不知道父亲的文化是什么文化,也不知道母亲的文化是什么文化,自己身在何处,自己应该说什么……。由此我想到,如果中国文化真正地全盘西化,我不知道是复兴古希腊文化,还是古罗马文化,还是西方文艺复兴的文化,还是现代文化,还是后现代文化?这样我们的文化就会变成如同辩论中孩子一方那样的混血儿杂种文化,那时又该怎么办呢?是不断地一代一代混血下去,直到中国文化的血缘关系微乎其微?还是我们应该选择在相互的价值立场上进行对话和会通? 同样,在后殖民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身份问题非常关键。今天很多人都以知识分子自居,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没有思索,不能提出问题,不能对前沿的问题甚至是前提性的问题做根本性的追问,对问题没有本质性界定。一些思想的超越和形而上学的思考被取消了。因而,人文知识分子不仅要放弃虚无主义立场,还要放弃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才有可能在"极高明而道中庸"中,找到价值重塑的思想地基。 在我看来,我们在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中,只能是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审美共识(不管是文学的还是艺术的),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的"文化财"(狄尔泰),才有可能组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只有这样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维持整个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 七 在"文化拿来"中坚持"中国文化输出"
当代中国学者在文化拿来与文化输出问题上,遭遇到西方强大的语境。赛义德,德里克,只是为自己本土说"东方"。在我看来,周蕾无疑是海外华人学者中对后殖民语境中"中国问题"尤其是"香港问题"有着全方位思考的学者,她对后殖民霸权的"看与被看"的关系的分析,虽然受到福柯的影响但有着自己的提炼。她对海外汉学家"绝对化中国传统和轻视当代中国文化"的文化歧视和内在焦虑的分析,对外部殖民和内部殖民的双重警惕,对后现代混杂派无视后殖民中的"殖民"问题的批评,以及对第三空间的论述,都可以看到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深切关注。她敏锐的理论思维力,清醒的后殖民身份分析意识,都使得读其书,而能理解其处身第一世界学术圈层中的边缘性挤压。[35] 同时我也注意到,周蕾注意播撒自己的思想,其著作(如《写在家国以外》)相继出版英、中、日等多种版本,并微妙地变换书名,从三个书名中可以看出其中关键词转移的重心所在。她在海外研究香港远眺香港,用殖民话语框架和知识分子理论来看香港的流行文化,将主要为流行文化的内容命名为知识分子研究,不免显得有些勉强。书中有的论旨还可以再讨论,诸如作者反中心话语立场,使得反殖民主义时却将香港膨胀和置换成新的中心,强调香港的现代化就是中国的未来图景的"最前线"意识;书中多处言述表明作者存在着冷战意识,一方面反英、一方面拒斥大陆,认为香港语言与文化是杂糅的,因而它已不带有中国色彩而成为独立的"第三空间";具有浓厚的精英知识人情结,要以时髦的后殖民理论申说香港和中国的非同一性,强调香港经济地位、文化观念、历史处境同大陆的差异,为香港这个"沉默的"地区代言。在我看来,在多种体制和价值互补并存的时代,这种较明显的政治性情绪和"另类社会"意识与客观的学术研究所存在的距离,尚有待弥补。 另一方面,周蕾也指出了老汉学家阐释中国的焦虑。在批评哈佛大学汉学家宇文所安(另译欧文)教授对第三世界作者的政治歧视时,周蕾表现出相当的学术勇气和敏锐的眼光。在她看来,在宇文批评诗人(如北岛)为了"自身利益"而屈从于跨国文化商业化倾向时,宇文却没有反省造就他自己话语机构的资源--他自己的"自身利益"。这种批评他人不用同样苛刻尺度去裁判自己的态度,实际上形成一种固定权力形式,这种形式不断地被阐述和巩固,因而使东方主义在东亚研究领域中根深蒂固。对宇文来说,这种对他人"不忠诚"所作的道德主义的控诉,却掩饰着一种更根本的焦虑。"这焦虑来自汉学家觉得他致力探求的中国传统正在消亡,而他自己也正被人抛弃。"[36]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不仅中国学者内部出现了分化,即从事古代问题研究的学者对现代文化学者扬弃传统中的某些问题的做法表示反感,而从事现代文化研究则又深感古代文化研究的"保守主义倾向"。周蕾敏锐地看到中国身份地位的变化影响着汉学家的身份地位,使得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现代化(或西化)状况深感不安,这种情绪被周蕾看成是一种阐释中国的焦虑。这种"宇文所安的焦虑"--宇文所安因解读北岛的诗而感到其已经相当西化,中国诗歌的本质属性发生了变异,"中国"变得不再像传统的"中国",于是阐释中国现代诗的典籍阐释权威"对自己的学术位置感到焦虑"。在周蕾看来,这种研究事实上是"他者"的被他者化,"中国"的被中国化的现实处境,关注文化边缘化过程中,所呈现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意识"商品化"状态。周蕾的看法尽管相当尖锐,但是也说出了汉学家面对当代中国失语的几分实情。 文化透支和文化赤字仍然没有引起学界注意:百余年来中国从西方翻译了近10万本书,但是西方实际翻译的中文书却不到100本。日本1894甲午海战之前每年翻译中文书平均70本,但是1894-1911年16年间,大约只翻译了3本,而且还是数学方面的。[37]相反,20世纪初到日本求学的国人难以计数。从1806年到本世纪最初的十余年间,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有数万人之多。仅1906年就有8600人前往。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留学生到日本大多并非以学日本学术为目的,而是以学习西洋文化为目的。[38] 这些人或留学、或旅居著述、或流亡,均积极吸收新知识和新思想。这无疑对现代中国学术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认为,正是各种西方和日本译作涌入中国,与传统思想相较量,而最终改变甚至变革了传统精神,进而取代了传统思想的中心地位。而一些未能出国的学者,也在学习日语或翻译各类著作。在译西文东文时,又经常遭到国粹派攻击之苦;[39]在翻译西学和接受哲学思想方面,中国思想界本世纪初通过先行走向现代化的日本这一"中介",[40]开始了苦学外语(日语和西语),并急切地译书。[41] 就当代中国而言,问题在于我们经历过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后怎样走向文化输出主义?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我们如何输出?我们是否具有输出的资本?我提出关于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主义"的时候,有人认为走向输出主义,中国有这个本钱吗?好像中国是一无所有,落后西方很多,天天说落后就要挨打,居然还要说输出,认为是异想天开。我认为:我们有诸子百家群星灿烂,可以看到西方包括东亚若干国家,历史上几千年来没有中华民族这样多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在当代西方获诺贝尔奖的科技方面相当多的同样是中国人,同时还有二十年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经验。中国当代文化不能老依赖别人靠知识输血过日子,也要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文化创造性。与文化创造性相对的是"文化挨打性",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我们的文化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下,要化挨打为创造,化文化拿来主义为文化输出主义,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应该有足够的自信。问题是如何输出。 文化输出表明中国将在三个层面进行文化阐释和输出:知识型(古典经典),对话型(20世纪思想),生态型(东西互动的当代状态)。这种阐释和输出具有文化诸动性和自我选择性:以我为主,东西互动,合而不同,中国形象,文化生态平衡。面对当代的西方中心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文化思潮,中国在努力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应该从一个世纪的"文化拿来"推进,进入当代中国的"文化输出"。中国如何让外国人认识自己?日本人10年前从经济大国走向文化大国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中国应该使自己优美的文化精神走向世界,这需要几代中国学者的艰苦努力。 回到最初的话题。沙勿略到了澳门的门外,千辛万苦历尽艰难想进来,没能进来。是什么支撑他?他为什么要如此遭受磨难?他是在做文化和宗教输出!他想如果他将西方宗教让中国皇帝接受了的话,那么整个国民不就全接受了吗?其后的很多传教士,学中文,学中国的礼仪,三跪九拜,甚至将《圣经》按儒家的一些词汇翻译过来,目的就是让中国接受他们的思想。不妨问一下,当代中国还有哪个知识分子、哪个博士硕士有这种站在一个国家国门之外要想把中国文化传播输出的愿望和百折不悔的意志?今天很少有人有这种想法了。所以我每次读到那些传教士一个个前赴后继的到中国各个地方去,甚至到中国最穷的地方去,四川、山西等等地方去传教,不禁掩卷长叹。但是,今天中国文化人已经少有这种自信、自强和眼光了。 有人会说,西方文化那时很强盛才能传出。其实唐代时候的景教(基督教)并不是全球的强盛宗教,[42]而唐代长安政治经济之发达可谓全球之最,是外国人梦想进入的"天堂"--犹如我们今天去巴黎、伦敦和纽约一样心醉神迷。他们为什么在不发达之时尚能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思想文化传播出去?当代中国已经现代化之时为什么还自卑缺乏底气和不传播出去呢?为什么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不断提出,中国在四十年以后将同美国的生产力齐平,二十年之后将与日本齐平之时,中国还没有意识到在经济大国中文化输出的重要性呢?日本在1985年提出要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一个文化输出大国,因为日本人已经发现,西方人包括中国人东方人把日本看成是一个经济动物,而且它的国际形象不好,因而它开始通过输出文化获得他国的文化认同,由政府投资几十个亿,开始全盘输出他们的哲学、文学、史学和艺术。日本是接受中国文明的滋养长大的,而它先中国一步输出文化的结果,就是使日本进一步变成了东方文化的代表。而中国人今天是否应该也有这个共识?
八 文化输出的可能性与困难度
在后东方时代,关于东方文化魅力、文化对话与差异性互动,也应该成为超越冷战二元对立模式,而进入中西方文化互动互渗中。这就需要看看我们做西学或审视西方的基本视角。 审视西方有三种视角。一种是"仰视",我称之为叫做后殖民主义,把西方看得高大无比;第二是俯视,觉得是自己是老大,这叫做民族主义或者极端民族主义;第三是平视,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态度,具有良好的对话品质,就是对西方是平视,平视中西方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和生存困境,面对人类的未来。因此中国学者就需要对当今世界性的困境,比如说能源危机、环境恶化、战争升级,心灵焦虑,以及基因转换等等,提出中国解答的方案,比如说辩证适应,多元并存,平衡生态,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等等。这样对西方过分的竞争,过分的往前追新而造成的文化断裂,可以说是一种本体论抑制。同时,中国人再也不可以一味地"审父"--审判自己的传统,把所有脏水都泼到传统上面,都是因为儒家搞坏了,都是因为道家搞坏了,都是因为孔子搞坏了。错了!当时恰恰没搞坏,我们失败就是最近二百年。同时也不能完全是审"他者",他者是西方,所以我们批评起西方什么腐朽没落,什么资本"吃人"等等这种词尤其要谨慎。我们应该把视野从"审父"到"审他"变成"审己",审判我们自己,看看我们什么地方,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哪些地方不如古人,哪些地方不如西方人,我们面对的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能提出前沿性的话题,我们只能跟着别人后面去提话题,我们只能跟着别人后面去走,总是做第二第三。 我认为,审视西方的同时应该重新审理自己的文化。看自己的文化也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国粹主义,地方主义,就是说中国一切都好,妄自尊大,盲目排外,这在前些年"中国说不"丛书可以看出来;还有一种是虚无主义,自卑主义,奴性主义,就是西方一切都好,中国一切都不行。有人说,中国如果全盘西化100年就好了。这不值一驳。我们知道,印度和我们周边有几个小国就是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但他们现在的处境还不如中国,所以被西化或者被殖民并不意味着更逼进现代化;第三是文化集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这是将文化意识形态化,同样值得注意。这三种"主义"都有自己的盲点,需要重新获得文化对话的新视野。 文化输出的主要障碍在于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可分为几个方面来看: 其一,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有的人的心理被打败了。拼命跟西方,跟还来不及,遑论输出。超前性眼光和对话气度很难成气候。缺乏评价自身文化的眼光,要么数典忘祖,要么什么都好。 其二,我们的文化之"水"还不满,没有输出的前提。但我们有这种可能性,有想法。中国茶道、中国书法、中国武术就输出去了。最近出现了文艺生态学、生态文化,就有东方色彩综合治理、协调平衡精神,无疑吸收了中国文化精髓。 其三,我们缺乏有文化输出胆识的人。热衷于节日庆典、大型歌舞,把书画看成退休老人的事,把琴棋变成了少儿的所谓素质培养。目前的文化输出多是民间团体在做。几年前季羡林先生就提到关于中国文化的送出主义。不是人家来拿,而是我们送出去,但是我们主动送出,人家不要,对我们也很不利。因此,我认为用一个中性词"输出主义"比较好,就是源源不断输出。 其四,我们在普及的基础上没有提高。我们的书法练习者有百万大军,国家书协有五千会员,地方一级有近十万会员。但应该在普及基础上推出能够与外国书法家对话的重要书家。新加坡十年前开始搞书法国际联盟,中国作为书法宗主国,却没有什么发言权,不是没有写字的书家,而是没有能代表文化高势位的真正的大师。在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将书法写好了提升了,我们才可以输出。我想,送出去不好的过时的东西,甚至已经被抛弃了的、僵化的东西,人家当然不要。如果你送出去的是一个具有特色的东西,我就不相信我们具有乡土气息的中国书法就没有人要。应该明白:不是"新就是好",而是"好就是好"! 其五,我们缺乏可"文化的持续发展"的眼光。活动前搞排练,过了就完了。现在太多的急功近利、太多的短期行为。"文化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概念,也不是一个国策的问题,我认为是东西方文化共同发展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化战略问题。我们需要弄清:中国文化哪些东西还残存着思想的碎片可以被我们整合起来?哪些残存的文物和文化形态可以被我们聚集起来?当代学者都应该用心去思考,这样方可以发掘出本土文化精髓,逐渐地生成出新文化的可能性。我们不要把中国文化艺术搞成千人一面,而是要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不可替代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又同中国整体文化的根相联系。可持续性发展就是发掘民族的根、发掘具体心灵的根,应尽量以不同的形式做得更完美。 最后,文化输出缺乏资金。只能通过民间方式吸收国内和海外资金。我们的海外华人有七千万呀!这个工作意义非常大。有一段时间,外国人把中、日、韩称为"筷子文化圈"。我认为应该是"汉字文化圈",吃饭的筷子可以变成刀叉,它只是一个运作的问题,它不会进入神经、进入身体,化成我们的血肉。汉字则可以进入思维、血脉和集体无意识中。我们可以不用筷子用刀叉,但是不可以废除汉字。历史证明,离开了汉字,中国文化仅仅两代人就中断了;韩国很多思想包括名字的叫法都不太清楚;日本的片假名,在写一个名字的时候就可能出现许多歧义,因为它的名字用汉字表达时是浓缩了的意象。因此,强调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地位,在东西方互动并重新"发现东方"的新世纪尤为重要。
九 "文化输出"的整体工程
任何一个民族接受异质文化都奉行文化拿来主义,但是只有自觉的文明形态,才会再拿来的同时考虑文化输出问题--知识型输出,文化行输出,当代性输出,没有价值批判的意味。 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交流,就是思想和哲学交流,文化分为三个层面: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实用文化。停留在实用文化和民俗文化是不够的,注重风情,民风习俗,节日庆典,仅仅是一般层次的交流。只有思想哲学层面的交流才能深入到文明的内部神经。很长时间内,中国文化输出仅仅注重器物类工艺层面的"中国化":茶、瓷器、丝织品、工艺品(漆器、玉器、景泰蓝)、建筑园林17世纪18世纪,而对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尤其是20世纪和当代文化输出相当缺乏。而且,输出的大多是精致性的(清代):鼻烟壶、蛐蛐罐、景泰蓝等,而对中国文明气象收缩:新石器时代的陶罐,汉代的陶罐…… 这样一个长期、浩大的工程,需要众多的学者集体参与,需要中国学界有自觉的向世界整体推出中国古代和中国现代思想家群体思想。古代精品文化的输出同样重要,如四川的三星堆、内蒙的成吉思汗陵、湖北的编钟等,皆为上品。我曾在谈到这几个文化符码可以向西方介绍的过程中,遭遇到了本土虚无主义者。谈到三星堆青铜雕塑时,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教授说,中国的雕塑不行,当古希腊雕塑已经美仑美奂时,中国雕塑还不敢雕人,只能雕那种傻大粗的鼎。我马上到湖北省博物馆看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细细考察出土的编钟和各种青铜器,我看到了《青铜尊盘》,其复杂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尊盘共雕饰龙84条,蟠縭80条,尊盘中尊与盘的口沿均雕饰以透空花纹表层纹饰互不关联,彼此独立,圈靠内层铜梗支撑,达到了玲珑剔透、层次分明的艺术效果。这是用湿蜡法一次制作成功的。到现在用高科技都难以重复。是怎么做的模子,能够如此繁复精美。西方人用重金买这二百多公斤的鼎,可以想象这是什么价值。而这位教授说中国不能雕出人面,也不正确。四川三星堆出土的人面像《青铜纵目面具》,顺风耳千里眼,近1.38米宽的巨大的脸,眼球伸出16厘米长,硕大无比,十分壮观,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古代蜀国的社会意识和宗教观念。西方人认为不是中国人造的,认为是外星人造的。为什么中国就不能造这种青铜人面像呢?而且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中国说问鼎中原,"鼎"是权力的象征。三星堆的权力表达是同西方 "金杖" 一样的象征意味,一根1.42米的金杖。由于经过了三千五百年了,里边的木头已经完全毁掉了,但是外面包的金皮还在。可以说,中国的三星堆比希腊的文化还要早。它的雕塑不能说是不美,还有很多女性的装饰品,细如发丝骨针,非常漂亮。所以不应该妄自菲薄。 还有湖北隋州的编钟。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亲耳告诉我,中国的编钟不行,连十二平均率都不是。我听了以后带着这个疑问请博物馆专业人员用锤子敲整套编钟,他轻松愉快的就半音阶下行,就是钢琴的黑白键下行的方式就敲出了十二平均率,而且一个钟可以敲出两个不同的声音。在两千四百年的战国时代,我们中国的十二平均率就已经出现了,为什么我们音乐学院的教授就一叶障目看不见呢?令人不解。 中国应该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文化传统我有四重态度。第一就是看看我们两千多年的文化,哪些已经变成死的文化僵化的文化,就坚决抛弃之,诸如裹脚束胸等。第二要用另一只眼睛去看,哪些文化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我们的硬盘需要整理一样需要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集中使用的"文化群"。第三,可以看看两千多年的文化中,那些是可以弘扬光大的还有生命力的文化。我不相信一个民族有十三亿人,文化死掉了以后她的精神还不死是不可思议的。第四,就是要看那些文化经过与西方思想碰撞以后变成了新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不仅滋养中国,有可能变成世界的共识框架。我认为这四个层面我们都应该去思考。 我们还需先从头做"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因为一个不懂得自己历史、自己文化本源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文化的未来的。就像尼采所说的,有人永远只懂得向这个世界"索取",而不是"塞入"。尼采说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对这个世界创造和塞入意义,一种就是取出和消费意义。可惜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取出。 中国迫切需要"自我发现",这种"发现"就需要总结文化深层内容: 首先,挑出从先秦古籍里一直到清代中的重要作品翻译成英文,这个工作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经做过一些,可惜他们很多是老外翻译的有不少错误,再加上没有导读,就像我们今天读柏拉图、苏格拉底,如果没有导读,这样一本《理想国》,人们恐怕也会不知深浅,所以需要我们自己展开。集中力量翻译影响中国的一百本经典。我大抵是受了玄奘的启发,他"出国留学"--到西方取经,历经了多年回到中国后,在大小雁塔开了译经场翻译佛经,并进行到底。那么,我们今天只能小规模地翻译。 其次,把二十世纪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一直到季羡林等的思想结集出版并翻译。我在1995年就开始做了,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套《20世纪学术文化随笔》一百本。这些书是这些学者经历了欧风美雨之后的中西思想火花碰撞的结果。 再次,翻译六十本"中国当代文化生态"问题,如中国书法生态、中国戏剧生态、中国建筑生态等,分析考辨各种文化形态在二十世纪的痛苦发展和未来处境,做六十本。整套书一共260本书,全都译成英文。当我们把这260本书放在外国人的书架上之时,他会对"远东"的中国有新的解释和了解。这时文化误读就会少一些。千万不要认为"文化输出"就是要拯救西方的精神文明,这是痴人说梦,我们再也不可能有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那样的拯救西方的思想了。 就文化输出而言,有人问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输出,这其实是想说明只有"高势位文化"才可以输出。我想问,为什么西方人要去看云南丽江?丽江文化难倒比现代的北京或者西方还要高明吗?难道就人类不可以怀着古之忧思吗?我们去看的古罗马文化就比现代美国文化具有高势位吗?"文化输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高势位地征服别人,也不是水往低处流。在我看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输出",是为了不让西方误读我们。我们面对一个强大的西方,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它,我们是与人为善的,我们是有悠久历史的,我们的祖先就是温文尔雅的。通过文本阅读,他们会知道中国文化是一种可以对话的和平和的文化。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