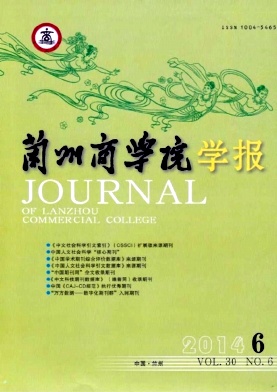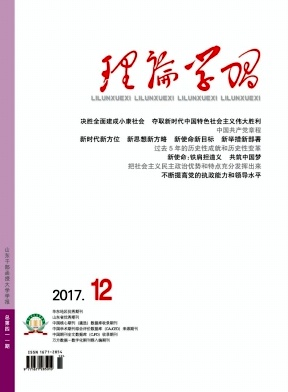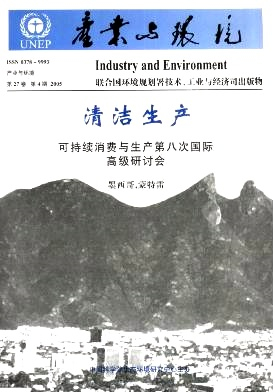发现东方与重释夜郎文化
王岳川 2006-01-22
当代中国已经真正走向了与其他文明对话的世界性开放之路,这意味着她更加理性地对“他者”文明,同时更清醒地面对自身文明,在质疑文化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寻求着真正平等对话的文化新秩序。在东西方文化平台上,世界需要重新“发现东方”,发现中国文化的独特的东方生态文化魅力;而中国也需要面对世界,读解自身的文化之谜并获得全新的普世性文化认同。
一 在全球化语境中强调“发现东方”
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社会遗产和话语编码,不仅有民族创造和传递的物质产品,还有集体的思想和精神产品与行为方式(各种象征、思想、信念、审美观念、价值标准体系)。这意味着文化无优劣,而只有差异,并必须学会尊重文化的差异。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一直经历着与西方和其他文化的长期对话和文化碰撞,文化互渗(acculturation)已成为新世纪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基本品格。
冷战结束使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北美经济军事的发达一体,欧洲经济货币的统一,而亚洲统一的排头雁问题成为相当敏感的问题。于是,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诸如近些年文字印刷界和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之争,已引起各方的关注。
李学勤认为:“有意无意对中国古代文明贬低的倾向,仍然是存在的。其具体表现有两方面,一是把中国文明的历史估计过短,二是对中国文明发展的高度估计过低。……这样做,抹煞了近十几年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实在是不公平的。” 在我看来,文化交流不是一种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种交流的多极性问题。只不过在西方现代性光谱中,“东方”已经削弱了立法和阐释的权力。进一步说,“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本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是东方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因此,东方(尤其是所谓“远东”的中国)如果继续沉默、失落、被误读,将使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出现严重的问题。
近来,西方提出“生态批评”或“生态文化”的新理论,其实吸收了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仍有生命的思想,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思想等。 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互动的结果。因此“发现东方” 是发现中国有生命血脉的东西,使其变成世界文化中的鲜活的精神。
全球化的深入,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将终结,而东方文化应该得到重视。新世纪的“发现东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已经死亡了?哪些部分变成了博物馆文化只具有考古学的意义?哪些部分变成了“文明的断片”可以整合到当代生活中?还有哪些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一言独霸的话语置疑?当然,“发现东方”是要发现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东方,不是要怀旧,也不是要退守,更不是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东方,而是要将中国当代新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从而梳理我们的理论范畴、基本命题、核心概念、关键词,广泛参照日本、印度、阿拉伯、欧洲和美国五大地区的文化精神,同时借用现代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传播学、文化生态学方法,以重新去解读中国传统的文化诗性的哲学和独特理论。
人文社会科学的兴盛是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命脉,其价值高低成为“国家柔性国力”的综合呈现。文化的意义在后工业时代日渐突出,西方不断在输出自身的文化意识形态,美国的“三大片”——“薯片”式的快餐生活方式,“芯片”所代表的电脑核心技术,“大片”式的影视视听方式,也有人称之为“可口可乐殖民”(Coca-colo-nization),似不无道理。而中国文化却在一个多世纪的“拿来主义”中,被逐渐排除在集体记忆之外。因此,必须将重建文化根基和民族认同的地基,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二 发现“中国两河流域”中“长江文明”的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中有一个思维定势,总是单面强调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而且虞夏商周各代王朝都在黄河一带建都,文化中心从黄河中下游向外扩展。有人甚至认为长江文化区域长期处于蛮夷匮乏状态,直到六朝乃至宋代,南方才成为发达地区。这种看法在如今的考古发现面前已经站不住脚。
长江上中游的成都平原田野考古发掘,表明古代巴蜀先秦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已然形成:宝墩村文化(前2700-前1700)-三星堆文化(前1700-前1150)-金沙遗址(前1200-前600)等,尤其是近年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面具和玉器等文物,表明金沙遗址与三星堆一脉相承。 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出现许多不同于殷墟甲骨文和中原青铜器文字,这些巴蜀特有的符号文字,至今无法识读。 可以说,三星堆等珍贵文物的发掘,呈现出长江文明在史前的辉煌灿烂。
但是,面对这样辉煌灿烂的文明,有人仍用某种殖民文化的眼光看中国。如苏三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三星堆大猜想》,认为全球文明同源即人类文明都发源于一个中心区域,各个文明并非割裂生成。三星堆文明不是内生而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Semite)人,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的闪米特人建立的政权,即古犹太人的一支,他们在历史上曾大规模地迁徙,后经过现在的伊朗、印度等国家及地区,于4000年前左右来到成都平原。因此中华文明起源于古代中东,犹太人是中国人的祖先之一。在我看来,这位作者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和考古材料,充满了误读式的理解和缺乏依据的充满主观臆断的过度“猜测”。在《向东向东,再向东》中,她认为文明起源地从中东不断向东方迁徙,处于东方的中华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宫外孕”。这位考古的外行用《圣经·旧约》的材料加以牵强附会的解释,认为中国文明是中东文明或中亚文明,最终都经过了基督教的熏陶。这种“中国文明西来说”,不过是再次重复上个世纪的西人斯坦因的殖民理论罢了。
事实上,不仅长江上中游具有高度发展的文明,下游地区同样有相当高度的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年代当不晚于仰韶文化;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对夏商周中原文化饰物上纹饰饕餮纹的影响一目了然; 湖南澧县屈家岭文化城址距今4800年,当比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古城更早;商周时期中原王朝青铜器原料考古证实来自南方的江西、湖北和安徽,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要津是在南方; “古夜郎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更加凸现出整个长江流域文明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西亚文明起于著名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文明兴盛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那么可以说东方的“两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共同哺育了中华文明。“中国两河流域”及其文化意义在于,长江文明的重新“发现”“探索”,使一段失落的文明和掩埋不彰的文化终于浮出历史地表。于是,整个长江流域的历史因此而重新改写,整个中华文明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乃至艺术美学史,正在重新书写。
三 寻找“失落的文明”与重释“夜郎文化”
中国过去是“国中之国”“中央之国”,人均GDP在1820年仍然处于世界的前列。 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初到中国,向中国人展示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使士大夫们大为不满的是,中央之国被挤到地图东北的一角。虽然当时中西双方力量的对比依旧可以支撑天朝上国的自信,但“大世界”却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中国人传统的“夷夏”观念。到清末,鸦片战争以降的一系列败绩致使中国甚至难以维系自我身份的认同,产生了重大的身份危机和面对世界的焦虑。
如果说,现代性西方中心主义使得古老的中国被边缘化,那么,古代中国汉文化中心观又使其将中原地区之外的民族看成“夷”“蛮”之地,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缺乏平等交流的基点。其中,“夜郎自大”这一成语流传甚广于其中可见一斑。
国人大抵是通过“夜郎自大”这一家喻户晓的成语触及到夜郎的。夜郎作为一个被历史误读了两千多年的名字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夜郎历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起于战国而终于西汉成帝年间,后来又神秘地消失,存在大约三百多年。对夜郎国记载主要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书中。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从此,这个本当属于“滇王自大”的说法,就成为西南地区古国“自大”“夜郎”的别名。如今,古夜郎都邑、夜郎王、夜郎国的范围,以及夜郎民族的生活习性和夜郎文化的基本特征等,都成为历史之谜,引起各种不同的文化论争。
20世纪90年代末,湖南、贵州、云南、广西的学者开始深入讨论夜郎文化历史和意义。古代西南地区冠以“夜郎”县名的地方为数不少,古代贵州有三个“夜郎县”,湖南新晃有一个“夜郎县”,云南也有一个夜郎。云南专家据新近出土的“铺汉王印”为据认为夜郎古都在云南沾益;湖南学者则提出怀化西部方属古夜郎发源地;广西学者坚持夜郎国都应在广西凌云。在我看来,根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出土文物和地上文献互考,夜郎古都应在贵州境内,其地理范围大致包括贵州黄平以西,广西百色以北,四川宜宾以南,云南楚雄以东的范围,形成一个横跨几省的“大夜郎”的观念。出土文物的支持非常重要——2000年的贵州可乐墓葬群的发掘考古,出土一批极为珍贵的青铜文物; 普安县铜鼓山遗址出土的夜郎时期的铜兵器、陶器、套头罩, 还有一些生活器具。其精美的程度与中原无异,令人吃惊。
据《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以计数,夜郎最大。”又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在当时西南诸国中,的确是“夜郎最大”。但是不是“自大”,还应该认真讨论。细细斟酌“汉孰与我大?”不难看到,这其实是古汉语的疑问句,一种正面的试探性提问,而不是一种自大的口气。作为南方诸国中的一个大国,夜郎真正希望知道外面的大千世界,处于这四面环山的封闭的云贵高原,想知道外面的精彩世界,想探究中原究竟有多大。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夜郎王向往汉朝的文明,不仅约为置吏归属汉朝,而且受金印册封,并派使者到京城朝贡。在这个意义上,“孰大”不是说自己就一定“大”,这个疑问词并不是说夜郎与汉朝比大,而是在求知求证和比较层面上对外部世界的大小表示“惊奇”。事实上,“夜郎自大”的命名,是汉民族中心主义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歧视造成的,这种文化压抑和文化解释是由于当时的汉文化中心主义使然。
长期以来,“夜郎自大”在汉族中心话语中成为了贬义词,使得其走向了漫长的“夜郎文化自卑”。今天,在中国文化走向理性和平等对话的时代,在全球化中发出“发现东方”和发出“中国声音”的时代,夜郎文化应走出贬义自卑而走向“夜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表明对自己劣根性的分析,对自己发展可能性的清理,对自己未来可能性和文化交流对话的前景加以展示,最后走向“夜郎文化自强”。
夜郎作为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国度,是“西南夷”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方国或部落联盟。多种族群和不同地域的文化因子经碰撞和互渗,各民族在大杂居环境中逐渐积淀在夜郎文化的各个层面中。夜郎文化与周边几乎同期发端的滇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同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文化史价值和人文价值。长江文明中的河姆渡文化、三星堆金沙遗址文化,以及夜郎文化均不可忽略。夜郎文化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这神秘地出现又神秘地中断的夜郎文化,形成两千年的历史文化之谜。夜郎古国尽管灭亡了,但夜郎文明还在云贵高原某些少数民族身上在传承着。关于夜郎文化的传承者有多种说法,有彝族说、苗族说、布衣族说、还有仡佬族说。 也许可以通过人类学考察,从这个民族身上饰品、婚娶、丧葬方面的种种风俗上看出来。可以说,古夜郎人的住房、发型、服饰、婚俗、葬式、饮食、节日、风俗等等,在贵州的一些民族风情中均不乏其踪迹,可以利用最新科技DNA的遗传工程鉴定,去寻找夜郎文化遗传编码。 在没有更重要的文物发掘出土之前只能通过解读史料,同时进行人类学、民族学的考察研究。 这一研究非常艰难但意义重大。从某种意义来说,研究夜郎文明是对中华文明完美的文化版图和两河流域文化的重要补充,是对汉民族中心主义的扬弃,是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性的尊重。
四 坚持多元文化对话中的“大夜郎”文化景观
作为一个全国皆知的文化品牌,夜郎成为了一些省市县争夺的对象。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只要是能够被尽可能多的人所认可的东西,就被认为具有含金量。“夜郎自大”千百年来成为了尽人所知的文化符码,它具有了名人效应、名地效应、名胜效益等附加值,各地纷纷争抢,很多是从经济帐、文化帐、知名度、含金量几个角度来“争夺命名权”。我认为这种人为的争夺有害无益,应该建立“大夜郎”意识,品牌共享,共同建设。
简言之,应当从文化争论和做秀中走出来,不要争名人秀。我们提倡一种宽泛的泛夜郎文化——“大夜郎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而应是以贵州为中心辐射周边的古夜郎文明区域。夜郎应该寻求当代意义,因为夜郎文化意义的发现可以提供一些供汉民族、供全球思考的问题。这里意味着夜郎故地除了强调工业、旅游业、凉都的特色以外,还要思索一些更深的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才可以逐渐消除附在夜郎上的不实之辞和文化歧视,使夜郎古国文化成为中国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想,今后在经济、文化综合实力上升的时候,夜郎就会在富民兴黔的伟业中再铸辉煌,真正地走向“夜郎自强”。
失落的文明应该找到重新传承的文化血脉。当我们走出“夜郎自大”的误区,摆脱历史迷雾制造的以讹传讹,以西南民族文化源流交融的大视角来看待夜郎文化时,就会发现夜郎国虽然于今天相隔两千年,但夜郎文化的密码却在长江文化精神生活中得以保存下来。
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一项关于建立一个国际鉴别的决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遗产优秀作品》。中国作为人类四大文明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形态,是人类发展历史的见证,其优秀文化应成为新世纪人类的精神瑰宝。在这个意义上,夜郎古国文化的重新发现,将展示西南民族历史变迁和发展,从中发掘、整理、展示包括地名文化遗产在内地“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应该成为世界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不仅应该拿来优秀的文化,而且应该输出优秀的文化。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世界潮流,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以一种全新的眼光与胸怀重新发现东方文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独特魅力,并以此为底蕴,获得与世界先进文明对话的能力,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换言之,中国不仅要建设成为经济大国、强国,而且要建设成为文化大国、强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以鲜明、自信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发现东方和重新阐释包括夜郎文化在内的长江文明,是建设“文化大国”的重要内容。我要说的是:那些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故国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版图的基本单元。而深入探寻多民族的历史人文景观的流变,正是展示中华文明的东方生态文化特征,唤醒集体文化记忆的最切实而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