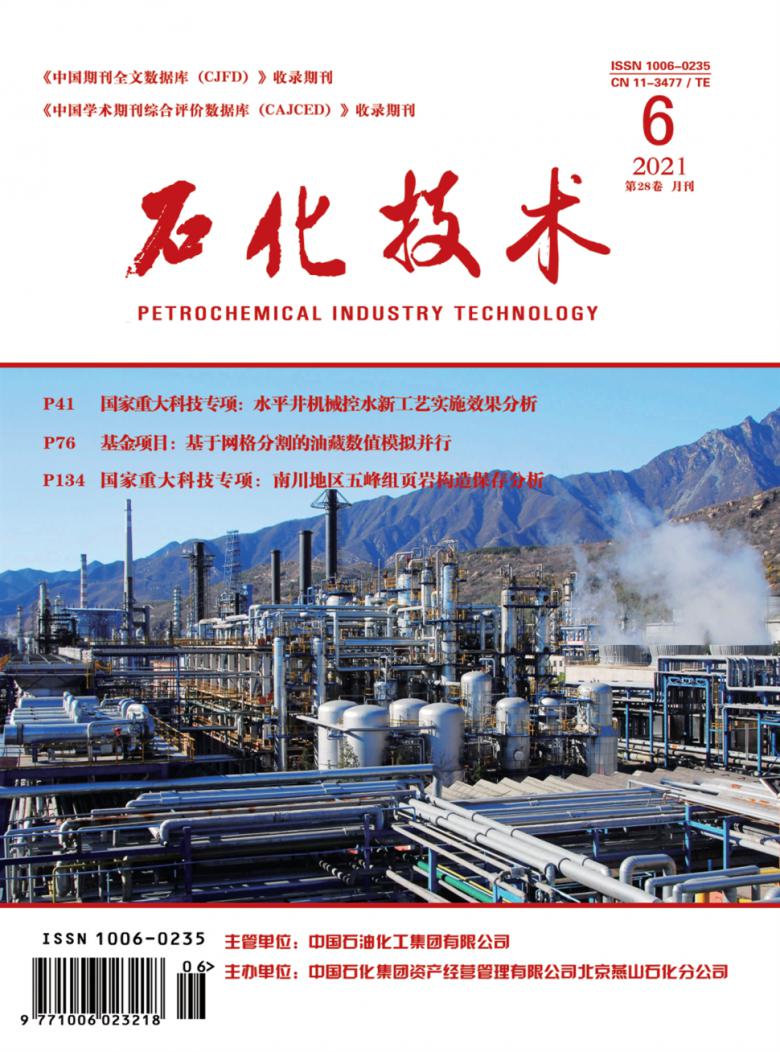从引进到本土化:民国时期的农业科技
曹幸穗 2006-04-23
[摘要] 本文从发展中国家近代科学发展的特点及中国近代农业科学发展的道路、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6)农业科学的体系构建、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农业科学的本土化发展、战乱时期(1938-1949)农业科学活动的变化以及民国时期的农业科学遗产等五个方面概述了民国时期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及其特点。
[关键词]:民国农业史,近代农业科技,科技本土化,农业技术变革
科学技术的本土化,是指发展中国家接受或采纳西方先进技术、并能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和自主创新技术的过程。科学技术后发展国家,起初只能向科技先进国家学习和引进。但是科学技术必须经过本土化改造之后,才能成为植根于本国文化之中的实用技术。对于农业科技而言,本土化改造尤为重要,因为农业生产具有最为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延续性。只有经过本土化改造、与当地农业生产紧密结合的农业科学技术,才能在生产实践中获得应用,成为指导农业生产的理论和提升农业生产水平的新技术。
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本土化通常有两种类型:一是通过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引进来实现本土化,这种情况适用于那些具有独立主权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二是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则常常是随着国家的独立、民族解放之后,才逐渐走向本土化。在中国,由于近代历史的曲折多难,这两种类型的科学技术发展道路都曾同时存在。本文只对民国时期在中国政府主导下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情况做出分析。有关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台湾省、南满州铁路附属地、伪“满州国”以及“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广大沦陷区所开展的农业科学技术活动,将另行撰文。
一、农业科技事业的本土化改造
在清代晚期中国开始启动科学技术近代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启蒙思想家还是政府的达官要员,都主张学习日本的经验和做法。当时在中国成立的农政机构、农业试验场、农林学堂等等,基本上都是日本的翻板。对中国而言,所谓接受近代欧美农学,最初并不是直接向欧美先进国家学习的,而是假道日本而引进的。当晚清政府决定推动“农事改良”时,日本成为中国引进欧美先进农学的“文化中转站”。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中国的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基本走完了从启蒙到体制化的过程。到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时,它给历史留下了如下的新式农学遗产:
农业教育方面,高等农业学堂5所,在校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在校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59所,在校生2272人。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还在安徽省成立了一所私立高等农业学堂,但是没有史料证明这所私立高等农业学堂在革命的当年已经招生。此外还有一所当时的最高农业学府——京师大学堂农科,但是这个农科(1910年改称农科大学)招生很少,1910年只招收了17名新生,1913年的毕业生人数为农学科25人,农艺化学科17人。农业教育的另一方面是农科留学教育。据不完全的史料统计,辛亥革命时,中国的农科留学生人数是:留学日本112人(其中各级农业学堂58人,帝国大学农科54人);留学欧洲各国12人;留学美国51人。
农业科研方面,设有国立的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还有省立的如山东农事试验场,保定直隶农事试验场,江西农事试验场,奉天农事试验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1908年清廷厘定官制时专门设立了一个“劝业道”的机构,归督抚领导,其职责是掌管全省农、工、商、矿、交通等。因此,各省劝业道实际上也兴办过一些农事试验场或类似于试验场一类的机构。到辛亥革命时,全国约有各级农事试验机构40余处。总的说,尽管清末从国外引进的许多农业科技都没有在生产实际中得到应用,但它们的兴风气之先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完成了近代农业科技从启蒙到体制化的历史转变。[1]
晚清政府对农业科技近代化所作努力,只是初创期的“体制化”,是一种未加甄别改造的引进。它们给下一代政府留下了农学遗产,同时也留下了难题:源于西方先进国家、经过日本改造的“西洋农学”能否在中国生根成长,能否在改造中国传统农业中产生作用,取决于对这些脱离中国实际的农学理论与技术进行全面的“再改造”。
(一) 农政机构的本土化改造
1912年元旦,新生的中华民国在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时,其政府部门中设有实业部,该部兼有掌管全国农政的职责。同年中央政府迁往北京,将实业部分为农林、工商二部。次年又将工商部中的商业职能划入农林部,名称也改为农商部。1927年再度将农商部改组成农工部。但是这次改组不足一年北洋政府就倒台了。
北洋政府管辖下的各省地方政府,一般都设有实业厅,县级政府设实业科,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政管理体系。在一些边远小县,人力财力不足,政府机构不健全,其县内的农政职能则委由教育科掌管。总之,从政府建制上看,北洋政府的农政事业还是做到了“事有专司、业有专管”的。经过这么一番从上到下的农政管理体制的“改造”,基本上实现了农政管理体系的本土化,并且融入了中国的官僚文化体制之中,为中国社会所认同和接受。在政府的组织系统中确立近代式的农政体制,是北洋政府农业管理本土化努力的历史成果之一。此后的历届政府,大都承袭了这个农业管理体系。
有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政管理部门之后,北洋政府也开始着手对清政府遗留的农业试验机构进行本土化改造。作为肇始阶段的晚清时期农业试验场,它们多是生搬硬套地移植日本的模式创建起来的。由于脱离中国的农业生产实际,它们在当时没有取得应有的业绩。北洋政府除了对当时的中央农事试验场进行改组扩建之外,还针对中国农业实际情况而新建了一些具有专业性、地域性特点的新机构,例如,在北京天坛、山东长清和湖北武昌分别设立了林业试验场,又在河北正定、江苏南通、湖北武昌、河南彰德等地设立了棉业试验场,在河北张家口、北京西山、安徽凤阳设立了家畜良种试验场。这些农林试验机构都直属中央农商部,名义上都是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在当时的农业试验风气影响之下,不少省份也相继改组、扩建、新建了农业试验场。到1917年,全国共有各类试验场113处。其中最具有本土化特点的是那些与地方农业特点紧密联系的专业性试验场,如棉花试验场、水稻试验场、麦作试验场和茶业试验场等等。它们都是为了解决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而兴办的,是一种实用性的农业试验场所,而不是学理性的研究机关。
(二) 农业教育机构的本土化改造
应当说,民国成立初期,对教育事业是很重视的。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蔡是精通现代教育理论的教育实践家和管理者,他一上任,就提出了许多教育改革的新主张,主持起草了1912-1913年颁布的“大学令”,当时通称“壬子癸丑学制”。这部教育法令,是民国政府对教育事业本土化改革的宣言。在晚清时代,教育体制基本上也是模仿日本的方式,甚至高等学校的教师也大都是从日本延聘。民国甫立,即博采欧、美、日本的近代教育之长,同时参酌我国的实际,对高等教育从组织系统到教育内容进行全面改革。在这部“大学令”中,农科列为大学的七科之一,入学条件规定为中等学堂毕业后须入大学预科3年,然后入本科3年或4年。同时在该大学令中,将清代的中等农校改为甲等农校,定为4年毕业;初等农校改为乙等农校,定为3年毕业。
到1921年,教育部再次颁行“新学制草案”,并于当时呈请大总统公布,称为“壬戍学制。”该学制参照美国的学制,规定教育系列为: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2年,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各3年,大学本科4-6年,大学专科3-4年,其专科4年者视同本科待遇。大学本科和专科均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新学制还规定,取消实业学校系统,改称职业学校,分为高等和初等两级,高等农业职业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入学,初等农业职业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入学。1921年制定的学历教育中的阶段划分和学习年限的规定,一直被延用至今。
1924年,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同时宣布废除1912年的“大学令”和1913年的“大学规程”。这个条例规定,国立大学实行学位制,学生在大学内修学某个学科满4-6年,经考试合格准予毕业者,获得某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可进入大学院,研究有成就者可获得某科硕士或博士学位。同时还规定了大学校长、系科主任的职责,规定了学校须设立董事会、评议会、教授会等组织。这些制度对中国近现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它表明了教育事业的本土化改造越来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
1913年,教育部颁发的《大学规程》,规定农科大学分设四门(相当于四个学部),即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和兽医学。并且规定了每个学门所应开设的科目课程。例如,“农学门”本科在四年中所开设的部颁课程为:地质学、农艺物理学、气象学、植物生理学、动物生理学、法学通论、经济学、农学总论、土壤学、农业土木学、农学机械学、植物病理学、肥料学、作物学、园艺学、畜产学、养蚕学、家畜饲养论、酷农论、农产制造学、昆虫学、害虫学、细菌学、生理化学、农政学、农业经济学、殖民学、植物学实验、动物学实验、农艺化学实验、农学实验、农业经济实习、农场实习、林学通论、兽医学通论、水产学通论等,共36门课程。与清末以日本农科大学课程为基础所规定的课程比较,这时期中国农科大学所开课程增加了9门,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农业教学课程体系。
(三) 农科大学教科书的本土化改造
科技本土化的核心是人才本土化。而本土化的人才必需在本土化的教学环境及本土化的教学内容中培养。但是,当时中国的农业教育存在许多问题。著名农学家沈宗瀚先生[2] 回忆其母校北京农业专科学校1915年前后的教学情况时,这样写道:“外籍教授对中国情况茫无所知,自不待言。即使中国籍的教授,多系日本留学生及京师大学堂农科毕业生,教学中多摘译日本课本为讲义,购用日本动植物标本以代本国实物,农场实习不过播种、除草、施肥、收获等普通简单工作,教授与学生对于中国农业认识甚少,遑论研究改良。”而那时的农科学生“几乎均为城市子弟,对于实地农情,极少明了。”[3] 这种情况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农业学校中非常普遍,它反映了新旧教育思想并存、新旧学制交替的时代特点。针对农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农学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改进的意见。
当时任南京东南大学农科主任的邹秉文教授[4] 提出,农科大学应当承担四项基本职责:一为造就农民领袖及研究专家;二为研究解决农业上的困难问题;三为实行农业推广事业和农村成人农业补习教育;四为提倡襄助改良中国农业及农村生活的组织。[5]
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的董时进教授[6] 更进一步指出:“高等农业教育应当培养出多方面的专门人才,如农业技术人才、农业教育人才、农民领袖人才、农业行政人才、农业经营人才(如县知事)。”为了实现农业教育的目标,他认为必需切实改变农业教育脱离中国农业实际的状况,改变多数教员都由日本、美国教师以及由近期从国外留学归国的留学生担任的状况,改变在教学上生搬硬套地直接翻译外国农业教材的状况,必需提倡农业学校教师开展中国农业理论方面的探讨和农业科学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以期推动中国农业的进步。[7]
在本土化教学科研风气的推动下,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的农业教育家和农业科学家,开始倾力于编写切合中国农业实际的大学教科书。1920年代公开出版的农科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有:邹秉文等《高等植物学》、陈焕镛《植物学》、胡步青《应用植物学》、叶元鼎《农业化学》和《种烟学》、王陵南《高等果树园艺学》、章之汶《植棉学》、朱凤美《植物病理学》、蔡邦华《昆虫学》、周汝沆《作物学》和《稻作学》、侯过《测树学》、曾济宽《造林学》、邓植仪等《土壤学》、温文光《果树园艺学》、赵烈《家蚕生理学》、谢醒农《实用生丝检验学》、顾青虹《养蚕法讲义》和《人工孵化育种学》等。各大学自编自用的教科书,目前已无法汇集了。但从以上所列之出版教材情况看,当时中国农科大学已经在教材本土化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业绩,有的已经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例如,上面提到的邹秉文、钱崇澍、胡步青等编写的《高等植物学》,被认为是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植物学教科书,书中厘定许多植物学名词,如将此前所称之“隐花植物”改为“孢子植物”,“显花植物”改为“种子植物”,“羊齿植物”改为“蕨类植物”等等,都受学术界认同,定为植物学专用名词,沿用至今。此后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前,经各地出版机构发行的由中国教授编写的农科教材种类达到100余种。至此,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针对中国地域情况、适合中国教学需要的大学农科教材体系。[8]
二、作物育种技术的本土化改造及其成果
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各农科大学任职的教员通常都是只教书授课,不从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研究工作。这是因为,中国农业大学初创时,教员很少,教学任务非常繁重。根据政府教育部规定,大学教员每周必须授课24学时,一个教员要能完成额定的教学任务,必须同时开设很多门课程,例如一个专攻动物饲养学的教授,他可能除了自己的专业课程之外,还同时要教作物育种学、植物保护学等。大学教授们已经没有时间精力来从事科学研究了;二是当时学校的经费缺少,无法为教员添置必要的研究设备和试验用品,教师们只好安于教课,维持现状。三是当时的一些专业农事试验机构,既然缺少经费又缺少人才,更无科研学术积累,无法开展切实的农业研究。就连号称国家级的北京农事试验总场,竟委任一位没有受过现代农业科技训练的中国“末代状元”刘春霖为场长,农业研究机构的研究创新能力之低下,就可想而知了。[9]
当时任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主任的过探先教授[10] 撰文提出:“吾国最初之农业教育设施,教者缺乏实地之经验,故不得不空袭东西之旧说,国内又绝少农事之研求,足供教材之选择,故不得不翻译国外之课本;学者亦毫无真实之目的,只求进身之阶梯,故实习则敷衍塞责,谋业则困难倍多,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有来由矣。”中国大量延聘外国农学家来任教讲学,也存在许多问题。正如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唐启宇[11] 所指出:“然而殊方之士,异域之人,对于吾国背景与环境,无深到的认识,若与其谋大纲大策有确切之贡献,是属不智,此为国人应行解决之事,可以自求解决者也。”[12] 1915年前后正在北京农专就读、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农学家的沈宗瀚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吾国)大学设立农科则始于清末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来自各省,聘请日人教授,用日文讲义及日本图表标本讲解学理,对于中国农业问题殊少实地研究。”
创办农业大学和兴建农业试验机构,其目的就是为了改良农业生产,提升农产品质,改善人民生活。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之一就是开展有针对性的、切合农业生产实际的科学研究工作,以其研究成果贡献于社会,推广于农民,使之成为推动农业进步的现实生产力。如果国家供养的农业专家学者,都只知道在课堂上使用外国翻译过来的洋教材教授学生,而对于国家的农业状况、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等等漠不关心,茫无所知,则他不仅没有承担起农业改良的历史重任,而且他所培养的学生也只能“纸上谈兵”,没有改良农业的知识本领。长此以往,则国家的复兴就永无希望。许多怀有报国大志的农学家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农业调查研究,在农业技术本土化历史进程中做出了开创性的业绩。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农村凋零,农业落后,农民困苦。问题千头万绪,作为农学家,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学识专长,推广先进农业科技,提高农业产量和品质,解决亿万人民“穿衣吃饭”的困难。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学家们的科研选题,大致都围绕棉花和粮食作物的良种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配套技术研究而开展起来的。
(一)美国棉花的引进与“风土驯化”
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兴起,对棉花原料的需求急剧增长。而中国原先栽种的棉花品种纤维短,品质差,不能适应近代式机器纺织的需要。于是朝野人士从不同途径多次引进了美国的优良棉种。但是美国棉花不能适应中国的风土气候,导致栽培上出现品种严重退化,品质下降,以至于最初的几次引进均未成功,出现了“良种不良”的情况。于是,如何对引进的美国棉种进行驯化和提纯,成为中国棉业发展的关键问题。1914年,著名实业家张謇出任农商部长,他立即批示在河北正定、上海、武昌、北京等地设立了四个直属农商部的棉业试验场,以试验、驯化、选择美国棉种为主要任务。事隔5年的1919年,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出资成立民间性质的“植棉改良委员会”,并在宝山、南京设立棉业试验场。各产棉大省也成立了专门的棉业研究机构。此外,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和金陵大学的专家教授也参与了棉花选种研究。到30年代初,中国成立了拥有现代科学设备和管理机制的中央农业实验所,以及此后不久成立的中央棉产改进所,为中国棉花育种研究增加了科学力量。经过近20年的科学选育,集中了大批棉业专家,在中国南北各地设置数十处试验种植点,对从美国购进的31个棉花品种进行严格的驯化栽培和选育,先后选育出适合黄河流域种植的“斯字棉4号”和适合长江流域种植的“德字棉531号”作为当时的推广品种。1940年,再次从美国购入一个新棉种“岱字棉”进行驯化试种,经过近5年的选育提纯,育成“岱字15号”良种,比此前推广种植的“斯字棉4号”和“德字棉531号”更为优良,成为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主要种植品种。[13]
在推广种植经过改良、适合中国不同区域栽培的良种棉花之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棉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棉花产量从良种化前的700万担增加到1450万担,产量增加了一倍。而且所产棉花纤维品质大幅提升,适应了机器纺织的质量要求。
(二)水稻良种选育技术本土化改造与应用
水稻是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因此水稻育种也成为近代农学家的研究重点。与棉花的引种驯化、选育推广的方式不同, 近代的水稻育种是将基于生物遗传学原理的育种技术应用到中国原有水稻品种上,使之成为具有高产、优质、适应性强的新品种。中国近代水稻育种家主要采用了三种育种技术,并在育种实践中,结合中国水稻品种的生长特点及栽培习惯对这些源自西方的育种技术作了改进,
原颂周教授被认为是中国近代运用遗传学原理开展水稻育种的首创者之一。他于1919年利用南京高等师范的试验农场,对当地栽培的以及从其它地方征集而来的10个水稻品种进行了品种比较试验和选种改良。这次严格按照水稻育种学的原理和方法所进行的育种试验,整个过程从1919年开始,历经6年,至1924年秋,育成了“改良江宁洋籼”和“改良东莞白”两个品种。经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试种,产量及品质均优于当地原栽品种。自此开始,各地的南方地区的许多大学和农事机构都加入了水稻育种的试验工作。1933年至1936年间,曾由中央农业实验所主持,开展了对2031个水稻品种在全国范围内同时进行品种比较试验,选出良种89个,其中表现最优的“南特号”早熟水稻品种,在当时及此后30年间都是中国南方稻作区推广的重要品种。
近代中国水稻育种方法,主要采用了美国康乃尔大学作物育种家洛夫(H.H.Love)教授所创立的“纯系育种法”,一个新品种的育种周期至少7年,即:第一年“单穗选择”、第二年“单行试验”、第三年“二行试验”、第四年“五行试验”、第五年“十行试验”、第六年“高级试验”、第七年“繁殖推广”。经过中国水稻育种家的多年应用,认为这种原于美国的育种方法,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育种实践,一是育种周期长,育成一个新品种需要7-9年;二是此方法适合美国的水稻栽培的“直播法”,而中国习惯上采用“移栽法”;三是中国水稻成熟期易倒伏,单穗选种有困难。针对这种情况,著名水稻育种家、广州中山大学丁颖教授创造了“小区移栽法”来代替了洛夫的“纯系株行法”。丁颖教授[14] 的办法在育种周期上将洛夫的7-9年缩短为4-5年,而且适应了中国水稻栽培的移栽技术特点。这次育种技术的改良,再次说明了从国外引进的技术,需要经过本土化改造的过程,才能适应中国的农业文化环境。
丁颖教授主持的广州南路稻作试验场,于1927年开展了水稻杂交育种研究。他利用在广州郊区发现的野生稻与当地的农家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经6年选育,育成了包含有野生稻基因的水稻良种“中山一号”。此后,丁颖教授又采用印度野生稻与广东地方品种“银粘”杂交,育成一个特大穗型的品种,单穗稻粒达1300多粒,故取名“千粒穗”。中国育种家在借鉴学习外国杂交育种经验和技术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结合自己实践进行本土化创新。如通过遮光覆盖处理,控制水稻植株光照长度,以便在一年中实现繁种加代,缩短育种周期;应用光照长短解决水稻杂交父母本植株花期相遇问题,提高杂交成功率。这些育种技术的改进,使中国的育种技术在实践中获得了发展。据统计,20世纪上半期,中国各地开展水稻育种的大学和研究所共17家,育成经过鉴定推广的水稻新品种300多个,其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面积推广的品种就有10余个,对中国的粮食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15]
(三)近代面粉工业的兴起与小麦良种选育
与水稻以南方为主产区相对应,小麦是黄(河)淮(河)平原及西北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特别近代使用机器加工的面粉业兴起以后,市场对小麦的需求急剧上升,为了增加小麦产量和提高小麦品质,中国育种家顺应时代需要,运用近代育种技术,自20世纪初期开始,进行大量的小麦育种科学研究。
南京的金陵大学是最早开展小麦育种的机构。该校于1914年南京郊区的麦田中发现一个表现优异的小麦植株,当即摘回,以后连续8年采用“纯系穗行育种法”对其进行提纯和选择,至1922年最终获得了一个符合育种目标的优质小麦良种,取名“金大26”。这是中国近代采用科学育种技术培育成功的第一个小麦良种。受此次成功的鼓舞,金陵大学自1925年起,先后在华北地区各省设立了8处小麦试验场,先后培育出一批小麦良种。其中由沈宗瀚教授主持育成的“金大2905”是当时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新式小麦品种。
南京的另一所著名大学——中央大学也是近代重要的小麦育种机构。1920年该校获得了上海面粉厂商协会的经费资助,大力开展小麦育种试验,育成早熟高产品种“江东门”等一批良种。1930年后,该校又从国内外引进征集了1000余个小麦品种进行品比试验栽培,从中选出了优良品种“中大2419”。该品种原产于意大利的“孟它那”(Mentana),中央大学教授金善宝对它进行12年的驯化选择培育,育成了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栽培的优良小麦品种。新中国成立后,该品种是中国小麦的主要栽培品种。
地处中国陕西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也是近代的小麦育种的重镇。1930年代,该校育成“武功27”小麦良种。特别值得介绍的是,该校教授赵洪璋先生自1942年起,将当地小麦“蚂蚱麦”、及金陵大学育成的“金大2905”、美国小麦“Quality”、意大利小麦“Villa Glori”等四个小麦品种进行复合式杂交选育,至1948年育成一个适合西北地区种植的优良小麦品种“碧蚂一号”,这是新中国在西北地区推广种植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16]
三、农业科技本土化的历程
上述的中国近代棉花品种驯化栽培和稻麦良种选育成果,显示了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也证明了科学技术及其物化成果的“地域和文化”特性。一个国家不可能依靠全盘引进他国的现成技术而实现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其中关键的一个步骤是对引进技术进行适应性的“本土化改造”。日本在引进吸纳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的“本土化”问题,因此有的日本学者提出“技术风土论”,这正是对日本现代化发展的最深刻的历史总结与归纳。
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在分析19世纪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原因时,尖锐地指出:“第一是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18世纪中年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而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17] 蒋先生又说:“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18]
为了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的历史局面,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的近百年间,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代农业科学先驱者的努力与奋斗。
第一代是旧式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他们本身没有西方近代农学的素养,没有接受过西方近代的教育,但他们清楚地感受到了中国农业的落后。“他们只是从不同来源的分散的知识信息中,依稀地感觉到西方农学的先进。因此,他们所介绍的西方农学,是一种表象化的农业技术,或者说是一种被物化了的技术,比如农业机械和作物良种等等。他们还没有揭示农业科技与整体科技文化之间的关系,没有揭示近代农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没有揭示农业科学技术内部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结构。”[19]
第二代是早期学成回国的农科留学生。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农学事业的开创者。他们在农业教育、研究、推广等领域,奠定了近代农学的学术基础。他们几乎都参与了中国的农业教育研究机构的创建直至大学科系课程的开设,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农业科技史上“第一”,如第一个创办了某个专业,第一个开设了某门课程,第一个编写某部教科书,等等。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各项农业科技工作都处于初创阶段,国内的实验式农学体系还未建立,因此这一代人主要是将国外的农学知识介绍引进到中国来,他们主要利用翻译过来的教材培养学生,科研上也多是照搬国外的做法,既少独创,又少切合中国实际。总之,在近代农业史上,第二代农学家承担了承上启下的历史责任。
第三代是国内培养的农学人才为主,加上少数从国外学成回国的农科留学生。这一代人承接了前辈的工作基础,无论在科研上还是人才培养上,都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尤其是他们在推动农业科技的本土化应用方面,在培养了解中国农业国情的专业人才方面,都写下了近代农学事业中辉煌的篇章。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第三代中国农学家在他们的事业认为黄金时期,很不幸地遇到了长达8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和紧接着的3年中国内部的解放战争。他们在战乱的颠簸流离的艰苦环境中依然执着地坚持教书育人,坚持科学研究,把农业科学的“接力棒”亲手送进了新时代。
[1] 曹幸穗:《启蒙和体制化:晚清近代农学的兴起》,《古今农业》,2003,2期。
[2] 沈宗瀚(1895~1980),中国著名农学家。
[]3 沈宗瀚:《中华农业史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页。
[4] 邹秉文(1893—1985),字应松,江苏吴县人,中国杰出的农业教育家和农学家。
[5] 邹秉文:中国农业教育,转引《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第94页。
[6] 董时进(1897—? ),四川垫江县人,中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1951年移居美国。1983年回中国省亲访问。卒年不详。
[7] 周邦任、费 旭:《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10月,第92页。
[8] 周邦任、费 旭:《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42页,附录二。
[9] 周邦任、费 旭:《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10月, 33。
[10] 过探先(1886—1929),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棉花育种的创始人,著名农业教育家。
[11] 唐启宇(1896—1977),中国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史学家。
[12] 唐启宇:《四十年来之中国农业教育》,《农业周报》,1935年第9期。
[13] 曹幸穗等:民国时期的农业,江苏文史资料第51辑,1994年,第114-116页。
[14] 丁颖(1888—1964),广东高州(今茂名市)人,中国水稻育种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
[15] 白鹤文等:《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45-50页
[16] 郭文韬等:《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163页。
[17]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2页。
[18]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3页。
[19] 曹幸穗:《启蒙和体制化:晚清近代农学的兴起》,《古今农业》,2003,2期。
From the Introduce into to the Indigenous: On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1911 to 1949 in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paper were pided five parts as follow: First,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modern sci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road of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science in China; Second,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from 1912 to 1926;Third, the Indigenou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in the period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from 1927 to 1937;Fourth, the chang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ion during the war from 1938 to 1949; Fifth, the heritag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in the period of the Minggu government from 1911 to 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