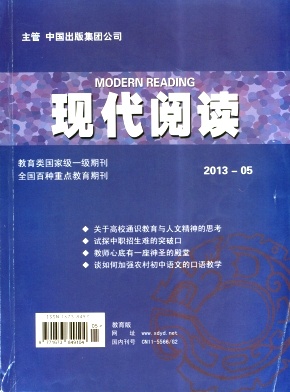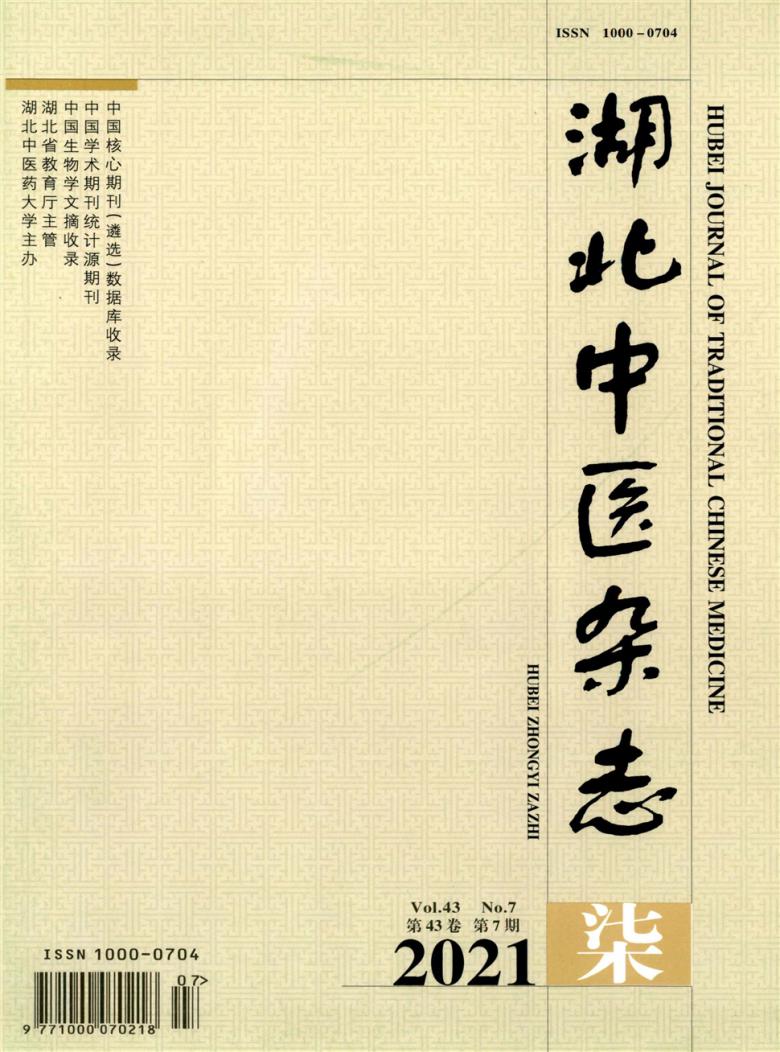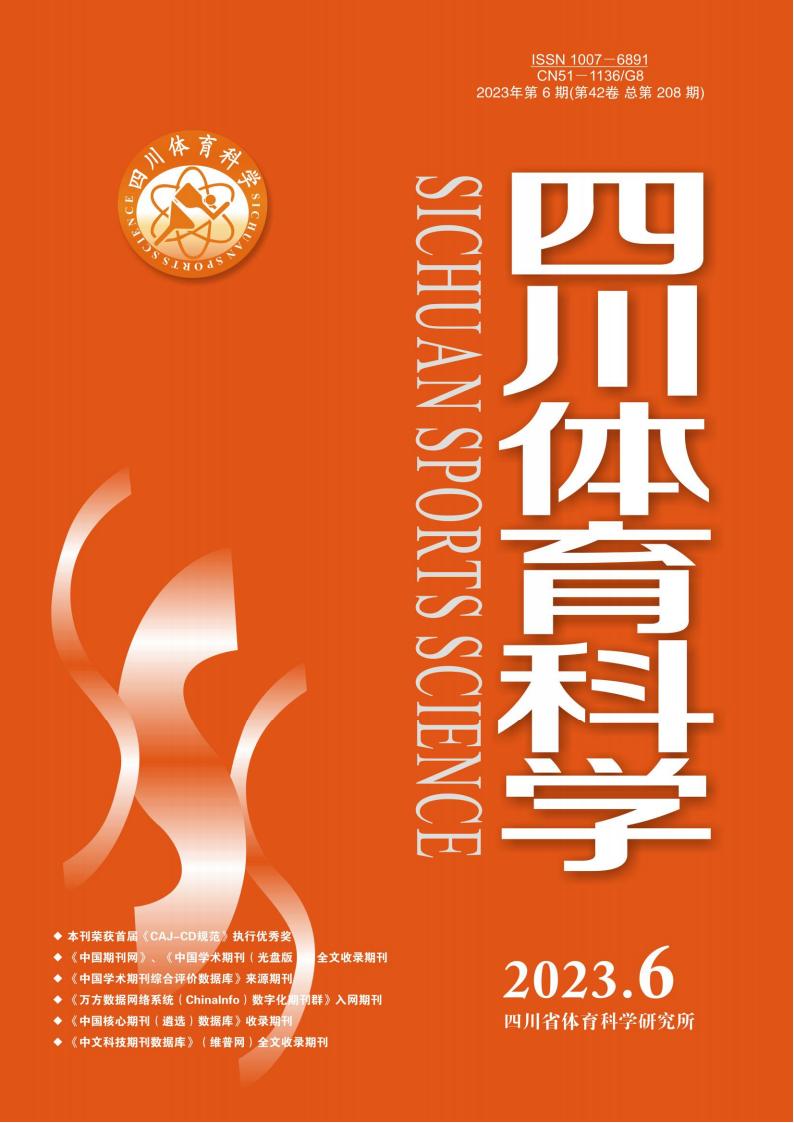全汉昇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何汉威 2006-04-05
编者按:全汉升先生是中国经济史学科最早的开拓者和成绩最为卓著的学者之一,深受海峡两岸学术界的尊敬。全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兹转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何汉威先生的文章,以寄托我们的怀念。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革命运动密不可分。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勃兴,知识分子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力于探析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及经济关系实况,籍以指引革命的进程;学术中最为扣人心弦的现象,当推1927—1937年10年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论战不仅强化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论战中所提出的问题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熟。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内部,特别是经济层面的复杂性,实非简单化的概念所能概括,遂转趋穷研史料,撰写专题式的学术论著,而对于先前社会史论战参与者所专注思索的理论问题,仅略表关切。同时,新史料如军机处档案的发现及系统性整理,更促成学界的研究热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从而开始出现。
全汉昇(1912—2001)是这一学风转变中,研究成果最为辉煌的史学工作者。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就学期间,受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影响,专致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为当时社会经济史主要论坛《食货半月刊》的踊跃撰稿人。1935年他大学甫毕业,即被傅斯年教授选拔,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自此即坚守学术岗位,以经济史研究为终身志业,并为培养经济史人才、而备尽心力。全先生治学60年来,著作弘富;他的学术见解及成就,深受学界同道重视推崇。去年(2001)年11月29日因肺炎病逝于台北,享年90岁。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语所集刊》1,1[1928])一文中提到学问的进步,系于能直接研究材料,扩张研究的材料及应用的工具;从全先生毕生治学的历程所见,他既能充分发扬,而又超越这一学术传统。以下仅就近日展卷重读他的遗著的体会,略陈他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贡献:
1、发掘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全先生初期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唐、宋时期;《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剖析经济重心南移后,连结经济重心南方及军事政治重心北方的大运河,其或暢或碍与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他的另一重大贡献厥为探研唐宋商业发展与杭州、汴梁、扬州和广州四个性质不同城市的都市化,尤着眼于交通运输与国际贸易对城市发展的可能影响。货币经济与物价变动史研究方面,1942年他在《史语所集刊》第十本所发表的长篇论文《中古自然经济》,至今仍是阐述魏晋以迄唐中叶中国货币演变的错综复杂现象的最重要论著。明代中叶以降约400年间,中国币制可说是铜银复本位制。全先生的研究特别着重货币供给,籍以明了币制的发展,曾发表《明季中国与菲律宾贸易》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多篇。中国物价的历史研究因史料缺乏及过去币制与度量衡不统一而不易展开,但全先生仍作出可观的成绩。我们对民国以前约千余年间物价变动有一概略认识,全先生实厥功至伟。他对清代物价史研究用力尤深,透过他从物价、货币及国内外贸易等多方面的深入探讨,我们方能对清代整个经济体系的演变面貌,有一更完整的认识。他另一重大研究课题为中国近代工业建设,或就工业化作广泛考察,或对一些关键企业、地区和问题作深入个案探讨。研究成果中有关汉阳铁厂及汉冶萍公司、江南制造局、甲午战前中国工业化等论著,俱为力作。他数十年来的研究工作,点出许多可以引伸推衍的重要课题,留下足供后学跟进的轨迹;最显著的例子莫如美洲白银与明清经济及清代粮价及米粮市场与贸易,近已成为经济史坛显学,名家辈出。凡此实以全先生的著作为嚆矢。
2、广征博引,扩大史料搜集范围。全先生著作的一大特色是网罗史料,巨細靡遗。1942年他所撰文《宋末通货膨胀及其对物价的影响》于《史语所集刊》第十本发表,东北史及辽、金史名家金毓黻先生读后,在日记中谓该文“颇致研几之功……盖南宋末年史料极其缺乏……全君于宋人文集搜讨至勤,苟有片言只字亦必具录,以成此篇,可谓难矣”[1] 。其实全先生在早期唐宋史研究中,正史、通鉴及诗、文集而外,举凡笔记、政书、类纂,以至敦煌写本及简牍,无不穷加疏理。1949年后,全先生研究重点转移到明清及近代,捜讨之列更扩及中外档案、书信、年谱、碑刻、矿冶资料及地志。1961年,全先生第三度赴美研究,留美两年期间,得阅1903—1909年间在美国克里夫兰出版的55巨册《1493—1898年的菲律宾群岛》这一重要史料;日后他自中、菲、西班牙商贸互动以析论美洲白银与中国丝货贸易,实以此为契机。按,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取代西班牙统治菲律宾,为了参考西班牙人过去330余年间的统治经验,遂由E.H.Blair及J.A.Robertson有系统地搜罗西班牙公私文献,迻译为英文,辑成是书。因中国邻接菲岛,当西班牙人的势力从美洲墨西哥扩伸到西太平洋的菲律宾以后,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故书中有关中、菲、美贸易的史料非常丰富。自西班牙占领菲岛后,输往中国的银货数究竟有多少,中国史籍记载几付阙如;全先生以是书为根据,搜罗详密,遂能推知其大略,填补了中国文献记载的空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研明中叶以还中、日、萄、荷的贸易关系及金银比价诸问题,发为累积效应,取得累累硕果。
3、吸收西方经济史的新观念、新方法和新成果。全先生甫进史语所,即勤习英语[2] ,目的在于扩张研究的工具。他受德国历史学派权威B.Hildebrand的经济史分期学说启发,认为“约由公元二世纪末至八世纪中叶,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较占优势”,撰成《中古自然经济》一文。文中他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说明商业盛衰对货币使用的进步与退化,关系密切。当交换仅在于取得自己所需的消费品,对货币需求量不大时,交易过程是C(自己所余货物)—M(货币)—C(自己所需货物);反之,当交易频繁、专业商人取代以前的消费者从事商贸,货币需求因而大增,交易过程便转变为M(货币[自己资本])—C(货物)—M(货币[含有利润])。汉末以后因战乱的影响,商业衰退萧条,货币使用自亦相应退步。1944年10月蒙傅斯年所长及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所长提拔,全先生获派赴美,先后于哈佛、哥伦比亚及芝加哥三所著名学府进修,从游于Abbott P.Usher,Shepherd B.Clough及John U.Nef等经济史大师,汲取国外经济史学界的新观念及新方法,并与西方经济史家建立联系,奠下日后学术交流的基础。在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时,全先生受Usher及Nef等论著的影响,运用工业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从煤的运输成本出发,说明煤矿资源对工业区位决定关系至巨,籍此追寻中国工业化失败的症结所在。1955年全先生重访哈佛大学后,开始探研明清以还东西经济交流互动,尤着力于美洲白银流入对中国财政与经济生活的影响这一课题。他发现17世纪末至18世纪结束百年间,粮价及物价呈现长期上升趋势,而此实与其时美洲白银大量进口息息相关。这一项研究的代表作《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显受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Earl J.Hamilton于193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布的论著《1501—1650年美洲白银与西班牙的物价革命》所启迪。全先生胪列多种史料,参考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Irying Fisher的货币数量学说(按全先生文中没有列示Fisher的方程式PT=MV),配合细针密线的分析,发现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出,对物价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即使遥远中国亦被波及。必须指出的是,在上述这些研究中,全先生实事求是,不先入为主,削足就履,根据先有的模式选择材料。
4、重视量化及数据。中国史料的数据记录,大多零碎而欠明确;土地买卖劵契、租簿、商号帐册等原始材料,则甚少存留。复因度量衡和币制的不统一等因素所限,即使勉力收集到一些物价材料,仍难以从时间上或地域间加以比较。全先生排除万难,多年来奋力搜求整理,将唐宋期间的物价变动勾划出一个轮廓。无可讳言,诚如剑桥大学唐史专家Denis C.Twitchett教授所说,这段时期史籍记载的物价数据,主要失之于偏高或偏低,若以之编制成物价变动曲线,时有夸大失实之虞。[3]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先生先后与王业键及Richard A.Kraus等合作,主要利用史语所典藏资料,探究清代物价,并对地区粮价差异与经济交流详加考察。他们认为清代粮价陈报制度在经济繁荣及政府施政活力充沛时最为可靠。全先生根据这些数据,旁参其他记载,因数据所限,探讨范围只能及于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时间则集中于18世纪,其中江南及其附近地区的资料尤为丰富,更是他的切入点。为了便于统计,在列表图示前,他和王业键等先生就诸如斗石、米谷折算、米的等级、取代表值及时空等技术问题或事项作出界定规范,使数据可相比较;数据选择方面,凡因灾歉造成急剧波动的米价数据,他们都不予采用,籍以避免这些数据存在的重大不规则变量。盖他们所要解释的,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长期的趋势。全先生着手这项研究时,在掌握到的资料中,部分虽仍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推测,但无论就质或量来说,都是早期研究唐宋物价史时不可比拟的。他的研究显示清代“已有一个自由的米粮市场……清政府虽力图以官运、仓储及籴卖米来影响米价,但明显地从不直接干预市价机能的自由运作”[4] 。他在这一领域的卓越成就,实非他人所能企及。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清代原始档案的开放,资料远比全先生开始研究时丰富,不但扩大了研究的时空范围及考虑因素(如气候循环等),学者相应地也可应用较为严谨的统计学方法处理资料,很多重要历史现象因此得以解释,把清代经济史研究推展至一个新境界。饮水思源,当拜全先生开山之功所赐。
全先生的研究范围,上至魏晋以迄抗战前夕,绵长辽阔,据初步统计,凡专著9种,论文115篇,书评10篇及杂著6篇,专精博通兼顾;无论就研究的质量和深度来说,实同辈经济史家所稀有。论者云日本学人研究中国史,成绩以经济史等三数领域最为显著;较早期国人在经济史方面堪与日本学界相抗衡者,或仅他一人而已。[5]
全先生木讷寡言,自进史语所后,但知遵照傅所长“闭门读书”的指示,养成习惯,孜孜不息,以研撰经济史论著为一生的志业与嗜好,予人冷漠和不通世务的印象。实际上,他不少研究都甚具现实意义。他自言货币供给与物价变动为毕生最感兴趣的课题,实与抗战时对通货膨胀的切身经验与体会分不开。他既于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远离贫困家园,亲身体验美国先进富庶的物质文明,复深受Nef《英国煤矿工业的崛兴》一书启发,遂开始关注中国工业化成绩何以迟缓而乏善足陈这一重要历史课题[6] 。意大利名史家Benedetto Croce“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7] 这句名言,在当时这位30岁出头的青年经济史家的著作中,得到最有力的印证。
全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并非全无异议。如针对中古自然经济,何兹全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史语所集刊》14[1949])一文中便认为此时期南北两个区域情形迥异。北方因战乱迭起,逆退至自然经济状况;南方因大量移民迁入开发,反而逐渐繁荣,货币经济遂居主导地位(按全先生考虑过几位Hildebrand论说批评者,如Henri Pirenne、J.H.Clapham及Norman Angell等的意见,对Hildebrand的意见有所修正。他认为尽管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不能截然划分,但同一时期内只能有一种经济形态占较大比重;南朝的钱币势力虽然雄厚,但无法取代自然经济的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部分西方经济史家即对美洲金银与西班牙物价革命是否相关存疑。他们表示作为历史分析的工具,Fisher货币数量学说方程式的用处极微;早在数量可观的美洲贵金属运抵西班牙前,当地的物价便已迅速上升;解释历史现象方面,货币论不及“实质原因”,如人口增加引起的供求情况改变,来得有说服力。[8] (按,全先生在《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的变动趋势》一文中也提到:“这一世纪内中国的人口大量增加……土地生产大大受到边际收益递减率的影响,粮食供给赶不上需要的增加……于是米价不断上升。其次,同样重要的是白银的大量进口。”)王业键教授也指出18世纪的百年间中国政治安定,国内外贸易空前发达,生产所得大增,当时物价长期上升的趋势,并不单纯是美洲白银大量进口的结果;即使从货币供应方面考虑,也是白银、铜钱、私票三种货币大量扩充所导致[9] 。又全先生认为战前中国工业化不能起飞,资本匮乏为其主因。唯据美国学人Carl Riskin的研究显示,战前中国国民生产中可观的比重耗用于非必要消费上;故问题不在于贫乏,而在于不能将潜在的剩余转导入投资的途径。[10]
今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面貌,已与这门学问天地初开全先生脱颖而出时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他堪称以一己之力为研究带动新风气,开拓新视野,并提升学术水准,极尽筚路篮缕、拓荒发韧之功。回顾20世纪这一领域的长足发展,无处不见他的心血灌注。转眼间,全先生去世快一年了,谨草此文用志悼念。
注释
[1] 金毓黻著:《静晤室日记》(金毓黻文集整理编辑组校点)辽瀋书社1993年,第4938页,民国31年5月14日。
[2] 据全先生同事石璋如先生记载,1935年7月底他抵南京,与那廉君、全汉升、丁声树等同住。“丁、那两先生住在大房子里,全汉升先生不住大房子,因为住大房子,晚上聊天不易入睡,他又在用功背英文字典,所以独居在大房子旁边的小房子。”见《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陈存功、陈仲玉、任育德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114—115页。
[3] Denis G.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2nd ed.,Cambridge Uniuersity Press , 1970,p.298.按本书所指的虽为唐代情形,但同样的批评实可施于宋代的物价资料。
[4] Han-sheng Chuan and Rishard A. Kraus , Mid-Ch’ 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Essay in Price Histor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nd University,1975,pp.6—7。
[5]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4页。
[6] 全汉升:《回首来时路》,《古今论衡》1(1998):82—3。
[7]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原著为意大利文,傅任敢据1921年英译本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页。简言之,这句话是指过去事实“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生活与思想在历史中的不可分割联系得到体现”。参同书第2、4页。
[8] 相关讨论的最佳入门论著为:petr H. Ramsey ed. ,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91,特别是Ramsey所撰导论及收入书内ingrid Hammarstrom 及J.D.Gould所撰写的论文;R.B.Outhwaite , Inflation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London : MacMillan,1999。
[9] 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1,第22—5页。
[10] 据Riskin研究,1933年中国农业和非农业部门运用不足及未运用的潜在剩余,约相当国内净生产额的27.2%。详参Riskin , “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 ,” in Dwight H . Perkins ed. , China’ 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dl Persective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6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