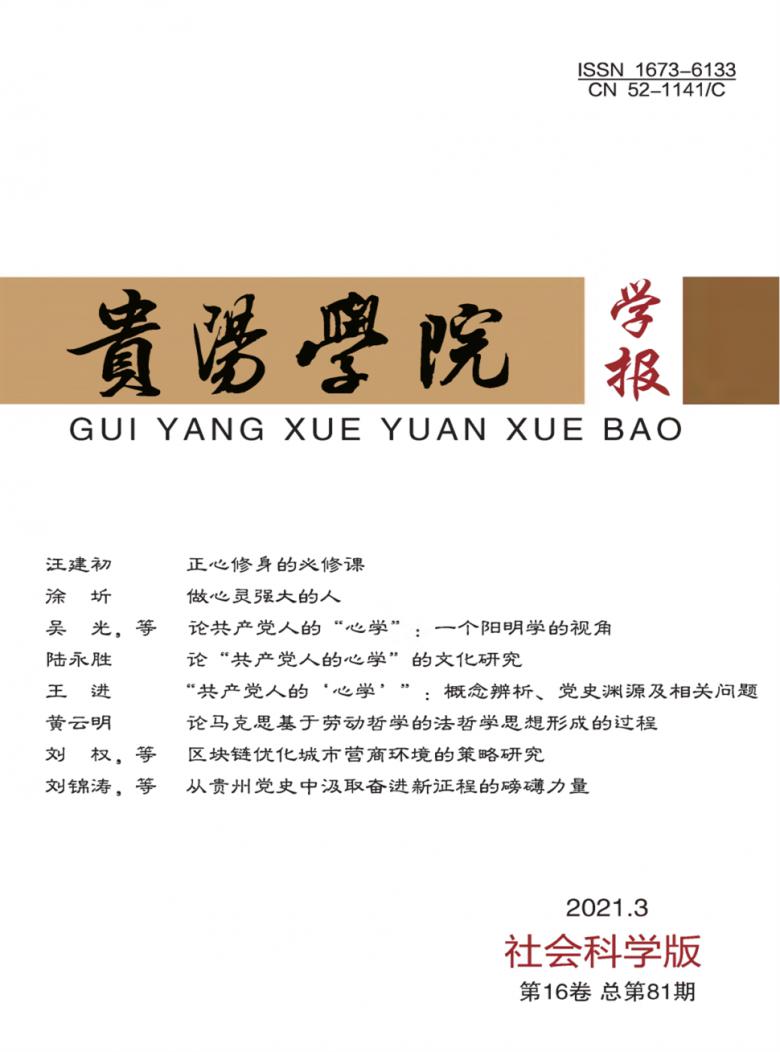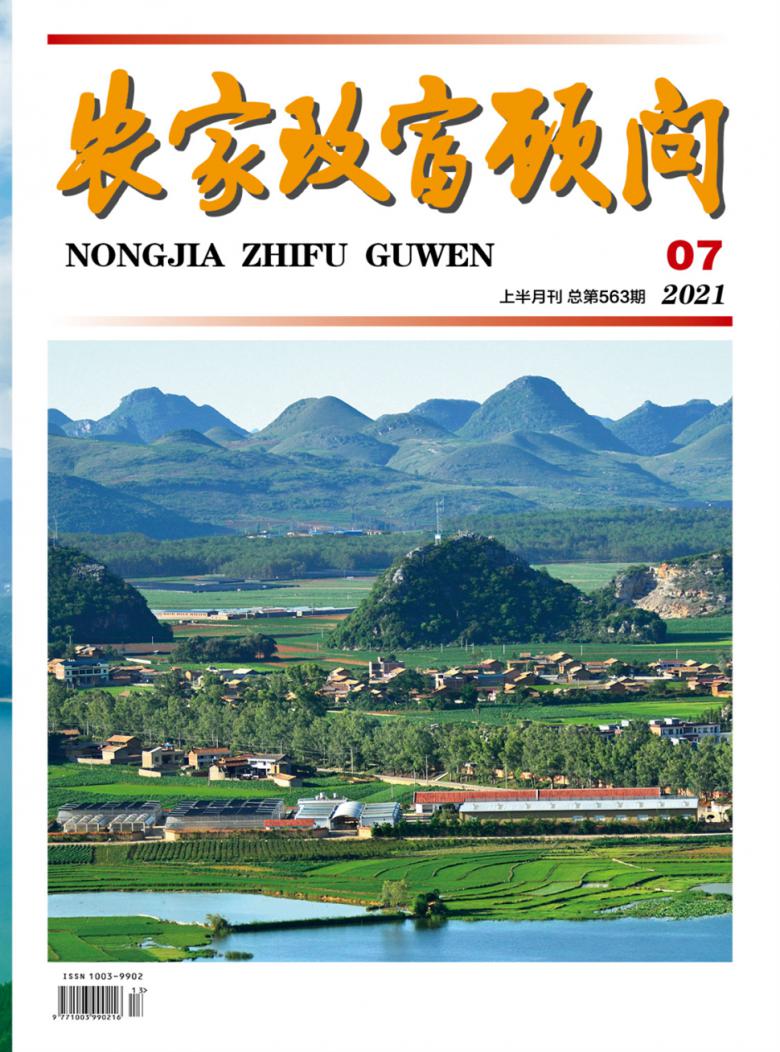当代文化的众声喧哗1.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2.当代中国娱乐文化的三大新变(上)
柯林·坎贝尔 2008-07-23
[摘要]本文为英国社会学家柯林·坎贝尔《浪漫主义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的导论部分。此书从标题到研究思路沿袭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通过对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伴随而来的消费革命的梳理与分析,探寻现代消费主义的起源,试图将文学浪漫主义与现代工业社会的“获取与花费”相联接。通过对文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例证,坎贝尔提出现代社会消费主义的特征不仅源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市场力量,也与获取快感和白日梦的浪漫艺术相关。此书是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经典作品,也是研究消费文化的必读书目。此书在消费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领域影响深远。在导论一节中,作者主要介绍了研究的方法、方法论及其思路形成过程。
[关键词]浪漫/消费(主义)/现代化/马克思·韦伯
牛津英语辞典对浪漫的定义是“标志为、暗示为、赋予为罗曼史的,想象的,远离经验的,幻想的,以及(与文学与艺术方法相关)指高贵或是激情或是不寻常的美”。这些注释与冠以“消费”之名的行为看上去没有关系。① 恰恰相反,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例如我们购买大件物品,如房子和汽车,我们通常将挑选、购买与使用商品和服务全都视为无趣和平淡的日常行为。消费作为经济行为的一种形式,在生活中通常被放在我们所认定的“浪漫”的对立面。这种对立的合理性很容易掩人耳目,然而,一旦我们认识到有一种重要的现代现象将两者直接相联,事情就变得明晰了。
这种现象就是广告,只要粗粗浏览几页时尚杂志,瞅上几眼商业电视,就会发现有多少广告与“浪漫”主题相联,多少影像和拷贝与“远离日常经验的”、“想象的”、暗示为“高贵或是激情”的场景相联。在涉及香水、香烟或是女式内衣的广告中,狭义的浪漫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有些图像与故事中,更典型地使用着异国情调的、想像的、理想化的等广义的浪漫。而广告的实际目的当然是诱使我们购买它们所表现的物品,换句话说,就是消费。② 基本的“浪漫”文化物质通常以这种方式用于广告,这一点经常被注意到,因此,可以说,对“浪漫主义”与“消费”之间联系的共识业已存在。在包括社会科学学者在内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中流行一种设想,即认为正是广告商出于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商的利益,决定了物品的用途,因而,应当认为在这种关系中,“浪漫的”的想法、灵感与态度对“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③ 的利益有用。本书稍后将挑战这种观念(不过没有拒绝),本书主张在将文化的“浪漫”因素(romantic ingredient)视为现代消费主义本身发展的重要部分的同时,也对相反的关系加以详察。其实,消费(consumption)可以决定需求(demand)和需求供给(demand supply),可以认为, 浪漫主义本身在推动工业革命时地位突出,在现代经济特征中拥有一席之地。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主张,因而,我一开始将解释我是如何到达这一立场的。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一些事件导致了本书写作。如同众多的欧洲与北美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学者,我认为那一时期动荡不安、充满挑战,有时甚至振奋人心。大学校园处于代际战争的前沿,在这场战争中,拥有特权和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仿佛将历史的进程偏移到前途未卜的轨道上。没有学者,至少没有社会学家,能经历这一场知识(intellectual)与文化的动乱,而不促使自己反思并重验指导他们专业与个人行为的假想。我的有些同行,经过适当的自我权衡,决定加入年轻的“反文化者”(counter-culturalist), 然而有些人对他们称之为年轻人反常规的疯狂(youthful antinomian madness)④,采取了更加顽固的立场(entrenched position)。我本人,对于给个人带来两难困境的现象更为兴趣盎然;对我不能完全理解的事情,我在宽容(condone)与声讨(condemn)之间难定取舍;我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令人不知所措的文化剧变的研究。尽管一开始,这只是一个个人调查,对于它很快成为具备专业观照的事情,实际上,我后来发现,它对我的专业意味更多。 在后来几年中,我的研究主要采取了阅读文献方式,我不仅阅读“水瓶座时代”⑤ 的先驱们所炮制和青睐的文献,甚至阅读比他们更早一些的卫道士们的作品。我力图通过阅读这两者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世界观。⑥同时,我也考虑到了数量有限,然而日益增长的社会学专论,它们也声称将阐释这一令人不知所措的新现象。⑦ 二战后既有的社会学常识(其实是此前一代)建立的基础是认定现代社会将继续沿着理性、唯物主义和世俗的道路演进。这使得后者格外困难。让人预料不到也无法解释的是,相当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人转向了巫术、神秘事物与海外宗教,明显地偏离理性文化,坚决地反清教徒主义。对此现象的叙述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没有直接挑战长期“理性化”(longterm“rationalization”)的大前提。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理性,是学科创始人以及他们现在的大多数执行者坚持的原则,即使解释对这种假想的挑战,已经是对原则的质疑了。
不久前,我才确信类似的文化革命曾经发生过,反文化者所支持的世界观只有用“浪漫”来修饰才充分。我并不是唯一持这种观念的人,在上一轮“浪漫热”(romantic fever)爆发时已经有支持者与批判者偶尔比较过浪漫运动了。⑧ 不过看起来,我是唯一将这种同一性(identification)当作问题延伸而非问题答案的人。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现象,一向引发强烈的情感,很明显许多评论者能够给反文化戴上如此标签不仅仅是去除它的神秘色彩(demystify),而是解决如何评价它的问题。这种比较值得注意之处在于, 他们试图通过对语境的分析来讨论当代文化变迁(也就是说,可以回指到浪漫的对应物,或是将第一次浪漫运动的信念与态度投射到后继者的观念上),这种被认定的同一性的后果却几乎没有论及。由于我能找到的对浪漫运动的这些“解释”在形式上侧重探究历史,强调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之类的特殊事件,将反文化认定为“浪漫”并不能解释它为何发生。
并不是说,学者们对于浪漫运动、浪漫主义者及其作品缺乏学术兴趣,恰恰相反,这类作品多得惊人。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作品在形式上是文学、美学和哲学的,另外附上些社会政治史或知识分类史(intellectual variety),尽管我发觉很多学者的工作是无法估价的,然而并没有像样的社会学讨论。也就是说,学者们至少将浪漫主义视为社会文化运动,将其在功能上与新兴的工业社会相联系,然而,我却找不到任何对所谓现代生活的“浪漫因素”的检视,将“浪漫”与“理性”相对。如果60年代和70年初的事件仅仅被作为浪漫主义的最新宣言来看待,很明显,它需要被理解为现代文化一个持续的元素。
我发现浪漫思想对于社会学的影响经常被讨论,但是很少有相应的浪漫主义社会学来加以平衡。浪漫思想与启蒙⑨ 运动的观念和态度(至少部分地作为一种反动),是将社会学造就为一门学科的主要知识材料。这门学科的大部分创始人仿佛超越了他们自己的浪漫趋向,采取了进步论的历史观,将浪漫主义视为不同于现代生活中的任一“反动”因素,视为一种植根于过去而为文化和社会的理性因素之手灭绝的现象。正如曼海姆阐述的,这已经被当作一种既定的常识。 当这些想法在我脑海中结晶的那些年,我的精力转向研究新、旧的浪漫主义,与此同时我教授宗教社会学的课程,那是我兴趣所在的主要领域,我的社会学事业也从此起步。很自然地,我开始关注与韦伯作品相关的问题,“清教伦理论”成为我研究的天然焦点。在我教授这一课程期间,我对伦理的命运产生了兴趣,随着时间流逝,这个论题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强。尽管社会学家并未将此作为详细研究的对象,其他领域以及理由充分的大众常识却提出了要求,共同致力创建一种观点,韦伯所确定的伦理,在现代西方工业社会已不再是主流的社会伦理,取而代之的是与之相对的“其他方向的”、“社会的”或是“表现性”的伦理。我一开始并不倾向挑战“清教伦理论”,我只是被这个论题所呈现的众多困境和矛盾所困扰。
首先,那些被当作支持“新教伦理衰落论”(decline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thesis)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仅凭印象和新闻式的特征。更令人困扰的事实在于,正如怀特(White)所说,大部分的作者涉入发展一种“知识意识形态”(intellectual ideology),他们涉及的是对文化变迁方向的悲叹而不是描绘。其次,任何研究必然存在着方法论的困境,尽管它本身在时间上仅仅只是一张“快照”,却被用作评述历史过程,由于缺乏适当的纵向研究,必然导致对过去和现在的假设。似乎这些困境仍不足够,此后许多争论显示极少有讨论是关于新教伦理如何甚至何时在想像中被推翻的。曾经有人宣布关于眼前的和即将到来的新教伦理之“死”一系列声明,奇怪的是,另一天它又活过一次,死去一回。更有甚者,伦理是如何被斩尽杀绝,到底是社会经济还是文化该对“谋杀”伦理承担更多责任,存在相当的观点差异。此外,从16世纪初新教伦理首次被阐明到20世纪它被宣布推翻存在令人困惑的历史脱节问题。难道它真的在四百年间始终丝毫也未受到挑战?由于这些原因,我开始越来越怀疑既定的观点,开始倾向于觉得无论什么力量致力于挑战新教伦理,它们不可能仅是存在于现在,而是回溯到20世纪以前的系谱。历史纪录中的鸿沟,使我感觉到需要更新韦伯的分析,也就是说,我认为需要继续他关于西方宗教传统发展以及它与社会、经济生活关系精致详实的讨论,跨过《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表现的时间线,这条时间线某些社会学家认为在1920年前后,而我认为早至1620,最好在1720年。
大约正在这时,我的两大兴趣首次会师,本书的观点在我头脑中开始构思。对我而言,如果文化反清教力量可能本质上是“浪漫的”,它们也与消费相关;如果在60年代,消费与浪漫主义相关;那么它们可能一直如此?可能,存在一种“浪漫伦理”致力于促进“消费主义精神”,正如同韦伯曾经假定“清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当然,正是“浪漫文化运动”时常被作为清教主义的“天然敌人”。
这种观点足够促使我以一种新的视角观察浪漫主义,同时着手查找消费以及消费者行为的材料。不久后,我读到麦克·肯德尼克(McKendrick)、布鲁尔(Brewer)、普拉姆(Plumb)的书,我所读到的内容激励我深化这一论题。我将在第二章讨论此书。
此书作者们继续使用“消费革命”一词,用以指代他们所评注的明显与浪漫运动同时的变迁。我此时不仅认为,既然有必要在细节上检验两者的联系,本书的标题也自然地浮现在脑海。除了将它称为“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精神”,我还能起别的什么名字呢?
此时,我的论题证据积累希望十足,不幸的是,我碰到了最麻烦的障碍。那就是,仿佛并没有理想的现代消费主义理论。
韦伯的论题建立在一个假想之上:工业革命构成了人造产品生产体系最重大的剧变,这种剧变史无前例,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相关。在他的时代这不是韦伯一个人的假想,大部分社会理论家持有这种假想,它也是可观的研究与讨论课题。论争主要rage它的原因,而不是它的形式,然而对于生产性资本主义构成却存在共识。对于消费却不是这样。如果如今看起来是这样,经济史学家开始持有观点,工业革命也见证了消费的重大革命,至于“现代”消费的本质是什么没有确切的理论。
这主要是因为消费行为的对象完全被经济学家独占,他们典型的研究是通过非历史的假想框架,认为消费行为对于任何人任何时间都是基本相同的。我很自然地求助于那些将注意力转向消费的社会学家们,主要是凡勃伦(Veblen Thorstein,也译维布伦,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和桑巴特,然而我发现很少有人真正从事这个问题关键之处。我只能独自面对令人畏缩的重任,力图创建一套现代消费主义理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个课题上韦伯仅用了十多页(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我却用了四章来讨论。首先,创建现代消费行为理论是必需的;其次,经典的经济学和凡勃伦都没有提供一套合适的理论;第三,享乐主义的社会行为理论完全不同于当前经济学的实用主义为基础的视角;第四,现代享乐行为理论确实可以说明现代消费行为的独特之处。
由于我并不急切地斗胆涉足其他学科,我并未毫不迟疑地着手这一野心勃勃的行为。我对肯德尼克、布鲁尔与普拉姆对18世纪消费革命的叙述的检视,使我确信,他们在阐释上的无力是直接源于缺乏准确的理论,这并不只是代表在经济学部分的失败,而是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家的罪过。而且,从他们提供的材料以及我关于60年代和第一次浪漫运动的研究可以清楚发现,诸如时装、浪漫爱情、品味与小说阅读等现象被社会科学家们所忽略。这些现象深深地暗示着消费革命与现代消费行为。
这些课题为人忽略,这一事实在我看来是一个重大的遗憾,尽管有些现象,比如时装与浪漫爱情,对社会学家缺乏吸引力是因为有影响的理论视角来suggest它们的重要性,它们在现代社会的无处不在已经足以不言而喻了。社会学家们的忽略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源自偏见,源自假想先于调查的潮流,认同这些现象在某种方式上是微不足道的,是不值得认真研究的。有一种观点部分地是从生产论(productionist)经济学偏见派生出来而弥漫到整个社会科学界,这种观点与潜在的禁欲清教主义态度相关。这些课题未被适当地研究应当归因于这种偏见的因与果。毋庸置疑,如果社会科学家们许久以前就将注意力转向对这些现象的认真思索,现在偏见也不会在各个学科中流行。在凡勃伦的作品中,纵容教化消费实践的趋势非常明显。他的后继者也是一样,里兹曼(David Riesman,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则将此鼓吹为一项美德。即使意见相左的两位当代大师赫伯特·马尔库斯(Herbert Marcuse)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也成为相同的趋势的例子,倾向批评与谴责而不是调查和解释。
然而,此时另一个同样令人困惑的问题浮现出来。如果,按我所想像的,浪漫主义有利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格兰现代消费行为的出现,有利于“消费伦理”的合法有效,那么从新教主义派生,又与“生产伦理”相悖,如何能够在同时同地运作?是否真的存在两种社会伦理,它们在形式上相对,却又并肩相存,一个支持生产,一个支持消费?如果是这样,是否有两个社会群体(group)分别担当文化载体?韦伯的论题明显与生产伦理和新兴资产阶级相联,那么有可能消费伦理与贵族相联?然而事实证明需求的新潮流来自新富(nouveaux riches)。可以得出结论, 资产阶级同时拥有清教伦理与消费伦理,这一观点与我认定浪漫运动主要与中产阶级特征有关相吻合,不过这带来新的社会学迷惑。
我逐渐开始感到消费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历史问题:如果没有解决潜在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关于现代消费主义核心的变迁机制,就无法成功地解释消费革命来源。这一变迁机制无论如何转变,都暗示着文化过程。因而,正如同韦伯从事他关于生产革命来源的原创研究时关注历史、经济与社会学问题,我开始关注到这些密切相关的问题。
正是在此时,我认识到我正在写作的论文对于现代工业社会及其文化的出现的传统既定观点是怎样一个激进的修正,远超于我原先的想像。首先,在工业革命名义下的巨变应当被视为集中于消费的革命,正如集中于生产的革命。很大程度上,这一点是由经济史家提供的证据清楚显示的,他们仿佛是渐渐改变主意形成这个观点。如果,他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那么在他们觉醒后会紧跟有一系列其他结论。例如,“消费伦理”必须一开始就存在于工业社会,而不是后来出现的,这当然暗示着新教伦理与无论哪一种被伦理合法化的消费很大程度上是同时的现象。这引发以下的想法,可能清教与浪漫互为文化替换物(cultural alternatives),正如社会学家通常视为的那样,这种想法不仅挑战了流行的“文化矛盾”(cultural contraction)论,也质疑了被广泛接受的假想:“理性化”是资本主义与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所有这些推论仿佛都拒绝广泛流传的错误,将工业革命仅仅当作以生产为手段构成的激进转变。这当然,由于韦伯采取了狭隘的观点,将清教主义的理性与美学特征挑出作为至关紧要的影响:如果,他错在明显忽视了相伴的消费革命,基督教传统的其他因素可能会对现代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吗?这些都是我开始着手此书时脑海中浮现过的想法,我转向韦伯的原文以便启迪与指导我的任务。
马克思·韦伯作为学者和社会学的“创始人”在社会学家中享有盛誉,社会学家们更多的是书写他以及他的作品,而不是仿效他。也就是说,有一个巨大的韦伯产业,而没有人对他开创的文化社会学付诸努力。有可能沿着他的足迹这一任务本身明显令人畏惧,除此之外,很难说清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在韦伯那个时代,由于他那渊博的学识没有学者可以成功地仿效他,自从世纪之交以来学术界日渐学科专业化,他那种范围广、多学科的风格实际上更不可能被任何人效仿。这并不意味无法尝试,正如韦伯本人描述的,对现代社会的社会文化变迁的洞见可能只能通过不同领域的探寻才能获得,诸如宗教与经济,通常被认为是没有联系的,这种洞见因而也可能只是刻意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即使其他学科的学者会对这些不当行为侧目以视,社会学家并不是太过羞怯去越界。部分的答案在于,许多高度赞赏韦伯的社会学家在研究文化时,实际上选择跟随马克思,所关注的不是韦伯成功运用的独特类目,而是关注“意识形态”的概念。
反讽的是,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正是对韦伯作品及其所蕴含的世界观的尊敬,他所赞成的理性世界观(rationalistic Weltanschauung)想像出了他终生致力研究的现象的实际消失。尽管韦伯的兴趣广泛,包括机制例如科层制,劳动分工,法律与国家这些仍是现代社会的重要部分,然而他主要的兴趣还在于宗教,如果不是这一现象确实消失,他对于去魅(disenchantment)和理性化整体过程的强调就失去了影响力。对于现代社会诞生的主要特征,他的观点看上去,宗教的助产士功能是不容置疑的,接着它在世界舞台不再有任何重要作用。To the extent, 社会学家接受了韦伯式(weberian)的观点(当然不仅仅限于韦伯的观点),他们可能原谅了假定从事他所擅长的特定形式文化分析没有什么意义(point),因为韦伯采用的很多概念,比如神正论、禁欲主义与预言看起来仅仅适用于信仰与价值的“宗教”体系。
稍作反思,就能暴露这种假想的错误,然而,正如韦伯使用和发展了术语,与宗教的必然联系并不多于超凡魅力(charisma),是在韦伯所有的术语中最明显突破了概念窠臼的。当然,韦伯的分析风格对当代文化现象看起来并不比他曾研究过的宗教的历史形式更有用。这也是本书潜在的假想。
但是那些以宗教作为特定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通常对他们的研究对象会采取奇怪的含混态度,在研究现代时具有涂尔干的特色,在回顾过去时却是韦伯式的。也就是说,他们自作聪明,在寻求当代行为与机制时,采取涂尔干式对“宗教”功能和本质的洞见,当作富于洞察力的时尚;而研究过去时,他们紧随韦伯,采取传统的被视为“宗教现象”的观点。韦伯雄心勃勃的计划是研究世界宗教及其截止于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发展。
然而由于韦伯没有将他对神学体系演变的研究继续到18世纪,在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一个尴尬的时代阴影。这段时间将封建和前现代社会与当代社会分开,那时可以想见所有重要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运动可能以“宗教”的形式被宣告,并伴以被认可的神学。在当代社会中则是相反的假想大行其道。在中间这段时间——在1650至1850的关键时期,韦伯的“新教伦理论”已经谈得十分清楚。不幸的是,太容易忘记韦伯的论题是针对特定问题而阐发,即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会首先在西欧出现,因而,不能对直到现代的西欧宗教思想发展尝试做一完整而全面的叙述。
本书表明,对伟大人物表示敬意最好的方式不是仅仅赞扬他,而是仿效他,本书既是对学者的赞颂,也是对他名作的完善。本书不是作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姊妹篇,也不是对它的注释,或许它同时含有这两种风格。本书主要观点事实上目的是对韦伯完善,效果上是他观点的镜像,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本姊妹篇。韦伯关注新教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联系的主张并没有被否认,但是拓展了宗教理性禁欲(raional ascetic)与感伤虔诚派(sentimental Pietistic)两方面对于现代经济发展的贡献。为了实现更具雄心的整体叙述,本书对韦伯的观点作了些改进,特别是关于他对待新教主义的方式和对待新教主义“伦理”的合理构成的方式,以及对待它命运的方式。对韦伯的修正并不是对他主张的毁灭,恰恰相反,这些修正是为了解决接受他的论题所带来的长期存在的问题。 本书依照韦伯的榜样,第一部分勾勒出“消费精神”,接下来第二部分讨论“新教(浪漫)伦理”,这一步骤由于需要以一定篇幅讨论现代消费主义的本质而变得复杂。最后,它的精神具体到自给(automonous)自我想像(self-illusory)的享乐主义,这样便可以转向勾勒出推动它产生的文化伦理。
在对待方式上的不同是韦伯自己作品的直接后果。因为,他认为新教说教影响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有益的伦理发展,当他专注于勾画出那些新教说教时,必须从那些self-same的说教中清理其他伦理的来源。用于证明消费合法的伦理规范(ethical code)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描绘为一个从韦伯描述的“新教伦理”区分出来的过程。尽管有这些差异,本书潜在的结构尽力与韦伯相对应,强调“文化伦理”在引入经济行为的“现代”模式时的中心地位。展示它们的一致(congruence)与它们的心理与文化联系。
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观点史的运用,却像韦伯的作品,推行某种意味的取向(approach),这并不只是赞成思想(mind)与精神(spirit)是历史发展最终力量的一面之词,而是承认,当观念运动构成受人重视的人们的“活的信念”(living faith)或是(formulated aspirations)之时,观念运动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依照韦伯的榜样,由既定信仰而产生的行为的真正本质被视为有问题的(problematic),它本身也是研究所关注的中心。因而,本书最主要的关注在于追踪社会风俗(manner),正是在社会风俗中,社会真、善、美观念的变迁影响行为模式(patterns of conduct),不是任何直接约定俗成的时尚(prescriptive fashion),而是观点为确认特质的行为(characterconfirming conduct)给出了方向。虽然本书并不追随物质力量对于观念构成与接纳的影响的观点,但也不忽视这一观点。
诸如声名赫赫的阿瑟·洛夫乔伊⑩ 与观念史更为相近,他关注的是默许假想和预设形式的观念与“思想”及外在的信仰体系。洛夫乔伊称之为人们的“无意识的精神习惯”(unconscious mental habits)可以清楚而意味深长地理解为他们的伦理行为(ethical conduct)与公然的信条(professed creeds),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文学批评的材料被认为特别有价值。与此同时,从术语的完整意义上如同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而非文化史,存在一个忽视大众(popular)与民间(folk)信仰的趋势,以便集中更高雅(higer)文化, 如果不是仅仅集中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对此的论证(justification)有赖于更大的影响,后者建立在总体思潮,特别是伦理理想的阐述(formulatin of ethical ideasls)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此后的篇幅中,几乎没有涉及工人阶级。 与此同时,本书的调查分享了观念史的跨学科特性,充分利用了洛夫乔伊认为用来建造“分离学科围墙”的“大门”。它有一种纹理不规则特征,不仅是源自从通常的学科语境之外检验课题,也源自使课题与拒绝它们的意义达成一致。伤感主义(sentimentalism)被视为重要的社会伦理(socioethical)运动,而不是仅仅影响了浪漫主义的不走运的文学潮流;类似地,时尚被视为显示了现代中心价值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美学现象,而不仅仅是精巧宣传的销售诡计。本书涉及了一定数量对现代社会诞生传统说法的言外之意的阅读,不仅挑战了历史和社会科学中生产论偏见,也挑战了现代文化发展具有不断增长的理性化特点的假想。
当然,任何人承认这种“完善”韦伯的主张,都会引发对将两个论题整合的整体更深的思考。如果承认,平行的文化进程与现代生产相联而产生,又与现代消费相联而产生,那么等式两边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如果生产论偏见影响了韦伯关于工业革命的观点需要修正,那么它应当被消费论取代吗?还是存在对现代经济的产生有完整的“平衡”的论述,从而避开这个问题的两者取一?这个问题饶有兴趣,有待于其他后继的作品来思考。
注释: ① 牛津英文词典1969年版,“浪漫”词条(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969,s.v.“romantic”)。 ② 不是所有的广告都使用“浪漫”版本,当然不是所有的消费具有“现代”特征。 ③ 可以在皮斯关于现代广告的产生中找到此类观点。参见奥梯斯·皮斯:《美国广告的责任:私人控制与公众影响,1920—1940》(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merican Advertising: Private Control and Public Influence, 1920—1940, New York: Arno Press 1976, pp.40—41)。 ④ 这一类反应的例子可以在大卫·马丁(David Martin)的《无政府与文化:当代大学问题》(Anarchy and Culture: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Universit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9)中找到。 ⑤ “the Age of Aquarius”,水瓶座时代,占星学名词,可能由于BEATLES的同名歌曲(1962)而风靡一时,指1960年。当时有一批人根据占星学分析而表示,水瓶座时代即将降临,在这个时代中,人类的精神层次将会提升,爱与和平将降临大地。从而兴起了所谓“新时代运动”,也称水瓶时代运动,是一群西方的知识分子,对于过去过于重视科技与物质,而忽略心灵与环保的一种反动。 ⑥ 我见到格外有用的汇编包括约瑟夫·伯克(Joseph Berke)编辑的《反文化》(Counter Culture, London: Peter Owen, 1969);杰里·霍普金斯(Jerry Hopkins)编辑的《嬉皮档案:地下报刊笔记》(The Hippy Papers : 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 Press. New York: Signet Books,1968);彼得·斯坦西尔(Peter Stansill)与大卫·扎恩·麦罗(David Zane Mairowitz)《BAMN:反判宣言与昙花一现1965—70》(BAMN: Outlaw Manifestos and Ephemera 1965—70.Harmondsworth, Middx: Penguin Books,1971)。 ⑦ 主要的文本为肯尼斯·维斯修斯(Kenneth Westhues)编辑的《社会的阴影:反文化社会学研究》(Society's Shadow: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ountercultures. Toronto: McGraw-Hill Ryerson,1971),与弗兰克·穆斯格鲁夫(Frank Musgrove)《痴迷与神圣:反文化与开放社会》(Ecstasy and Holiness: Counter Culture and the Open Society. London: Methuen, 1974 )。 ⑧ 这种对比可以在布克(Booker)的作品中找到,他评述了20世纪60 年代和第一次浪漫主义之间氛围上“封闭的平行”(Close parallel)。 ⑨ 关于浪漫主义在现代思想的发展中所起作用可见H. Stuart Hughes《意识与社会》(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79)。 ⑩ Arthru Lovejoy,1873—1962,美国哲学家。以对观念史和知识论的研究而著名,主要著作为《存在的巨大链条:观念史研究》(1936),《观念史论文集》(1948),《反对二元论》。他的晚期作品《对人性的思考》(1961)、《理性、悟性与时代》(1961)都和浪漫主义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