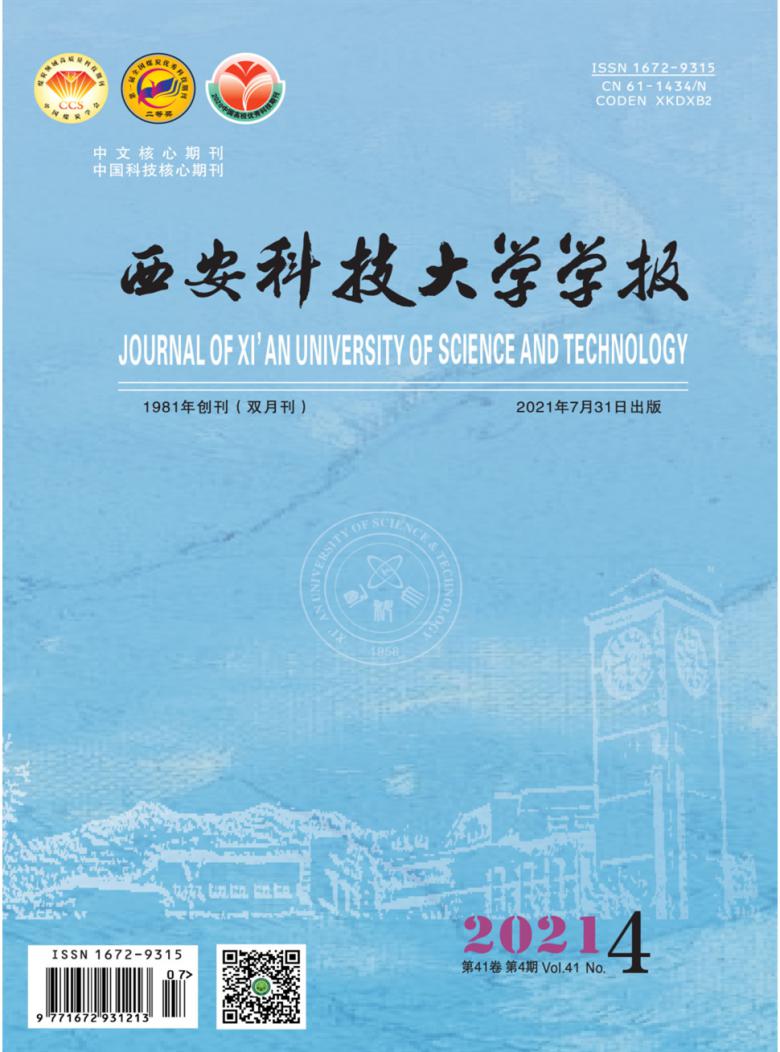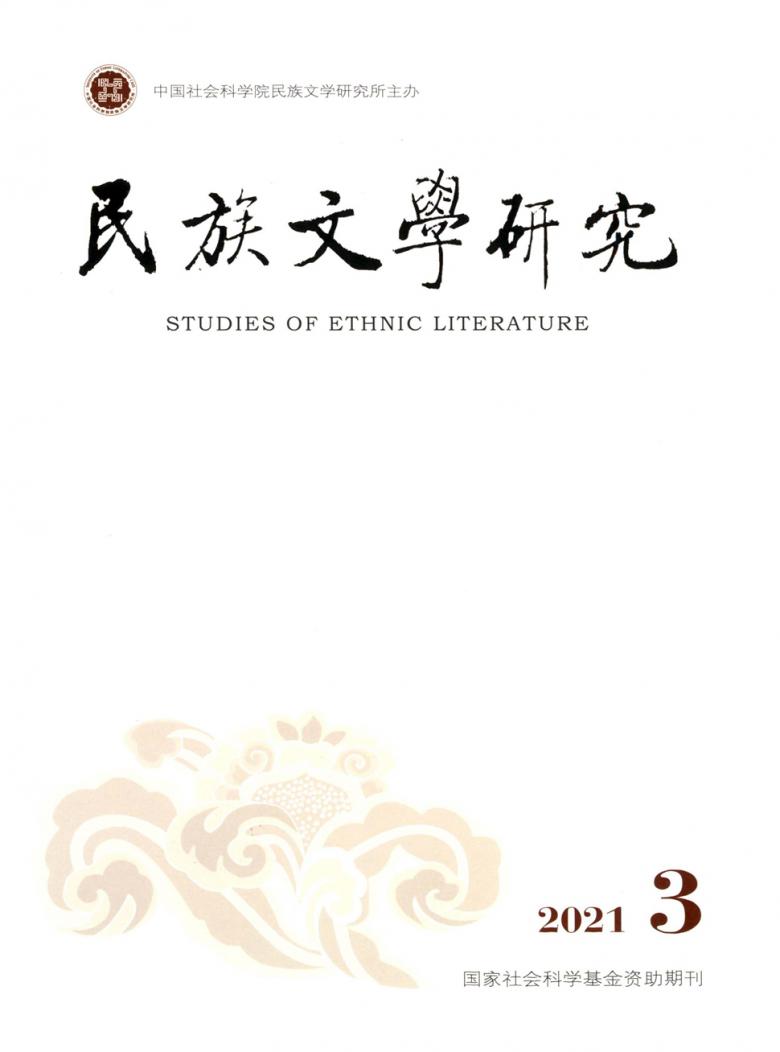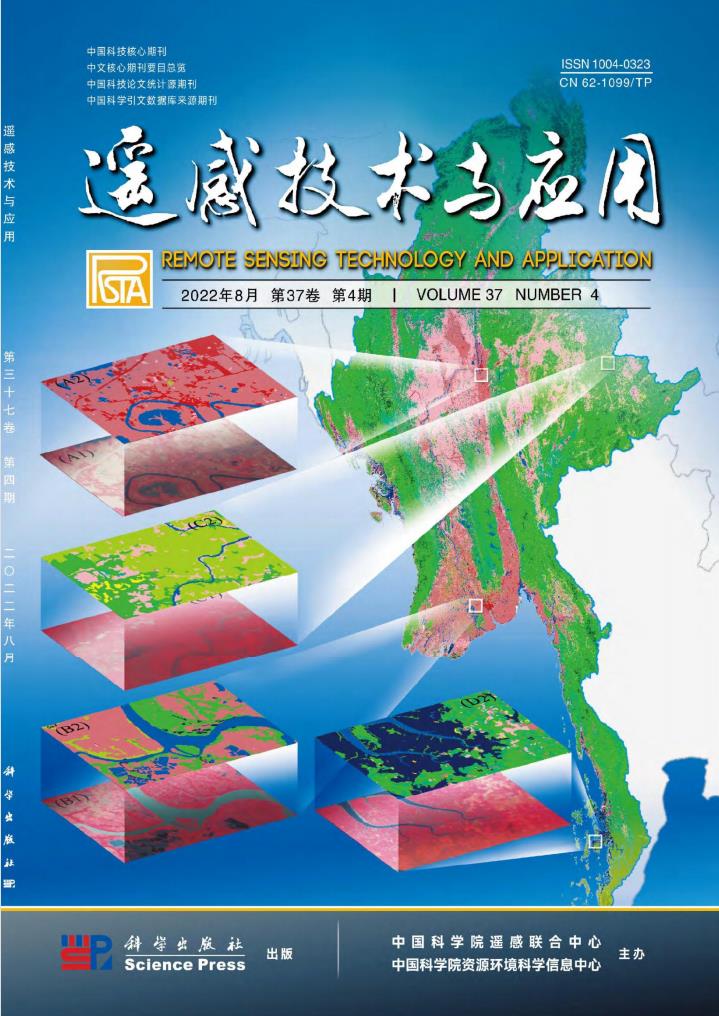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业规制的启示
佚名
摘要:合理适度的金融规制对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规制的好坏直接关联一国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危机的形成。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它发源于市场经济和现代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因此,对于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意义更为深远。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化的推进,这些问题也极有可能在中国发生。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规制;衍生品风险;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52-03 引言 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全球金融震荡,并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经济学家在高度关注危机蔓延与趋势的同时,也开始从制度因素上关注危机产生的原因。有人提出对美国近年来金融规制的变革与放松的思考[1]。有学者从金融反垄断的角度思考次贷原因,认为次贷危机使现代金融制度面临重大变革压力,使金融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格外重要[2]。不少学者均指出,次贷危机将带来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新审定与变革,正如1929年的金融大危机导致美国金融强规制体系构建一样。 二、规制缺陷下放大的金融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是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subprimemortgage loan),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 美国次贷市场总规模约为8 500亿~1 300亿美元,在美国14.3万亿美元抵押贷款市场规模的占比约为5.9%~9%;然而却酿成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进而向全球实体经济蔓延的大危机。截至2008年8月底,全球金融机构由于次贷危机而核销的坏账已经接近5 000亿美元。里昂证券日前的投资报告指出,全球的信贷相关损失会增至1.5万亿美元。日本《每日新闻》10月11日报道,包括美、日、欧和新兴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损失在内,今年全球金融资产损失高达27万亿美元。危机过程发展之快,影响之大出乎许多经济学家、更不用说普通人的预料。不足10%的不良资产何以酿成如此大的风险? 次贷危机爆发后,关于危机的根源,许多文献均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3]。从众多的原因分析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根源在于房地产抵押贷款规制放松后的衍生品风险被资产证券化数倍放大。风险形成与传递的内在机理则众说纷纭。 美国的按揭贷款市场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优质贷款市场(Prime Market);第二层次是“Alt-A”贷款市场;第三层次是次级贷款市场(Sub-prime Market)。美国房贷危机从次贷开始,现在已经扩散到Alt-A抵押贷款和商业地产抵押贷款,涉及的资产规模约为2万亿美元。 风险传递机理的简要概述,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竞争和金融创新的推动下,美国房贷机构与商业银行合作,为实现贷款资产现金流的提前释放,将次级房贷资产通过金融创新打包为住房按揭抵押债券(MBS),投资银行买回MBS后根据不同的期限、风险、收益率等特征,对基础资产的现金流加以剥离与重组,设计成不同档级的新债券(CDO),在CDO的基础上,进一步设计出信用违约掉期(CDS)和次级债券价格综合指数(ABX)等衍生工具,为持有质量很低的CDO的投资者提供风险对冲工具。这样,通过金融创新工程设计,创造了一个以房地产信贷为核心的金融衍生品链条。再经由各种评级机构对这些金融产品进行分类评级,便使这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得以在全球金融市场上销售。 在这一系列的次贷衍生产品运作过程中,美国整个规制监管出现了风险覆盖空白的缺陷。首先,次债基础资产的发放中,次贷源头的金融机构为更多的发放贷款,突破了自律界限,有意放松了对贷款人基本贷款资质和条件的审查。金融业的过度竞争和“两房”的回购机制,还促使一些贷款机构与开发商共谋,对资质不良的部分房贷者实行低首付甚至是“零首付”,为次贷风险的形成留下了隐患,这其中既存在担保过度的问题,信用增强的手段也过于单一,主要是依靠“两房”背后的隐性国家担保;其次,金融衍生品创新的次贷转为次债的过程中,次贷衍生品经过复杂的模型设计后一系列的重新捆绑,产品的内在成分与价值不再清晰,原始的借贷关系不断模糊,责任约束也变得越来越松散,大多数人都难以了解这种金融衍生品的真实含义,而金融规制与监管对于这种跨行业和领域的产品基本没有发挥任何效用;第三,作为金融市场上公平公正透明原则执行机制的各种具备极强垄断性质的权威信用评级机构,在次债产品衍生过程的各环节信用评级中则出现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些次级的贷款被评为A级。海外投资者对权威评级机构的信任,使贷款者的违约风险通过资产的证券化被广泛地分散到了证券市场的各个投资者身上。 在金融监管体系繁复,规制严格的美国,何以也会出现这一系列的违规操作事件,究其原因,与1990年后,美国政府放松了金融规制直接关联。 三、美国金融规制的变动与风险覆盖缝隙 尽管关于银行业是否需要规制和如何规制,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在经济实践中,由于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具有金融信贷产品本质上的风险特性和金融风险的传导效应,进而危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安全。 规制(Regulation)指的是国家以经济管理的名义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政府公开宣布这种行动是为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4]。 政府对某些行业进行规制的理由由多方面组成,按照斯蒂芬·布雷耶尔和保罗·W.麦卡沃伊的归纳包括:(1)卖方垄断权力的存在;(2)评估外在不经济的成本;(3)补偿不充分的信息;(4)其他根据。而管制的方法包括:1)制定服务费率的成本;2)根据历史上的最高价格水平制定最高限价;3)发放许可证;4)制定标准[4]。 美国金融市场的运作和监管机制一直被视为全球的典范,被形容为利于金融创新和富有韧性的金融体系。美国的金融监管与规制,伴随着经济的变化,经历了自由放任—强化规制—金融创新加强监管—放松规制的多次转折。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美国逐步构建了以《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为基础严格的金融规制框架。20世纪80年代,从里根政府开始推动放松金融管制,认为市场本身会纠正失衡问题,先后通过了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混业经营、鼓励信贷等一系列法案。1999年,美国正式用《格雷姆—里奇—布利雷法案》取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许多商业银行加入到金融衍生品业务,投资银行迅速发展。 美国的金融规制框架典型特征是“双重多头”架构。美国联邦金融监管的立法权在国会。相关监管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据国家立法制定部门监管规章,构成《美国的联邦监管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CFR)》。法典共分50个部分,对应不同的联邦监管内容。联邦政府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权力,注册地是界定银行监管部门的主要依据,监管职责由多个部门负责。联邦政府设有八个主要的监管机构:美国货币监理署(OCC)、美国联邦储备体系(FED)、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储蓄机构监管署(OTS)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NCUA);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FC)、保险业联邦保险署(SIC)。各州政府还设有金融监管部门对在各州注册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美国大多数金融机构均由不止一家监管机构负责监管。 客观上看,这套体系庞大繁复的监管体制为美国金融业的稳定繁荣提供的坚实根基,大危机后的70多年,美国金融业虽然也经历了几次风险,但基本尚能消化和控制住风险的蔓延。然而,随着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的推进,原有的规制架构弊端不断显现。 此次次贷风险迅速放大的载体是金融衍生工具,衍生工具作为金融创新的主要内容其效用在经济学界一直引起争议,一方面,它被看成金融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金融风险的始作俑者。截至2007年底,全球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工具(OTC)与场内交易工具名义本金之和已经超过67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规模的12倍。在市场投机增大,不确定性更加明显的情况下,金融监管规制显得日益重要同时也更加困难起来。正如萨缪尔森所言:“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 在金融创新下衍生品工具不断推出、各市场品种边界日益模糊的情况下,美国双重多头监管的协调与风险覆盖之间的缝隙日益加大。立法滞后于金融发展,监管机构之间的交叉、重复监管、监管标准的不一致、FED、OCC、SEC等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分歧、监管过度与监管空白等问题使得监管缝隙不断加大,有效的金融监管规制不足,风险难以全方位覆盖,一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则处于完全没有监管的状态。 另一方面,美国的监管成本则居高不下,根据美国金融业研究报告的分析,2006年,美国金融服务的监管成本高达52.5亿美元,大约是英国FSA6.25亿美元的9倍。据估算,美国监管成本占被监管的银行非利息成本的10%~12%。 四、危机后的美国金融规制演变趋势 美国目前对于规制监管的措施还主要集中在应付危机的短期性措施上,基于应对“安然事件”而匆忙出台的《萨班斯法案》的教训,美国下一步金融规制监管的变革将十分谨慎,但可以肯定,拯救这场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规制必然面临新一轮的革新。 事实上,从2007年起,从促进金融竞争角度,美国金融业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报告,从不同角度对美国监管体系的改革提出了建议: (1)2007年1月,美国参议院查尔斯·斯库莫(Sen. Charles Schumer)和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联合发表的报告提出:建立“共享的监管原则”、推行“安全审查改革”和制定“更为现代化的金融服务法规”等;(2)2007年3月,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的报告提出:“美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受到了限制,美国目前的监管框架是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已经不适应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需要,美国政府应当考虑更加面向金融市场和参与者的监管改革”;(3)2007年11月,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Financial Services Roundtable)发表了《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的报告,指出美国的监管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4)2007年11月,美国证券行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IFMA)对美金融监管体系发表了评论报告,主张重整美国的金融监管架构,包括合并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规避多头监管模式下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问题;(5)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长亨瑞·保尔森提出要改革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和《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方面提出了监管框架变革和最优监管架构的建立;(6)2008年5月,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演讲中提出:“监管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来应对金融创新”;(7)2008年7月,美联储消费者和社区事务司司长桑德拉·布思庭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监管与调查分会上作证时,也表明了规制信贷歧视并加强公平信贷执法的必要性。 这其中美国财政部的提案最引人注目也争议最大。这一提案提出在长期目标上向目的为导向的监管方式(objectives-based regulatory approach)转变。在机制架构上提议设立由美联储担当的负责市场稳定的监管当局(Market Stability Regulator);肩负目前OCC和OTS责任的负责与政府担保有关的安全稳健的审慎金融监管当局(Prudential Financial Regulator);负责商业行为的监管当局(Business Conduct Regulator);以及联邦保险保证公司和公司财务监管当局。在规制框架下,提议废除联邦储蓄章程,将其纳入国民银行章程;合并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期货和证券行业提供统一的监管和监督;提出对于州注册银行进行适当的联邦监管等。 上述一系列改革提案中,尚未能构成美国下一步金融规制变革的权威内容。财政部的提案从长期看是从混业规制角度整合美国监管机构,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以开放的姿态进行监管框架的构建。从改革的趋势看,美国目前的双重架构仍会继续存在,多头监管模式预计会进行较大的调整,法律规制会强化,尤其是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和引导金融交易的去杠杆化方面,在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金融交易的透明度方面的规制将被强化。 五、结论及对中国金融规制的启示 从美国次贷与金融规制变动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得出,金融规制与金融风险覆盖的缝隙是构成有效监管不足从而酿造风险的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一般认为,各发达国家的经济改革是市场体制的竞争,是不同经济模式之间的较量[5]。整个国际金融制度发展就是一个制度构建调整的过程,一个“无规制(non-regulation—规制”(Regulation)—“放松规制”(Deregulation)—“再规制”(Re-regulation)的演变进程。 此次的次贷危机不仅给美国,同时也给各国金融规制体系敲响了警钟。在金融市场和产品复杂性不断增加的环境下,如何构建一个适应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风险状况的有效金融规制体系,是各国都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规制之间,迫切需要寻求一种有效的模式。 次贷危机对于正在向市场化转型的中国金融业而言具有很好的反思和警醒效应。随着中国金融规制的变动、利率放开和金融创新的推进,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中的违规行为极有可能也会在中国金融业出现,中国的金融业应如何借鉴美国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实现合理有效的规制和监管,是迫切需要探讨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一行三会”的监管框架历时五年,从规制监管效应看,已逐步显现出与上述美国监管体制极为相似的现象,竞争在加剧,然而协调则日益欠缺,规制与监管缝隙不断增大。2006年以来,中国金融综合经营的步伐越走越快,并已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在金融业发展不断向国际化和混营突破的趋势下,经营的边界日益模糊,规制与监管的漏洞和空白则日益放大,整合目前条块分割的金融监管模式,以避免出现监管制约和缝隙,下一步的规制监管模式变革是不可避免的。 从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看,目前这种分权式的多机构监管模式并非最佳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的弹性变通意识将会使金融规制与监管的缝隙不断加大,因此,鉴于中国的国情,需要约束性的监管规制制度。在规制监管理念上,应采取从分业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在模式选择上,应考虑统一的集权式监管机构,可采取合并一行三会为统一的金融规制局,根据金融市场和工具分类设置具体的监管部门,同时还应针对金融创新与金融融合的趋势,设置交叉监管部门,这样既能保障规制的统一和有效,同时也能实现监管机构之间信息的统一和共享;并尽快逐步构建较完善的规制法规与条例,实行统一约束;在制度构建上,还要逐步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动态地适应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并尽快健全金融同业自律机制,强化市场自身的约束机制。然而这次危机的警示并不意味着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步伐要受到制约,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应该是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根据中国的国情寻求有效的规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