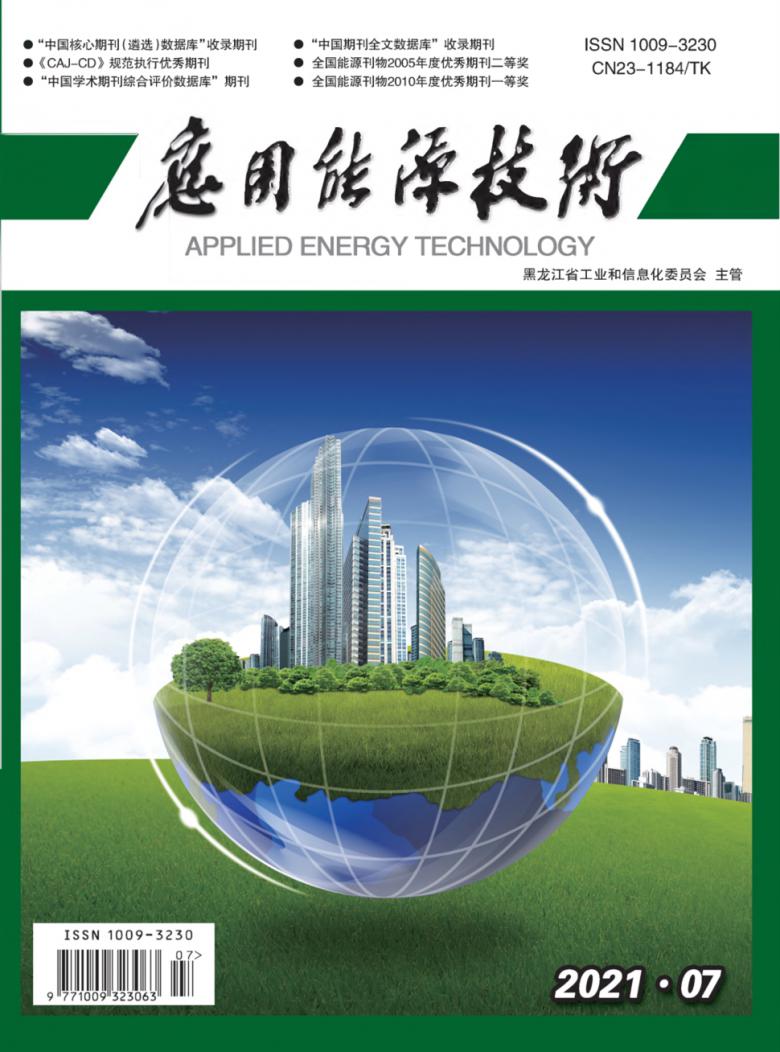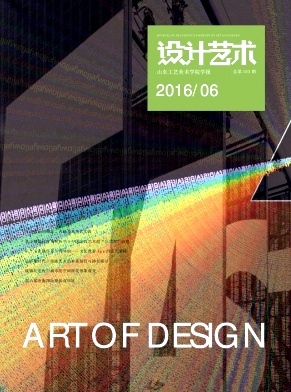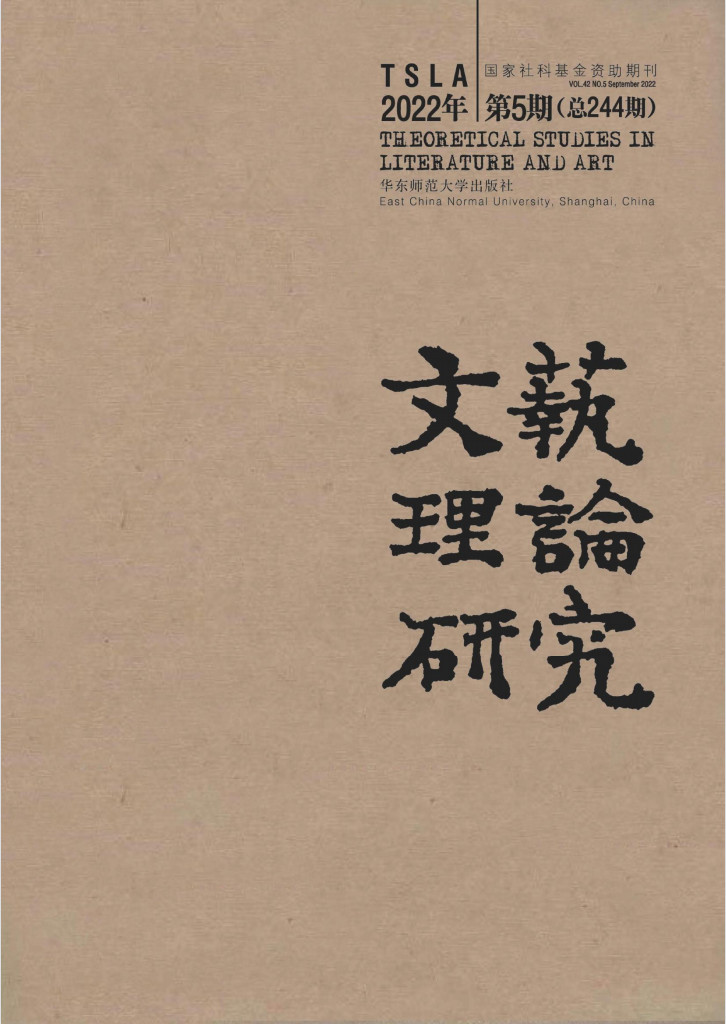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
傅兆君 2006-04-13
【正文】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大变革时代。领主制经济的衰落是造成当时城乡对立运动特点与经济制度变迁的时代背景。深入探讨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发展的特点和制度方面的创新,对于科学地解答春秋战国社会性质和古史分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春秋战国时代“工商食官”制的瓦解
商品经济是共产主义以前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现象,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均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均有不同利益的社会成员以及社会分工。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商品经济本身不构成某种社会经济形态形成的标志,至多不过是某种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环节而已。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才发展到渗透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中的地步。因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只是与自然经济相伴生的经济形态,是农、工、商诸产业分工结构的一部分,不能将商品经济当作分析社会性质的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
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1页。)
春秋战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较前有了显著提高,领主制经济呈衰落状态,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引起这种变化的起点,此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领主制经济的解体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诚如吕振羽先生所言:“由于封建庄园经济的衰退和地主经济的代起,农村中便出现了大量相对过剩的人口;加之,适应于庄园经济的衰退而来的领主们对农民的扩大剥削等原因,又扩大了农民人口的逃亡。这种形势,由于商业资本与高利贷所直接或间接不断地渗入农村的作用,便愈益加剧了。”(注: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40页。)因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页。)。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突破旧的宗法性、身份性的领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促进土地制度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在土地可被转让、抢夺之后,它作为商品形式可供买卖,也是自然而然地迟早要发生的事,非身份性领主贵族的商人也有权拥有土地,新兴地主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产生和壮大的。小农的自由土地所有制,“这种私有制的真正自由,没有土地买卖的自由是行不通的”(注:《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1页。)。地主制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形态等上层建筑也必将随之而变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权是政治与经济的结合,地主实行“超经济的强制”来榨取农民的地租,这种“新的剥削方式”是与其土地所有权的性质相统一的,土地赋予了人格,并没有像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所有权那样拥有纯粹经济的形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依附性,换言之,无论封建领主制经济还是封建地主制经济,本质上都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体系,商品经济都是从属性的,并不占支配地位,甚至“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7页。)。农村的经济关系侵蚀城市,封建土地所有制性质也浸透到了工商业中去。况且,城市中有大量农田及园艺田。城市中农耕人口占相当大的比重,农业及其土地所有关系对工商经济的渗透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严格的“工商食官”制度,就是与周代领主制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性质相吻合的一种工商业经济管理制度。“工商食官”制不仅表明“食官”的生活来源,更是表明阶级身份。它不仅是职业的原始色彩的或分封制等级制下的社会分工,更是指官府垄断工商业的地位(注:关于“工商食官”制,朱家桢在《河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著文指出:“工商食官”只表明生活来源,不表明阶级身份。它是封建领主经济体系下的一种官办手工业和政府管理商品市场的一种模式。邵鸿在《南开学报》1991年第6期著文《“工商食官”新解》,认为这里的“官”非指官府,而是职事。这些观点颇有新意,但值得商榷。)。
在春秋战国时代,井田制度走向瓦解,没落领主的土地所有权受到了新兴地主的排挤,一时便出现了土地所有状况相当混乱的局面。新旧生产关系交替之际的一系列矛盾便激发起来,与土地所有制的变化相适应,农、工、商业也都在矛盾中向前发展着,这主要表现在官营形态的农、工、商业与私人农、工、商业之间的矛盾。
私营工、商业的兴起,正是钻了“工商食官”制的空子,挖了“工商食官”制的墙脚。独立的手工业者、商人阶层出现了,城市经济相对繁荣了。过去它们只是以满足领主的需要为主要目的。其中,商贾的地位显比工匠身份为高,大多是领主的臣仆,不具有独立人格。同时,在领主制封建政权垄断性“工商食官”制下的工匠、商贾皆是执行官府差役的人,工商食官使实行关税制度成为无利可图。同时官商身份也有免税的特权。后来,商贾职业与封建领主的关系日渐疏远,行商坐贾也不一定是领主的臣仆、门客,在这种私营商业发展之后,领主只要在领地上设关卡收税就同样可获得远比商贾要多得多的利润,“关市之讥而不征”(注:《管子·五辅》;又见《孟子》。)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工商食官”的陈规旧制也日益松弛下来,这一商业经营活动正为一种先由地方领主后由国家拥有的统一管理商业市场的政府职能所代替。
私营工商业的兴起,这是对西周以来工商业发展的一个新突破。但与此同时,作为“工商食官”遗制的“处工就官府”(注:《管子·小匡》。),官营手工业仍然存在,并且还会有发展的趋势,其工业基础规模和技术实力毕竟是雄厚的;官营商业和官商也是存在的。所有这些新变化,正与土地制度由公有制向私有制的历史发展相合拍,封建领主制经济的阵地日益被新兴商人地主经济所蚕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掌握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实在是正确理解“工商食官”制兴衰的关键。
无独有偶,中世纪西欧领主制封建社会走向瓦解过程中同样地经历过类似的历史进程。比利时经济学家亨利·皮雷纳在《中世纪的城市》一书中写道:
从十一世纪末起,世俗的和教会的领主们到处建立“新城”。这是称谓在处女地上建立起来的村庄,村庄的居民以缴纳年金的办法得到一块块的土地。这些新城市的数目在十二世纪时一直增加,它们也是“自由城市”。因为领主为着吸引耕作的人,答应对他们免除那些压在农奴身上的负担。一般来说,领主只保留对他们的审判权;对他们废除尚存在于领地组织的中的老的权利。……于是一种新型的农民出现了,完全不同于旧式的农民。后者以农奴身份为其特征;而前者享有自由。这种自由也是仿效城市的自由,产生这种自由的原因是农村组织受到城市的影响而出现的经济动荡。(注:〔比〕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3页。)
当然,农奴的解放并不是领主们的慈悲和施舍,而是数百年的封建社会经济规律客观运行的结果,特别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所以,他接着又说:
土地制度改变的同时,人的身份也改变了,因为两者都是一种正在消失的经济状态的产物。长期以来领地竭尽全力自给自足的所有必需品,现在商业都可以供应。再没有必要每个领地都生产自己用的一切物品,只要到附近城市去就可以买到。……在一个为商业和城市经济所改变了的时代,旧的领地制度必然消失。商品流通变得越来越快,必然有利于农业生产,打破在此以前束缚着它的桎梏,把它吸引向城市,使它现代化,同时使它获得解放。商品流通使人摆脱长期奴役它的土地。(注:〔比〕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4页。)
商人及商品经济的历史作用是如此巨大,乃至将“旧的领地制度”推向埋葬的境地,从而代之以新式的生产关系,这是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经济史的真实写照,虽然古代中国的国情与中世纪晚期西欧各国的国情是有差异的,不曾有西欧那样由逃亡农奴建立起来的市民城市,也不曾出现西欧那样城市与乡村的强烈对立,但是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领地制瓦解而出现的商人强烈地影响历史进程的情形却毫无二致,史载:
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注:《管子·禁藏篇》。)
商人于国,非用(庸)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取而利之,市廛之所及,二依其本。(注:《管子·侈靡篇》。)
上有天子诸侯之尊,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注:《韩非子·解老篇》。)(猗顿以盐业起家,而邯郸郭纵以冶铁治富。)
国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注:《史记·苏秦列传》。)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注:《史记·货殖列传》。)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注:《墨子·贵义篇》。)
由此可见,社会分工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冲击领主制封建社会秩序的强大力量,而手工业者和商人则是活的社会生产力。发生在春秋时代的“野与市争民”(注:《管子·权修篇》。)的现象,就是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和转移。这种人口结构上的变化,如同中世纪欧洲农奴逃离领主庄园的情况一样,都是对旧的封建经济秩序的冲击,都是对自然经济体系的否定。恩格斯说:
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要素。……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9页。)
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对于我们正确估价春秋战国时代商人及商品经济的进步历史作用,无疑是恰如其分的。“工商食官”制瓦解了,商人地主来到了这个为反动领主阶级所统治的世界,他们的事业便同为推翻这个旧世界的人民解放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二、都城形制的变迁与具有综合性功能的城市形态的形成
人类社会的进化,就其物质形态来说,主要表现在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上。其中,赖以广泛展开社会关系的聚落形态乃是人类社会物质属性的重要特征。人类聚落形态长期演变的结果,便是产生了乡村和有着特殊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的城市这两大类型。“城市本身的单纯存在与仅仅是众多的独立家庭不同。在这里,整体并不是由它的各个部分组成,它是一种独立的有机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0页。)换言之,城市自它形成的时候起,就具备与村落迥然不同的社会意义,其中城市所体现的社会分工的深化、生活方式的特色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都是乡村聚落形态无法比拟的,都表现出城市作为“一种独立的有机体”的社会复杂性。城市作为有别于乡村生活方式的本质属性表明,没有体现社会分工的私人工商业经济及其非农业人口的存在,就不能说有城市的诞生。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前尚不存在城市,只能说是城市的发生时期,即城堡一都城的历史时期。
春秋以前,“城”、“邑”、“都”、“都邑”与“市”还是分别独立的范畴,况且该时期的都、城、邑往往是没有城墙的,有的仅是宫城有墙,宫殿、宗庙、住宅、手工业作坊遗址皆很零散地分布着,尚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有机体”存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都城遗址、河南郑州的商城遗址,湖北黄陂的商代盘龙城,河南安阳殷墟以及先周宗周的岐邑、丰镐皆是这类典型的例子。在陕西岐邑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官府宫殿、宗庙、屋舍遗址有岐山的凤雏、扶风的召陈、强家、庄白等地;周族人的住宅则广泛地分布在岐山的礼村、扶风的齐家多处地点;手工业作坊遗址也零散地分布在扶风的云塘、白家、齐家、汪家、召陈等村周围。这些彼此独立的遗址散布在东西3—4公里、南北4—5公里的范围内(注: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1975年第10期;《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反映出城内的社会经济生活是非常松散的。各遗址之间的大片空地说明农业在早期城市中的主导地位,居住点的松散分布也反映出城乡刚刚分化的时代特征。像这种先周的城邑,按张光直的话来说,“对整个三代时期的其他城邑也应同样适用”。它的建造,“不但是建筑的行为,也是政治的行为”。城邑的宫殿大小、城墙高低、规模上的等级制度完全表现着宗法性政治权力。(注:详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0—117页。)。
似乎城邑的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相比远在其次,这不能不说是春秋以前城邑的重要特点。
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考察,我们发现,明显地呈现出春秋与战国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春秋时代的城市,从规模上看,可分为周王城、诸侯国都、大夫采邑和子男之城四个等级,抑或也有王都、大都、中都、小都之别。按周代礼制:“匠人营国(指天子之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注:《周礼·冬官·考工记》。)“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注:李诫:《营造法式总释上》。)由此可见,按旧制,各级领主城邑的宫室尊卑“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注:《汉书·韦贤传》。)。即以九、七、五、三为二的级差递减。但在事实上,春秋时代的城市规模早已“僭礼逾制”了,反映了春秋时代封建领主等级制度已随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动而在发生着变化。黄国是周初分封的子爵,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潢川县发现的春秋时代黄国故城东西约1800米、南北约1600米,大大超过了周礼三里城的规定(注:杨履选:《春秋黄国故城》,《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鲁国是侯爵,本为方五里之城,而春秋鲁故城东西长处约3700米,南北最宽处约2700米,城周长约11770米(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版。)。楚国本属子爵,而春秋时代的郢故都遗址面积有16平方公里之大(注: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春秋秦故城雍东西长3300米,南北3200米(注:《陕西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3期;《秦都雍城钻探和试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滑国故城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000米,中部宽700米,南部宽500米,呈南北长、东西窄的形状,国虽小而城不小(注:《河南偃师“滑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晋国原封于翼地,昭侯封桓叔为曲沃大夫,曲沃大夫势强,后来攻灭翼侯自立为晋君,是为晋武公,立都于今山西翼故县与曲沃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故绛)(注:邹衡:《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年第1期。),不再都翼,史载:“曲沃邑大于翼”(注:《史记·晋世家》。),春秋以后晋都僭礼是不言而喻的。
当时,城市兴起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大批中小城市采邑的修筑,见于史的筑城活动骤增,有的考古家视之为一场“大规模的筑城运动”(注:马世之:《关于春秋战国城市的探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都邑》所统计的各国城市有:周40、齐38、郑31、宋21、卫18、曹9、邾9、莒13、纪4、徐1、晋71、虞2、虢2、秦7、陈4、蔡4、许6、庸3、麋1、吴7、越11,总计达380起,仅见于《春秋三传》记载的就有70起,这还是不完全的记载。以至有的城市史研究专家估计说:“《春秋》、《左传》、《国语》共出现城邑地名1016个,其中有‘国’名为城邑之名者百余,这样推算春秋城市(邑)可达千余之论是有案可稽的。从逻辑上推论,春秋这190余国,绝不止一千个城邑,也就是说190余国的大多数,应该不少于10个城邑,而最多者应达百余以上,这样推论,国外学者认为春秋城邑可达二千之数是可信的。”(注: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这么众多作为区域性政治或经济中心的城市(邑)群的兴起,标志着我国古代真正意义的“城市革命”的到来,即城市由过去城堡、都城的发展阶段而跨入了第三个真正“城市”的历史阶段,“城市”的诞生,不仅意味着旧的依宗法分封而形成的城邑正在开始被新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城邑所取代,而且还意味着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的到来。城市的兴起与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社会繁荣,已使得时人深深地感受到历史前进的步伐在急速地加快,赵奢曾说过:“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注:《战国策·赵策》。)在千丈之城、万家之邑中,工商业人口所占的比重很大。如前文所述《管子》中有“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经济管理思想,特别是他将工商业者一道视作“国之石民”(注:《管子·小匡》。),反映了工商业者地位的上升和对城市的重要性,正是他们支撑起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局面,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郑国巨商弦高、孔门弟子子贡、《管子·轻重甲》中从事园圃农艺而谋生的“北廓之民”等等。
迄于战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局面。
首先,春秋时代兴起的旧城在战国时代得以发展壮大。其中,作为列国诸侯都城的城市成为战国各自城市群经济文化区的核心,以及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新兴国家的政治中心。因此,它们作为各区的中心城市在区域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诚如《盐铁论·通有篇》所载:“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注:战国时代,温地即今河南温县,轵即今济原县,荥阳即今荥阳东北,宛城即今南阳市,陈即今淮阳县,阳翟即今禹县,两周城系指洛阳、巩二城。)上述城市只是当时城市的一部分。关中一带的咸阳、栎阳,此时已发展成富甲天下的名城了;齐鲁大地的陶、即墨、莒以及吴越的吴城、会稽,三楚的寿春、江陵等地皆为一方之会。据估计,战国时代的这类国都城市大都拥有数万户的人口,比如临淄有7万户,薛6万户,咸阳12万户,如果数据确实,且每户以五口计,则临淄人口有35万,薛30万,咸阳60万,在这些众多的城市居民中,亦工亦商亦农的人口构成肯定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反映着城市经济的繁荣。
其次,郡县制的大力推行促使大批中小城市(邑)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早在春秋中晚期,郡县制即已产生。《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左传》哀公十七年亦载:楚文王曾任彭仲爽“实县申、息”。如此看来,秦楚灭国不再封人,而设郡县长官以治的事情,已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迄至战国更是广泛存在,频繁的兼并战争以争城夺县为特征。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城”(注:《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秦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余”(注:《史记·穰侯列传》。);“秦七攻魏:五人囿中,边城尽拔……所之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注:《史记·魏世家》。);赵曾“割济东城邑五十七与齐”(注:《战国策·赵策四》。),这种“三里之城,七里之廓”(注:《墨子·非攻》。)乃到“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注:《战国策·赵策三》。)的景象,决非虚言。再如“燕国攻掠东胡之地千里,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注:《史记·匈奴列传》。)。秦将蒙恬亦出击匈奴,占有九原,设九原郡,辖34县。因此华族与少数民族的接壤之地,兴起了一批郡县城市。同时在各诸侯国交界之地,亦有大批边境新城兴起。周人城浑到楚国新城(指韩楚交界的襄城新城),对其县令说:“郑、魏者,楚之耍国;而秦,楚之强敌也。郑魏之弱,而秦以上谷应之;宜阳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围之。蒲反、平阳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袭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袭之,上梁亦不知也。今边邑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为主郡也,边邑甚利之。”(注:《战国策·楚策一》。)这些边境城市大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又是各国互市贸易的商品集散地,经济职能也是显而易见的。
再者,战国时代城市经济大发展的又一现象,突出地表现在各具区域特色的大小城市群经济文化区的兴起。一定的经济区,一般地是由具有某些相似性的自然地理条件、地域生产力集约化状况、风土人情等经济生活面貌集结而构成的区域单元。这些集结点,是指该经济区内对人口流动和物质财富交换产生巨大调剂功能的城镇,由各个集结城镇共同构成的城市群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而能够将区域内各集结城镇在经济上联系起来的中心城市,是由其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它对该经济区乃至其它经济区都会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和经济辐射力,从而深刻地影响该地区的社会发展面貌。早在春秋时代,已经形成了较为原始的几大经济区(如关中区、三晋区、江南区、齐鲁区等)。在此基础上伴随着领主制经济的衰落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社会区域经济随地域生产力向纵深发展的结果,导致了原先各经济区的分化与组合,许多大的区域通常被许多瑰丽纷呈的小区所代替。李学勤先生依据考古文化将东周时代分为七大文化圈(注: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2页。),即中原文化圈(指黄河中游的周和三晋)、北方文化圈(赵、中山、燕国为代表)、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和秦文化圈,是皆有其物质文明的属性,皆有其社会经济区域性发展背景的,并且还主要是以城市(邑)为纲来划分的。战国时代社会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突出地反映在社会产业分工的发达上。如《周礼·冬官·考工记》云: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踰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燕之角,荆之干,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
又有谓:
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
《史记·货殖列传》亦曰:
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
在社会区域经济日益发展和各地产业日益分化的条件下,城市的作用以及长途贩运商业的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拿关中经济区来说,“关中自湃、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及秦、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注:《史记·货殖列传》。)关中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在发生转移,初由雍转至栎阳,再转至咸阳,其转移的方向是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咸阳是关中平原的心腹之地,交通也很发达,东接三晋、齐鲁,南通巴蜀,也利于商业的发展。及至秦国灭蜀,秦惠王遣司马仪、司马错筑城,“与咸阳同制”。从此,巴蜀经济区便渐渐纳入秦国关中经济区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轨道,巴蜀的丹沙、石、铜、铁、竹、木、锦缎在秦都皆能买到,其风俗习惯也与关中相似了。所以,战国末年至秦初,关中地区便实际上成为全国的核心地带,史载:“(关中)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注:《史记·货殖列传》。)
相对于关中经济区而言,江南经济区是比较分散而且开发较晚的区域。但是自春秋时起,楚、越、吴三国迅速崛起,其国都皆为人文物产荟萃之地。战国时代,楚兼并吴越之地,乃有三楚、四楚之称。西楚之郢都有云梦之饶,北楚之陈有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南楚之长沙(青阳)为“楚之粟也”(注:《史记·越世家》。),是楚国的粮仓。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是江南经济区及其城市群初步发展的奠基时期,“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六朝政治中心的南渐和社会经济区域的大变动,南方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普遍性的城市兴起与城市繁荣的局面”(注:详见拙文《六朝城市经济的特点及其在新经济区发展中的作用》,《学术月刊》1992年第11期。)。因此,我们说没有春秋战国时代江南经济区的奠基发展,就不会有后来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振兴和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局面。
从关中、江南两大经济区发展的状况可以看出,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在战国之世,城市经济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新现象。以城市为中心网络而兴起的经济区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时商品经济已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自然经济的封闭体系,使得本来发展极不平衡的各个区域以商品交换物资交流为纽带联结在一起,中国封建社会的面貌因而焕然一新,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趋势。诸子百家的文献对这一历史形势有着生动的描述,荀子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斵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注:《荀子·王制》。)
社会上各种行业的分工,各地区物产的交流,没有长途贩运商业和城市市场的繁荣,是难以想象的。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城市与乡村的分化,起源颇早,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分化的进程加速了,兴起了真正意义的城市;使中国早期城市发展史进入到第三大历史阶段。就周代而言,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形态,以社会分工的进步与“工商食官”制的瓦解与否为标准,明显地表现为前后两个阶段。西周为其前期阶段,封建领主制盛行,按宗法分封的等级制度原则分配土地和人口,“建邦启土”,立“国”定“制”,各级领主建筑了大批采邑城堡。地位高的宗子领主,即诸侯国君的采邑城堡称都,建都的行为称城。地位低的别子、余子或功臣大夫的采邑城堡曰邑,立邑的行为称筑,即《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所谓:“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故而《诗·大雅》有所谓“宗子维城”的说法。西周时,无论都城还是采邑,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就经济形态而言还只是自然经济形态,没有私人工商业(洛邑等个别城市除外),不构成独立的城市生活方式。但是它们作为有别于乡村的聚落形态的特征已开始出现了。春秋战国时代领主制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进步,社会产业分工有了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乃在城市中大大发展起来,独立的手工业者与独立的商人产生了,出现了城市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这时的城市生活方式已告成立。在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态势,即进入了早期领主制封建社会向后期地主制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
在封建社会前期向后期阶段的过渡过程中,城市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具有腐蚀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积极作用,商人与地主的身份人格的统一,及其与农民阶级对立社会关系的展开,乃是社会过渡时期地主阶级发展壮大以及封建社会形态长期延续的主要根源。 三、市场货币关系的深化及其对乡村土地所有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城乡对立运动的规律,主要表现在城市在政治上对乡村的统治、在经济上对乡村的财富掠夺。在夏、商、西周时代,早期城市还没有独立的经济职能时,城乡的对立运动表现为浑然一体的城乡统一,城堡只是作为政治、军事的据点而存在。及至春秋战国时代,独立的私人工商业兴起了,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官营手工业发展和官营垄断商业作为主导因素而存在着,私人手工业发展的历程是极其艰难的,这与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国情相吻合。“城市手工业在实质上虽然是以交换和创造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所以生产处处从属于作为前提的消费,供给从属于需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6页。)中世纪城市手工业生产的这种本质特征,限制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官营、私营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贵族领主的消费需要,而不着眼于广大的百姓平民,春秋时就有的“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于备用者,其悦在玩好”(注:《管子·五辅》;又见《孟子》。)的说法,便是这一历史状况的真实写照。因此,城市具有很强的消费性和经济基础的脆弱性,根本无法摆脱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用孟子的话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注:《孟子·滕文公上》。),城乡对立关系便简明地体现为领主与农奴的阶级对立关系和赋税贡纳等剥削关系,以及国与野、都与鄙的对立关系。从性质与作用上讲,中国中世城市与欧洲那种完全独立于封建统治秩序之外的自治城市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中国城市与乡村仅是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一元化体系上的两块聚落形态而已。这就是当时城乡对立关系的大体状况。但是,春秋战国城市商品经济发展之后,对西周以来城乡对立关系是不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调整作用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换言之,城市市场货币关系的深化在某种程度上已影响了乡村,影响了土地所有制形态。尽管影响的程度并不及乡村与土地所有制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生产关系就本身来说却是崭新的、史无前例的。
城市经济发展以后,市场货币关系深入农村,大大小小的市场遍及全国城乡各地,出现了“野与市争民”的现象。当时,置市贸易十分发达。史载:“梁之东地,尚方五百余里,而与梁,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大县十七,小县有市者三十有余。”(注:《战国纵横家书》。)“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注:《战国策·齐策五》。)这说明当时城邑中普遍设市,甚至将“市”的有无看成城邑发展的标志。在农村也有置市贸易或者自发的集市,按周制:“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注:《周礼·地官·遗人》。)《孟子》有所谓:“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注:《孟子·公孙丑》。)《墨子》谓:“市去城远。”(注:《墨子·杂守》。)《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因井田以为市,”这一系列现象,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城乡之间商品交流十分频繁,市场成为“四方来集,远乡皆至”(注:《礼记·月令》。)的人员聚集和商品集散之地,市场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乡居民正常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条件,农民需用的生产工具多从市场上购得,城市居民所需的粮食、蔬菜也多从市场上购得。“无市则民乏”(注:《管子·乘马篇》。),如果没有市场那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经济发展之后,人们受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对农业人口的吸收和涵容能力增强,这一过程同样也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苛政暴敛所致,史书上关于统治者暴政而导致民不聊生的记载很多,如:“庶民疲敝,而宫室滋侈”(《左传》昭公三年)。“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左传》昭公八年)。“宋君夺民时以为台”(《战国策·东周策》)。“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下,“其野不足以养其民”(注:《管子·八观》。),流入城市的人口多是有事可做才能站稳脚跟的,其中有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园艺耕作者、佣工、卖艺者等各色人物。
此外,城市经济发展后,金属货币作为商品交换和流通手段与储藏手段的地位得以牢固地确立,拜金主义也已产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注:《管子·国蓄》。)。春秋战国时期的金属货币种类繁多,大小轻重不一,在考古发掘中出土量极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货币经济的繁荣,真正改变了物物交换的历史,对商品经济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故可将春秋战国称作货币经济的确立时期。据解放以来的考古发掘楚墓而得到的货币来看,金币所占的比重很大,有五百多块。金币之外的铁币、铜币、贝币就更加难以胜计了。“解放以来出土的东周钱币,见于正式报道的达七万余枚”(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页。)。货币经济发展之后,有钱人就可以用钱买奴婢、买田宅和从事高利贷业投机活动。齐国是个工商业较为发达的诸侯国,早在春秋初期其高利贷业就很发达,曾一度达到了高利贷为害农民影响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地步。故齐桓公、管仲不得不以行政干预的方式来打击高利贷者,调低利率。史载“(西方)其称贷之家,多者千钟,少者六七百钟。其出之钟(中)也一钟,其受息之萌九百余家。……(南方)其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伍(十)也,其受息之萌八百余家。……(东方)其称贷之家丁、惠、高、国,多者五千钟,少者三十钟,其出之中钟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北方)其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余家。”对此管仲感叹地说:“欲国之无贫,兵之无弱,安可得哉?”(注:《管子·轻重丁》。)
在商品货币关系大大发展的情况下,土地买卖也成为司空见惯的事,“田里不鬻”的硬地产化已成过眼烟云。俞伟超在《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以春秋战国时代的“族坟墓”地所有关系的变化来解释土地私有化历程,观点很是独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春秋战国时代土地作为商品买卖的现象是大有裨益的。他认为:“这种以族为单位的公共墓地,特别是其公墓制度,至少在部分国家中到战国时已发生着变化。……墓地是血亲关系的体现物,只要血缘纽带尚未完全松弛,它就会保存着氏族、公社乃至家族的公有制,从而在土地公有制的破坏过程中,它的自由买卖是会很晚才发生的。但只要耕地的私有制一出现,墓地的自由买卖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并且估计说:“从商代的氏族墓地经周代的‘族坟墓’到汉武帝以后个体家庭或嫡长制家族的私有茔地,说明了墓地制度从公社所有制到私有制的变化。这种变化,比耕地所发生的同样变化大概要晚三四百年,但墓地所有制的这个变化,总是反映了耕地的所有制,也是按照古代社会的基本规律而发生着从公社所有制到个体家庭私有制的变化。”(注: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7页。)我们对俞先生的古史分期派别姑且撇而不去评说,可他对春秋战国时代井田制瓦解后耕地私有化和土地买卖的估计却是可信的。这一结论,可以从秦汉时代刻有“买墓地券”明器上推知,也可以从文献记载中得到证明。西周时的《格伯簋》中已可见土地交易的萌芽,《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有晋国向戎狄购地的事:“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韩非子》、《史记》等文献中都有“卖宅圃”“买田宅”、“卖宅”的记载。《庄子·让王篇》亦记载说:“回(颜渊)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饣+亶]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这种“郭外”、“郭内”同时有田的情况实属罕见,其中可能包括买来的田地,也未可知。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后,商品货币关系对土地所有制的影响。
总而言之,春秋战国时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与乡村经济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并以两个不同的侧面反映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